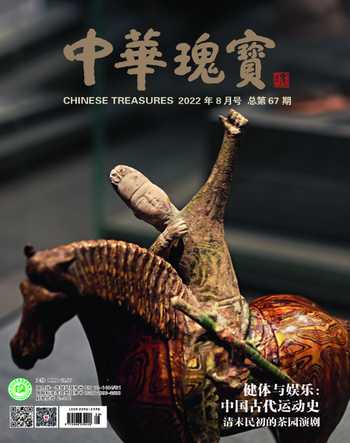鱼龙百戏尽精神
王亚中



中国杂技以鲜明的民族风格和高超的艺术技巧著称于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技巧表演艺术之一。从远古到当代,从民间到宫廷,从中国到世界,中国杂技所承载的不仅是艺术技巧,还有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和生生不息的体育精神。
古人的生活有时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枯燥无味,他们在劳动中创造快乐,在戰斗中培养精神,在祭祀中寻找灵感,在表演中提炼技巧,经过漫长的实践探索和岁月积淀,创造出形式多样的杂技艺术,成为中华文化中独树一帜的艺术奇葩。
百兽率舞
远古时期,杂技处于萌芽状态,存在于各种生活技能与生产活动之中。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人们对生活中各种实践活动场景进行简单模拟,如渔猎、农牧、驯兽、战争、祭祀等,然后加以提炼和美化,创造了最初的表演艺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原始的表演艺术逐步分化成奏乐、歌唱、舞蹈等形式。其中偏重于技艺性的表演,便是萌芽状态的杂技。
传说3000多年前,尧帝有一名乐官名叫“夒”,他能演奏石制的乐器,指挥各种动物跳舞。这件事后来被记录在《尚书》中,即“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这是关于杂技最原始形态较早的文字记录。汉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黄帝战炎帝时曾驱使熊、罴、虎、豹等猛兽冲锋陷阵,最终取得胜利。这与“百兽率舞”十分相似,都是动物被驯化为人所用的场景。也有人认为,黄帝调动的实际上是以这些猛兽为图腾的部落,尧时的“百兽率舞”也不过是人乔装成动物在表演跳舞的节目。
奇伟之戏
夏代,杂技开始逐步成为独立的表演艺术形式,被称为“奇伟之戏”。西汉刘向《列女传·孽嬖传》中记载,夏桀“既弃礼义……收倡优、侏儒、狎徒能为奇伟戏者,聚之于旁,造烂漫之乐”,宋代罗泌《路史》也称“桀广优猱,戏奇伟,作东歌而操北里”。这是最早的有关大型杂技表演的文字记载,可见当时已经出现了专门展示奇异技能的队伍。
“奇伟之戏”已从娱神转向娱人,虽然具体表现形式不得而知,但至少已具备了早期杂技的以展示奇绝技巧为主的表演特征。同时,夏代宫廷中还有“舞九州之马”的演出,或许是从“百兽率舞”演变而来,堪称最早的马戏表演。
“奇伟之戏”在周代与乐舞融合,如武王时期的“成童舞象”,具有了“以巨为美,与众为观”的审美倾向。后来,所有的民间乐舞由“旄人”掌管,被称为“散乐”,其杂技特征愈加明显。在后世,散乐曾一度成为杂技类艺术的代名词。
角抵相争
先秦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各种杂技表演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但并没有统一的名称。秦统一六国后,杂技艺术与其他表演艺术相融合,才有了一个统一的名称“角抵戏”。
关于角抵戏的起源存在两种说法。其一,源自蚩尤部族创造的一种角力的游戏—“蚩尤戏”,参加者头戴牛角饰物,三两排列组合进行较量,这种游戏在古冀州(今山西与陕西间黄河以东,河南与山西间黄河以北,和山东西北,河北东南部)十分流行。其二,认为“角抵戏”源自战国。《古今事物考》中记载:“战国时增讲武为乐,相夸角其材力以抵斗,两两相当。”所以称这种“讲武”活动为“角抵”。
上述两种说法,起源时间有所差别,表现形式却极其相似。实际上,战国时期的“角抵戏”比“蚩尤戏”和“讲武”内容要丰富得多,已然贴近后来的百戏杂技艺术。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收集各国的乐人倡优(包括杂技艺人)近万人充实秦宫,“讲武之礼,罢为角抵”,把原来分散于六国与“讲武”有关的角力、角技、角射御的诸般技艺统一归于“角抵”。这种集中统一为后世百戏杂技的兴盛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百戏纷呈
汉代百戏异彩纷呈,汉武帝对杂技乐舞“复采用之”,加强对正规乐舞的管理,促进了民间杂技的普及与发展,从而出现了百戏盛行的局面。这在出土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和陶俑中有大量体现。如:河南新野樊集画像砖上的“戏车走索”便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杂技,表演者在行走的戏车和晃动的绳索上作高难度的动作,非常惊险;一块东汉的画像砖上,跳丸、盘鼓、叠案三项表演同时展开,生动传神。还有汉代彩绘陶樽上倒立杂技俑、乐舞百戏俑群、彩绘乐舞杂技俑等都是当时杂技表演的真实写照,形象地再现了汉代杂技乐舞表演的概况。
随着汉代民间宴乐杂技的兴起,杂技乐舞向多样化和小型化方向发展,与宫廷“大角抵”等大型表演相互补充、交相辉映,使汉代百戏杂技更加丰富绚丽,出现了宫廷民间两开花的局面,“百戏”逐渐取代“角抵”的称谓,成为散乐杂技的总称。这种局面一直延续至盛唐,宫廷百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宫廷极盛
杂技艺术在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唐代获得空前发展。唐初,杂技仍沿袭秦汉称谓,称角抵、鱼龙漫衍、百戏及散乐,由太常寺管理。
唐代百戏的兴盛得益于唐玄宗的改革推动。唐玄宗偏爱百戏杂技,在还未登基时就在府中蓄养了许多百戏散乐艺人。在登基第二年,他就重建教坊,将其改为独立机构,专门管理雅乐以外的乐舞百戏,组织排练和演出,对杂技艺人的管理更为专业化。
教坊内部分工非常细致,具体管理散乐的部门称“鼓架部”,表演项目包含“代面、钵头、踏摇娘、羊头浑脱、九头狮子、买白马益钱、跳丸、吞刀、吐火、旋盘、筋斗”等诸多杂技项目,可见在当时杂技表演形式已经相当丰富,其中舞狮、吞刀、吐火、旋盘、筋斗等表演形式在现代杂技中依然常见。
唐玄宗从教坊中挑选出一批优秀艺人,集中在梨园,亲自教习其音乐,“梨园子弟”的称谓即源于此,后世杂技艺人亦多有人将唐玄宗尊为“祖师爷”。唐玄宗掌握了一支技艺非凡的艺术队伍,既满足了宫廷娱乐需求,又可对外国来使彰显中华大国的文明气度。在他的推动下,宫廷百戏技艺不断提高,规模与水平都超越前期。由此,宫廷百戏达到了极盛。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民族大融合进一步促进了杂技的多样化,“胡技”“胡舞”与中原百戏融合,产生了新的表演形式,使表演形式更加丰富,也更富于艺术性。如唐代彩绘陶黑人百戏俑表现的就是胡人进行杂技表演的场景,这些场景在陶俑、壁画、绘画中多有呈现。
复归民间
民间百戏兴盛是宋代杂技的最大特点。与唐代不同,宋代对杂技艺人没有严格的限制,从村落瓦舍到都会杂技,从民间社火到瓦舍伎艺,民間技艺类型丰富、精彩纷呈,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
北宋画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便有街头艺人表演杂技的场景。清明,对于宋代的百戏艺人来说是一个盛大的节日,不仅有街头杂技表演,还会举行水上百戏、诸军百戏表演。
《东京梦华录》记录了宋徽宗在临水殿观看水上百戏的情景:水中横列四艘彩舟,“上有诸军百戏,如大旗、狮豹、棹刀、蛮牌、神鬼、杂剧之类”,乐部在另外两条小船上。乐声响起,有木偶人划船、垂钓,来去自如的“水傀儡”表演;也有艺人在船上爬杆、空中荡秋千,然后凌空转体入水的“水秋千”。水傀儡有些玄幻色彩,而水秋千则与今天的跳水有几分相似。
水上百戏演毕,众船奏乐摇旗相继退去,大龙船、小龙船、鳅鱼船、虎头船陆续上场,开始热烈欢腾的舟技夺标表演。宋徽宗在这里看完水上百戏,还要移驾顺天门外的宝津楼观看诸军百戏。诸军百戏不仅有舞旗、狮豹、上竿、打筋斗等传统杂技项目,还有军队列阵、对舞、击刺、爆竹、报锣、舞判官、马戏、打彩球等特别表演,其中舞判官表演至今依然流行于民间。这些表演已经与今天的杂技项目十分相近,完全具备了杂技的艺术特征。
宋徽宗观看着民间百戏,幻想着国泰民安的盛世,可最终还是梦华一场,唯有百戏在他身后一直流传至今。
庙堂余韵
宋代后期至元代,原本活跃的杂技遭遇了禁锢和压抑,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杂把戏”。随着戏曲的诞生与发展,杂技失去了娱乐主导地位。明代循宋制,保留了教坊,虽然杂技成分减少,但仍保留一些宫廷百戏的余韵。
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元宵节,明宪宗在皇宫观看了一场宫廷百戏杂技演出。他身穿浅黄色龙袍坐在彩色御帐中,出神地看着阶下的百戏表演,这一场景被宫廷画师记录在《明宪宗行乐图》中。罗圈献彩、蹬人、蹬高竿、钻圈、蹬车轮等表演项目,和着乐声,或轻盈爽快,或惊险刺激,令人目不暇接。不过因为都是轻巧的技巧型小节目,已无唐代宫廷百戏的恢宏气势。这场表演如同夕阳的一抹余晖,记录着宫廷百戏的最后余韵。
清代的帝王把看“百戏”改为看“冰嬉”,每年在太液池举行冰嬉大典,延续了近百年。冰嬉大典主要由八旗子弟参与,旨在检阅士兵技能,提升军队素质。冰嬉所有比赛项目更倾向于竞技性,也保留了弄幡、爬竿、翻杠子、飞叉、耍刀等具有表演性质的冰上杂技项目。
清后期,大量的杂技艺人以跑马卖解、堂会、走会为主要表现形式,更加贴近民间风俗。杂技一部分技艺被戏曲演员吸收,应用在戏曲舞台上,也有一部分凭借顽强的生命力被传承下来。一直到民国时期,杂技依然是散落民间的江湖艺术,不复昔日辉煌。
新中国成立后,杂技迎来了新的生机。1950年,新中国成立了第一个杂技团“中华杂技团”,1953年更名为中国杂技团,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指导下,由中央政府组建的唯一的国家级杂技艺术表演院团。从此,中国杂技有了新称谓,也有了新使命,在国际杂技比赛上屡获大奖,绽放出绚丽夺目、生生不息的艺术之花。
——兼论敦煌壁画、文献中的相扑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