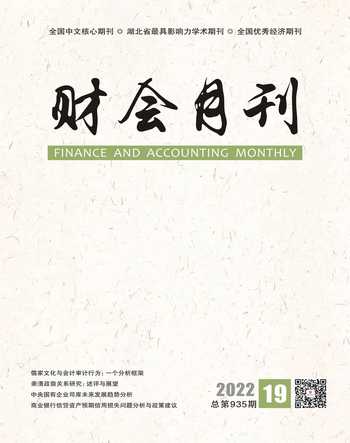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研究:内涵、动因与模式
苏明明 叶云
【摘要】在大智移云时代, 平台经济模式兴起, 平台企业成为21世纪的新兴产业, 但是随着平台企业的蓬勃发展, 社会责任异化行为不断涌现, 目前多位学者对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展开了研究, 多聚焦于对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动因、边界以及机制等话题, 但相关话题内容比较分散。 因此, 本文从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内涵、动因与治理模式三个方面对国内外关于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研究进行综述。 研究表明: 以平台企业社会责任内容边界的三个层次为依据, 可将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内涵划分为独立运营平台、商业运作平台以及社会资源配置平台的社会责任治理; 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驱动因素主要由法律、行业、企业与消费者四个层面的因素组成; 基于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治理主体,可将其治理模式分为个体自治、政府治理、多中心网络化治理以及生态化治理。
【关键词】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动因;治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F275;F83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22)19-0135-9
一、引言
在互联网新经济时代, 以互联网信息服务、技术服务与电子商务为基础的网络消费领域已经进入社会市场, 并逐渐发展成熟。 同时,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以及5G技术的市场规模逐渐扩大。 这些高新技术服务体系的构建推动着平台经济的飞速发展, 平台企业所需承担的社会责任必然随之加重。 在平台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 其不断面临着新问题、新挑战, 社会责任缺失、伪社会责任以及寻租等异化行为层出不穷, 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平台经济中的垄断现象, 平台企业借助大数据优势进行“大数据杀熟”, 损害社会福利、阻碍行业创新发展、侵害消费者正当利益。
我国在规范平台经营者行为、保护数据安全以及规避垄断行为等方面采取了较多措施, 如制定《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 中国互联网协会也出台了《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 但不管是法律层面的规制还是行业协会的约束, 都无法全面结合平台企业的特征和发展特点实现有效的治理。 因此, 本文基于文献分析法, 归纳、梳理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内涵、驱动因素, 整理我国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治理模式与机制, 以期使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研究更加系统化, 为后期学者对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实证研究奠定基础。
二、平台企业内涵
(一)平台企业定义
平台是一个虚拟的空间, 两个或者更多的客户通过这个空间达成交易[1] 。 根据《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法指南》的界定, 平台是指通过网络信息技术, 使相互依赖的双边或者多边主体在特定载体提供的规则下交互, 以此共同创造价值的商业组织形态。 Roche等[2] 认为, 在双边市场中, 平台企业是为买方和卖方提供交易平台与服务的企业, 当买卖双方达成交易时获得利益。 胡国栋、王琪[3] 从功能视角出发, 认为平台企业是通过借助互联网技术, 旨在为用户服务的一种高效率、低成本的资源整合体。 Cennamo和Stantalo[4] 认为, 平台企业就是平台的提供者与运营者, 为了维持平台商业生态圈的合理有序交易, 其会制定相应的规则。 肖红军、李平[5] 认为, 平台企业是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 为有偿提供商品和服务建立多边交易平台的新兴组织。
(二)平台企业特征
1. 虚拟性。 平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主要依赖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 这些技术的最大特征就是具有虚拟性, 即能够打破时间、空间上的限制, 在所构建的虚拟网络中实现交易与服务自由。 但是在这种虚拟的网络空间中, 双方用户之间进行交易会加重信息的不对称性, 从而出现逆向选择问题, 导致平台企业以及双边用户有机会实施社会责任缺失与伪社会责任行为[6] 。
2. 双边性。 与传统的交易市场相比, 平台具有双边性, 为双边用户提供交易市场。 Armstrong[7] 认为, 一个用户从该平台上得到的好处是由另一方用户的加入决定的。 参与平台交易的双方, 其目的是满足各自互补的需求, 只有双边用户同时参与平台进行交易, 平台才能实现其自身价值并获得盈利。
3. 交叉网络外部性。 Katz和Shapiro[8] 认为, 网络外部性是指当顾客在使用相同的商品或服务, 且使用的顾客数量发生变化时, 这种产品或服务会给顾客效用带来变化。 交叉网络外部性是平台企业的特征之一[7] , 即買方在平台获得的效用取决于卖方加入该平台的数量, 在正外部性的作用下, 形成网络规模。 但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等异化行为的发生在交叉网络效应的作用下会呈现出负外部性, 使得社会责任缺失现象在社会中大量普及, 对社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5] 。
三、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内涵
(一)平台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与维度
目前, 有关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还未形成统一的规范。 黄慧丹、易开刚[9] 基于互联网平台企业, 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 对平台提供商、用户、平台企业内部员工以及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专家进行深入调研, 将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界定为: 在“企业功能”和“准公共权利”的双重责任逻辑下, 平台企业基于其独立运营主体和商业运营主体的双重角色, 对社会和双边用户承担不同层次的责任。 结合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规律以及平台企业特征, 肖红军、李平[5] 将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边界划分为三个层次, 即作为独立运营平台的社会责任、作为商业运作平台的社会责任和作为社会资源配置平台的社会责任。
1. 作为独立运营平台的社会责任。 平台企业作为独立运营的个体企业, 以经济社会学理论为基础, 兼有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 是一种既有经济作用又有社会作用的社会经济组织[10] 。 对于个体企业而言, “企业功能”是最底层的逻辑, 企业存在的根本在于企业为社会提供商品与服务, 但企业还可以通过提供商品与服务, 对交易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进行管理, 引导创造社会价值。 李伟阳、肖红军[11]结合企业本质观, 从个体企业的功能视角出发, 将独立运营的平台企业的功能分为核心社会功能与衍生社会功能。 核心社会功能是指平台企业要为社会创造价值, 提供用户满意的商品与服务, 不跨越法律红线, 不违背道德底线; 衍生社会功能是指平台企业要以利益相关方为主要载体, 满足利益相关方的合理期望与价值诉求, 承担相应的法律与道德义务[5]。
2. 作为商业运作平台的社会责任。 平台生态系统是在互联网技术条件的支持下, 由平台和平台建立者与其互补者之间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12] 。 Cennamo和Stantalo[4] 将平台生态系统视为“多边市场”。 Wareham等[13] 认为, 该“多边市场”在平台建立者的指导下, 促进不同用户主体达成交易。 平台企业以生态系统的形式嵌入社会商业圈系统, 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作为个体企业对自身的行为负责, 更要对商业生态圈的组织成员进行约束与规制。 平台企业既是平台运营者又是平台管理者, 在整个商业生态系统中处于核心位置, 其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影响力, 在遵守基本法律法规的同时规范自身行为, 将规范自身与对外监督并轨运行。
3. 作为社会资源配置平台的社会责任。 平台企业并不只是作为独立运营的个体企业和商业运作平台, 还需要承担“社会公民”的角色。 其不仅要对自身的行为承担责任, 还要对其所处的生态系统进行管理与治理, 合理有效配置市场资源。 所以, 平台企业以高层次的社会功能为目标, 形成打破独立自履、协作自履与价值链共履的社会资源配置平台履责范式[14] 。
(二)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定义与维度
在平台经济背景下, 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责任实践行为, 在双边市场的前提下, 基于公共选择权力并以商业生态圈的方式嵌入社会, 对平台生态系统内部成员的履责行为给予规范以及对异化行为给予治理[5] 。 在平台企业的社会责任治理范式下, 治理主体实现由单一性向多元化的转变, 不再由传统企业单边管理或政府单边推进, 而是由平台企业、政府、利益相关者以及社会公民与组织协同治理[15] 。 在治理客体方面, 遵循匹配原则, 也实现了由单一性向融合式多元化的转变, 由过去只治理大型国有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 演变为对平台企业、平台企业与买方、平台企业与卖方、平台内买方与卖方等多元利益相关者的治理。 在治理角色定位与治理目标方面, 平台企业的社会责任治理旨在打造一个社会责任价值共享生态圈, 通过平台将不同价值偏好与价值诉求的各个主体集聚在一起, 建立以合作、共享与信任为基础的治理机制, 最大化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相融合的综合价值[5] 。 基于平台企业社会责任内容边界的三个层次, 可以将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划分为作为独立运营平台的社会责任治理、作为商业运作平台的社会责任治理和作为社会资源配置平台的社会责任治理三个维度[5] 。
1. 作为独立运营平台的社会责任治理。 平台企业作为独立运营的个体企业, 其社会责任治理的实施主体为企业自身, 企业需要依据自身的道德意识以及自我觉悟的内在驱动来规范自身行为, 属于自发式的治理范式。 但这种理想化的治理范式在现实中难以实现, 企业作为一个“经济人”, 追求利润最大化, 平台之间会展开激烈竞争, 从而忽视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当性, 漠视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 导致社会责任缺失行为的发生。 同时, 当买家的个性化需求逐渐转变为大众化需求后, 平台为满足市场需求会降低门槛, 引进素质参差不齐的卖家, 受机会主义的驱使, 容易产生社会责任寻租行为[16] 。 而在网络效应的作用下, 这种行为的负外部性的作用凸显出来。 因此, 平台企业仅作为独立运营的个体企业发挥自身履责的作用, 效果并不是很显著, 其治理范式难以奏效。
2. 作为商业运作平台的社会责任治理。 平台企业与各利益相关方参与平台的运营过程, 各参与方基于价值共创的需求共同打造一个商业生态圈。 作为商业运作平台, 其治理对象主要为买卖双边用户[5] 。 平台企业是商业生态圈的核心企业, 主要依靠其自身的影响力承担社会责任治理之责[17] , 充分发挥自身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并使其在生態系统中发挥作用, 避免机会主义行为因网络效应而造成平台声誉下降、价值毁损[18] 。 对于卖方用户的治理, 平台企业通过制定交易互动规则, 要求卖方用户坚持底线要求, 满足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提供安全有保障的产品, 同时激励卖方用户能够满足各利益相关方底线要求之上的价值诉求和合理期望, 贡献卖方用户现存以及潜在的优势条件, 与卖方进行合作, 共同为社会创造价值, 增加社会福利。 对于买方用户的治理, 平台企业通过制定用户使用规则, 要求买方用户坚持底线要求, 遵守道德底线, 规范自身的购买与消费行为, 遵守卖方的交易规则, 同时激励买方用户绿色消费, 对社会以及卖方负责, 满足其合理期望, 鼓励买方用户参与到治理过程中, 发挥自己的优势长处, 贡献自己的知识技能。 总之, 充分发挥生态圈中每一位组织成员的功能, 协调资源, 发挥资源最大优势, 对整个商业生态圈内的社会责任行为进行规范, 从而保障平台企业所处的商业生态圈可持续发展。
3. 作为社会资源配置平台的社会责任治理。 平台企业作为平台运营商, 其社会责任的承担主体不只是企业本身, 也不仅仅局限于对商业生态圈的社会责任治理, 而应发挥企业的社会功能价值, 定位于对平台内部以及整个社会的责任治理作用[5] , 将社会资源重新整合、有效分配。 平台基于其自身的特征, 可以将各利益相关方主体聚集在一起, 发挥平台内不同主体所具有的资源优势, 构建社会型平台, 整合社会资源, 解决社会问题。 因此, 作为社会资源配置平台所需承担的社会责任, 仅依靠个体自治难以实现, 无法发挥平台企业对社会的资源配置作用, 需要借助外部力量, 以个体自治为基础, 在政府的监管以及行业规制下, 发挥平台企业的“类政府”角色, 并引导社会公众参与到治理活动过程中, 形成多元主体融合的多元治理模式。
四、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驱动因素
(一)法律层面因素
1. 基础性法律建设不全。 目前关于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相关法律政策与平台企业的发展存在脱节, 平台企业在互联网的背景下高速发展, 但相关政策的制定并不完善。 2019年开始实施的《电子商务法》 对平台企业的管制不能全部覆盖, 存在治理空白, 致使平台企业以及平台内部成员利用政策漏洞, 实施社会责任异化行为。 这种行为在网络效应下, 传播性更广, 造成逆向选择问题, 进而使得社会责任缺失、寻租等现象层出不穷。 《网络安全法》是当前我国以平台企业为主体的法律法规, 但该法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规范也只是停留在原则性层面, 缺乏对平台企业的针对性、明确化规定。 此外, 我国经济持续增长, 世界经济形势也随之发生变化, 过去的《反垄断法》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制度规定偏于原则性、惩罚力度较小以及执法体制不健全的缺陷, 因此这一法律法规的制定要与时俱进, 以满足目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反垄断法(2022修正)》中虽然讨论了互联网领域涉及的数据、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特殊问题, 提出要加大处罚力度, 健全执法体制, 但对不同类型的平台规制不明确, 未解决制度原则性的问题。 因此在政策制定中, 要将法律法规的制定充分明确化, 落实法律责任, 加大惩罚力度, 以体现法律的强制性保障作用。
2. 监管手段与方法单一。 平台企业是一种新兴企业, 所构建的商业生态系统不断发展壮大, 经济规模不断扩张, 在整个社会市场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平台企业具有技术以及信息优势, 集大数据与算法等技术于一体, 因此在发展过程中所实施的社会责任异化行为具有隐蔽性, 难以对其进行直接监管与治理。 在平台企业所搭建的商业生态圈中, 可以跨界、跨地域交易, 因此传统的以地理单位和业务类型为特点的监管方式已不再适用于对平台企业的监管。 由于对平台企业的监管力量有限、监管手段滞后, 导致难以甄别其行为是否违反法律法规。 应实施多元化的监管手段与方法, 坚持分类监管和精准监管的理念, 结合平台企业的特征, 把握平台企业的发展规律, 采用多样化手段和工具进行综合监管[19] 。
(二)行业层面因素
1. 行业监管规则不足。 互联网行业的与时俱进与高速发展, 使得平台经济成为新的规制领域。 《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是中国互联网协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旨在建立自律机制, 规范从业人员的行为。 但该条公约于2002年制定, 对平台企业的规范尚不完全, 对平台企业经营者的监督力度较弱, 同时缺乏相应的惩罚措施。 为规范平台经营者的异化行为以及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中国互联网协会相继制定行业规约、标准、倡议等自律性文件, 但实施效果并不显著, 没有建立长效机制, 主要原因在于自律性公约的制定和执行并不规范、严谨, 具有严重的阶段性特点以及政府强制性色彩, 起到的更多的是事后防范作用。
2. 缺乏专业型监管人员。 当前我国监管部门采取的是包容、审慎的数字经济监管理念, 但现阶段, 平台企业的监管规则不完善、行业自律组织缺乏专业型人才, 从而导致了企业的包容发展与审慎监管脱节的现象。 目前在平台领域中监管套利与监管真空等问题较为明显, 有些监管部门对部分平台企业实施垄断行为、不正当竞争以及社会责任异化行为采取“包容审慎而不监管”的方式[19] , 这会严重削弱监管机构的权威性, 同时为平台企业的违规行为提供便利条件。 对平台企业的监管离不开具备高度专业性以及综合处理能力的专业型人才, 而我国目前缺乏相应的专业人才, 监督、奖励与惩罚机制模糊不清, 难以执行监管, 这会导致监管力量严重不足。
(三)企业层面因素
企业层面的因素主要表现为平台企业自我规制机制不健全。 尽管京东、淘宝与拼多多等平台分别出台了《京东全渠道开放平台业务管理总则》《淘宝平台规则总则》与《拼多多用户服务协议》相关规则, 但在实践中, 平台的自我规制如同束之高阁, 存在严重的失职越位现象。 在现实中, 平台企业为获得垄断地位, 会采取巨额补贴甚至亏损的方式, 进行捆绑销售以及歧视定价, 提高进入壁垒, 削弱中小企业的竞争力。 Armstrong[7] 指出: 如果平台企业对买卖双方同时提供具有差异化的产品或服务, 那么双边用户更倾向于选择单一平台, 即用户是单归属的; 而当平台仅对一方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表现为差异化时, 那么另一方会选择多个平台进行交易, 即用户是多归属的。 在买方用户多归属的前提下, 由于大型平台企业具有用户规模优势, 初创期的平台企业进入壁垒高, 难以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生存, 因此會采取寻租行为[20] , 与大型平台企业签订结盟条约, 造成市场配置效率低下, 不利于市场正常运行。 平台企业不同于传统企业, 具有准公共的权力, 扮演着公共监督者的角色, 对平台企业双边用户行为的监管, 需要借助平台企业私人定制的规则。 但对于具有外部性的交易, 平台企业缺乏监管的积极性, 漠视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现象的发生, 而且平台企业不同于国家机关, 不能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监督权力有限, 这也为社会责任治理带来了困境。
(四)消费者层面因素
消费者层面的因素主要表现为消费者正当权益受到损害。 平台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首要条件是形成用户规模, 其核心就是定价问题。 平台企业的定价模式是在价格总水平的前提下, 将总价在买卖双方之间进行合理分配, 从而促进双边用户对平台企业服务产生需求并达成交易[18] , 平台企业因此获利。 价格制定的绝对优势主要依靠信息量, 平台企业作为双边信息的承载者以及协调者, 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来获取利益。 由于平台企业的双边性, 平台卖方为获得买方用户会虚假宣传, 联合部分“消费者”披露不真实、不准确的信息, 甚至以威逼利诱的方式阻碍消费者维护正当权益, 踩着法律的边缘线, 欺骗其他买方达成交易。 平台企业要想在双边市场中形成用户规模、实现稳定发展, 不仅需要获得用户数量, 而且需要增强用户粘性, 其采取的主要方式是提供价格补贴。 平台所具有的交叉网络外部性是其进行交叉补贴的主要原因, 它可以将利润让给某个市场, 从而将该市场的用户拉入该平台, 在网络的外部性作用下, 获取另一方的用户[7] 。 当大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之后, 平台企业利用自身优势, 实施“大数据杀熟”行为。 在数字化市场中, 平台企业进行数据垄断, 利用技术锁定, 逐渐形成寡头垄断格局。 大型平台企业的封禁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 消费者被迫进行平台“二选一”的决定。 上述社会责任缺失行为对消费者正当权益造成严重的损害, 降低社会福利, 因此对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治理亟需深化。
五、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模式
(一)个体自治
1. 个体自治模式。 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个体自治模式不是仅局限于企业自身构建内部治理机制, 而是利用平台特性, 将各利益相关组织聚集在同一平台, 形成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多元自主领域。 在个体自治模式下, 平台企业既是治理主体又是治理客体, 发挥自治作用的关键是激发企业自身的道德觉悟, 属于自发式的治理范式。 平台企业不同于传统企业, 其所具有的双边特性也异于传统市场的单边性, 因此其个体自治模式也从单向供应链治理转向多中心网络化治理[21] 。 不同时期的平台企业所处的网络节点具有差异, 因此对于不同时期的平台企业, 其所需承担的治理之责也不完全趋同。
处于初创期的新兴平台企业具有较高的竞争壁垒, 缺乏网络用户资源, 难以充分发挥其自身的治理优势, 因此这一时期平台企业的个体自治模式, 侧重点主要在于发挥其学习机制与激励机制, 加强平台企业内部的履责管理与实践, 夯实社会责任治理方面所需的知识资源, 形成社会责任知识溢出效应, 建立双边用户的参与、交易与权益维护等相关的规则秩序。 处于成长期的平台企业与用户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密, 这一时期平台企业的个体自治应结合平台企业的特征, 将不同用户聚集到同一平台中, 促进平台内用户之间履责信息的传播, 更好地开展共建共享的履责活动[15] , 建立协调机制, 为履责过程中的个体自治搭建桥梁。 处于成熟期的平台企业具有一定的垄断地位, 拥有庞大的用户规模, 用户粘性较强, 发展趋于稳定, 所以这一时期平台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更重, 对其责任治理的方式也不仅仅局限于对履责知识的学习以及内生化规则秩序的建立, 而是要组织平台企业内价值偏好统一的用户构建协同、统一的履责规范, 并将其应用到实践中, 从而充分发挥平台企业在社会责任个体自治中的渗透效应与扩散效应[15] 。
2. 个体自治机制。
(1)考核认证机制。 平台企业具有庞大的数据资源, 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来考核认证平台内双边用户的声誉, 避免用户的机会主义行为影响平台的价值声誉。 政府通过自身的影响力, 以企业设租的形式进行社会责任排名, 从而产生社会责任寻租行为[22] 。 但平台企业由于自身的“类政府”角色, 具有公共权力, 在大数据的支撑下, 平台企业对双边用户的治理更加高效。
(2)声誉激励机制。 平台企业的声誉激励以卖方为主要对象, 其治理核心是解决社会责任缺失与寻租问题[21] 。 在平台企业的网络效应下, 卖方用户的整体声誉提高会带来价格溢价, 产生声誉激励效应, 从而吸引更多买方用户达成交易。 平台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对双边用户进行治理, 对接受卖方寻租行为的买方进行惩戒, 不断对卖方实施声誉激励, 卖方在声誉激励机制下, 会不断提高产品与服务的质量, 从而降低卖方用户实施社会责任寻租行为的可能性。
(3)审核与监管机制。 平台企业既是平台的搭建者又是平台的运营者, 其自身可以建立准入门槛机制与监督惩戒机制, 对平台内部各独立主体的社会责任异化行为进行有效治理[21] 。 一方面, 可以预防和规避潜在社会责任缺失的经营者进入平台; 另一方面, 可以通过标准化的规则对平台双边用户的不合规行为进行惩治, 以防社会责任缺失等异化行为在网络效应之下, 对社会造成更加深远的影响。 所以, 在平台治理中应充分发挥其自治功能, 并在尊重平台企业独立主体的基础上, 制定相应的治理规则, 将平台内经营者的行为透明化, 推动平台企业良性可持续发展。
(二)政府治理
1. 政府治理模式。 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政府治理模式主要是以政府为主体, 基于政府这一公共领域, 创造社会价值, 增加社会福利。 平台的监管与治理要运用法治思维, 采取法律手段, 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 法无授权不可为”[19] , 增强政府监管与治理的权威性, 发挥法律的强制性作用, 制定健全的惩罚机制并严格落实[23] 。 无论是传统企业还是平台企业, 市场中都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 从“经济人”角度出发, 企业的目标是成本最小化, 这一目标容易导致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一致, 从而造成市场失灵[24] 。 为了纠正市场失灵现象以及存在的社会责任缺失与寻租行为, 就需要政府的监管。 政府在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过程中发挥着社会责任制度供给的作用, 扮演着公众利益监督者的角色[15] 。
由于平台企业所具有的特征不同于传统企业, 平台企业之间各主体的关系也有显著区别, 因此不同平台企业所产生的社会责任异化行为与社会责任管理实践活动具有一定的差异性[15] , 进而对经济社会环境中的利益相关方产生不同的影响。 所以, 对于不同类别属性以及处于不同成长时期的平台企业, 要建立差异化的监督管理制度, 出具社会责任负面清单, 加快平台企业法律规范体系的建立, 弱化政策的滞后性, 对其权利义务做出精准定位, 实现法律制度的规范惩治作用[15] , 做到精准监管。 政府在监管的过程中要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标, 对平台内各独立主体秉持公平公正的态度, 维护社会公平[22] 。 我国政府应结合平台企业所具有的开放性、交叉网络外部性以及虚拟性等特征, 顺应平台企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发展潮流, 结合平台企业的案例, 制定系统化、精准化的法律政策, 不断完善平台企业的治理体系。
2. 政府治理机制。
(1)评估机制。 对于平台企业社会责任异化行为, 政府要充分发挥制度供给的作用, 加强外部制度约束, 同社会研究机构一起出台相应的评价标准, 与国际的社会责任评价标准趋同, 增强企业与利益相关方的认可度[25] 。 同时, 出台相应的激励性产业政策, 对社会责任管理与实践行为表现优异的平台企业给予财政补贴。
(2)监督机制。 要想实现平台企业社会价值创造, 不仅需要政府发挥制度供给的作用, 还要加强监督, 通过颁布企业社会责任制度与规则, 运用科层式命令协调企业与社会资源[25] , 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 针对平台企业最为突出的垄断问题, 政府要充分发挥监督作用, 建立数据管理制度, 打造公平合理的競争型市场[26] 。 此外, 政府通过引导平台企业内部成员之间、平台企业之间互相监督, 为平台企业主体之间的社会责任良性互动提供便利条件, 通过制度设计监督来评估平台的自治行为[27] 。
(3)声誉机制。 政府以法律为准绳, 依据相应的制度规定, 根据多方认可的评估标准, 对出现社会责任异化行为的平台企业出具负面清单, 协同利益相关方监督, 与大众媒体展开合作, 呼吁大众媒体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加大宣传, 将出现社会责任异化行为的平台企业进行媒体曝光谴责, 利用声誉激励效应对平台企业施压, 使其自觉履行社会责任。
(三)多中心网络化治理
1. 多中心网络化治理模式。 平台企业的治理模式已经从传统的单向供应链治理模式转为多中心网络化治理模式[21] 。 单纯的企业个体自治模式与政府治理模式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例如: 很多平台企业缺乏履责主动性, 难以融入企业所构建的社会责任运营管理过程中; 政府干预无法杜绝平台企业的社会责任缺失、伪社会责任以及寻租等行为的发生。 该模式是基于平台与各利益相关方主体之间的一种网络结构, 融合了企业个体自治与政府治理两种治理模式, 将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共享公共权力的良性互动搭建成社会责任治理网络[15] 。
在这种模式中, 治理主体不再单一化, 而是将企业个体、政府、社会公众以及舆论媒体等多个治理主体聚集在同一平台, 不同主体基于共同治理价值观, 资源共享, 协调合作, 来解决履责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在平台所搭建的商业生态圈中, 各个主体之间的关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共同构成一个没有绝对统治力的社会责任“超系统”[28] 。 虽然系统内部组织成员、政府、平台企业以及相关社会组织等主体间治理能力的侧重不同, 但彼此之间交流互动、协同共治, 形成外部监管、内部自律以及第三方监督的网络结构。
政府作为企业社会责任外部治理的主体力量, 要为平台企业的长效治理做好制度铺垫, 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平台企业具有双重角色, 既是治理主体又是治理客体, 在做好企业内部社会责任管理制度的个体自治过程中, 要积极配合政府的相关政策, 充分发挥企业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 保障企业的良性发展。 平台企业用户等第三方治理主体之间要建立信任机制, 发挥各自的功能作用, 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建立有效互惠与监督选择的沟通关系[15] , 优势互补, 使杠杆效应最大化。 媒体中介在社会责任治理过程中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利用新闻媒体等多个渠道对企业社会责任缺失、伪社会责任行为以及社会责任寻租现象进行披露, 通过社会舆论与道德谴责的方式引导平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强化社会责任治理, 完善社会责任评价机制。
基于多中心网络化治理模式, 平台企业的自治是基础, 是平台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的前提; 政府在治理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 这是由政府的强制性色彩决定的, 任何企业的发展都需要政府这一公权力的参与; 同时, 政策的执行与协会的规制也需要高质量的社会公众充分发挥其治理作用。 因此, 平台企业需要搭建多中心的网络, 建立价值共享的信任机制, 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 形成彼此之间信息互通的多中心网络化治理。
2. 多中心网络化治理机制。
(1)个体社会责任治理机制: 内部治理体系。 平台企业个体自治的前提条件是认识并发挥平台所具有的双重属性, 在平台领域中, 平台不仅仅扮演着“经济人”的角色, 更扮演着推动平台内部组织成员创造社会价值的“社会人”角色[20] 。 从制度逻辑的角度来看, 平台企业的个体社会责任治理机制主要是基于市场和社会的双重逻辑而产生的一种内部治理体系。 需要增强平台企业以及平台内组织成员的社会责任意识, 嵌入社会责任制度, 增加相关议题的讨论, 防止平台企业在运营过程中与社会脱节, 形成双重制度逻辑下的共益型企业, 进而创造平台企业的综合价值与共享价值[18] 。
(2)政府元治理下的社会责任治理机制: 制度规制推进机制、监督与评价机制、激励机制[18] 。 政府作为制度供给者, 通过建立制度规制推进机制, 运用科层式命令来对平台企业实现价值创造过程中的负外部性进行治理, 为平台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提供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 通过建立相应的监督与评价机制, 明确不同类型的平台企业的“底线责任”, 在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建立不同行业的平台企业奖惩标准, 充分保障平台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符合“三重底线”。 在治理过程中, 除了运用刚性的制度来进行规制以及相应的惩戒进行约束, 还应建立激励机制, 激发平台企业个体自身的社会责任意识, 推动平台企业主动参与到公共性和社会性议题中, 实现高层次的价值创造[5] 。
(3)公民社会组织的社会责任治理机制: 舆论引导与标准推进机制、社会监督与评价机制[17] 。 公民社会组织治理平台企业个体的实现机制主要是: 通过引导平台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符合社会大众期望与公众需求, 使各利益相关方参与到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过程中, 加强对其外部监督以及惩戒[29] 。 治理机制的实现方式为: 一是, 严格响应政府的号召, 遵守相应的社会责任指南; 二是, 推动平台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满足社会期望, 促使社会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中来。 充分利用舆论引导以及相应的标准评价体系, 规范平台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向高层次的平台化履责范式转换。
(四)生态化治理
1. 生态化治理模式。 直接将传统的社会责任治理模式移植到平台商业生态圈中, 与平台企业的平台情景模式不相适应, 不能最有效地对平台企业的社会责任异化行为进行治理。 因此, 肖红军、李平[5] 在突破传统企业社会责任的模式下, 结合平台企业的特征以及所处的商业生态圈, 对社会责任异化行为的治理范式进行创新与发展, 对平台企业所处的商业生态圈进行生态化治理。 在平台生态系统商业圈中, 系统内组织成员互惠共生, 生态系统内部成员的健康发展依托于商业生态圈, 组织成员内部发生的社会责任异化行为也同样会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 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由系统内所有成员共同承担, 真正实现“荣辱与共”。 社会责任生态化治理不再局限于单一层次上的治理, 而是更加重視单一层次与多层次之间的互动, 形成一个系统内不同成员之间、不同生态位之间以及个体成员与环境之间共同互动的超级系统[5] , 实现共同治理格局。 Moore[30] 根据地位将商业生态系统的成员划分为主要生态位和扩展生态位。 其中: 主要生态位成员包括平台企业以及平台内双边用户、各个参与主体, 其是生态位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成员, 具体可分为核心型、主宰型以及缝隙型; 扩展生态位成员主要包括政府以及第三方主体成员, 其对平台企业起着监督以及舆论指引的作用。 两个生态位之间通过共建共享进行互动, 形成立体式的网络治理结构, 互惠共生, 协同治理。
2. 生态化治理机制。
(1)主要生态位的自组织治理机制: 个体社会责任管理机制、责任型审核与过滤机制、责任愿景认同卷入机制、责任型运行规则与程序、责任型评价与声誉机制、责任型监督与惩戒机制[5] 。
平台企业作为平台商业生态圈中的核心成员, 具有重要的地位, 通过建立个体社会责任管理机制, 预防和规避生态系统成员内社会责任异化行为的出现。
平台企业具有开放性, 平台的开放性越高, 产生的竞争效应也越强, 治理的难度也越大, 因此对于平台商业生态圈的用户不仅要在经济上做出条件限制, 还应考察其责任偏好以及声誉, 建立门槛制度, 从源头上防范失责行为的发生, 即建立责任型与过滤机制。
平台生态系统中的组织成员基于同一价值诉求聚集在平台中, 为保证生态系统的良好运行, 将为社会创造价值的美好愿景融入生态圈, 建立民主式的责任愿景认同卷入机制, 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解决社会问题, 实现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可持续发展。
合理的规则与程序是平台生态系统得以良好运行的基础, 经济支配下的规则与程序会引发双边用户大量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致使他们采取寻租行为, 出现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 在生态化治理模式下, 责任型运行规则与程序在共同责任愿景的指引下, 将底线要求与合理期望嵌入平台的运行过程, 对平台以及平台内用户的行为进行约束。
声誉可以成为“显性激励”的替代物, 为平台企业、卖方和买方带来“隐性激励”[5], 平台企业与双边用户群体形成社会责任声誉共同体与耦合体[31], 成为生态化治理的重要隐形机制, 发挥声誉的激励约束作用。
生态化治理要求平台、卖方与买方之间建立多层次的社会责任监督机制,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严格的惩罚机制, 对平台以及平台双边用户的失责行为做出严厉打击, 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2)扩展生态位与主要生态位的共演机制: 协同共治机制。 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生态化治理不仅需要主要生态位成员发挥治理作用, 而且离不开扩展生态位成员的参与[5] 。 平台商业生态圈中的所有生态位成员都具备同边与跨边的双重网络效应[1] , 可以让主要生态位成员以及扩展生态位成员共同参与到共演机制中, 各成员之间互惠共生, 建立协同共治与动态治理机制。 政府作为扩展生态位成员, 发挥着制度供给的作用, 但其执行效力不能仅依靠政府单一主体实现, 而需要扩展生态位的其他成员以及主要生态位成员共同参与, 各利益相关方建立协同共治机制。
六、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现有文献的归纳整理, 认为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治理研究对市场发展、企业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福利等多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 在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内涵上, 本文基于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主体、客体以及治理目标三方面来对其进行定义; 此外, 从独立运营平台、商业运作平台、社会资源配置平台三个维度分别阐述其内涵。 在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驱动因素上, 从法律、行业、企业以及消费者四个层面对其展开论述。 在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模式上, 对个体自治、政府治理、多中心网络化治理以及生态化治理这四个治理模式进行探讨。 其中: 个体自治机制主要包括考核认证机制、声誉激励机制、审核与监管机制; 政府治理机制主要包括评估机制、监督机制、声誉机制; 多中心网络化治理机制主要包括个体社会责任治理机制(内部治理体系)、政府元治理下的社会责任治理机制(制度规制推进机制、监督与评价机制、激励机制)、公民社会组织的社会责任治理机制(舆论引导与标准推进机制、社会监督与评价机制); 生态化治理机制主要包括主要生态位的自组织治理机制(个体社会责任管理机制、责任型审核与过滤机制、责任愿景认同卷入机制、责任型运行规则与程序、责任型评价与声誉机制、责任型监督与惩戒机制)、扩展生态位与主要生态位的共演机制(协同共治机制)。
(二)研究展望
1. 理论与实践同步。 平台企业在技术的催动下应运而生, 并不断在市场中发展壮大, 形成平台经济模式, 但平台企业的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 研究范围主要侧重于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边界、治理与评价, 过于狭窄, 因此要与时俱进, 使理论研究追上平台企业的发展步伐。
2. 構建完整的理论体系。 目前关于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研究的内容主要为治理目标、治理主体与客体, 以及治理模式与机制, 研究内容过于分散, 未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 所以要结合平台企业的特征, 顺应平台企业的发展, 建立完整的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体系。
3. 进行定量实证分析。 目前关于平台企业的研究主要使用的是文献归纳法, 大多为规范性分析, 缺少对平台企业理论进行的实证研究, 主要原因在于平台企业的一手数据资料难以获取。 未来可以拓宽数据收集渠道, 采用合理技术手段获取正当数据, 从微观视角研究平台企业的社会责任治理对不同时期的平台企业有何具体影响, 还可以将财务绩效与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联系起来, 通过实证的手段, 探究平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对平台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 实现平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
[1] 徐晋,张祥建.平台经济学初探[ J].中国工业经济,2006(5):40 ~ 47.
[2] J. C. Roche, J. Tirole. Platform 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 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03(4):990 ~ 1029.
[3] 胡国栋,王琪.平台型企业:互联网思维与组织流程再造[ 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2):110 ~ 117.
[4] Cennamo C.,Santalo J.. Platform Competition:Strategic Trade-offs in Platformmarkets[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3(11):1331 ~ 1350.
[5] 肖红军,李平.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的生态化治理[ J].管理世界,2019(4):120 ~ 144+196.
[6] 郭凤娥.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及其治理机制研究[D].济南:济南大学,2021.
[7] Armstrong M.. Competition in Two-sided Markets[ J].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2006(3):668 ~ 691.
[8] Katz M. L.,Shapiro C.. Product Introduction with Network Externalities[ J].The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1992(1):55 ~ 83.
[9] 黄慧丹,易开刚.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及其结构维度构建——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J].企业经济,2021(7):31 ~ 41.
[10] 肖红军,阳镇.平台企业社会责任:逻辑起点与实践范式[ J].经济管理,2020(4):37 ~ 53.
[11] 李伟阳,肖红军.企业社会责任的逻辑[ J].中国工业经济,2011(10):87 ~ 97.
[12] Jacobides M. G., Cennamo C., Gawer A.. Towards a Theo-ry of Ecosystem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8(8):2255 ~ 2276.
[13] Wareham J., Fox P. B., Cano Giner J. L.. Technology Ecosystem Governance[ J]. Organization Science,2014(4):1195 ~ 1215.
[14] 肖红军.企业社会责任议题管理: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7.
[15] 阳镇,许英杰.平台经济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的治理[ J].企业经济,2018(5):78 ~ 86.
[16] 汪旭晖,张其林.平台型电商企业的温室管理模式研究——基于阿里巴巴集团旗下平台型网络市场的案例[ J].中国工业经济,2016(11):108 ~ 125.
[17] 肖红军,张力.社会责任生态系统:美团外卖履责范式的创新[ J].清华管理评论,2020(12):101 ~ 110.
[18] 肖红军,阳镇.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理论分野与研究展望[ 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57 ~ 68.
[19] 王磊,王丹,郭琎.新时期全面加强互联网平台监管的政策建议[ 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1(2):30 ~ 35+70.
[20] 李广乾,陶涛.电子商务平台生态化与平台治理政策[ J].管理世界,2018(6):104 ~ 109.
[21] 阳镇.平台型企业社会责任:边界、治理与评价[ J].经济学家,2018(5):79 ~ 88.
[22] 阳镇,许英杰.“互联网+”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变革趋势与融合路径[ J].企业经济,2017(8):38 ~ 45.
[23] 王磊.互联网平台企业定价问题及监管对策研究[ J].价格月刊,2021(11):8 ~ 13.
[24] 王勇,冯骅.平台经济的双重监管:私人监管与公共监管[ J].经济学家,2017(11):73 ~ 80.
[25] 阳镇,许英杰.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成因、模式与机制[ J].南大商学评论,2017(4):145 ~ 174.
[26] 伏嘯.平台监管要最大化社会整体利益[N].社会科学报,2021-01-28.
[27] 魏小雨.互联网平台信息管理主体责任的生态化治理模式[ J].电子政务,2021(10):105 ~ 115.
[28] 易开刚,黄慧丹.平台经济视阈下企业社会责任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基于平台型企业视角双案例的研究[ J].河南社会科学,2021(2):1 ~ 10.
[29] Tiwana A.,Konsynski B. R.,Bush A. A.. Research Commentary-platform Evolution:Coevolution of Platform Architecture,Governance,and Environmental Dynamics[ J].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2010(4):675 ~ 687.
[30] Moore J. F.. Predators and Prey:A New Ecology of Competition[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3(3):75 ~ 86.
[31] 汪旭晖,张其林.平台型网络市场“平台—政府”双元管理范式研究——基于阿里巴巴集团的案例分析[ J].中国工业经济,2015(3):135 ~ 147.
【作者单位】长江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荆州 434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