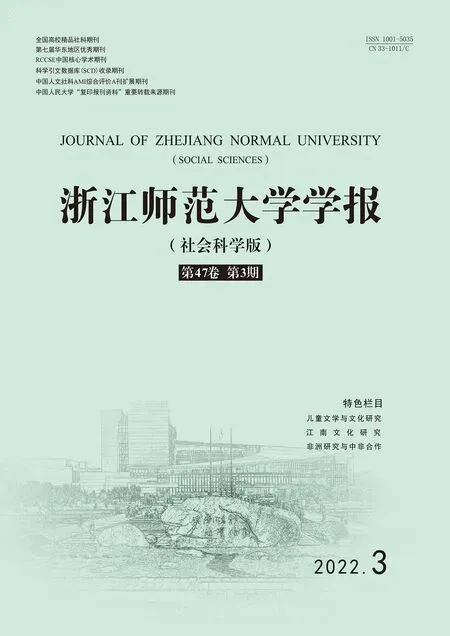战疫治理共同体:一个村庄的再组织
金姗姗, 冯夏宇
(1.浙江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2.浙江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乡村历经十年的“迟滞性稳定”后,在城市化、市场化双重冲击下,迎来了开放年代的村落变迁。农村人口的高流动[1]以及村庄异质分化,[2]冲击着乡村原有的内聚文化结构。[3]由此,旨在提高农村组织化程度的村庄再组织问题成为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重大课题。通过村庄再组织,一方面,可以引导村落重新回归稳定的社会结构,成为“社会整合器”,彰显农村社会的基础载体在维护政治秩序中的力量;另一方面,村庄再组织的过程,势必带来村庄内部深刻的博弈与调整,使得再组织的村庄成为“与之前都不同”的“社会启动器”,[4]从而强化政治秩序的有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地方政府依靠行政力量积极整合农村,下移治理重心,使权力、资源汇聚于基层,开启了乡村治理新局面。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集中检验,也是对我国农村组织化程度的一个考验。基层农村作为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第一线,在抗疫期间的组织程度如何?何以落实联防联控措施,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本文通过剖析浙江省A村①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透视其村庄组织程度,探讨中国农村再组织化问题。
A村地处浙中地区,位于某县宅山镇东北面。村域面积约为1平方公里,有耕地面积383亩,山林面积659亩,户籍人口306人,共计118户。2019年村民人均收入1.2万元。村内主要产业为农业,以种植葡萄、桃子、柑橘等水果和养殖猪、鱼为主。2020年2月5日报告第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月6日报告第二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全村共有39名密切接触者接受医学观察;同日,A村实行封村封户管理。2月20日,全部确诊病例治愈出院,39名密切接触者陆续解除医学观察。2月21日,鉴于A村连续15天无新感染病例,A村调整为新冠肺炎疫情低风险地区,并解除A村封村封户管理。A村内设卡口管理保留至3月15日,此后A村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管理。本课题组针对A村疫情防控的实地调查工作历时半年多,②期间主要通过参与式观察和个案访谈方式进行实地调查。调研后得出结论:A村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生成了“战疫治理共同体”,初步完成了村庄的再组织。
基于A村的典型性和独特性,本文选取其作为案例进行研究。A村的典型性表现为:其一,由于属地管理原则,浙江省委、省政府制定的抗疫政策在省域内基本一致。其二,浙江农村深受城市化、市场化影响,村落分化普遍较为严重。A村的独特性在于:一是,A村有2例确诊病例,并且密切接触者接受医学观察者也较多,非常考验其村庄治理能力。二是,A村在疫情暴发前属于正在解体中的村落,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间状态”,既非强村亦非弱村,获得乡镇政府的项目供给较少。
二、村庄再组织:他组织与自组织的二元实践进路
A村外出务工人口比例近三分之二,村庄空心化程度高。A村是集体经济薄弱村,③多年来,村庄治理运行低效。如,2017年、2019年,浙江省乡镇政府推动了两项省重点项目建设,一是对应“三改一拆”政策的“无违建村”创建;二是旨在打造“美丽乡村”的“八有八无创建村”建设。然而,A村既未能按时完成“无违建村”创建,也并未申请“八有八无创建村”建设。为了激发乡村发展的内源动力,A村一直走在再组织的路上。
(一)A村再组织的尝试:自组织
上个世纪末,折晓叶在对广东“超级村庄”的考察中,发现了借由经济关联、自下而上自组织达成村庄再组织的可能性,发现以经济利益为关联纽带能增强村庄内聚力,实现村庄的再组织。[5]折晓叶的研究后被众多学者跟进。郭圣莉和王兴等人的研究也认为,村庄在集体资源壮大前提下形成了利益依赖结构,使村民形成身份认同。[6]莫艳清则将折晓叶提出的“超级村庄”概念应用于浙江村落的研究,着重强调了村落精英的作用,认为村庄可以结成政经社一体的“利益关联共同体”。[7]331-347从1978年到1997年,浙江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推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A村也在20世纪90年代初创办了村办企业——“A村砖瓦厂”,而且它还是被寄希望于形成理论界期盼的“利益关联共同体”对象。[7]335-347“A村砖瓦厂”虽然并未出现理论界预想的过密化问题,④但它只维持了7年。2015年,根据村级组织再建的试点工作安排,A村成立了经济合作社再度尝试自组织,但是这一组织一直处于职能“空转”状态。
(二)A村再组织的另一尝试:他组织
基于对自组织的失望,政府和学界不约而同地给出了自上而下国家嵌入的他组织路径。该路径最早由项继权提出,他认为以经济关联的方式不足以构建真正的共同体,应基于村民的共同需求,通过国家项目来维系村民间关联,增强村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8]吴业苗认为,发展农村社区服务,能够拓展公共空间、壮大公共利益、培育公共精神,促进其公共性的增长。[9]他主张国家权力主导下的村落重建,认为国家应以城乡均等化发展要求为村落提供公共服务,增强村落的向心力与凝聚力。[10]分税制改革之后,随着国家—农民关系由“汲取型”转变为“悬浮型”或“服务型”,国家试图通过以项目为载体的转移支付来实现村落服务供给。[11]在“项目治国”的背景下,浙江省将项目制作为构建村落服务的主要制度框架,但现实中,项目的落地并不均衡,大多数项目进入了经济与社会基础发达的“强村”,其他村庄则难以获得,依旧无法摆脱衰落和解体的命运 。[12]A村就处于后者的境地。
A村再组织的实践,主要通过两个路径展开:一是自组织之路,自下而上地,在没有特定外部力量介入下借由原有的组织基础自行建立;二是他组织之路,自上而下地,由特定外部力量嵌入培育而成。从结果看,A村非此即彼的二元尝试并未使其完成再组织目标。相反地,疫情前A村的村庄治理绩效堪忧。然而,A村的疫情治理却交出了亮眼的答卷。确诊病例出现后,全村并无二次传染病例,疫情防控秩序有条不紊,村庄社会秩序井然。原本组织涣散的A村,何以承受住了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验?本文认为,A村能够构筑起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是其村庄再组织的结果。战疫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意味着A村再组织又进行了一次尝试。
三、战疫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机制
(一)战疫治理共同体的生成
组织化的村庄作为共同体,能衔接个体与国家,可有效防止两者的断层与中空。村庄共同体能够对村民形成软性约束,是村庄内生秩序生产的主体。而村庄这种内生秩序生产能力,是“国家与村落进行有效衔接并积极互动的前提”。[13]在互动过程中,国家完成对村庄的社会整合,促使乡村社会对国家的认同。故徐勇断言,将“一盘散沙”的乡村社会聚合起来是现代国家建构的社会组织基础所在。[14]伴随着一套维持秩序的内生规范的出现,战疫治理共同体在A村得以生成与发展。
1.战疫治理共同体生成的时间脉络
第一阶段:外生强制秩序嵌入(2020年2月4日—2月5日)。2020年2月5日,即A村报告第一例疑似病例但尚未确诊的那天,“我(网格长,王珺)十点多从村里回去后,和我们镇党委书记去县里参加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访谈编码:20201002AA002)。此次紧急会议确定了封村封户管理的基本行动规范。这一外生强制性秩序规定:封村封户后,密切接触者统一送往集中隔离点,间接接触者、无接触者统一居家隔离不得外出;由医院专家评估确认安全后才能解除隔离,村民出村需要说明缘由并进行登记。期间村落进行临时交通管制,任何聚集活动不得进行。(具体内容详见图1)
伴随着外生强制性秩序出现的是政府权威的嵌入。第一例确诊病例报告后,联村干部第一时间入驻A村,起到了临时权威中心的作用。网格长王珺回忆:“他们(村民)完全懵了,除了听我们统一指令,也没有别的想法了。”(访谈编码:20200901AA002)
第二阶段:内生自发秩序生成(2020年2月6日—2月20日)。封村封户期间,政府敏锐地觉察到村庄治理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亟待内生权威来组织村民更高效地应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强制性秩序嵌入后,倘若村民主观上拒绝遵守,强制执行外生秩序的治理成本则会很高。正如网格长王珺坦言:“村民如果不主动说自己有没有接触过(病患庄东),我们真的没办法搞清楚谁是直接接触者,其实他们瞒报的话我们也不知道的。”“如果他们自己不进去(隔离点),那我们工作会很难做。”(访谈编码:20200905AA002)因此,自发性秩序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了。而自发性秩序的生成,关键是要让村民意识到自己的安全需求。村书记庄星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跟村民讲新冠肺炎疫情,他们也不懂,(我)就说外面发瘟疫啦,赶快躲起来吧,这样做起工作来顺利多了。”(访谈编码:20201002AA001)另外,通过微信群、村广播、流动小喇叭等媒介的宣传,疫情防控措施的具体内容和必要性逐渐被村民知晓,也促进了自发性秩序的生成。意识到自身的安全需求后,村民自发地与工作人员对接:
大家都很害怕。有些人甚至只(和感染者)说过一句话,由于害怕,后来想想还不如去那里(隔离点)安全,至少还可以检测一下到底有没有被感染。然后他自己会过来说,“我在几月几号,大概几点钟的时候和他隔了多少米相遇过,但是没有戴口罩”。然后自己要求去集中隔离点。(访谈编码:20200905AA002)

图1 A村疫情防控工作流程图
村落内生的权威在疫情治理过程中逐渐被激发。一方面,村干部在疫情治理期间表现出的共同体善,得到了村民的认可。“他们(村干部)很认真的,很得力的嘞。”(访谈编码:20201002AB008)另一方面,安全需求本身也容易激发权威崇拜。人们在面临安全威胁时往往会倾向于听从权威人物的领导,这与访谈中村民的回忆相符:
疫情那个时候,村干部都很严肃,不跟我们开玩笑的。我们自己也怕,叫我们去隔离,我们都老老实实去的。(访谈编码:20201202DA033)
第三阶段:内生自发秩序维护(2020年2月21日至今)。A村解除封村封户管理措施之后,政府转变了嵌入方式,降低了嵌入强度。联村干部逐步撤出A村,作为内生力量的村落精英重新成为村治中的权威中心,主导后期的疫情治理。村庄共同体秩序由村干部和村民的自我规范来维系,如减少聚集性娱乐活动、进出村庄实行等级制等,这些规范都由村民自觉遵守和村干部负责监督。
2.战疫治理共同体的功能解析
从某种意义上说,战疫治理共同体是A村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形成的高度关联的新型共同体,也是村落组织化的一种新型样态。战疫治理共同体凭借着单一个体对其的高度依赖性,既满足了共同体需求,又确立了共同体边界,最终将多元主体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实现着共同体秩序,具体地说:
第一,共同体需求得到满足。成员需求的满足是共同体生成的核心因素。正如沃尔泽所言:“我们相聚在一起……其目的便是满足我们的需求。”[15]村庄主体性的生成正是满足村民多样需求的结果。战疫治理共同体以真正契合村民需求为基础,满足了村民需求的多样性、公共性和共同体善。
一是战疫治理共同体满足了需求的多样性。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其传播速度快、感染范围广、防控难度大,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安全。在这种安全威胁下,村民产生了恐慌情绪,“从眼神里就能看到恐慌,甚至恐慌到(是否接触过感染者的)细节都想不起来”(访谈编码:20201002AA002)。这种情绪甚至影响到村民的生理状况:
有些人就是心理压力大,感觉自己很不舒服,恶心啊,头痛啊。然后医生上门去听他讲一讲,他就又觉得舒服了。(访谈编码:20201202AA004)
战疫治理共同体将遏制新冠肺炎、保证村民生命安全作为首要目的,并针对村民的恐慌情绪,介入心理支持。情绪安抚组是战疫治理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责任医生、联村干部、村干部、部分村民联合组织而成,在封村封户管理措施执行之日即已成立(详见图1)。该工作组通过逐户访问或电话交流的形式,⑤直接回应村民心理需求。情绪安抚组的一位党员表示:“我们(当时)不停地在(村里)走走转转……第一时间给他们安抚情绪。”(访谈编码:20201002AC003)有村民表示:“那时候一个人居家隔离很孤独,我每天在窗口和他们远远地打个招呼,心里就踏实很多。”(访谈编码:20201207AB009)
同时,隔离状态下村庄日常生活运转的维系,依托于村庄资源需求的满足。在浙江快速城市化的影响下,村落人力、物力、财力本就不足,运行资源也不够,[16]疫情期间的资源运行成本更高。A村是集体经济薄弱村,本身资源匮乏,依靠自身难以满足村庄抗疫的资源需求。因此,外来资源输入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在乡镇政府主导下,民警、民兵、行政执法人员和医务人员等人力资源,防疫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等物力资源,以及安排集中隔离和设置封村卡口等工作所需的财力资源,得到了迅速满足。⑥
二是战疫治理共同体满足了需求的公共性。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安全威胁会不加区分地对所有人产生影响,这种情况下,安全需求成为平等分享的公共现象。作为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是私人安全的威胁者,也是村落公共安全的破坏者。一位村民谈及她为村集体疫情防控捐款的原因时说:“毕竟这疫情是关乎每一个人的,如果能够控制下来,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益。”(访谈编码:20201002AC004)正因为疫情本身的公共属性,疫情防控的基本单元是村庄整体而非个体家户。
三是战疫治理共同体满足了需求的共同体善。战疫治理共同体超越了工具性需求的满足,最终满足的是需求的价值性,即共同体善或美德的凸显。在疫情防控过程中,舍己利他的美德、他人优先于自我的行为表现,成就了战疫治理共同体的伦理特征。向善向上文化的出现,使村庄不再是一个“工具性共同体”(The Instrumental Conception of Community),而成为了一个桑德尔意义上的“构成性共同体”(The Constitutive Community)。例如:
我站岗是为了保卫我们的家园。(访谈编码:20200829AB007)
医院需要王英(第二例确诊病例)的就诊卡。为了不耽误她的治疗,王斌(村主任)在明知道王英房间没有消毒的情况下,只带了一个口罩就进去了。(访谈编码:20201003CA025)
王英发烧后情绪很激动,和女儿通电话后,一定要书记(庄星)和她女儿说几句。她直接把手机递给书记。明知接触那个手机很危险,书记还是拿过这个手机就接电话了。王英确诊后,庄星书记就觉得自己风险特别大,因此工作时心理包袱很大,刻意和我们保持距离……那时候他老婆还怀孕了,为了尽量不接触他老婆,他就在这个(村办公大楼)一楼的一张简易床上睡觉。(访谈编码:20200903DB036)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向善向上文化在战疫治理共同体中得以涌现,这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对受市场经济和个人主义荼毒的乡村价值体系的修复。
第二,共同体边界得以确立。无论是共同体权威中心的出现还是共同体秩序的生产,都限定在治理边界内。如前文所述,浙江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人口急速流动逐渐消解着村落边界,而疫情期间的封村举措则以最突兀的形式重新明确了村落的自然边界和社会边界。
一是战疫治理明确了村落的自然边界。A村地处平原,与附近的渡村、刘村道路相通,没有任何的地理屏障,故自然边界不清晰。出现确诊病例后,村落在交通要道设立了两个封村卡点,成为A村自然边界的显著标志物。正如一个村民所形容的:“A村到渡村的路拦起来了,你自己跑也好,飞也好,都过不去。”(访谈编码:20201203BA015)另外,村落自然边界明确的另一个表现是封村卡点成为外来物资输入的中转点。所有外来物资不直接输入村庄,而是在卡点消毒后再由村庄内部工作人员搬运分配。由此,封村卡点成为村民、物资流动的地域边界。
二是战疫治理明确了村落的社会边界。自然边界的明确为社会边界的明确打下了基础。A村疫情基本控制后,封村卡点的人员构成由最初外来的民警、民兵和行政执法人员转为A村内部村民。A村村民可以在卡点处完成登记手续后出入村庄。但是,村民在登记、测温时都需要确认村民身份。村民身份的反复确认和强调,使得社会边界也被明确起来了。
(二)战疫治理共同体的驱动:他组织与自组织的联动
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村庄共同体需求得到了满足、共同体边界得到了确立、共同体权威中心得以出现、共同体秩序得到稳定,最终生成了战疫治理共同体。那么,这一共同体何以生成,其背后的驱动力何在?笔者认为,区别于自组织和他组织的二元路径,战疫治理共同体是自组织与他组织自下而上、自上而下联动驱动的产物。
自上而下的驱动来自国家通过准军事化的组织技术,[17]实现行政体系的全面动员和抗疫政策的快速下推。疫情暴发后,党中央于2020年1月25日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国务院随后于2020年1月26日下发了《关于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社区防控工作的通知》,为全国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工作作出总体部署。浙江省委、省政府分别于2020年2月6日、2月8日拟定了《浙江省农村地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暂行)》和《当前农村地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应急15条措施》,为省内各市县农村疫情防控提供指导意见。宅山镇也相应地设立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和疫情综合指挥平台,并将全部乡镇干部下沉至村庄开展工作,实行镇干部包村制度。村庄作为抗疫堡垒,自上而下驱动着战疫治理共同体的生成。
如果仅依赖于国家力量下沉至村落,而忽视村落内部社会力量自下而上的驱动,就无法形成有效运转的战疫治理共同体。其原因在于:一是,对于单一村庄而言,A村虽然在有确诊病例后的14天内,有来自宅山镇的干部、民警、民兵和行政执法人员共5人的支援,但随着村内感染者数的清零,疫情的严重程度降低,行政力量不再集中于A村,此时村落战疫基础事务的运行如果没有自下而上的驱动就会趋于停摆。二是,对于乡镇政府而言,如果没有自下而上的村落自组织,乡镇政府就不得不面向个体村民进行社会控制或社会治理,将付出很大的治理成本。
综上所述,战疫治理共同体是自上而下的动员和自下而上的有机关联驱动生成的,是自组织和他组织联动的结果。这种双向驱动在封村封户阶段最为突出,集中体现在临时党支部和尖刀队的成立上。
尖刀队由宅山镇政府组建,由镇干部、村两委、民警、民兵和行政执法人员等5人组成。临时党支部由尖刀队中的所有党员组成,是尖刀队的领导力量。尖刀队和临时党支部主要负责封村封户阶段的防控工作。这两个临时组织由镇党委和政府组织发起成立,是自上而下驱动的结果。但同时,两个临时组织又是自下而上驱动的必然要求。村两委代表了组织化的村集体,通过临时党支部和尖刀队自下而上地与镇党委和政府实现了有效对接。

图2 A村疫情防控组织架构图
虽然战疫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驱动双向作用的结果,但其中自下而上的驱动机制是战疫治理共同体得以生成的关键。另外,对战疫治理共同体自下而上的驱动边界的考察,能为今后的乡村治理重新确定治理边界增添事实依据。
四、战疫治理共同体的运行机制
我们不仅能从中观层面强调村庄有机关联的异质性特征,从而理解战疫治理共同体自下而上的驱动机制;还能从微观层面,来理解战疫治理共同体的运行机理。在微观层面上,村民面对危机时建立的一致行动能力,即社会关联,成为战疫治理共同体运行的关键所在。
团体的一致行动能力,部分来源于原有社会关系。心理学实验表明,群体在遭遇威胁事件时具有更强大的凝聚力和一致行动能力。⑦A村村民参与战疫行动多数由党员牵头实施,党员的动员能力,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党员联户”制度与村民长期交往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基础上。⑧A村村民在自愿报名值守卡点时,都是“认识的一起去报名”(访谈编码:20200904BC001)。据此可以判断这种一致行动能力是在长期熟人社会环境下形成“差序格局”的结果。
物理性隔离产生的社会性连接需求,[18]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A村的社会关联。长达两周的物理性隔离催生了高度的社会性连接需求。之后,A村封村措施仍保持了较长时间,由于减少了村落和外部社会的联系,使村民社会性连接需求的满足从村庄外部转到了内部。村民为了社会性连接需求的满足,增添了内部行动的一致性。访谈中有村民回忆:“(封村的时候)出也出不去,在家里也没意思,朋友叫我去那边(卡点)值班就去了。”(访谈编码:20201203BA014)
除此之外,A村抗疫过程中的“权威—服从”关系也成为疫情期间社会关联的基础。乡镇政府临时嵌入的权威和因疫情激发的村落内生权威,能够将村民组织调动起来,使其按照权威中心制定的方案行动,实现社会行动的一致性。
概括地说,战疫治理共同体的高社会关联是由之前的社会关系基础、隔离产生的社会性连接需求以及“权威—服从”关系生成的,这种社会关联或一致行动能力推动着战疫治理共同体的行动。
(一)基于社会关联的共同体空间产生
一般认为,社会关联不仅会在公共空间内形成,[19]还会以特定形式固化为公共空间。[20]在战疫治理共同体的运行过程中,村民的社会关联在实体和虚拟两个层面建构了村落的公共空间。
实体公共空间。封村卡点由村民共同值守,固化为实体公共空间。村民在共同值班时或进出卡点时就村落生活琐事的闲聊,对其他村民、村干部、驻村干部在抗疫中的行为进行闲言碎语(gossip)式的评价,对政府自上而下的防疫措施的议论,成为封村卡点这一公共空间内的公共议题,具有内生色彩。这种内生的公共空间,不仅满足了国家疫情防控政策的要求,还成为增进村民感情、巩固村民关联的空间载体。
虚拟公共空间。A村卡点的建立是封村举措之一,这一暂时性的实体公共空间终归消失,真正存续下来的是以“微信群”为载体的虚拟公共空间。虚拟公共空间的交流与互动提高了村民的一致行动能力。A村的虚拟公共空间有三类:一是通告性虚拟公共空间,该类虚拟公共空间覆盖整个A村,成员达到131人,群名为“和美A村”。聊天内容主要包括村庄战疫信息的发布、村民对战疫工作人员的建议等。二是功能性虚拟公共空间,该类虚拟公共空间主要是满足各战疫工作小组内部、各战疫工作小组间、隔离人员与服务人员间的信息交换。如“A村疫情防控群”“物资采购工作群”等。三是交往性虚拟公共空间,该类虚拟公共空间是为了满足疫情期间的联系交往建立的。如,年轻人专门组建的游戏群,“疫情期间因为无聊,组团打游戏”。又如,村民们组成的娱乐群,“那时候(大约3月份),城里也没有复工,我们就在群里约,约好了就一起到‘田里野(田里玩)’” (访谈编码:20200903BA014)。相较于实体公共空间,虚拟公共空间更具有灵活性,根据不同目的将不同人群聚合到一起,实现“虚拟在场”。
(二)基于社会关联的共同体信任的产生
如前文所述,在政府权威与内生权威的共同带动下,村民间、村民与权威人物间产生了高社会关联。这种社会关联,使村落得以快速自组织,并与乡镇政府行为保持了协同作用,满足了村落在疫情期间的多元需求,取得了良好的抗疫成效。在疫情的高度不确定性下,这种成效反过来又为村民带来确定性,满足了村民的预期,使村民将未来的预期赋予权威中心人物,即代表基层政府权威的驻村干部、村落内生的权威人物,如村书记等。此时,作为一种对他人行为预期的信任就生成了。村民在访谈中提到:“那几个小姑娘(联村干部)都很负责任,我们一直都很信任这些年轻人。”(访谈编码:20201102AB012)最后,基于社会关联的共同体关系产生了。
韦伯认为,“只要社会行动——无论是个别情况、一般情况还是纯粹类型——的取向是基于各方同属的主观感情,这种社会关系就可以叫做共同体关系”。社会行动的行动者在基于“各种类型的情绪、情感或传统”结合为共同体的过程中,“也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以工具理性的考虑为取向”。[21]基于村民社会关联的共同战疫行动的出发点是满足村民多元需求这一“工具理性的考虑”,抗疫共同体中,村民间发展出了“各方同属的主观感情”,即共同体关系。各个工作组的村民在维持战疫治理共同体运行过程中,通过共同处理事务增加了相互之间的感情。正如有村民表示:“组里的人本来只是认识,一起干活感情变好了嘛。”(访谈编码:20200831AA003)在这种情感关联基础上,A村形成了新的以事缘为基础的社会交往圈子,“我们组里男同志给她们女同志过情人节,还买了花”(访谈编码:20200831AB006)。解除封村措施后,村民在社会关联中产生的共同体关系仍以一定方式维系着,如去镇里采买前,村民都会在微信群里喊一声,“看看哪家要带点东西,以前都各家管各家买”(访谈编码:20201002AA001)。
这种共同体关系的出现是反村落解体的关系再造。在我国传统社会,村民间存在多元的共同体关系,如稳固而强大的宗族关系、基于共同信仰的祭祀关系、水利防卫治安的协同关系、生产生活的互助关系等,[22]但在城市化和市场化的作用下,村民之间的感性关系断裂而走向原子化。[23]战疫过程中共同体关系的出现,或是遏制我国村民原子化趋势的一个契机。
结 论
区别于自组织、他组织的二元再组织路径,得益于自组织和他组织上下联动的多元生成路径,战疫治理共同体得以生成。本文对战疫治理共同体何以生成、何以驱动,何以运行三个问题的回答,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多维度确定这一共同体存在真实性的过程,笃定了战疫治理共同体的真实性也就确定了村庄再组织的可能性。
首先,战疫治理共同体是一个治理共同体。钟南山2021年警告称,“农村地区是重点,从最近发病情况来看,60%到70%都在农村”。[24]农村防控仍然是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战疫治理共同体从生成之日开始,便确切地指向疫情治理,并且在治理过程中发掘了治理主体的主体性,为今后的乡村治理带来了一套可依赖路径的运行逻辑。在这样的运行逻辑下,A村治理绩效斐然。在2020年底的宅山镇年度评选中,A村党支部被评选为“五星党支部”,并成功申请了“和美乡村”项目。2020年8月,A村村社组织换届。原A村的党支部书记庄星以93.5%的得票率被选举为A村村委会主任 ,⑨远远高于A村前三届村委会主任平均63.7%的得票率,在宅山镇全镇的村委会选举中名列第三。但我们也要看到,相较于城市社区,农村的战疫治理共同体的治理工具还非常有限,科技支撑也不足。
其次,战疫治理共同体是一个伦理共同体,其为村庄再组织奠定的是道德基础。抗疫中,无论是利他精神的涌现还是责任优先性的彰显,都强化了村民和村民之间、村民和村级组织之间、村民和基层政府之间的社会关联度,同时也强化了个人和组织对共同体的依赖性。在这一伦理共同体内,不仅没有贬低个体的生命意义,还扩展了利他原则的外延,在要求兼顾个人利益、社会利益的同时,强调自然利益。也就是说,伦理共同体以向善向上为伦理基础的价值尺度,体现了个人、社会乃至自然命运的共进退。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战疫治理共同体只是一个暂时性共同体,这一村庄再组织的持续性有待观察。战疫治理共同体源于对全体成员无差别的安全威胁,也可以说,是原本有一定社会联系的群体,面临突发生命安全危机时,在应急反应中形成的共同体。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常态化,客观上助力了这一暂时共同体的存续。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安全威胁不可能长期作用于乡村社会。因此,如果我们追问战疫治理共同体如何从暂时性共同体转变为常态化共同体,其实质应落脚到自组织和他组织持续联动问题上来。这应是我们今后着重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根据学术伦理,本文所有地名、人名均为化名。
②较为集中的调查阶段如下:2020年8月29日至2020年9月5日、2020年10月2日至2020年10月6日、2020年12月2日至2020年12月8日。
③根据地方政府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指导意见》文件,将年总收入10万元且经营性收入5万元以下的村庄界定为集体经济薄弱村。
④村办企业为保护村民的劳动权利而产生的“在一些管理类岗位上形成的人浮于事、冗员甚多的现象”。折晓叶:《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⑤据基层政府统计,情绪安抚组在封村封户期间,日均接打电话100余个。
⑥截止2020年2月20日,已有17家企业为宅山镇疫情防控捐款约93万元。2020年2月9日,上级党委划拨了专项党费来支持宅山镇党组织疫情防控的工作所需。
⑦详见JOHN F. Organized and unorganized groups under fear and frustration. University of Iowa Studies in Child Welfare, 1944: 231-308; JOHN F. The disruption and cohesion of group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41, 20: 361-377.
⑧调研中,党员倪锋讲述了党员联户时发生的故事,这一故事反映了党员与村民之间的社会关系。“我是党员,我联系他家的。(他)中考考了四百五十几分,公办普高可能上不了,想去A中学读药剂师。我说你能上普高就上普高,哪怕是民办普高。药剂师面太窄了。他最后去B中学读了普高。小伙子现在都很感激我。”(访谈编码:20201003BB018)
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第十八条规定:全面推行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委会主任,俗称“一肩挑”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