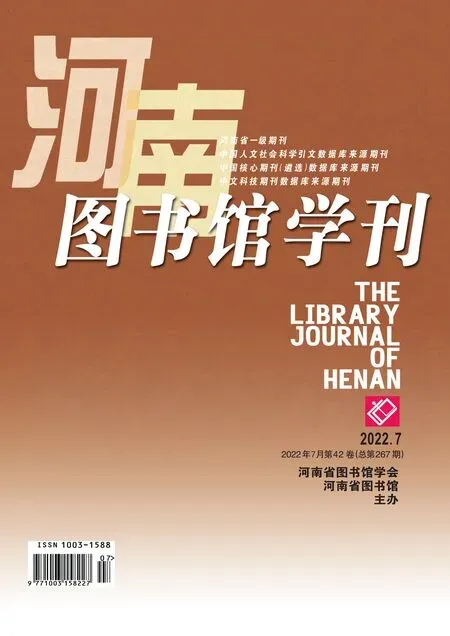传统哲学与现代新儒学之融通
——读郭齐勇教授《熊十力哲学研究》
徐默苒
(郑州大学哲学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几十年来,随着中国哲学研究的深化,对熊十力先生哲学思想的研究是一个充满挑战、不断抽丝剥茧的艰巨历程,郭齐勇教授是其中的领航者。郭齐勇教授是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及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会长与副执行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现为国家社科基金评委、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是现代儒学具有开拓性研究精神的著名学者。郭齐勇教授从其博士论文《熊十力思想研究》开始,即深入思考中国现代哲学思潮的特有风貌,这种儒学现代性的重建是以“五四运动”为文化背景的开放下产生的,“我们认为现代新儒家思潮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它是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的一种保守的回应,也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力图适应现代、走向世界的一种努力。”重温郭齐勇教授的著作《熊十力哲学研究》,结合熊十力思想体系建构的历程,以其他有关熊十力思想研究为补充,运用文献综合研究方法,既是对熊十力哲学主体思想的再次梳理,更是回望了现代新儒学发展中散发出的独特魅力。新儒家在复杂多变的情势下依然以民族为大任的使命感,对当下构建中国文化思想路径具有启迪作用。
1 儒家“道统”学脉与新儒家之真性情
熊十力生活在社会出现大变动的时期,由于经济、政治的落后,西方列强入侵,民族危机形势十分严峻。熊十力出身农村,家境贫寒,他的年少时充满了贫穷与无奈经历,外部与自我生长环境严峻的双重体验,使熊十力很早便感受到了他人难以体会的生命自觉和对探讨宇宙人生终极存在的心路感触。熊十力曾在《船山学自记》中记述自己进入有关本体论思考的缘由:“余少失怙,贫不能问学,年十三岁,登高而伤秋毫,时喟然叹曰:此秋毫始为茂草,春夏时,吸收水土空气诸成分,而油然滋荣者也。未几,零落为秋毫,刹那刹那,将秋毫且不可得,求其原质,亦复无有。三界诸有为相,皆可作如是观。顿悟万有皆幻。由是放浪形骸,妄骋淫佚,久之觉其烦恼,更进求安心立命之道。因悟幻不自有,必依于真。如无真者,觉幻是谁?泯此觉相,幻复何有?以有能觉,幻相斯起。此能觉者,是名真我。时则以情器为泡影,索真宰于寂灭,一念不生,虚空粉碎,以此为至道之归矣。既而猛然有省曰,果幻相为多事者,云何依真起幻?既依真起幻,云何断幻求真?幻如可断者,即不应起,起已可断者,断必复起。又舍幻求真者,是真幻不相干,云何求真?种种疑虑,莫获正解,以是身心无主,不得安稳。乃忽读《王船山遗书》,得悟道器一元,幽明一物。全道全器,原一诚而无幻;即幽即明,本一贯而何断?天在人,不遗人以同天;道在我,赖有我以凝道。斯乃衡阳之宝筏、洙泗之薪传也。”
喟然而叹之伤秋毫,是因熊十力觉察生存之根本所含的有限性,欲求将真我能够安心立命。入佛门、入宗教,助人去实现终极关怀。而《王船山遗书》使熊十力悟到了道与器本无二,天在人,道在我,可以超越有限的“我”以得同天凝道之真我,在天道与真我同一中来安顿自我。
思考人生终极关怀问题大致来看可分为两类:一是顿悟万有皆幻。虽佛教说无,此“无”没有依据,没有实体所承托,不过是因缘和合所引发的因果轮回,这样的个体生命因无所依而变得消极涣散,即使暂时忘却了世间的烦恼,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安心立命问题。二是得悟道器一元,幽明一物。由于在佛教中并不能找寻身心之主,不得安稳,进而转求王夫之,接续了传统儒家天人合一理论。体是存在的根本依据,用是由本体所展现的功能与现象,本体与功用如同大海与众沤,体用本无二。这样的体用论为儒家所推崇,儒家的天与道即是本体的呈现。郭齐勇先生也认为熊十力的本体是将天地万物、宇宙人生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又是内在的道德主体、主客内外合一的“生命本体”。
在郭齐勇教授看来,中年时的熊十力处于沉潜冥思、自立权衡的时期,此时“五四运动”所带来的新思潮的涌入,使曲折多变的历史路径又焕发了新的光芒。“熊十力先生以大无畏力,平章华梵,融会佛儒,自创新论,于西化之风狂飙突进之年代,为改造东方旧学,开辟新途,可谓辜往直勇,用心良苦。”而到了晚年时的熊十力,将天下庶民的忧虑,民族文化的危亡与屈折的生活经历在其特立独行的品格下,融化在了他自己的哲学思想中,以孤芳自赏的傲气展现出那个时代新儒家的真性情。
2 传统与现代哲学融合之努力
2.1 新旧唯识差别与儒佛心性论异同考辨
法相唯识学以其大乘佛学三大体系之一的属性被后世所关注。以熊十力为代表的新儒家对唯识学有了新的阐释和理解,在印度佛学、西方理性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糅合下,熊十力的思想推陈出新,并由此达到了熊氏哲学思想体系至高之处。
然而,同一时期的其他学界有为人士并不赞同熊十力果敢创新的学术思想。与熊十力一同求师的有吕澂、王恩洋、刘定权等,在老师欧阳竟无(欧阳渐)的授意下,刘定权回应熊氏而另作《破新唯识论》,熊十力勇猛不迫,围绕此次论战又作了《破破新唯识论》以反击,后期加入论战的还有本是其他学派的太虚和其弟子印顺。此次激烈的学术之争,首先是由于对“性体”中“性觉”与“性寂”的分歧。欧阳竟无派与法相唯识学思想相一致,在心性本然即净的基础上,法相唯识学主张自性涅槃,强调修行乃为一缓慢工夫之路;而熊十力将“性空”“寂静”等抽离出来,站在那时儒家学派的角度上观望群芳,得出此“心性”非“空”,而是“实”的,是非“静”而“动”的;另外,欧阳竟无派对熊氏所称儒家本性之“仁”与佛家之“寂”能否等量齐观也产生了不同看法。其次是对“心体”的状态是完整形成一体还是零落拼凑、散漫各处的分歧。熊氏认为心体即性体,这是一个整体而不能割裂开来,并且这一本心有其实在性,具有变现世界的功能;佛家看待此世界如同幻象,“我”等世界中的一切皆由各种因缘和合而成,彼此间的由条件相框互相制约着彼此,因此万物不过是许多“空”的聚合而已。再次是熊氏还谈到了道德理性的阐发,此种道德意识的出现是直接明了还是繁琐迂回,熊十力也在著作中对他人有所答复。
法相唯识学既有可吸收之处,也有需改造之点。郭齐勇教授认为“熊十力对法相唯识基本精神、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的汲取和改造是全面的。就‘万有论’来说,心王与心所、色法与心法、能缘于所缘、无为法于宇宙法的宇宙构成论,都深刻地影响了熊氏……以阿赖耶识作为宇宙的根源、万有的总体,森罗万象无不是阿赖耶的变现,无疑是熊氏‘心体’论的原型之一。”熊十力一生学术思想浩瀚,涉猎范围甚广,其既拥有鲜明的佛教思想,然亦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性人物,熊十力将佛学进行了“改造”与新的诠释,儒佛在人性本善和个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体悟天道方面,都可达成一致。熊十力受唯识学复兴之风的影响而研读佛典、钻研佛学,在支那内学院求学于法相唯识学所带来的感导,也反映出熊氏借批判唯识学,乃至佛教空、有两宗的不足而阐发其自我目的,在新儒家卷入近代佛学争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2.2 熊十力易学思想之特性
除了上述佛学观,熊十力先生认为自己“生性疏脱,少时喜老庄”,中年游心于佛,久之皈向孔学《大易》。其借易学阐发自己的心学本体论与方法论,易学作为其思想渊源亦被学界所认同。熊十力易学的核心是对“易之体”与“易之蕴”的创造性阐发。一方面,熊十力既是早期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其也深受易学生生变化之性的熏陶。熊十力取孔子的“天何言哉”和《易》家“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摆脱逻辑思想的束缚,多以暗含、多义的比兴语言表达自己形而上学的意涵,提升道德人格感染力,达至“乾元性海”之境。
其实,从早期的《新唯识论》开始,熊十力即已归本易学,并以易学建构体系,透过易的乾、坤两大原则,用以比配心与物(精神与物质),而其功用为一种辟、翕的动能,并且以易学体系涵摄中、西,融摄儒家与佛家唯识学思想,建构一大体系;以易之变易、不易精神,收摄佛学的无常变易之法,并以易学为宗,平章儒家的汉学与宋学。“易体”与“易道”所要解决的是超越性的精神世界与现实人生世界的关系问题。
“乾元性海是回归对本体论的探讨,“翕辟成变”则是熊十力对宇宙论进行的新的诠释。他认为,世间宇宙的万象不过是本体所含“功能”的显现而已,此种“功能”即是“非常”之“恒转”,不易与变易中存在两种恒转形式:一是易学中所得出的翕辟成变说,二是佛教提出的刹那生灭说。此“恒转”非一般意义的“位移”,它是真实的。将《大易》《中庸》与华严宗、禅宗相融摄,此类特性即体现出刚健有力的创制性精神。
2.3 “涤除玄览、明觉澄然”之道家观
郭齐勇教授所理解的涤除知见,不是对世间一切知识都不理会,而是在作本体玄思时,不能随知见支配。任何冥思都使人超逾当下,趋于玄远,把握永恒,倾听未来,体悟吾人与世界的真实关系。而道家澄心凝思的玄观,给予熊十力深深的启发。
从中国哲学史的历程中回看,早在魏晋时期就出现了王弼、郭象这些翩翩风度的名流士族,他们崇尚思想的自由与处世的洒脱,虽然从哲学的思想根底看外来的佛学与魏晋玄学有很大的不同,但在南北朝分裂与民族矛盾深陷的大背景下,玄学与佛学并为一谈,即融摄了老庄崇尚无为逍遥的气禀,是中国传统哲学具有独特气质的代表性时期。这种独特之中包含着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者们以“无为”为循的政治抱负和找寻生命活动意义的过程,一种个体与人生相交融的情境所在。
熊十力哲学对老庄思想吸收与改造究竟有何种意义,也是郭齐勇教授研究的重点。同是传统经典,熊十力对道家思想所持的态度与易学略有差别。老庄本体之有无观,熊十力既汲取又改造。“老氏之无非空无也。本性虚寂,故说为无,儒者亦非不言无,《中庸》言天性曰‘无声无臭至矣’。但儒者不偏着在无上,与老氏又有别。”熊氏文章中多有批评道家,并且在郭齐勇教授看来,熊十力肯定道家的道之有无本体论和超本体论的价值。儒家的“仁”“诚”是化生万物的根本依据,这是从“有”的一面,而道家之“道”既包含现实界的“有”,也存在通往恒常性之“无”。此外,郭齐勇教授也提到熊十力批评了以虚无为本的老庄宇宙——人生论思想,此种思想下满是消极无为厌世的感触。有批评,就有吸收,在新儒家试图以佛、道弥补儒家理论之不足以及遭受西方文化冲击的时代背景下,熊十力先生阐发其“新唯识论”思想体系,亦是研究现代哲学复兴的必达之路。进入现代,东方文明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在诸种纷然杂陈、神秘怪诞的状态下,儒学、佛学与道学在新儒家的笔中隐含着对于话语的论定所导致的种种染污异化独有的反思,蕴涵存在的回归之道。
3 熊十力与同时期新儒家之比较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在以“五四运动”为背景的思想浪潮中,激荡着现代批评的传统和以传统批评现代的双向交互的文化新运动。传统夹杂着不适应当世价值的思想理路,而现代思想的冲击让哲学的发展陷入窘境。
与熊十力年纪相仿的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诸位哲学思想家,对中西文化交融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欧美文化的袭来,重新找寻安心立命、寻找终极关怀的问题意识出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动摇,自我意识的丧失,传统哲学、宗教观等世界观的迷惘,此种情景下的现代新儒家们在缝隙之中看到了希望——他们摆脱情绪化的对峙,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新的综合”,即在吸收融化、超越扬弃中外文化遗产的基础上,重建民族文化精神。为解决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熊十力与其他诸位新儒家们在哲学思想的阐述上殊途同归。
在郭齐勇教授看来,熊十力哲学的中心范畴是“本心”“仁体”,范畴体系围绕“体与用”而展开;冯友兰哲学的中心范畴是“理”“气”“道体”“大全”,范畴体系围绕“理与气”而展开。熊十力哲学研究的重点是对本体论展开的,在“本体”中生发出“大用”,此种本体不是脱离于宇宙人生之上的“绝对精神”,而是如《大易》之中刚健有力、生生不息之本体,这种活泼泼的本体以“即体即用”“体用不二”为本。在西方外来精神文化的映射下,熊十力哲学也有柏格森的影子,但是他批评西方生命哲学将本能、欲望等与形骸俱始得习气作为生命力的本质去看待。此时儒家的道德自性融在了熊十力哲学之中,幻化成为一种新的生命力的存在并映射到天地万物之中。冯友兰站在实用主义的角度批评中国传统哲学形而上的不切实际,但也认为这种哲学的引导能够给人安身立命的慰藉。金岳霖把“道”作本体,他在《论道》里同样认为现有的世界是生生不息运动变化着的,在这种“生生之变”中蕴含着“道”的规律,存在着具体事物中共相与殊相的矛盾。同样,熊十力认为本体至虚至静而生生化化无穷无尽是含藏万德故;动而不暂留,新新而起,因此得以显现仁的本体。
作为熊十力的学生,唐君毅、牟宗三和徐复观将老师的哲学思想带入了港台地区,甚至在海内外掀起了中国现代哲学人文精神的风潮。从西方思想中汲取力量,再由熊十力等人创制后重新分享于世界,是现代哲学独有的魅力所在,也是包容与开放的文化场景的显现。首先,熊十力与唐君毅哲学思想也存在很大分歧:郭齐勇教授在二者有关心与性、科学真理与玄学真理、思辨与体认的关系问题时指出:“唐君毅考虑的是如何从分析科学中之概念、假说以汇归或依附于玄学,即科学真理与哲学真理的流通问题。熊十力则批评近世学术,重客观而黜主观,虽于物理多所甄明,而于宇宙真理、人生真性之体验,恐日益疏隔而陷于迷离状态矣。”其次,对于儒家之“性”的思考,唐君毅与熊十力均站在了相同的立场上,唐君毅认为儒家最为圆融,因其“天心神性,本心本性,佛心佛性,皆同依于人观‘人之成圣,所根据之有体有用之同一形上实在,或神圣心体’之异相,而有之异名。”再次,从陆王心学思想理路出发,熊十力与牟宗三思路一致,有关心性本体之不二,心性之中可取其能动的、道德情绪之价值的一面,由心性本体所涵盖的道德情感是进行道德实践的内在生命力,从而推动了熊十力关于“性智”之“智的直觉”彰显,形成思孟学——陆王心学相一体的道德哲学。最后,徐复观与熊十力都反对传统的专制主义,但儒家思想不是专制主义的附庸,儒家之“仁”即是“诚”的主要内容,“诚”是“仁”外在实践的表露。将个体的生命与群体间的生命结合在一起,这是中国哲学的特性,继而融会出现代中国哲学特有的风度。
尽管在中国现代哲学漫长且艰辛的发展历程中,不同的思想家们因有不同的性格、出身背景等对中国现代思潮阐发出各自不同的思想注解,但面对从传统到现代的必然性进程,如果没有创造性的转换,没有新儒家们逐渐形成的特有风度,势必会在历史前进的脚步中面临巨大的阻碍。在维护儒家传统、反对全盘西化的意义上,现代儒家有其保守的一面,也有选择性地吸收西方哲学文化。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熊十力融会传统儒佛道思想,阐发“新论”,发扬以民族为大任的使命精神,这不仅体现在熊十力身上,与其同时期的新儒家们一并发出了强大的号召力。
4 余论
上述是对郭齐勇教授所著《熊十力哲学研究》的梳理与解读,熊十力哲学接续了文人士族极高的文化修养,在融会佛教、中国传统儒道二家与中西文化的基础上渐渐形成了自领风骚的哲学思想体系。于浩浩数十年的学海中苦心研究,熊十力先生受尽身体与精神上的重重苦难,从最初1926年创作的《唯识学概论》,到1932年《新唯识论》文言文体版的出现,对自我“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建构一直从未停息,并不断地创新、充实自己独到的观点。在1944年出版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和接续的《读经示要》,熊十力表明其逐渐摆脱了纯粹佛学的思想理路,转而归心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当前,对熊十力的哲学研究,仍有许多学者愿意深入其中探寻理论来源和把握其整体思想脉络,对熊氏思想的研究依然是现代中国哲学思想界的一大关注点。熊十力研究成果丰硕,只是因其思想体系的庞杂以及处于特殊时期的一些因素,导致对熊十力哲学思想的研究陷入困境,对于解决深层次问题仍处在百废待兴时期。
郭齐勇教授所著的《熊十力哲学研究》一书较全面与系统地涵盖了熊十力哲学主要内容,是深刻研究熊十力思想体系的典范之本。在郭齐勇教授大量阅读文献、实地访查的基础上,一方面清晰再现了熊十力哲学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表达了熊十力对待传统与现代哲学的特有姿态,对当下甚至未来中国哲学发展路程给予许多深刻的反思,体现出熊十力哲学应有之价值,更是体现了熊十力哲学对天人性命关注和社会人文的关怀。
从熊十力哲学的主要内容看,虽复杂晦涩,但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较明显的触类旁通之考量,也有对现代文化冲突之思考。熊十力认为自己“余年四十以前,于儒学犹无甚解悟,及深玩佛家唯识论,渐发其短,不当墨守,而求真之念益迫,姑置无着、世亲,上穷龙树、提婆之法,于空教四论备费钻研。”于是,熊十力放弃了仅仅只对佛学形而上的苦苦追寻,由向往彼世的人生态度转向了在社会现实中体悟真正的“识”,由本体与大用存在之“空”转向了以儒家易学为基础的本体宇宙论与生生之性的有机阐释。
熊十力哲学的广集深奥可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体与用。“体”“用”在熊十力心中并无二类,从本体的存在而阐发出“用”的功能,如大海之于众沤并无形而上的本质差别。二是基于佛教对人生性命的体悟。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来,佛教中国化在发展历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熊十力早年在南京内学院长时期学习佛教唯识学,佛教思想是其最初阐释哲学思考的理论方向。熊十力对旧的唯识学理论有所不满,于是在唯识学方面提出了独到见解并狂放不羁地称自己的学识为“新唯识论”,但由此引发了维护正统“唯识学”一派的严厉指责与学术纷争,而道家的“道体”令熊十力找到了体与用与道家血脉相连的理论支撑。老庄对“无”有精神超越境界之逍遥无所待的生命态度,在肯定“有”的现实存在中对个体自由的无限追寻,熊十力利用郭象将现实世界中的名教纲常抽离出来,将个体性上升为宇宙之本体,在此之中进行批判与重塑。三是儒学中的经学与易学。熊氏以“六经注我”的态度从经学中钻研其中深细,用德治反法治,在有关功利问题上严辨公私,并提出了政治——历史哲学的主张。另外,其归宗《大易》作其本体论与方法论的指导,从探究本源引出对存在根据的问题。
从熊十力哲学意义上看,他的哲学思想体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最早尝试,其中不免有些体系庞大和“系统化”构建仍需完善,但熊十力哲学亦是“保守”与“开放”看似矛盾的创新思维方式的体现。这种模式下的理论构建注重现实的变革和传统延续的关系问题,不仅创造性地汲取了西方哲学思想的养分,也从自身传统文化中发凿出仍有刚健生命力的智慧之因,认识到使中国摆脱理论困境的出路不能仅靠感性认识外来世界,更须经过自我生命的体验与情感价值的体悟才能发现尚可延续的价值源泉。这是“跳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二元对立,重新思考东亚、中华精神文明与现代化、现代性的关系问题”的突破性尝试。
郭齐勇教授对于熊十力哲学的研究,为现代新儒学具有张力的一面作了总结。将熊十力哲学放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交融历程之中,重估熊十力哲学思想的历史意义,探求熊十力哲学在现代儒学思潮中重要的学术价值。此种交融是在现代哲学冲突与传统哲学体系崩坏的碰撞中形成的,对于创建本体论、宇宙观、心性论、人生论等赋予了新的诠释,并用一位哲学思想家的目光重塑时代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