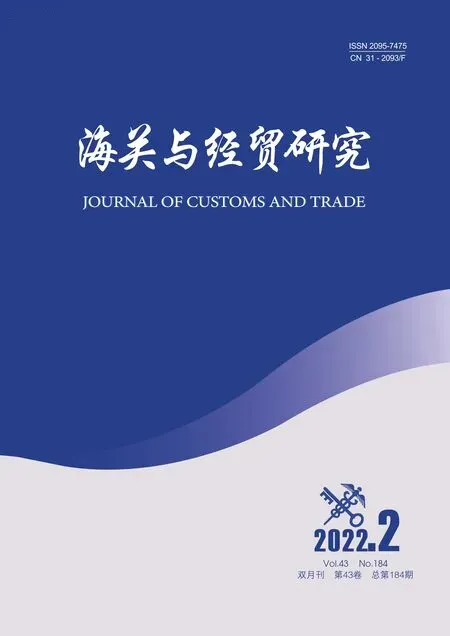整体性治理视野下的口岸管理现代化:理论逻辑、兴起动因与实践路径
王菲易 黄胜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政治安全形势的变化以及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各国相继开展以“整体性治理”理念为指导的口岸管理现代化改革,通过跨关境、跨部门、跨层级的口岸国际合作、口岸监管流程再造、信息共享和权力重构以及口岸公共服务供给,推动不同国家口岸管理部门之间的国际协调、一国内部口岸管理部门之间的跨部门协同和口岸管理部门与管理相对人之间的合作,进而推动碎片化、分散化、封闭化的口岸管理走向主体协同、多元互动、多国共治的口岸治理。
一、整体性治理的兴起:口岸管理现代化的理论逻辑
(一)从“碎片化”到整体性治理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快速发展,日益复杂化、多样化的社会问题对政府部门的公共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引起了政府部门对跨部门协同的关注。传统的多层管理模式,复杂的机构设置,使各个部门难以迅速准确达成政策目标,“合作政府”理念兴起,核心目的是打破政府部门之间的孤立隔绝,对原本独立的部门进行整合,使各部门基于共同目标开展合作。(1)张康之:《论社会治理中的协作与合作》,《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1期,第49-54页。由于“合作政府”考虑的只是合作的机构、内容以及合作时机,忽略了合作方式、产生问题以及应对机制,容易在具体合作中产生各部门权责不清的功能碎片化和机制碎片化现象。
针对政府追求效率所带来的“碎片化”等一系列问题,在对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反思之后,希克斯等人提出了“整体性治理”(Holistic Governance)、“整体性政府”(Holistic Government)理论。其主要内涵是合作的“跨界性”,主张在不消除专业分工、组织边界的条件下,通过长期有效的制度化协作,促使各个公共管理主体,包括上下级政府之间、同级政府之间、公私部门之间通过多种协同行动发挥政府的整体效能。整体性政府改革摆脱了新公共管理以特定功能建立组织的管理理念,转而以结果和目标进行组织结构设计和管理制度创新。(2)Perri 6,Holistic Government,Demos:Bridewell Place,1997.转引自黄宏主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与社会组织创新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8页。英国政府1999年的《政府现代化白皮书》、美国政府2002年的《总统管理议程》,都对跨部门协同提出了要求。跨部门协同研究逐渐成为政府改革的热门实践和国际公共管理研究的前沿领域。凯特尔认为跨部门网络是当代政府改革的重要趋势。(3)[美]唐纳德·凯特尔:《权力共享:公共治理与私人市场》,孙迎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政府机构间的合作、协同和整合,可以称为“协同的”“全面的”或“整合的”,在组织结构和表现形式上多以伙伴关系、协同政府、整体性政府出现。整体性政府是政府公共服务机构为了实现政府的共同目标,满足公民需求,以信息技术为手段,协调整合某一领域中不同利益主体,以为公民提供无缝隙服务的政府组织模式。(4)Tom Christensen and Per Laegreid,Autonomy and Regulation:Coping with Agencies in the Modern State,Cheltenham:Edward Elgar,2006.信息技术和跨部门协同的意义首次在这里被重视和强调。
整体性治理是以公民需求为治理导向,以信息技术为治理手段,以协调、整合、责任为治理机制的政府治理图式。(5)蔡娜、姚乐野:《“整体政府”治理理念下灾害信息资源协同共享途径研究》,《理论与改革》2015年第2期,第91-95页。在公共管理实践中,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智能技术为支撑的跨部门协同治理实践越来越多,智慧技术+跨部门协同日益成为整体性治理的主要模式。(6)应验:《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与共享社会建设:海南的举措和探索》,《电子政务》2019年第6期,第84页。整体性治理的过程充分体现了政策协同的理念,强调政府部门间政策目标的连续一致、政策执行手段的相互强化,关于整体性治理的改革甚至被称为“政策一致性”改革。(7)顾玲巧、余晓、卢宏宇:《基于政策协同的政府整体性治理水平测度框架分析》,《领导科学》2020年第20期,第20页。在技术推动的整体性治理改革中,地方政府面临的挑战主要与行政过程再造、项目管理、目标和责任界定等政府内部各部门、各层级之间的协调问题有关。(8)Ales Groznik & Peter Trkman,“Upstream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in E-Government:The Case of Slovenia”,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Vol.26,No.3,2009,pp.459-467.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口岸管理领域。
(二)口岸管理现代化的基本维度
整体性治理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为政府部门间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口岸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可行思路。解决口岸治理难题需要技术方案,而技术运用亟需口岸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保障。其中,管理体制的保障主要体现为通过口岸管理职能整合和监管流程再造所实现的口岸管理机构改革,运行机制表现为在口岸管理过程中搭建各种类型的跨部门协同机制来实现口岸管理过程的智慧化。
整合(integration)是整体性政府的本质内涵,主要涉及口岸管理组织结构整合、口岸通关业务流程整合、口岸政务信息资源整合和口岸公共服务供给整合(参见表1)。在《2009-2014年战略规划》中,美国海关与口岸保护局(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简称CBP)就引入“整体性治理”理念,强调要加强多方合作,大力拓展海关管理的时空和资源。口岸管理现代化关注如何依据包括企业在内的口岸使用者及运营主体的实际需求重建口岸管理部门,建立更加灵活的跨关境、跨部门、跨层级的协调机制,在口岸管理部门之间实现信息共享,为口岸活动主体提供“一站式”服务。口岸执法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是跨部门协同执法的必要前提。信息共享使各口岸执法部门能够进行联合或者独立监管。(9)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编译:《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上册),中国海关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基于互联网的智能化口岸通关流程与管理平台使得基于整体性治理理念的口岸管理现代化成为可能。

表1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口岸管理现代化的基本维度
二、口岸管理现代化的起因
口岸管理现代化的兴起有着深刻的理论动因、组织动因、经济动因和技术动因。从理论动因看,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兴起与发展为口岸管理现代化提供了理论依据;从组织动因看,口岸管理现代化是整合口岸管理机构、推动口岸监管流程再造、增进口岸监管部门合作的需要;从经济动因看,减费降税、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是口岸管理现代化的经济诱因;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电子政务的演进,从技术层面实现了口岸监管流程的再造和跨部门、跨层级的信息共享和跨关境的信息交换,为口岸管理现代化提供了技术支撑。
(一)组织动因:“政府再造”运动的兴起与政府监管流程的重塑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兴起了一场“政府再造”运动。政府再造不是简单的组织再造和重组,而是对政府治理的理念、原则、结构、行为等进行大规模改革,以提高政府的绩效和服务的品质。企业流程再造理论被引入政府管理领域,形成政府流程再造理论,强调以公民需求为核心,对政府部门原有的组织架构、服务流程进行全面重组,优化政府内部决策与执行过程,提高政府绩效,并得到更多公民的认可和满意。(10)姜晓萍:《地方政府流程再造的基础理论与现实意义》,《中国行政管理》2006年第5期,第37-41页。流程再造以强调客户满意、绩效提升为最终目标,对各个子流程、环节进行再审视,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对子流程、环节进行改造与重塑,增添必要的流程环节,删除冗余与流程降效环节,建立全新流程导向与业务架构,实现运营成本降低、运营效率提升、运营效益提高、客户满意度提升。(11)彭东辉:《流程再造教程》,航空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2页。
信息技术的运用不断塑造着政府内部流程,各级政府部门也不断尝试运用新兴信息技术实现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与整合以及政府内部流程的再造。口岸管理现代化的关键是对口岸通关流程的再造,即运用新技术改变现有的口岸管理组织结构和口岸通关业务流程,使其为实现口岸管理职能转变和管理模式的创新提供技术支持。流程再造着眼于对既有的口岸管理流程、运营流程的精细化拆分,寻找口岸通关中存在的问题,旨在删除无益环节、增添缺失环节、优化口岸监管流程。加拿大的移民、检疫等口岸查验部门不在口岸现场进行检查,而是由海关“一口对外”(one face at the border),代替行使移民、检疫的查验职能,当海关在口岸查验发现非法情况时,移交给相关的移民、检疫等查验部门进行相应处置。
(二)经济动因:经济全球化与贸易便利化的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贸易快速增长,全球进出口贸易总额急剧增加,经济全球化趋向深度发展(参见图1)。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以及商界越来越关注各种贸易管理程序的合理化,希望减少和消除“贸易的非效率”“隐形”的市场壁垒,减少和消除货物、资金等要素跨境流动的障碍,降低交易成本,建立便捷、协调、高效的国际贸易程序以实现贸易便利化。世界银行认为,贸易便利化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必要因素。(12)World Bank,“Trade and Transport Facilitation-a Toolkit for Audit,Analysis,and Remedial Action”,Research Report,p.5.1982年,欧洲工业家圆桌会议发现货车在欧共体内的口岸通关平均要接受80分钟的口岸检查,导致每小时增加36-48美元的成本。1988年“切克奇尼报告(Cecchini Report)”(13)1986年欧共体在经济暨财政事务总署内专门成立由意大利经济学家保罗·切克奇尼(Paolo Cecchini)任主席的“非欧洲代价”项目委员会,从事欧洲经济一体化理论和学术研究。1988年委员会发布了“1992年欧洲的挑战”,史称“切克奇尼报告”,对20世纪90年代欧共体内部市场进行剖析,研究没有形成欧洲统一市场的代价。估计欧共体内部口岸查验程序每年带来的成本是100亿美元,占整个欧共体内部贸易额的2%,此外还有55亿美元的潜在贸易额因为通关程序复杂而被主动放弃。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估计,在口岸清关程序中节省的每一天可以将贸易额从1%增加到7%。(14)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AID International Border Agency Cooperation:A Practical Reference Guide”,2020.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过境货物和人员数量激增,欧盟面临巨大的口岸管理压力;在节假日等高峰时期,每天有10万人进出英国,每年约有9亿人次进出前联邦德国,三分之一的荷兰人在暑假时外出度假。随着欧洲单一市场的扩大,更多的人员和货物需要在欧盟内部快速流动。(15)Alan Butt Philip,“European Border Controls:Who needs them?”,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Vol.6,No.2,1991,p.36.每天进出美国口岸的人员、货物和交通工具也在急剧增加;2010年,平均每天都有965167名旅客和行人、47293辆卡车、铁路和海运集装箱(16)On a Typical Day in Fiscal Year 2010,Feb.25,2011,http://www.cbp.gov/xp/cgov/about/ accomplish/previous_year /fy10_stats/ typical_day_fy2010.xml.以及 257990辆私家车进入美国。(17)U.S. Customs& Border Protection,Import Trade Trends:Fiscal Year 2010 Year-End Report 18 (2010),http://www.cbp.gov/linkhandler/cgov/trade/trade_programs/trade_trends/itt.ctt/itt.pdf。

图1 1990-2010年全球进出口贸易数据
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供应链中全球开发、全球采购、全球生产等模式应运而生,只有实现贸易的安全和便利,零库存、准时制等先进供应链管理方式才能为制造业等提供生产保障。而与之紧密相关的口岸管理体制和运作模式是能否实现贸易安全和便利化的关键环节。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外国投资全球竞争的兴起,各国日益意识到落后的、效率低下的口岸监管手续会增加贸易商的成本。另一方面,进出口商期待更迅速、更可预见的进出口通关程序,这也是私人部门在先进的物流和即时生产制度方面加大投资的结果。在关税壁垒和以许可证为代表的非关税壁垒日益消减的今天,为降低贸易成本、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各国的注意力更多转移到影响国际贸易的程序和单证要求方面。一般来说,一项贸易活动大约要进行60多项程序(参见表2);据国际商会统计,国际贸易中平均一票货物通关需要60多种单证,其中80%单证的主要内容都是相同的,复杂贸易手续引起的费用占交易货物价值的2.5-15%之间,尤其对中小企业而言,行政手续成本占总交易成本的比重甚至超过30%。(18)Carolin Eve Bolhöfer,“Trade Facilitation- WTO Law and its Revision to Facilitate Global Trade in Goods”,World Customs Journal,Vol.2,No.1,2008,pp.31-38.

表2 贸易程序类别及活动列举
由于快速获取他国进出口政策信息和减少市场进入的繁琐程序等贸易便利措施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交易时间的节约和交易成本的节省,给贸易商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贸易便利化成为世界各国所追求的共同目标。贸易数据和文件要求的简化和协调对减少国际贸易交易的时间和成本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区域贸易协定的蔓延,使海关工作更复杂,进出口企业对贸易便利化的需求更加强烈,迫切需要通过简化程序提高口岸通关效率。2013年12月,世界贸易组织巴厘部长级会议上通过了《贸易便利化协定》;这是中国入世后参与并达成的首个多边货物贸易协定,已于2017 年2月正式生效。《贸易便利化协定》第8条“口岸机构合作”(border agency cooperation)条款规定“世界贸易组织要求其成员国负责口岸监管的机构相互合作并协调其贸易便利活动”。据世界贸易组织估计,全面执行《贸易便利化协定》的规定,每年可使全球货物贸易出口值增加1万亿美元。(19)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USAID International Border Agency Cooperation:A Practical Reference Guide”,2020.如何妥善处理贸易安全和贸易便利的关系,做到既“管得住”又“通得快”已成为口岸管理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技术动因:信息技术的发展与电子政务的演进
信息技术是指应用信息科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信息产生、传递、处理的技术,具体包括有关信息的产生、收集、交换、存储、传输、显示、识别、提取、控制、加工和利用等方面的技术。信息技术包括微电子、电脑、电信、广播以及光电等集合而成的整套技术。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5G、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物联网等新科技的高速发展推动人们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悄然发生改变,打造智慧国家、数字政府成为趋势。邓利维认为:“信息系统几十年来一直是引发公共管理变革的重要因素,信息技术成了当代公共服务系统理性和现代化变革的中心。”(20)Patrick Dunleavy,New Public Management is Dead- Long Live the Digital Era Governance,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2006(3),p.467.信息技术革命引发政府改革,在口岸管理领域表现为信息技术运用于推进口岸管理改革和改进口岸政务服务。打破“碎片化”模式下口岸监管部门之间的组织壁垒,强化部门之间的合作和协调,促进信息资源共享,加强口岸监管服务方式和渠道整合,构建无缝隙、一体化的“整体性政府”成为口岸管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整合”是指组织功能上的协调与合作,是整体性政府改革中组织创新基本内涵的集中体现。(21)谭海波、蔡立辉:《“碎片化”政府管理模式及其改革——基于“整体型政府”的理论视角》,《学术论坛》2010年第6期,第32页。构建整体性政府需要从组织架构、信息资源、业务流程、服务沟通渠道等方面加以整合。信息技术的发展与电子政务的演进对于口岸管理现代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只有将信息技术的应用与口岸管理体制改革有机结合起来,通过信息技术提升口岸监管部门的数字化管理能力,才能实现从口岸监管各部门、各行业根据不同需求的、各自为政的“蜂窝煤式”口岸管理向跨部门、跨行业领域、跨层级、跨区域、跨应用系统的口岸治理转型,从而实现口岸管理组织结构的重构、口岸通关业务流程的再造、口岸信息资源的共享以及口岸公共服务的跨部门供给。
(四)全球化的发展、口岸管理场域的演变与口岸保护职能的强化
朝仓弘教认为:“海关是政治组织为公共财政需要而设立的征税机关。”(22)[日] 朝仓弘教:《世界海关和关税史》,吕博等译,中国海关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从本质上而言,税收征管是海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一种方式。自古以来,安全不仅与人类的商品交换和贸易活动紧密关联,也与人类的疾病防治和生活保障紧密相连。国家安全是推动海关产生的根源和直接动因,维护国家安全是海关最基本的职能。2005年世界海关组织通过《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标准框架》,指出“海关在加强全球供应链安全、通过征收税款和便利贸易为社会经济发展作贡献等方面有着独特地位”,提出了保障供应链安全的两大支柱——海关与海关之间的合作和海关与商界之间的合作。2020年12月,美国海关公布《CBP战略2021-2026》,将美国海关的职责界定为“保护美国公众,维护口岸安全,强化国家经济繁荣”,(23)“CBP Releases 2021-2026 Strategy”,December 18,2020,https://www.cbp.gov/newsroom/national-media-release/cbp-releases-2021-2026-strategy。凸显了海关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重要角色。
在“9·11”事件前,国家安全和反恐在全球范围的海关内均非其主要任务和职责(24)Robert Ireland,“The WCO SAFE Framework of standards:Avoiding Excess in Global Supply Chain Security Policy” ,WCO Research Paper No.3,2009.。发达国家海关的监管重点在例如毒品和侵权品等违法货物上,部分国家海关尝试通过贸易便利化平衡业务量迅猛增长与一线监管资源不足之间的矛盾;发展中国家海关最重要的任务是税收征管,因为关税收入是这些国家政府开支的重要支柱。“9·11”事件后,发达国家海关工作的重心逐渐向国家安全领域倾斜,加大了口岸反恐的力度。(25)Alan D Bersin,“Lines and Flows: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Borders”,World Customs Journal,Vol.6,No.1,2012,pp.115-126.美国、欧盟、新加坡海关一方面不断健全国门安全风险分析和管理系统,一方面通过海关国际合作、与商界建立伙伴关系等方式开展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以维护国门安全。CBP通过实施“全球盾项目(Global Shield Programme)”(26)全球盾项目是指通过鼓励打击全球威胁的集体行动,监控可以用于临时爆炸装置非法生产的化学品扩散。“集装箱安全倡议(Container Security Initiative)”(27)集装箱安全倡议是CBP于2002年提出的一项旨在加强美国及全球海上运输安全的检查措施。美国海关向境外港口派遣关员,使用非侵入式查验和放射性探测技术,在集装箱装船前进行安全风险评估,其目的在于过把甄别货物安全风险和查验的环节前置在海运集装箱的出口港和转运港,防止恐怖分子利用海运集装箱藏匿运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美特大型港口计划”(简称“大港计划”)(28)大港计划通过在外国港口安装核辐射探测仪,美国把甄别货物安全风险和查验的环节前置在海运集装箱的出口港和转运港,防止核和其他放射性物质非法贩运。等,把美国的国门安全守护边界拓展至美国的国境之外。欧盟税务及海关同盟总司将“管理并保护欧盟统一的外部边界(external border)”确立为其主要职能之一。新西兰海关“2006-2010年海关成果目标”中的第一项内容就是“国门安全——提高海关的协同作战能力”。(29)陈晖:《国际贸易安全与便利:我国〈海关法〉面临的新课题》,《国际贸易问题》2008年第8期,第120页。虽然发展中国家海关仍以税收征管职能为主,关税及其他进口环节税在国家税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在组织隶属关系上这些国家的海关往往隶属于财政部门;但在发达国家,海关主要以安全准入职能为主,(30)David Widdowson,“The Changing Role of Customs:Evolution or Revolution?”,World Customs Journal,Vol.1,No.1,2007,pp.31-37.重在实施禁限措施。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从1972年到2019年,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关税及其他进口环节税在政府收入中所占比重都在降低,在部分发达国家甚至降为0(参见表3)。近年来,特别是继美国之后,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整体考虑,海关陆续从财政部转隶至国内安全部门或内政部,如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等,海关维护国门安全的职能日益凸显。

表3 1972、1995和2019年部分国家关税及其他进口环节税占政府收入的百分比(%)
国门是海关维护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场域,维护国门安全是海关的根本职能。各国之间相互联系、互相依赖,构成国门安全复合体,在“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的过程中呈现出由冲突形态向安全机制转型的趋向。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以及国与国之间相互依赖日益增强的今天,伴随开放而带来的走私、涉枪涉爆及卫生、健康、环保等非传统安全风险日益增加。口岸的主权性、开放性、国际性和国门安全风险源的多样性导致国门安全风险的流动性、衍生性、外溢性和不确定性。国门安全的内涵与外延日益拓展,海关维护国门安全面临监管时空前伸后延、监管对象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治理体系碎片化、治理目标冲突化的新挑战。2014年11月,《海关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中国海关需要正视非传统安全所带来的威胁,拓展视野,及早布局,开展基于安全准入问题的研究。2018年3月,《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出入境检疫管理职责和队伍划入海关总署”,中国海关新增“出入境检验检疫职能”,“海关口岸监管范围扩大,维护国门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31)倪岳峰:《努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海关》,《求是》2018年第20期,第32页。中国海关既面临着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叉重叠“全域安全”维护需求与国门安全维护能力不足的困境,更面临兼顾国门安全管控与促进贸易便利化的双重目标。2021年6月,中国海关总署发布《“十四五”海关发展规划》,将中国海关“坚决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能职责独立成章,就海关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以风险管理为主线的国门安全防控体系、全面履行监管职责作出详细部署,从强化进出境实货监管、确保税收安全、维护口岸公共卫生安全、严格进出境动植物检疫监管和外来入侵物种口岸防控等八个方面提出具体要求,筑牢国门安全防线。
三、理解口岸管理现代化的内涵与关键要义
(一)口岸管理现代化的概念与内涵
以往的口岸管理改革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所有的口岸执法部门虽然都在处理相似问题,但它们之间没有协调和配合;二是口岸管理改革仅仅关注海关改革,忽视其他口岸监管部门在海关改革以外口岸执法管理领域进行变革的需要。上述问题直接导致口岸管理改革的努力被重复、资源被浪费,口岸管理改革成效很不理想。口岸管理现代化以“整体性治理”理念为指导,通过口岸执法管理改革实施一种新的、更全面的贸易便利化方法。与注重改善海关业务的传统口岸管理改革相反,口岸管理现代化既重视海关改革也触及海关以外的领域,其范围更加广泛。(32)Gerard McLinden,Enrique Fanta,David Widdowson,Tom Doyle,eds.,Border Management Modernization,The World Bank,2011,p.1.
口岸管理的具体内涵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指为确保人及物合法跨境的监管程序,二是指各口岸执法部门如何组织起来适应一个统一的口岸执法理念,三是供这些部门使用的口岸基础设施如何设计和管理。有效的口岸管理(effective border management)不仅能够确保跨境的人员、货物和交通工具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监管程序,守法的使用者能享受便利的监管服务,而且能够及时发现违法者并加以阻止。全球化态势下,国家、次国家、超国家行为体的联系日益紧密,全球范围内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的规模与层次迅速延伸,国门安全风险借由全球化带来的世界性人口流动与要素传播更加频繁地跨越国境,口岸管理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发布的《国家生物防御战略》中认为“哪怕是发生在世界最遥远地方的传染病暴发事件,也会快速传播至各大洲、各大洋,从而直接影响美国人民的健康、安全和繁荣。”(33)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Washington,D.C.,2018,p.2.
作为跨境物流、客流、信息流、资金流的交互节点,口岸不仅是口岸管理国际规则的交汇点,也是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的交汇点,需要以深化安全领域的合作为重点。一方面,国门安全风险的复合化、常态化和跨境传播特点要求口岸管理的协同化,另一方面,口岸管理中的分权化、部门化和碎片化现象严重;现实困境以及参与全球治理的需要要求探索多元行为体共同参与的口岸协同共治机制。因此,口岸管理现代化强调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前提下,确保口岸运行安全和顺畅高效;既要维护口岸安全和国家安全利益至上,又要兼顾通关便利化,促进国际经贸合作和人员交往。因此,口岸安全与便利的平衡构成口岸管理现代化的双重目标,积极推行“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的口岸协作执法机制,优化口岸管理体制,整合口岸管理资源,提高口岸大通关效能,已成为口岸管理现代化的题中之意。(34)沈扬:《连接欧亚的国际联运大通道》,《学习时报》2014年11月3日,第11版。
(二)口岸管理现代化不仅仅是海关现代化
各国的口岸管理职能主要包括税收征管、运输与物流监管、贸易政策执行、维护健康与公共安全、维护国家安全等。(35)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编译:《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上册),中国海关出版社2016年版,第24页。上述口岸管理职能与海关职能存在高度相关性,海关发挥着牵头、参与、协商、通报等不同角色。然而,并非每个国家地区的海关都承担上述全部职能;在有些国家地区,其中某些职能可能不是海关的主要任务,而是政府其他部门的职责。2012年,世界海关组织发布《协调型口岸管理纲要》(Coordinated Border Management Compendium),强调海关与其他口岸执法部门之间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的合作与协同,提出必须围绕一个共同的愿景,将资源、职能、程序和立法调动起来,以实现有效的口岸管理。
口岸管理现代化不仅仅是海关现代化,我们以压缩货物通关时间为例,说明海关现代化改革与口岸管理现代化之间的差异。由于传统的口岸管理改革仅仅关注海关改革,人们倾向于把“整体通关时间”化约为“海关通关时间”。实际上,整体通关时间与海关通关时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货物整体通关时间是“从货物到达港口、机场、陆路边境开始,直至货物放行为止的时间”,包括海事、海关(包括出入境检验检疫)、理货、港务等单位办理验放手续时间,以及船代、货代、运输企业、报关企业、银行和其他社会中介机构办理手续时间。海关通关时间指“从海关接受企业申报至放行指令送达为止的时间”,包括海关审单、接单、查验、征税、放行等各环节作业时间以及此过程中的企业交单、缴税时间等。(36)2018年9月27日,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指出,整体通关时间是指货物抵港到货物允许提离整个进出口环节的时间,包括货物的抵港、装卸、堆放、理货、申报、查验、放行、提离等多个环节的耗时;海关通关时间是指货物从申报到放行,在海关的单一环节内的海关作业时间。参见《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2018年9月27日)》,中国政府网,2018年9月27日,http://www.gov.cn/xinwen/2018zccfh/35/。(参见图2)

图2 整体通关时间和海关通关时间图示
由图2可以发现,货物放行时间在很大程度上由口岸监管链上最薄弱的环节所决定,整体通关时间并非海关单独可以左右的;整体通关时间更取决于港口、物流机构的经营方式以及货主主动提离货物的意愿。因此,口岸管理现代化不仅仅是海关的任务,提升整体通关时效应当从口岸管理领域着手。各国政府逐渐认识到,传统的口岸管理改革通常集中于海关领域,但绝大多数国家的口岸都是多个部门单独执行的管理体制和多部门共同参与的通关机制。2018年,一份由上海海关、上港集团联合第三方机构进行的调研报告显示,从货物抵港到货物提离港区的总平均用时中,向海关申报到海关放行仅占比8.7%,九成以上时间消耗在前段和后段——从船舶抵港到向海关申报占比54.5%,从海关放行到货物提离港区占比36.8%。(37)《上海通关时效海关占比仅8.7%》,解放日报网,2018年5月20日,https://www.jfdaily.com/news/detail?id=90148。实践证明,改善口岸通关环境,需要除海关以外的其他口岸部门共同努力才能取得实效;对口岸作业效率提升的关注重点应该由原来的通关扩大到报关前和放行后的各个作业段,在继续优化通关制度,缩短通关时间的同时,通过突出瓶颈问题的整治和整体协调协同协作来实现提高口岸整体作业效率的目标。因此,许多国家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分别在口岸管理体制机制上推行合作化、协同化甚至一体化的改革,或是通过口岸国际合作来提高口岸通关效率。
一是在口岸执法机制的合作化上,许多国家的海关、边检和检验检疫等口岸执法部门建立了与商界和跨境人员之间的广泛合作机制和伙伴关系,形成执法与守法之间的良性互动,实施“经认证的经营者(AEO)”和“受信旅行者(Trusted Traveler)”计划,提倡守法便利,应用风险管理技术,提高执法效能和效率。欧盟《现代化海关法典》第26、27条规定,海关应努力协调与税务、边检、警察、动植物检疫、环保等部门之间的关系,协同监管进出境货物,尽可能为其提供一站式服务(one-stop service)。(38)Article 26,Cooperation between authorities,Regulation (EC) No.648/2005 of The European Pari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Amending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2913/92 establishing the Community Customs Code”,13 April 2005.《欧盟海关法典》强调“部门间的合作”,提出“如果海关当局以外的其他主管部门对同一货物实施了海关监管措施以外的其他监管措施,海关当局应与这些其他主管部门紧密合作,尽可能在与海关监管措施相同的时间和地点实施其他监管措施(一站式作业);为实现这一做法,海关当局应发挥协调作用”。(39)海关总署国际合作司编译:《欧盟海关法典》,中国海关出版社2016年版,第31页。截至2022年2月28日,中国海关已经与韩国、新加坡、欧盟等22个经济体共48个国家(地区)签署AEO互认协议。(40)《中国-乌拉圭海关AEO互认实施助力中乌进出贸易更加安全便利》,海关总署网,2022年2月28日,http://www.customs.gov.cn/qgs/zwdt61/4205686/index.html。
二是在口岸管理的协同化方面,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口岸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各部门之间加强了信息共享,有的国家在此基础上进行口岸执法流程再造,一次申报、共同查验甚至部门之间代行职权、互派人员等实践大大提高了口岸执法的整体效能,方便了旅客和进出口企业。海关与其他政府部门之间应加强信息沟通,对货物的进出境转运、仓储、最终用途、邮政运输、关境内移动等进行充分的信息交流,以防控通关程序简化后的口岸管理风险。2014年,国务院成立口岸工作部际联席会议,(41)《国务院口岸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国函[2015]97号),中国政府网,2015年6月5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6/15/content_9847.htm。各成员单位通过签署合作备忘录等形式深化执法互助,海关与公安、海事、税务、工商等部门就反恐、反偷渡、打击骗退税以及查处逃避贸易管制等安全议题开展了密切合作。
三是在口岸管理体制和口岸执法机制的一体化方面,一些国家通过口岸各执法部门的机构重组和职能整合,减少口岸管理部门的数量,建立了一体化的口岸管理体制。尚不具备这种条件的国家,也通过合署办公、单一窗口等先进做法实现了口岸执法机制的一体化。(42)黄胜强:《借鉴国际口岸管理最佳实践,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口岸国际合作》,《国际贸易》2019年第4期,第14-15页。截至2021年底,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已与25个部委实现“总对总”系统对接和信息共享,对外提供18大类、729项服务,基本实现口岸执法服务功能全覆盖。
四是在口岸国际合作方面,很多国家或地区采用了信息互换、执法互助和监管互认以及“一站式”国际口岸(one stop border posts)等形式。其中“一站式”国际口岸,即两个接壤的国家或地区的口岸在地理上并排设立,货物和人员跨境时只在一个地点办理通关手续、一次停留,而不再像过去那样分别在出境国家和进境国家停留两次。国与国之间的口岸信息互换、执法互助和监管互认,可以使跨境贸易商和旅客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和一次放行。口岸国际合作的开展需要依靠两国间或多国间以及国际组织间达成的法律框架或合作协议,合作的表现形式可以是政策公告、谅解备忘录、双边或多边协议。口岸国际合作主要机制可分为三种:地方层级的边境口岸合作或直属海关层级的关际合作、双边口岸国际合作和多边口岸国际合作(参见表4)。关际合作主要是指直属海关与我国非毗邻国家地方海关开展合作,如上海、广州、宁波、南宁等11个直属海关开展的关际合作;边境口岸合作主要是指直属海关与我国陆路接壤国家海关开展的口岸合作,如哈尔滨、乌鲁木齐等沿边海关与我国陆路接壤的11个国家海关开展了边境海关检验检疫国际合作,满洲里海关和长春海关与俄罗斯、蒙古、朝鲜三国开展边境口岸合作,乌鲁木齐海关构建的中哈、中塔、中吉三国四线的口岸农副产品“绿色通道”运行体系。

表4 口岸国际合作机制的分类与实践
口岸国际合作的主要内容,既包括税收征管、联合执法等传统业务领域的合作,也包括出入境检验检疫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9·11”事件后,随着美国将国家安全战略向打击恐怖主义转移,中美海关合作逐步超越了贸易便利化的传统合作范围,开始将重心向维护供应链安全、公共卫生安全、联合打击跨国犯罪、防止核武器扩散等任务转移,在合作项目中增加了关于强化贸易安全、防止核及其他放射性物质运输和打击武器贩运等有关内容。美国海关与加拿大海关开展合作,提出了大陆边境线“边缘安全”的概念,内容涵盖多个方面,如交换监控人员名单、实施入境港的双向咨询、开展陆路货物预放行和在入境港实施联合执法行动。美国海关与墨西哥海关的合作主要围绕共同打击跨境贩毒集团违法犯罪活动;2001年,美国与加拿大签署《智慧口岸宣言》;2002年,美国与墨西哥签署《口岸合作伙伴关系协定》,旨在通过双边合作和技术手段将美墨双边口岸建成面向21世纪的智慧口岸。(43)王吉美:《9·11后美国边界安全政策变化研究》,外交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74页。泰国海关和老挝海关于2005年7月签订谅解备忘录,提出“在泰国莫达汉和老挝沙湾拿吉口岸实施一站式查验监管,简化货物和人员的过境手续”。“十三五”期间,中国建立并巩固了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越南等国家口岸管理部门之间的口岸国际合作长效机制,推进修订中俄、中哈、中蒙等两国政府间边境口岸管理协定。(44)《国家“十四五”口岸发展规划》,海关总署网,2021年9月17日,http://shenzhen.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zfxxgk/zfxxgkml34/3896488/index.html。“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中国开展口岸国际合作的重点,合作内容包括加强执法机构情报交流、联合执法、联合反恐和检验检疫合作,以及打击跨境毒品、枪支、濒危、废物走私和商业瞒骗活动;中国海关已与沿线三十多个国家进行疫情口岸防控经验交流,与俄罗斯、老挝、缅甸、新加坡等国签署了国境卫生检疫合作协议;与柬埔寨、新加坡、缅甸等国建立了应对疫情紧急热线联系机制。(45)《海关总署:建设智慧海关,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光明网,2020年10月13日,https://m.gmw.cn/baijia/2020-10/13/1301666513.html。
四、口岸管理现代化的主要实践
口岸管理现代化覆盖对口岸管理体制(内涵口岸管理机构改革和职能整合)、行为方式(口岸通关监管流程再造)和管理技术(信息共享平台、风险管理技术)的改革,主要实践包括口岸执法机构改革、风险管理技术和信息通讯技术的运用、单一窗口与口岸监管流程再造、加大口岸基础设施投资等,以促进口岸管理组织结构整合、口岸通关业务流程整合、口岸政务信息资源整合和口岸公共服务供给整合,实现跨境贸易便利和维护国门安全的平衡。
(一)口岸执法机构改革与口岸管理组织结构整合
经济全球化及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促使货物、服务、人员、信息及技术等快速流动,这既推动了经济发展,也衍生了非法贸易和跨国犯罪的危险。对此,一些国家基于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门安全的考虑,通过对海关等口岸执法机构进行改革来整合口岸管理职能,进而提升口岸监管效率。职能整合与口岸通关流程再造是口岸管理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国外口岸管理主要遵循“海关管物、移民局管人”的原则,通过口岸执法机构重组和跨部门执法合作,实现口岸通关流程再造和减少口岸管理成本。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已经采取由一个综合执法部门统一履行进出境口岸监管职责。
“9·11”事件引发了美国对国土安全(Homeland Security)的担忧。2003年3月,美国改革口岸管理体制,设立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它是由在美国政府中先前分别设立的22个部门合并而成。(46)History:Who Became Part of the Department?,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http://www.dhs.gov/xabout/history/editorial_0133. shtm.其中,负责口岸管理事务的4个机构分别是原隶属于美国司法部的负责管理计划合法或非法进入美国境内人员事务的海岸警卫队和移民及归化局、隶属于美国财政部的负责管理货物进出口的海关与口岸保护局,以及隶属于美国农业部的负责处理农业虫害及对美国农作物的潜在生物入侵的农业检验局。(47)The Future is Now,U.S. Customs Today (Feb. 2003),http://www.cbp.gov/xp/CustomsToday/2003/February/future.xml.隶属于国土安全部的CBP主要负责全美的口岸保护,重点是反恐、保障和便利货物和人员安全进出境、执行移民政策、打击毒品等职能。CBP的成立,实现了美国口岸管理的一体化,突出口岸保护职能,使海关成为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部门之一;从全球来看,第一次实现了移民、海关和农产品检查的职权(48)CBP还同时是其他40个联邦机构的唯一执行机构,这些机构承担着对进出境的人员和货物进行监管的职责。这些机构主要包括:食品药品署、环境保护署、消费者食品安全委员会和交通部。统一由同一名执法人员来行使,而这名执法人员是为了一个以安全为首要使命的单一机构工作的,创造了联合口岸管理体制(Joint Border Management)。(49)Alan D. Bersin:“Lines and Flows: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Borders”,World Customs Journal,Vol.6,No.1,2012,pp.115-125.2019年4月,CBP公布《CBP2020-2025战略》,将美国海关定位为“保卫美国口岸,维护口岸安全和公众安全,促进合法贸易和旅行,提高美国在全球经济的竞争力”。
加拿大口岸服务局(Canadian Border Service Agency,简称CBSA)整合了多个参与货物流通、人员出入境监管的口岸管理机构,承担的职能过去是由以下三个机构分别负责:海关与税务局(the Canada Customs and Revenue Agency)负责的海关管理,公民与移民管理局(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负责的情报、查禁和执法领域,食品监察局(Canadian Food Inspection Agency)负责的进口货物查验。CBSA也是2003年制定的加拿大公共安全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旨在协调管理所有负责国家安全、突发事故管理、执法、处罚、犯罪防御和口岸服务的联邦部门。
英国自21世纪初开始推出了一系列口岸机构改革举措。2005年,英国政府合并在口岸上的海关和移民两大职能机构,整合英国财政部、英国海关、英国税务局,成立皇家税务与海关署(HMRC),隶属财政部。2008年,英国将口岸和移民局、签证部门和皇家税务与海关署的调查职能归入口岸管理署(UKBA)下,隶属内政部。从2007年“英国口岸法案”(UK Borders Act)到2008年“英国国家安全战略:独立世界的安全”(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Kingdom:Security in an independent world),再到2009年“英国国家安全战略:下一代安全”(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Kingdom:Security for the Next Generation),都强调了加强口岸监管作为英国国土安全政策核心原则的承诺。2012年,口岸执法部队(Border Force)从口岸管理署分离,成为内政部下一个独立操作指挥中心,负责移民和海关职能,同时撤销口岸管理署。口岸执法部队的主要职责包括维护口岸安全,防止高风险货物进入英国境内,加强国际合作,便利货物和旅客合法进出。此外,它还承担替皇家税务与海关署征收关税及其他进口环节税的任务。英国口岸执法部队还设有两大指挥中心:一是位于伦敦的全国操作指挥中心,主要处理诸如恐怖袭击的紧急事件、运作部署等事务;二是海关业务局,主要负责设定海关监管战略方向,负责和皇家税务与海关署、港务、运输企业、航空公司的联络事务。
2014年5月7日,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将澳大利亚海关和口岸保护局(Australian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Service,简称ACBPS)以及移民和口岸保护局(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Border Protection,简称DIBP)整合为一个政府部门;2015年7月1日,新的移民和口岸保护部成立。同日,澳大利亚口岸执法署(Australian Border Force,ABF)正式组建,成为DIBP的执行部门。DIBP的职权范围包括贸易和海关、近海海事安全和税收、难民和人道主义方案、移民和公民身份认证等。新机构成立后迅速出台了《2020行业参与战略:贸易、海关和旅行者》(Industry Engagement Strategy 2020:Trade,Customs and Traveller),将口岸安全置于至高的位置,强调保护和管理澳大利亚的口岸,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在其四个具体目标——国家安全维护、高效移民管理、促进贸易和税收、口岸管理创新中,国家安全维护被置于首要位置。其中,国家安全保护的重点内容包括:实现口岸安全风险防控,有效识别和管理移民和货物风险;优化法律体系和简化相关手续,便利货物进出境;与相关部门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扩大新技术运用,创新人员能力建设和培养机制,建设高效、精干的人员队伍等。2017年12月20日,DIBP与联邦警察、国家安全部等部门合并,成立内政部(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简称HA),履行DIBP先前承担的移民和口岸保护职能。
整体而言,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口岸管理体制改革的趋势是朝向大部制演进,这和新公共管理运动、整体性治理理念的兴起密切相关,主张通过协调合作来提高口岸管理水平及口岸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口岸管理职能整合是口岸管理机构改革的重要前提;口岸管理现代化要求实现跨部门的口岸通关流程再造、信息共享和权力重构,口岸管理体制改革中的关键问题是口岸各部门之间的跨部门协同议题。大部制改革需要考虑机构合并的成本,监管权力过于集中也可能会带来监管俘获的风险,(50)刘亚平:《中国式“监管国家”的问题与反思:以食品安全为例》,《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2期。跨部门协同机制的建构需要避免监管协调机构虚化和重叠的倾向。
(二)单一窗口、风险管理与口岸通关业务流程整合
简化贸易程序和减少贸易单证要求已成为当前贸易便利化的关键内容。2013年12月,世界贸易组织第九届部长级会议上达成“巴厘一揽子协定”,其中一条专门对“单一窗口”制度做出规定,要求“成员国应尽力建立或者维系‘单一窗口’,允许贸易商通过单一入口提交进出口或转运货物所需的单证或资料”。2017年2月,随着《贸易便利化协定》正式生效,“单一窗口”已经成为许多国家政府促进贸易便利化、简化手续和实施电子商务的重要政策工具。“单一窗口”建设涉及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包括有贸易商、生产商、物流商、供应商、口岸监管机构等。“单一窗口”建设的核心是改革口岸管理运行机制,统一口岸输入输出机制,使得跨国贸易的利益方只需向一个窗口(海关)提交事先公布并标准化的单证即可完成大部分通关手续,避免跨国贸易利益方的一单多递和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行为的重复。(51)曾文革、江莉:《〈贸易便利化协定〉视域下我国海关贸易便利化制度的完善》,《海关与经贸研究》2016年第1期,第7页。近年来,“单一窗口”已成为诸多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海关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和国家(52)包括欧美国家、澳大利亚、日本、韩国、东盟10国,以及南美的哥伦比亚、危地马拉、秘鲁,非洲的毛里求斯、加纳等国都采取了这一措施。优化口岸通关模式、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的重要实践。
在国际上,风险管理已成为各国口岸管理部门应对形势和挑战、化解矛盾和压力、预防和分析危机事件的共同选择。国外口岸安全风险评估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风险评估机制和流程,并将风险管理作为口岸管理的常态和主要手段。FTA故障树分析法、(53)FTA故障树分析法(Fault Tree Analysis)是指首先选定某一影响最大的系统故障作为顶事件,然后将造成系统故障的原因逐级分解为中间事件,直至把不能或不需要分解的基本事件作为底事件为止,从而得到了一张树状逻辑图,称为“故障树”。ETA事件树分析法(54)ETA事件树分析法(Event Tree Analysis)源于决策树分析,是一种按事故发展的时间顺序由初始事件开始推论可能的后果,从而识别危险源的方法。这一方法以初始事件为起点,按照事故的发展顺序,分阶段逐步进行分析,每一事件可能的后续事件只能取完全对立的两种状态(成功或失败、安全或危险等)之一的原则,逐步向结果发展,直到达到系统故障或事故为止。等风险评估方法被引入口岸管理领域。1997年,世界海关组织将风险管理纳入“京都公约海关监管指南”,作为简化和协调海关手续的一项具体措施。(55)孙毅彪:《海关风险管理理论与应用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世界海关组织将风险管理列为《21世纪海关战略文件》中十大重点工作的第三项,并在推动成员应用风险管理技术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包括制订了供各成员国参考使用的《风险管理汇编》。为在贸易便利和法律监管之间达到平衡,各国海关大都摒弃其传统的 “关口”检查,引入风险管理原则。(56)[比]Luc De Wulf、[巴]José B. Sokol主编:《海关现代化手册》,上海海关翻译小组译,中国海关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以世界海关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海关界通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认为直接加强对风险载体(如货物生产者、运输者、进出口商等)的监管和管理是防控风险的关键。需要指出的是,风险管理主要是为了解决“单货相符”和“能不能进(出)口”问题,即通过X光机、核辐射检查仪器等物流检查设备和人工开箱查验等“见货”方式来验证舱单申报数据的真伪,所以其主要适用于涉及安全、健康、环保等方面的非涉税风险,如查缉武器、危险化工品、毒品、侵权货物以及废物垃圾等。对于涉税的技术性验估类风险,如归类、估价等方面的风险在这一环节难以完全通过查验解决。
(三)信息技术的运用与口岸政务信息资源整合
进入21世纪以来,以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迅速发展,推动人类社会迈向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时代。信息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赋予了政府再造整体性政府的可能性。(57)Richard Heeks,Reinventing Government in the Information Age:International Practice in IT-Enabled Public Sector Refor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9,pp.9-21.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空间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是智慧政府的六大关键技术;其中,物联网采集数据,云计算处理数据,移动互联网传输数据,大数据挖掘数据。(58)金江军编著:《电子政务理论与方法(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97页。传统的口岸管理无法有效应对口岸管理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为智慧口岸治理的实现和口岸管理现代化提供了技术支撑(参见表5)。美国海关对新技术的运用贯穿整个业务流程,从货物与旅客入境前的筛选、审查,到入境后相关信息的维护、监控,再到出境时的审查。2021年,第四届进博会期间,上海海关首次运用AR眼镜、数字标签等新技术开展展品监管。(59)《保障更精细、品牌更响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9日,第10版。

表5 新一代信息技术及其在口岸管理中的运用
第一,物联网(The Internet of Things),简言之,就是“物物相连的互联网”。物联网通过智能感知、识别技术与普适计算、泛在网络的融合应用,被称为世界信息产业发展的第三次浪潮。物联网因其网络化、精细化和智能化的工作特性,有助于创新监管模式,改进业务流程,推动海关实现集约式发展。物联网在海关的应用主要表现为:一是实现单货的“关联化”,确保信息流对实际物流形成有效的牵制作用,提升海关监管效率;二是实现监管的“实时化”,当货物或集装箱的电子标签和无线网络传输结合后,海关可以随时掌握货物的实时状态,一旦出现集装箱被非法打开等情况,系统会自动报警,运输途中的违法行为将不再可能发生。(60)参见朱孔嘉:《海关业务工作的八对主要矛盾及基础建设方向》,《上海海关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第34页;吴非:《应用物联网技术加强海关出口公自用物品监管的可行性研究》,《上海海关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第98-102页。
在口岸监管中,对于海关,物联网技术可以应用于车辆通关自动核放、电子关锁、电子围网、海关物流监控等方面。2002年,深圳海关建立公路口岸车辆自动核放系统,该系统主要应用RFID技术,集成电子车牌、司机识别卡、电子地磅、电子栏杆、地感线圈、红绿信号灯、声音报警、LED显示、防闯关路障、红外感应、GPS和电子关锁通信设备多项数据采集传感器和末端设备,该系统把以前每辆车的通关时间由2分钟缩减到了5-6秒,避免了堵车现象。2009年6月,深圳海关辖下的盐田港与黄埔海关辖下的车检场在广东省内率先启用电子关锁卡口联网,两地卡口联网试点车辆逐步推广使用电子关锁。深圳海关还通过综合运用电子关锁、GPS等技术手段实现了区域间的物流严密监控,建立起电子围网。(61)金江军编著:《电子政务理论与方法(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05页。对于出入境检验检疫,物联网技术可以运用于进出口食品安全溯源等方面。对于边检,物联网技术可以用于出入境管理,如公安部推出的“电子护照”。
第二,云计算(Cloud Computing)是网格计算、网络储存、负载均衡等技术发展融合的产物。“云”其实就是将资源进行整合后提供给用户的网络。云计算在海关领域的运用有助于实现布局的“虚拟化”,海关的物理布局将不再受到地域限制。云时代的理念就是把产品直接变成一种服务,集中储存信息资源让每个人都可以分享使用,实现海量信息存储共享、海量数据的运算应用、海关管理资源的整合集成,进而实现应急指挥、业务监控、风险防控的目标。(62)吴非:《“云存储”助力构建海关报关单证电子档案库》,《上海海关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109-115页。
第三,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是在计算机硬、软件系统支持下,对整个或部分地球表层(包括大气层)空间中的有关地理分布数据进行采集、储存、管理、运算、分析、显示和描述的技术系统。美国海关将地理信息系统应用于西南边境,用来追踪非法移民的路线,以使有限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得到更好的配置。
第四,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为推动口岸管理改革提供了技术支撑,各个口岸监管部门以数据共享为支撑、新技术运用为手段,着力打造智慧口岸。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以及5G信息通信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急剧影响、颠覆并重塑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63)P K. Agarwal,“Public Administration Challenges in the World of AI and Bots”,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Vol.78,No.6,2018,pp.917-921.随着网络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兴起,国门安全风险的复杂性使得治理的难度日益加大。大数据的海量数据来源和多元分析技术有助于实现国门安全风险的精准识别、准确评估、实时预警和有效防控,推动国门安全风险治理从传统的“撞击-反应式”应对模式向数据驱动模式转型,从“经验治理”向“数据治理”“智慧治理”转变,加快构建覆盖供应链全过程的海关风险防控体系,发挥好风险防控中心、税收征管中心统一防控的优势,综合运用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企业等各方面的数据信息开展风险分析。(64)倪岳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坚定不移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在海关落到实处》,《人民论坛》2018年第1期,第7页。从总体上看,大数据技术驱动口岸管理改革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深圳口岸着力用先进技术打造智检模式,将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移动互联、感知识别、快速检测、智能装备等科技和信息化手段大量应用于智慧口岸建设。2016年4月25日,杭州海关对外通报了一起海关与电商平台联手查获的互联网跨境电子商务出口侵权案件,这是全国首起应用大数据分析查获的互联网跨境渠道出口侵权案件。(65)《杭州海关运用大数据查获互联网跨境侵权案》,海关总署网,2016年4月26日,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xwfb34/302425/367313/index.html。2020年,上海海关推广应用大数据平台供应链安全评估模块,运用大数据对货物从发货到收货的全过程全链条实施安全风险评估,将海关风险分析处置从进出口环节向供应链全程延伸,给予安全供应链货物最大程度通关便利。(66)《大数据分析无干预通关守法企业最便利》,《科技日报》2020年8月19日,第4版。
第五,人工智能是一种模仿人脑构建的计算机系统,可自我学习。在智慧海关中人工智能技术主要用于提高对各类风险目标的识别范围和精度以及自动化处置能力,提高智慧海关的执法作业的生产率。通过智能审图技术,将集装箱图像的识别从分钟级降至秒级,帮助海关对监管目标物更为精准、快速的智能识别,减少一线监管强度。智能审图系统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海量机检图像及图像对应货物物品信息的学习,形成对大型集装箱检查设备(H986)、CT机等机检图像的自动识别系统海关采用远程集中判图、智能辅助审图算法等技术和海关智能查验台建设,对入境托运行李远程检查、自动布控、智能拦截,实现绝大多数守法旅客的无感通关。2020年,青岛海关集中审像中心完成机检审图超10万幅,“智能审图”覆盖率超过98%,通过“先期机检+智能审图”移交风险线索1000多条,接连查获走私固体废物、夹藏化妆品等案件。(67)《青岛海关进出口货物查验进入智能模式,“智能审图”覆盖率超过98%》,中华网,2021年2月1日,https://tech.china.com/article/20210201/20210201707613.html。2021年,黄埔海关通过“智能审图+人工查验”方式查验进出口集装箱8.6万标箱,同比增长四成以上,拦截固体废物267吨,同比增长近45倍。(68)《既要管得住、又要通得快——黄埔海关深化“智慧海关”建设提升监管效能》,海关总署网,2022年月21日,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ztzl86/302414/302415/gmfc40/2813466/4270075/index.html。截至2021年6月,智能审图系统已覆盖主要大型集装箱/车辆检查设备和CT设备,累计实现有效识别商品1868种,提高了海关查验作业效率。(69)《智能审图,大大提高海关查验作业效率》,中华网,2021年6月29日,https://tech.china.com/article/20210629/20210629814709.html。
第六,区块链技术作为现阶段比较前沿的信息通讯技术,正在为口岸管理现代化带来新一轮革新。区块链技术引起的行政体制改革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重要改革领域之一。2017年以来,国内外电子政务领域开始探讨区块链在电子政务中的应用前景,提出了如权限明晰性、合约可靠性、数据安全性等潜在风险。(70)Svein Ølnes,Jolien Ubacht Marijn Janssen,“Blockchain in Government:Benefits and Implications of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 for Information Sharing”,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Vol.34,No.3,2017,pp.355-364.2019年10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探索利用区块链数据共享模式,实现政务数据跨部门、跨区域共同维护和利用,促进业务协同办理。凭借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可追溯性、公开透明等特征,区块链技术成为具备颠覆式计算范式创新特征的普适性技术框架。2018年,世界海关组织发布《揭示海关区块链应用前景》研究报告,指出海关应用区块链技术将有助于提高贸易合规性、跨境便利化、打击走私犯罪,提升海关监管效能。2019年,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推出多项融合区块链技术的跨境人民币融资、医药供应链追溯、辅助海关智慧监管、融合第三方贸易服务等应用成果。(71)沈文敏:《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兼具“监管+服务”十大功能 上海电子口岸区块链联盟成立》,《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11月14日,第4版。2021年,天津海关出台全面推动区块链验证试点工作13条配套业务措施,提出建立上链企业海关联络员制度、实施采信便利化等措施,简化海关对数据、单证的审查手续。(72)马晓东:《天津海关13条举措推进区块链技术应用,上链企业可享便捷通关》,《天津日报》2021年1月4日,第5版。
2021年2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上提出“深化海关贸易安全和通关便利化合作,开展‘智慧海关、智能边境、智享联通’合作试点”倡议(简称“三智”倡议),(73)《习近平主持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中国政府网,2021年2月9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02/09/content_5586387.htm。为口岸管理现代化提供了中国范式的有效范例。从主体维度看,“三智”强调多主体协同,旨在实现海关、社会组织与公众之间的整体治理和智慧治理;从治理手段看,“三智”通过搭建数字化的治理界面,打通不同的政府部门之间、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数据信息流通闭环,避免数据信息应用的“巴别塔”效应;从治理过程看,“三智”倡导通过信息技术的运用来保持治理韧性,实现不同治理主体间信息的融通与共享。
(四)口岸基础设施投资与口岸公共服务供给整合
通过口岸管理部门内部的部门合作以及与邻国之间开展口岸国际合作,改善口岸基础设施,是实现贸易便利化和口岸监管改革的重要内容。(74)Gerard McLinden,Enrique Fanta,David Widdowson,Tom Doyle,eds.,Border Management Modernization,The World Bank,2011,p.16.贸易便利化有助于各国实现国家发展目标,这使得它们更有竞争力,允许货物和服务按时交易,降低交易成本;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除非能够超越传统的改革议程,兴建专门用于海关改革的基础设施,否则无法充分利用国际贸易所创造的各种机会。各国政府需要对口岸管理现代化建设投入巨资,改善口岸基础设施。
口岸基础设施投资指航空、水运、铁路口岸主体设施的投资,口岸查验设施投资包括口岸监管部门行使跨境活动监管职能所需的业务技术用房投资。口岸查验基础设施是指海关、检验检疫、边防检查以及承担口岸查验职责海事机构等查验机构在国家批准对外开放口岸实施口岸查验执法过程中所使用的专用设施。(75)《国家口岸查验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建标185-2017)第一章总则第四条。口岸查验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公共查验场地、业务技术设施设备及国门形象建筑等。公共查验场地指旅检大厅、货物查验场地、交通运输工具查验场地等。业务技术设施设备指查验、检测、执勤、技术设施设备等。国门形象建筑指国门楼、牌楼、文化长廊等。(76)《广西口岸管理办法(暂行)》(桂商口发[2020]2号),第七条。国家口岸查验基础设施是口岸运行和管理的基本前提,是口岸进出对象,即人员、货物、物品和交通运输工具通行的物质条件,是海关、检验检疫、边防检查、海事等部门执法的重要保障。(77)《国家口岸查验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建标185-2017)条文说明 第一章总则第一条。
口岸监管部门要充分利用不断涌现的各种新技术以加强风险管理,提高口岸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如将物联网、云计算、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应用于口岸管理过程中,因为海关自动化能降低海关放行的、相当于0.2%贸易商品价值的直接成本,再加上减少耽搁时间的间接收益,实际成本减少达到商品价值的1%。(78)世界银行编:《全球经济展望2004:履行多哈议程的发展承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页。需要指出的是,口岸信息化建设已经纳入口岸基础设施建设范畴,如2020年3月31日印发的《广西口岸管理办法(暂行)》提出“口岸信息化建设与口岸查验基础设施建设、同步提升。口岸信息化建设包括‘智慧口岸’、‘单一窗口’、通道卡口、视频监控设备等。”
五、结论
口岸管理现代化兴起的根本动因在于社会需要,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先后进入后工业社会,多元价值和利益诉求开始涌现,使得原先工业时代的政府管理理念、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和绩效标准难以满足当下口岸管理的现实需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子技术的研发、应用与普及,促使公民越来越难以逃离国家的“电子版图”,而公共部门也开始通过先进的软硬件技术设施来再造政府机构及其运作流程。(79)[美]杰伊·M·沙夫里茨、E.-W.拉塞尔、克里斯托弗·P·伯里克:《公共行政导论(第六版)》,刘俊生、欧阳帆、金敏正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9页。从本质上看,口岸管理现代化是口岸管理职能边界厘定与口岸治理工具选择之间的持续调试和动态匹配的复杂互动,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口岸管理现代化是一种复杂的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是一种综合运用各种治理工具,包括经济工具、法治工具、权力工具、价值工具、技术工具等来实现管理目标的过程,在手段与分析工具上,包含了定性和定量两个维度。(80)王升平:《西方行政理论本土化的形态与逻辑探析——以公共行政主流理论的交融与转化为例》,《治理研究》2019年第6期,第42-52页。在治理理论看来,公共管理是一种上下联合互动的过程,不是单向管理,而是需要各个社会管理主体通过协调合作,才能实现最终目标。(81)孙萍、闫亭豫:《我国协同治理理论研究述评》,《理论月刊》2013年第3期。口岸管理具有主体的多元性、权威的分散性、关系的对等性、目标的一致性以及自组织的协调性等特点,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管理活动。口岸管理现代化改革的难点在于碎片化的口岸管理体制朝向整体性治理理念下的口岸治理体制转型中的协调难题。
第二,口岸管理现代化是一系列试错行为的组合,其主要目的在于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和维护国门安全。口岸管理环境复杂多变,口岸管理现代化在促进贸易安全、便利发展,保证旅客安全方面的需求与日俱增。同时,口岸管理机构面临高昂的管理费用,迫切需要转移管理风险,分担管理成本。国门安全不仅是安全问题,更是发展问题;只有在口岸最大限度实现人便于行、物畅其流的同时,有效防止跨境疫病疫情、国际犯罪集团、恐怖主义、非法移民、固体废物、危险化学品、有害生物和生物武器等通过口岸入境,才能实现可持续的贸易便利化。
第三,口岸管理现代化意味着口岸管理结构从垂直化走向扁平化,即从科层制的垂直型管理结构走向扁平化的网络治理结构。传统的科层制结构过分强调等级制,权力集中,上下级机构与同级职能部门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和协调,权力运作的向度是自下而上的,这种缺乏弹性的垂直型管理结构不仅影响行政效率,而且增加了行政机构的交易成本。(82)唐亚林著:《区域治理的逻辑:长江三角洲政府合作的理论与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8页。通过重新界定口岸监管部门的职责权限范围及其行使方式,以分权的方式重塑口岸治理结构,借助网络与信息通讯技术,构建扁平化的网络治理结构作为对垂直型口岸管理结构的有效补充,成为口岸管理现代化的主要特点之一。
第四,口岸管理现代化是一个政治博弈过程,参与其中的不仅包括口岸执法机构等公共部门,还包括口岸经营者和口岸使用者等私营部门,以及其他国家的口岸管理部门等国际行为体,涉及复杂的责任、权力和利益的调整。口岸管理现代化的发展反映出国际贸易中的各种行为者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83)Gerard McLinden,Enrique Fanta,David Widdowson,Tom Doyle,eds.,Border Management Modernization,The World Bank,2011,p.79.口岸管理越来越注重对口岸活动的国际协调,如陆路边境口岸之间建立的“一站式口岸”,可以在减少延误、重复、繁琐的同时,改善口岸管理效果并降低走私和错误申报风险。“一站式口岸”建设需要非政府的利益相关者从一开始就介入此项工作,包括进出口商、中间商、报关行、边境口岸使用者(旅客和运输服务提供人)以及边境口岸的周边社区。(84)Erich Kieck,“Coordinated Border Management:unlocking trade opportunities through one stop border posts”,World Customs Journal,Vol.4,No.1,2010,p.6.
第五,口岸管理现代化涉及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多个层面,应将涉外跨国的协同关系纳入研究范畴,探索口岸管理现代化的国际合作路径,中国提出的“三智”倡议为促进“走出去”战略、国际共治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提供中国方案。“三智”倡议是中国海关围绕世界海关组织关于“智能”治理理念和“协调型口岸管理”的积极探索,其本质在于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推进海关国际合作和口岸国际合作,促进国际海关间及全球供应链相关各方之间的互联互通,实现全球贸易的安全畅通。
口岸管理现代化不仅仅是海关现代化改革,而是整个口岸通关流程的现代化,表现出治理主体多元化、技术运用数字化、治理过程协同化的特点。口岸管理现代化不同于仅仅注重改善海关业务传统的口岸管理改革,它不仅是口岸监管模式的创新,更是口岸管理理念的更新;不仅是行政操作前台的流程再造,更需要后台不断运用新技术、新工具、新理念对系统进行整合,搭建无缝隙的口岸公共服务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