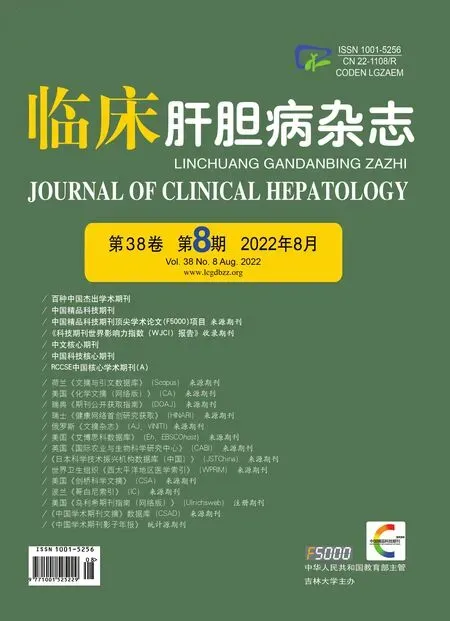衣壳组装调节剂联合核苷(酸)类似物治疗慢性乙型肝炎临床试验中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
鲁凤民, 黄鸿鑫, 毛天皓, 陈香梅, 庄 辉
1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肝病研究所, 北京 100044;2 北京大学医学部 基础医学院 病原生物学系暨北京大学感染病研究中心, 北京 100191
HBV感染是病毒性肝炎、肝硬化和原发性肝癌的主要病因。2021年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1]显示,全球慢性HBV感染者约2.96亿人。我国自1992年开始实施新生儿乙型肝炎疫苗免疫规划管理,2002年实行乙型肝炎疫苗免费,2005年正式实施乙型肝炎疫苗免疫规划,HBV新发感染大幅减少,其中5岁以下儿童HBV感染率已降至0.2%,全人群的慢性HBV感染率也下降至6.1%[2]。但我国既往慢性HBV感染者众多,现仍有7000万例,其中亟需治疗的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2000~3000万例[3]。2016年5月,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公共卫生危害”的全球战略,要求将新发感染减少90%、死亡减少65%[4]。当下我国每年HBV相关死亡约40万例,但CHB诊断率仅为22%,治疗率为17%[5],距离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诊断率90%、治疗率80%尚有很大距离。
现有的两类一线抗HBV药物包括核苷(酸)类似物(NUC)和聚乙二醇干扰素α(PEG-IFNα),均可有效抑制病毒复制,减缓疾病进展和减少终末期肝病的发生。其中,PEG-IFNα主要通过免疫调节发挥抗病毒作用,经过有限疗程后,其HBsAg清除率约为10%,在优势人群中可有更高的临床治愈率[6-8],但由于存在一定的副作用,限制了其广泛的临床应用。NUC主要通过不可逆地阻断HBV聚合酶(polymerase,P)介导的病毒RNA逆转录过程,显著抑制HBV DNA复制以发挥抗病毒作用[9],加之口服方便、副作用较少,NUC在临床上得到广泛应用。然而,停药后反弹是NUC最大缺点[10],患者一旦开始NUC治疗,往往需要长期甚至终生服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患者的治疗意愿。因此,目前亟需研发抗HBV新药,以显著提高CHB的治愈率。
近年来,靶向HBV生命周期不同层面的直接抗病毒药物(DAA)如进入抑制剂、衣壳组装调节剂(capsid assembly modulators,CpAM)、HBsAg释放抑制剂、干扰共价闭合环状DNA(cccDNA)转录及表达过程的RNA干扰,包括小干扰RNA和反义寡核苷酸等均已进入不同临床试验阶段。其中,CpAM是截至目前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较多的一类在研药物,但在以“安全停药”为主要治疗观察终点的CpAM联合NUC临床试验中,几乎所患者停药后均发生反弹[11],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CpAM联合NUC的用药策略,以选择适宜的临床试验终点。
1 cccDNA与CHB的临床治愈
近年来,靶向HCV复制的DAA药物成功治愈丙型肝炎,再次将“CHB治愈”推到聚光灯下。但与HCV基因组RNA在肝细胞质内通过快速自我复制维持慢性感染不同,以稳定的微小染色体形式存在于感染肝细胞内且有转录活性的cccDNA是HBV复制的源头,也是维持HBV感染的关键。加之慢性HBV感染过程中普遍发生的HBV DNA整合[12],以及HBV的免疫逃逸[13],CHB的临床治愈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尽管HBV基因组仅有3.2 kb长,但却有2种病毒基因组形式:即松弛环状DNA(relaxed circular DNA,rcDNA)和cccDNA。HBV进入肝细胞后,rcDNA进入细胞核并被修复形成cccDNA[14-17]。cccDNA在细胞核内以微小染色体形式存在,可转录出病毒的全部mRNA,故有转录活性的cccDNA的持续存在,被认为是HBV慢性感染得以维持和患者难以治愈的最主要因素[18]。除此之外,HBV DNA的复制有其独特的逆转录过程,在细胞质内新合成的核心蛋白将前基因组RNA(pregenomic RNA,pgRNA)/P蛋白复合物包裹形成核衣壳,随后P蛋白以pgRNA为模板逆转录合成负链DNA,再以pgRNA的5′端残余为引物合成出长度不一的互补正链,形成子代病毒rcDNA。期间,P蛋白要确保有3次正确的跳转才能完成上述复杂过程[19]。肝细胞核内的cccDNA池除了来源于新感染过程中进入肝细胞内的rcDNA,还可由感染肝细胞胞质内新形成的、带有rcDNA的核衣壳直接入核并释放rcDNA形成[14,20]。而病毒蛋白HBx对于形成有转录活性的cccDNA至关重要[21-22]。
我国学者[23]曾通过对CHB患者HBV耐药病毒株动态变化的分析,推测患者肝组织内cccDNA的半衰期可能只有数月。cccDNA的较短半衰期带来了通过NUC抑制HBV DNA复制阻止新病毒的产生,从而耗竭cccDNA实现乙型肝炎治愈的希望[24]。然而,在临床实践中,即使接受长时间NUC治疗,也仅有极少数患者血清HBsAg消失(伴有或不伴有抗-HBs阳转),实现临床治愈(功能性治愈)。与之一致,2020年美国肝病学会年会报道一项来自10个国家(地区)、25家医院的国际多中心真实世界队列研究[25],共纳入初治CHB患者7697例,其中,5430例接受恩替卡韦(ETV),2267例接受替诺福韦酯(TDF)治疗,结果显示,ETV和TDF队列的8年累积血清HBsAg清除率分别为1.69%和1.34%。此外,由于NUC的作用机制是竞争性抑制P蛋白的逆转录活性,其往往难以完全阻断cccDNA池的内补充[26],导致停药后病毒学复发和疾病反弹发生率较高,患者不得不长期甚至终生服药,给患者和社会带来健康和经济双重负担。因此,对于长期接受NUC治疗的患者,安全停药是一项无法回避的需求。
2 CpAM联合NUC治疗CHB临床试验中需考虑的科学问题
在研的CpAM类药物可分为2种作用类别:Ⅰ型CpAM干扰病毒核衣壳的正常组装,使之形成多种形态的非衣壳结构[27];Ⅱ型CpAM则促进结构“正常”但无pgRNA/P蛋白复合物的空衣壳形成[28]。CpAM的上述作用均可抑制pgRNA的包装[29-30]。此外,CpAM还有增强成熟核衣壳的非正常解聚和干扰rcDNA正确释放入核以回补cccDNA的作用[31-33]。并且,由于HBV抗CpAM的潜在耐药位点与NUC耐药突变不重叠,预计对NUC耐药变异株也有作用[34]。因此,已有的CpAM的临床试验设计多与NUC联合。有研究[35]显示,相较于ETV单药治疗,CpAM与ETV联合治疗患者的HBV DNA和HBV RNA往往有更大幅度的下降。
目前,对于是从病毒学还是从临床角度去定义“CHB治愈”尚缺乏一致意见,并可能对新药的临床评价带来一定的困扰。总的来说,仅仅是病毒学意义上的HBV cccDNA持久沉默或清除的CHB患者仍有较高的原发性肝癌发生风险。而以血清HBsAg阴转(伴或不伴抗-HBs阳转)为标志的临床治愈[36],则不仅是所有病毒学标志物的完全阴转,包括肝癌在内的相关肝病死亡风险也大为下降[37]。血清中HBV RNA病毒样颗粒的发现为指导NUC治疗的安全停药提供了一定帮助,原因在于血清中的HBV RNA多为未完成逆转录的核衣壳内包裹的pgRNA[38],NUC治疗阻断了逆转录过程,使核衣壳内的pgRNA不再为P蛋白的RNase H活性所降解,并以HBV RNA病毒样颗粒形式释放至血循环[38]。因此,血清中HBV RNA检测阳性往往反映了患者肝组织中cccDNA仍在活跃转录,故血清中HBV RNA阳性时的停药往往提示更大的反弹甚至疾病复发风险[38-39]。但在CpAM治疗时,HBV RNA减少仅仅是药物作用于靶点的重要证据,并非代表cccDNA被清除或被静默[11]。在HBsAg或乙型肝炎核心相关抗原(hepatitis B core-related antigen,HBcrAg)无明显下降的情况下,以“安全停药”为重要观察终点的两项CpAM临床试验[40-41]中,几乎所有患者均在停药后发生了反弹,未能观察到持续的治疗效果,由于治疗过程中出现ALT水平升高,研究暂停。
CpAM的药理作用主要是干扰核心蛋白的正确组装,使pgRNA/P蛋白复合物无法被有效包裹,从而使逆转录过程受阻;或引发已经形成的成熟核衣壳易被拆解而稳定性下降。而NUC则是在核衣壳内竞争抑制P蛋白以pgRNA为模板逆转录合成子代病毒负链DNA的过程。临床上,二者联用具有良好的协同作用,对rcDNA合成过程的抑制作用更加彻底;但由于二者均为通过干扰抑制子代病毒rcDNA的形成过程发挥抗病毒作用,当与作用力超强的CpAM联用时,NUC可能将主要作用于逃逸了CpAM干扰作用的核衣壳内的逆转录过程,仅仅发挥“堵漏”作用。或许不能期待在临床试验的短疗程条件下,CpAM+NUC两强联合实现“1+1≥2”的叠加效能。
此外,可以预见的是,核衣壳内的pgRNA并非以无序状态自由悬浮其中,更可能是以适当的方式“悬挂”在填充着dNTP和一些未知宿主蛋白的衣壳腔内。生物信息学分析[42]提示,在pgRNA上或许存在与构成衣壳的核心蛋白结合的基序。也有研究[43]证实,pgRNA的5′ε茎环结构与核心蛋白相互作用,促进衣壳的组装。在CpAM作用下失去了正常结构和壳内空间的核衣壳内,pgRNA/P蛋白复合物是否能够有效启动由P蛋白第63位酪氨酸引发的逆转录起始引物前3个脱氧核糖核酸的合成?随后是否可以正常进行首次跳转以确保逆转录的精准启动?如此多的不确定性提醒有必要探究联合用药下,NUC是否还能够发挥对逆转录过程的有效竞争抑制作用。若果真如此,两者联合的叠加抗病毒作用是否更容易碰到药物效应的天花板?期许两强联合加速cccDNA池耗竭的作用会不会难以成真?事实上,从既往报道的CpAM联合NUC临床试验研究结果来看,患者血清HBsAg或HBcrAg在短期治疗后的确无明显下降,也许提示联合CpAM并未显著加速NUC治疗下的cccDNA耗竭或静默,以至于几乎所有患者在有限疗程的联合治疗后均发生了停药后的病毒学反弹[44]。目前比较确认的是,在未来以安全停药为观察终点的临床试验中,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CpAM和NUC联合治疗以耗竭或静默cccDNA池,提高安全停药的可能性。此外,基于人肝嵌合鼠的动物实验[45]发现,CpAM与PEG-IFNα联用能够进一步增强PEG-IFNα诱导的肝内干扰素刺激基因表达,提示在未来对特定人群以临床治愈为目的的临床试验中,有必要考虑CpAM在与一线NUC联用的基础上,加用长效干扰素,或与在研的免疫调节剂联用,以提高临床治愈率,减少肝细胞癌的发生(图1)。

图1 影响CpAM联合NUC对抑制HBV DNA复制发挥叠加作用的可能机制及启示
3 小结与展望
在本期发表的文章中,陈娟、黄爱龙从HBV cccDNA 的角度讨论了慢性乙型肝炎的治愈问题。除此之外,整合来源的HBsAg持续表达也是影响慢性乙型肝炎临床治愈的主要因素。由于缺乏直接靶向cccDNA的抗病毒药物,且整合的HBV DNA可持续表达HBsAg,通过调节宿主免疫清除感染及携带整合HBV DNA片段的肝细胞、或使之转录沉默,对于慢性乙型肝炎的临床治愈尤为重要。这方面,高子翔等就一些关键细胞因子在CHB感染及治疗中的研究进展进行了总结与讨论;郭艺飞、张继明对影响慢性乙型肝炎功能性治愈的因素特别是宿主免疫因素及其机制进行了讨论。在抗HBV新药研发上,CpAM无疑是最受关注的一类,刘慧等系统阐述了CpAM 靶蛋白-核心蛋白的功能、CpAM 分类、作用靶点及抗HBV机理及CpAM 临床试验现状等,并预期联合治疗可能是CpAM未来临床应用的最佳选择。笔者团队认为,现阶段CpAM的联合治疗之路布满荆棘,可能需要放缓步伐,优先着手解决一些影响CpAM联合NUC治疗效果的相关问题。这或将对CpAM的临床应用有更切实的预期与定位,使未来的临床试验设计更为合理,并最终使CpAM类药物及早进入临床,使患者获益。
近年来,包括固有免疫调节剂、治疗性疫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以及单克隆抗体在内的免疫调节剂均有长足发展[46-49]。考虑到激活体内特异性抗HBV免疫反应在清除感染肝细胞及其cccDNA池、清除有转录活性整合HBV DNA肝细胞中的重要作用,未来的联合治疗或许是在更强的抗HBV DAA抑制病毒复制、静默及清除cccDNA池和减少免疫抑制性的HBsAg水平的基础上,再联合免疫调节药物,以诱导抗HBV特异性后天免疫,为CHB临床治愈带来更大希望。
关于多靶点联合治疗,目前看来似应综合考虑如下几点:(1)安全性;(2)疗效;(3)多靶点药物的相互作用及其与患者因其他疾病而用药物的相互作用;(4)成本效益比;(5)患者的经济承受能力,即可及性等。我国CHB临床治愈(珠峰)工程项目最新研究[50]结果显示,对于NUC治疗下达到HBV DNA检测不到、HBsAg≤100 IU/mL的患者,联合PEG-IFNα治疗后,临床治愈率可高达55.3%。因此,未来如出现比现行NUC(ETV、TDF和TAF)更强效、低耐药的DAA药物,再联合一种比PEG-IFNα更强效的免疫调节药物,也许能够获得更高的临床治愈率。总之,多种潜在的联合治疗策略仍有待深入研究。
利益冲突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鲁凤民、庄辉拟定写作思路并最终定稿;陈香梅指导文章撰写并修改文章关键内容;黄鸿鑫和毛天皓负责文献检索并参与起草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