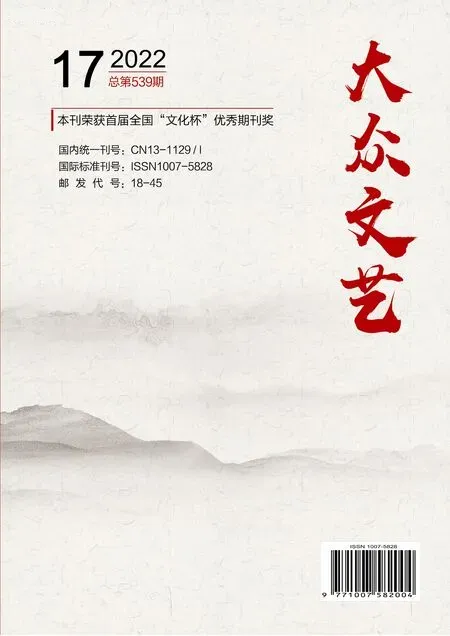文明与荒芜:浅析《尘埃落定》中的独特审美
竺弋昱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浙江宁波 315000)
《尘埃落定》以宏阔壮丽的叙事手法和空灵细腻的诗化语言,展现了藏族独特的民族历史与文化,在探求生存本质和人性救赎的过程中,借超现实主义为小说增添了一抹浪漫神秘的色彩。阿来曾用近十年的时间进行素材的收集和情节的构思,在人物、意象、语言等各个方面精雕细琢,达到了极高的境界。
历来对于《尘埃落定》的评论,多数围绕着“傻子”形象、女性形象、叙述视角等主题展开,而小说的审美意义通常是附着在人物、情节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另外,许多学者为这部小说贴上“魔幻现实主义”的标签,并将其与《喧哗与骚动》《百年孤独》等作品相比较,可见其独特风格在中国文坛的影响力。尽管如此,阿来在访谈与演讲中还是坦言创作背景,讲述了自己在藏族文化孕育下迸发的创作灵感。
作为作家,阿来同时也是一位诗人,他用诗的语言、结构乃至诗的独特魅力与韵味,以及敏锐的感知力和无穷的想象力,创作了这个故事,其审美价值不可小觑。基于作者的个人创作以及藏族的传统文化,诗意与神秘更是成了《尘埃落定》的关键词。那么,这种美感与神秘感究竟源自哪里?本文深入剖析小说的审美特性,并将其置于“文明”与“荒芜”的主题背景下,在对立统一中审视摒弃了明确的价值判断的美与丑、善与恶。
一、文明:神圣与奇迹
《尘埃落定》的创作根植于嘉绒地区的文化土壤,土司制度和小说中呈现出来的民间神话、史诗、传说等是一部分,而更深层次的是渗透其中的藏族宗教文化。在这一神秘朦胧的面纱之下,神圣、祥和的气息笼罩着春雪覆盖的土地。“傻子”的形象指向阿古顿巴的民间传说,“是较之居住于宏伟辉煌寺庙中许多职业僧侣具有更多的佛性的人,一个更加敏感的人,一个经常思考的人,也是一个常常不得不随波逐流的人。”他不是凌驾于众人之上的神佛,但兼有智者的先见之明和孩子的童真无邪,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摒弃世俗的情感羁绊,在众人百般质疑下坚持自我,追寻人性的至善至美。
“傻子”的“佛性”是隐藏在空洞与迷惘背后的睿智,是根植于灵魂与思想中的至善。对于“傻子”来说,他的智慧是以启示和灵感的方式乍现的,宛如神迹般似有若无:在其他土司纷纷种下罂粟的时候,麦其土司听从“傻子”的决定种下了粮食,当秋收以后其他人都饥肠辘辘的时候,掌控着粮食的麦其家仿佛成了掌控着命运的救世主;“傻子”在边境镇守仓库时做出了一系列壮举,不仅娶到了最美丽的女人,还成了市场这种“新生事物的缔造者”。在土司制度和权力崇拜的环境中,他却“同情弱小者,凭直觉而不是思索出世,通晓是非而不较利害”。正如孔子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他的“傻”是无拘无束天性的释放和不分等级向善的本能,模糊了土司制度森严的等级界线。
在这个权力统治下的社会,在这个野蛮战胜文明的社会,人们或是在追逐权力时化为残暴的野兽,或是匍匐在权力下只剩一个空洞的躯壳,只有“傻子”在呼唤人性的溯源,他没有自私自利的欲望,没有迫害他人的恶意,这一份纯粹像镜子一样,照出了人性深处的温情与善意。“傻子”所带来的神圣感绝大部分来自这样一种充满怜悯的救赎者形象,但也体现在他的脱离世俗、不惹尘埃。作为一个异禀的俗人,他承担着“高处不胜寒”的孤独:从出生来看,“傻子”作为麦其家的二少爷,贵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但因为众人的普遍认同,他被贴上了“傻子”的标签,于是从小被排挤到了权力争夺之外。这就造成了他“夹缝区身份”——“脑子有点问题但生来高贵的人”,于是他享受着虚无缥缈的尊贵,却又被排除在权力之外,至死都没有与暴力、欲望同流合污。
除神圣外,作者在小说中也呈现了奇迹之美。奇迹是藏族文化的内蕴,是自由和理想的外化,它迸发出的生机与希望,构成了万物复苏式的强大的美感。小说中提到关于藏族世界起源的神话是这样描述的:“有个不知在哪里居住的神人说声:‘哈!’立即就有了虚空。神人又对虚空说声:‘哈!’就有了水、火和尘埃。再说声那个神奇的‘哈’,风就吹动着世界在虚空中旋转起来。”这段话不难让读者联想到和合本《圣经》中对于神创造世界的描写:“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相比之下,《尘埃落定》中的神话对创世人的身份、言语没有详细的描述,也没有明暗、善恶、爱憎的对立,呈现出无拘无束、野蛮生长的藏族特色,在神话所蕴含的浪漫主义色彩中更增添了一抹纯真朴素的自由。
在小说中,作者始终用奇迹的力量牵动着读者的内心。传教士翁波意西与活佛辩论,最终却被冠上攻击宗教的罪名而失去了舌头。但在奇迹的作用下,翁波意西竟有一日能够重新说话了,这象征着他坚守理想信念的内心执着,冲破权力束缚的强烈愿望,以及高傲不屈的思想与灵魂。殉道者的形象在古今中外比比皆是,例如不忍看到国家灭亡而投身汨罗江的屈原,秉笔直书不畏生死的齐太史,捍卫真理最终却被判为“异端”烧死的布鲁诺……翁波意西亦可归入其中,他虽是一个寄人篱下的流浪者,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但他的精神却坚不可摧。他甚至能够在土司的死亡威胁下无惧无畏地回答道:“你可以杀掉我,但我要说,辩论时,是我获得了胜利。”这种“吾更爱真理”的伟大品质,是导致他失去舌头的直接原因,也是推动奇迹降临的内在契机。尽管翁波意西之后为了维护“傻子”继位的权利,再次因不合时宜的规劝惹恼土司而失去说话的权利,但这样一种蕴含着奇迹、自由、理想的美与力量却于他心中茁壮生长,不曾磨灭。
二、荒芜:野蛮与暴力
尽管有宗教文明和传统文化的影响,这片土地上仍存在着封建社会落后、野蛮的色彩,例如马梯是用活生生的人搭起来的,土司们在惩戒下人时轻贱人命、不辨是非,以及麻风、梅毒等恶疾的出现和传播。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战争与暴力,土司和他继承者的无知自大,原始欲望的挺立与道德伦理的坍塌,这一切荒芜的存在却并非不能称之为美,作者用艺术的美去修饰荒芜,颇有“审丑”的意味。对照法国伟大诗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阿来的《尘埃落定》恰巧也展现了这样一种非常态的美。
在小说中,“罂粟”作为一个重要的意象,与枪支、军队等外来因素一起,为这片土地带来了虚幻而短暂的新生。显然,“罂粟”是“恶之花”的集中体现,是打开封闭藏族地区的入侵者,是土司制度逐渐瓦解的导火索,也是信仰迷惘和道德失语的具体呈现。罂粟花盛开的时候,那“红艳艳的花朵”和“白色的乳浆”形成了一道壮丽的风景线,倘若将其当作是一种观赏性的植物来说,罂粟花本身并不承载着罪恶,但由于近代鸦片战争带来的屈辱感和民族创伤,罂粟被赋予了腐败和罪恶的特殊含义。
但阿来着笔“罂粟”时刻意地避开了其与历史的相关性,将暴力、血腥、战争等因素隐匿在罂粟妖艳而迷乱的自然之美下。苏童在访谈时曾说:“以前的小说文本通常是将人物潜藏在政治、历史、社会变革的线索后面,表现人的处境。我努力地倒过来,将历史、政治的线索潜藏在人物的背后。”在苏童的《罂粟之家》中,罂粟反映了地主阶级内在的衰颓与萎靡,以及时代背景下人物内心的迷惘与麻木;而在《尘埃落定》中,罂粟则被称作“心房上的花”,在熊熊燃烧的欲望中开花结果。麦其土司在罂粟花的撩拨下霸占了查查头人的妻子央宗,并借他人之手将查查头人杀死,而正是这段错乱的感情,延伸出许多本不该发生的事故,为土司制度的没落和麦其土司的覆灭埋下了祸根。作者在描绘暴力、野蛮的时候,采用了诗意、平和的语言,冲淡了忐忑起伏的紧张感,最终回归到尘埃落定的恬静之感。
除意象之外,作者在塑造女性形象时也大多呈现出荒芜的美感。侍女桑吉卓玛拥有活泼的性格,美妙的歌喉,是“傻子”最亲近的人之一。在少女时期,侍女桑吉卓玛的身上散发着不加修饰的欲望与蓬勃向上的活力,洋溢着青春的魅力,是美的象征。但她的身份早已注定悲剧结局,当她下嫁银匠后,逐渐转变成了一个粗俗、平庸的妇人,甚至在边界与管家有了私情。卓玛的出嫁是她跌落凡尘的起点,也是她身为美的堕落,体现了时代和社会对女性命运的禁锢。但在另一方面,桑吉卓玛的堕落并非一味地丑恶,而是充满了挑战和反抗的精神。“丑之所以能够成为审美的范畴,是因为美所呼唤的情感意义能够在丑中找到共鸣。”卓玛的浪漫主义是建构在权力的基础上的,是献出自由、尊严以及身体换来的,而婚姻作为她独立个体的自由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又代表着精神的解放。
小说中的另一个重要女性形象是塔娜,她被当作政治工具嫁给“傻子”,却不由自主地移情于更有力量、更有前途的哥哥,虽打破了常规的伦理但终于弥补了内心的不平衡与不满足。她的身上存在着更加复杂的情感宣泄:她承载着一个家族的兴亡,却又对丈夫和家庭不满;她如同被迫远嫁和亲的昭君,却又多了几分娜拉出走时的勇气和决心——在思想和情感的维度上。由此可见,那些古今中外被支配的、被压抑、被牺牲的女性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有共同之处,“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相同的是落后制度对女性的压迫”,她们企图以自毁式的疯狂打破封建制度对女性命运的界定,以几近绝望的方式追求个性解放与自由发展。超越个人情感的荒芜,突破无价值、无意义的荒芜人生,这种带有自我毁灭意味的选择,又何尝不是令人既痴狂又痛恨,既恐惧又向往呢?
三、对立:走向荒诞与崇高
在小说中,文明与荒芜以一种荒诞的方式交织在一起。在争夺罂粟种子的过程中,汪波土司派来的间谍被全数杀死,但后来“傻子”在巡逻中却发现了三棵盛开的罂粟花。灿烂的罂粟花扎根于牺牲者的头颅中,“汪波用这种耳朵开花的方式来纪念他的英雄”。英雄们壮烈赴死,但他们的使命与生命却化作罂粟延续,在“死亡”和“生命”的对立中,作者极致的想象力更展现出惊人的魅力。这一场荒诞的悲剧中,文明以荒芜的形式盛开,恰如那充满生机的罂粟花,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美,不是完全正面的、端庄的、纯洁的美丽,而是带有一丝压抑的、疯狂的、悲壮的美丽,令人排斥却魅惑人心的美丽。
另一种荒诞体现在文明与荒芜的不对等关系,两者相较,孰强孰弱,显而易见。在强权的霸凌下,文明只剩下一个表面的空壳,虚弱得伏在地上苟延残喘。作者刻意地将文明的重担放到弱者的身上:被排除在权力话语之外的“傻子”,毫无身份地位还被二度割去舌头的传教士翁波意西……他们无一例外地守护过自己所珍视的信仰,哪怕是嫁为人妇后的厨娘桑吉卓玛,也在施舍的权力中体味到一点文明的美与善,但最后依然被荒芜以压倒性的优势摧毁了。“也许在秀美带一点悲哀意味的时候,与悲剧感最接近”,正如俄狄浦斯终其一生抵不过命运,哈姆雷特在理想主义的虚幻中彷徨延宕,《尘埃落定》中的“傻子”在生与死中自觉地走向悲剧,在纯洁与自由中走向泯灭,由悲悯和哀怜上升到哲学式的崇高。
从荒芜走向文明的过程中,作者似乎也有过徘徊和犹豫。小说中有个并不显眼的角色——姐姐,她嫁给了一个英国贵族。她从土司家族走出去,学会了英国那一套礼仪,自以为是从荒芜走到了文明,但在众人看来显得浮夸而虚荣。姐姐回来的目的是功利而明确的,不过是想要拿走一份嫁妆,而在与家人相处的过程中,她只懂得指指点点,毫无温情,在离开时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舍与留恋。从这位英国贵妇人的身上,作者便自然而然地引出了一个疑问:文明一定是好的吗,荒芜一定是坏的吗?这不仅是对惯性思维的反叛,也是对于现代文明的追问。但无论如何,作者在结尾处还是站在了文明这一边。
文明的胜利并不仅仅是土司制度的覆灭,更是道德伦理的回归和因果报应的轮回,这场悲壮而唯美的死亡盛宴宛如昙花一现,却迸发出了崇高的色彩。小说中的“傻子”最终死于仇人的冰冷的刀子下,他之所以放弃反抗而选择赴死,也是抱着一种就义的心态。他明白对方是来报杀父之仇的,仇恨的一部分是来源于父亲霸占人妻造成的混乱,另一部分且更直接的便是来源于“傻子”的一手精准枪法。在生命流逝的过程中,文明与荒芜以具象化的形式在傻子身上呈现,他的生命历程具有普遍性和历史性,在原始的本真与蓬勃的欲望中向死而生。“傻子”用亡灵的视角最后审视这个世界,想到的是美好,看到的是光明。小说的结尾以返璞归真的意境作为底色,似乎到达了庄子所谓的“灵性”层面,摆脱一切束缚,回复到自然、自在、开阔、平静的状态,模糊了血腥与暴力带来的恐惧。
造就崇高的另一个因素是情感,它是独属于人的心灵层面的力量,超越了诗意的语言和辞藻,暗潮汹涌般激荡着读者的心。小说中描写死亡并不只有结尾一处,但唯独“傻子”的死是如此深刻且令人惋惜,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他不是冷酷无情的机器,也不是愚昧凶悍的野兽,而是一个真真正正带有温度、情感丰富的人。对于“傻子”来说,情感是他与生俱来的天赋,也是他与这片土地交流的方式,恰到好处地展现出“迷狂的气息和神圣的灵感”。“傻子”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不单是作者情感抒发的通道和主旨升华的阶梯。他是一个拥有生命激情的个体,是复杂而多面的存在,会顺从而反抗地接受“傻子”的标签,会快乐而痛苦地爱上一个人。他的情感释放同时体现了克制的美德,以更为复杂而深沉的心理活动呈现,进而构建起独特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这种在文明与荒芜冲击下率真而理性的情感表达,不仅是引起读者共鸣的本源,也是对于人性最好的诠释。
文明与荒芜是相对存在的,而其中蕴含的深意,是人类在回望历史和展望未来时皆不可忽略的命题。黑格尔在《美学》中提道:“如果一部民族史诗要使其他民族和其他时代也长久地感兴趣,它所描绘的世界就不能专属于某一特殊的民族,而是要使这一特殊民族和它的英雄品质与事迹能深刻反映出一般人类的东西。”《尘埃落定》书写的是藏族文化历史,但其意义却并不限于此,正如“傻子”对于身份认知和自我本质的苦苦追寻:“我是谁?”“我在哪里?”这两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成了无人能解的哲学难题,成为人类精神层面上共同的“无知”。而正是这样一种残缺,溯源了人性中的文明与荒芜,完成了小说主题的升华:作为个体存在的人终将走向死亡,但站在时间的顶峰俯瞰,人类追求善与美、智慧与文明的脚步不会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