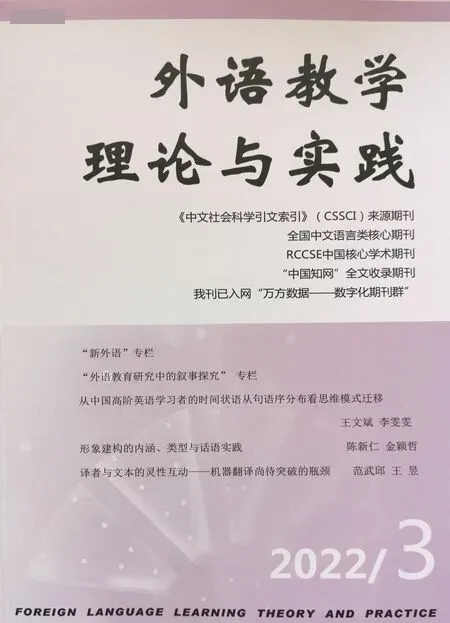形象建构的内涵、类型与话语实践*
南京大学大外部/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
陈新仁
南京大学大外部/铜陵学院外国语学院
金颖哲
提 要: 形象一直以来是哲学、社会心理学、文学等学科的经典话题,但相关研究往往采用宏观视角。受社会建构论思潮的影响,形象研究迎来了“话语转向”,形象建构与传播开始引发话语分析、语用学等领域学者的关注。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基于话语分析或会话分析探讨形象建构问题,但这些研究因缺乏合适的分析框架而总体显得片面、主观。为此,本研究在现有文献基础上,以形象的话语建构观为理论导向,尝试对形象建构的内涵、类型和话语实践方式作系统考察,以期能够为未来的形象研究提出一个可操作的分析框架。
1. 引言
任何层面的行为主体都需要有良好的形象。从国家层面来说,良好的形象对内能够增强国家凝聚力(陈琳琳,2018)、对外能够构成国家文化软实力,进而影响其综合国力(谢莉、王银泉,2018);从机构层面来说,良好的形象能够影响机构与民众的关系及行事目标的达成,比如良好的政府形象能够体现执政能力、凝聚社会力量(谢金林,2010)、顺应民众期待、满足民众需求(金颖哲、陈新仁,2022);在社会个体层面,良好的形象往往意味着好人缘、个人魅力、发展机会等。
形象研究由来已久,成果颇丰。早期相关研究的学科视角主要包括西方哲学(如Miller et al., 1960;Wittgenstein,1986)、社会心理学(如Schlenker,1980)、(比较)文学(如Leerssen,2007;巴柔,2001;王运鸿,2018)等,如今则主要包括受社会建构论影响的批评性话语分析(如周鑫宇,2016)及语用学研究(Ren & Guo,2020;Chen & Jin,2022;杨小敏,2018)。总体来看,学界对于形象的理解和认识经历了由本质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转变(金颖哲,2021b),发生了形象建构研究的“话语转向”(陈琳琳,2018)。从社会建构论角度看,形象并非“与生俱来”,同样也非静态不变,而可以通过话语加以建构、管理或修复。例如,企业对于其形象的话语管理和修复能够帮助调解其与公众之间的关系(Page,2014);社会个体形象的策略性话语建构或管理能够帮助达成相应的人际目标(如Chen & Jin,2022;金颖哲,2021a)及行事目标(如Zhong & Zeng, 2020)等;与城市关联的新闻报道能够塑造相应的城市形象(袁周敏,2018)。然而,相关研究显得较为片面、主观,根本原因在于缺乏针对性、操作性分析框架。
基于此,本研究尝试在厘清形象概念、阐释形象建构观的基础上,探究形象话语建构的内涵,借鉴Spencer-Oatey(2008)提出的关系管理取向及话语实践方式的分类,尝试提出形象话语建构的类型及具体话语实践方式,以期为形象的话语建构研究提供一个可操作的分析框架。
2. 理论基础
1) 形象的界定
中文中的“形象”多对应英文中的“image”。Williams(1976[2015])在其所著的:一书中追溯了该词的词源和演变,“image”一词的出现可以溯源到拉丁词汇“imago”,而后者逐渐演变出“幻影、概念或观点的含义”,该词经过了由物理成象到文学修辞再到心理表征的发展过程。客观世界投射并存在于人脑中形成的心理表征,就成了我们常说的印象(impression)。
在个体层面上,形象可以指行为主体呈现出来的样貌或者给人留下的印象,或曰“被感知到的名声”(perceived reputation)(Williams, 1976 [2015])。从这个角度看,形象与面子密不可分。Goffman就曾提出面子是“根据既定的社会规则刻画的自我形象”(1967: 5),是“每个社会成员希望为自己在公众面前争得的个人形象”,即“自我公共形象”(public self-image)(Brown & Levinson,1978 [1987]: 61)。形象有积极、中性、消极之分(Li & Ran,2016)。一个人如果具有好形象,就会有面子,反之就没有面子(中性的个体形象则不关涉面子,Spencer-Oatey,2007);一个人的形象如果崩塌就会丢面子,形象修复则可以挽回面子。当然,形象与面子并不等同,面子还与财富、权势、地位、尊严(Wang & Spencer-Oatey 2015)、关系等有关。另一方面,形象侧重他人感知,而面子偏重自我感知。
形象与身份之间同样存在密切的关联。Tracy & Robles(2013)将身份区分为主体身份、交际身份和个人身份,其中个人身份指自我相对稳定的特征,依附于主体身份和交际身份而存在;这种“特征”或“属性”也被不少学者(如Lakoff,1989;Spencer-Oatey,2007;袁周敏,2018)看作(自我)形象。在以上观点的基础上,陈新仁(2020a)将形象纳为身份的一个维度,关注“在他人眼里‘我是谁’的问题,即个体在交际互动中呈现出来的符合或违背他人期望的身份特征”(p. 5)。又如,金颖哲(2021b: 15)将形象定义为交际者“通过有(无)意识的(非)言语选择或调整所动态建构的涉及名声、名望、能力等方面评价的身份属性”。形象往往依附于身份的其他维度,如角色或行动者(陈新仁2020a)。举例来说,张教授在课堂上的角色是教师,基于这一角色,张教授可以呈现出博学、严谨、诲人不倦的教师形象,进而给学生留下相应的印象。
当然,不只是社会个体拥有形象特征,其他行为主体(如机构、城市、国家)同样也具有形象属性,只是在其内涵方面有所差异而已。譬如,一个国家的形象是指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生态环境、价值观等在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心目中的综合印象,涉及美好程度、开放程度、文明程度、守信程度、自由程度等。同样,一个国家的整体形象往往由各种局部形象构成,后者与其承担的特定角色(如常任理事国)或行动者(如维和力量、大型赛事东道主)直接关联。
2) 形象的话语建构观
以西方哲学为代表的形象观传统上将形象看作对于客观世界的镜像反映,如Wittgenstein(1958)将形象看作是人们“证实的方式”或“看的方式”(阮凯,2019: 93)。传播学、管理学、比较文学、跨文化交际学等领域的主流观点也与此相类似,如谢金林(2010: 52)认为形象是物质的一种“能够对人产生一定的影响,使对象公众产生某种心理的活动或对客观物质(产生)的心理反应”的“具体形态”;胡易容(2015: 24)认为形象可以表现为: 1) 具像化的某种图像或文字;2) 投射与感知形成的心象,或言之“印象累加”。上述将形象看作某种独立存在的社会或心理事实的观点可以视为一种本质主义观(参考Joseph,2004)。
在社会建构论的影响下,人们对形象的认识发生了由本质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转变。目前,具有建构主义色彩的形象研究主要包含三个方向: 以社会心理学(如Schlenker & Pontari,2000;Schlenker,2012)和传播学(如Rui & Stafanone,2013)为代表的自我呈现(或印象管理)研究;以语用学(如Ho,2009,2010;任育新,2013)为代表的身份形象建构研究及企业身份形象研究(如王雪玉,2013;李梦欣,2021);以及以批评话语分析(如汪徽、辛斌,2019)为代表的形象建构研究。
(1) 自我呈现(self-presentation),或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最初由著名社会学家Goffman(1959)提出。他将社会交际比作一出“戏剧”,交际者是“戏剧”中的“表演者”,其他人则是“观众”: 在这出戏中,“表演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表达自己,从而激活“观众”心中对自己特定的印象,是发话人对于自我形象的控制(Schlenker,2012)。印象管理涉及发话人尝试塑造听众对于个人(如自我、朋友、敌人)、团体(如俱乐部、商业机构)、事件(如礼物、车)或观点(如堕胎与反堕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印象。
(2) 语用学视角下的身份形象建构研究大多采用语用身份框架,且将形象建构看作是一种主动选择、具有不同意识程度的话语实践,而非无意、无目的的流露或呈现。例如,Ho(2009,2010)通过对高校邮件往来中发件人的个人身份建构之分析探讨,研究了他们分别作为领导、同事、下属身份时建构出的个人身份,在邮件往来中,发件人通过对于关系的管理能够达到建构积极个人身份形象(如体贴礼貌的领导身份、谦虚顺从以及关怀他人的下属身份)(Ho,2010: 2258)。李梦欣(2021)基于身份工作(Chen,2022;陈新仁,2020a),发现商家在线上回应话语中会通过话语对身份进行不同类型的操作,从而建立或协商合适的语用身份形象,达到管理与(潜在)消费者之间关系的目的。
(3) 批评性话语分析视角关注话语和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将语言视为一种社会实践,意图揭示语言中隐藏的社会主体、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形态(Fairclough,2003;田海龙,2019),以及由此所反映出的国家或特定社会群体的形象。
上述关于形象话语建构的研究尽管视角不同,但具有以下相同或相似的观点:
(1) 形象是与身份和面子具有交集的一个维度。形象可以被看作动态交际中交际者身份和面子工作的产物,“交际者在自我定位的过程中对他人眼中的自我形象非常敏感”(Hall & Bucholtz,2013: 130)。对此,Tracy(1990: 214-215)也曾明确提出“自我呈现与面子密切相关;二者都假设交际者在动态的交际过程中有着特定的、意义重大且希望能够被展现出来的身份类型”。
(2) 形象由交际者通过各种类型的话语实践方式来实现。正如社会心理学家在自我呈现中的研究中所提及的,依据行为人的意识不同,自我呈现可以分为前景化自我呈现(foregrounded self-presentation)和背景化自我呈现(backgrounded self-presentation)(Schlenker et al.,1996;Schlenker & Pontari,2000)。其中前景化自我呈现具有更高、更显性的认知性和自我监督性,而背景化自我呈现则相对更为隐性。van Dijk(2000: 47)也曾提到交际者会“隐晦性表述不符合自身积极形象的话语;相反,任何对于我们的敌人或对手不利的事宜则会在篇章或对话中被明示”。由此可以看出,交际者会依据形象的需求,在话语方式的选择上进行显性或隐性的考量和管理。
(3) 形象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交际过程中动态产出的。Turner et al.(1987)曾提出自我概念(self-concept)作为无法被观测到的假定的自我认知表征结构,在交际中能够表现为可以被感知的自我主观经历,这种主观的经历结果即自我形象;“创造特定自我形象的特定交际语境能够激活(或者“开启”)特定自我概念”。由此可见,在不同的交际语境中,交际者对于自我的定义能够表现为不同形象的呈现。形象作为身份的维度之一,形象的动态可变性在现有文献(如Antaki & Widdicombe,1998;Ho,2009;陈新仁,2018a)对于(个人)身份可变性的探究中也能够得以证实,如Scollon & Scollon(2001: 45)将呈现给外界的自我形象直接称为“可磋商的社会形象”。
3. 形象话语建构的内涵
从社会建构论角度看,“建构”可以是语篇整体的“建构”,涉及整个语篇对于特定行为主体的形象塑造,也可以是局部的“建构”,关涉特定话语对于特定行为主体的形象塑造。从语用角度看,形象的建构可以是交际目标、交际手段,也可以体现为交际过程。
1) 作为交际目标的形象建构
作为目标的形象建构是指以形象塑造(building)或形成(formation)为主要交际目标的宏观形象建构行为,相关研究隶属传播学、管理学及批评性/话语分析范畴,主要以语篇整体为研究对象,关注语篇中被建构主体(某一国家、省市、特定机构或群体)的形象类型或者服务于形象建构的话语类型的形象建构,比如国家领导人或政治人物在媒体或新媒体上的形象建构(如Sampietro & Snchez-Castillo,2020;陈风华、查建设,2017)。
例1 @共青团中央: 【今日,小暑】今日5时51分太阳达黄经105°,小暑至。随着12日入伏,桑拿天将频繁出现。① 外出注意补充水分;② 饮食以清热解暑为主,可多吃西瓜、苦瓜、绿豆等;③ 不要长时间待在空调房,空调房不要长期关闭;④ “春困秋乏夏打盹”,多吃土豆、菠菜、海带等富含钾的食物,可驱困意。转发提醒!
例1为邹煜等(2020)在政务微博中政府形象建构的研究中提到的一个案例,选自博主“共青团中央”。在该例中,该博主作为政府官方账号,根据当下的节气向粉丝推送了夏日养生的四点注意事项,在生活、饮食等方面给粉丝提供建议,关注民生、并提高民众生活质量。邹煜等(2020)认为,这条微博能够建构该官方政务账号的“以人为本”的“服务”型形象。由此可见,该案例涉及的形象建构将特定形象的建构作为目标,关注语篇整体对于该定形象的塑造。
2) 作为交际手段的形象建构
作为手段的形象建构即在交际互动中通过话语对于形象进行策略性建构以达成特定行事目标或人际目标的建构行为。我们不妨仿照Goffman(1967)、Locher & Watts(2005)、Tracy & Robles(2013)、Chen(2022)等人的做法,将言语交际中交际者出于特定交际目标“对自我或他人的形象类型进行选择或调整时作出的话语努力”看作“形象工作”(金颖哲,2021a)。换言之,在交际过程中,交际者能够根据交际需求通过话语选择能够满足该需求的形象类型,并随着交际的进展,可以对形象进行实时或阶段性调整,从而满足不断发展及变化的交际需求及交际目标,这种在交际局部环节中发生的形象工作即“作为手段的形象建构”。请看下面两个例子(引用自金颖哲,2021a):
例2 Z老师这个人态度非常明确的,,“除非”,加个条件是吧,“除非”你真的能找到很好的问题。
例3 很高兴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IPRA(国际语用学会议)的见闻。这个……我是替补的哈哈哈,然后我不会占据大家太多的时间。
上述两个例子便是形象选择和形象调整的案例,例2中的说话人使用了发话人元话语(陈新仁,2020b)进行自我评价,并建构了自我“爱变”的形象。例3中的说话人在发言开始时使用了演讲的常见开场白“很高兴可以和大家分享……”,建构其开放、乐于分享的形象,而“IPRA”作为语用学领域最具权威性的国际会议之一,他的“见闻”也能够帮助建构专业的学者形象。但是,在短暂的停顿和犹豫后,该说话人使用元话语建构了自己作为“替补”的身份,并表示“不会占据……太多时间”,间接否定了自己在当下语境中他被赋予的“演讲者”“经验分享者”或“权威/国际化学者”的身份,这种自我贬低可以被看作谦虚行为,也因此建构了他作为“谦虚”或“谨慎”的形象。由此,在例3中,发话人通过话语选择,对自己的形象进行了由专业到谦虚的调整。
上述两个例子中的形象话语建构都属于手段类、策略型的形象建构,例2的发话人的观点与Z老师略微相左,因此在表达自己的观点前,对自我负面的“爱变”形象的建构一定程度上能够缓和由不赞同行为带来的对对方面子的伤害;同理,例3中的发话人在现场出席的嘉宾中并不算资深,因此,在话语表达过程中,其专业到谦虚的形象转变不仅符合观众对他的身份期待,也符合现场资深专家对他的身份期待,从而达到不与其他专家“争风”的人际目标。
3) 作为过程的形象建构
在双方或多方共同参与的言语交际活动中,交际者不但会对自己进行自我呈现,也会对其他交际对象进行他人呈现(other-presentation)(Tracy,1990)。因此,形象话语建构的内涵还包括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对于特定形象进行的磋商。请看下面在某一个学术研讨会上的片段:
例4 主持人: 接下来是来自某某大学的X教授,那么能够主持X老师的这个讲座呢也是非常荣幸,为什么呢,因为X老师是我们学界青年这个学者的杰出代表啊,他非常年轻,但是呢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就,发表了一系列高质量的成果。
X教授: 谢谢主持人的溢美之词。您……您实在是过誉了。我们还是刚刚蹒跚学步,确实是有这样的机会,感到非常的战战兢兢。
在例4中的话轮1,主持人通过对报告人的社会身份、学术成就的介绍,建构了对方“有成就的青年学者”这一形象。而在后续的话轮中,该教授将主持人的介绍总结为“溢美之词”、是对自己的“过誉”,并将自己评价为“学步”“战战兢兢”,从而否定了对方建构的“有成就”的形象,建构了一个青涩、稚嫩的青年学者的形象。因此,在通过上述两个话轮,交际双方完成了建构他者形象、否定他塑形象并重构自我形象的磋商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形象话语建构的动态性、互动性,以及形象的可磋商性(Scollon & Scollon,2001)。
4. 形象话语建构的类型
形象话语建构的类型可以从建构取向、建构主体两个方面来划分。
1) 基于取向的形象话语建构类型
Arkin(1981)在研究中提出自我呈现可以分为获取型(acquisitive)自我呈现和保护型(protective)自我呈现,分别表现为行为人希望主动争取的积极形象以及行为人希望能够避免的消极形象。Alicke & Sedikides(2009)认为自我呈现研究关注的取向主要表现同样为两极式,即自我提升(self-enhancement)和自我保护(self-protection),或自我提升和自我贬低(self-denigrating)(如Schlenker & Leary,1982)。因此,我们似乎可以将形象话语建构笼统地区分为积极形象和消极形象的建构。不过,我们可以借鉴相关文献做进一步的细分。Spencer-Oatey(2008)提出,在人际交往中,交际者能够从四个取向对关系进行管理,分别是关系提升取向(强化或加强交际者之间的和谐关系)、关系维持取向(维系或保护交际者之间的和谐关系)、关系忽视取向(对交际者关系质量不关心或不感兴趣)以及关系挑战取向(挑战或伤害交际者之间的和谐关系)。陈新仁(2018b)则将关系伤害独立出来单独作为取向的维度之一,把关系管理取向分为五类。据此,我们可以更为细致地区分形象话语建构的取向,如表1所示:

表1. 形象话语建构的取向
2) 基于主体的形象话语建构类型
Tracy(1990)曾提到,交际作为一个由交际双方乃至多方共同参与的社交活动,交际者不但会进行自我呈现,也会呈现他们如何看待他人,后者便是他人呈现。由于交际活动的复杂性,除了自我呈现、他人呈现外,社交活动还包括共同呈现。相应地,形象话语建构从建构主体来看,也包括自塑、他塑和共塑三个类型。自塑形象指的是交际者对自我形象的建构,比如“我这个人最投桃报李了”;他塑形象指他人对自我形象的建构,比如在上文的例4中X教授的有成就的青年学者形象便是由主持人建构的他塑形象;共塑形象则指的是由交际双方或多方共同建构的形象,试看例5:
例5 窦文涛: 他做的这个吉他真是寄托着他的爱,我听说跟你三个女儿的名字的这个字母有关系?
李宗盛: 对,反正我这个人很family,我是巨蟹座的。
例5中窦文涛提到李宗盛用女儿的名字为吉他命名,通过话语内容建构了李宗盛非常爱女儿的父亲和音乐人形象;李宗盛则在后续的回应中先是直接表达认同(“对”),然后使用了非常显性的形象标记语“我这个人很family”,回应了主持人对自己的形象建构。因此,在该例中,窦文涛的话语内容和李宗盛的形象标记语共同建构了后者热爱家庭的形象。
5. 形象建构的话语实践
上文中我们提到,在社会建构论的理论框架下,形象能够通过不同类型的话语实践来实现建构。形象建构的话语选择类型在不少批评性话语分析研究中也有探究,大多基于系统功能语法来进行考察,适合通过“更加精细的语料库数据,对及物过程和参与者、评价理论、名词化和语法隐喻、以及主位-述位结构做出[……]更加复杂的理论阐释”(董敏,2017: 38)。考虑到形象的话语建构不仅涉及语言形式的选择,而且依赖话语内容的选择,笔者并不认为这一框架完全适用于形象的话语建构研究。同样,现有语用学视角下的形象策略研究涉及到的话语类型则较为单一,大多与社会心理学领域(如Kowalski & Leary,1990;Schlenker & Pontari,2000;Alicke & Sedikides,2009;Schlenker,2012)提出的自我增强、自我贬低的自我呈现策略相关。
Spencer-Oatey(2005)曾提出交际中关系管理话语的选择具有规约性(regularity),体现为以下五种语言域的选择(Spencer-Oatey,2000,2005,2008): (1) 言语行为域: 具有关系威胁、关系增强倾向的言语行为,如道歉、请求、称赞等;(2) 话语域: 交际过程中的话语内容和话语结构,具体包含话题选择、话题管理、信息组织和信息排序;(3) 参与域: 交际中的程序化部分,譬如话论转换、对于在场第三方的融入或排他、对于受众(言语或非言语)反应的重视或忽略;(4) 文体域: 交际的文体部分,如音调、与体裁相适应的词汇或句法选择、与体裁相适应的称呼语或敬称的选择;(5) 非言语域: 交际中的非言语部分,譬如姿势以及其他肢体动作、眼神接触。Chen(2022)在此基础上结合语料勘察了身份工作的话语实践方式,提出在进行语用身份建构时,交际者会在称呼和指称域、言语行为域、文体域、参与域和非言语域中进行话语类型选择并实现身份工作。
鉴于形象是语用身份的维度之一,形象建构也与关系管理有着密切联系;此外形象建构本身也是身份工作的维度之一。因此,形象的话语建构同样可以从称呼与指称域、言语行为域、话语域、参与域、文体域和副 /非言语域进行建构。
1) 称呼与指称域
称呼与指称域话语指的是交际中交际者对于自我、交际对象或第三方的称呼或指称(Chen,2022)的话语选择,在形象建构过程中,交际者对于称呼或指称的选择能够帮助建构自我或他者的形象。请看例6(转引自陈新仁,2018a: 78):
例6 莫非这枚邮票有文章?我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之感。这位先生问我:“陈老头,不,陈老先生,你这邮票可以交换吗?”“不!”“可以卖给我吗?”
这个例子中,“这位先生”对“我”的称呼发生了一个即时的变化,由“陈老头”变为“陈老先生”,可见对方对“我”的身份选择发生了即时变化(陈新仁,2018a)。然而在此处,称呼语的变化不仅体现了交际者为他人进行身份选择的即时调整,也体现了交际者个人建构的形象在发生了由不礼貌、不尊重人的形象到礼貌、毕恭毕敬的形象的转变。
2) 言语行为域
形象建构的言语行为域话语指的是在交际中,在说话人以特定身份说话时,能够帮助对其形象特征加以呈现的言语行为,譬如自我提升/自夸、自贬、问候、道歉等。请看例7:
例7 某教授: 如果你对实验对象进行选择的时候,这个其实是作假行为的,这个是学术作假的事情的,所以……,其他的太……太……。但是我问题说这个问题一定是要考虑。
说话人先是对学界某种现象作出了断言,接着在划线部分中止了上述批评,提到“但是问题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即解释说明前文表述的批评并不是针对某一具体事迹或者对象,也并不清楚当前学界是否真正存在以上问题,之后又做出自我否定“这话是不对”。通过上述的描绘和话语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学者在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表述的过程中,进行了两次自我修补,第一次修补了的“实验对象选择”的存在真实性,第二次通过自我否定修补了“作假”的严厉批评。通过上述一系列的自我修补行为,我们可以看出该教授在进行学术讲座的过程中,对自己的话语表述有着高度的自我监控意识,并及时作出调整。这种调整性的自我修补行为可以建构该学者在当下场景中作为一名报告人发言谨慎的形象。
3) 话语域
话题和话语内容的选择对形象建构具有直接影响。试看例8:
例8 某教授: 我和王教授主要是想把外语教育学作为一个学科来设计。那么这样的话,在讨论这个之前,我们就需要首先来明确一下,学科到底是指什么。
在例8中,该教授便对信息呈现方式进行了管理: 在引出此次报告的核心话题“外语教育学的学科设计”后,首先对核心术语进行了界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该教授对于报告信息内容的呈现的设计,能够帮助呈现严谨的形象。
4) 参与域
参与域指交际者在对话中的参与情况(袁周敏,2016),比如话轮转换、对于在场人员的纳入或排出、对于听话人回应的采纳等(Spencer-Oatey,2008: 20)。请看例9(基于蒋婷等,2016):
例9 1 仲裁员: 你说他没尽到责任,你要出示证据。
2 申请人: 不不不,你叫他把公证书拿出来看嘛。公证书拿出来。
3 仲裁员: 你不要求对方,是你主张,谁主张,谁举证。
4 申请人: 那……那个事实要以法律为准绳,要讲事实嘛
5 仲裁员: 不,我给你说,你
6 申请人: 那个要调查,哪个在这个文字上来搞嘛。为啥子我说你这个合同,那就是为啥
7 仲裁员: 不,你现在不说那些,现在合同上有一条,签合同付的7000块钱。他只有这一个条件,签合同就付7 000块钱。你看清楚合同。
在例9中,仲裁员两次打断了申请人的话语,通过参与域的话语资源进行了管理。首先在申请人两次拒绝了仲裁员在话轮1和话轮3的要求,并反复强调自己的需求时,仲裁员在话轮5通过话语标记“不”进行了首次打断以及“我给你说”的话轮控制语,之后当申请人在话轮6打断仲裁员的话语时,仲裁员在话轮7再次使用了标记词“不”,并使用“你现在不说那些”直接阻止对方的辩解,终止了对方的插话。仲裁员两次的“阻止式打断”(蒋婷等,2016)直接抢夺了话语主导权并控制话题走向,凸显了自身在该语境中的高权势,从而建构了自身的强势形象。
5) 文体域
文体域是交际者在交际中的交流风格和方式,譬如语调(严肃或玩笑)、体裁适应的词汇或句法的选择、体裁适应的称呼或敬语的选择。与形象建构相关的文体域资源包括但不限于人称指示语、元语用提示语(语用标记、自我指称)、形象标记语、低调陈述、话语正式度(白话或术语)等。比如上文例2中的“我这个人有点爱变”就是形象标记语,是说话人通过自我评价对于自身形象的直接建构。试比较:
例10 A品牌试衣间标识: 小心粉底别蹭衣服上
B品牌试衣间标识: 别让衣服蹭花您的妆容
例10中的两句话分别是两个品牌试衣间的提醒标识,从内容上都表达了希望顾客在试衣时要小心不要将妆容蹭到衣服上,但不同的是A品牌的提醒更加严肃、官方,B品牌则从客体角度出发,希望不要让衣服蹭花妆容,从语气来说更加和善、温和,因此分别建构了两个品牌严肃冷漠和温和体贴的形象。
6) 副/非言语域
副/非言语域即与交际同时发生的非言语或附属言语的部分,非言语资源包括但不限于肢体动作、面部表情、眼神,副言语资源则包括笑声等。比如Sampietro & Sánchez-Castillo(2020)统计了西班牙政客Santiago Abascal的社交媒体中的所使用的话语选择和表现出的视觉因素(如视线、手势、面部表情等),发现该政客在使用第二人称单数代词“你”来指代社交媒体阅读者时,会直视镜头,从而获得对视的效果;而在提到其他政党时,不同的非言语资源如朝其他方向的手势、愤怒的表情等都占据较大比重;由此,该说话人建构了自己善于表达的政客形象。
6. 结论
本文以形象的话语建构观为理论导向,探讨了形象建构的内涵、类型和话语实践。研究表明,形象的建构可以体现为作为目标的建构、作为手段的建构和作为过程的建构。关于形象建构的具体取向类型可以从取向与主体两个方面来区分: 就取向而言,形象建构可以区分为形象提升、形象维持、形象忽视、形象挑战及形象伤害;就主体而言,形象建构包括自塑、他塑和共塑三种类型。此外,形象的话语建构可以发生在称呼与指称域、言语行为域、话语域、文体域、参与域和副/非言语域。本研究通过对形象话语建构尝试展开较为系统的探索,希望能够深化对相关现象的认识,同时能对未来形象建构的研究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分析框架。
需要承认的是,由于形象概念本身在现有研究中并没有统一的界定,因此本研究对于形象建构的理论探讨只是基于身份研究、面子研究和自我呈现研究展开,未必全面。同时,本文对于形象话语建构的讨论主要涉及社会个体,对于机构及国家层面的形象建构的特性着墨不多。此外,研究对于形象话语建构类型的归纳具有一定的探索性,难免挂一漏万,其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也有待在未来的研究中结合语料加以佐证、查缺补漏并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