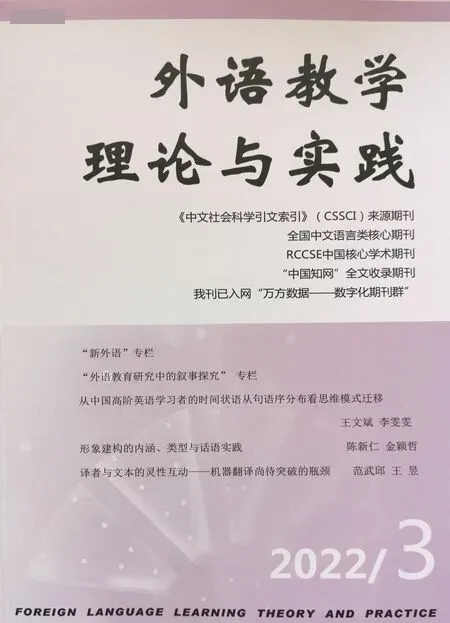从中国高阶英语学习者的时间状语从句语序分布看思维模式迁移*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
王文斌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北方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李雯雯
提 要: 本文主要究考英汉本族语者及中国高阶英语学习者时间状语从句语序分布的动因。研究发现: 1)英语时间状语从句前置或后置于主句均可,但以后置为其语序主导性倾向;2)汉语时间状语从句以前置为其绝对优势语序;3)中国高阶英语学习者习得英语时,其时间状语从句的语序分布也明显呈现出前置倾向,偏离了英语目标语的语序主导性倾向,这不仅关涉表层的语言迁移和深层的概念化迁移,而更与其基底的思维模式迁移相关,其根源在于王文斌(2013a,2013b,2019)提出的关于英语民族的强时间性思维特质和汉语民族的强空间性思维特质差异。
1. 引言
不同的民族对世界往往具有不同的信仰和经验,既表现于主观认知系统,也表征于自然语言构造(戴浩一,2002: 2-4)。而自然语言是由符号组成的系统,其特征之一就是各符号的组织具有顺序性,即语序。在语序中,语言符号或单位在句子中呈线性排序,具有自身的顺序规律。时间状语从句是自然语言的普遍现象,其主要功能是说明事件或行为的时间。然而,在不同的语言中,时间状语从句具有不同的语序分布,其句法特征往往具有独特性。英汉时间状语从句在语序分布方面就存在明显差异,如:
(1) a. Stand clear of hazard areas
b., stand clear of hazard areas.
c.,禁入危险区。
d.禁入危险区,。
例(1)说明,英语时间状语从句可前置也可后置于主句,如(1a、1b),而汉语时间状语从句则通常不能后置,如(1d)。以往关于英汉时间状语从句语序的对比研究多偏向于现象描写,尚未探及根源性的制约因素。诸多对英汉本族语者及英语学习者时间状语从句语序分布动因的研究也仅涉及语言形式层面,缺乏对其本质性根由的考索。时间状语从句的语序分布虽是自然语言中的一个句法现象,但其背后隐匿的是人类大脑认知的策略和不同民族思维模式的偏好。我们认为,对英汉认知顺序差异的对比有助于深度认识这两种语言的特质以及潜隐于语言背后的民族思维特性,而对二语学习者语序习得的探索则有助于从深层次上洞察语言习得的认知动因,窥探语言习得的规律,促进教学效果的提升。有鉴于此,我们拟以中国高阶英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针对学习者时间状语从句语序的分布特征及认知动因展开讨论,旨在从深层次上检视母语迁移发生的认知因素,剖析隐藏于语言习得表象背后的民族思维根由。我们在此主要追问三个问题: 1) 英汉时间状语从句语序分布为何存在明显差异?2) 这种差异会对二语学习者的习得造成怎样的影响?3) 学习者的语序分布特征源于怎样的深层动因?
2. 英汉时间状语从句的语序分布及动因
上文已提及,所谓语序,就是各符号的组织具有顺序性。说得详细一点,语序就是语言中各级单位按照一定的时间或空间排列而形成的线性顺序(吴为章,1995: 429)。面对相同的客观世界,不同语言可以对同一现实使用不同的认知策略,并由此构造表层语言形式的序列(张敏,1998: 161)。因此,语序不仅是自然语言编码的形式表现,更是反映人类思维及其认知顺序的重要手段(卢卫中,2002: 5)。人类对客观事物的感知方式会影响语言成分的排序(秦洪武,2001: 40),因此,不同语言具有不同的语序规律。
1) 英汉时间状语从句语序主导性的不同倾向
基于对40种语言状语从句语序的研究,Diessel(2001: 433)认为状语从句与主句的相对位置通常存在两种类型: 第一,从句既可位于主句之前,也可位于主句之后;第二,从句位于主句之前。英汉时间状语从句的语序分布规律遵循以上原则(Quirk,1972: 607;Biber, 1999: 802;Diessel,2005: 449-470;Wang,2006: 49;张斌,2010: 663;刘月华等,2012: 518)。以往学者基于Brown、BNC、ICE-GB英语本族语者语料库对英语时间状语从句的考察显示,分别有81.63%、70.29%和70.88%的从句后置于主句(Diessel,2001: 444;谭晓梅,2006: 47;Diessel,2008: 473)。而针对汉语时间状语从句的研究,Chen(2000: 366)、陈春华(2004: 76)、Wang(2006: 54-56)、谭晓梅(2006: 47)和宫同喜(2014: 89)发现,几乎所有从句都前置于主句,其前置率分别为97%、98%、99.5%、100%和99%。可见,英语时间状语从句以后置为语序主导性倾向,而汉语时间状语从句则以前置为绝对优势语序,二者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
2) 英汉时间状语从句不同语序分布的认知动因
英汉时间状语从句具有不同的语序表现,其前置与后置的功能和动因也截然不同(Chen,2000: 365;Wang,2006: 52)。语序表达受多种因素制约,学者已从语法、句法、语篇、认知等多个层面进行了考察。
语法层面,石毓智(2010: 13-17)认为语序和语法存在互相制约的关系。英汉语言均需借助语序安排句子成分的先后次序,但其依赖程度存在强弱之分。英语为形态型语言,语序在整个语言组织中处于相对次要地位;汉语为分析型语言,缺乏形态标记,语序是确保其语义连贯完整的主要手段(潘文国,2010: 271-293)。英语句型重形式组合原则,更受形式化原则的制约,依靠形态变化表达句子各成分之间的先后关系,借助谓语动词的时体标记明确时间关系和意义;而汉语句型重概念组合原则,更受概念化原则的制约,具有较多的直接投射,因而语序是其最重要的语法表达手段之一(戴浩一,2002: 10)。英语用语法标记表示语法意义,汉语则往往用语序来表达,比如时间信息。这也合理解释了为何相较于英语,汉语时间状语从句的语序更为固定。
句法层面,Hawkins(1994: 360)认为自然语言的语序会受句法加工难度的制约。对于英语而言,从句后置比从句前置的句法加工难度更小。受工作记忆的限制,人们倾向于选择句法加工难度较小的语言结构。刘金路(2017)基于《纽约时报》的研究发现,状语从句是其构成的英语复合句句法结构难度增加的关键要素之一,前置状语从句的句法复杂度显著高于后置状语从句,即前置从句更难加工。因此,英语从句更偏向位于主句之后。句法加工难度对认知负荷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自然语言语序的选择。
语篇层面,陈春华(2004: 75-79)指出,时间状语从句位置的选择要从该句子与其上下文之间的逻辑关系出发,考虑语篇连贯问题。汉语状语从句通常前置于主句,这种语序特征的形成正是受到语篇信息需要的驱动(Wang,2006: 78)。前置状语从句通常包含旧信息,为正在进行的话语组织信息流,其功能是与前面的话语之间起到主题连接作用(Diessel,2005: 449-470),为话语发展建立某一背景,为句子提供主题或方向信息,并对主句的理解起到指引和限制的作用或起到话题转变的过渡作用(Charf,1984: 437-449)。汉语时间状语从句倾向于前置于主句,为主句提供背景框架,在语篇层面起到主题句的作用,同时预设下文内容(Wang, 2006: 52)。时间状语从句可以使时间指代由宽泛过渡到具体,也可以由具体过渡到宽泛,同时兼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将上下文有效连接并形成对照(Chen,2000: 365-366)。不同的是,后置状语从句的作用通常是补充主句信息以及提供新信息,或者提出事后的想法(Diessel,2001: 345-365;Wang,2006: 52)。因此,前置从句具有更突出的语篇功能。
认知层面,Diessel(2008: 465-490)基于语料库对英语时间状语从句的语序进行研究,发现时间顺序象似性是状语从句语序分布最为重要的认知动因,语言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是概念结构的反映。语言结构的特点反映了大脑中语言相关区域的内在组织和功能特点(Talmy,2000: 334)。认知语言学视域下的焦点-背景(Figure-Ground)原则是从空间关系的角度描述复句中主句和从句的关系,从句事件一般是主句事件的前提或起因,因此从句对应背景,主句对应焦点(Talmy,2000: 321)。英语母语者习惯于先交代事件主体信息,时间状语从句遵循时间顺序象似性(Croft,2003: 102;Diessel,2005: 449-470;2008: 465-490);而汉语母语者则倾向于先交代事件背景信息,时间状语从句遵循空间顺序象似性(李锡江,2016: 683)。时间顺序象似性和空间顺序象似性的认知基础为英汉时间状语从句的语序分布提供了合理的解释。英语焦点先于背景(Talmy,2000: 321),这是英语无标记的标准结构(Clark,1971: 266-275),而背景先于焦点的英语结构则属于特殊的、有标记的句式,往往需要特定的衔接条件或是出于修辞、风格上的考虑;汉语背景先于焦点,由参照体到目标体的句式是惯常的、无标记的,这是汉语偏正复句的基本语序(赵世开,1999: 28-31;张璐,2002: 13;张斌,2010: 663)。焦点-背景的认知功能已深入语言系统和认知系统之中。英汉语序的不同并非是参照体的不同,而是人们认知策略的不同(张璐,2002: 11)。英汉语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焦点、背景的先后顺序就是英汉民族不同认知策略的体现,说明两个民族的认知方式存在倾向性差异(刘宁生,1995: 85;赵世开,1999: 28-31)。
在不同语言中,以及在同一语言的不同结构、不同历史时期,动因竞争会导致不同的语序分布结果,也促成了语序类型学上差异的存在(张敏,1998: 185)。总体上,语法因素和句法加工难度的制约为英语时间状语从句的后置偏向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与合理的解释;而汉语时间状语从句的前置倾向主要受到语法因素和语篇因素的驱动。作为“语序一般规则”,时间顺序原则(戴浩一,1988: 10)是自然语言语序的基本原则,但自然语言的语序可能同时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语言的组织信息原则并不是单纯的语法临摹现象,而是语法系统内部长期发展整合的结果。现实规则并不能直接或者必然地投射到语言中去,它们对语法规则的影响受到语言结构特点的制约(石毓智,2010: 29)。语法、句法、语篇、认知等多重因素会影响一种语言的语序特征,而这其中,认知因素对“语序一般规则”能起决定性作用(李锡江、刘永兵,2020: 91)。
时间和空间是事物存在的两种基本方式,更是人类认知体验中的两个关键概念。英汉语言的时空系统因物质条件的相似而具有类同性,而又因民族思维的彼此差异而不同。论及英汉的本质性特质差异时,王文斌(2013a: 163;2013b: 29;2019: 4)提出英语具有强时间性特质,而汉语则具有强空间性特质。前者表现为通过主句和从句中谓语动词形态变化的时体标记表达时间概念,借以定位事件与事件之间的时间先后,指明事件不同的行为、动作和状态之间的时间关系(赵朝永、王文斌,2017: 18),而且具有强制性。英语复合句以主句的谓语动词为轴榖,形成前呼后拥的时间链(崔靓、王文斌,2019: 31),即主句谓语动词的时体标记是时间信息的核心,而时间状语从句并非时间信息的必要载体,可前置亦可后置于主句,而且从句倾向于后置则是由于英语惯于突显主句谓语动词所表达的动作行为及其事件,主要是对主句动作加以限定或补充,辖域较窄,仅关涉局部的语义关联;而后者,即汉语,因缺少谓语动词的时标记而需借助前置的时间状语从句锁定相关时间信息,对整个事件加以限定或提供必要的时间语境信息,对多个事件的时间进行定位,辖域较宽,涉及既离又合的语义关联,既可提供可转换为具有空间特性的背景作为参照,又可以此统摄全句语义,以表达空间关系从大到小的特有方式来表达时间,这是汉语强空间性特质的体现。
探讨一种语言的时间性或空间性,主要是观察一种语言有别于其他语言的不同表现形式或结构,而语序分布便是汉语有别于英语的重要表现形式或结构。通过对英汉时间状语从句语序分布差异及其动因的对比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对于发生在特定时空中的事件,英语和汉语母语者都会借助特定的方式把事件突显出来作为认知焦点,将时空信息作为参照背景,从而实现对事件时间的定位。所不同的是,英汉两个民族往往遵循相反的认知顺序。这两种语言语序分布的差异表面上看是语言之间信息打包方式的不同,而深层次上却是两个民族认知习惯差异的反映(李锡江、刘永兵,2020: 91-92),彼此在时间状语从句的语序分布上表现不一,缘于英语的焦点优先和汉语的背景优先,其本质是语言背后所隐藏的英汉民族在认知方式和思维习惯上的差异,彰显出英语民族的强时间性思维和汉语民族的强空间性思维。
3. 中国高阶英语学习者时间状语从句的语序分布及认知动因
中介语是二语学习者产出和使用的语言,其语言系统处于母语与目标语之间(Selinker,1972: 209-231)。母语和目标语在认知方式、认知策略和民族思维方面存在特质差异,都会给学习者造成习得困难,而英汉时空性思维特质的差异对汉语母语者的英语习得过程具有显著影响(王文斌、陶衍,2020: 7)。中介语作为一种过渡性语言,其语序分布的特征及认知动因值得深入探究。
1) 中国高阶英语学习者时间状语从句的语序分布
中国英语学习者时间状语从句的语序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前置倾向。针对这一现象,陈春华(2004: 77)、谭晓梅(2006: 40)、方子纯(2009: 59)和李锡江(2016: 686)基于CLEC语料库和SWECCL 2.0语料库等,对中国英语学习者时间状语从句进行了考察,发现when引导的时间状语从句前置率分别为76%、71.92%、73.02%和70.37%。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高阶学习者的从句前置率为58.79%。可见,即便是中国高阶英语学习者,其时间状语从句语序分布仍偏离英语目标语的语序主导性倾向,与英语本族语者(ICE-GB语料库)存在显著差异(=91.829, df=1,P=0.000),具有明显的前置倾向(王文斌、李雯雯2021a: 40)。
由此可见,中国高阶英语学习者时间状语从句的语序分布与英语目标语偏向于从句后置的语序主导性倾向存在明显的不同,如:
(2) John heard the explosion from his office. (英语本族语者时间状语从句后置)
(3),上课铃响了。(汉语本族语者时间状语从句前置)
(4), he realized it was late.(学习者时间状语从句前置)
2) 中国高阶英语学习者时间状语从句语序分布的认知动因
我们认为,对于中介语时间状语从句语序分布的探索,不能仅局限于语言层面现象的观察和描述,还需解释语言背后的深层认知动因。以往针对中国英语学习者时间状语从句语序分布动因的研究,学者更多从语言迁移的角度来考量(陈春华,2004: 77;方子纯,2009: 59)。语言的形式系统受制于其概念系统,因此也有学者从概念性迁移的角度开展对中介语的探究(李锡江,2016: 682-692),把停滞于语言表层形式的观察和描写引入概念层面的阐释。
概念性迁移假说(conceptual transfer hypothesis)认为,学习者在习得一种语言时所获得的概念(concept)和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会影响其对于其他语言的使用(Jarvis,2007: 53)。概念是人类对于世界一般知识的内在组成部分,是人们基于身体体验而形成的对某类基本相同或相似事物的心理表征,是一种离线产出,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概念化是对既有概念的激活和加工,是个体参与世界活动的基本方式,是一种在线或即时思维,具有动态性、互动性、图示性和想象性等特征(Slobin,1991: 7-25;Jarvis,1998: 8; Pavlenko,1998: 1-19; Jarvis & Pavlenko,2008: 115;Langacker,2008: 43)。Langacker认为,概念化是一种认知活动,是人的思维对眼前现实现象概括的结果,反过来决定句法结构(转引自石毓智,2006: 45-46)。这说明,语言的句法结构并非自主,它受制于现实现象和人类认知。概念结构深刻影响句法结构,语言现象是概念结构概念化的结果。对于同一类现象,不同的民族因其概念结构的不同而可能采用不同的概念化方式。换言之,不同语言的语法差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其概念化方式的不同造成的(石毓智,2021: 703)。一种语言所遵循的组织原则往往使得该语言的整体结构特性具有系统性与和谐性(石毓智,2010: 21)。每一种语言都有各式各样的语法标记和结构形式,而每一种语法手段都有自身的表征、功能和使用规律。这些具体的语法形式背后所隐藏的是更高的组织原则,即信息的概念化模式,制约着各种具体结构的顺序。概念化差异引起的跨语言影响并非来自于不同的概念储存,而是取决于哪种概念被选择,以及在信息加工过程中如何有序地排列组织信息(Jarvis,2007: 43-71)。不同母语者对当前现实世界中事物的意象基本相同,但不同语言使说话者在把思维变成语言时对这些意象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包括选择哪些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组织形式等(Slobin,1991: 7-25)。这些观点可以合理解释为何有些语言从句前置,而有些则后置(戴浩一,2002: 1-12)。
本族语者对时间状语从句语序的偏爱反映了本族语者的概念化模式,中介语呈现的语序分布倾向也自然能昭示出学习者的概念化方式。母语和目标语的概念结构差异引起概念迁移(concept transfer),而母语和目标语不同的概念化模式则诱发概念化迁移(conceptualization transfer)。前者发生在学习者的概念集层面,由储存在二语使用者长时记忆中概念范畴的跨语言差异引起,强调已有的大脑概念结构对其他语言学习产生的影响;而后者则发生于学习者的概念加工和在线思维过程中(Slobin,1996: 70-96),源于二语使用者在工作记忆中处理概念知识、形成临时性表征时的不同跨语言方式,强调学习者在不同语言在线思维模式中的差异(Jarvis,2007: 53-56)。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概念性迁移是上位概念含纳概念迁移和概念化迁移。可见,学习者发生概念性迁移的根本原因是其母语与目标语概念系统和概念化模式的差异(Jarvis & Pavlenko,2008: 122-148)。英汉时间状语从句在概念结构层面存在相似性,均可借用从句的形式来表达和限定主句事件的时间,这样的相似性有利于学习者对时间状语从句这一语言结构的认知,但其在概念化模式方面却存在差异性,呈现不同的加工方式和加工过程,形成了不同的语序特征,这样的差异性阻碍了学习者对英语时间状语从句语序的习得,使其偏离了目标语语序主导性倾向。母语的概念化模式占据学习者的认知主导地位,这会干扰学习者对目标语概念化模式的认识和习得,制约其对目标语概念加工方式的重组和生成。中国高阶英语学习者时间状语从句偏离英语目标语语序主导性倾向,其主因是学习者对英语概念化模式缺乏足够的认识,导致他们用汉语的概念化模式支配英语的形式表征。近来,国外学者在这方面的实证研究重点关注对学习者认知过程的探索,为概念性迁移研究提供了诸多实例和证据(Tang et al.,2020: 205;Wolter et al.,2020: 595;598),印证了概念性迁移对学习者二语习得的影响,进一步促进了概念性迁移研究的发展。
4. 思维模式差异与思维模式迁移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心理基底(underlying)结构的外在表现,能反映出一个民族的特殊性。民族思维方式是指在一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那些能持久、稳定和普遍起作用的集体性思维方法、思维习惯、对待事物的审视取向和众所公认的观点。思维方式是从方法论角度对民族文化和其他实践活动的一种抽象,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张岱年等,1991: 206-207)。由此可见,思维方式是概念和概念化的基底要素。
如上所提,语序是人类对事物和事件认知顺序在语言形式层面的映射。英语和汉语在语序上存在不同,这反映出两种不同的民族思维方式、不同的概念化过程和认知倾向。焦点和背景在语言信息结构中的不同突显方式决定了语言结构的线性排序。英语语序中焦点先于背景的认知基础映照经验结构的时间顺序,而汉语语序中背景先于焦点的逻辑依据彰显经验结构的空间顺序(俞咏梅,1999: 28)。在此不难想见,英汉语序分布的差异缘于英汉民族对焦点和背景的认知顺序差异。人类虽生存于同样的物质世界,使得英汉民族对语言和概念中焦点和背景的匹配具有相同的认知结果,即以中心事件为焦点,以时空参照为背景,但其感知焦点和背景的方式却存在差异。根据von Stutterheim(2003: 186)对概念性迁移研究范围的阐述,言语生成前的概念计划过程包括切分、选择、构架和排序四个阶段。对于在时间上两个关联事件的识解,英语和汉语母语者在事件切分和信息选择方面没有明显差异,但是在信息构架方面却有区别,彼此分别依照时间顺序和空间顺序组织信息,其概念化模式存在差异,从而导致在信息排序上主、从句语序的差异(李锡江,2016: 688)。而概念化模式的差异,其根源在于民族思维的差异,即思维模式差异(difference in the mode of thinking)。在此所言的思维模式差异,是指不同民族在认知事物的角度、方法和概念组织方式上的集体性差异,根植于各民族的基底观念(the underlying concepts),是不同语言认知策略差异和概念化模式差异的根源。思维模式是一个民族内在的共有的本质属性,对一个民族的语言和认知起决定性作用。
语言的形式系统无法独立于语言的概念系统,而概念系统会深受集体文化经验的影响(戴浩一,2002: 3),更与思维模式密切关联。学习一门新的语言,不仅要学习其语言形式和语言系统,还包含全新的观察世界的方式(Bylund & Athanasopoulos, 2014: 954),即思维模式。我们学英语,常强调要学会用英语思维(Think in English),其实就是强调要学会使用英语的思维模式,而不仅仅是用英语进行表达和概念化(Speak in English and Conceptualize in English)。要了解一门语言,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这门语言创造者和使用者的民族思维特质(diSessa, 2014: 92)。思维是语言的内容,语言是思维的外壳,其表征形式的根源在于思维,即语言作为思维的一种介质将思维外化于形,思维则借助语言这一介质得以外显,但思维必然带有民族性,将民族所特有的思维方式通过语言得以传达(王文斌,2019: 14;崔靓、王文斌,2019: 37)。Wierzbicka(1979: 313)强调,每一种语言在其结构中都会体现出某种特定的世界观。换言之,一个民族的语言往往能昭显出民族的思维特质。季羡林(2002: 2-4)也曾强调:“语言之所以不同,其根本原因在于思维模式的不同。”
任何语言虽都兼具时间性和空间性,但不同的民族思维模式会造就不同的民族时空意识,形成强时间性思维特质或强空间性思维特质的差异,投射到概念层面,表现为不同的认知顺序,而映照到语言层面,就表征为不同的语序偏好。英汉时间状语从句的语序差异便是英汉语民族的思维模式差异在语言结构编码中的外化。英语民族对事件的认知倾向于时间视角,而汉语民族的世界经验方式则偏爱空间维度。英汉民族思维之间的这种差异,表征于语言表层,是语言结构和表现形式的差异;体现于概念深层,是概念结构和概念化模式的差异;追根于基底的思维层面,是英汉强时间性思维和强空间性思维的差异。
如上所提,母语和目标语的不同会引发学习者的习得困难,中国高阶英语学习者时间状语从句语序偏离英语目标语语序主导性倾向,就是受到语言迁移和概念性迁移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基于概念性迁移研究的跨语言影响加深了人们对语言与思维关系的了解,有利于解释思维对语言的作用(张素敏,孔繁霞,2016: 17)。关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语言相对论与概念性迁移假说对此都尤其关注,但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关注语言对思维的影响,而后者更多关注思维对语言使用的影响,尤其是学习者通过一种语言获得的思维方式对理解或产出另一种语言的影响(Bylund & Athanasopoulos,2014: 954;张素敏,孔繁霞,2016: 13)。因此,在关注语言迁移和概念性迁移的基础上,我们还需关切不同民族的思维模式差异在语言习得过程中的关键作用。需指出的是,在此所言的思维模式迁移(thinking-mode transfer),是指学习者因受到一种语言思维模式的干扰而影响其另一种语言思维模式的建构和语言结构的产出,其研究重点在于探索母语思维对学习者思维模式及思维发展模式的影响。中国高阶英语学习者习惯于运用汉语的概念化模式加工英语的概念结构,用汉语的思维模式支配英语的形式表征,其根本问题在于思维模式的迁移,如:
(5) Not a single snowflake is innocent(英语本族语者时间状语从句后置)
(6),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汉语本族语者时间状语从句前置)
(7)not a single snowflake is innocent. (学习者时间状语从句前置)
(8) Things are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英语本族语者时间状语从句后置)
(9),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地提升。(汉语本族语者时间状语从句前置)
(10), China is becoming a very strong country.(学习者时间状语从句前置)
学习者因母语中突显的语言结构所形成的习得注意机制,会遮蔽或阻挡二语习得中构式的形义映射过程(Ellis,2006: 173-181;Ellis,2008: 383-389)。换言之,母语思维中已经固化的思维模式会干扰此后其他语言学习的加工方式。汉语时间状语从句的绝对前置优势作为汉语中突显的句法结构,会对学习者习得英语产生明显的影响。学习者对英汉语言结构和概念结构的配对理据缺乏充分的认识,惯于用母语思维习惯支配英语形式表征。学习者时间状语从句偏离目标语语序主导性倾向,看似只是表层的语言迁移,实则源于深层的概念化迁移,而其根源在于基底的思维模式迁移。英汉在形式结构、认知概念和思维模式上的差异导致了语言迁移、概念性迁移和思维模式迁移的产生,共同作用于学习者二语习得的形式表征(王文斌、李雯雯,2021b: 5-6)。思维模式迁移的根源在于英汉民族的思维模式差异,换言之,思维模式差异是思维模式迁移的根由。
思维模式迁移的提出标志着对语言迁移本质的考索从语言层面上升到概念层面继而深入到民族思维层面。这对二语习得研究和外语教学研究的重要启示意义在于促使人们认识到二语习得与外语教学需超越表层语言形式规则,注重对母语思维习惯的转换,辨析英汉在思维模式上的异同,深刻认识英语的强时间性意识(pro-temporal awareness)和汉语的强空间性意识(pro-spatial awareness),重构目标语思维模式,学会用目标语思维并习得二语。教师在教授目标语语言形式的同时,更应注重促使学习者洞悉形式背后的认知理据,调整学习者原有的思维模式,推进目标语思维模式的内化,从根源上克服母语迁移,实现母语和目标语在语言形式、概念化模式和思维模式层面的有效转换,促进中介语各层面的有效发展,其彼此的具体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二语习得思维模式迁移框架
5. 结语
近年来,学界多试图为错综复杂的二语语言迁移现象构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解释性理论模式,其深度前所未有。本文以王文斌提出的英汉时空性特质差异为视角,尝试从民族思维层面对语言迁移和概念性迁移研究做了思辨性思考和相关的英汉二语习得语言例证分析。本文首次对思维模式差异和思维模式迁移这两个概念进行了界定,以期为传统的二语习得研究提供一个新思路和新视角。然而,二语习得在多大程度上伴随语言迁移、概念化迁移以及思维模式迁移的发生,母语思维模式迁移的机制又是怎样在二语习得过程中运作?该如何通过实验手段加以验证?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今后继续深入研究。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思辨研究往往是一切研究的起点,而实证研究则是对思辨研究的验证。思辨研究主要在于“思”,而实证研究则主要在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