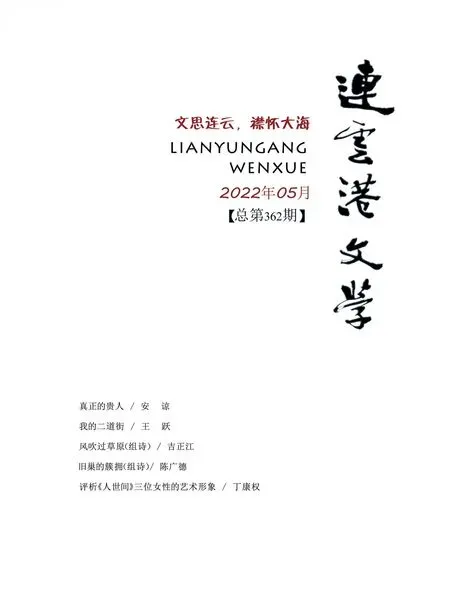野蔬帖
马 浩
贼 蒜
春风一起,野蔬便可上桌了。
人的胃口是有记忆的,这种记忆,往小里说,来于自己的儿时,往大里说,源自人类的童年。野蔬,饥年可供人度命,小康日子又成了春盘美味,锦上添花。
吾乡有种野蔬名曰“贼蒜”。野蔬本是清雅之物,怎么叫这么一个粗野的名字?这不得不说方言了,土语多形象传神,往往能抓住事物的特点,“贼”在方言的语境里含有皮实、古灵精怪、神出鬼没的意思。贼蒜,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冷不丁地就出现了,成片成片的,山贼一般声势浩大,又神出鬼没,当你要寻它的时候,却踏破铁鞋。
贼蒜,有的地方又称野蒜、野葱、野韭菜,其实,它有个很古雅的名字,薤,或者藠头。它有着蒜一样的鳞球状的根,叶神似葱,又仿如韭,瓜须般细长翠绿,随风而舞,有娉娉袅袅之态,茎在土下,银白如线,味道似蒜似葱似韭,而又似是而非,如同王右军书法,集众家之长而自成一家,别有风味。
“薤上露,何易晞。”这样的画面,对我来说,太熟悉了,晶莹的露珠缀在水绿的细叶尖,微风一吹,露珠便会如雨纷落,水意尚在,鲜嫩娇媚可人。一铁铲子下去,挖出白白的球根,便是藠头。
说到藠头,想到一则有关苏东坡的趣事。一天,好友请苏东坡吃藠饭,东坡一听就来了兴致,不想,仅白饭一碗,白萝卜、白盐各一碟,不禁哑然失笑。是东坡想多了,也难怪他想多,藠头,作为饕餮之徒的东坡,怎能不浮想。
在我的印象里,贼蒜多生在麦田、荒滩废地、土堰河边,常以麦苗、杂草为掩护,在风中得意地摇头晃脑,欲盖弥彰。它喜欢聚居,发现就是一片。贼蒜是针叶,看家的本事便是耐旱。不怕天旱,根就要深扎,挖时亦需顺应着它的特性下铲,否则,根挖断了,失其窈窕之美。
仲春,贼蒜的味道最为鲜美。此时天朗气清,田野随处可见挖贼蒜的人群。乡村的集市上,半条街都是卖贼蒜的,篮子接着篮子,青白素雅,低眉浅笑,一派旖旎风光。
时令野蔬,食的便是山野的清鲜。一般的野蔬,多有清寒苦涩之味,诸如荠菜、马兰头之类,需水焯,以除苦涩清寒之气,贼蒜却是个例外,可直接入口,挖出来,捋去碎土,放到嘴里大嚼,一股清鲜之气直冲眉心。
说来野蔬真是奇妙,贼蒜味道融蒜葱韭之味,又能独上高楼。家乡有种名为“黄瓜贵”的野菜,薅一株于手中搓揉,能散发出黄瓜的清香,乍暖还寒时,可聊解黄瓜之馋,非常奇妙。写贼蒜时,偶然想到,回笔入正题。吾乡吃贼蒜,通常有三种吃法,似乎颇具地方特色。
一是做菜煎饼的馅料,亦是最普遍的吃法。吾乡煎饼是主食,小麦在石磨上磨成糊,用铁鏊子烙。煎饼直径一尺有八,可以想见煎饼有多大。如今,手工煎饼稀有了。把贼蒜用清水洗净,切碎,都说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贼蒜切碎一饰两角,且远胜小葱与豆腐,放油和细盐,嗜辣者,可放红椒面,拌匀,红青白三色,很悦目,平摊夹在煎饼里,放到平底锅上塌。“塌”乃方言的音,意思是煎,远比煎贴切。煎饼塌得两边金黄,而贼蒜面不改色,椒面似乎更赤烈,丝丝热气从菜馅中冒出,鲜香四溢,尚未下口已垂涎。用纸包着煎饼一端,一口下去,酥脆鲜香,烫得龇牙咧嘴亦不自觉。
再者便是凉拌。洗净的贼蒜切成半寸长小段,加细盐、生抽、醋,拌匀,淋麻油数滴,佐酒就粥下饭卷煎饼无一不可,滋味岂一个鲜字了得。
三是烧豆腐。豆腐乃卤水老豆腐,俗话说,千滚豆腐万滚鱼,豆腐在小锅中咕嘟着,已过千滚,撒上切好的贼蒜,出锅装盘。别小瞧这一配角,可是贼蒜豆腐的精魂,豆腐的味道、品格提升岂止一个档次。
时令野蔬,食的就是时令,时机一过,已然成明日黄花。贼蒜秋天开紫色小花,亦可观,不能饱口福,可饱眼福。
荠 菜
荠菜可以说是野蔬中野蔬,不但滋味鲜美,还有故事、有学问、有性情、有趣味,被历代文人墨客吟咏。
面对荠菜,如醉春风。
荠菜:养胃、悦目、滋心。在此,不妨让我借用前人的材料,拼一盘别有风味的凉拌荠菜。
大凡野菜都有着不拘的个性,不为外物所动,否则,早就被收编了。古往今来,荠菜一直被人青睐,却始终守着初心。《诗经·谷风》中有“谁谓茶苦?其甘如荠”之句。那就先泡一杯“甘如荠”,诸君慢慢饮着,待我洗手入厨下。
荠菜不但被古人用以做羹汤,亦用来做时令菜肴。
宋人叶茵,闲散疏淡之人,与写《山家清供》的林洪是好友,一日路过渔村,被眼前的烟火情景所感,题《渔村》诗,“古柳溪头枕断槎,横篙挂网几渔家。得鱼去换红蒸米,呼子来挑荠菜花。”渔家的日子是清苦的,亦是温暖的,打来的鱼卖掉买米,让孩子到野地去挖荠菜为肴,桌子就摆在古柳下,一大碗碧绿的清炒荠菜,一大盆白米饭,一家人围坐着吃饭,倒有几分清雅之趣,至少在叶茵眼中是这样的。
与叶茵的旁观者不同,陆游独自在“幽居”中,食荠菜饼,就着槐芽腌制的咸菜,甘之如饴,不亦快哉。赋《幽居》诗,“宿志在人外,清心游物初。犹轻天上福,那习世间书。荠菜挑供饼,槐芽采作菹。朝晡两摩腹,未可笑幽居。”
以上是以荠菜做菜食的,其实,围绕着荠菜,还有诸多有趣的故事。宋代大词人辛弃疾,豪放派的代表人物,其笔下的荠菜别有一番风情。他的《鹧鸪天·春日平原荠菜花》:“春入平原荠菜花。新耕雨后落群鸦。多情白发春无奈,晚日青帘酒易赊。闲意态,细生涯。牛栏西畔有桑麻。青裙缟袂谁家女,去趁蚕生看外家。”词以乡野的荠菜花为背景,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唯美的乡间爱情故事,一位身穿青色裙子,披一袭白衣的养蚕女前往桑林赴约,多么美的场景,想来剧中的男子该手捧着一束素雅的荠菜花吧。
唐朝的高力士,因为李白脱靴而被为人所知,给后人留下不太好的观感,没想到他的“荠菜诗”写得实在不坏。《感巫州荠菜》:“两京作斤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有殊,气味都不改。”好像他蛮懂荠菜的,亦不知荠菜做何感想。
2.3.6 修剪:当苗木新梢长到10cm左右时,选择1主干直,生长势强的新梢作为保留枝,其余枝条剪除。6月中旬对保留主干上的叉枝进行剪除,有利于养分集中提供给主干枝条。7月上旬,对主干枝上的叉枝再进行剪除,有利于培育通直的主干。7月中旬剪枝时要注意,剪除与主干争养分的徙生枝,以及剪去主干70cm以下的叉枝,只保留主干70cm以上的叉枝,因为此时苗木进入生长旺期,过度的剪枝对苗木会造成伤害,又不利于苗木的光合作用,会导致苗木徙长而细小;因此适当保留 主干70cm以上部分叉枝,有利于培育主干通直、粗细均匀的苗木。
宋人范镇,苏东坡的忘年之交。苏轼被贬黄州期间,曾一度被世人误传已仙逝,年事已高的范镇还让儿子前往黄州吊唁。苏轼的好友,大多是性情中人,范镇写的荠菜花,亦是颇有趣味。诗名《春》,“春入长安百里家,湖边无日不香车。一林柳色吾无分,看杀庭前荠菜花。”
写《小窗幽记》的明人陈继儒,写了一首《十亩之郊》,“十亩之郊,菜叶荠花,抱瓮灌之,乐哉农家。”青菜青,荠花白,生趣盎然,一派醉人的田园风光,浇菜顺便亦把荠菜浇了。
荠菜名为野蔬,实则被人们视为“家菜”,庭中院内,无处不有。荠菜不仅入诗,亦可入画,清代书画家郑板桥曾以荠菜为题材做过画,画已失传,好在有题画诗传世,诗曰,“三春荠菜饶有味,九熟樱桃最有名。清兴不辜诸酒伴,令人忘却异乡情。”从诗句中可想象画境,亦是一件有趣的事。
菊花脑
菊花脑,名字有点意思。脑者,头也,言下之意,说她是菊花的头。作为一种乡间野菜,何德何能成为菊花王国的首脑呢?
既然人们如此称呼她,自然是有道理的,不可能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菊花本身个性十足,不受百花之主东君的挟制,我行我素,狂放不羁,“我花开后百花杀”,百花迎着春风绽放时,菊花眼皮都不翻一下,顾自遵循着内心慢慢地生长,百花开得姹紫嫣红,菊花长得枝叶葱茏,一团浓绿。菊花脑有着一般菊花的品性,不过,她有个特长,是一般菊花所无,嫩嫩的枝叶,可作餐桌上的美味。
有大智慧者,多沉稳内敛,不事张扬。菊花脑看上去比一般菊花长得清秀,叶片细细碎碎的,依附的枝茎筋骨瘦硬,如果让她入画,枝茎就是一条细细的墨线,叶子便为乱点的磨痕,如此不起眼的菊花脑,把她掐下来,烧汤、清炒、凉拌,制作菜肴,食过之后,会让你眼前一亮,不怕你不记住她。
菊花脑,不会去迎合你的口味,你只有慢慢地适应,渐渐地接纳,不知不觉地就喜爱上了,接下来的事,便是让你回味她的种种好。
我第一次吃菊花脑时,不习惯她独有的味道。微苦,又不是完全的苦,似乎夹杂着一丝腥寒,隐含着淡淡的艾草气息。入口的刹那,有些抗拒,但慢慢地咀嚼,嚼着嚼着,就会感觉到丝丝缕缕的清香氤氲口中,不由地又让你伸出筷子。
菊花脑汤,估计是菊花脑的神来之笔,无论春季、夏季、秋季,有条件的,冬季似也可以做。烧制菊花脑汤很简单,没有多少花里胡哨的技术。掐一把菊花脑的嫩头,菊花脑是不怕掐的,她可以在掐断的枝茎上生出更多的枝芽,所以菊花脑越掐越旺盛,若不掐,反而保守不发,少了生机。新鲜的菊花脑的茎叶,用清水冲洗干净,放着备用,鸡蛋打好。那边开火置锅,根据自己的喜好,或放油加葱姜炒香加水,待水滚,把鸡蛋转着圈倒入锅中,蛋花浮起时,放入菊花脑,用铲子让其在沸水中打个滚,加盐少许;或直接用清汤烧制。无论怎么烧,菊花脑都碧绿鲜亮,似乎比生时更有质感。不像其他的菜,在沸水中往往残颜落色,面目全非。菊花脑汤,蛋花清白,菊花脑鲜碧,汤色豆绿,十分悦目,勾人食欲。
菊花脑,春季亦可凉拌,可谓清新脱俗,比荠菜、马兰头、枸杞头之类的野菜,还要养眼可口。鲜嫩的菊花脑用滚开的水汆过,拧干水,切碎拌以香干丁,或花生米,佐以姜丝葱花香醋麻油之类的调味,能吃出春的滋味。
清炒菊花脑,相对烧汤与凉拌,简便又省事。一般情况下,蔬菜喜欢与荤菜为伍,相互影响,互补渗透,相得益彰。可菊花脑特立独行,喜清欢,只做自己,你喜欢与否无关她的事。
有些清苦的菊花脑,却富含着蛋白质、纤维素、维生素,以及黄酮类物质。食之可以祛火凉血,滋肝明目,神清气爽。
金风吹来了,菊花开始粉墨登场,自然菊花脑也迎来自己的花季,一簇簇菊花脑顶着金黄灿灿的花朵,璨若星河,把秋天推向了高潮。偷闲半日,漫步秋野,采一束菊花脑的花枝插在瓶中,一屋的闲适,暖暖的秋意。
无怪名曰菊花脑,三季可食,一季看花,真是实至名归,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什么杯都不如众口交誉的口碑。
蕨 菜
不知因何,蕨菜对我来说,充满了神秘感。这种感觉,就像走进了一条凋敝幽寂的小巷,断壁颓垣,瓦砾上生满荒草,破败的窗棂上卧着慵懒的花狸猫,天色暗淡,有窸窸窣窣的声响从爬满薜荔的深院中传来,犹如人细碎的脚步,一种无以名状的惊惧,犹如寒意从胆边暗生。
蕨,身上似乎有种神性。
论资排队,大自然中,蕨差不多是元老级别的吧,可以说,蕨是看着人类一步步从森林走出来的,只是它拒绝岁月的叩门,有所摒弃,有所坚守,身上始终散发着神秘的幽光,让人知道敬畏。
古代,有两个殷朝的遗民,一个叫伯夷,一个叫叔齐,在周朝的统治下,心怀故国,不吃周朝的粮食,相约隐居到首阳山,采野菜度日。司马迁的《史记》中说“采薇而食之”,有趣的是,我读这段文字时,满脑子是蕨的形象。后来,还真让我在古诗中找到了佐证——李白的“有耳莫洗颍川水,有口莫食首阳蕨”(《行路难》)。
蕨,多生于山林,似乎亦是隐者。隐者多为君子,君子有成人之美,别说,蕨菜还真客串过月老的角色。“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诗经·草虫》)少男少女相约在林中私会,为掩人耳目,少女提着竹篮到山林里去采蕨菜,心上人迟迟不来,女孩子哪有心思采蕨。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人悟不透,蕨又不言。
我曾多次看过地球生物、人类的进化之类的史料及音像资料,无不有蕨的身影,看到蕨破土而出的样子,无端地想到人的胚胎。儿时,跟着母亲上山采蕨菜,蕨菜给我的感觉就像婴儿握着的小拳头,后来,随着年岁的增长,这种感觉又后退到了子宫的胚胎。
蕨菜,似乎在什么地方都能生长,印象最深刻的是生在井里。村中有口老井,井壁上长满了蕨菜,一簇簇,狭长的叶片深绿,努力向着井口,印象中,冬日亦不凋,始终没有机会验证。读书的时候,曾到山里采蕨菜的叶子做书签,我把这段记忆留在了文章《书签》里,夹在人生的册页中。
前些年,到浙江金华访友,友人相邀游“地下长河”。“地下长河”穿行在大山的腹中,上不见日月,下不着泥土,光线昏暗,空气潮湿。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里边居然生长着蕨菜,那散落在崖壁间的簇簇绿意,让人眼前一亮,心生暖意。一次,去重庆的石柱县,与好友逛菜市,菜市乃一条弯曲的小巷,菜摊子沿着小巷一直摆到巷子的深处。正是布谷啼鸣的暮春时节,卖新鲜蕨菜的摊子举目可见,卷曲如婴儿拳,又神似菊花的蕾扣,或散放在竹篮中,或扎成把码在白色的塑料布上,鲜嫩可感,在满耳朵的生鲜的方言里,一时之间,犹如梦里人。
这,似乎是蕨菜的别样滋味,其滋味越过味蕾一路形而上,然后,回到舌尖,回到青瓷盘中。(为什么是青瓷盘,而不是白瓷盘。)说蕨菜,当然是绕不过它的美味的。
鲜嫩的蕨菜,宜于烧汤,汤色碧绿。蕨菜脆嫩爽滑,入口鲜香,当心舌头顺着汤咽到肚子里去。时令野蔬,采摘要应时及时。为了便于储存,也为了过了时令,仍有野蔬可食,采摘新鲜的蕨菜,沸水汆之后,晾晒成蕨菜干,随吃随取。蕨菜干烧五花肉,家常菜,名字朴素,味道殊佳,别说吃,闻一闻,便是矜持的淑女,怕也要不断吞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