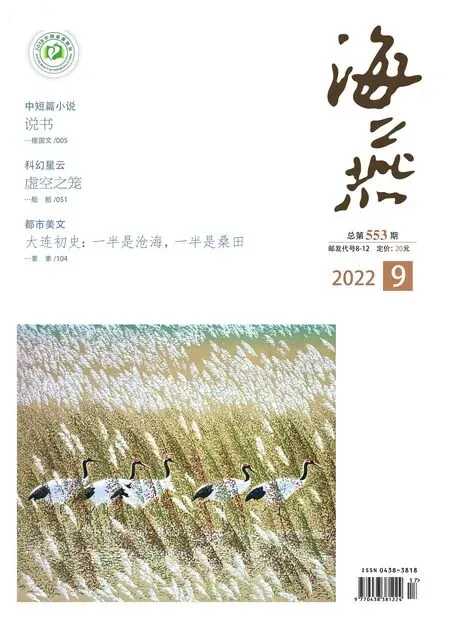陈响马和我隔着一堵墙
文 孙鲁梅

这首诗正在走向
寂静的尾声,像是来到了
它倾诉的草尖。那悬着的
露珠里藏着
我为你盖的小寺。而你
正在醒来的路上
路过那些雪,那些夜晚里
遗忘在水里的碎银子
现在都是你的了
——节选陈响马写给我的诗
一
唐宁再来时是个傍晚,夕阳将她一米六五的个子拖得像个模特。清隽又骨感。她把军绿色风衣脱下来跟她的背包一起,挂在博古架旁的衣架上。没等我动手她自己烧水,沏茶。就像当年她在这里给陈响马端茶一样,端给我第一杯。
唐宁回我话的时候也只是抬眼瞥了我一眼。她更多的注意力都在那茶盘上。洗茶涮杯不停下。
唐宁在这里上大学学的就是设计,干回本行那是自然的。她最初来书店做考试复习,甚至也是想过要考研的。那时候陈响马在,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那么用功了,跟在陈响马身后在店里打下手。后来毕业非要留下来。她是来店里第一个做工的大学生。我觉得她这样很可惜,大学白读了,鼓励她继续考研,给她一个专用的学习房间。怎想陈响马半年后就出事了,唐宁也追着陈响马辞职走了,我以为她会回河南老家。
她好像很渴,我没敢说什么,陪她静静喝了一壶茶。她又洗了一壶茶,动作才慢下来。我把身子向桌子前探了探。
“陈响马,还好吗?”问完身子又挪回来,“他还好吗?”
唐宁一直俯下的眼神更深地俯下去,盯着杯底的一朵莲花。热气像缭绕的雾升腾而出,没等绕过她盘起的发髻就消匿了。
“挺好,比原来看上去文气了。”唐宁端着水杯在鼻尖处晃了晃,没有看我。
“哦。”
她把茶杯放下,不再理我,站起身拿过她的蓝色背包,从里面抽出一个纸袋子递给我。
“陈响马给你的信。”
我有些惊愕地看了看这个纸袋子。
唐宁顺手喝空了那杯茶,抬起头看向我,绽开跟一进门时一样的笑眼,就像看墙壁上贴的廉价壁纸。
我也喝了一口茶把所有的追问一同咽进肚子里。
我没有留住唐宁,她说这次主要去学校跟同学见个面,就回历城,那边工作很忙。我把信封放到桌子上站起身送唐宁。唐宁的目光扫过信件又看向我,眼角的微笑在她明净的脸颊上消散掉了。
我从袋子里抽出三个信封。期望在陈响马的信里看到未知的部分。当然陈响马肯定在信里会跟我说。
陈响马虽然上学的时候不学无术,可字一直写得好,只是过于潦草,但在信封上“陈小安收”四个字却写得如小楷一般。右下角用美术字工整地写着日期。
二
安:
我并不擅长写信,上高中时调戏过几个女生,给人家写过纸条,仅此。但最起码的格式我还是知道的,得先说您好或者见字如面,但是我们俩就省了那些个客套话吧,没必要。而且就算站在你身边,有时都会觉得不真实。这感觉有点邪乎。从一认识你就这么邪乎。
我打算给你写信是进来后一个月就想好的,可是一直没有机会跟领导请示,我也怕写了白写,他们会给我撕了,因为我粗鄙不堪的词组。写这封信我是已经觉得能足够克制不说脏话。我想找个人说话,主要是我想跟你说说话。他妈的,我快憋坏了,从心理到生理。你就笑话我吧,我知道就算你捂着嘴大笑,我也得说。抬头瞅着坐在桌子对面的张警官,猜不出他会怎么处理这封信,我猜想,他不至于给我撕了。最近我一直在给他献殷勤好好表现。
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总想起你蹲在咱们学校公园小亭子里数柳树叶子来。我知道你根本不会为我数叶子吧。当然我也不稀罕,你冲我笑笑就行。我就知道你跟那个油耗子团支部书记没有好结果,那人不适合你,太油太滑。不说他,一说我就觉得磕碜。
我很想念你听我扯淡时哈哈大笑的样子。我得说,你笑起来和哭起来是最好看的。我能惹你笑,从未惹你哭过。
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不如我跟你聊聊第一次见你的事吧。其实第一次见你是在我们学校的院墙上,因为你冲我笑让我差点从院墙上掉下来。那时候你们新生入校,排着队去操场举行开学典礼,我跟几个哥们儿骑在学校的院墙上,挑漂亮姑娘。那个时候我们乐意干些让所有人不齿的事,好像唯独这样才有存在感,才有荣誉感。我看到你时,你正冲着我笑,我盯了一眼就赶紧低下头了,然后再抬头寻你时,竟然就找不到了。我是谁呀,我是陈响马,一天之内就确定你的班级。后来我故意用篮球打破你们教室的玻璃,被你们班主任逮着,我跑回宿舍把早就买好的玻璃拿来,拿着锤子叮叮当当开始安玻璃,说实话这活儿我也是第一次做,当然最后做得还蛮好。你就坐在这窗子跟前,那是一节自习,你在做财务核算题,我一敲你就停下瞪我一眼,我停下看你,你再做我又敲一下,你又瞪我一眼。哈哈哈,现在想起来还能笑得岔气。一块玻璃安了半节课。从此你就认识我了。
安,今天窗外的阳光像白炽灯管,冷冷的,很刺眼。一朵白云都没有,我怀疑白云都化身成一层白雾裹着太阳呢。这里的窗子很小,天空被铁棂子和交错的电网线分割,总觉得心脏也被十字切开了。我用手指在天空画了一朵白云,跟我们老家的棉花一样,盈盈一握暖到心里去。我想躺进去,等星星出来,月亮出来,你也出来。
三
窗外的夜色氤氲着混沌,黛西湖过来的风带着冰冷,清明节已经走了一个礼拜,在这个春天的最后一公里依然有冬天不肯离去的背影。白天我没有抬头看天,不知道有没有陈响马说的云朵。因为霓虹灯看不清星星,月亮懒得很,下半夜才肯出来。我突然很想知道陈响马发生了什么,总觉得写信的不是他,或者不全是他。
在经济学院时的陈响马,经常带着学校几个不务正业的同学,在校园内外流窜。教学楼前的公示栏常看到陈响马的违规违纪通报,可在同学们眼里反响却出奇地好,受到许多女生崇拜。陈响马学的是机电,教室在三楼,我学财务在一楼。在我们共用一间计算机教室,还有学校在礼堂举行活动的时候,他都会嬉皮笑脸地坐到我身边,不跟我说话,跟其他同学聊得火热。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跟我们班里几个同学都很要好,他毕业的时候约好了一起吃饭,因为没有约张浩我也没有去。那时候我喜欢张浩,他是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一双温暖而深沉的大眼睛。后来我们有过短暂的恋爱,毕业后他回了老家,带着艺术班的校花走了。我是从小道消息里后知后觉被分手,可我并没有很悲伤,也没有觉得有多大的耻辱,好像我数柳叶猜张浩喜不喜欢我的那些难熬的日子都是假的。我只是有些恐惧自己这份骨头缝里的冷血。而对于陈响马,直到他毕业离开学校,也只知道他在外面挺能挣钱,学费和兄弟们的吃喝都是他挣来的,学习其实并不差,毕业分数还是优秀,其他一无所知。那晚同学给我拿回来一块手表。我无法拒绝,因为直到再次遇见他已经是三年之后。
我刚从税务大厅走出来,后面有人喊我:“陈小安。”我回头,看到穿着休闲服的平头男人,右手揣在裤兜里,穿过人流踏着慢条斯理的步子,笑嘻嘻地向我走来。
“陈响马?”其实我一回头好像就认出了他,除了陈响马谁还能在阴沉的傍晚走出太阳光环下的神态。
陈响马走近我,从裤兜里伸出手,我也伸出手打算握手,他却把胳膊搭在我肩上,笑着揽着我的肩膀向前走。
我挣脱开他的胳膊,“你怎么来这里?”
没等他回答,对面走过来一个小姑娘,“我去开车。”小姑娘讪讪笑着盯着我看了好几眼。
我望向陈响马,“哟,你女朋友。”
“不是,是公司的小会计。等会儿和你说,等我。”陈响马走到小姑娘身边说了两句话,回头走向我,“走,请你吃饭。”
陈响马打了车,来到我们母校附近的老餐厅。我才知道陈响马现在跟他一个哥们儿合伙开了一家商贸公司,倒卖名牌运动服。
“原来上学时的第一桶金是倒卖服装挣的。”我竖起眉毛,筷子点在盘子沿上,发出敲击的声响。陈响马竖起眉毛撇嘴向我抛出绣球一样的笑。
“别这么盯着我,好像我脑袋长得畸形。”陈响马愉悦的笑声引来邻桌的侧目。
其实陈响马并不算畸形,脑袋不过是有点圆,后脑勺有个两厘米的疤,说是跟人家打架打的,其他也没啥大毛病。五官看上去比较让人不喜,恶狠狠的样子,不管他怎么笑,总觉得带着戾气或者那叫霸气么?我捋了捋,应该是戾气多一些。
此后七年,他好像一直在我身边又好像一直不在。后来他跟我们公司老板竟然也混成好哥们儿,仿佛是一种轮回,我们又回到上学时期的状态,我身边的人他比我都熟络。
我们会一起吃饭一起去爬书店前面的黛西山,更多的时候他还是忙着鼓捣他的生意。他也时常回家,说家里还有个老奶奶。我们的关系没有进一步也没有远一点,有时他自己在我的客厅看电影直到在沙发上睡着,而我去卧室睡觉也不用管他。有时早晨醒来,也会发现他和衣躺在我身边。他的女朋友总是换来换去,空闲时也会陪我去相亲。直到两年前我开了书屋,他突然决定把公司撤资出来,他说再去干一点别的。我不知道他脑子里整天怎么想的。那半年的时间他几乎天天在我的书屋二楼住,也是那时候唐宁一直追在他屁股后面。跟我吵架前,我们聊得正高兴,说起他跟唐宁的婚事,说他已经老大不小了,赶紧结婚,把奶奶接到身边。他脸突然就阴下来,没好气地甩了一句,“你是谁呀,管得那么宽。”忽地站起来,“是不是吃住在你这儿,你烦了。”我一听特别不得劲儿,这话说的。我也站起来踮着脚指着他,“陈响马,你滚。”陈响马拿起挂在墙上的车钥匙,下楼走了。我没有追下去。楼下一屋子读书的人。我并没有想到,陈响马这一走就没回来。站在吧台的唐宁追出去被训回来,蔫蔫地瞅了我几眼,第二天就走了。走呗,有啥了不得的。一星期后唐宁告诉我她要辞职。
陈响马出事后我得了失眠症,从市区小公寓搬来书屋住,书屋二楼的卧室真正用起来。我一边吃着中药调理一边借着看书来催眠。后来发现我对动力学类的书籍特别敏感,最多一页半就能昏昏欲睡。这个陈响马一定不会想到。我想,他回来后我就没有资本再笑话他了。失眠症治疗了半年好起来了。
在街灯灭之前,我终于睡着了。一直做着一个轻飘飘浮游在空中的梦。身体是空的,所以会轻,轻得找不到附着力,就那么飘着,信马由缰,好像谁碰一下,就贴上去,推开,就浮动很远。
四
安:
如果,我有一支笔,会每天写一封信给你。哈哈哈,你猜,我如愿了,是的,我现在在澡堂干,这活儿特别有趣,我喜欢泡在水里给别人搓澡的感觉,比电动缝纫机更适合我。而且我有一支笔,大部分用于填写卫生记录表或者其他什么表格,它属于我,我每天都装在口袋里,担心弄丢了。我还有纸张,有时候纸张会湿哒哒的,可我觉得这有水声的日子,就像我站在岸边看着你一样。
前几日,唐宁来了,我没见。我希望这个女孩以后遇见更好的人,我算个球啊。那天跟你生气,是我每个月的生理期,每个月我都有这样一个时刻,突然会忍不住,想迸发一次,想对你大吼,想骂你。因为唐宁来了,这个周期不过是变得长了一些。其实我也想过要跟唐宁结婚,我不想总这么吊着。可你一说我就遏制不住了。
我听老张说,唐宁离开的时候哭了。对了,老张是我的教官,特别严厉但跟我很合得来,我常常找他谈心。我的人生中做的好事坏事都给他交代了。因为他过于苛刻,我刚进来的时候,仇视他。有一次出工,我被铁管穿透了小腿,他扯下他的衬衣袖子给我包扎止血,又把我背上救护车。那可是大冬天,冰天雪地的大冬天。所以你应该知道,我会怎么做,老张让干啥我干啥,他就是我亲哥。
老张安排唐宁在他办公室等了半小时,来劝我。我只是不想耽误一个姑娘。最后我还是没去见。老张站在走廊里骂我,你活该倒霉。我可不就是活该嘛。安,我也真不知道怎么办,其实唐宁走后我就后悔了,我至少给她一个交代。我想过或者等出去就跟她结婚,真的,你说得对,奶奶已经等不及了,在这里我最担心她,我一定要早出去,她需要我。尽管我进来之前,她还跟我说,没啥可怕的,有奶奶在,我等你回来。我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坚强的女人。对,还有你,你一个人执拗地过了这么多年,你跟我奶奶很像。
安,你其实是座火山,正在度过冗长的休眠期。你的色彩质地,是火的颜色和黑夜下迟落的光影。你用一种慵懒遮蔽真实的你,我喜欢看你慵懒和无所谓的样子,也期待你的火山爆发,所以才赖在你的太阳屋。原来不知足,现在觉得那些时光真的很好,那是一种漫长也是一种稍纵即逝。而在这里,却只剩下漫长了。
五
我选择喧嚣都隐去的深夜才看陈响马的信,是因为在相对安静里我才有足够的时间思考,才有足够回旋的余地,用以找到赦免自己,找到陈响马诸多与我无法在一起的理由,找到唐宁跟陈响马般配的蛛丝马迹。
唐宁是个漂亮的女孩,她第一次来店里是一个人,怯生生地问了一句,“您这里免费看书吗?”那时候我刚开业不几天。我正在学着做果茶。“可以啊,免费看书免费借书。”陈响马在安装吊灯。他说原来的格调太扎眼,选了一款比较中式的。他踩在木梯上向下望了一眼,呵呵笑起来。“小姑娘,来接一把,不能白免费啊。”唐宁赶忙跑过去接着陈响马递下来的地中海式吊灯。这个灯足有六七十厘米大,像一捆乱柴火。唐宁提着有点费力,她在寻找能放的地方,没等找好位置,失手落了地,一共六个灯泡,碎了两个。吓得唐宁啊的一声跳老远。我被唐宁的声音吓得一哆嗦,赶紧跑出吧台。
唐宁十分拘谨脸颊绯红。
“吓着了?”陈响马从梯子上下来,拿着块抹布擦了擦手,伸出手去,唐宁伸开右手,食指被钩子划破了一层皮,“没事儿没事儿。”唐宁赶紧把手攥上。
我到吧台找药箱子,“陈响马,碘伏哪里去了?”
陈响马走到唐宁跟前,抓过她的手,掰开。“安,别找了,我看没啥事儿。姑娘,以后有啥事儿来找我陈响马,现在看就是划破一层皮。”唐宁怯怯地点着头。
唐宁后来说,陈响马走向她的那刻,她的心就乱了。即使那时候还以为我们是两口子。唐宁从来不掩饰她的真诚和目的。我知道女孩子对陈响马都没有抵抗力,但真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我问过唐宁,“陈响马哪里好?”唐宁想了很久才说,“想不出哪里好,可就是很喜欢,很喜欢。”
唐宁追随陈响马的时间几乎没有离开过书屋。陈响马喜欢在二楼沙发睡觉或者喝茶。唐宁就待在上面,给他沏茶或者陪他聊天。陈响马从来没有跟我说与唐宁走得有多近,我也不想问。只是有一天唐宁在一楼学习的时候,我在二楼写字,陈响马上来,坐在沙发上。陈响马拍了拍他身边的位置。
我剜了他一眼,“哟,找事儿呢。说就行我又不耳聋。”
陈响马夺过我的笔,把我拽过去,差点就坐到他怀里。
唐宁来了以后我们说话的时间的确少了很多。我知道自己一直故意或者无意识地给他们留出空间和时间。我希望陈响马好,希望有个可以照顾他的姑娘。
“你觉得唐宁怎样?”
“很好啊。”为了证实我的真诚,我扬起灼灼发光的眼睛,盯着陈响马。
“别这样看我。”陈响马站起身准备下楼。
“怎么不说了?”我追问。
“突然觉得特没劲。”陈响马继续向前走。
“我有话说……陈响马,你不能跟唐宁用我的卧室。”我不知道怎么突然会这样说。陈响马没有回头也没有回答我,走下楼梯。
陈响马走后,我坐回桌子前,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我扔了笔。倒了一杯温开水一口灌了下去。
六
安:
今天我突然好想回家乡。想来是你把多愁善感传染了我,这德性我最讨厌,可没办法,今天就是特别想你,我在镜子前照了又照,仔仔细细看自己的脸,真的,你得相信,我变得好看多了。看来你这么多年乐此不疲地叫我改变,没有白费口舌。好吧,我承认你在我身上下的魔咒终于应验了。尽管我非常讨厌这该死的状态。回忆跟虫子一样在心里咬。
恐怕你也是知道,我原来是多么憎恶那个小村庄。骨灰盒一样大的地方,全他妈是一群刁民。而且我最害怕春天回去看奶奶,因为春天一来人们就开始春灌。春灌是我至今常做的噩梦。那时候我上初三,春灌一开始,村里人跟抢爹一样,争那点水,其实他妈的,黄河水那么多,早晚浇上就行,可非得你抢他抢大家都抢。我听我爸说,都他妈因为我们那是退海之地,盐碱得很,谁先浇灌,田地里的碱就压到邻家田地里,所以一年的收成,得先看春灌。每年我爸都跟邻居陈五子约好一起浇灌,本来约好的,那熊人却提前一天就支泵浇灌了,说是记错日子了。我妈着急上火,大清早跟我爸也运了电机水泵去。陈五子正在地边上拿着锨堵水漏子,我妈在他跟前走过,没有理会他,他低着头端起一锨泥甩到我妈腿上,我妈回头上前跟他理论,两人吵骂起来。陈五子把我妈拍倒在水里,我爸急了扔下刚拖起来的水泵,跑过去夺铁锨,没想到,在抢夺中,陈五子把电缆线切断了,电流一下就烧开了地里的水,我妈那时候还没爬起来呢,我爸去拉我妈,两人倒在田地里。陈五子吓跑了。四周干活儿的乡亲给打了急救电话,可是已经晚了。
后来不依不饶的奶奶在村领导的帮助下,好歹跟陈五子要了三万块钱,我上学就是花的那钱。大专那三年假期在家,我去拾掇那户人家,爬上他们房顶揭瓦,在屋顶掏个窟窿,把他家养的鸡、狗都给药死。我看到他们就恨得牙痒痒,他们要把我送到派出所,苦于没有证据,再就是他家有个女儿,比我小一岁,长得那个丑啊,但是我威胁他,我说你再告我,我就糟蹋了你家闺女,那次是我最痛快的一次,你是没见他那尿性。后来,奶奶跟我说,你要有出息,谁都怕你。不然我等不到毕业,早就进来了。
安,可是我现在突然很想回老家,现在想想那小村景色倒是很好,土地基本改良了,村子后面、左面、右面方圆十里都是田野,村子后面有条公路顺着这条线就是连接其他村落和进城大公路,远远看跟一条绳上的蚂蚱一样。村后有条干沟,干沟上有座桥,过了桥还是田地,每一个季节都有不一样的颜色。我知道你肯定喜欢,要是你肯跟我回家,我会让你过上村里女人们都羡慕的生活。你负责在家守着小院泡茶煮风月,写你的小说,我承包百亩地种谷子种大豆种棉花。我还想着弄个池塘养鱼养虾,在池塘边上给你再盖一个小木屋,收拾收拾,小院子待够了就去池塘边听蛙声一片,不比你的书屋更有味道吗?此刻我想着觉得可幸福,你不会正在骂我吧,容我笑几声你再骂。呵呵,其实我最想说的还没说呢,我怕你真的生气,骂我是畜生。我承认这辈子就怕你一个女人,我其实至今真正只有你一个女人。你别骂我。
昨夜我梦到我们在一起,是真的在一起了,我的身体感觉得到你,我笑着看着你,你笑着看着我。我喜欢这样的你,你得承认,只有跟我在一起才是真的你,你追着打我,大声骂我的声音,隔着一条街,都能听到。我想着每天这样跟你在一起,咯咯笑起来,可是你突然从我身边消失了。找不到你,我站在一团雾里,雾太大了,白茫茫一片。脚下没有路,连一棵草也没有,就像小时候家乡的盐碱地。我不知道向哪个方向去找你,没有路能通向你,我一抬脚,就跌进万丈深渊,我醒了。
安,如果一生有两条路,我还是希望你跟我走在一条路上,让另一条路彻底荒芜。如果一生有两个选择,我还是希望一条是罪恶一条是救赎。不然我怎么是陈响马,不然我不是陈响马。
七
我做了一个梦。爆米花竟然开在田地里,像豆棵子。一棵伸出几个枝,每个枝上都盛开一簇簇爆米花,白花花的,撸一把放嘴里,脆脆香香。可能土质不好,一块田地里稀稀拉拉隔着一两米才长一棵。陈响马就坐在那豆棵子之间,看着我从田垄上向他走去,嗤嗤坏笑的模样一点也没变。怎么还是这副德性,我撇着嘴,抬手向他打招呼,一眨眼他消失在白茫茫的虚空里。陈响马,陈响马,我大喊。
醒来一翻身,陈响马给我写的信从被子上掉到地板上,我闭上眼回忆那个梦。窗外蒙蒙擦亮的时候,我看了看手机,晴,空气优,20℃/10℃。我决定去看看陈响马。
坐上去历城客车时,已经是八点半,我打算给唐宁打个电话,想了想,没有打。打开班得瑞的轻音乐,塞上耳机,闭上眼,让脑子空转。到历城需要四个小时的路程,这段时间我打算睡一半,醒一半。我会在监狱附近找个酒店住下,睡觉的时候我看看是不是还能梦到陈响马,梦到的话我就问问他为啥爆米花长在田地里,醒着的时候我要看看历城,看看这个改造陈响马的地方。
我用手机导航,监狱在郊区,最近的酒店离着五公里。我住下后,已经是下午两点。我决定先去监狱附近转一转,打听一下探视日。酒店门前是条特别繁华的小吃街,我看了一遍只买了一个烤地瓜。等陈响马出来,我们一起逛吃逛吃还是逛吃,填满他荡气回肠的胃。出租车师傅听说我去监狱,在后视镜疑惑地看了我一眼。我们沉默了一路,下车后那个地瓜才吃完。
我一下车,司机师傅用点头一笑来回复了我的一声谢谢,打了一把方向盘,转弯走掉了。
监狱的墙很高,围了一圈铁丝网,还种了一圈杨树,杨树很高很密,最高的枝头到了墙头的位置。大片茂密的绿色渲染青色天空。墙上爬满了藤蔓,这让我想起一部叫做《移动迷宫》的电影里的高墙,就像一座山的屏障。陈响马这一年多就在这里面。我想象了一下,这头野马套上缰绳正低头温顺吃草和仰望天空。
历城监狱的大门口站着两个哨兵,远远地我定了定神,慢慢向前走,哨兵稳如磐石,可我知道他们的眼珠子盯着我,跟着我移动。
“您好。”我尽量俯低身子倒像是鞠躬了。
“您好,我是……”我一时不知道怎么给自己定位,我不算陈响马家属吧,说错了话会不会把我也抓起来。
“您好,我来探视,想问一下探视时间。”
啪,哨兵给我敬了个礼,吓得我差点蹦起来。
“每月一次,每次半小时。”哨兵没有笑脸,声音和身体都跟他手里的那杆枪一样直,一样硬邦邦的。
“谢谢。”我还想问的时候,门卫房里出来一个人,穿着警服,是个老者,他问我有什么事,依然一脸严肃,我仰着头满脸堆着虔诚又说了一遍来因。老干警说,“你明天来吧,明天是探视日。”我低下头连声说谢谢,依然是鞠躬。转身往回走,我大抵知道了,陈响马在里面可能真的是被改造了。
回去后,我去了附近的超市,打算给陈响马买点吃的穿的,我后悔没问让不让带东西进去,但是不让也没事,反正买了再说。我记得陈响马喜欢吃辣条,喜欢吃薯片,他怎么爱吃的都是垃圾食品呢!不管了,多少买了一点,剩下的都是我爱吃的零食一大包,仅凭着自我感觉罐头之类的没敢买,我觉得在警察眼里,所有铁片之类沾着金属字眼的可能都算凶器。然后我去商场给他买了几件内衣内裤袜子什么的,我觉得是我错了,作为这么多年的朋友,我应该常来看看他。我打算这一年多来几趟。
清晨太阳还没起来,我就起床了,其实说实话是没睡着,一边翻看陈响马写给我的诗,一边翻来覆去想了一夜。那是最后一个信封里的纸条,我一直怀疑这并不是在监狱的时候写的,那是我书屋里曾经卖过的信笺纸,纸的背景是一束淡淡的栀子花。上面的字迹是硬笔小楷,每个字都像是雕刻的。
安
你睡意朦胧,像无名之鸟
栖在枝头。书页
翻动,那是风替我阅读你
时光深处的溪流声
安
石头已经打磨好,你醒来时
带上它温润的行李和剔透的禅心
小小的宇宙里
它是你返回尘世的星辰
安
这首诗正在走向
寂静的尾声,像是来到了
它倾诉的草尖。那悬着的
露珠里藏着
我为你盖的小寺。而你
正在醒来的路上
路过那些雪,那些夜晚里
遗忘在水里的碎银子
现在都是你的了
安
我其实不懂陈响马这首诗的意思,见到他我要问问。
匆匆在酒店吃了早点,吃完,特意给陈响马买了一份,煎蛋、油条、小笼蒸包、寿司、炸鸡腿。他胃口大,吃得多,不能不够。
到了监狱门口,司机师傅从后备箱给我拖出那两个大包扔给我,卷着一屁股尘土,一溜烟就跑没了影,比昨天的师傅还溜,好像这里是个不祥之地。两大包东西埋过我小腿。
果然有很多不让带进去的东西,万幸衣服都让拿着了。登记时,我写陈响马的名字,觉得特别陌生,可能我真的就没有好好写过这三个字。在关系一栏,我想了想还是写了妹妹。我名字还没写上,站在我身边的一个年轻干警就拿起我的表,他看着我问,“你是谁?”像在审问一个犯人,可眼睛里却并不严肃,有些东西我看不明白。难道陈响马在这里面又犯了事?
“妹妹。”我眼睛向下看着那张表回答。
“你跟我来一下。”我提着包跟着他去了一间办公室。
“陈响马的妹妹。”他回头看了我一眼,伸出手掌指向我,对坐在办公桌前的老干警介绍。
老干警迟疑了一下。
“你是陈小安?”
我挺惊讶,他们居然连我也知道。这是个国字脸大约五十多岁的男人,一双剑眉下的大眼睛发着幽深的光。脸上横竖交错的褶皱好像都是果敢的坚毅和直抵人心的箭头,让人不寒而栗。
“陈响马提前刑满释放了。”他的脸上没有一点表情,眼窝太深我看不到底。
我犹豫着向门外走,离开前转回头又看了老干警一眼。他站起身一步跨过来,伸出手把我手里的袋子像提一只小鸡一样提起来,我没有拒绝的意思,好像也没有勇气拒绝。
走出大门之前,我停住脚步,“很感谢。”他把袋子递给我,“陈响马在里面的时候常跟我说起你。”他停了停,盯着我的眼睛看了看,又回头看了看那座办公楼,再看我时,眼神已经波澜不惊。
“陈响马那小子说得一点没错,你的眼睛不能直视。”我看到了他尽量控制着的皱纹还是展开了淡淡的微笑,然后迅捷地收回去,“去看看他吧。”他游弋的眼神和转身的背影消失在那扇大门后。
站在路边的我茫然发现,居然没有陈响马任何能联系的方式了。我给唐宁打电话,打了三遍才接起来。唐宁说,“我在单镇。”我说,“我现在就去找你们。”我向公路中间走,我要打一辆车去陈响马的家,这样傍晚之前能到。唐宁说,“陈小安,你不要来!”
我坐在包裹上看着对面紧闭的监狱大门。雨水滂沱我才知道下雨了,而我觉得这是雪花,是染了月色的雪花,是落进夜晚的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