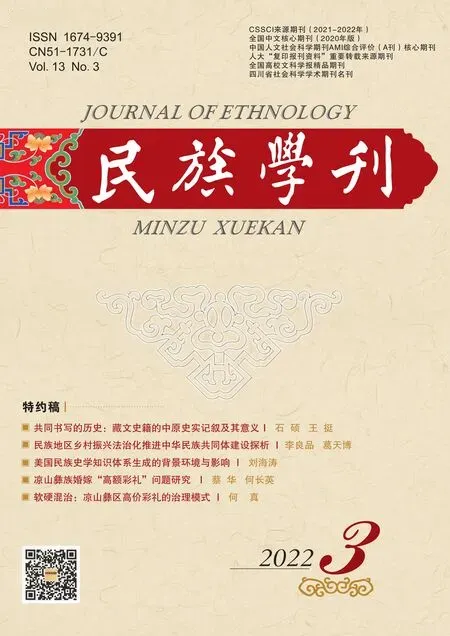北朝时期关中氐族的分布与融合
徐 晨
氐族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常与羌族并称。从先秦起,一直分布在今四川、陕西、甘肃等三省交界处。陕西关中地区作为氐族的外迁聚居地之一,北朝时期,氐族逐渐在与当地汉、羌等民族杂居、交往过程中走向了融合。以往学者对这一时段关中氐族的分布与融合研究,多将重点放在渭北地区。如马长寿先生将出土碑刻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在着重论述北朝关中渭北地区羌、胡等民族分布与融合时,对相关的氐族分布与融合情况也有过简要的提及。[1]54-78杨铭先生在此基础上,指出北朝关中渭北氐族主要分布在三原、蒲城及蓝田等地,在与汉族或羌、胡等民族的杂居、通婚中走向了融合。[2]95-96但整体上,对这一时期关中氐族的分布与融合研究较少,至于融合过程更是鲜有探讨。随着近年来北朝时期关中碑刻的相继出土,为关中氐族分布与融合的整体性研究提供了条件。据此,本文将在利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新出土的碑刻资料予以较详辨析,以期揭示出北朝时期关中氐族分布与融合的大致历程,为之后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关中氐族的分布
关中氐族历经西晋十六国以来的民族迁徙,北朝时期(公元386-581年)已遍布关中雍、岐、华三州。尤以雍州地区氐族分布广泛,且活动频繁。除传统聚居地京兆郡的长安(今陕西西安长安区)、蓝田(今陕西蓝田县)外,还扩散到了今咸阳的三原、礼泉、彬县、永寿、泾阳、淳化、兴平;铜川的耀州、宜君;渭南的富平等地;岐州氐族分布在传统的美阳(今陕西省扶风县东南)、雍(今陕西凤翔县东南)、汧(今陕西陇县东南)、隃麋(今陕西千阳县东)一带;华州氐族则分布在氐、羌聚居地李润堡(今陕西大荔县西北)附近及今华县地区。
(一)雍州地区的分布
雍州早在三国时,便有大量氐族移居,多集中在京兆郡等地。南北朝时,氐族再次迁入。早在北魏明元帝泰常二年(417)十二月,“氐豪徐騃奴、齐元子等,拥部落三万于雍,遣使内附”[3]58。太武帝始光三年(426)十二月,北魏军队在大将奚斤率领下攻入长安,“秦雍氐羌皆诣斤降”[3]72。宋文帝元嘉十一年(434),杨难当克汉中,向魏告捷,“送雍州流民七千家于长安”[4]3851,这七千流民中应有氐族身影。西魏文帝大统四年(538),因镇守长安的侯莫陈顺于渭桥平定赵青翟之乱,“南岐州氐苻安寿遂率部落一千家款附”[5]2150。这一时期,在诸多迁入地中,雍州京兆郡仍然是氐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其分布除以长安为中心外,还扩展到了蓝田地区。
蓝田县在京兆郡以南,北近冯翊,西临长安,自三国起一直隶京兆郡。前秦苻健子苻苌、将苻雄曾分别率众与桓温战于蓝田及长安东灞桥与蓝田县之间的白鹿原。后秦时,安乡侯康宦曾“驱略白鹿原氐胡数百家奔上洛”[6]767。蓝田县与白鹿原相邻,又曾是征战之地,也是进入上洛(商洛)必经之路。安乡侯康宦要驱氐胡数百家至上洛,必经蓝田。如此规模庞大的战争及氐胡的长途迁徙,会导致部分氐族因各种原因滞留蓝田,形成了北朝时期,当地氐羌大姓与汉族杂居的局面。今蓝田县出土的《罗晖造像记》(北魏)题名50人,其中羌姓17人,其他多为姚姓。氐姓苻、石、杨各1人,吕氏2人。[7]313《长方形四面柱状造像碑》(北周天和五年)也有氐族吕姓8人。[8]170-171
同时,氐族也逐渐向周边扩散,尤以今咸阳、铜川、富平等地活动较为频繁。
关于咸阳氐族,《北史·毛遐传》云:“毛遐字鸿远,北地三原人,世为酋帅。正光中,与弟鸿宾聚乡曲豪杰,遂东西略地,氐、羌多赴之,共推鸿宾为盟主。”[5]1808渭北氐族毛氏,最早可追溯到东晋穆帝永和六年(350)的氐酋毛受。毛遐家族世为酋帅,在三原地区有着深厚的根基和极高的威望,氐羌民众纷纷依附。北周时,当地还有氐族活动。今三原县博物馆藏《柱状四面体造像碑》(北周天和四年)存题记“女官啖□女造像区”。[9]啖姓为氐族原有姓氏之一,女官啖□女应为氐族。
前、后秦时期的九嵕(今咸阳礼县)和新平(今咸阳彬县)也有关于氐族的记载。东晋康帝建元十六年(380),“苻健曾分三原、九嵕、武都等地氐族十五万户于诸镇”。[4]3295后秦时,姚苌平魏褐飞之乱的次年,“苻登将强金槌以新平来降”。[6]759北朝时这两地应还有部分氐族活动。
除上述地区外,在今永寿、泾阳、淳化及渭河南岸的兴平地区也有氐族分布。永寿县出土的《晏僧定等六十七人造像碑》(北魏神龟二年),题名盖氏多达27人。[7]250-255盖姓为少数民族姓氏,或胡姓或氐姓。①氐姓有秦州氐帅盖闹,胡姓有卢水胡盖吴。历史上的卢水胡是在西戎彭卢戎遗民基础上,广泛吸收周边其他部族而形成的一个民族共同体。作为与西戎关系密切的氐族也应包含在内,卢水胡中的盖姓应与融入的氐族有关。从文中盖姓人数来看,北朝时今永寿县的氐族有着一定的数量,以家族为单位聚族而居,他们的先辈很早便迁入永寿地区,与当地汉族杂居、融合。
泾阳县出土的《雍光里邑子造像碑》(北魏正光元年),题记有杨、梁、强、窦、但等氐族常见姓氏,“但”应是“啖”的同音异写。[7]256-269泾阳地区南与礼泉氐族相近,北临三原氐族,又处在泾河下游,与氐族原居住地环境相似,是其理想的聚居地。
淳化县处在永寿、三原氐族居住地之间,北临氐羌聚居的北地郡。前、后秦时该地便有氐羌活动,明《隆庆淳化志》载:“秦王殿在县北五十里白堡地方箭幹山”。[10]405即今淳化县安子哇乡东湾村北箭幹山,又名秦王殿山。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384),苻坚将姚苌在此起兵,立国号秦,秦王殿应建此时。翻越箭幹山,东面是氐、羌杂居的北地郡治所今耀县境内。因此,淳化县成为氐族在咸阳地区的又一个聚居地。本地出土的《北周保定五年造像碑》(北周保定五年),题名邑子200人,其中可辨识158人,氐族阎氏25人,啖氏21人,杨氏29人,仇氏3人,姜氏1人,占总题名人数的三分之一。[7]470-473占总题名人数的三分之一,应是以家族为单位,经数代繁衍才有如此规模。
咸阳南部的兴平地区,三国时便有氐族移居此地。史载曹魏曾“前后徙民、氐,使居京兆、扶风、天水界者万余户,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负而随之。”[11]704清《兴平县志》也载:“境内有小槐里城,引《一统志》云在兴平县西接武功县界”[12]51。该地又西临氐族聚居的扶风地区,进而发展成为了外迁氐族的又一聚居地。北朝时仍有氐族活动,兴平市出土的《王妙晖造像记》(北周武成二年),题记有氐姓邑人苟、窦、吕、杨、成、阎等。[7]401-405
今铜川、富平地区在南北朝较长时间内属雍州北地郡管辖,是氐、羌、匈奴、汉、鲜卑等民族杂居的中心地带。其中,铜川是以宜君卢水胡及耀县氐羌为主的多民族杂居地。耀县出土的《四面像主造像碑》(北周保定五年至天和五年)题名46人,可辨认34人。其中氐姓杨氏11人,强氏3人,梁氏1人,共14人,占总数四分之一左右,余下或羌或汉。[7]484-488此外,耀县出土的氐族碑刻还有北魏《吕思颜造像碑》《氿臣生造像碑》;西魏《毛遐造像记》《和伏庆造像座》《辛延智等七十人造像记》;北周《绛阿鲁造像碑》《同蹄延檦等造像碑》《邑主同蹄龙欢合邑子一百人造像》《荔非郎虎造像碑座》《毛明胜造像碑》等。[7]149-482氐族主要姓氏皆有出现,持续时间从北魏延续至北周,贯穿整个北朝时期。在耀县地区众多不同氐姓部族的聚集,显示了其较强的开放性。
以卢水胡为主的宜君地区也有氐族移居。在宜君福地石窟,一个造于北魏初年的主龛两侧小道龛的供养人道士吕清黑及另一个建于西魏文帝大统元年(535)的左龛供养人道士吕贵里,二者皆为氐人。[13]氐族还扩散到了宜君周边地区,黄陵县出土的《符茂造像碑》(北朝)有氐族符氏家族、氐姓杨氏[14];洛川县出土的《法龙等合邑六十人造像碑》(西魏大统十二年)也出现了氐族梁、杨大姓。[7]357-360
富平自秦朝设置起便隶属北地郡,东汉为郡治,境内羌族活动频繁。该地东晋时为前秦统治,为更好的管理当地氐羌等少数民族,苻坚曾在境内频阳县设立土门护军。北魏撤护军划归同官县(今铜川),西魏时归入宜州(今耀县)。自东汉至北朝以来,逐渐发展成为了多民族汇聚之地。富平县出土的《法超造像记》(西魏大统四年)题记37人,其中氐姓齐氏14人,仇氏14人,吕、苻各1人。[7]340该造像应是以齐、仇两姓氐族为主的家族造像。富平地区出土的氐族碑刻还有北魏《杨阿绍造像碑》、《杨缦黑造像碑》、《邑子六十七人造像碑》等。[7]183-241其中以杨、吕、齐、仇等氐姓为主,多以家族的形式出现。
(二)岐州地区的分布
岐州氐族的迁入,始自三国时期,曹魏政权为防氐族归附蜀汉,遂将川陕甘相邻地区的氐族向关中迁徙。东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曹操灭兴国氐及氐王杨万千后,将一部分二氐王余众迁入扶风之美阳(今陕西武功西北)。之后,曹操恐武都被蜀汉占领,又迁氐族五万余户至扶风、天水界。时刘备据汉中,迫近下辨,曹操又徙武都汉、氐万余户于京兆、扶风、天水等地。扶风郡成为汉魏氐族分布的中心地之一,且数量众多,郡内氐族多集中在雍、美阳、汧、隃麋等地。前秦时期,苻坚曾迁汧、雍等地氐族15万户分散诸镇。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394),后秦安南强熙、镇远杨多叛姚兴,推窦冲为盟主,所在扰乱。后窦冲走汧川被汧川氐仇高执送,汧川即今陕西陇县至千阳一带。上述地区北朝时皆属岐州,且氐族活动频繁。《魏书·陆真传》载;“北魏和平三年(462),雍州陇东汧城附近因北魏长蛇镇的建立,引起扶风氐豪仇傉檀、强免生等聚众反对,氐族人民纷纷响应,其众甚盛。”[3]730《魏书·高祖纪》亦载:“北魏太和四年(480),雍州氐齐男王反,杀美阳令,州郡捕斩之”[3]148。北朝岐州氐族多分布在美阳、雍、汧、隃麋一带。
(三)华州地区的分布
华州始置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治所起初在李润堡(今陕西大荔县西北),后移治华阴县。辖境大致在今陕西省黄河以西,黄龙县以南,蒲城、华县及以东,华山以北地区。李润堡是魏晋时期关中冯翊羌族的主要聚居地。前秦时,发展成为了氐羌等多民族杂居之地。蒲城县出土的《邓太尉祠碑》(前秦建元三年)中军府僚佐29人,皆属少数民族。其中羌族22人,占75.9%,氐族、卢水胡、屠各各2人,分别占6.9%。[1]12-13此外,附近白水县出土的《广武将军□产碑》(前秦建元四年)有羌族39人,占31.7%;氐族23人,占总人数18.7%。[1]28氐族人数仅次于羌族,相互间交错分布。自前秦以来李润堡的得失常关乎长安的安危,后秦担心李润堡羌族势力过大,曾两次对其进行分化迁徙,却始终未能削弱李润附近羌族的势力。
北魏建国初期,冯翊和杏城地区的羌豪纷纷归降。太武帝始光三年(428),魏将奚斤占领长安,秦雍氐羌皆叛,这次叛乱中应有李润羌的参与。太平真君六年(445),杏城爆发了卢水胡盖吴领导的反魏运动。杏城即今洛川县西南黄陵县附近,黄陵县在南北朝有部分氐族活动,这支以卢水胡盖吴领导的反魏队伍中应有氐族参加。十一月,盖吴遣部落帅白广平掠新平,在安定诸夷聚众响应下,杀汧城守将,进军李润堡,又分兵掠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南)。后叛乱平定,李润附近叛羌被镇压。之后有部分氐羌仍居住在李润堡地区。此外,西魏文帝大统九年(543),东秦州氐酋梁道显聚众反魏,进攻南由镇。在赵昶抚谕下,“梁道显主动归降,徙豪帅40余人并部落于华州”。[5]2402北周明帝武成二年(560),李润堡附近还有氐族活动。蒲城县出土的《合方邑子百数十人造像记》(北周武成二年),题名有氐、羌姓氏吕、梁、彭、程等。[7]406-414至武帝天和元年(566),李润堡附近的氐族明显减少,蒲城县北出土的《昨和拔祖等一百廿八人造像记》(北周天和元年),题记86人,氐姓吕氏2人,余下多为西羌大姓。[7]476-480此时李润堡地区的氐族大多与当地汉、羌民族相融,仅有小部分合而未融。
二、碑铭所见关中氐族的融合
关中地区在北朝前已是氐、羌及其他民族聚集、杂居之地,北朝时因北方相对统一,周边各民族纷纷大批移居。加之北魏统一北方后对关中氐、羌等民族所采取护军、军镇及郡县、编户化的管理策略,民族间交往日益频繁。在共同地域范围及统一的政治实体下,各民族互融性加强,氐族的民族融合也逐渐深化。关于民族融合,主要有杂居融合、通婚融合及自由迁徙融合等多种形式。
(一)民族杂居融合
北朝氐族对关中地区的再次迁入,形成了各民族的交错杂居。这些杂居在不同大小地方社会里的民族,相互间的关系十分密切。通过日常频繁的交往,能充分了解对方民族的生活方式,这促进了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互相学习,也实现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转化与交流,最终发展成为了民族间的大吸收、大融合。与汉族的融合是主流,但也存在其他各民族间的互融。
富平出土的《邑子六十七人造像碑》(北魏熙平二年)佛、道造像各占一半,题名67人,其中除氐族吕氏33人外,还有李、王、刘、张、颜、段、胡、子、垣、其等姓氏,王氏5人或羌或汉,余下应为汉族。[7]237-243题名人数按姓氏来划分,氐、汉各半,相互杂居。当地氐族与汉族共同崇尚佛教或道教,题名中有些氐姓竟未与同族人并刻,而以氐、汉姓氏交错排列的方式出现。二者民族间的区别,开始从民族符号向地域文化转变,在共同的宗教信仰下,民族界限变得模糊。甚至有些氐族还担任教内要职,统领一些汉族信仰者。发愿文中也出现了“眇执玄其,同心上世”等语句,证明这里的氐、汉民族在宗教信仰的推动下,结成了一个拥有共同心理素质的较强凝聚力团体,民族融合不断深化。
耀县出土的《仇臣生造像碑》(北魏正光五年)②载:“上为皇帝陛下,州郡令长,七世父母,愿上生天上,值遇诸佛,下坠人间侯王长者之家,现世之安,延年益寿,子孙兴隆”。[15]耀县《辛延智等七十人造像记》(西魏大统十四年)亦载:“上为皇帝陛下、大丞相,群僚百师僧父,父母,囙缘眷属”。[16]402此时生活在耀县地区的氐族等民族以佛教为纽带,民族情感不断增进,普遍接受了汉文化的儒家伦理,孝道文化深入内心,成为了不同民族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氐族开始将自己视为北朝政权统治下的子民,从内心深处认同了北朝国家的合法性,民族融合走向了成熟。从上述氐、汉融合的史实来看,进一步表明长期在共同宗教信仰下的多民族个体,彼此间了解较多,人们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洞悉每个人的性格、能力和道德。民族间的差异在实际的具体宗教事务性工作中逐渐淡漠,被宗教文化信仰的不同所取代。这种转变打破了过往单一的仅以“家”“族”为单位的思考模式,不同宗教文化的信仰成为了促进域内民族发展与融合的主要因素之一。
氐族杂居融合的对象除汉民族外,还有其他民族。蒲城县出土的《合方邑子百数十人造像记》(北周武成二年)反映出一个村邑内氐族与其他民族杂居融合的史实。碑文题名150余人,包括匈奴鲜卑化的贺兰氏及鲜卑部吐谷浑、乙弗、库、揳拔、拓跋、若干、普屯、宇文、如罗、和稽、俟奴、费连等氏,东夷部岛六浑氏,高车部斛斯、屋引、贺拔、乞伏、乙旃氏等,氐羌彭、梁、吕、程等氏,西域胡人支白氏等。[1]56居住民族庞杂,且几乎涵盖了北方所有的主要民族,汉族却出现较少。说明这是一个游离于汉族之外的,有着共同宗教信仰的多民族聚居地,即属于关中各民族大杂居中的小聚居。各方邑子,根据不同的部族分刻在造像的四面,如斛斯氏多在西、南面;携拔氏、匈奴、高车诸姓多在北面;宇文氏多在西面;氐羌多在西、北面。方位的不同,或许预示着各自民族的来源方向。在这样一个不大的村邑内竟有这么多不同民族的杂居,各民族间的关系自然十分紧密。由于人际关系中有着互相牵制的力量,形成互动模式的循环,使三个以上民族不易产生整体隔离或对立的状态,往往利于互相交往。民族融合在日常交往与共同宗教信仰的推动下,走向了成熟阶段。
咸阳出土的《王妙晖造像记》(北周武成二年),题名是羌族弥姐娄,邑主为匈奴大姓,即呼延蛮獠。其中氐羌姓氏有苟、窦、吕、成、段等,还有一些汉姓。[7]401-405从数量上看,羌族的题名明显少于氐、鲜卑、匈奴等民族。这一地区有些村邑羌族合族而居,并以羌族为主的格局正逐渐被以汉、氐、羌及北方各族杂居所取代。题记在描述他们共同弘扬佛法时说:“邑子五十人等,并宿树蓝柯,同兹明世,爰讬乡亲,义存香火……佥渴家资,共成良福……遂于长安城北、渭水之阳,造释迦石像一躯,永光圣宅,见在眷属,恒与善居。”[17]34以乡亲互称,为维护彼此的亲善,共同出资建造佛像。这表明当地氐羌等各族人民在不断的交错杂居及相互交往过程中,以共同宗教信仰为纽带,打破了以单一民族为主出资、劝化等传统造像建设形式,彼此间的隔阂日渐消弭,开启了一起出资、策划及参与的新型造像活动模式。这种转变意义重大,标志着当地人们民族观念的一种革新,逐步摆脱了从古代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仅以“家”“族”为单位的思考模式,开始以社会崇尚的主流文化观念来作为民族发展的导向,以此来实现不同民族间的真正融合。
(二)民族通婚融合
通婚作为一种常见的交往方式,在民族相互交往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突破民族界限,实现与他族接触、融合的重要途径。
藏于今耀县的《杨阿绍造像碑》(北魏景明元年),题记中北地郡富平县氐族杨阿绍的妻子为“姜小姬,息文要妻为王阿双,息文识妻为张买女,息文安妻为王乐”[16]369。无独有偶,同时间、同出土地的《杨缦黑造像碑》(北魏景明元年),③题记中北地郡富平县氐族杨缦黑的妻子为“王白□、泉公,杨小黑的妻子为王鲁女、李□”[16]369。从姓氏上看,上述姜、王、李三姓或氐羌或汉,张、泉二姓应是汉族。碑刻撰写时间都在孝文帝汉化改革后,属单一氐姓的家族碑刻。由此推测,此时富平地区的氐族已经开始由传统的内婚制向外婚制转变,与羌、汉进行了通婚,且与汉族婚配成为了主流。
耀县出土的《郭羌四面造像铭》(北周),从造像内容看,郭羌上一代的两个母亲,一李氏当为汉姓,一蒲氏为氐姓。三弟妇分别为白、杨、鱼,杨氏当为氐族。[1]77-78马长寿先生认为这与郭羌的豪强身份有关,唐代以前,无论鲜卑或西羌普遍都保有族内婚制,不与外族通婚,只有上层人物如贵族、达官不在此限。[1]77即便如此,该造像内容也能反映出北周当地氐族与羌、汉上层的通婚情况,不管出于何种目的,民族融合随着民族间相互的通婚而走向了成熟。
(三)民族自由迁徙融合
关中氐族与其他民族在长期的交错杂居过程中,出于各种原因的自由迁徙者也有存在。相比规模较大的群体性整体移居,此类迁徙人数较少,更容易被融合。魏晋南北朝时,因战乱、灾荒或受政府政策的影响,关中诸民族的自由流动性往往很强。耀县出土的《同蹄延檦等造像碑》(北周保定二年)题记云:“知命弗常,漂流四使”[1]93。“使”作“徙”讲;“四”表示迁徙的次数,意在描述邑落氐羌诸民族迁徙流亡之苦。
北朝时的关中氐族因各种原因,开始由雍州中、西部地区向北部羌胡聚居地铜官及东部华州等地迁徙。除大规模人为或政府行为移居外,还存在一些自由迁入者,从事共同的宗教活动是其迁徙的主要原因之一。耀县出土的《仇臣生造像碑》(北魏正光五年),碑主仇臣生“原为雍州北地郡三原县人,值遇上世,信心三宝,为了家人的长寿与子孙兴隆,特造此石像一躯。末尾还题有其亲祖、亡父及亡叔的姓名”。[15]从题记“原”字推测,仇生臣离开了家乡三原县,迁至石像出土地北地郡,并为家人造像祈愿。蒲城县出土的《合方邑子百数十人造像记》(北周武成二年),不同的部族被分刻造像四面,氐羌民族刻在北、西两面。[1]406-407预示这一地区氐羌民族的来处。蒲城县北面是羌、胡聚居的铜官、洛川等地,距雍州三原、淳化的氐族也较近。西面是关中氐族分布中心长安、兴平、扶风等地,沿关中道可直抵此处。蒲城县的氐族可能是从铜官、洛川及雍州附近迁徙而来,时间最迟在北周明帝武成二年(560)前。从题记中的姓氏来看,氐族数量很少,应是个体行为,非大规模的迁入。
除受宗教信仰影响外,也有因做官而迁入的情况。耀县出土的《毛遐造像记》(西魏大统元年)④像主毛遐官职为大行台、尚书、北雍州刺史、宜君县开国公。[15]《北史·毛遐传》载:“遐为北地三原人,世为酋帅,因平定萧宝夤谋逆有功,诏以遐兼尚书,二州行台。孝武帝入关,敕周文帝置二尚书,分掌机事,遐与周惠达始为之。稍迁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卒”。[5]1808碑刻撰写的时间在西魏文帝大统元年(535),从官职称谓来看,毛遐任职时应在孝武入关后至西魏初期,正值北魏衰亡、西魏崛起的动荡年代。统治者为震慑北地诸羌胡,遂加封毛遐为大行台、尚书、北雍州刺史、宜君县开国公,赴任宜君地区。毛遐利用宗教信仰相劝氐、羌、胡、汉等民众“减割家珍,造以佛像。立在通衙,祈求天下太平,皇治永康”[15],缓和了当地的民族关系。
三、结语
根据相关历史文献及关中地区出土的碑刻,经西晋十六国以来的民族大迁徙,北朝时期,关中氐族已遍布雍、岐、华三州,与各民族交错杂居,且出现了以家族为单位聚族而居的现象。共同的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素质等因素促使氐族与其他民族在彼此互动的过程中,开始与异族通婚,从种族、语言、习俗、经济、文化等方面强化了沟通,使通婚的民族在各个方面都趋于统一,最终走上了民族融合的道路。此外,还有一些自由迁入民族杂居地的氐族,因数量较少,难以形成本民族的聚集地,不能够产生集群效应,只能依附当地势力较强的民族团体,进而融入到多民族聚居的民族共同体内。这一时期关中氐族分布与融合的历程,体现出了中华民族关系的主流是相互学习、相互吸收、相互依靠、相互繁荣。尽管氐族进入关中的原因、时间、方式各有差异,但其结果都是融入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共同体内,且融合的广度与深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扩大与深化,进一步说明中华民族的历史是有多民族共同造就的,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是多民族交融的结晶。
注释:
①曾晓梅,吴明冉《羌族石刻文献集成》(巴蜀书社,2017年第255页)将盖氏归为卢水胡,宋莉《北魏至隋代关中地区造像碑的样式与年代考证》(西安美术学院,2011年第157页)倾向为高丽人。
②碑石出土地点,暨远志《北朝杏城—鄜州地区部族石窟的分期与思考》《艺术史研究》(8)(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15页)、罗宏才《中国佛道造像碑研究:以关中地区为考察对象》(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63页)皆称原刻在“三原县”、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线装书局,2008年第275页)称刻于“河南省辉县。”曾晓梅等《羌族石刻文献集成》(巴蜀书社,2017年第281页)经过考证认为该碑刻1933年7月出土于陕西耀县城南。
③碑石出土时间,李淞《长安艺术与宗教文明》(中华书局出版社,2002年第369页)、曾晓梅等《羌族石刻文献集成》(巴蜀书社,2017年第186页)皆作1937年;李改、张光浦《药王山北朝碑石研究》(陕西旅游出版社,1999年第21页)作1938年。出土地点,暨远志《北朝杏城——鄜州地区部族石窟的分期与思考》《艺术史研究》(8)(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01页)认为出土于陕西富平、曾晓梅,吴明冉《羌族石刻文献集成》(巴蜀书社,2017年第186页)指出出土地不详。
④碑石出土时间、地点,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线装书局,2008年第162页)作1940年出土于陕西耀县沮河旁;罗宏才《中国佛道造像碑研究:以关中地区为考察对象》(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6页)、宋莉《北魏至隋代关中地区造像碑的样式与年代考证》(西安美术学院,2011年第95页)皆作1930年出土于陕西耀县漆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