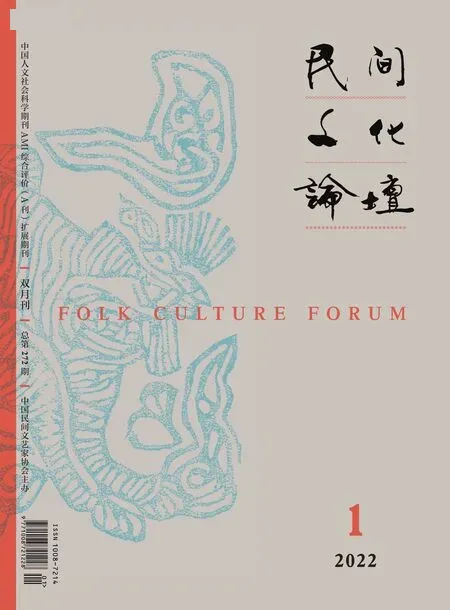奇幻的变创
—— 歌德叙事谣曲中的侨易现象
王 微
一、谣曲与歌德
德语中叙事谣曲(Ballade)的概念源自法国南部奥克斯塔尼语(Okzitanisch)中的“balade”,即一种跳舞的歌。①Winfreid Freund, Deutsche Phantastik, München: Wilhelm Fink Verlag,1999, p.16.该词从词源学考察又可追溯至晚期拉丁语的“跳舞”(ballare)一词。它的初始形式是由游吟诗人创作、为宫廷队列舞蹈伴唱的一种舞蹈歌曲。后来又在诗歌形式中加进了叙事性和戏剧性的内容,从而发展成为民间叙事谣曲。②Rein Zondergeld, Lexikon der phantastischen Literatur. Stuttgart, Weitbrecht, 1998, p.12.到了18世纪后半叶,叙事谣曲已经摆脱了原有的跳舞歌曲的概念,被用来指称情节丰富、具有隐喻意义、大多为悲剧性的叙事诗歌体,即一种用歌谣的形式叙述民间故事的诗歌体裁。德语文学中的叙事谣曲题材涉猎范围极为广泛,远可至古希腊神话、中世纪童话,近可及当代的最新素材。其中蕴含的辩证美学彰显了“已然”与“未然”之间的巨大张力,能尽可能地展现隐藏在井然有序的表象之下的混乱、无序和威胁。“它在内容上以反映人民的喜怒哀乐为主,语言通俗易懂贴近百姓,内容丰富。英雄、鬼神、强盗、古代传说、现代爱情都能成为谣曲述说的对象。”③陈壮鹰:《解读歌德谣曲风格》,《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可以说叙事谣曲是一种具有明显民间文化面相的文学形式。
在18世纪70年代,叙事谣曲已成为德语文学中一种极为重要的文学体裁。这种由民间诗歌发展而来的文学形式,让人们找到了表达在一个文明开化的社会中所潜藏的不适与苦闷的媒介。当时,以歌德和席勒为代表的德国狂飙突进诗人创作了不少传唱至今的经典谣曲,使其成为了当时文学创作的主流。①Karl Otto Conrady, Goethe: Leben und Werk, Königstein: Athenäum, 1985, p.176.尤其是在1797年,德语叙事谣曲大获丰收。这一年因此被称作“叙事谣曲年”(das Balladenjahr)而载入德国文学的史册。
作为德国文学领军人物的歌德曾“把谣曲喻为诗歌的鼻祖,在它的基础上诗歌才发展繁荣,形成无数的流派门类”。他认为,谣曲将文学中那些最基本的要素,如叙事性、抒情性和戏剧性等融为一体,如同包含着生命全部信息的尚未孵化的蛋,是诗歌中的“原始植物”(Urpflanze),是植物变形时最初的“嫩叶”。②陈壮鹰:《解读歌德谣曲风格》,《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歌德本人就写下了许多著名的叙事谣曲。这些作品充斥着魔鬼、女妖、摩诃天、魔法师等自然魔幻题材。其中包含的文化意象和元素涵盖了东西方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不同国家的民间传说。同时,在融合多元文化的基础上,作者又根据自己的创作理念进行了改写与再创造,给作品赋予了引人入胜的奇幻色彩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这种异质文化间的传播、接受、吸收、改写和创新本身就是一种内涵丰富的侨易过程。本文将从侨易学的视角出发,以《柯林斯的未婚妻》《魔王》和《神与舞女》为例,深度解析歌德叙事谣曲中的侨易现象,揭示其背后的流力因素和文化融创形成的质变,并探究这一过程体现出的世界文学观。
二、变创之象:多元的神魔
“侨易”二字之立意源自《易经》。有论者认为《易经》表达了三个方面的哲学思想,即:观物取象、万物交感、发展变化。简单来说,就是阴阳两种势力交互作用产生合力的过程。所谓“侨”,意指侨动,即两点之间特定距离中发生的位置变动,而“易”的核心则是“交易”,或曰“二元相交”的互动过程,即因较大异质性的环境变化而导致的事物的质性变化。③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页。
所以“侨易学”的基本理念就是因“侨”而致“易”,其中包括物质位移、精神漫游所造成的个体思想观念的形成与创生。而侨易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侨易现象”,即由“侨”致“易”、由“因”结“果”的过程。其核心点有二,一是“迁移”,二是“变化”。这种距离的变化一般是指具体有异质性的文化体之间的变迁。从内在的本质而言,作为主体的人的精神世界发生的较大变化,也可以说是一种“质性变化”。④同上,第19—21页。
侨易学以“二元三维,大道侨易”的思想为基本架构,主张“观侨取象,察变寻异”。而“取象说易”则是侨易学中最关键的一个方法,即选取“侨易现象”,将之上升到一个质性的概念层面,讨论这种经由侨易过程而发生的质性变化。⑤同上,第21页。
如前所述,歌德笔下的叙事谣曲融合了多种文化元素。而当异质文化体发生碰撞时,总会产生相互作用力。本文首先寻找的,便是作为侨易主体的叙事谣曲经过歌德创造性的诗情与笔触,呈现出怎样的新面相,其中包含了哪些不同文化间的交感点,并深入探讨相关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促发因素。为此,有必要先进行“观侨取象”。
纵观歌德之前的德语叙事谣曲,多以黑暗、魔鬼、噩梦为母题,表达人们对不幸生活的悲郁之情和对灾难的恐惧之感。赫尔蒂1771年所作的《阿德斯坦与小玫瑰》(Adelstan und Röschen)可算作德语文学史上的第一首带有奇幻色彩的叙事谣曲。它讲述了对宫廷生活感到百无聊赖的贵族青年与纯洁质朴的农家女孩在充满田园风光的意境中相遇,由此发展出无法预料的悲剧:一边是一心想在尔虞我诈的宫廷生活外寻求恋爱刺激的贵族青年,他突然发现自己被一种无法抵抗的欲望征服;另一边是心怀懵懂爱意的女孩被强占为前者的恋人。她在绝望和痛苦中死去,又作为遭受欺骗且无法得到慰藉的幽魂重新回到那轻浮的负心人床边。最终,那位贵族青年终因不堪忍受女孩冤魂的无声控诉而自杀身亡。两年后的1773年, 赫尔蒂又创作了一首同样关于背叛与复仇的谣曲《修女》(Die Nonne)。女主人公比前作中被抛弃的女孩更为主动地对欺骗他的负心人实施了血腥报复。她不但将其杀死,还把他那颗不忠诚的心从坟墓中的尸体里掏出来踩烂。
同年,作为狂飙突进运动重要代表的德国诗人毕尔格写下了他最著名的叙事谣曲《莱诺勒》(Lenore)。故事以普鲁士与奥地利争夺西里西亚的七年战争为背景:战争结束后,莱诺勒四处打听未婚夫威廉下落,结果杳无音信,这使她悲痛欲绝。后来威廉的鬼魂在黑夜中骑马而来,带着莱诺勒驾飞马奔向作为婚床的坟墓。飞马一路奔驰,开始时越过牧场、荒原、田野,之后是群山、城镇,最后是天空、星辰,那已是鬼神的世界。结尾处威廉突然变为骷髅,黑马喷火,骷髅和马都坠入坟墓。
整体而言,早期的德国叙事谣曲可以说是人们表达反对贵族阶层剥削却又无力反抗的情感的媒介。在这些作品中人们可以感受到入侵理性主导地盘的如火山喷发般的澎湃情感。故事里一幕幕诡异、惊悚的场景与画面无一不在诉说那被启蒙理性的规约排挤和压抑的情感冲动以自我毁灭的方式冲击着人们习以为常的现实秩序,动摇着原本熟悉可靠的生存基础。
而歌德笔下的叙事谣曲,除了保留魔幻和超自然的传统外,最显著的一个突破便是借用不同国家的民族文化构建起一个神奇的隐喻世界。具体来说,歌德的叙事谣曲中主要包括了以下几种变创之象:
首先是古希腊罗马文化的遗风之象,此处可以《柯林斯的未婚妻》(Die Braut von Korinth)为例。这首谣曲叙述了来自雅典的青年和来自柯林斯的女孩间离奇而惊悚的爱情故事。两家的父辈曾相互交好,并许下承诺在子女间缔结姻缘。后来女孩一家改信了基督教。长大后的雅典青年来到柯林斯赴婚约,却不能如约与自己的未婚妻修好。因为女孩虔诚的母亲一直强迫女儿严守教规并终身禁欲。于是,当雅典青年来到柯林斯时,女孩早已在极度的忧郁和怨恨中去世。死后的女孩会在晚上化作吸血鬼回到人间。就在雅典青年意外到来的这天夜里,她决心要找回自己失去的幸福,爱上生前无法与之相爱的雅典青年,并要吸食他心里的鲜血。尽管最终的结局没有明述,但人们不难推测出,雅典青年终将难逃一死,却在死后和自己的柯林斯新娘实现永恒的结合。
《柯林斯的未婚妻》取材自古希腊作家弗勒工(Phlegon von Tralleis)的《述异记》 (Das Buch der Wunder)。在弗勒工的笔下,那化作鬼魂的女孩名叫菲林宁,她的未婚夫叫马凯蒂。女佣撞见了本已死去的菲林宁和作为陌生客人到来的马凯蒂共处一室,于是便告诉了女孩的母亲。在母亲的恳求下,马凯蒂拿出了前一夜女孩留给他的作为婚约的信物——一个金戒指和一条围巾。认出女儿之物的父母放声大哭。马凯蒂答应他们如果菲林宁再回来的话,一定会告诉他们的。第二天夜里菲林宁如期而至,他们在一起亲热着,同时还一起吃喝。为了弄清事实,马凯蒂悄悄叫来仆人,将菲林宁出示的衣服和黄金饰品送到父母那里。匆匆赶来的父母看到变成鬼魅的女儿吓得大惊失色。而此时的菲林宁也对父母道出了自己心中的怨恨:“父、母啊,你们不公义、不敬虔,不肯容我在这寄居的人那里安然待三天。现在,你们要因自己的好奇心,再悲哀一次。”说完便倒地而亡。①Phlegon von Tralleis, Das Buch der Wunder und Zeugnisse seiner Wirkungsgeschichte,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2002, p.81-200.
歌德将事件发生的背景从雅典移至因圣保罗的传道而很早就成为基督教扎根之地的柯林斯。他保留了两个家庭的婚约关系和女主角在家中冤死并化为鬼魂,以及未婚夫妻夜晚在闺房中偶遇的桥段,同时也借用了未婚新娘和新郎出示信物、共享饮食等细节。值得注意的是,歌德在自己的创作中强调了古希腊信仰中的多元开放与基督教的专制教条间的冲突,因此也通过诸多象征性的符号和意象的对比凸显两种意识形态间的鲜明对立,其中不乏大量的古希腊与罗马神话中的元素和母题,比如雅典青年初见化为鬼魂回到房间的女孩便急忙从床上起身说道:“这里有谷神和酒神的礼物;可爱的姑娘,你又带来爱神。”②本文所引用歌德作品中文翻译均出自《歌德文集》第9卷,钱春绮译,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同等情况本文统一用中注(歌德 页码)表示。此处德语原文为Hier ist Ceres', hier ist Bacchus' Gabe,Und du bringst den Amor, liebes Kind!(歌德 53) 原文中“Ceres”便是罗马神话中的谷神刻瑞斯,喻指面包,而“Bacchus”则是酒神巴库斯,喻指酒。“Amor” 是爱神的名字。拉丁文有句名谚:没有刻瑞斯和巴库斯,维纳斯也要受冻。歌德在此处化用此名句,既贴合了此时女孩带来面包和酒水,与雅典青年共处闺房的场景,又巧妙地借青年之口表达了希腊人愿尽享眼前美食与爱欲之欢的思想。这种思想不同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
面对雅典青年的示爱与追求,女孩却道出了心中的苦楚:“形形色色的古神立即离去,剩下空空的房屋,沉寂无声。我们崇拜十字架上的救主,不可见的、唯一的在天之神;祭献的牲口,不是羊羔、公牛,而是活人,真是闻所未闻。”(歌德 54) 此处“形形色色的古神”代表古希腊的群神,“十字架上的救主”“唯一的在天之神”则明显指涉基督教。不仅交代了女孩家人宗教信仰的转变,更是一针见血揭露了宗教禁欲观枉顾人性的残酷与荒谬。
当雅典青年认出眼前的女孩就是自己的未婚妻时,便当即表示要和她完成婚约:“不!就凭着这支烛火起誓,这是许门预先显现的恩典;欢乐和我并没有将你抛弃,请跟我同往我父亲的家园。”(歌德 55)许门(Hymen)是希腊神话中的婚姻之神,为一有翼男孩,手持火炬和面纱。这也说明,在雅典青年的观念中,人生的婚姻是和神的恩典结合在一起的,或者说神也要这对有情之人终成眷属。
在故事的结局上,歌德也展开了大胆想象,让女孩在一番痛斥之后提出了要和自己的未婚夫一起接受火刑的要求,同时也明示自己的目的并预见了最终的结果:“一待冒出火星,一待烧成灰烬,我们就急忙去见古代的神灵。”(歌德 60)生物性上的死亡将这对恋人送上了形而上的顶峰。古老的希腊众神是作者歌德心中完美人性的象征。只有在奥林匹斯神山上,爱欲和信仰方能得到和解。③Daniel Wilson, Das Goethe-Tabu. Protest und Menschenrechte im klassischen Weimar,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Verlag,1999, p.47.因此,当柯林斯的未婚妻和雅典青年在人世消亡的瞬间,他们将获得人性的圆满与生命的整全。在肉体灰飞烟灭的刹那,短暂的毁灭与永恒的存在也会实现融通合一。④Roberto Zapperi, Das Inkognito. Goethes ganz andere Existenz in Rom, München: Beck, 1999, p.8.两相比较,这样的改写比原版结尾中女孩的倒地身亡更能突显主角性格的刚烈与执着。如此创新不仅为故事增添了奇幻的色彩,渲染了悲壮的氛围,更是画龙点睛般地深化了整个作品的主旨思想。
由此可见,原本的希腊鬼怪传说通过歌德的创造性改写,使人们在古希腊文明的自由精神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的对比中,体会出打破教条桎梏,追求自由解放的精神宣言。这便是异域文化经由侨动过程而产生的质变效果。
其次,歌德的谣曲中也不乏北欧民间传说之象。其中的典型便是那首广为流传的《魔王》(Erlkönig)。这是歌德于1782年为奥古斯特大公的母亲安娜·阿玛丽亚女公爵的歌唱剧 《渔家女》(Die Fischerin)所作的开场诗。据考证,1781年歌德来到图林根地区,在住宿的旅馆里听说当地一位村民连夜骑马带着重病的孩子去城里寻医看病,途中要穿过一大片树林。不幸的是,由于病情实在太重,孩子在求医归来途中还没能进到家门就死在了父亲怀里。听闻此事的歌德又联想到赫尔德收集的丹麦民歌《爱尔王的女儿》(Erlkönigs Tochter)。这首民歌讲述的是爱尔王之女邀请奥拉夫先生共舞,但却遭到了后者的拒绝,因为他要赶回家参加自己的婚礼。妒火中烧的爱尔王之女击打了奥拉夫的心脏,然后又将他放置于马背上,让他痛彻心扉地踏上归程。①Hans Mayer, Goethe - Ein Versuch über den Erfol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7, p.35.歌德受到这首民歌的激发,又联想起民间传说里的魔鬼夜里勾魂抢孩子的故事。魔鬼只要碰一下孩子,就能摄去魂魄,孩子便气绝而亡。于是他便将偶然听到的生活事件与民间传说相结合,创作了这首谣曲。
《魔王》的故事情节紧张而充满神秘色彩:父亲怀抱发高烧的孩子在黑夜的森林里骑马飞驰,森林中的魔王不断以各种美好的事物和神奇的幻象引诱孩子。深陷幻觉的孩子发出阵阵惊呼,最后在父亲怀抱中死去。
这是一首典型的民歌体诗,每段四行,抑扬格,相邻两行押韵,浊辅音结尾。诗的第一段首先交代了事情的缘由:“谁在深夜里冒风飞驰?是父亲带着他的孩子;他把那孩童抱在怀中,紧紧搂住他,怕他受冻。”(歌德 16)。第二段是父亲与孩子的对话,描述了两人对大自然的不同认识。“我儿,为何吓得蒙住脸?啊,爸爸,那魔王你没看见?魔王戴着冠冕拖长袍?我儿,那是烟雾袅袅。”(歌德 16)孩子眼中的大自然是感性的、神秘和充满魔力的,以魔王的形象出现,而父亲眼中的大自然则是客观的、理性的。接下去第三至第六段是故事发展的高潮,魔王、孩子和父亲三人的对话交替出现,直到最后悲剧的发生:“辛辛苦苦他赶回家门,怀里的孩子已经丧生。”(歌德 18)
需要说明的是,标题“Erlkönig”这一名字的由来,源自一个偶然的误会。赫尔德所收集的丹麦民歌原来的标题为“ellerkonge”,对应的德语单词应为“精灵王”(Elfenkönig),但赫尔德却将丹麦语“Eller”误译成了“Erle”(赤杨),由此产生了“Erlkönig”一词。②Peter Boerner, Johann Wolfgang Goethe, Bonn: Inter Nationes,1983, p.88.而丹麦语中“Eller” 其实是指一种外形类似侏儒的小妖,住在小山上或森林里,喜欢音乐和舞蹈。他们常对人类示好,但如果有违其意,也会逞强施暴。不无巧合的是,丹麦原型中“艾尔芬”(Elfen)小精灵与自然有着密切联系,而歌德塑造的魔王作为自然神力的象征,把人与自然、现实与超现实艺术地结合到一起。可以说,魔王这个形象全面反映了歌德的自然观,即他对大自然的认识。在歌德的眼中自然是伟大而又神奇的。他无边无际包罗天地万象,人在其中无法控制和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他面前人是孱弱渺小的。这一点在诗中得到充分体现。歌德笔下的魔王时而亲切和善甜言蜜语,时而面目狰狞逞强施暴。他代表着大自然的力量,代表着大自然的强大。父亲和孩子在他面前毫无抵抗之力。可以说原本丹麦传说中的小精灵在歌德这位德国作家的笔下变身为具有引诱性、象征自然之神秘的魔王,异质的文化在侨变过程中再次实现了“融化创生”的效果。
除此之外,歌德也将来自遥远东方的印度宗教之象融入自己的创作中。那首曾经备受争议的《神与舞女》(Der Gott und die Bajadere)便是最好的例证。
《神与舞女》取材于法国人皮埃尔·宋涅拉(Pierre Sonnerat)所著 《1774-1781印度及中国纪行》(Voyage aux Indes Orientales et a la Chine, fait par ordre du roi, depuis 1774 jusqu'en 1781)中的一个宗教传说,这一点从副标题“Indische Legende”(印度宗教传说)就能明显看出。该书的德译本于1783年在瑞士苏黎世出版。歌德在创作时除去了原作中描述印度风情的部分,这样的改编使故事超越了地域上的局限,从而升华为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神传说。
这则谣曲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摩诃天(即湿婆神,为印度教的主神)为了亲自体验人生,第六次下凡来到人间。在城市的边缘,神遇到一位舞女。看到她婆娑的舞姿和恭谦的态度,神很是欣慰,认为“她堕落虽深,倒有慈悲的心”(歌德 62),也感受到了舞女善良的本性。为了进一步考验她,神决定让舞女经受从极乐到至苦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舞女成为了神 “爱情的俘虏 ”(歌德 63),而这仅仅是实现完满人性的第一步。第二天清晨,舞女“发觉那可爱的客官,在她怀里已呜呼哀哉”(歌德 63-64),便倒在他身上悲啼,痛苦不已。尽管僧侣们提醒她:“这位不是你的丈夫。你过的是舞女生涯, 因此你并没有义务。”(歌德64)但真挚的爱情却能超越一切等级森严的区别与界限。舞女坚定地表示:“我要再看到我的丈夫!我要到墓地里去寻访。我怎能让他这样火化? 这是神一般的贵体。”于是“她伸出了她的手臂猛地跳进灼热的死亡”(歌德 65)。不料此时情节却发生了惊人逆转:“可是那位天神青年,却从火中坐起圣身。爱人投入他怀抱里面,跟他一同飘飘上升。忏悔的罪人使天神欣慰;不朽的圣神伸出了火臂把沦落的人带上了天庭。”(歌德 65)
根据宋涅拉书中所述,当舞女的决意尚未付诸实施以前,天神就显露出自己的身份并将她带走。其实,宋涅拉笔下的天神只是一位半神。而歌德却将原版的男主角升级为法力强大的摩诃天。在印度宗教中,印度主神一身有三相,即梵天、毗湿奴和湿婆。摩诃天即湿婆神的别名,或称大自在天,原为破坏之神,但同时也是繁殖与再生之神、舞蹈之神、忏悔者的保护神,据说拥有一千个名号。因此歌德这一谣曲中的神能在火中坐起,带着心爱之人一起升入天庭。如此改写,更加突显了拯救灵魂的主旨意义,也使故事有了更加超然的意境和更加高远的格局。
歌德保留了原版传说中非常的人物关系,并巧妙利用印度神话中神多次转世、化身为人或动物的叙事基础展开了大胆想象,创作出一个神人之间突破世俗价值和等级观念的动人爱情故事。有观点认为此首谣曲也表达了歌德本人对妻子克里斯蒂阿涅的忠贞之爱的感激之情,但其蕴含的普世价值却不容否定。甚至可以说这首谣曲表达了与《浮士德》相似的主题: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完全丧失人性,而爱情则可以使人由恶变善。因而对任何曾犯下罪过之人都不应放弃对其进行启发和引导。只要肯从罪过中走出来,他就能得到救赎并成为真正的人。
另外值得注意的还有,虽然谣曲中故事的发生时间被设定在远古,但歌德却在文中使用了现在时态,而且加入了不少当时的流行用语,如:“快乐和痛苦 ”(Freud’ und Qual)、 “惩罚或是赦免 ”(strafen oder schonen)、“大人物 ”(Die Großen)、“小民 ”(Kleine) 。这使故事的时间格局突破了常规的限制,具有了现实意义。而这种超越时空局限的普遍性和有效性正是古典主义文学所追求的完美境界。
“歌德在这首谣曲中既没有蓄意美化印度宗教,也没有将故事以任何形式与基督教联系起来。摩诃天的死不同于基督之死。基督为拯救人类而死,摩诃天的死是考验舞女人性的方式。摩诃天拯救舞女是因为她具有完美的人性,基督拯救人类恰恰是因为人类的人性缺陷。摩诃天作为神性的代表,舞女作为人性的代表,是两个极端,然而两者最终合而为一,意味着完美人性与神性的一致性。这种人性完美的社会标准在歌德眼里是超越宗教界限的。”①陈壮鹰:《解读歌德谣曲风格》,《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总之,古老的东方传说通过侨易过程,在这位德国作家的笔下绽放出了充满真爱与人性的光芒。
综上分析可见,经过歌德的变创,德国的叙事谣曲超越了发展初期以混乱、危机、扭曲和破坏为主的基调,不仅呈现出多元文化融通的丰富面相与内涵,而且还从最初的强调刺激、崇尚叛逆逐渐转向了追求和谐统一的古典之路,也因此多了份沉稳厚重的哲思深韵。
三、变创之因:包容的民间意识
德国的叙事谣曲之所以能在歌德笔下呈现出如此变化,是与诗人自身对各国的民间文化那海纳百川的包容态度密不可分的。
歌德曾在撰文评论阿尔尼姆(Ludwig Achim von Arnim)编辑的民歌集《儿童的神奇号角》(Des Knaben Wunderhorn)时写道:“有些诗歌虽然既不是由人民所写也不是为人民所创作的,但多年来我们却习惯地称它们为民歌,这是因为它们蕴含着健康精干的东西,它们懂得各个民族的核心和主干所包容、保持、吸收以及继续培植的正是这些东西。因此,这样的诗是真正的诗,再也没有比它们更纯正的诗了。这些诗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魅力……这里艺术同自然处在冲突之中,但正是这种相互的作用,这种努力似乎在追寻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已经到达。”②范大灿:《歌德论文学艺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45—246页。这里所说的目标,便是“用诗人的眼光活生生地观看一个有限的状态,可以把一个个体提升成为虽有界限但又无限的宇宙,以致我们以为在一个小小的空间内看到了整个世界。”③同上,第246页。
歌德还表示:“外来的财富必须变成我们自己的财产。要用纯粹是自己的东西,来吸收已经被掌握的东西,也就是说,要通过翻译或内心加工使之成为我们的东西。”④同上,第264页。
这足以证明,歌德正是以一种睿逸的眼光和博远的胸怀看待和接受那些来自民间的“健康精干”的营养,并在那种自然与艺术的张力中发现了属于诗歌的纯正魅力,也由此看到了一个无限广阔的世界。
在谣曲创作中,歌德正是广泛地吸收了不同国家民间文化里的“核心和主干”,然后“内化加工”成“自己的东西”。古希腊与罗马的众神、北欧的精灵传奇、古印度的神话,都转化成诗人笔下灵感的源泉,浓缩为触及认知世界和存在之本质的精华。
四、变创之思:歌德的世界文学观
如前所述,侨易学的基本构架具有“二元三维”的特点,即兼顾“物质现象”与“精神现象”,在器物、制度、文化三个层面的三维结构中进行考察。“它要求我们必须从具体的物质层面提取出更深层次的东西来,这就是物质背后的制度、文化、思想乃至精神。”①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第92—93页。所以,侨易学强调的是“物质性行动”而导致的“观念性变更”,即从一般的物质结构层面上升到高级的文化思想观念层面的情况。即是说,侨易学是一种反思科学—人文之现代问学方式的简单二元论划分,倡导以知识融通的手段应对被分科割裂得过于破碎的世界的方式②叶隽:《作为系统结构的侨易游戏——答范劲、杜心源君》,《上海文化》,2020年6期。,是一种通观的学术态度。
具体到歌德的谣曲而言,无论是古希腊罗马的遗风,还是北欧的民间传说,抑或是古印度的宗教故事,当它们在这位德国文豪的笔下融入德语文学的浩瀚海洋时,就注定会有侨易现象的发生。而这现象的背后,便是深广而宏大的观念性和精神层面的融通。这种融通的结果,就集中体现于歌德那举世闻名、影响深远的世界文学观上。
歌德在《艺术与古代》杂志的第六卷第一期中写道:“我坚信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文学正在形成,而在未来的世界文学中,将为我们德国人保留一个十分光荣的席位。”在给友人施特来克福斯的信中,歌德又写道:“我深信正在形成一种世界文学,深信所有的民族都心向往之,并因此而做着可喜的努力。德国人能够和应该做出最多的贡献,在这个伟大的聚合过程中,他们将会发挥卓越的作用。”③转引自杨武能,莫光华:《歌德与中国》(增订插图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1页。
由以上论述可见,歌德的目光远远超越了德国乃至欧洲的界限。他密切关注着人类的发展进步,并且实际参与了因为人类的进步而开始了的那个“伟大的聚合过程”④同上,第102页。,即由民族文学和地方文学形成世界文学的过程。
无数关于歌德的考据研究都已证明,歌德很早就了解了古代希腊罗马文学、希伯来文学以及古日耳曼文学三者融合而成的德国文学和西方文学全貌。随着对世界历史和现状的眼界日益广阔,他的文学兴趣也在发展。从阿拉伯文学到波斯文学、再到古印度文学,晚年又倾心于中国文学。可以说,“整个世界文学都在歌德的视野之中,他有可能比较它们,找出差异,但却发现了更多的共同之处。不仅如此,他还博采众长,致力于将不同民族的文学融合起来”⑤杨武能,莫光华:《歌德与中国》(增订插图本),第104—105页。,这便是歌德世界文学观形成的重要基础。
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主要包含以下几层意思:首先,是各民族间普遍的包容,即通过包括文学交流在内的精神交流,各民族间学会相互了解,相互关心,相互尊重。这种尊重主要体现在对待各民族文化自身特点的态度上。
在谣曲中,歌德就巧妙地将北欧、古希腊罗马和古印度文明中的各种元素化入自己的创作里,但同时又保留了丹麦神话中对神秘自然的崇拜、古希腊人酒神式的热情以及印度宗教中神变身下凡的文化内核,这便足以见其对异域文明的尊敬和重视。
另外,从谣曲的故事情节和主题思想中也可看出歌德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的宽容和容忍的主张:《柯林斯的未婚妻》通过一个由无情的教条引发的奇幻悲剧,揭示了对所谓的“异教”排斥打压的后果,从反面宣扬了包容的重要性;《魔王》中流露着对被夺去生命的孩子的哀叹和同情,同样饱含人道主义的悲悯;《神与舞女》中对舞女灵魂的拯救更是表达了超越一切等级界限的博爱。
正如歌德在为卡莱尔的《席勒生平》一书写下的序言里所述:“须知各民族在那些可怕的战争中受到相互震动以后,又回复到了孤立独处状态,会察觉到自己新认识和吸收了一些陌生的东西,在这儿那儿感受到了一些迄今尚不知道的精神需要。由此便产生出睦邻的感情,使他们突破过去的相互隔绝状态,代之以渐渐出现的精神要求,希望被接纳进那或多或少是自由的精神交流中去。”①转引自杨武能,莫光华:《歌德与中国》(增订插图本),107—108页。
事实上,根据以上分析,歌德的创作过程一直离不开对“一些陌生的东西”的吸收,也一直在传达着这种“迄今尚不知道的精神需要”。在诗人的笔下,北欧与南国,东方与西方,神灵与魔怪,神坛与坊间,理性与感性,都实现了自由的交流和有机的聚合,并最终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伟大影响。
其次,从歌德对世界文学的相关阐述来看,他从来都不会狭隘地只站在德国人或者德意志一个民族的立场来观察问题,而是胸怀着作为整体的全人类和全世界。歌德说过:“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公民,诗人会爱自己的祖国。然而,他在其中施展诗才和进行创造的祖国,却是善、高尚和美。”又说:“广阔的世界,不管它何等辽阔,终究不过是一个扩大了的祖国。”②同上,第103页。也就是说,歌德心目中的世界文学,不仅仅属于一个地区、一个民族,而属于全人类和全世界。他深信,“诗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不难发现,不管叙述的是怎样的故事,无论选取的是怎样的题材,诗人的终极主旨始终是作为整体的人:《柯林斯的未婚妻》立意对人之自由精神的追求,《魔王》关注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神与舞女》聚焦人性的真善美和对灵魂的拯救。可以说,歌德笔下的这些谣曲,绝对不是从某一种文化或某一个民族出发,而是放眼于整个人的平衡性、整体性、人道性和完美性。它们所体现的是歌德那格局广大、积极乐观的人文精神,和那深邃超前、充满辩证性的世界文学思想。
总而言之,诗人歌德乃是一个以全人类为同胞、以世界为祖国的胸怀博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事实上的世界公民。在这样一个世界公民的眼中,只有属于全人类的文学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文学。而他笔下的叙事谣曲中所呈现出的侨易学现象,正是这种世界文学观的直接表现和实现方式。通过侨易学的方法对其进行“观侨阐理”“取象说易”和“察变寻异”,探究这伟大的“聚合过程”背后那饱含对人类真挚情感和热爱的世界文学观,对于今天全球化背景下人们面临的种种困惑和矛盾也具非同一般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