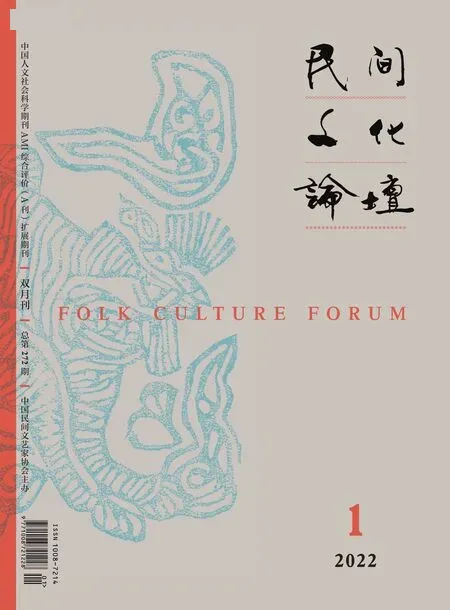关注世事变迁、追问“生活革命”的民俗学
周 星
民俗学长期以来把自己的研究对象确认为“民俗”,但民俗学家个人的“民俗观”却多有认知差异;或把它视为过往旧时在当下社会里类似“活化石”一样珍贵的“残留物”,或把它等同于传统文化;或把它局限于口头传承,或认为它关涉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的学者把民俗理解为从日常生活中提升的文化精华,另有学者则把民俗视为百姓平凡的日常生活(或生活文化)本身;有的民俗学家较多强调民俗的传承性、稳定性或连续性,另外一些民俗学家则较多强调民俗的流变和演进。有的民俗学家相信民俗内涵有民族精神或民族文化的本质性DNA,另一些民俗学家却认为民俗不过是人们在生活中的自主选择和人为建构。从民俗学的概论类著述中,读者们可以看到民俗被划分为不同的门类,且有关它们的描述往往是固定化的,然而,很多看起来传承久远的民俗,往往在现实中却不容易见到;与此同时,现实生活中的很多民俗,尤其是新民俗,却无法及时被民俗学的概论性知识体系所涵括。
近些年来,东亚各国新兴的现代民俗学的动态之一,是把研究对象确认为当下无数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生活”的本义是为了生存而活动,或为了生存而展开各种各样的实践,也因此,以“生活”为关键词的民俗学就必须聚焦普通生活者的日常变革,并把他们的主体性实践视为“日常化”生活文化之创造力的源泉,当然也视为是民俗变迁和生活革命得以发生的根本性动力机制。有鉴于此,本文拟对一直以来较多关注世事变迁和生活革命,以及生活改善运动的日本民俗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予以初步的梳理,以便我们在思考中国现代民俗学所面临的类似问题时,能够有所参考。
关注世事变迁的民俗学
民俗学曾经特别关注旧时过往的习俗在当今社会的“残留”,为了获得对这些“残留”的理解,早期的民俗学有对其“起源”的执着,也有对此类风俗演化至今的变迁史的追寻。因此,有一种理解是民俗学要从现存的民俗去发现过往被忽视的历史(例如,日本民俗学曾通过某种民俗分布的地域差异去探讨其传播的过程),它的指向是过去。但更多的民俗学家相信民俗学可以“经世致用”,对当下的社会有建设性价值,因此,他们特别关心世事的变迁,聚焦当下的现实生活和民俗文化,认为其与普通民众日常的幸福密切相关,亦即把民俗学视为现代之学,它的志向是当下。无论哪种理解,都不认为民俗是恒久常态的存在,也都不承认民俗有固定不变的原生形态。
虽然很多民俗学家更多地关心具有传承性的事象,或认为传统民俗根深蒂固,有着难以改变的观念或结构,但其实民俗学始终对世事的变迁,尤其是普通民众的生活文化的演变深感兴趣,并往往由此展开各自的理论。①鳥越皓之:《民俗学と近代化論》,鳥越皓之編:《民俗学を学ぶ人のために》,世界思想社,2003年,第42—59页。根据福田亚细男等人的归纳,关注世事变迁正是日本民俗学的重要特点之一。②[日]福田亚细男:《日本民俗学的特色——福田亚细男教授北师大系列讲座之一》,萧放、朱霞主编:《民俗学前沿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5—7页。柳田国男认为,民风民俗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变化不断;因此,他非常关心自身所处时代正在发生的世事变迁,这在其完稿于1931年的名著《明治大正史•世相篇》中有非常明确的体现。③岩本通弥:《世相》,小松和彦•関一敏編:《新しい民俗学へ―野の学問のためのレッスン26》,せりか書房,2002年,第75—86页。此书重点关注变动着的日常生活,按照柳田国男的说法,他是想依据现代生活的横断面,亦即每天在人们的眼前出现或消失的事实来书写历史。④柳田国男:《自序》,《明治大正史 世相篇》(新装版),講談社,1997年。为此,他大量采撷数十年间的新闻报纸资料,关注眼下存在但又不断消失的民俗,旨在透过素描日常生活中不断消失及出现的事实与现象,深刻揭示从明治到大正时代日本社会的近代化过程。第一章“映入眼帘的世相”,第二章“食物的个人自由”,分别讨论服装和食物;随后各章进一步论及日常生活的不同方面,诸如色彩、声音和气味,以及房屋与居住的感觉等,很多都是从未受到学者们重视,但确实又很有意义的问题。⑤[日]福田亚细男:《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说——柳田国男与民俗学》,於芳、王京、彭伟文译,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年,第113—116页。例如,他认为有些人在平常生活中也使用鲜艳色彩,这其实是与现代人的日常与节日发生了混淆有关。他颇为细腻地讨论了袜子和木屐等鞋履在明治大正数十年间的变化,从庶民普遍光脚到日常穿“足半”⑥“足半”是日本一种传统的草鞋,因长度只是一般草鞋的一半,故称“足半”或“足中”。它的优点是因为和足心紧密切合,一般难有泥沙进入,其功能类似当今的拖鞋。,后来才慢慢穿上袜子和木屐;劳作时的鞋履则从草鞋到橡胶长靴,但农用橡胶长靴必须用金钱交换才能获得,这意味着商品经济已经渗透到了乡村。关于食物和用餐方式,柳田认为,曾经以家族为单位的大灶塘构成了家族成员用餐的基础,但由于物流发达、生活方式变迁等给饮食环境带来冲击,逐渐出现了小灶用餐和个人进食,这些变化与家族单位的共同进食制形成了背反,有损家族的向心力。在他看来,孤独进食还有可能与现代社会的自闭症有关。关注身边诸如此类细微且持续变化着的人间世相,包括了解人际关系的存在方式以及人们意识的变化等,其研究是指向普通民众的“生活改善”①岩本通弥:《日本的生活改善运动和民俗学—Modernization和“日常”研究》,謝舒恬译,《日常と文化》,第7号,2019年10月,第19—133页。。
岛村恭则等学者均注意到社会学家鹤见和子对柳田民俗学的评论。鹤见认为,柳田民俗学并非单纯地探究民间传承,而是追求富有个性的社会变动论,它既不是对基于欧美中心主义的近代化理论的套用,也与社会学的近代化论理路不同。②[日]岛村恭则:《社会变动、“生世界”、民俗》,王京译,《民俗研究》,2018年第4期。鶴見和子:《社会変動論のパラダイムー柳田国男の仕事を軸としてー》,《曼荼羅Ⅰ基の巻―鶴見和子の仕事•入門》,藤原書店,1997年,第442—483页。柳田不把社会的变动归因于大人物们,而是围绕着庶民生活展开分析,在他看来,庶民生活的变化虽没有具体年号,但内发性的变动还是有大致的方向。柳田关心的是人们的生活世界中那些语言、艺术、感情与感觉的变化,包括信仰和行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女性的日常、儿童的文化创造性等等。在社会的结构性变动中,它们是如何内因性地发生变化的,哪些应该舍弃,哪些应该被保留,哪些又应该从外部汲取;当面向未来时,那些得以保留和新近吸取的要素之间又应该如何组合或彼此搭配等等。因此,民俗学的任务是要考察和阐明生活方式发生的演变背后的法则和因果关系。③[日]柳田国男、关敬吾:《民俗学研究的出发点》,王汝澜译,王汝澜等编译:《域外民俗学鉴要》,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4—60页。值得一提的是,柳田认为,对这一切的必要考察最好是由生活者、当事人自己来选择和做出决断,而民俗学只是推动实现这一状态的方法或路径。④[日]岛村恭则:《社会变动、“生世界”、民俗》,王京译,《民俗研究》,2018年第4期。
在柳田国男影响之下的日本民俗学,其基本立场曾经是把民俗学视为研究长时段的民俗历史变迁的学问,不仅如此,其对当下的社会及民俗变化也必须做出适时应对。例如,1980年代及以后,对乡村“过疏化”引发的民俗文化变迁问题,就进行了颇为集中的研究;1990年代及以后,对应于社会的人口高龄化和临终医疗,又加强了对生老病死等民俗的研究。⑤蔡文高:《日本民俗学百年要略》,周星主编:《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29—262页。铃木正崇曾经把1990年代后期视为日本民俗学的重构时代,他指出,由于民俗学逐渐摆脱了一直以来视“民俗”与“近代”彼此对立的观念,才有可能更好地处理现代社会中各种新的民俗现象及生活文化问题。⑥[日]铃木正崇:《日本民俗学的现状与课题》 ,赵晖译,王晓葵、何彬编:《现代日本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年,第1—20页。面对都市化发展出都市民俗学,面对环境问题发展出环境民俗学;面对都市化彻底完成、实现了城乡一体化的现代市民社会,又出现了“现代民俗学”的新动向,必须承认,日本民俗学确实是在努力地与时俱进。
由福田亚细男和宫田登合编的《日本民俗学概论》⑦福田アジオ、宮田登編:《日本民俗学概論》,吉川弘文館、1997年,第223—232页、第233—243页。,曾以专题形式论及人口过疏化与民俗变迁,以及都市民俗等话题,指出导致急剧的民俗变迁的原因,除了人口流动和都市化,还有消费革命等。乡村人口的过疏化使地域社会的传统民俗活动不得已中断或简化;诚如汤川洋司所指出的那样,“过疏化”意味着曾经连接不同农户的生活组织不再有效,从而使村落的功能丧失或退化,甚至影响到日常生活的维持,当很多农户出现继承问题时,村落的民俗也就无法继续传承下去了。①湯川洋司:《ムラの過疎化》、市川秀之他編著:《はじめて学ぶ民俗学》,ミネルヴァ書房,2019年,第222—231页。与此同时,消费革命带来物质生活的改善与生活方式的变迁,家用电器的普及改变了家庭的饮食结构,减轻了主妇的家务劳动,甚或促使故事等口头文学传统彻底趋于衰落;道路交通的整备和汽车的普及扩大了乡民交通圈及日常活动的范围;技术革新引发了乡民生计和生产民俗的变化以及传统技能的衰微;资本主义企业的组织原理影响和改变了社会的人际关系,进一步还影响到民众心态及意识的变化。此外,还有都市社会中邻里关系的变化、都市祭礼的新形态、市民信仰生活的世俗主义和个人化倾向等等。有些民俗文化逐渐脱离其传承母体而在博物馆和舞台上得以展示或展演,甚或成为文化遗产。直面诸如此类的世事变迁,日本民俗学颇为重视对具体变迁过程的微观分析,同时也较为关注伴随着民俗文化的变迁过程,民众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宇宙观以及宗教理念和情感等意识或精神层面的各种变化。
佐野贤治等合编的《现代民俗学入门》对世纪交替时期日本民俗学的课题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认为应该关注民俗在具体生活场景中发生变迁的过程,关注人们是如何具体地应对生活方式的各种变革的。除了突出地重视民俗传承方式(从口承到书写,再到电子传媒)的变化,该书还特设“现代社会与民俗”“国家与民俗”两章②佐野賢治、谷口貢、中込睦子、古家信平編:《現代民俗学入門》,吉川弘文館,1996年,第205—244页、第245—288页。。“现代社会与民俗”强调在地域社会发生巨变的背景下民俗事象的变化,对都市传说和都市空间中民俗文化的实际形态进行描述,同时还就应对现代社会的不安而不断演化的“治愈民俗”(包括疾病的意义、病因论的复合性、民间疗法、新兴宗教的医疗等)展开分析,最后则以南美日系移民的物质文化为例,讨论了越境移民的民俗。在“国家与民俗”的课题群中,首先是集中讨论了传统教育和近代学校教育此消彼长的嬗变关系、儿童的游戏和民俗、方言等如何在学校教育影响下走向衰微等问题,指出学校教育不仅不能传承日常生活的知识,还促使知识形态的传承发生彻底变革,亦即人们获得知识、进而判断事物的方式均由此发生了巨变。也因此,如何在学校教育中包含乡土文化的学习成为值得重视的问题。其次是讨论了国家对青年的规训、引导和征用,对于青年的社交、游戏等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再次是讨论了战前的地方改良运动和战后生活改善运动的关系,揭示了国家权力对国民生活的强力干预所导致的社会变革与民俗变迁;最后讨论了战争与民俗的相关问题,例如,战时统制导致国民生活,尤其是饮食民俗和衣着民俗的均质化等等。
民俗学早先曾重点关心农村生活和乡土文化的变迁,但很快就发现变化的主要原因其实是来自都市和都市化。有一些长期关注民间传承的民俗学家在面对都市时感到力不从心,但也有研究证明,通过将都市新形成的民俗与农村、山村、渔村的传统民俗进行比较,进而去深入地理解民俗的变化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③[日]上野和男:《都市民俗学》,陈秋帆译,王汝澜等编译:《域外民俗学鉴要》,2005年第80—86页。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起,日本逐渐兴起了都市民俗学。1970年,千德叶儿发表论文考察了丧葬习俗在都市中的状况和问题④千葉徳爾:《都市内部の葬送習俗》,《人類科学:九学会連合年報》第23集,1970年,第1—14页。;1973年仓石忠彦发表论文讨论了都市小区公寓的传统民俗⑤倉石忠彦:《団地アパートの民俗》、《信濃》25—8,1973年,第31—42页。;继在都市公寓“发现”民俗之后,仓石忠彦进一步明确地主张应把都市生活视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从而完善民俗学的学科体系。随后,宫田登、岩本通弥、中村美孚、高桑守史、小林忠熊等人分别发表论文或调查报告,都市民俗学一时形成潮流①[日]福田亚细男:《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说——柳田国男与民俗学》,於芳、王京、彭伟文译,第28—31页。。新兴的都市民俗学是呼应都市化发展的民俗学新动向。都市居民小区迅速和大量增加,都市化渗透农村促使专业农户急剧减少和农村生活方式巨变;新市民追求新生活,以效率与合理主义为标准,在日常生活中选择传承或创新,但在求新求变的同时,生活文化的某些连续性依然存在,或基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还会把某些并不那么“合理”的传统看得格外重②[日]仓石忠彦:《日本民俗学的城市化概念》,陈晓晞译,《文化遗产》,2008年第4期。。仓石忠彦认为,有些变化其实应归因于近代化而不是都市化,像农业机械化和技术创新降低了体力劳动的强度,并使上一辈人以身体体验所承载的知识逐渐失效,进而失传。在都市生活中,人们不再通过身体劳作直接从自然获取生活资料,都市生活方式必须把货币价值视为日常的优先考虑,并为此经营各种人际关系。仓石忠彦认为,新的住宅小区作为生活场所,人们在其中生活,自然就会有传承性的事象存在,因此,在住宅小区展开民俗学调查时需要关注诸多调查项目。例如,户主们如何建立邻里关系,如何彼此打招呼;业主自治会的组织形态如何,居民们创设或延续的节日(正月和盂兰盆节以及小区的各种庆祝活动),居民是否参加小区所在地域的民俗活动,当然,还包括小区居民每天的时间安排,以及人们是如何利用单元住宅内部的空间等等③[日]仓石忠彦:《都市中的传承与调查》,西村真志叶译,王晓葵、何彬编:《现代日本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第78—90页。。仓石忠彦经过调查发现,尽管小区生活仍可能存在一定的地域性,但公共假日、学校假期和商业活动等对居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更大。通过调查,他发现居民个人生活史的研究在都市民俗学的研究方法上很有意义。
都市民俗学在日本经历了去都市“发现”(传统)民俗、承认存在都市民俗(包括如宫田登指出的那样,都市人的不安导致特有的都市民俗)、承认都市形成新民俗(都市传说、小区民俗、繁华街的民俗)等几个不同阶段。但仅仅过了20年,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都市民俗学逐渐地就不再为民俗学家提及了。究其原因,主要是都市化的彻底实现使得民俗学面对的不再是都市和乡村的区分,而是都市化在全国实现后的现代社会,无论大都市还是稍微偏远的地方,全国均处于现代生活方式或现代民俗的状态之下。④[日]福田亚细男:《日本现代民俗学的潮流——福田亚细男教授北师大系列讲座之四》,萧放、朱霞主编:《民俗学前沿研究》,第45—60页。于是,都市民俗学就在发展中逐渐朝“现代民俗学”的方向演进,自称都市民俗学的研究者逐渐消失。⑤福田アジオ:《現代日本の民俗学―ポスト柳田の五〇年》,吉川弘文館,2014年,第180—182页。现代社会当然也会有新民俗的产生,民俗学不应只以老人作为访谈对象,例如,小学校的学生群体也可产生新的民俗(校园传说)。不过,在解释现代社会的新民俗时,民俗学家通常还是会把它和此前曾经存在过的民俗或传统联系起来进行解说。
在顺应社会时代之变出现都市民俗学以及随后它朝向现代民俗学发展的过程中,日本民俗学界也经历了一些必要的学术辩论。20世纪70年代有关“常民”概念的讨论,其实就有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大变迁的背景,后来基本放弃此概念,事实上也与都市民俗学有关。因为现代社会里个性多样化的国民已无法用“常民”去概括了。至于民俗学究竟是过去之学,还是现代之学的讨论,较为多数的民俗学家倾向于认为民俗学是通过研究当代生活文化,揭示当代生活中各种问题的现代之学。⑥[日]仓石忠彦:《日本民俗学的城市化概念》,陈晓晞译,《文化遗产》,2008年第4期。民俗学家在田野调查中遇到的所有人,都是生存在现时今日的生活者,他们对以前过往的记忆虽有多层累积,但与其说“中世”“近世”,不如说“近代”才是与“现在”密切相关的“最近的过去”。对日本民俗学而言,所谓“近代”就是指从经济高速增长期上溯至二战战败时或稍微再早一些,至明治、大正或昭和初期。①岸本诚司:《日本民俗学的可能性与近代》,於芳译,《民俗学刊》第六辑,澳门:澳门出版社,2004年,第35—42页。换言之,民俗学虽然留心旧时过往的传统,但归根到底,它研究的是“近代”以来的当下。
虽然都市民俗学在发展中归于消解,但20世纪90年代至今有关世事及生活文化变迁的民俗学研究却从没有中断。例如,福田亚细男曾提及的川村邦光的研究,在《幻视的近代空间》一书中②川村邦光:《幻視する近代空間―迷信•病気•座敷牢、あるいは歴史の記憶》,青弓社,1997年。,作者对各种“迷信”,诸如狐狸附体、座敷牢(关押精神失常者的小屋)、神经病、巫女等,以及涉及儿童、少女、战争等很多社会民俗事象的变迁轨迹展开论述,凸显出社会文化转换时期人们宇宙观的变化;其研究并不是只关心某些民俗要素的变迁,而是宏观地描绘出人们的心性和精神世界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人的生活方式迅速“平准化”,号称一亿国民都是中产阶级,因此,民俗学以往那种从全国各地搜集民间传承的事象予以比较,进而探索其起源或祖型之类的研究方法就显得落伍了。③石塚尊俊:《山陰地方の民俗研究》,《日本民俗学》第200号,1994年11月。民俗学必须面对生活方式的变化,不断探索新的课题。1995年10月,日本民俗学会第47届年会以“追问‘故乡’”为主题,多位民俗学家集中讨论了“故乡”这一范畴的复杂性,但大都充分地意识到因为世事变迁、生活革命和人生过程,故乡(家乡、故里)也会发生巨变,人们的“故乡观”和故乡意识也随之变化。虽然离乡经验是乡愁产生的前提,但没有离乡的人们也会因为居住环境的巨变、物是人非的世事和人生变故等而产生和乡愁类似的共鸣或感慨。面对美化故乡日益成为普遍现象的社会现实,民俗学家追问故乡,同时也就是在追问现代社会。④田中宣一:《故郷および故郷観の変容》,《日本民俗学》第206号,1996年5月,第2—12页。1997年,日本民俗学会的机关刊物《日本民俗学》第210号出版了以“地域开发与民俗变化”为主题的专辑,高桑守史对日本的地域开发做了分类,指出有三种不尽相同的开发,一是地域居民内发的持续性开发,二是由国家和民间企业等来自外部的资本所主导的大规模开发,三是大规模开发导致难以维持自立性的地域社会出现了生活的危机感,在经过反思之后出现的地域振兴活动。第三种开发往往是由地方政府行政主导,但同时也是本地生活者试图在便利性和地域社会需要调和的状态中有所创新的运动。他指出,村落或地域社会振兴运动的过程,往往伴随着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亦即对故乡传统的动员,这往往形成一个套路,希望很多人前来观光。导致这种情形的原因,主要是缺乏资源或不具有内部资本,于是只好向地域社会的传统寻找资源。不过,如此的故乡或传统,只是引起离乡者或都市居民等“他者”的乡愁,其与地域社会的实际生活状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跌宕,如此的地域振兴可能只是在人们的乡愁情怀中基于印象而生产出虚像,似乎是要重现所谓理想的过往,但实际上有过当地生活经验的人们却并不认为曾经有那么美好。高桑守史认为,地域开发必须根植生活者的日常,才能够为子孙带来真正的幸福。⑤高桑守史:《地域開発と民俗変化―総論にかえてー》,《日本民俗学》第210号,1997年5月,第1—5页。
2010年10月,日本民俗学会第62届年会的公开研讨会以“生老病死所见之民俗变化”为主题。与其相呼应,此前于7月11日举办的第850次座谈会,深入讨论了“民俗学如何把握‘变化’”的课题,福田亚细男以“作为历史认识之学的民俗学与变化”为题,真野俊和以“变化和变异:民俗为何分布”为题,新谷尚纪以“日本民俗学的基本是传承论,也是变迁论”为题,分别从不同角度讨论了民俗学研究民俗变迁的必要性、独特的路径与方法等。进入21世纪,日本民俗学一如既往地关心当下正在兴起或变动中的民俗与生活文化。2003年11月,《日本民俗学》第236号推出“民俗主义”特刊,除进一步梳理来自德国和美国民俗学的一些新概念及其意义之外,共有11篇论文分别讨论了节令食品、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常生活再现的展示、观光、传统文化产业、基于传说的地域认同建构、乡土玩具、民艺和民俗文化的审美化、葬仪、乡愁与摄影家的作品、媒体表象的节祭以及文化政策等多个重要课题的相关事象,以及它们在当下日本社会中各自具体变迁的历程。①[日]西村真志叶:《民俗学主义:日本民俗学的理论探索与实践——以〈日本民俗学〉“民俗学主义”专号为例》,《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随后,“民俗主义”成为现代民俗学中较为核心的概念之一,日本民俗学的“民俗主义”研究,其实也就是对民俗在现时当下的变化及其相关的机制和逻辑的揭示。
经济高速增长与消费
成城大学的民俗学家们曾在20世纪80年代实施了对20世纪30年代由柳田国男主导的山村调查和海村调查时隔半个世纪之后的追踪调查,结果证明几乎所有地域社会的所有民俗事象均发生了剧烈变化。②田中宣一:《〈山村調査〉追跡調査の追跡》,《民俗学研究所紀要》第41号,2017年3月,第49—81页。高桥泉以地域社会的近代化为主题,分别对“山村地域社会”和“沿海地域社会”的经济(尤其是生产结构与消费生活)、政治(尤其是村落结构)、社会(尤其是社会集团)、文化(尤其是信仰生活)的近代化过程进行了验证。③高橋泉:《地域社会と「近代化」―柳田国男主導〈山村調査〉〈海村調査〉の追跡調査から》、まほろば書房,2005年。虽然有批评认为,其未能聚焦个人而使论述流于表面,但对于大规模和系统性的民俗变化的掌握确实非常重要。田中宣一在论及“当今传承的变化”时,尤其强调了1960-197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变化,诸如,机械化带来了农业生产方式的极大变化;石油大量输入带来的能源革命促使传统的薪炭行业衰落;根植于稻作农耕传统的祭祀与节日持续变化,甚至结婚和生孩子的仪式也在快速变化等等,民俗学家必须正视这些变化并进行正确的记录。但是,在很多民俗事象不断变化的同时,有些却保持不变或较少变化,那么,它们是如何传承的?保持不变的原因何在?民俗学必须追究其中的原因④田中宣一:《有关传承和陋习的认识》,宗晓莲译,《日常と文化》第5号,2018年3月,第81—87页。。
伴随着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大规模的都市化、近代化,日本全社会得以实现国民物质消费水准的大幅度提升,衣食住用行等日常生活发生了全面变革和整体性巨变,亦即“生活革命”。所谓“生活革命”就是狭义的民众“消费革命”。1954年,日本电机行业提出了“家庭电气化”的宣言;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的《经济白皮书》与《国民生活白皮书》均对民众旺盛的“消费”行为和由此导致国民生活的变化予以了特别的关注。当时在日本社会出现了追求生活革新的几大标准:生活的西化程度、家务劳动的合理化、休闲消费的增加程度。例如,都市家庭的谷物消费中面包类的支出比例,衣物中西装的支出比例,各个家庭拥有写字台的比例等;在农村,除了面包,还关注肉乳蛋的支出比例等。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逐渐为消费所牵引,“消费革命”表现最突出的便是家用电器的逐渐普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先是有“三种神器”之说,人们把家庭拥有电冰箱、黑白电视和洗衣机等视为生活现代且富足的象征;随后,又有“新三种神器”之说,又把彩色电视、空调机和私家小汽车视为新的家庭目标,由于彩电、空调机和小汽车的英文表述分别为Color TV、Cooler、Car,大众媒体又把“新三种神器”表述为3C。
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出现了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常生活的怀旧氛围,当时的民俗学也参与其中,并被福田亚细男称为“乡愁的民俗学”①福田アジオ:《現代日本の民俗学―ポスト柳田の五〇年》,吉川弘文館、2014年,第258—261页。。有关这一时期的生活再现展览引起了广泛关注,其展品不再是土灶、火炉、厨房的旧家具之类,而是黑白电视、用旧的电饭煲、冰箱、收音机、洗衣机之类,由于与当下的现代日常生活直接相关,并属于身边“过往”的生活经验,所以,这些实物所构成的生活场景引起了很多人怀旧的共鸣。②青木俊也:《再現•昭和30年代——団地2DKの暮らし》,河出書房新社,2001年。松户市立博物馆在1993年4月开馆时举办的现代史展览,以“常盘平团地的诞生”为主题,以原大尺寸复原了日本住宅公团提供并于1960年开始入住的小区公寓(4389户)的一个家用电器齐备的2DK单元③2DK:LDK是英语单词living、dining和kitchen的略称,分别对应于商品房的客厅、餐厅和厨房。若是有两个单间(卧室),再加上LDK,便称为2LDK。,再现了入住者一家积极地投入都市新生活的居家日常,这可以说是以博物馆展示的方式,对集合住宅在20世纪后期以来日本式生活方式的建构和确立方面做出的历史性贡献进行了恰当的评价。这类涉及生活革命的专题展览的成功之处,除了可以和重点展示生活革命之前乡村传统生活的展览形成鲜明对比之外,还总是吸引家长们带着孩子去看展览,很多家长作为曾经的生活经验者,总是会一边回忆,一边给孩子解说。④青木俊也:《昭和三十年代生活再現展示とノスタルジアに見るフォークロリズム的状況》,《日本民俗学》第236号,2003年,第82—91页。
民俗学家认识到,上述家用电器只是都市家庭热衷与追求的部分物品,这个与现代日本式生活方式直接相关的旧物清单,其实还可以列入更多,例如,煤气灶(以及电饭煲)、吸尘器、洗碗机、抽水马桶、合成洗净剂、塑料或金属容器等等。伴随着这些全新的生活机器(或产品)进入家庭及陆续普及,很多传统的生活技术趋于消亡,一般民众的居家生活自然也就焕然一新。对于那个尚未完全富足,但对未来充满乐观、憧憬和希望的时代的怀旧或乡愁,在世纪之交前后成为日本社会的一个市场级的现象,的确与博物馆对当时生活的展示热潮有关。对于民俗学而言,研究现代生活的起源和搜集、积累与之有关的民俗资料,成为了重要的课题。重要的是,这些资料和传统的民具或民俗文物截然不同。在高速经济增长期,很多人家的旧器物被大量抛弃;与此同时,伴随大阪万国博览会(1970)的举办,日本全国兴起了古董收藏热。各地涌现的古董市场上,相继出现了两类以前不太常见的旧货,一类是传统的民具杂货,再就是那些不久前被淘汰的家用电器。前者往往是各地兴起的历史民俗资料馆或博物馆着力收藏的,后者则成为以生活革新和生活革命为主题的特别展览所青睐的展品。日本各地的民具搜集往往是由地方上的老人们进行的,有时会利用废弃的小学校舍等作为乡土博物馆的馆舍或仓库,展示或收藏这些民具,在这个过程中,民俗学家往往也介入其中。⑤門田岳久、杉本静:《運動と開発—1970年代•南佐渡における民俗博物館建設と宮本常一の社会的実践》,《現代民俗学研究》,2013年第5号。
2010 年 3 月,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综合展览的“现代”展,其前半部分的主题为“战争与和平”,后半部分的主题即“战后的生活革命”,包括“高度经济成长和生活的变貌”等。该展览生动再现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因经济成长而导致生活变化的实际过程,包括消亡的山村生活和全新的都市小区生活,后者的基本原型是从1962年起陆续入住的公营赤羽小区。该展览对战后高度经济增长与生活革命的主题非常重视,可视化地反映了涉及生活革命的民俗学研究成果,在日本有一定的示范意义。各地的历史民俗博物馆或资料馆在涉及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和生活革命等主题时,往往会以它作为参考。为配合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的这次展览,2009年6月20日在东京举办了主题为“高度经济成长和生活变化”的学术论坛(第69回历博论坛),通过民俗学和经济史学的学术对话,深入探讨了高速经济增长和生活革命的关系。①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編:《高度経済成長と生活革命ー民俗学と経済史学との対話からー》,吉川弘文館,2010年。全程参与策展和相关学术研究工作的岩本通弥在此论坛的讲演,便是后来他的著名论文《现代日常生活的诞生》。岩本通弥基于现代民俗学的立场,借助官方统计资料和民俗志资料,深入研究了经济高速成长时期的国民生活,揭示了与现今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的现代日常生活的诞生及形成的基本过程。他认为,家庭的变化和少子化均与作为家庭的“容器”,亦即模式化集合住宅的生活方式日益普及有关。岩本通弥把高层集合住宅密集的小区、仅由夫妇和未婚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以及清洁卫生的室内生活视为现代日常的基本要点,认为此种都市型日常生活方式的普及,其实是与水、电、煤气的稳定及大量供给密不可分的②岩本通弥:《现代日常生活的诞生——以昭和37年度厚生白皮书为中心》,施尧译,《日常と文化》第2号,2016年3月,第127—140页。。在岩本通弥看来,曾经受制于村落社会传统的约束、基于辈分连续性而纵向跨辈分传递的经验、智慧和日常知识逐渐失去重要性,而如媒体带来外部信息那样,由外部传来的知识、经验和价值观开始支配生活世界的新时代已经到来。他认为,高度经济增长导致民俗学的环境发生变化,使之有了危机意识;与此同时,民俗的消亡与衰落,则促使国家将其文化遗产化,使之成为保存和欣赏的对象,由此,民俗学也就出现了“文化遗产学化”的倾向。③岩本道弥、菅豊、中村淳:《民俗学の可能性を拓くー「野の学問」とアカデミズム》,青弓社,2012年,第14—34页。
曾经负责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高度经济增长和生活变貌”主题展览的关泽真弓,主持了文部省重点课题“关于高度经济增长和生活革命的民俗志追踪研究”(2013-2015),也试图通过民俗志追踪研究,揭示都市型生活方式得以实现的过程、动力与机制,并得出了和岩本通弥类似的结论。关泽认为,战后经济的发展带来劳动力的大转移,曾经自给自足的农村、山村、渔村的传统生活方式趋于解体;从1955年起,日本“住宅公团”(都市建设机构)开始大量地供给住宅小区,从而推动了由年轻夫妇和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居住在2DK单元房里的现代生活模式的诞生。但这种生活方式一方面是清洁、舒适的都市新生活,另一方面则是对大量能源的消耗。与此同时,她还对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及其前后日本人的葬礼、墓制以及饮食生活等的变化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④関沢まゆみ:《火葬化とその意味─「遺骸葬」と「遺骨葬」:納骨施設の必須化─》,《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第191集(高度経済成長期とその前後における葬送墓制の習俗の変化に関する調査研究─《死•葬送•墓制資料集成》の分析と追跡を中心に─),2015年2月,第91—136页。関沢まゆみ:《お煮しめとサラダ》,《歴博》196号,2016年5月,第10页。
坂田稔认为,现在日本一般民众的生活方式,正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20世纪70年代前期这段时间确立的,至今它已有数十年的历史,可以说形成了规范,进入到传承领域的状态,故不妨将其命名为“日本式现代生活方式”。所谓“日本式生活方式”的关键词之一,就是“消费”,全社会人口的主流亦即工薪阶层生活在消费品信息和物质的汪洋大海中。在这种生活方式下逐渐形成了具有稳定性的新民俗文化,例如,饮食以米饭为主,同时采用日西中合璧的副食;衣着基本为西式,和服作为盛装;住宅被改造成和式榻榻米房间与西式房间并置,并配有完备的厨房、餐厅、浴室和卫生间设施;红白喜事的婚礼、葬礼及婴儿出生,已不再在家庭或社区内部举办或完成,而是分别委托给婚宴设施(或宾馆)、殡仪馆和医院;人生仪式除满月初拜神社,儿童的“七五三”庆贺仪式也基本固定化;节假日体系除周末和政府主导、体现天皇制国家的节日之外,传统岁时也得到一定程度的青睐,例如,正月、盂兰盆节、春分、秋分等;中元节和岁暮年末的礼品馈赠逐渐形成模式;人际互动中鞠躬行礼的问候方式,以及室内看电视和户外体育休闲也都逐渐形成模式等等。①坂田稔:《日本型近代生活様式の成立》,南博•社会心理研究所:《昭和文化続 1945—1989》,勁草書房,1990年,第7—32页。上述日本人生活文化的当代特点确实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它仍处于持续变动之中。20世纪50年代后期,消费重点从食品类转向服装类,20世纪60年代以后再朝耐用消费品大件转移,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又朝观光旅游转移,这时日本的恩格尔系数已降到26%,个人消费结构有了更多余地,因此变化也就愈加丰富。②崔世广主编:《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变革与文化建设研究》,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4页。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消费,彻底从基本消费及物质需求的饱和状态进入到追求满足自我实现、自我开发和个性价值观层面的需求,即便是在生活领域也特别重视文化性需求,并由此催生和推动了服务业的全面提升。③王斌:《步入小康社会的日本休闲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53—54页。
高桑守史认为,民俗变迁往往容易因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物质发明而引起,它们使迄今沿用的技术和生活用具等被废弃,取而代之以更有效率和更为合理的技术或器物。新的技术和器物以极快速度引起持续变化,并从物质器物层面朝社会生活层面延伸,例如,渔具、渔法的革新导致传统的渔捞生产组织解体,从而形成新的组织机制等。④[日]高桑守史:《人口过疏与民俗变异》,刘文译,王汝澜等编译:《域外民俗学鉴要》,第109—118页。
民俗学家若是从生活者的角度直面普通人的日常实践,就很容易发现与都市小区的单元住宅、核心家庭、家庭生活的西化(近代化)趋势相配套或关联的,便是家具的电器化,亦即具有耐用消费品属性的家用电器彻底占领和主导了人们的室内空间。冰箱、煤气灶和电饭锅等生活机器以及厨房环境的改善,减轻了主妇的家务劳动;电视普及使都市日常生活场景瞬间传到乡村,乡民日益倾向于接受都市生活方式,超越各个地域的全国性普遍的生活方式渐趋形成。消费革命及物质生活的合理化还是促使村落及家庭个性逐渐消失的原因,甚至农家的饮食生活也迅速出现了快餐类食品。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仅从物质和社会变动来解释生活民俗的变化还不够,例如,煤气灶取代火塘土灶,带来炊事场所均一性的合理化转变,但也存在地域、环境及家庭的不同情形,若是观察实际发生的变化,便可知晓人们拥有改善自身生活的目标,同时也是依据自身的价值观对新生事物有所取舍或选择的。⑤山中健太:《戦後の生活変化の受容と生活改善》,八木透編著:《新•民俗学を学ぶー現代を知るために》,昭和堂,2013年,第233—237页。换言之,生活者内在的意识、价值观和动因亦应得到关注。
早期的民俗学对“消费”研究的不多,后来才逐渐重视对消费行为与民俗变迁之间关系的研究。大藤时彦曾在柳田国男主编的《明治文化史•风俗》中执笔“第12章 消费生活”⑥大藤時彦:《第12章 消費生活》,柳田国男編:《明治文化史•風俗》,原書房,1979年,第417—450页。,他把消费行为限定为金钱的支出,深入讨论了明治时代以降商品经济渗入日本农村的过程,从集市、商店到百货公司的发展,从自产到购买消费品的转变,商品充足供应使旧时储备货物的必要性趋于消失,民众生活用品逐渐出现流行现象,人们醉心洋货并形成互赠礼品的习俗等等。阿南透对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消费革命格外关注,重点对消费中的“晴“与”亵”①“晴”与“亵”:由柳田国男提示的日本民俗学的一组重要概念,可分别对应于文化人类学文献中的“非日常”和“日常”。例如,婚礼、节日等属于“晴”,每天重复的普通日子属于“亵”。但由于消费革命,民众生活中此前的这类区分出现了混淆和暧昧的情形。(亦即非日常与日常)做了深入分析。他把日常生活必需品消费区分为“亵”的消费,亦即基础性消费,例如,购买大米和面包等生活必需品,购买方式出现了推销上门、送货上门、赊账、分期付款等多种花样,尤其是超市的出现与普及,迅速成为人们穿着随意即可随时去购买廉价必需品的场所。但是,由于市民日常居家生活和超市的关系日益密切,一旦发生危机导致物流有可能中断,马上就会出现连卫生纸也抢购一空的景观,这种现象的背后乃是市民家庭孤立无助的现实。和必需品的日常消费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所谓“晴”的消费,亦即非日常的购物,例如,去高档百货商店消费或购买价格昂贵的高档家用电器,以便让自己成为别人攀比羡慕的对象(或因攀比羡慕别人而去消费)。阿南透指出,伴随着消费革命产生的变化有多个层面,例如,男子上交工资,由主妇统筹安排家庭消费支出;家务劳动因家电化而大幅度减轻,因此,家务也就形成了不求外人的倾向;家庭成员一起用餐的频次下降,外食机会增加,饮食个人化趋势日趋显著等等。②[日]阿南透:《民俗学视野中的“消费”》,赵晖译,王晓葵、何彬编:《现代日本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第405—421页。
耐久性消费品的普及和一次性用品的泛滥,均预示着不久以后一个人的单身生活将越来越便利,已经核心家庭化了的社会,还将进一步出现家庭原子化(个人化)的趋向。在消费革命的发展过程中,作为消费者的普通民众往往就是通过拥有或选择不同的物质消费品,来表达或建构自身日常生活的方向和意义。目前,日本已从所有人均渴望同样的物质(消费品)的大众消费社会,达到了刻意追求附加值与个性的高度消费社会,但是,过度消费导致出现物质饱和现象,并产生越来越多的垃圾,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们为物质的包围所困扰,因此,近年遂出现了颇具逆反性的“断舍离”现象。
“生活革命”前后的民俗变化
几乎所有民俗学家都意识到了消费和生活革命带来的日常生活剧变,深切感受到民俗文化传承发生的断裂,以及民众生活意识的巨大变化,因此,生活革命长期以来始终是日本民俗学颇为关注的课题领域。不少学者采用“今昔比较”的方法,亦即将生活革命之前和之后民众生活文化的变迁状况予以比较,在细密观察的基础上探讨各类民俗传承的连续性和断裂性等问题。除了对新近诞生并逐渐成为现实的新岁时习俗、新人生仪礼和新的娱乐、艺能等予以关注之外,民俗学家还必须同时面对如何理解消失的民俗、变异的民俗以及它们与新生的民俗之间复杂的关联性等全新的课题。当然,学者们的观点并不完全相同,既有较多强调断裂性的立场,也有较多强调连续性的见解。
以前日本民俗学的饮食文化研究,主要是以山村、农村、渔村的传承性食材、调理方式、节日饮食等为中心,各市町村的饮食习惯调查以及《日本饮食生活全集》等①日本農書全集編集室編:《日本の食生活全集》全50巻,農山漁村文化協会,1993年。,便属于此类研究。这些研究较多偏重节日饮食和日常饮食的区别,较多讨论大米或杂谷的饮食生活史、诸如正月制作年糕等礼仪饮食及其信仰的意义、或者还有所谓“神馔”②神馔”是指神社举行祭祀时,人们为神贡献的各种以食物为主的供品。通常多为白米、酒、山珍、海味、时令食品、本地土产以及和祀神存在特别因缘的食物等。祭祀仪式结束后,供品由参与祭祀的人们“共食”,从而既增加与神的一体感,也加强人们的连带感。“神馔”有“生馔”和“熟馔”之分,前者指食材本身,后者则是经过加工料理、并受日常饮食化影响的供品。的象征性等。不过,生活革命前后饮食生活的变化,也很快引起了关注。③新谷尚紀、関沢まゆみ編:《民俗小事典•食》,吉川弘文館,2013;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歴博》第196号(特集:《高度経済成長と食生活の変化》),2016年5月。古家晴美对长野县立科町的农户进行的民俗学访谈,发现了人们意识和感觉的微妙变化,例如,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物质尤其是食物的丰足,人们对于丢弃食物的行为还会产生一种愧疚心理。④古家晴美:《ある農村における硬度経済成長期の食生活―《ビシャル(捨てる)》ことと向き合った時代―》,《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第171号(特集号:《高度経済成長と食生活の変化」),2011年。现代民俗学会2013年的年会,主题即为“高度经济增长期饮食生活的变貌”,西野肇、表真美和村濑敬子等人分别发表了题为“家电制品的普及与生活变化:以冰箱为中心”“饮食生活与家族团圆”“料理与媒体”的研究报告,证明了从民俗学路径研究现代饮食生活及文化的有效性,令人耳目一新。⑤関沢まゆみ:《食生活の変化と民俗学》,《日本民俗学》第300号,2019年11月,第17—30页。经济高速增长和生活革命,促使一般人的饮食生活进一步西化,冰箱的普及使食物的冷藏、冷冻成为可能,饮食生活开始追求新鲜食材,并促使人们发现了“冰镇”的美味。早期的民俗学曾经重点研究厨房里的民具,但这一时期家用电器成为生活的重心。家用电器的普及和饮食生活的洋风化,相当程度也受到以NHK“今天的料理”为代表的饮食节目和各种妇女杂志的菜谱、食谱等以及电视和电视剧的影响,电视里的料理节目推动了家庭饮食的西化,导致人们憧憬、渴望被洋式料理和各种家用电器所包围的日常生活。随后,伴随着快餐业的兴起,冷冻食品和各种半加工或全加工的食品进入日常饮食;食品外卖业的发展,也使得人们的饮食生活程度不等地出现了外部化的倾向,亦即外食的机会和次数日趋增多。⑥崔世广主编:《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变革与文化建设研究》,第180页。
研究者们当然也注意到传统的年节行事发生的变化。比如,传统节日普遍出现简略化倾向,有的甚至趋于消亡;很多年节的气氛日趋淡化。都市化导致农村人口过疏,很多村落的传统节日或祭祀难以为继。⑦[日]高桑守史:《人口过疏与民俗变异》,刘文译,王汝澜等编译:《域外民俗学鉴要》,第109—118页。但另一方面,城市生活形成了新的节奏,企业、职场和学校的运行节奏和公共节假日构成了现代都市生活基本的时间框架。学校本身形成的生活文化及其节奏,诸如开学和结业典礼,还有修学旅行等,通过各个家庭对全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⑧古屋和久:《学校で学ぶ民俗》,市川秀之他編著:《はじめて学ぶ民俗学》,ミネルヴァ書房、2019年,第266—276页。值得一提的是,处在地域社会的学校逐渐部分地承担起一些民俗传承的功能,除了课程涉及“节供”之类民俗的内容之外,还有多种汲取了民俗性活动的校园生活。在年节行事的不断调整中,逐渐出现了一些新节日,例如,圣诞节、情人节、母亲节等。此外,个人生日、结婚纪念日、家庭旅行计划也逐渐受到重视。但有研究显示,有些新节日往往只是为孩子们才特意举办活动的,不少家庭随着孩子的长大成人,也就不再举办了。①牧野真一:《祭りと年中行事》,谷口貢•松崎憲三編:《民俗学講義-生活文化へのアプローチ》,八千代出版,2006年,第203—222页有些传统上曾经是地域社会或家族集体性的节日,如今却日益个人化。②荻野裕子:《コンビニで知る年中行事》,市川秀之他編著:《はじめて学ぶ民俗学》,ミネルヴァ書房,2019年,第256-265页。在日本,由于年节行事的商业化,现在的人们往往是通过全国连锁的便利店而感受一年之中那些节日的,例如,中元节和年末,便利店就会有包装好的礼品供人选购;情人节到来之前,有大量的巧克力被堆上货架等。
传统的人生通过仪礼,例如,涉及“生”与“死”的民俗也发生了巨变。以前生孩子,有“产秽”意识,所以,在村落旁边另行搭建小“产屋”,让产妇在那里隔离一段时间,围绕着孕产和生命的诞生,形成了很多传统的仪式和礼俗。③板橋春夫:《出産とジェンダー―男性産婆の伝承》,八木透編著:《新•民俗学を学ぶー現代を知るために》,昭和堂,2013,第119—139页。从临时搭建“产屋”,到常设“产屋”,再到产妇逗留其中时间的缩短,“产屋”在有的地方还成为产妇的短期疗养场所,但其终结和医院出产的普及基本上同步。④板橋春夫:《産屋習俗の終焉過程に関する民俗学的研究》,《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第205集,2017年3月,第81—156页。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起,孕妇在医院分娩逐渐成为常态,各地的“产屋”习俗也基本是在这一时期消亡。医院把产妇和新生儿视为自然的身体生命来对待,不再允许有产神和灵魂之类介入的空间。⑤猿渡土貴:《婚姻と出産•子育ての民俗》,谷口貢•松崎憲三編:《民俗学講義-生活文化へのアプローチ》,八千代出版,2006年,第123—143页。于是,诸如“胞衣”之类的礼俗自然走向衰落,在医院生孩子,人们慢慢地不再关心它,形成了任由他人处置的态度。曾视“胞衣”为婴儿分身的观念,由于人们身体观、胎儿观、出生观等的变化而不再流行,对于战后出生的人们而言,它几乎成为“死语”⑥猿渡土貴:《現代の出産とエナ観を捉える試みとしてー東京都目黒区在住の女性たちを対象としたアンケートの結果よりー》,《日本民俗学》第232号,2002年11月,第19—34页。。以前民俗学有关产育民俗的研究,主要围绕诞育的系列仪式及民俗事象展开,同时关注孕妇—产妇—母亲的身份转变。但在现代社会,产育环境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由于大家族和村落制度解体,核心家庭的产育仪式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例如,丈夫积极参与诸如安产祈愿、产前检查、带新生儿去神社参拜等仪式活动。过去,新生儿作为地域社会或大家族的一员备受重视,如今,这些因素淡化了,不再需要共同体的认可与接纳,于是,各种仪式主要就成了为新生儿的健康成长祈愿,归根到底只是核心家庭内部的祝贺活动。⑦佐々木美智子:《生む性の現在―現代社会と民俗学》,《日本民俗学》第265号,2011年2月,第92—103页。
传统葬礼以前是以村落或大家族为单位举办,但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及以后,出现了殡葬礼仪的产业化⑧山田慎也;「変容する死の文化と民俗学研究》,《日本民俗学》第300号,2019年11月,第66—82页。,亦即逐渐改由专业的殡仪公司和殡仪馆安排在专门的葬仪场举行。于是,有关葬礼的风俗,实际就出现了部分地由行业公司来设计的现象。⑨[日]山田慎也:《丧葬礼仪与民俗主义》,周星译,周星、王霄冰主编:《现代民俗学的视野与方向》(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89—299页。从亲族近邻互助操办丧事,到委托专业公司来安排,这当然也伴随着相关仪式空间的变化,告别仪式从在家举行转移到专用设施,自然有所简化。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临终死亡的场所由家内为主转变为医院为主,因此,专用的葬仪场就成为既非临终场所、亦非火葬场的中间性空间。虽然有些地方曾利用寺院的专用空间或经堂作为葬仪场,但大的趋势是城市不断增加葬祭设施,寺院的存在意义趋于模糊。在一个时期内,人们还把死者遗体带回家安排葬仪,等入殓之后,再举行守夜和告别式,但到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地域社会和家族结构的变化使得以前那样的丧葬仪式难以为继,逐渐出现了小规模化和短缩化的趋向。由于前来参加葬礼或吊唁的人数越来越少,直接把遗体从医院搬送到葬仪场的情形也就逐渐普及。于是,守夜和告别式逐渐合流,甚至还出现了“一日葬仪”,亦即省略守夜等环节,当天就完成葬礼的情形。再进一步,便是只有近亲家人参与的葬礼,或不举行仪式而直接火化的“直葬”。“直葬”这种形式,以往主要是穷人或死因不想让人知道的情形下(例如自杀)举办的,现在也逐渐一般化了,据说在东京可以占到20—30%左右。目前在日本,新的丧葬方式仍在持续摸索当中,不久前还出现了老人们生前就为自己安排好后事的“终活”(临终活动)。总之,丧葬礼俗日趋多样化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常识,全社会如何理解葬仪、如何接受死亡以及如何才是合适的葬仪等,越来越难以达成基本的共识了。①山田慎也:《第二章 儀礼の変容―葬送空間の変化と通夜•告別式の儀礼化》,山田慎也、鈴木岩弓編:《変容する死の文化―現代東アジアの葬送と墓制―》,東京大学出版会,2014年,第31—54页。
20世纪60年代以来,很多地方自治体一直在推动冠婚丧祭的简朴化运动,且往往是从政府职员和学校教员的婚礼开始,简单而又隆重的集体婚礼和快乐的新婚旅行等受到奖励。但相关举措除了导致一些传统仪式细节消失之外,也有适得其反的情形,例如,选择豪华宾馆等设施举办豪华装束的婚宴,反倒推高了费用,与简朴化的目标背道而驰。葬礼的简朴化在有些地方也不是很顺利,火葬场和葬仪场的建设与普及促使传统葬礼的某些环节,例如,灵柩离家和送灵去墓地途中需要“换鞋”等民俗趋于消失,但很长时期内参加吊唁时的“香典”(份子钱)并未减少,有的地方甚至还年年增高。“香典”在日本属于社会人际“义理”,是家族世交、礼尚往来之连锁性人际关系中诸如“还礼”之类的环节之一;由于丧葬费用居高不下,“香典”往往也是丧主办事费用的重要补充。②小田嶋政子:《生活改善運動と婚姻•葬送儀礼の変化―北海道伊達市の事例からー》,《日本民俗学》第210号(特集:地域開発と民俗変化),1997年5月,第109—120页。有些丧主配合简朴化运动,用电话卡、茶叶或手帕等小礼物对吊唁者当场还礼,结果却使前来吊唁的客人感到尴尬,并使彼此互惠、互酬的人际关系原理发生了改变。正因为如此,丧葬礼俗的简朴化努力在不少地方遭遇到了顽强的抵触。
村落曾被很多民俗学家视为传统民俗的“传承母体”,但传统的村落生活发生了质变,很多新民俗的产生无法用“传承母体论”来解释。③福田アジオ、菅豊、塚原伸治:《「二〇世紀民俗学」を乗り越える》,岩田書院,2012年,第93—95页。资本主义经济原理渗透到农村,以往那些共同劳动或互助习俗逐渐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劳动作为商品被交换。农业劳动机械化、农活作业的合理化水平不断提高、多种经营的发展等,使得“兼业农户”的数量大幅度增加。自来水和上、下水系统的建设,逐渐替代了水井和传统的茅厕,也推动了洗衣机的入户普及,于是,曾经的妇女井边或河边聊天之类的情景便随之消失。当然,村民的价值观和生活意识也发生很多变化,在有些地方,神社的神职甚至找不到后继者,很多墓地也因外出者不再回来祭扫而渐趋荒废。在较为偏远的地方,由于年轻子女外出后不再回来,年迈的父母就倾向于把家族墓地移至住家附近,为的是盂兰盆节时回乡的子孙们比较容易去上坟,或使后人更容易记住。
汽车(包括各类农用汽车)的普及,当然还有道路系统的整备,使得偏僻乡村的生活便利性大幅度改善,它带来的变化之一就是村落“境界”(两个村落之间的交界处)的消失。遍地开花的住宅小区开发使得曾经的境界之地不再幽暗暧昧,全社会用电量剧增甚至使黑夜消失,这意味着昼夜的境界也趋于淡化。乡民身份职员化,促使其人际关系从村内延展到村外更广阔的世界。换言之,经济高速增长和生活革命促使均质性空间扩大和异质性空间消失,传统的境界意识日趋消解。也因此,妖怪和狐仙附体之类的故事不再有暧昧空间作为依托,取而代之的便是都市传说。①喜多村理子:《ムラにおける共通の身体感覚の喪失》,《日本民俗学》第210号(特集:地域開発と民俗変化)1997年5月,第71—86页。偏远山村因交通改善被纳入全国的公共交通网络,人们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日趋活跃,年轻人越来越容易离乡外出就学或打工。外部商品对山村的农林产品形成挤压,村落的传承越来越难以为继,不少传承成为文化遗产后变成了表演,似乎去外地演出比起在本村内举办更加重要了。②永松敦:《宮崎県椎葉村の民俗変化―外的要因と内的要因―》,《日本民俗学》第210号(特集:地域開発と民俗変化)1997年5月,第15—25页。
关于生活改善运动
田中宣一曾坦率承认,未曾料到战后日本政府发起的各种计划以及各地响应这些计划而积极推行的生活改善事业和新生活运动成为民俗变迁的要因。他指出,以前的民俗学对国家的政治动向和政策不太关心,往往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而致力于调查各地的生产生活方式,记录各地的祭典、庙会和节日,追溯婚姻变迁和关注民间信仰等。但经由对“山村调查”的追踪调查,非常清晰地了解到地方各种传承在政策影响下不断变化的事实③田中宣一:《有关传承和陋习的认识》,宗晓莲译,《日常と文化》第5号,2018年3月,第81—87页。,于是才开始高度重视起政策和民俗的关系。田中宣一多年关注生活改善运动和民俗变迁之间的关系④田中宣一:《生活改善諸運動と民俗の変化》,成城大学民俗学研究所編:《昭和期山村の民俗変化》、名著出版,1990年。田中宣一:《生活改善諸運動と民俗―《官》の論理と《民》の論理》,《民俗学論叢》19,2004年5月,第1—18页。,他对生活改善运动的定义是: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透过政府及有关机关的政策举措,有意识地推进国民生活的改善;由地方自治体、地域社会的各家各户以及诸多团体密切互动,以改善国民自身生活为指向的创意和努力;与官方企划相呼应,基于民间民众的意愿、努力和实施而指向于生活近代化、合理化的各种活动的总称。⑤田中宣一編著:《暮らしの革命—戦後農村の生活改善事業と新生活運動》,農文協,2011年,第11页。例如,通过各种路径启发和推动居民发现自身生活有哪些地方不合理、不健康,并予以改善等,由此,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改灶、改善厨房、改善卫生、改善饮食生活等各种实践。
日本政府通过国家政策或各种运动对国民日常生活加以干预,这从战前到战后其实是有一定的连续性的⑥佐野賢治、谷口貢、中込睦子、古家信平編:《現代民俗学入門》,吉川弘文館,1996年,第265—276页。,但和战前的目标是“富国强兵”不同,真正的生活改善还是在战后。在战争废墟上重建日常生活,战后的生活改善运动旨在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其中包括促使传统民俗趋于合理化和简素化的指向。这里所说的“生活改善运动/新生活运动”,主要是指二战以后日本的农村改良事业及运动。1955年鸠山一郎首相曾提倡“新生活运动”,而所谓“生活改善运动”通常包括由总理府下属的新生活运动协会主导的“新生活运动”和盟军占领当局(GHQ)进行农村改革、为实现农村民主化而于1948年启动的农林省系统的“生活改善普及事业”等。①在此暂不讨论战时和战前的一些项目,诸如内务省的“民力涵养运动”、农商务省的“农山渔村经济更生运动”以及1941年制定的《国民礼法》等。岩本通弥指出,以生活改善为名目的运动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日中韩几乎同时出现,但战后则走向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民俗学应该关注这些运动的“同时代性与异质性”。参见岩本通弥:《生活,日常,世相—为了变化的把握》,王京译,《日常と文化》第5号,2018年3月,第73—80页。虽然运动往往存在不同的系统,但落实在生活改善的现场,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区别。所有这些运动的目的,就是从衣食住行到社交礼仪等生活各方面的改善与合理化,以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指令性为特点,例如,农林省向基层派遣农业改良普及员或生活改良普及员,但要真正获得成效,则必须有当地居民的响应与参加。
岩本通弥曾把近年来日本民俗学有关“生活改善运动/新生活运动”的研究,溯源至田中宣一编的《生活的革命——战后农村的生活改善事业与新生活运动》②田中宣一編著:《暮らしの革命—戦後農村の生活改善事業と新生活運動》,農文協,2011年。和大门正克编的《新生活运动与日本的战后——从战败到20世纪70年代》③大門正克編著:《新生活運動と日本の戦後―敗戦から1970年代》,日本経済評論社,2012年。这两本书。前者是民俗学家和相关研究者从2004至2009年合计20次共同研究会的成果,其以上述生活改善普及事业和新生活运动为中心,尤其关注保健所和公民馆的活动,不仅致力于追问官方推动运动的逻辑、内容和方法,同时也致力于揭示民间亦即成为运动之对象的地域或团体是如何接受并予以反应的。由于民间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活形态或传承自有其逻辑,故其反应自然也包括无视或反驳、抵触等。田中宣一认为,除了包括厨房和洗澡间等在内的居住空间的改善,有关营养和卫生思想的扎根,结婚和产育形式的变迁,以及人们有关生活的意识变革和家庭中女性地位的提高等,都非常重要。其结果便是指向现代生活,故应称为“生活革命”。民俗学对于这些运动的研究,同时也就是对现代生活的思考。④田中宣一:《はじめに》,田中宣一編著:《暮らしの革命—戦後農村の生活改善事業と新生活運動》,農文協,2011年,第1—2页。
田中宣一指出,虽然对怎样才算改“善”有不同观点,但运动总是官民互动、一起参加推动的。⑤田中宣一:《有关传承和陋习的认识》,宗晓莲译,《日常と文化》第5号,2018年3月,第81—87页。例如,农林省1948年新设生活改善课,其内又下设衣食住和家庭管理、保健育儿等科室。农林省推动的“生活改善普及事业”把农、林、渔从业者衣食住的改善、家庭收入、家内女性地位、家人健康(特别是婴幼儿健康)等均纳入规划;通过考试招募、培训生活改善普及员并派遣到地方。生活改善普及员大多是女性(全国约2000名),她们到各地召开讲习会,说明改善生活的必要性;推动由当地女性(年轻主妇为主)组成生活改善小组,寻找需要改善的问题,再通过协商解决,主张由村民以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民俗学家注意到,旨在追求更好生活的生活改善运动在村落层面的实践,主要是以女性为主力、主角和主要的受惠者;各地都把动员妇女作为工作的重点。在不少村落,妇女也因此获得了以前不曾有过的地位。生活改善普及员引导妇女所做的工作,包括提高制作衣服的技巧(劳作服和内衣的制作、衣服的防水加工)、改善饮食(面包和副食制作、季节性料理、零食和点心制作、食物保存、学习营养知识)、改善居住条件(厨房和灶炉改良、改善供水和洗澡间)、讲求卫生(驱除蚊蝇和寄生虫、重视农忙期保健等)、重视家庭管理和经营(家计簿记录、每月的生活安排、孩子分担家务、家人间的协作)等。显然,有些举措可能会与传统民俗发生冲突,例如,有人说改灶会让灶神不高兴,家人怀孕的话还会使新生儿兔唇,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促使居民改变其自身的价值观。在这些过程中,妇女会之类的组织发挥了作用,但变化最大的则是参与生活改善运动的妇女们的自我认知,亦即她们从各家农户的媳妇由此变成具有掌控自身生活之能力的女性。①安井真奈美:《生活改善》,市川秀之他編著:《はじめて学ぶ民俗学》,ミネルヴァ書房,2019年,第242—250页。
相对而言,新生活运动则主要是在都市及各单位内推进,以全体国民为对象,重点在于改善精神生活层面。1955年政府设立了新生活运动协会,旨在促进国民形成合理、民主的生活习惯。例如,要求国民以勤劳为贵、不要浪费铺张、奖励储蓄、废弃封建的人际关系及习俗、提升公众道德水平,推奖良风善行、努力改善衣食住等日常生活。具体的方法是由地方组织和民间团体等提出需改进的问题,新生活运动协会派遣讲师指导,并向地方提供已采取行动的其他地方及团体的信息,或对实施行动的团体予以财政援助。各地具体实施的活动非常丰富,例如,推进健康合理的娱乐、红白喜事简朴化、排除浪费、储蓄和家计合理化、严守时间等,进而还有对一些仪式和习惯的改善,打破迷信陋习,注重保健卫生,计划生育;改善衣食住的环境,消灭蚊子和苍蝇等。此外,厚生厅管辖的保健所以保健卫生为中心进行的活动,主要有结核病对策、传染病预防、母子保健、改善营养和食品卫生等。文部省管辖下的社会教育设施公民馆也积极推行公民教育,开展地方文化教育活动,内容多为民主主义的启蒙和普及,以及在公民馆举办婚礼或涉及保育、托儿等有关生活福祉的活动。②田中宣一:《はじめに》,田中宣一編著:《暮らしの革命—戦後農村の生活改善事業と新生活運動》,農文協,2011年,第11—27页。
在上述运动中,显然是有国家对民间传承的直接而又强力的干预,试图让它朝向“善”的方向改进。所谓“善”,主要包括卫生健康的生活环境、物质生活的安定、互助合作精神、合理性思考等。诸如祭祀庙会和节日庆典等仪式中的浪费及仪式性的偷窃,对寺庙神社的过度祈愿,各种消灾仪式,婴儿出生后的各种仪礼,婚丧仪式中的各种馈赠习俗,似乎都有改“善”的余地,但将它们一律视为陋习,进行强制性改造,民众可能抵触,也会觉得生活枯燥无味。前已述及的红白喜事简朴化,曾被视为是新生活运动的目标之一③山口睦:《冠婚葬祭の簡素化は可能かー山形県南陽市の贈答記録を中心に》,田中宣一編著:《暮らしの革命—戦後農村の生活改善事業と新生活運動》,農文協,2011年,第352—372页。,但除了场所和仪式程序的一些改变之外,涉及馈赠和还礼以及精神领域的葬礼和祭祀等部分并不是很顺利。这类目标在村落的传统规矩、商业化和炫耀性消费及非日常消费等要素面前,往往显得很无力。民俗学家认为,导致这类情形的理由主要是冠婚葬祭本身对于人生的意义,较难被简朴化;再就是伴随着互酬原理的馈赠具有连锁性,对于乡民的生活世界而言非常重要。田中宣一认为,外来人视为浪费或不合理的,对当地人而言却可能是让生活充满活力必不可少的,也因此才代代相传的。民俗学家应该如何理解这类情况?当事人为了美好生活,愿意接受什么、拒绝什么或改变什么,民俗学家应通过对他们如何参与这些活动的观察,努力准确地理解人们所追求的美好生活的方向。④田中宣一:《有关传承和陋习的认识》,宗晓莲译,《日常と文化》第5号,2018年3月,第81—87页。
至于大门正克编著的《新生活运动与日本的战后——从战败到20世纪70年代》,主要是从历史学的立场展开研究。和田中宣一等人基于民俗学立场的相关研究聚焦于接受或抵触、反抗政策的人们的实践及与之伴随的记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历史学立场的研究主要是分析有关政策的记录,重视对其政治性意图的揭示。⑤大門正克編著:《新生活運動と日本の戦後―敗戦から1970年代》,日本経済評論社,2012年,第19—20页。显然,将上述两者结合起来是很有必要的。
岩本通弥对“生活改善运动”“民俗学”和“日常”的关系做了进一步审视,他追随柳田国男和今和次郎的足迹,试图重新探讨日常生活的近代性是如何在日本展开的。在岩本通弥看来,日本民俗学的诞生其实与生活改善运动属于表里一体的关系,较早时的民俗学曾把生活(民俗)视为是应该改善和变革的对象,而不是应该受到保护和保存的对象;但到20世纪70年代,亦即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后,在日常生活持续快速变化的趋势中,日本社会和日本民俗学产生了美化过去和美化民俗的视点。面对不断快速变化的生活,民俗学以恒久的日常亦即通过对“民俗”的界说,改良主义式地应对过度的社会变革。岩本通弥认为,民俗学必须追问现代及迄今为止的日常生活的演变过程,近代以来,日本都市社会出现了新的日常,工薪阶层亦即上班族激增;同时世界各地也都出现了相似的近代生活方式;电影院、演讲会、展览会等新的公共空间领域的诞生,催生了对公共空间行为举止的要求和规范;资本主义迅猛发展使此前很多习惯和经验知识再无用武之地。①岩本通弥:《日本的生活改善运动和民俗学—Modernization和研究》,謝舒恬译,《日常と文化》第7号,2019年10月,第119—133页。在多种要素复杂交织互动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承认各种纠结于国民身边琐碎生活小事的“运动”,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是一种“搅乱”,也总是能够产生程度不等的影响,有时甚至是革命性的影响。②岩本通弥:《生活,日常,世相——为了变化的把握》,王京译,《日常と文化》第5号,2018年3月,第73—80页。
小岛孝夫和成城大学的研究团队以田中、大门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致力于把新生活运动协会的活动记录和东京都多摩地区的生活改善运动的开展情况数据库化。从2014年起,他们以政府部门发行的宣传杂志等记事为资料,在使之数据库化的同时,召开研讨会验证生活改善运动在全国的开展与差异性;与此同时,坚持民俗学的立场,亦即以个人的日常生活事象作为基础资料,对生活改善运动相关人员进行了必要的访谈。小岛孝夫认为,生活改善运动作为战后民主化的一环而展开,虽然政策在全国是一致的,但对于在地域社会经营日常生活的人们而言,秉持传承而来的意识和价值观,平均化的生活改善政策未必能被理所当然地接受,其不少部分是经过一段时期的抵触或对抗,才逐渐接受的。各种生活改善运动同时也是居民们自觉摸索改善自身生活的活动,一定意义上,正是它们构成了当今日常生活的根基。③小岛孝夫:《东京都多摩地区生活改善运动的诸相——以立川市砂川为例》,孙敏译,《日常と文化》第5号,2018年3月,第89—92页。小岛孝夫还特别指出1947年日本实施新民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它改变了明治以来的家族法,确立了家庭的民主化和男女平等原则,以前的婚姻是女性嫁入夫家,如今则是自由的男女通过婚姻组成新家庭,于是,以前有关家族永续的理念就慢慢地发生了改变。小岛孝夫认为,这也与年轻人作为自由的个人接受生活改善运动有着密切的关联。
山中健太对爱媛县南予地区两个基层社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无蚊蝇生活”的各种活动进行了深入的个案研究。④山中健太:《战后南予“无蚊蝇生活”活动的开展——从喜多郡旧五十崎町到宇和岛市石应》,孙敏译,《日常と文化》第5号,2018年3月,第105—112页。“无蚊蝇生活”是环境卫生改善活动的一环,旨在杜绝传染病的媒介鼠类蚊蝇之类,但作为国民运动,它并未局限于公共卫生范畴,还与改善生活紧密相关,并涉及教育方面的因素。社区层面的活动内容包括改建厕所和水渠,配备垃圾焚化炉并改善堆肥和畜舍等;厕所改造的重点是彻底密闭便池,下水道则提倡V字型沟渠,以便节水并容易清扫;再进一步还有改善厨房、设置简易自来水管道等。所需材料、费用和劳工,则由地方政府和居民按不同比例分摊。山中健太提供的这两个社区案例形成了鲜明对照,一个是自上而下由町政府强力推动,虽然整齐划一并有效率,但较难持续;另一个则是自下而上由居民主导,虽然不那么立竿见影,但却能够从改善下水道的活动逐渐朝改善生活其他各方面不断扩展,进而还陆续解决道路、边界、防止青少年不良行为等其他问题。换言之,生活改善由谁主导,如何定位,以何种方式推进,均会影响到其后续的展开。
田村和彦认为,从行政角度试图改善生活时,由于将具体对象问题化,并必须确认改善的措施和成果,通常就会使生活碎片化,而不再顾及生活本身或生活的整体。由于此前没能将“生活”提炼为民俗学的重要概念,因此,民俗学家对眼前实际展开并极大改变着人们生活的各种运动熟视无睹,从而也就丧失了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并去探讨生活整体的可能性。①田村和彦:《我们以“生活”一词想说明什么,能说明什么》,宗晓莲译,《日常と文化》第5号,2018年3月,第123—130页。他指出,由行政主导的运动,一旦确定的项目得到改善,运动就会终止;若由当地居民发起,以改善自身生活为目的、具有主体性的生活改善行动往往会一直持续,没有完结之时。对此,民俗学家需要直面自己的田野调查经验,思考生活改善运动改变了什么,如何将人们卷入其中,以及对今天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等问题。
即便在彻底实现都市化、现代化和生活富足之后,日本社会有关不断提高生活质量、追求更美好生活的运动并没有停止,只不过逐渐从重视物质朝向重视精神和情感层面的方向演进。例如,1974年发祥于福岛县三岛町的“故乡运动”,主要就是一些地方自治体以大都市居民为对象,征集特别市民,一方面收取会费,另一方面则向应募者提供某种特惠,亦即帮助市民和“乡土”(地域社会)建立关系,使他们可以定期访问“乡土”之家,满足其“望乡”的期待。②[日]真野俊和:《“乡土”与民俗学》,西村真志叶译,王晓葵、何彬编:《现代日本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第214—238页。这类运动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对于因代际交替而失去“故乡”的市民们而言,乡愁成为其幸福生活中的稀缺或缺憾之物,因此,这便成为一种需求。的确,以高速经济增长和生活革命为背景,传统文化的流失及未来命运成为日本知识精英的焦虑,民俗学在推高和应对此类焦虑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对曾经有过的“美好”生活(民俗)的乡愁,使得“乡土”被理想化,换言之,民俗学家有意无意地参与或助长了上述那样的乡土运动,直至近年才有部分民俗学家对此有所反思,并试图把它作为研究的对象。此外,还有1975年发祥于爱知县丰桥市的“零垃圾运动”③周星:《日本的垃圾分类与再生利用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研究报告),2008年电子版(未发表)。,2002年静冈县挂川市发布“慢生活城市宣言”④横山廣子:《スローライフが展開する日本》,《月刊みんぱく》,2005年10月号。等等,民俗学几乎都没有对它们展开过像样的调查研究。
讨论:不断刷新的“理所当然”与民俗变迁的方向
岩本通弥曾引用德国民俗学家海尔加•根特(Helga Gerndt)的民俗学定义:“民俗学是研究较广范围居民集团日常生活的学问。其视线投向过去及现在的文化表现。民俗学追问的是大多数人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为何会成为理所当然。即与我们共有生活空间,体验空间的人们,是如何在过去以及现在塑造自我这一存在的。”以此为依据,他认为,民俗学应该关注日常生活成为理所当然,也就是被许多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成为理所当然(“日常化”)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的各种变化。⑤岩本通弥:《生活,日常,世相—为了变化的把握》,王京译,《日常と文化》第5号,2018年3月,第73—80页。在指出现代生活不断平准化,亦即全球化促使各国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日益趋同的同时,岩本通弥对“日常化”这一概念进行了解说,指出日常化就是“成为理所当然”的过程,其中包括各种各样的文化转移、越境以及从外部吸取的新文化要素在“生活世界”里也成为“理所当然”的意涵。正如鲍辛格所说的“科学技术世界”,指的是科学技术原理渗透其中的生活用品一般化的“生活世界”,汽车、电话、电视、电脑、智能手机等均成为近在身边、理所当然的生活环境的一部分,从对这些新事物感到异质性或有所抵触,到它们不知不觉间成为不言自明的存在,甚或进一步开始“理所当然”地规范人们的生活。民俗学对于“日常化”的实践过程,对于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应该质疑,通过将生活世界客体化,使之成为可能凝视的对象。①岩本通弥:《“理所当然”与“生活疑问”与“日常”》,宗晓莲译,《日常と文化》第1号,2015年3月,第113—124页。
世事人事的变迁,包括人们处在其中的生活方式与民俗文化的变迁,应该是所有民俗学家均能够意识到的。经由梳理日本民俗学对世事变迁和生活革命以及生活改善运动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的是,由于民众对更理想生活的发自内在的追求,也由于各种外来的干预、推动或渗透,日常生活的常识总是不断地被刷新,亦即总是从一种理所当然的状态进入到另一种新的理所当然的状态。只有新的理所当然得以形成,人们才能感受到日常生活的安定感。但斗转星移,物是人非,生活者个人的生命历程同样也会逐渐刷新眼下似乎是安定且日复一日的日常,为了使生活得以过渡到全新的理所当然的状态,社会就需要有人生过渡仪式的“发明”,通过这些仪式,人们获得或加持新的日常状态。日常生活世界既有滴水穿石或潜移默化的微调,也有剧烈的地壳变动,于是,那些总是得到特别关注的“民俗”,就成为民俗学家观察变迁及其方向的线索或指标。标榜朝向当下的现代民俗学,需要把研究的重心置于深入和细微地观察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是如何不断地刷新着常识和生成着意义,也因此,现代民俗学应该就是关注我们同时代人民的民俗学。
外部力量尤其是行政权力对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的干涉,当然会程度不等地破坏当下的理所当然,从而“搅乱”生活、颠覆常识。如果类似的运动过于频繁或过于不可抗拒,亦即若运动成为常态,则“非日常”状态就会替代“日常”状态,从而使日常生活本身遭受严重的冲击或持续的破坏,从而无法产生新的生活安定感。从这个意义上讲,并不是所有的运动都必定能够推动生活的改“善”。太过偏离当下常识的运动,即便在权力推动下获得一时成效,或多或少也会遭遇民众各种形式的拒绝、抵触或变通。中国在“文革”结束之后,民众的日常生活从过度意识形态化的状态逐渐回归,即便是有无数痕迹留在了此后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但新的理所当然和新时代的常识还是得以确立(部分地属于恢复)。②周星:《“文革”期の民俗文化現象》,田宮昌子译,《中国21》第6号,風媒社,1996年,第207—219页。显然,民俗学家不仅需要对民众的日常生活及其理所当然进行观察,还需要关注激烈动荡时期社会意识结构的复杂变化,也需要对变革趋势中所谓人之“常情”“常理”予以追问。
民俗学的初心原点是要理解民众,并从民众的立场出发去认识人们在其日常生活中是如何主体性地创造民俗及文化,以及人们所追求的幸福美好生活的方向性。换言之,民俗学有助于提高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品质,因为它尊重普通人在建构、创造和提升自身日常生活中具有主体性的实践。日复一日的努力,日常实践的累积成就了普通人的日子;无数普通人的日子都有机会朝向美好生活的方向发展,才是较好的社会。无数普通民众依托于他们来自传承的过去经验、知识和智慧,在当下致力于个性化的生活实践,指向于未来可以期许的安稳而又美好的生活。政府致力于改善民生和干预民众日常生活的努力,只有符合这个方向才是好的政治。从东亚各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与生活革命的实际经验中,我们不难发现,确实是无数普通民众孜孜以求的生活实践支撑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及其不断涌动的变革。当现代民俗学把“生活”作为关键词并把它置于比“民俗”更为重要的地位时,它就需要持续地深思和追问“如何才能把转瞬即逝、流动不居的日常生活客体化”这一重要的方法论课题。
日本民俗学通过对日本近代以来的民俗文化变迁、战后由各方权力主导的生活改善运动,以及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生活革命等的深入研究,基本上揭示了日本式现代生活方式的基本形貌。那么,中国民俗学是否也需要有类似的研究,中国式的现代生活方式又是怎样形成的?近年来,笔者倡导对中国已经和正在发生的生活革命展开民俗学的研究,倾向于使用“生活革命”这一概念,用来概括中国普通民众的现代日常生活方式的整体性诞生及其提升的方向性。经由“生活革命”这一视点,我们可以把当下的中国社会理解为不同于“乡土中国”的现代中国,而不是或不再是那个“乡土”的乡村社会或与现代都市社会处于二元对立状态的中国。这意味着,当下的中国社会在总体上,无论城乡都是“都市型”现代生活方式已经确立和正在普及的现代社会。中国也犹如鲍辛格所揭示过的,早已是现代科学技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地渗透着的现代社会。只是在这样的社会里,仍需要时不时地有乡土性或本土性的“民俗”被再生产出来,以满足乡愁、认同、文化资源和观光等多种现代社会的需求。
中国有不少擅长于微观研究个别民俗事象的民俗学家,但他们对自己身边蔓延的生活革命却没有感觉,不觉得它和自己从事的民俗学有多么密切的关系。除了民俗学家经常可能秉持的“民俗观”较为重视民俗事象的稳定性、传承性或连续性之外,他们对日常生活中那些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变化熟视无睹,这恰好说明了民俗学的日常生活转向并非易事。民俗学家的视野、趋好和理念都会影响到他们的判断,例如,对于旧时过往的乡愁或审美,有可能妨碍民俗学家直面当下的生活课题;对于奇风异俗的过度关注,也很容易使民俗学家意识不到日常生活世界中不动声色、潜移默化的微变。重要的是,民俗学家截至目前所开发的概念工具,似乎也较难对世事变迁及生活革命给予很好的概括与解释。但无论如何,中国民俗学家也生活其中的当下中国现代社会,其日常已是现代的日常而非乡土的日常,更不是很多民俗学家热衷于采用“传统”或“民俗”等概念所描述的那个过往旧时的日常。中国已经和正在发生的生活革命,和日本当年的情形有一定相似性,因此,日本民俗学对生活革命的研究成果可以给中国民俗学带来一些参考。在中国,不仅政府对民生承担的责任更大,其对民众的日常生活干预的频度和力度也更多、更强;中国的生活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是一个连续性的不间断的过程;和日本社会的“一亿人口皆中产”及生活方式的平准化相比较,中国生活革命的过程尚存在贫富差距①丁紅衛:《高度経済成長期における格差問題と平等意識―日中比較》,石川巧、瀧田浩、藤井淑禎、渡辺正彦編:《高度成長期クロニクル:日本と中国の文化の変容》,玉川大学出版部,2007年,第47—71页。、社会保障迟滞、公共服务不均等,以及厕所革命与垃圾分类等非常重要却又难以迅速解决的诸多问题。虽然中产阶层在中国也出现了大面积崛起的局面,但“富了以后怎么办?”等问题,也还是与日常生活的价值观深切关联。所有这些都是需要中国民俗学家努力去关注、理解和研究的。中国民俗学如何走出只对生活中特定事象(民俗)感兴趣的局限性,从而把百姓生活的整体纳入视野,把当下的现代日常生活视为对象,可以说是当下颇为紧迫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