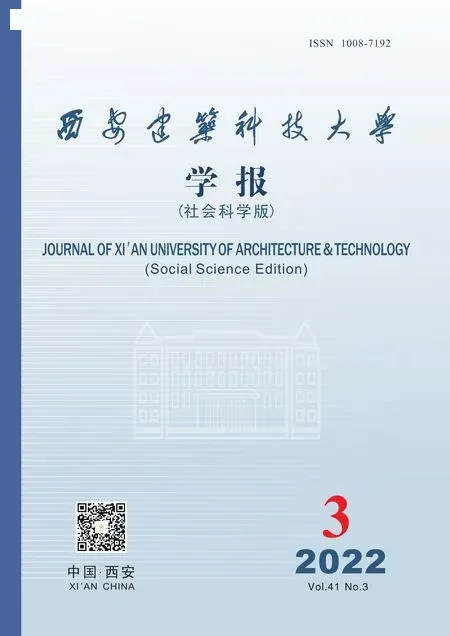释体校用:论《文心雕龙校释》校字的独特样貌
沈 旭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48)
前贤所以将《文心雕龙校释》尊为“20世纪龙学的四大基石”之一,多出于其义理阐释的影响。至于刘永济的校字,如詹锳评曰:“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因所据版本较少,校勘方面无多创获。”[1]序例4刘氏校字所用《文心雕龙》版本有唐写本、嘉靖庚子汪一元本、天启壬戌梅子庚本及合刻五家言本,并参以商务印书馆影印宋本、清代鲍崇城校刻本《太平御览》以及“明清两代各家校字”。虽然诸本皆属精品,但若与王利器、杨明照等人之作相较而论,则詹氏所言版本依据问题,确是《校释》校字的短板所在。刘氏也直言,其校未能“遍举各家所校文字之异同”,为“本书一缺点”[2]4。
詹氏所论,当就中华书局版《校释》而言。而从1937年《文心雕龙校字记》的发表起,刘永济对《文心雕龙》的字句校勘经历了多次自我修订。前后有1938年国立武汉大学出版社本《校释》,1948年正中书局版《校释》,最后才是1962年的中华书局版《校释》。各本中的校字内容不尽相同,且有愈来愈精之势。那么,久经打磨、反复修改的刘氏之校,为何未能得到后人首肯呢?虽然我们同意“《校释》之主要成就在释义”的共识,但认为学界对刘校的辨析或有遗漏之处,故不揣简陋,期望能抛砖引玉。
一、校字内容:影响的受与施
相关龙学史著述在提及《校释》(下文未注版本者,皆就中华书局版而言)时,常将其与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合观比论,以见二者在义理阐释上的联系。然若从校字着眼,则向前可见其与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同受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的影响,向后亦可知其对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等著作产生影响。
1937年,刘氏的《校字记》发表在《学筌》第1卷第1期上。翌年,“讲义《文心雕龙校释》由国立武汉大学出版部印行”[3]332。虽然国立武汉大学出版部本《校释》今已难见,但二者出现的时间如此接近;且1938年刘氏因时局动荡常辗转迁移,已无大规模改动之精力;加之《校字记》的校字不仅数量可观,内容亦多被后来的正中书局版、中华书局版《校释》继承,故而我们认为《校字记》实乃《校释》校字部分的前身。
《校字记》开篇即言:“舍人此书,传世惟见明刻,其间文句,无大差异。海外有唐钞残卷子,其与通行诸本异者,已具范君文澜补注中。此外类书所征引,昔人所校注,补注亦多採及。永济校读之暇,复有所得,辄条录之。其间亦有辨正旧校之未审者,都八十余条,写为校字记如左。”[4]47-64根据刘氏对唐写本的描述,可知其最初是通过范注知晓唐本的具体样貌。虽然“永济校读之暇”中“校读”的具体对象并未清楚点明,但就上下文语境来看,范注必然在刘氏“校读”的范围之内,且得到了高度关注。而细品“复有所得”“其间亦有”之说,则《校字记》之重心正在范注校雠未确之处。这与杨明照撰写《校注》时,“必先检范注然后载笔”[5]1-2,显然有相通之处。可见,刘氏最初校字乃为补苴范注,因而亦当视为“20世纪范注订补群体”[6]234-238中的一员。
就《校字记》的具体条目来看,其受到范注①的影响虽不明显,但“响浃肌髓”。如《声律》篇“良由内听难为聪”条,刘氏曰:“纪评曰:‘由字下,王损仲本有”外听易为□“六字’。按:王本是。”这便沿袭了北平文化学社本范《注》误将“黄评”作“纪评”的讹误②。
范注对刘校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最初,且有一个持续的过程,以至于正中书局版《校释》出现了刻意删减范注的现象。如《定势》篇“文之体指实强弱”条,《校字记》云:“黄氏《札记》曰:‘细审彦和语,疑此句当作文之体指贵强,下衍弱字。’范文澜引《抱朴子》‘强弱各殊气’,谓当作‘文之体指,实殊强弱’。按:此段引刘公干语而驳正之,公干原文已轶,陆厥与沈约书,有刘祯奏书大明体势之语,疑脱一‘势’字,‘指实’或‘指异’之讹。”而正中书局版《校释》则校曰:“黄氏《札记》曰:‘细审彦和语,疑此句当作文之体指贵强,下衍弱字。’按此段引刘公干语而驳正之,公干原文已轶,陆厥与沈约书有刘祯奏书,大明体势之语。体下疑脱一‘势’字,‘指实’或‘指异’之讹。”[7]20对比之下,二者的主要区别正在于范注内容的有无。另需注意的是,刘氏之校是在既不同意黄说,也不同意范说的情况下,单单删去范说。《校字记》有7条皆被否定的范注,然至正中书局版《校释》均被删去,而《校字记》的其他诸家,除因观点更改而发生变动外,绝大多数未被正中书局版《校释》删减。由此,刘氏的针对性和选择性,可见一斑。此似可以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释之。布鲁姆将诗坛领域的“迟来者”分为强者诗人和弱者诗人,能力和意志弱者受制于前代巨擘的强大影响,止步不前并将其著作奉为圭臬;而强者则凭借英勇无畏的顽强拼搏,至死不休地追求对威名显赫的前贤之超越,进而形成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两极分化。确实,作诗与校雠分属辞章和考据两个不同维度,但二者在创作的本质上是相同的。校雠之事,虽因知识性更浓,而极大减少了布鲁姆所言“影响即误读”的可能,但“影响即误读”背后的逻辑理路仍然适用,即后来的强者在面临前贤巨大影响而产生焦虑的同时,会采取各种方式彰显、实现的他们的反叛,并最终消解的他们的焦虑。经历正中书局版《校释》这样一个反叛的过程,至彻底成熟的《校释》,范注又回到了刘氏的话语表述之中,且多被肯定。
至于王利器《校证》,我们先看王氏的求学经历。1912年王氏生于四川江津,1940年毕业于国立四川大学中文系。因战乱,国立武汉大学曾于1938年迁址四川乐山,次年8月,刘氏亦来到乐山,而国立四川大学也于1939年底南迁峨眉。从地缘上看,王氏完全有可能关注到刘氏研究《文心》的成果。另,从实证上看,《校证》有承续刘校之处。
如《文心·祝盟》篇“颂体而祝仪”句,《校证》曰:“‘仪’疑作‘义’。”[8]70这就有两大问题。一是不符合王氏的学缘结构。王利器在国立四川大学受教于向宗鲁,而向氏要求“生徒四年中必须于经史子集各治一专籍,一以清儒雠校之术为旨归,期于毕业之时有所小成,由此而奠定治学根基”[9]79。其后,王氏至北大师从傅斯年读研。被视为“中国的兰克学派”的傅氏,反对疏通,而“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认为“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所以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内使他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10]146。《校证》整体上与傅氏的理念一致,且其自述“如要直下己见,决不臆逞自恣”。而这条校语简短无据,岂不怪哉?二是不符合全书体例。王氏言“我们搞校勘工作的任务,不仅在求异同,而是要定是非”,最终给读者提供一个简明可信的读本。《校证》所列《文心》正文,字句已经判断而被改动,故与校语结论一致。那既然校语认为“‘仪’疑作‘义’”,何以正文仍是“诔首而哀末,颂体而祝仪”呢?我们认为,本条当是迻录刘氏校语。早在《校字记》中,刘氏即言:“‘仪’疑作‘义’。”这一校语一直为各版本《校释》所继承。如此,便能说通这样一条充满推测性,且不符合王氏对定本看法的校语,为何会突兀地出现在此③。
再如《文心·总术》篇“若笔不言文”句,黄侃率先指出“不”当作“为”,并疏通文意,驳斥了纪昀“其言汗漫”之讥。其后影响甚大的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注释曰:“不:黄侃认为是‘为’字之误。王利器校作‘果’。此句是复述颜延之所论‘笔’是‘言’之文的意思。”[11]301这便为我们指出“为”与“果”两种见解,并使后来者以为“果”为王氏所校。实则不然。《校字记》云:“黄氏札记曰:‘不’为‘为’字之误。按:黄说是也,而所改之为字犹未的。‘不’乃‘果’之坏字,承颜说而言果也。”其后《校释》亦同。而《校证》曰:“‘果’原作‘不’,黄侃云:‘”不“字为”为“字之误。’今案‘不’字乃‘果’字草书形近之误,此承颜说而为言也。故改为‘果’字。《序志》赞:‘文果载心。’句法相同。”王氏校语的论证逻辑、话语表述与刘校有高度的一致性,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是在后者的基础上,所作的进一步扩充。
而对其他诸家的影响,又如《文心·史传》篇“人始区详而易览”句,《校释》云:“按‘区’下有脱字,天启本补‘别’字,疑当是‘分’字。”而“分”与“别”,“区分”与“区别”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和共通性。刘氏能做出如此精细的微调,实属不易。盖“分”就整体的状态而言,而“别”则偏重部分间的关系,且常以某一部分为参考坐标。如“分离”仅为彼此相隔的事实陈述,而“别离”则有“彼远离于此”之意。《校释》之校,意即司马迁《史记》的列传体例,使我们对人物的氏族关系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该校后来在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产生回响,杨氏说:“按今本语意欠明,确有脱文。以论说篇‘八名区分’,序志篇‘则囿别区分’例之,‘区’下当补一‘分’字,并于‘分’下加豆。”[12]217-218然而,以杨氏对《文心》的熟悉程度,其不可能不知《文心·书记》篇有“草木区别,文书类聚”一句,亦可为梅本所补“别”字作证,但他依然选择“分”字,并强为之解,便可能是在刘校的启发下,进而受到审美体验的感召。另外,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于该句注释处,明确宣称其是以刘校之“区分”来译注[13]147,亦可见刘校之影响。
二、范式突破:校勘的新样貌
20世纪30~60年代,刘氏不断完善其校。通过校语,即可发现他所掌握的版本在不断增多。比如刘氏在写正中书局版《校释》时,已拥有了他自己的唐写本。正中书局版《校释》例言虽未明说他所据的是“国人录回之文字”,但在《乐府》篇“缪袭所致”条校语中,其言唐写本作“缪袭所製”[7]90,与范注提到的“孙云唐写本‘袭’作‘朱’”已然不同④。至中华书局版《校释》,刘氏又得到了孙人和校本。此从《诠赋》篇“言庸无隘”条、《章表》篇“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条及《通变》篇“风味气衰”条可见。另外,我们根据《刘永济手批〈文心雕龙〉》所整理的内容,亦可见刘氏校读、批注《文心》之勤。
然而,刘氏作为一代宗师,又一直关注《文心》的校雠事业,那为何我们随手翻阅《校释》,便可得到刘校在条目、字数、材料等方面皆不及范、杨、王诸家著作的直观印象呢?
关于校雠之事,刘氏曾在《文鉴篇》《校释·知音》中,反复提及“知识诠别”与“性灵领受”的区别,以表明他的态度。其言:
至知识诠别之事,约有四类:求工拙于只辞。……一字之来历,征引及于群书,一事之典宝,辨诘等于聚讼,虽多阐发之功,亦有穿凿之过者,笺注家也。……四家之外,今世习尚,又有为校勘之学者,则笺注家之附庸也。有为表谱之学者,则历史家之枝派也。凡此诸家,固读书者所当为,然仅能为此,即谓已尽鉴赏之能事,获古人之精英,则亦未然也。朱子谓:“读诗者,当涵咏自得”,即舍人“深入”“熟玩”之义,亦即余性灵领受之说,合而参之,鉴赏之事,不中不远矣[2]187-188。
专注摘句批评的诗话家、极力征引字句的笺注家、喜欢援史证诗的考证家以及推举穷源究委的历史家,都不被刘氏提倡。这四种“知识诠别”之事,也被其视作未得文学之三昧。而对“笺注家”“校勘之学者”的批判,实已潜在地表明其龙学研究,不愿意走以范注、杨校为代表的传统考据学的路子。刘氏信奉“性灵领受”的心灵体悟,宣扬个体应在“深入”“熟玩”的基础上,以“目击道存”的方式,整体、直观地把握对象的本质特征。因此,《校释》之校,并不以材料征引为中心,而主要是以校勘的方式解决自身在“涵咏自得”时发现的疑问,有自觉寻求“义理”的意味。
对此,我们不妨参看《刘永济手批<文心雕龙>》以了解刘氏校字的挑选过程。根据目前整理的成果,有相当数量的批注未被收进《校释》校字之中。如《风骨》《事类》《指暇》篇,刘氏在《刘舍人文心雕龙十卷》本上分别批注15处、23处及19处,在涵芬楼本《文心》上分别校改9处⑤、13处及8处,而在中华书局版《校释》校字中分校2条、3条及2条,即这三篇的校字数皆不到其批注总数的十分之一。而单《书记》一篇,《校释》校字就较其批注少了近40条。如此大规模地的精简,正因刘氏“仅就极其重要的字词或他人误校者加以勘正,凡有校勘且合原文文义者即省而不录,故校字者少”[14]21。可见,《校释》对校字对象的取舍,自有其标准和目的。而罗立乾认为,刘氏校字“特别着意于每篇中历来考校欠密而与真正理解和把握住《文心雕龙》之精义有重大而密切关系者”[15]542。这说明刘氏选择校字对象的主要标准和目的,正在于其要能为《文心》义理阐释的进一步发展有所贡献。
刘氏作为“后来的强者”,他选择的路就是在龙学研究中,取消“校”的本体性地位,而以其为“用”,沿着黄《札》的路子进一步发扬义理。现代龙学由黄侃开山,发展至范注,“征引虽博,但有时释事而忘义”[1]序例4。范氏以考据为主,进而知识性大于思辨性。刘氏则融文献考据于理论批评之中,“充分注意到了对文字的校勘与对理论研究的内在密切关系”[15]542,即其以释义为主,从而思辨性大于知识性。龙学大家中,以考据为主者,其注皆重材料、重证据,而以释义为主者,其校则重义理、重体悟。故刘氏之校,在理路上没有继承惠栋、焦循等乾嘉时期的主流学者,而是发展暗流之袁枚标榜性灵⑥的观念;在方法上并不尊奉清儒“无征不信”的考据方法,而是宣扬“求诸义而当改则改之,不必其有左证”[16]314的汉人之法;在态度上非是以清末大兴的科学为准绳,而更倾向以“道”为核心的哲学态度。
概言之,在刘氏心中,《校释》校字于知识性上的欠缺无伤大雅,其蕴含的思辨性已经组成通往形而上之理的阶梯。他所重视的,疏通《文心》各篇义理的目的已经借由校勘的方式得以实现。《校释》释义的不断完善,便是他校字时愈发自信的根本保障。
而关于“释体校用”的模式,有典例可见一斑,即《神思》篇“视布于麻,虽云未费。杼轴献功,焕然乃珍”句,《校释》校曰:“按‘费’疑当作‘贵’。”校语极其精简,不像《校证》和《增订校注》那样罗列版本异同。
问题的关键便在于《校释》前言曾交代,其所据版本有天启壬戌梅子庚本,而梅本恰恰已将“费”改作“贵”。既有此先例,本就未掌握许多版本的刘氏却只字未提,显然是对其未遑细审,且于版本方面不那么上心。
刘氏曾言:“即使别无依据,然从文义及作者思想全面推究,知其必系某字之误,校字者但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亦所当从。”[17]209其还说:“我最欣赏段玉裁说的‘夫校经者将以求其是也,审知经字有讹则改之,此汉人法也’。”[16]314据此可知,《校释》校勘此条,一方面是因为刘氏校勘的动机是出于“义理”的体悟而非“考据”的启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对“性灵领受”之法有高度的自信。我们参看《校释·神思》篇的释义,其言:“末段补论为文有待修改之功,及文事之妙,有非可言说者二意:首言修改而后工者,属之人力……修改之功,为文家所不免,亦文家之所难。”可见,刘氏认为“杼轴献功”当指修改之工。则“布”属人工之产物,而“麻”为天赋之自然。由“麻”到“布”是以人工补足天然的创作过程,定有所费心故不能说是“未费”⑦。改为“未贵”,则是于《校释》所强调的“自然之道”之大背景下,站在天才与人工对比而非世俗价值判断之角度得出的结论,与《诗品》“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语有相通之处。这也符合前文中“虽云”的转折意味,四句意即“虽然人工之布并不比天然之麻更加宝贵⑧,但经过精心组织,确实更有光彩而惹人喜爱”。显然,刘氏之校意在配合通篇理论阐释的需要,他是站在“理”而非“据”的立场进行校勘。
姚鼐曾言:“学问之事有三:义理、考证、文章是也。夫以考证断者,利以应敌,使护之者不能出一辞。然使学者有意会神得,觉犁然当乎人心者,反更在义理、文章之事也。”诸家校字皆为求“真”,然重“考据”者,其严谨、翔赡的论证正是为了形成逻辑自足的闭环,以应对文本中的“隐含读者”或是现实中的论敌。如刘氏之校字,若单独视之,则仿若自说自话。然因其“释体校用”的模式,释义既是校语的目的指向,亦是其说服力形成的基础。由此,我们亦可知刘、杨虽同受范注的影响,但刘氏反抗的态度为何要远比杨氏温和得多。除性格因素外,杨氏以考据为主,如火般从正面突破范注已有的成果与影响,故《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举正》《评开明本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等文多针锋相对,且多“故有是瞽说耳”“匪特未审文意,且惑同鲁哀公矣”等意气之语。而刘氏自开创“校释”合一的体例及转移著述重心后,便已如水般避其锋芒,从侧面跨越范注既有的成就和地位。
从龙学史的宏观角度而言,“《文心雕龙》研究成为一门学问,应起自元、明”[18]67。传统的龙学研究多侧重于文献学的范围,虽有评点、序跋以明义理,亦多零散而不成系统,其中黄叔琳的注本成为传统龙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然自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冲击,掀起了重估一切价值的学术思潮,实现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已是大势所趋。而学者们要整理和超越的第一个对象,便是以乾嘉学术为代表的“考据”。这毕竟凝聚了学术共同体于一整个时代的智慧和记忆,且因中国极度落后的国情,“考据”背后的严谨态度亦与时人宣扬的“赛先生”高度契合,故纵使是激进派的领袖人物胡适,亦以考证言“红学”。
20世纪“龙学的四大基石”,无一不有考据的内容。但同时,他们对“校雠”的处理和贡献又不尽相同。现代龙学由黄侃开山,其《札记》开创“文字校注”“资料笺证”“理论阐释”三结合的新方法,然其因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故尚有许多不足。范文澜虽“追踪乾嘉”“笃守师法”,但勇于开拓、勤于进取,其校注完成由“注疏体”至“综合体”的转变,最终成为取代黄注的新范型。杨明照的诸多补注,则进一步解决由黄注带来的历史遗留问题。黄注因其为“客某甲”代笔而多有罅漏,虽有范氏的大规模补苴但弊处仍存,这使杨氏有机会为复原《文心》原貌再作巨大贡献。而刘永济则从范注侧重校注的趋势中跳脱出来,直承《札记》“文字校注”“理论阐释”相结合且以后者为主的理路,进一步为学界树立如何处理考据之学的另一种态度。当然这种态度之所以会出现在有“学衡派”立场的刘氏身上,也是因为范注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如《校字记》中“已具范君文澜补注”一语所代表的历史功绩,使得刘氏有机会脱身于知识性的材料积累。刘氏的这种转变为“发展期”的龙学研究提供了更多可能,也加速了义理阐释的整体步伐。
另外,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深入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广泛影响,“人民的文学”逐渐成为时代主流,则大众化、通俗化亦成为古代文论现代阐释的一项重要要求。包括范文澜本人的学术生涯,亦以1936年出版的《大丈夫》为界,可分为“追踪乾嘉”和“通史普及”两个阶段。在《校释》出版的60年代前期,出现了当代龙学的第一个热潮,而它正是以“译注”事业为主流。1961年春,张光年为《文艺报》编辑部同仁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年轻人讲解《文心》,并以“白话骈体”选译了6篇内容;1962-1963年,山东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了陆侃如、牟世金的《文心雕龙选译》上、下册,选译了《序志》《神思》等25篇内容;1963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郭晋稀《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另有周振甫于1961年至1963年间,在《新闻业务》上先后发表了《文心》28篇注释翻译。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著述中有校勘逐渐隐去的趋势。
《易·系辞》有言:“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落实于文艺现象的演变之中,则如叶燮所言“惟正有渐变,故变能启盛”。虽就《文心》校雠事业而言,刘氏的校字未能严格遵守乾嘉考据的范式,呈现出异样的形态,但它同时也为《文心》研究的新变鸣锣开道。换句话说,《校释》“释体校用”的模式,正与浩瀚的历史洪流同向,其上承《文心》校雠传统,中续《札记》阐释理路,下联龙学译注事业,见百年传承之斗转,证世纪学术之迭新,诚为推动龙学研究发展变化之伏流也。
三、整体推论:潜在的理与据
《校释》虽然以释为体,但不代表刘氏就抛弃了对校雠事业中“铁证如山”的自觉追求。《校释》共有280条校字,其中既没有为结论提供依据,也未对其作出说明者⑨,超过校勘总数的十分之一。这些推论初读似为妄言,但仔细品味后又别有一番滋味。
如《议对》“鲁桓务议”,刘校曰:“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引惠士奇说:‘当作鲁僖预议。’按宋本《御览》五九五正作‘预议’。‘僖’之误‘桓’,恐舍人误记,非字讹也。”此校前半部分尚无异处,“务”当作“预”的说法与黄侃、范文澜、王利器、杨明照等诸家相同;然而后半部分“恐舍人误记”一语,则如平地惊雷,让人大吃一惊。
对于《文心·议对》篇“春秋释宋,鲁桓务议”,黄叔琳引《春秋·公羊传》所言,依据“释宋公”之事发生于僖公二十二年,按曰:“鲁桓公无议释宋事,桓当作僖。”[19]155李祥《补注》首次提及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之语,而后黄《札》、范《注》《校证》《增订校注》的校注皆大同小异,认为“桓”当作“僖”。
《校释》与其他著作不同的原因,在于诸家校勘时,主要解决的是“今本对错之间的矛盾”,并将情理上的对错与文字上的对错直接等同。因此,他们在面对“鲁桓务议”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情况下,纷纷表示要对此句进行改动。刘永济并非不知晓该句的“鲁桓”一词在逻辑上说不通。校语中的“误记”二字,便已说明刘氏的看法。但刘永济在同意“桓”字有误的同时,将问题的视角转向“为什么错及错在哪里”。两千多年前的《文心》原稿,如今已不可得见。因此,刘永济推测为“舍人误记”的思路只能是“排除法”,即通过排除“僖”字在流传过程中讹误成“桓”字的可能,便可得到“《文心》原稿有误”,亦即“恐舍人误记”的结论。刘永济在《默识录·古书易讹之故》及《屈赋篇章疑信诸问题答席启駉先生》中,都标举了孙诒让《札迻序》之语,赞同孙氏对古书致讹之原因的判断,认为其“有三代文字之通假,有秦汉篆隶之变迁,有魏晋正草之混淆,有六朝唐人俗书之流失,有宋元明校椠之羼改。途径百出,多歧亡羊。”[20]264落实到具体的校勘之中,刘氏根据这些可能导致讹误的原因,认为“原文”与“讹文”之间应相应存在四种联系:“形似音近”“异体假借”“脱衍错序”“避讳换字”。而今本的“桓”字与当作的“僖”字之间,根本就没有这种关联。
我们再结合《奏启》篇“皂饬”的校语来看,《校释》云:“按孙诒让疑‘饬’当作‘袀’,以‘袀’为皂服也。然袀无缘讹为饬,‘饬’疑‘饰’之误。皂乃司直服色。”此中“无缘讹为”四字甚为关键。它正是刘永济在《议对》篇“鲁桓务议”条中,省略未说的潜台词。《奏启》篇“袀无缘讹为饬”,刘氏尚可另举出“饰”字替代;而《议对》篇“僖无缘讹为桓”,却不能再找出另一个字了,因为“僖”被公认为最合乎情理的答案。面对“流传过程中本不应该发生这种讹误”与“实际中这种讹误恰恰发生”的悖论,刘氏适时地提出“恐舍人误记”的结论。
其实,刘勰虽是公认的文章大家,但他的行文亦有疏漏之处。对此,《校释》中多有提及。如《校释·声律》篇“南郭”条,刘氏只引述了前人说法,并未做出判断,其主要目的是借孙诒让之口,指出原文不管是作“东郭”还是“南郭”,“但滥竽事终与文义不相应”。又如《校释·事类》篇“曹仁之谬高唐”条,诸家都依据《文选》中陈琳所作的《为曹洪与魏文帝书》,认为“曹仁”当作“曹洪”。刘氏也转引了这种说法,并在结尾处附上了点睛之笔:“然实陈代曹作,彦和未加分别”。简言之,《文心》文本不管是作“曹仁”还是“曹洪”,都不符合事实,因为该作品系为陈琳代笔。这都显示出舍人所作《文心》,实际上存在文句与逻辑不相符合的情况。据此,我们再回过头看“鲁桓务议”条的推论,就不能再视其为臆测了。
《校释》在“恐舍人误记”之后,紧接着说“非字讹也”。这里暗含着刘氏的一个建议,即不应改动“桓”字。这与李祥《补注》中的言论亦有相应之处。《补注》云:“《集解》:徐广曰:务,一作‘豫’。‘豫’与‘预’通,此作‘务’议,亦未为不可也。”李祥认为当作“鲁僖务议”,刘永济以为该作“鲁桓预议”。李祥认为“务”字不需要改;刘永济觉得“桓”字不应该改。二者结论不一,但均与应作“鲁僖预议”的一般观点有所不同。在此,刘永济或是受到李祥《补注》的启发,而后统筹各家观点并进一步提出自己的判断。
从“鲁桓务议”的案例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想要真正理解《校释》所作推测的理论依据,需要将其置于刘氏校勘思维的整体中去看。如《校释·祝盟》篇“颂体而祝仪”,刘氏校语仅短短五字:“‘仪’疑作‘义’。”然而,它实际上包含该篇“硕儒之仪”条校语的判断,即“唐写本‘仪’作‘义’,是。”若我们将前后两条校语联系起来看,便会明白“‘仪’疑作‘义’”中,蕴涵“形音的相似”“互讹的先例”及“文本的理解”等诸多内容。再如《校释·封禅》篇“骨掣”条,刘氏言:“‘掣’,疑当作‘制’。‘骨制’即‘体製’。本书‘製’或省作‘制’。”作“制”与《章表》篇“应物掣巧”条校语相呼应,其云:“《御览》‘掣’作‘制’,是也。‘应物制巧’,与下文‘随变生趣’,句例同。”刘氏通过本校法和对校法,证明了“掣”当作“制”,并明确了二者的联系。但在“骨掣”条校语中,刘氏又认为“制”为“製”之省写。这是因为“製”与“制”之间,不单单是繁简体或古今字的关系。《说文解字注》释“制”曰:“制,裁也。衣部曰:裁,製衣也。製,裁衣也。此裁衣之本义。此云‘制,裁也’,裁之引申之义。”[21]184简言之,“製”为“裁衣”,语义偏向于具体的“制造”;“制”为“裁之引申义”,相较而言更偏向于抽象的“制作”(当“制”在历史进程中占据主流,便吞噬了“製”的意义)。而古人秉持类比的形象思维,认为文章如人,称文章之内在曰“筋骨”、曰“骨鲠”,文章之外在曰“肌肤”、曰“体貌”,则古时关于文章之“体制”当写作“体製”⑩,有“人之着裳”之喻。刘氏综合考虑后,推断“应物掣巧”条,“掣”当作“制”;“骨掣”条,“掣”虽亦作“制”,但实际为“製”字之略写。
综上,刘氏在推论中高度关注字音、字形,继承了传统考据的核心理念,并糅合了《文心》的内证与外证,进而获得整体的观照。王更生曾说:“《文心雕龙》全文有特定的体系,不啻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22]47王氏此言,不仅可以移用于评价《校释》的释义部分,也可以用来形容刘永济校字的特色。前后呼应、内外相参,使得刘氏在校字上的推论熠熠生辉。
四、结 语
回到文首詹氏的评价,我们并不赞同刘校“无多创获”之说。限于篇幅,这里只简单说明。以《奏启》篇为例,《校释》有8条校字,其中“事略而意迳”“世人”“总法家之式”“取其义也”“谠者,偏也”“皂饬”6条被《文心雕龙义证》摘录以存说。须知詹氏《义证》以《校证》为底本,然其言“《校注》《校证》所作校语,本书并未全部罗列”。詹氏所录既有精心挑选的过程,则刘校之价值自彰。另外,《校释·奏启》“势必深峭”条校语,不仅对詹氏有所启发还引起争论,说明其亦收获了詹氏的重视。
那么,《义证》为何一边重视《校释》,一边提出这样的判断呢?福柯言:“一命题必须符合复杂和苛刻的要求才能融入一学科;在其能认定是真理或谬误之前,它必须如冈奎莱姆(Canguilhem)所言,先‘在真理之中’。”[23]13詹氏评价的背后,显然传承了乾嘉学派的传统理路,他是站在校勘学学科范式的立场加以审视,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明此,我们才能知晓本无绝对联系的“版本”与“创获”,为何在詹氏的陈述中变为前后相衔的因果关系,其背后正是“无征不信”的核心理念在发挥作用,进而使“版本”的作用及影响绝对化。而刘校的基本情况已如上述,其异样不仅是所据版本不多,更在话语层面发生了偏离,这也是学界长久以来对刘校习惯认识的深层原因所在。
当然,这种偏离也使其校在体例上的严谨性相对弱化。如刘校所用底本既非当时通行的黄叔琳注本,却又未交代究竟是何本。《校释·明诗》篇“继轨周文”条,校语为:“《御览》,‘文’作‘人’,是。”这说明其所据底本为“周文”,非是编辑过程中的字误。而当时流行的《文心雕龙辑注》正文皆作“继轨周人”。刘氏所用或是以杨慎批点为底本的明代刻本,但我们仅据《校释》前言无法得出具体判断。又如其引用时的标注不明,未能与前言保持一致。前言称他所据《太平御览》有二,即商务印书馆影印宋本及清代鲍崇城刻本。若鲍刻本与宋本同,“校字中但曰《御览》作某”。而《校释·杂文》篇“覃思文阔”条,校曰:“唐写本作‘文阁’,鲍本、《御览》五九〇同,是。” 此条“鲍本”与“《御览》五九〇”的内容相同却分述,显然不合这一体例。而且,宋本《御览》实际上“无覃思至其辞十八字”[24]752!我们推测,“《御览》五九〇”应是前言中没有提到的明刻本《御览》,且系转引孙人和校本所言。一方面,孙氏在以《御览》校《文心》方面的成就较为卓越,此从范《注》所引部分便可窥见;另一方面,前文已述刘氏手上确有孙人和校本。《校释》有22条校字出现“《御览》某某某”的句式,或皆为模仿孙人和校本中对明刻本(明代第一版倪炳刻本)的称谓。总而言之,刘校之体例未能详细交代、严格贯彻,实为其书一大缺憾。
而前述种种显现的根本原因,又可以归结至刘氏的文化理想和人生追求。刘氏在第一部专著《文学论》中,就对激烈的时代变局充满关切。他认为中西文化碰撞交融,固然会为我国文化带来进步与兴盛。然而,只有我国固有文化处于鼎盛大明之时,才能受其裨益,结出更加辉煌的成果。相反,“若一民族为学术荒落、政治紊乱之时,其固有之文化衰弱,而特性亦隐晦,则当其与新来之文化接触之际,必呈惊疑懊丧之状”[20]85。故其宣称当“用古典文学理论来检查古典文学作者和作品”[20]204,强调要探索自身的理论建设。其学术生涯始终对《文心》抱有极大的热情,正因其选择衡鉴我国纷繁复杂的文艺现象之标准就是《文心》诸论。再加上《校释·知音》篇云:“一民族、一国家已往文化所讬命,未来文化所孳育,端赖文学。然则识鉴之精粗,赏会之深浅,所关于作者一身者少,而系于民族国家者多矣。论文者又乌可忽哉?”盖刘氏以为文论家,尤其是古代文论工作者,肩负着导夫前路的时代使命和文化救国的重大责任,故其在不抛弃传统考据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别样的心灵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