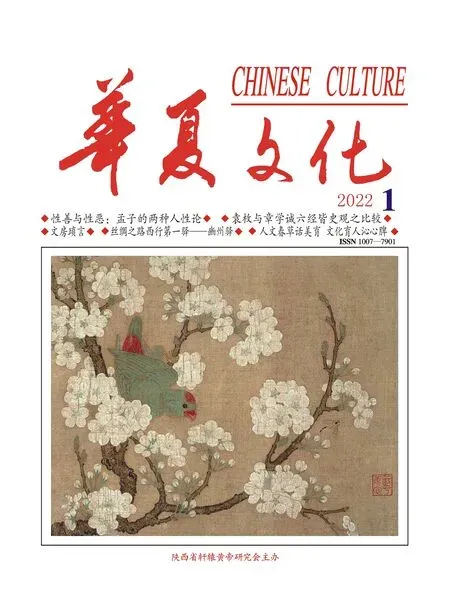性善情扰与息情复性:李翱《复性书》思想分析
□郝振宁
一、引言
隋唐以来,大一统的政治环境使得人们的生活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社会也愈发稳定。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文化也随之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变。一方面,儒释道三教之间的交流和融合逐渐显现,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遭到一定程度上的威胁。另一方面,社会重文之风大盛。重文而轻质的风气盛行,导致文人们过于注重文章辞藻的华丽,从而忽略了其中所蕴含的义理与内涵,使得文章多流于表面而失其核心义理。又加之安史之乱带来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特别是藩镇割据使得中央的权力被削弱。面对这种情况,以韩愈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开始觉醒,意图通过复兴古文来恢复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改善当时的社会环境,解决唐朝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
李翱即是其中的一份子,他与韩愈亦师亦友,同样也意图凭借自身的力量改善社会风气。李翱所处的环境各种思想交融驳杂,他的思想受韩愈的影响很深,除了遵从儒家正统思想外,也力主排佛。在李翱看来,儒家的正统地位已经岌岌可危,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儒家圣贤所倡导的“性命之道”已经遗失不传。虽然书卷犹存,但“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庄、列、老、释”(李翱撰;郝润华,杜学林校注:《李翱文集校注》,中华书局,2021年,第15页)。因此他立志于恢复儒家“性命之道”,以纠正社会现存的歪风邪气,进而发出了“道之极于剥也必复,吾岂复之时耶?”(《李翱文集校注》,第15页)强有力的呼喊,后“遂书于书,以开诚明之源”(《李翱文集校注》,第16页),以期实现“而缺绝废弃不扬之道,几可以传于时”(《李翱文集校注》,第16页)的伟大理想和抱负。
由此,李翱从人性论入手,在继承原有儒家思想的基础之上对人性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究,著《复性书》,意图以此教化百姓。《复性书》以“性”与“情”为主体,对“性”“情”及其关系进行阐释,其目的在于恢复人的本性,继承并发展儒家的正统思想。
《复性书》主要以《中庸》为蓝本,融汇《易》、《诗经》等经典,是对儒家先贤思想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复性书》有上、中、下三篇。上篇借圣人与百姓的差异性,阐述“性情”问题产生的原因,直言其写作的缘由;中篇通过问答的方式,借用各种经典文集,论述其“复性”的方法;下篇虽极为简短,却清晰地表述了“复性”的意义及其实现的迫切要求。
二、“性善情扰”的认识论
既然《复性书》主要是围绕着人之“性”与“情”的关系问题来论述,那么“性情”问题就成为了打开李翱哲学思想大门的一把钥匙。在“性情”问题上,李翱继承了《中庸》的“性情”观,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将其延伸和发展,将“性”“情”二分,不仅从认识论的角度对“性”和“情”的问题进行分析与研究,还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了一套人如何“去情复性”的操作指南。因而要了解李翱的“复性”思想内涵,首先就要了解李翱所提出的“性”与“情”。
“性”是李翱《复性书》一文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在李翱看来,圣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圣人,关键在于他凸显了人的本源之“性”。《中庸》言:“天命之谓性”,“性”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也是圣人得以成为圣人的原因所在,“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李翱文集校注》,第13页)作为人的本质的“性”,乃是由天所赋予的。“性者,天之命也”(《李翱文集校注》,第13页),是与生俱来而非后天习得的。作为上天所赋予的天然本性,其当应是善的而非是恶的,故“性无不善焉”,能够成就圣人的品格。这与孟子所言“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孟子·告子上》)的人性本善论有相似之处。然而这种“善性”并非是一直显现出来,而是时常以一种潜在的状态存在于人身之中。他以水火比喻“性”:“火之潜于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济之未流而潜于山,非不泉也”(《李翱文集校注》,第13页)。“性”如同山石林木中的“火”,其并非不存在,而是隐匿在山石林木之中,只需要一点契机,便可以使之凸显;水亦复如是。石木之所以能够烧山林,燥万物,是因为其中潜藏着火性;缺乏其中所潜藏的“火”,没有了这种本性的存在,则一切都成为空中楼阁,圣人也就难以成为圣人了。
人虽先天就具有这种本性,但并非意味着有此本性就能够成为圣人。作为上天赋予人的本质的“性”,既然是圣人能够成圣的原因,那么为什么拥有了“性”的普通人却仍旧成不了圣人?“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也”(《李翱文集校注》,第13页)。首先李翱否认了圣人之“性”与百姓之“性”存在差别的判断。“性”虽然是人人所具有的,但并非都能够使之凸显和清明,不能使其显现的原因就在于百姓往往惑于其“情”,“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李翱文集校注》,第13页)凡夫俗子虽与圣人一样都同样拥有上天所赋予的“性”,但却未能成为圣人,正是因为受“情”的影响。“水之浑也,其流不清;火之烟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过,沙不浑,流斯清矣;烟不郁,光斯明矣。”(《李翱文集校注》,第13页)水浑而不清,非水自性本浑浊,而是在于泥沙翻搅使之浑浊不堪;火本为光明,但受烟熏弥漫不散,因而也难以得见其光明。人之本性亦复如是。“性”本纯善,但受“情”所迷惑与搅扰,因而终难以成圣。“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过也,七者循环而交来,故性不能充也。”(《李翱文集校注》,第13页)故百姓虽有其“性”,但仍旧未能成为圣人。只得沦落为“交相攻伐,未始有穷,故虽终身而不自睹其性焉。”(《李翱文集校注》,第13页)故而不难看出,“情”使“性”不彰不明,“情”之七者交循而来,使得“性”不能充盈于人身之中。因此“性”虽人生来所具有的本质,但仍然并非人人皆可成为圣人。
尽管“情”是导致“性”不彰不明不充的原因,但是李翱并非否定“情”的存在意义,他认为“情”与“性”并生并存,“性与情不相无也,虽然无性则情无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李翱文集校注》,第13页) “情”由“性“所生,“性”因“情”所明。“情”并非是圣人所不具有的,如同先天禀赋的“性”一样,“情”同样也存在于人的身体之中。“性情”在李翱眼里甚至可以说是一体的,近似于一种辩证关系,“性”与“情”二者缺一不可。只不过圣人能够有所“先觉”,不受“情”所扰,不为“情”所困,不惑于“情”,并非是说圣人“有性而无情”。
他通过比较尧、舜与桀、纣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分析同样有情有性的人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相去甚远的结果。首先,他认为尧、舜与桀、纣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差别,他们的“性”都是一致的,而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善恶有别、昏明有异的情况,其原因就在于桀、纣受“邪情”所扰,“邪情”使得“性”昏暗不明,因而不能睹见其“善”。桀、纣在“邪情”的搅扰下自身先天禀赋的“善性”被掩盖,因而为恶。这是“邪情”扰乱了人先天所具有的“善性”的结果。但是“情有善有不善,而性无不善焉。(《李翱文集校注》,第22页)在李翱看来,“情”有善有恶,并不能片面地说“情”仅为“邪情”。但是无论是“善情”抑或是“邪情”总归是要对人的“善性”造成一定的侵扰,影响人自身本来“善性”的凸显,因而使之不彰不明。那么为什么圣人能够不为“邪情”所困扰?李翱进一步作出了解释,并为其提出了方法论指导。
三、“息情复性”的方法论
“邪情” 既然扰乱人的“善性”,尧舜却又如何能秉持“善性”而为,不受“邪情”的搅扰呢?面对这样的问题,李翱提出了一套复归人性的修养方法。
在李翱的思想体系中,普通百姓既然已经拥有了和圣人一致的“善性”,那么只要通过一定的修养方法,必定能够同圣人一样成就自身。圣人有别于桀、纣和百姓的原因在于“圣人至诚而已矣。”在这里李翱强调了一种成圣的先后关系,他认为“故圣人者,人之先觉者也。”(《李翱文集校注》,第14页)圣人能够保持自身“善性”的显现,是因为圣人得以“先觉”。“先觉”使人能够感悟到先天所秉持的“善性”,即在洞悉了“邪情”对人“善性”的搅扰所造成的恶果后,又挖掘出了百姓与圣人共有的“善性”。建立在善性的基础上,“圣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于圣也。”(《李翱文集校注》,第14页)因此圣人制礼作乐,建立一整套的规范制度,以促进百姓回归自身,修炼自我。“故制礼以节之,作乐以和之;安于和乐,乐之本也;动而中礼,礼之本也;故在车则闻鸾和之声,行步则闻佩玉之音,无故不废琴瑟,视、听、言、行,循礼法而动,所以教人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也。”(《李翱文集校注》,第14页)圣人意图通过教人节制欲望的方法,发觉自身的“善性”,使人能够通达自身,引导人通晓自身的本性,使之能够在社会中形成良性循环。
百姓本然“善性”的潜匿,是受到“邪情”的搅扰。“情”虽然有善有恶,但是无论是善情还是邪情,都会对百姓的“善性”产生影响,“七者”交循而来,使得“善性”不充不盈,不明不彰。“情之动静弗息,则不能复其性而烛天地,为不极之明。”(《李翱文集校注》,第13-14页)因此要使“善性”得以充盈于人身之中,使人不受“情”的搅扰,则需要“息情”。(张大伟在《李翱“复性”说及其援佛入儒思想探析》一文中也持有相同的观点,有别于“熄”,以“息”来表述李翱的方法论似乎更能切合其思想本质。)
“息情”并不意味着对人之“情”绝对的消除和磨灭,李翱在《复性书》伊始就表明了“情与性”的辩证性论断。人们一旦彻底抹去了“情”的存在,那么“性”也就难以明晰了。从这种层面上来说,“息情”既非是否定“情”在人身体中存在的必要性,也并非是肯定他存在的绝对积极意义,而要“邪思自息”。“弗思弗虑,情则不生;情既不生,乃为正思;正思者,无虑无思也。”(《李翱文集校注》,第19页)“息情”首先要“弗思弗虑”,不对外部的事物产生思虑,那么对外物的感情也就不会产生。但是,“弗思弗虑”只不过是“息情”浅显的外在表现,是人有意的动心而止地控制人的情欲,这只不过是“斋戒其心”的一种基础手段而已,“此斋戒其心者也,犹未离于静焉;有静必有动,有动必有静,动静不息,是乃情也。”(《李翱文集校注》,第19页)李翱以《周易·系辞下》“吉凶悔吝,生于动者也”,指明“弗思弗虑”,虽然表面上不动于“情”,但是仍然有动静之生。其表面上貌似是处于“静”的平和状态之中,实质上却是一种动静循环的过程,只是这种过程的外在表现不过是“静”的一面,尚未真正实现“息情”的理想目的。
要超越这种表面上的“静”,“诚”就成为了核心与关键。“知本无有思,动静皆离,寂然不动者,是至诚也。”李翱承袭《中庸》之道,认为“诚”是人修身息情以复性的核心之所在。“道者至诚而不息者也,至诚而不息则虚,虚而不息则明,明而不息则照天地而无遗,非他也,此尽性命之道也。”(《李翱文集校注》,第14页)他推崇“至诚”之道,并在韩愈“道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认为“道者”就是保持“至诚”而不停止的人,保持“至诚”的状态就能明白人的本性并无有动静思虑的偏邪,继而使人的本性明达,洞悉人自身先天禀赋的“善性”,进而回归到性命之道的本源上。百姓不仅有能够照见本性的能力,而且一旦人们返归到性命之源,照见了人自身本然的“善性”,那么就不会再受到“邪情”的搅扰,即“不复浑矣”。至此,即已洞悉“邪情”并非是有因存在的,只不过是由于人的昏昧因而得以影响自身的本性,使人的本然“善性”不彰不明,不能凸显出来。但李翱并不止步于此,他不仅向普通人提出了“息情复性”的方法,同时还向已经成圣的人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天之道,以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者也。”(《李翱文集校注》,第23页)李翱借伊尹之言指出对于已经“复性”的圣人来说,当有义务建立一种方法仪则来警醒其他尚处在愚昧之中的普通人,使其自身亦能够照见本性,继而不断警醒后来者。长此以往,整个社会就会形成一种良好的循环,使得人的“善性”能够不断地显现,不致于出现“性命之书虽存,学者莫能明是,故皆入于庄、列、老、释,不知者谓夫子之徒,不足以穷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这种“善性”断绝的情况。
四、余论
李翱基于其所生活时期的时代思潮,提出了他的人性论。他同韩愈一样,力主排佛,但他的思想却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参见张大伟《李翱“复性”说及其援佛入儒思想探析》,他认为李翱的“复性”说实质是一种内佛外儒的思想,并由此为儒学学者找到了一条崭新的修养道路)尽管《复性书》以“性情”为主题,但他仅仅给“性”做出了积极的肯定。而对于“情”来说,他虽然一方面表现出了“情”对于“性”所产生的搅扰的消极影响,但另一方面他却又没有彻底地否定“情”的存在。他试图通过用“诚”的方法来“息情”,调和“性”与“情”的冲突,并在照见“性”的基础上继承儒家正统思想,以恢复人的“善性”。李翱“性情”思想的核心即在于此,其济世情怀也正因此而得以被鲜明地凸显。
对于李翱而言,尽管他提出了“复性”的方法,但其实并不完善。首先,在“复性”的方法上,他并没有给出详尽的、可操作的行为指南,仅仅抽象地告诫世人“息情”而“复性”,保持“至诚”则人的“善性”就能够得以照见。其次,他认为“情”由“性”所生,“情”从属于“性”,但“善性”为何会产生“有善有恶”的“情”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仅仅是以“情”为“邪”的预设来实现“复性”的目的。最后,对“死亡”的问题他也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甚至采取了一种消极回避的态度,“此非所急也,子修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章章然言且书矣。”诚然,李翱的思想存在着诸多不完善之处,但对于当时的时代来说,却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不仅对当时的社会思潮产生一定的冲击,而且为后世特别是宋明时期的理学思潮回归“人性”的问题开辟了新的战场。他将“性”与“情”区分开来,不仅是对先前思想的继承,更是对后世思想产生了重要启迪,甚至可以被视作“天理”与“人欲”之辨的开端。从这一点上来说,李翱仍然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