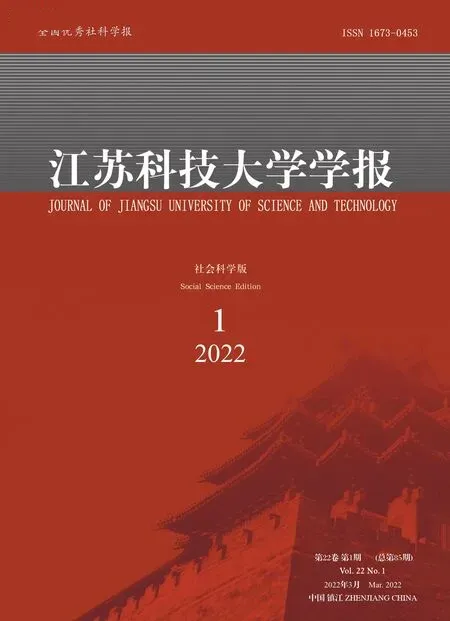近50年明代内阁首辅申时行研究综述
张 鑫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1)
申时行(1535—1614),江苏长洲人,字汝默,号瑶泉,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三月殿试第一释褐入仕;万历十一年(1583)四月,接任首辅大学士,主政内阁;万历十九年(1591)九月,因“争国本”一事被言官交章弹劾,被迫致仕下台,但其政治影响力并未因此终结。申时行以“传衣钵”的方式塑造了内阁首辅之间新型的政治继承关系,极大地稳定了当时的中枢政局,并持续影响了之后数任内阁首辅的执政理念和政策风格。其间,朝中仍不时有重臣举荐他重返内阁主持朝政,但因种种因素未能成行。直至万历四十二年(1614),申时行以年近八旬的高龄无疾而终,被明神宗追赠为太师,谥号“文定”,与此前因激烈的权力斗争而黯然下台或抑郁离世的内阁首辅相比,可谓极尽哀荣。
针对这位从政近30年的“状元首辅”,明清以来的整体评价渐趋负面,且长期没有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充分研究。但实际上,纵观申时行八年多的首辅生涯,在面对异常复杂的朝局形势和日益丛脞的中枢政务时,他展现出了较大的政治抱负和较高的施政才能;致仕后,也得到了后任内阁首辅的尊重和请益,对朝野各方政治势力依然保持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力。目前学界对申时行的研究仍不够深入,尚未发现研究申时行的学术专著。同时,借助《燕京学报》《明清论丛》《明史研究论丛》《明史研究专刊》《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百年明史论著目录》《江南区域史论著目录》以及“中国知网”“读秀”“万方”等学术平台,以“申时行”为题名进行搜索,仅得相关文献25篇,其中学术期刊8篇、硕士论文5篇、特色期刊9篇、年鉴资料2篇、学术辑刊1篇;若以“申时行”为关键词搜索,虽能得文献200余篇,但主题多元,体裁多样,内容分散,显然未能聚焦于申时行一生主要之行止、功业和影响。因此,笔者不揣浅陋,分别从综合研究、专题研究这两个方面,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界与申时行研究密切相关的现有成果予以梳理和分析。
一、 综合研究
(一) 年谱类
常蕊的《申时行年谱》应该是目前国内学界较早对申时行进行拓展研究的学术成果。《申时行年谱》通过对申时行相关史料的爬梳,初步考证了申氏一族的世系传承,并简要考订了谱主个人著述的版本和流变,可以说为申时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良好的前期基础[1]。但常蕊所利用的史料范围较小,主要局限于《万历起居注》《国榷》《明通鉴》等常规史料,对官方实录、档案、地方志、时人文集以及谱主的家谱、著述、奏疏、书信、诗文等第一手材料的挖掘力度还不够,特别是对谱主与同僚亲友之间的书牍往来没有进行细致的整理和解读。再加之受制于年谱的编撰体例,导致《申时行年谱》一文很难真实、系统、全面地还原一些重要历史事件的起因原委和前后变化影响,如“倒张运动”“国本之争”“辅臣子弟科场案”等。
(二) 评述类
李显的《申时行之政治角色研究——以国本之争为中心的探讨》一文,为申时行学术研究提供了“跨学科”的新颖视角[2]。该文立足于角色理论,重新审视了申时行在“国本之争”中的角色确认和扮演,客观分析了其“角色冲突”的无奈与困境,尤其在对申时行社会和政治双重角色重叠的“模型”解读上,凸显了一定的社会学、政治学理论功底。但鉴于学科背景的差异,该文对史料的遴选、甄别和使用并不尽如人意,缺少对当时官方文书、邸报、实录以及申时行个人著述、奏疏、书信的梳理和探究,使得很多探索性论断缺乏扎实的史料基础。刘倩的《诚与中庸:申时行的政治行为模式研究》一文,也是依托政治心理学的人格理论和社会学的角色理论来研究申时行的“政治行为模式及其表征”“政治行为选择的人格因素”“政治行为困境”等方面的内容[3]。相较而言,刘倩一文对申时行基本史实的表述、考证和分析更为规范、严谨,史料的选择也更为广泛、多元,但其所用理论和所述史实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比如“人格与政治行为互动理论”“角色理论”等。
(三) 传记类
197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由富路特(L.Carrington Goodrich)、房兆楹主编的《明代名人传》(DictionaryofMingBiography, 1368-1644)[4]。这部专著代表了当时海外明代史研究的最高水平。该书由125位汉学家参与撰写,旨在通过对明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军事、科技等各个领域重要人物(包括周边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重要政治军事家和使节)生平事迹的介绍,对上起元末下至明亡的300年间历史进行了全景式展示,勾画了整个明代历史的基本轮廓。但该书对申时行的描述和评价基本沿袭了清代官修《明史》的观点,同样认为“总体而言,他总是逢迎神宗,政绩不够卓越”,并进一步指责申时行在“主政期间,明朝法纪松弛,朝纲不举”。这种论断显然不完全符合史实,缺乏对历史细节的探究和还原,因而也难以深化对申时行的研究。
胡廉洁的《申时行研究》相对系统地评价了申时行主要的政治生涯[5]。作者强调,申时行在内阁主政期间“行宽大之政”,与张居正时期一味严苛压制朝野的执政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胡廉洁认为,在赈灾民、靖边境、止矿税、开言路等方面,申时行显露了较高的政治才能,有力地稳定了万历中期的政局。胡廉洁在此基础上还进一步分析认为,申时行为官执政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根源主要得益于他本人对儒家经典《尚书》的研修,其中“法天道以无为”的先秦圣王之道、仁君治民之道、贤臣事君之道就是申时行最大的政治理想和追求。但该书相关章节篇幅较短,未能围绕其核心论点展开学理性剖析。此外,该文对申时行主要从政经历的论述、评价和相关史料的选取,均没有跳脱前人的研究范畴,对其早年的成长经历和晚年生活的研究也明显不足。
(四) 著作类
目前国外研究申时行的代表性著作无疑是原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茨分校教授、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著的《万历十五年》(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theMingDynastyinDecline)[6]。该书作者认为,尽管申时行凭借各种娴熟的政治技巧和“中庸”的处事原则,在君臣朝野之间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微妙的“阴阳”平衡,但终究无法逃离整个文官集团“双重性格”的挤压。如何看待或解决申时行所遭遇的政治难题,恰恰是黄仁宇撰写该书的核心主旨,即中国未能走向“现代化”的症结在于没有引入西方“数目字上的管理”。尽管该书从较为新颖的角度探讨了申时行的政治行为和影响,但很多观点实为作者个人的猜测或推论,缺乏扎实的史料支撑,对申时行及其同僚著述的利用依然不够充分。
此外,《剑桥中国明代史》(TheCambridgeHistoryofChina:TheMingDynasty,1368-1644)[7]、《哈佛中国史·挣扎的帝国:元与明》(TheTroubledEmpire:ChinaintheYuanandMingDynasties)[8]在相关章节中也提到了申时行部分的政治活动,但篇幅有限,不再赘述。
日本学界历来重视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小野和子的《明季党社考》(明季党社考:東林党と復社)无疑是日本学者研究明代中后期政治及其派系党争的力作,也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9]。作者在书中详细论述了部分朝臣和言官在“国本之争”事件中对申时行展开的激烈批判。该书作者认为,申时行是姑息神宗怠政的始作俑者,因为他提出了“免进讲章”“奏疏留中”等多项消极建议,对朝局造成了负面影响。该书的诸多观点得到了国内如《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明史》《走进晚明》等著作的认可和阐发[10-12]。
而国内学界尚未整理出版申时行的个人文集或学术专著,虽有杜新中《太平宰相徐时行密档》[13]一书,但该书属于通俗读物,缺乏史料支撑和理论基础。该书搜罗了大量的民间传说、戏剧评弹如《芙蓉洞》《玉蜻蜓》以及《双泉徐氏宗谱》等资料,据此认为徐(申)时行原系苏州一纨绔子弟与庵堂尼姑偷情私生之子,后被抛弃,由路人东阳徐廷翠夫妇收养抚育,最后高中状元并官至首辅大学士。其实,对于申时行的身世和弹词《玉蜻蜓》的附会,吴仁安在其专著中早有详细辩驳。吴仁安明确指出,《玉蜻蜓》是别有用心之徒巧借“申家的关键人物(即徐士章与申时行等)的片段史实(诸如上述申时行‘复姓归宗’、时行之父徐士章与剧中申贵升同为长洲庠生、时行生母王氏与剧中尼姑王智贞同姓等)”[14]编创而来,用以诋毁和打击苏州申氏家族,进而动摇其在苏州的政治声誉和经济利益。
蒙思豪在前人的基础上详细梳理并分析了“玉蜻蜓”的故事流变、文学意涵和价值导向。他认为,“‘玉蜻蜓’故事流传中因为不断有人参与改编,改编后的文本相较现存最早的弹词《新刻玉蜻蜓》而言内容变化较大,情节增减变化情况较为复杂”[15],已经与历史的真实情况大相径庭。他指出,前人有关“万历间,吴县申时行,太仓王锡爵两家私怨相构。王作《玉蜻蜓》以诋申,申作《红梨记》以报之,皆两家门客所为,相传至今”[16]的观点也值得审慎怀疑。
此外,明史专家樊树志在其代表作《晚明史》中专题论述了“申时行辅政时期”的政绩,突出了他在“后张居正时期”对稳定朝局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充分肯定了申时行对神宗亲政初年励精图治的辅佐之功,但他对申时行在明代政治史中的地位和评价仍有所保留,没有完全突破过往之论[17]。之后,樊树志在其“重写晚明史系列”之《新政与盛世》一书中对前文相关内容予以增订,不仅扩充了对申时行“相业”的论述篇幅,而且补充了申时行执政期间重要事件的大量史料和相关评述,既指明了申时行执政能力的具体不足,也承认了他“太平宰辅”的历史地位[18]。可以说,此书应该是当前学界申时行研究中最新也是最有分量的专著。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申时行政治地位和功业的重新审视和评估,回应了学界对申时行“再研究”“再评价”的趋势和需求。就当前对申时行研究的深度、广度而言,两书也有稍显遗憾之处:一是没有充分利用申时行个人著述中的奏疏、书牍、诗文等第一手资料;二是受限于篇幅和体例,无法对申时行的政治行为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三是没有重点关注明代中后期内阁政治由“张居正时期”过渡到“申时行时期”的动态变化和机制迁移;四是没有进一步分析申时行执政期间朝局派系纷争背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
其他著作如近代明清史研究巨擘孟森《明清史讲义》[19]、樊树志《万历传》[20]、梁德等《荒淫天子明神宗》[21]、曹国庆《万历皇帝大传》[22]、林金树《万历皇帝传》[23]、战继发《明神宗评传》[24]、方志远《万历兴亡录》[25]、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26]以及刘志琴《张居正评传》[27]等,这些虽非研究申时行的专著,但均有相当篇幅介绍或涉及了申时行辅佐神宗、主政内阁、协调朝野的政治活动。上述著作论述主要来源于申时行的自述《召对录》以及《明神宗实录》《明史》等基础史料,对申氏的评价依然未能完全摆脱“软熟”“将顺”“遇事迁就”“媚君自保”“外畏清议,内固恩宠”等传统论述的桎梏。
二、 专题研究
(一) 史料类
南炳文在《历史教学》上发表专文,细致梳理了点校本《明史》中“申时行传”的史料源流,将有关申时行的11种传记资料进行了对比校勘,对传主的有关评价进行了分类和分析,“这些传记对申时行或仅记事迹不予评论,或极力歌颂,或予以肯定但行文平和,或虽以褒为主而批评用语亦有一定分量。而从问世时代分,则明代问世者大体持表扬歌颂态度,清代问世者则多半褒贬相兼且批评用语有一定的分量”[28]。文章作者还对申时行的籍贯、其子申用懋的任职经历等历史细节予以考订。该文史料精炼,立论扎实,考辨清晰,是研究申时行重要的基础性资料和指导性专论。
(二) 政治类
台湾学者林丽月在研究了万历朝党争与阁部冲突后认为,张居正去世后,继任首辅申时行通过与吏部尚书杨巍的密切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压制了言官势力的“野蛮生长”,但也造成了该群体与“政府”(内阁)之间的水火之势。同时她还指出,东林党人常常将君权的“绝对尊严”与内阁的“集权独制”对立起来,认为内阁的集权行为明显违反了明太祖的“祖制”,应当予以削弱,并还权于六部[29]。林丽月已经敏锐地发现了申时行执政对万历中后期政局的深远影响,但总体着墨不多,未能还原这个历史过程的动态细节。
刘莹莹、白燕斌的《试析万历朝首辅申时行的性格因素及成因》一文,主要从申时行个人性格的养成来分析他主政期间的政策得失[30]。研究认为,申时行的主要性格特征为“中庸且善良”“聪明但不张扬”“中庸并非无为”,并就此分析了影响其性格生成的主要因素是当时“文官集团”系统性格的具体表现、张居正身后被神宗严惩的余悸以及苏州区域文化的塑造等。总体而言,该文对申时行的评价和分析已经趋近于历史的真实,反映了当前学界对万历首辅申时行的研究定位重归理性、客观、公正的积极面向。但全文篇幅有限,文中关键性、探索性、建设性的论断缺乏强有力的论据支持,也没有进一步展开严密的论证,因此尚不足以支撑文中“他是功大于过的人,历史应该记住他的功绩”的观点。
何娅在刘莹莹、白燕斌的基础上进行了有益的拓展和探索。她认为,申时行“虽没有挽救明朝的衰败的气象,但稳定了张居正死后万历朝局,积极监督并运行了国家行政”[31]。何娅在文中探讨了申时行所面临的主要政治困局,尤其是内阁在中枢决策体制中始终缺乏“祖制”或“律法”的授权,无法独立、稳定地统筹中枢政务。这给申时行执政带来了巨大挑战,也是促成他形成无法“从道”、只得“从君”的政治态度的制度性原因。尽管如此,文章依然从“督促皇帝德行”“关心民生”“边防安全”“刑法人事”等方面总结、归纳了申时行积极、稳健的政治举措。该文尝试为申时行的政治行为寻找制度、政治、个人性格等多方面的深层次原因,但因篇幅所限均浅尝辄止,没有形成更具学理性的论述。
王宁在《政治无为和无为政治——晚明首辅申时行的主政特征》一文中认为,申时行的政治生涯平淡无奇,却能够在“儒家道统”的指导下,灵活运用“阴阳之道”,在君臣朝野之间折冲樽俎、中庸调和,在所谓的“政治无为”中彰显出“政治天分”[32]。但该文的主要问题在于:一是缺乏扎实有力的基础史料,论据、论点多转引自他人已有论著;二是行文表达不够严谨、规范,偏文学化;三是混淆了“道家”和“儒家道统”这两个基本学术概念,将“无为”思想误植入“儒家道统”,将“中庸思想”误解为圆滑世故、左右逢源。
张雪瑞另辟蹊径,以嘉靖四十一年(1562)壬戌科进士群体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对该群体中典型个案的分析,描摹出整个群体的时代特征。作者从政治、文化与经济等几个方面总结了该群体中的首要成员申时行的从政作为,但观点仍未跳脱往论之窠臼,依然认为“内阁首辅申时行以其‘中庸’的态度,周旋于各方,充当‘和事佬’的角色”[33]。
张鑫以“后张居正时期”中枢政局动态调整为观照,深入分析了申时行在履任内阁首辅后的政治行为,充分挖掘了他在皇权加持下对稳定当时朝局所发挥的积极作用[34]。同时,他还进一步提出了申时行以“传衣钵”的政治继承方式,将与自己政治理念相同,地缘、学缘相亲或资格、资历相近的官员遴选入阁,甚至传承首辅之位,进而确保了朝廷中枢的政务顺畅、政策延续和政局稳定。此论有力拓展并深化了对明代中后期内阁政治发展的内部律动及其相关个案的研究[35]。
同时,学界在论述“党派之争”“倒张运动”“国本之争”“辅臣子弟禁考案”等万历朝重大政治事件的过程中,也介绍了申时行作为内阁首辅的政治行为[36-38]。但总体而言,未能充分重视申时行在当时特殊情境下所持有的政治立场、所发挥的作用及其与当时朝野主要人物的互动,对其评价亦偏低。
(三) 思想类
日本“京都学派”代表人物宫崎市定在《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明代苏松地方の士大夫と民衆——明代史素描の试み)一文中分析“明代的政治和苏州”时认为,在当时的环境背景下,无论是经济界还是政治界,都已经走到了繁盛的尽头,显现出了无以遏制的衰败颓势,以申时行、王锡爵为代表的苏州士大夫在思想深处已经“先验地”对仕途宦情表现出了“恬淡”,自王锡爵之后的万历一朝,再无苏州人士入阁拜相。宫崎市定还认为,出自苏州的士大夫往往被“乡评”所束缚,为政做官者多数不敢肆意妄为,在他们看来,“与其说飞黄腾达做更大的官,毋宁说得到乡评的赞赏才是其本来的愿望”[39]。该文研究视角独特,尝试以区域文化、思想底蕴等内在因素分析申时行的政治抉择,颇具新意,对深化当前的申时行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国内香港学者朱鸿林在深入梳理申时行的经筵讲章后认为,申氏敬呈的讲章文法训雅,辞意豁达,与其谦逊温和、不激不亢的性格特征相契合。也正因此,申时行得以在“倒张运动”“争国本”等政治漩涡中保持与明神宗一定程度上的有效沟通[40]。此论基于对政局动态与学术思想的相互印证,从而丰富了申时行的历史形象。
复旦大学陈敏的《申时行及其〈书经讲义会编〉研究》是专题研究申时行政治思想理念的学术成果[41]。论文重点围绕申时行为明神宗经筵、日讲等教育活动编纂的讲章汇编——《书经讲义会编》,研究了申时行对儒家经典《尚书》的注解和阐释,表达了他对“德治”“勤政”“贤人政治”“君权神授”等政治概念的个性化认识,并试图藉此剖析申时行政治行为的思想根源。同时,论文还比较了申著《书经讲义会编》与另外两部书经研究经典——南宋蔡沈《书集传》与明初官修《书经大全》的旨趣异同,颇具开拓性意义。至于该文欠缺之处,诚如作者自己所言:一是将申时行政治思想的研究局限于对《书经讲义会编》的铺陈解读;二是对申时行阁僚、亲友的文集关注不足;三是对申时行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二者联系的分析“零敲碎打”,没有构建出“更有深度的结构完整的体系”。张鑫在陈敏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凝练了申著《书经讲义会编》的时代价值,认为“(该书)集中体现了他对儒家经典《尚书》的理解和阐释,也深刻反映出了他参与中国传统社会治国理政的思想渊源和价值基础”[42]。
(四) 军事类
张永强在《万历首辅申时行的边疆策略及其影响》一文中,通过列举申时行如何维持与蒙古鞑靼部封贡互市,处理云南陇川、四川松潘等地叛乱,以及选用边疆防务主将等具体史实,分析了申时行的边疆策略对明王朝国防政策制定的深远影响[43]。张永强既充分肯定了申时行在维护国家边境稳定、保证国内军事安全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也深入剖析了其边疆政策中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等因素。张永强认为,申时行对东北李成梁家族的政治庇护埋下了纵容建州女真部不断壮大、崛起的隐患。该文是目前学界率先研究和分析申时行军事及边疆策略的专文,具有一定的开拓性意义。但张文未能将申时行边疆策略的形成、制定和影响的全过程纳入当时朝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和边疆的整体形势中予以客观考察和全面分析,将部分边疆政策的偶然性、战术性失误归结为必然性、战略性失策,这样的观点难免偏颇。
(五) 家族类
李龙云以《申氏世谱》为中心,以申氏家族为研究视角,旨在通过对家族中继嗣现象的分类分析,进而揭示以申氏为代表的江南家族兴衰沉浮的一般性发展规律,分析导致家族内部与家族之间微妙关系的深层次原因。作者通过严谨、细致的整理考订,不仅系统阐述了申氏家族自申时行以来的发展脉络,还精心绘制了大量表明申氏家族关系建构的图表,并明确指出了申氏家族通过科举仕宦、义庄经济、婚姻交往、子嗣过继等方式,维系了自身在苏州地区绵延400余年的发展存续。该文为申氏家族研究提供了新方向,为明代江南地区家族史研究增添了经典个案[44]。
申友良与申东宁合作的《申氏家族与科举考试》一文梳理了申氏家族在中国古代科举社会中的发展和传承[45]。文章同时还重点分析了申时行高中状元、官至首辅的政治仕途对申氏家族产生的重要影响和巨大作用。虽然该文原创性内容不多,多数结论依靠转述他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但拓展了学界对申时行及其家族的研究领域。
(六) 文艺类
程宗骏的《明申相府戏厅家班考》《明申相府戏厅、戏班与李玉出身初探》两文,首开申时行与戏曲文化关联研究之先河[46-47]。前文主要是从申时行府上戏班的构成、等级、规模和演出作品等方面展开论述。后文则在前文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申相府宅邸的具体位置、府内戏班的内部构成和表演曲目,介绍了申府戏班由“小班”到“梨园班”再到“中班”的发展轨迹;同时,该文还考证、辨析了明清之际著名剧作家李玉的身世和作品,厘清了李玉并非申氏族人而是其家中仆人之子的真实身份。刘志强则在《明清“申氏家班”闻名吴中之原因探析》一文中发掘了申时行对昆曲的实践及理论的精湛见解和特殊贡献,并认为申时行通过自身“端拱静默”的个人特质促进了昆曲艺术的“雅化”,影响了当时昆曲演员的表演风格[48]。这些论著不仅使申时行的历史形象趋于饱满,也为学界全面研究申时行提供了多元视角。
杨晶在研究分析申时行书法册页的笔法和内容后,不仅高度肯定了他的书法造诣和家国情怀,还特别指出,“当时的书风、世风、士风、文风紧密相联,申时行自觉秉承传统文人的精神品质,又受到晚明商品社会的影响,还有江浙地域文化的影响。几者结合,他务实清醒,内蕴刚劲,外见平和,但因过于谨慎小心,又显得保守有余”[49]。其角度和观点颇有见地。
朱焱炜在其博士论文《明清苏州状元文学研究》中,用整整一章的篇幅介绍了申时行的生平事迹、为人处世、主要著作及其与曲艺文化的关系等内容,其中申时行的文学成就是全章的论述重点。该文有力佐证了其核心观点,即明清时期的苏州状元文学属于典型的“官人文学”“应试文学”,它是“服务于礼文化传统的,以明道、载道、传道为己任,所以以尚用为要”,同时注重阐发四书五经所承载的道德思想[50]。
罗宗强在《隆庆、万历初当政者的文学观念》一文中同样专门介绍了申时行的文学成就[51]。作者认为,申时行在徐阶、高拱、张居正等4位著名内阁首辅中,诗为最多且诗为最好,“实在是一位甚具诗才的人”。该文还介绍了申时行不同阶段的诗文创作意境和背景,也明确指出了申时行“重道而轻文”,经常批评当时繁词之弊端,认为朝廷科举取士更应该“重应用而轻文艺”。
三、 余论
综上可见,近50年关于明代首辅申时行的研究成果总体数量虽然不多,但呈现出研究领域的外延不断拓展,研究方法趋于多元,有理论、有深度的论著频出等可喜现象,特别是不少学者开始有意识地运用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理论开展跨学科研究。当然,学界有关申时行的研究还存在一定提升空间:
一是应加快对申时行个人著述的系统整理和研究。申氏存世的个人著述约计80余卷,其中包括《赐闲堂集》40卷、《书经讲义会编》12卷、《外制草》10卷、《纶扉简牍》10卷、《纶扉奏草》4卷、《纶扉笥草》4卷、《升储汇录》2卷、《召对录》1卷。这些文献极具史料价值,是管窥明代中后期政局变迁的第一手资料。由其主编的226卷《明会典》更是研究明代典章制度的皇皇巨著,蕴涵了申时行丰富而深刻的政治思想。因此,有必要对这些思想理论资源进行进一步的整理和研究。
二是应形成对申时行真实历史作用及地位的客观评价。应以申氏内阁为样本,通过官修起居注、实录、档案等史料与时人著述的对照、交互论证,揭示内阁在明代中后期的发展轨迹、内部律动、性质功能等方面的动态演变过程,再结合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律法等多重维度,充分探讨申时行及其内阁在明代中枢辅政体制中的真实地位和实际作用,最终呈现出一个相对全面、客观的明代历史人物研究成果,形成更加理性、科学的定位和评价。
三是应持续推动对万历朝历史的研究。应在申时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透视万历朝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在深度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和时代意义,深入研究申氏宗族与苏州文化的关系,建议适时成立相关研究会,提升对江南区域文化及相关代表人物的研究水平,扩大学术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