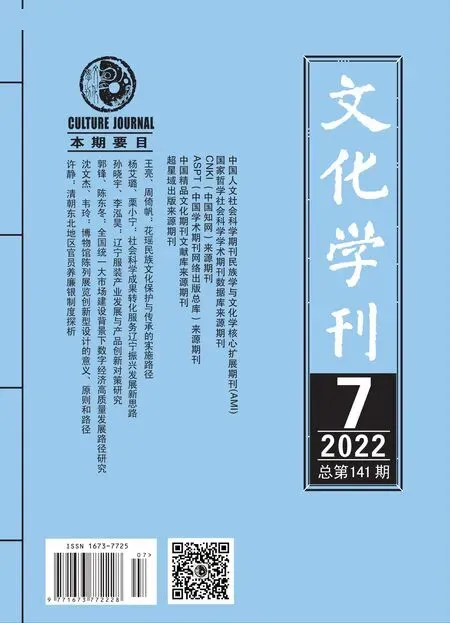身份、创伤与离散人群:一个世界主义视域下的《灼痕》解读
何 琦
一、引言
近年来,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在全球化语境下被越来越多的学者用来重新解读文学作品中人物的性别、身份等问题。政治哲学家奎迈·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提出世界主义的伦理原则,他强调在处理国与国之间,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时必须认识并尊重彼此的差异,使之可以超越血缘关系或民族主义的身份进行对话。阿皮亚主张世界主义应关注每个个体的“种族身份”“文化身份”和“伦理身份”这三种具体身份及其在具体身份下的个性[1],这为文学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
巴基斯坦裔的英籍作家卡米拉·夏姆斯(Kamila Shamsie)是一位具有人性关怀的世界公民(cosmopolitan)。她出生在巴基斯坦卡拉奇的一个写作世家,她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在美国、巴基斯坦、英国这三个国家生活,最终于2014年加入英国国籍后在伦敦安定下来。夏姆斯迄今为止一共发表了7部小说,其中多部小说获得文学大奖,她的作品已被翻译成20种文字,畅销世界各国。虽是族裔作家,但她的作品不仅体现了对本民族的关心,更融入了对全世界、全人类的关心。
夏姆斯于2009年发表的第五部小说《灼痕》(Burnt Shadows)[2]最能体现她的世界主义思考。小说的地点设定和主要人物的经历都有明显的世界性,这部小说以一名叫田中·裕子(Hiroko Tanaka)的日本女子为主线,讲述两个移民家庭三代人之间关于爱情与战争的故事。本文将借助阿皮亚的世界主义理论来解读夏姆斯《灼痕》中的世界主义倾向,关注夏姆斯如何通过小说主人公裕子及身边人的人生经历来体现离散群体(diasporas)在经历战争的创伤后如何抛弃民族性的身份,逐渐在全球化时代构建世界公民的身份,同时分析夏姆斯如何以一位世界主义作家的责任感反对战争,尤其反对以维护狭隘的民族主义为名义发动的反恐战争,呼吁人们对经历战争创伤的个体给予人性关怀。
二、主人公的世界主义身份
夏姆斯的世界主义思想在《灼痕》的主人公裕子的身份认同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裕子世界公民身份的建立源自每一次战争之后的被迫移居。她第一次离开自己的祖国日本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她失去了所爱之人——她的父亲和未婚夫,并在她后背留下了永远的伤痕——核爆炸那天她所穿的和服上鸟的图案。战后,她离开日本去印度德里投奔未婚夫同父异母的妹妹。从离开日本起她不得不抛弃她的民族身份,“事实上,她已经成为神话中的人物。这个人物失去了一切,在血泊中重生。在故事中,这些人物总是被简化为一个单一的元素:复仇或正义。所有其他的个性和过去的身份都被甩掉了”。在印度,裕子和信仰穆斯林的印度人萨贾德 (Sajjad)结婚,之后因为印巴分裂战争被迫从德里搬去卡拉奇。尽管凭借超高的语言天赋,裕子很快学会了乌尔都语,但她很清楚“在巴基斯坦她将永远是个外国人”。在丈夫死后,随着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逐渐紧张,她最终选择去纽约定居,在那里她以为自己会找到熟悉的感觉,因为在她看来,纽约是一个有着多元文化的城市。然而这种幻想在她见识了“9·11事件”之后的美国民族沙文主义而破灭。
皮亚杰认为,个体不需要放弃所属的国家或民族的身份来构建世界主义的身份。也就是说,一个人既可以保持对自己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也可以从普世价值或全球认同中建立自己的身份,并且人的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始终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因而一个人的身份可以是多重的。在异乡生活的裕子通过母语来保持自己的民族身份。她在家里与儿子拉扎(Raza)说日语,会因在卡拉奇遇到其他日本妻子并能参加她们每周的聚会时感到兴奋不已。在她看来“保证每周有一个晚上坐下来用日语大笑,这比她想象的要重要得多”。母语对身处陌生的他乡的人们来说是少数可以留住的对故土的熟悉和亲切感。在一次交谈中,裕子坦言自己对熟悉感的怀念:“我想听听日语。我想品尝我所理解的茶该有的味道。我想看起来像我周围的人一样……”。借此,夏姆斯想表达的是多语能力无法抚慰离散群体对熟悉的渴望和对家乡的渴望,这种渴望只能通过说母语来获得,因为“没有语言是在真空中使用的; 对说母语的人而言,它带有自己的更广泛的文化内涵”[3]。因此,像裕子这样生活在异国他乡的离散群体,他们想要通过说母语保留的是语言背后的民族身份和文化身份,他们追寻的是对已经离开的国家的文化和情感认同。
然而,在构建世界主义身份的过程中,裕子在一次次的迁移中不得不反复面临自己作为外国人的身份处境(foreignness)。渐渐地,这种“外国人”的身份成了她“唯一的身份和归属感”[4]。正如小说中某个和裕子有着相似异国居住经历的人物坦言:“我对‘外国人’这一身份很自在”。虽然离散群体大多掌握多种语言,语言能力可以帮助他们跨越地缘政治的边界,但有时他们不得不面临“处理现实和虚拟边界”的挑战[5]。离散群体在异国面临的挑战和压力是“无法通过融入一个新的民族群体来治愈的”[6]。与此同时,瞬息万变的国际关系和频繁的迁移使得他们早已习惯了看似永恒不变的民族的、国家的脆弱性,也使他们习惯了归属感的脆弱性。因此,裕子“没有兴趣归属于像一个国家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缺乏实质而有带有破坏性的事物”。像裕子这样的离散人群正是因为意识到民族主义的归属感有局限性,因此他们更倾向于成为世界公民。
裕子的世界公民意识还体现在她对个体的人性关怀。尽管历经磨难,裕子始终向她身边的人表现出善意。这种善意使她能在战争面前抛去狭隘的民族主义而保持人性的关怀。1945年在目睹了战争的残酷性之后,她仍能接受在东京给美国人当翻译的工作,因为她不把核爆怪罪于任何人。这是她对人性和世界的善意,但当她听到一个美国人说“这场爆炸救了美国人的命”之后却毅然决然地辞职,因为她意识到这个“民族的势利”,也第一次意识到战争带有民族归属感的邪恶目的,这种民族主义会凌驾于个体的人性之上。裕子一直不认为仅仅因为战争使她失去了亲人和同胞就给她造成了创伤,因为在她看来,战争造成的是一种更大规模的对人性的创伤。正是这种认识,促使她在面临身份危机时选择了世界性身份,这种身份使得她坚持道德行为和对他人的责任,并谴责以国家或民族或普遍善意的名义获得政治利益的服务。正因为出于对人性的关怀,所以在美国裕子能无偿帮助一名阿富汗非法移民制订通过进入加拿大边境秘密返回阿富汗的计划。在皮亚杰看来,对具体身份之下个体的关怀是人性可以回归的前提。从这一点看,夏姆斯的《灼痕》体现了她对具体人性的关注,也展示了她的世界主义思想。
三、对战争的世界主义批判
阿皮亚的世界主义构想有两个重点:1.尊重个体的价值观,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2.善待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这两个重点贯串夏姆斯的《灼痕》。夏姆斯反战的态度通过描绘主人公裕子及儿子的沉痛经历来表达。对裕子来说,“被爆者(hibakusha)”这个词是她最痛恨的,也是最有杀伤力的一个词,甚至比她背上的灼痕更难受。核爆之后,为了逃避“被爆者”这个词,裕子登上了一艘前往印度的船,“进入一个她一无所知的世界”。迫使她离开的是对战争造成的失去(reduction)的恐惧,而不是对新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当她一到达新的地方,“她就开始感觉到“被爆者”这个词已经开始吞噬她的生活。” 尽管身体上的伤痕可以通过衣物来掩盖,但“被爆者”这个词时刻提醒着她身体上的创伤。即使会说多种语言,她也找不到任何语言来描述战争的创伤。裕子坦言战争使她没有了归属感,她不属于任何世界,甚至不属于她自己的世界。她的长崎对她来说比德里更陌生,她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我那天的家更陌生了。那个不可描述的日子。一言难尽。我不知道任何语言的单词可以形容……”。为了避免成为“被爆者”,她终其一生都在跨越不同的国界来划清战争给她的身份,并以沉默和回避的态度来处理战争造成的创伤。她“从未告诉任何人她背上的鸟”,并谎称“虽然她在[长崎]长大,但炸弹落下时她在东京”。为了避免成为“被爆者”,她终其一生都在跨越不同的国界来划清战争给她的身份。然而,被爆者受到的创伤甚至会传给下一代、下下一代。裕子和萨贾德结婚第一年,她在怀孕五个月时流产了,裕子认为是爆炸造成的流产。就连裕子的儿子也得承受战争的创伤。出于对战争造成的后遗症的恐惧,拉扎的女友不愿意嫁给他,她的解释是:“除非他们实在没办法了,否则没有人会把他们的女儿嫁给你,拉扎,你可能会畸形的。我看过原子弹后在长崎出生的婴儿照片。”
夏姆斯反战的态度还体现在她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长期存在的权力滥用行为的谴责。在接受采访时,夏姆斯指出她的故事以民族国家开始和结束,她想让读者关注这些民主国家以自卫的名义都做了什么。她说“当人们说——而且很多人这样说——我的小说以长崎轰炸开始,以9·11事件结束时,我仍然感到非常恼火。 它以反恐战争结束。 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7]。这意味着夏姆斯始终批判的是美国在不同的历史事件中扮演的角色。
小说的开篇一个身穿枷锁、被扒光了衣服,即将被套上橘黄色囚服的身份不明的男人喃喃自语着:“怎么会变成这样呢?”此后,夏姆斯通过多个主要人物来回应这个反问。失去了爱人的裕子在1945年8月的长崎想知道“爱怎么就消失了呢?”萨贾德在1947年印巴分离战争期间曾绝望地问自己“我在坚持什么?我是一只飘荡在空中的风筝而已”。就连相信美国的绝对爱国主义者金(Kim)也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的纽约问了同样的问题“外面的世界怎么了?”直到小说的最后,夏姆斯才隐约地告诉读者开篇那个身着橘黄色囚服的陌生男人是裕子的儿子拉扎,而他所处的监狱是位于古巴的关塔那摩。这些反问将小说的叙述往前推进,同时也将这些问题来回拽了大约六十年。夏姆斯通过这样的情节安排强调,在看待造成全球分歧的近期事件时,需要分析背后更广泛的历史背景。
夏姆斯非常巧妙地将不同时期的日本和阿富汗联系在一起,通过裕子和拉扎两代人的经历反映了离散个体的个人命运在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中面临的不确定性。“9·11事件”后,道德价值观、个人关系和集体纽带更进一步地重申民族归属感和公民身份的边界。像拉扎这样的离散个体不可能再有他父母那代人所拥有的行动自由了。随着岁月的流逝,像裕子及拉扎这样的离散群体在“带有民族主义的全球权力斗争中所受的创伤甚至牺牲都将逐渐被世人遗忘”[8],只留下无处安放且不知该如何表达的愤怒。
四、结语
夏姆斯《灼痕》以长崎轰炸开始,以阿富汗反恐战争结束。她想让读者关注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国家都以自卫的名义对每个生命做了什么。民族主义者眼里的大局让无数无辜的普通人成为了战争的牺牲品。经历战争创伤的离散群体意识到了民族主义的归属感的局限性,逐渐在全球化时代构建世界公民的身份,但战争造成的身份危机和心理创伤是无法通过跨越边界的行为来解决的。夏姆斯以一位世界主义作家的责任感反对战争,尤其反对以维护狭隘的民族主义为名义发动的战争,呼吁人们尊重个体的种族身份、文化身份和作为人的伦理身份,从人性关怀的角度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