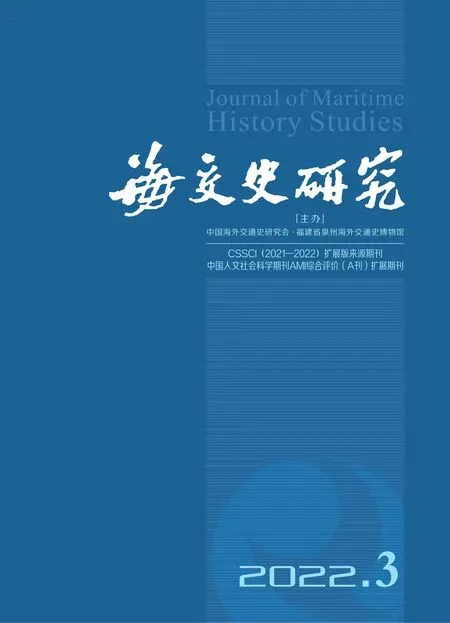九世纪中后期中日间的僧商互动*
——以《风藻饯言集》与“唐人书简”为中心
李怡文
自公元839年(唐开成四年,日本承和六年)最后一批日本遣唐使离开中国后,中日之间的官方外交往来趋于停滞,但同时也为更多的群体提供了参与东亚海域交流的机会与空间。已有学者指出,“整个9世纪可以看作古代东亚贸易史的转折期或过渡期”“9世纪东亚世界由朝贡贸易时代向商人时代过渡是最大的特点”。(1)冯立君:《唐朝与东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55页。关于遣唐使的终止,可参见王勇:《唐から見た遣唐使:混血児たちの大唐帝国》,东京:讲谈社,1998年,第243—254页。
9世纪中后期的短短几十年,在中日交流中实则为奠定、开拓之后数个世纪发展模式的关键时期。海上商人,特别是来自唐朝商人,在东亚海域中有显著增加。学者们认为这是由当时日本和新罗之间的紧张关系所导致。(2)相关研究参见黄约瑟:《“大唐商人”李延孝与九世纪中日关系》,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第47—60页;吴玲:《九世纪唐日贸易中的东亚商人群》,载《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17—23页。求法僧侣是当时频繁往来中日之间的另一重要群体,且他们与海商群体多有互动。僧侣乘坐商船渡海,商人受僧侣所托购买经书或传递信件等。(3)代表研究参见榎本涉:《僧侶と海商たちの東シナ海》,东京:讲谈社,2010年;姚潇鸫:《真言宗僧人入华与9世纪中叶后的唐日佛教交流》,载《古代文明》第12卷(2018)第4期,第99—108页。虽然海商与僧侣之间的互动已为学者在研究中所提及,但海商与僧侣之间的密切交往是否有更深层的原因?特别是,看似总在为僧侣服务的海商,可以从帮助僧侣中获得怎样的益处?
本文以《风藻饯言集》与“唐人书简”这两种特殊史料为中心,深入分析9世纪中后期在中日间往返的僧侣与海商之间的交往,力图呈现出当时这两个群体合作互动的基本模式与深层原因。《风藻饯言集》与“唐人书简”均收入由唐海商写给僧侣的信件或诗,为此提供了难得的海商视角。并且,这两种史料恰好都聚焦于9世纪中后期这一东亚海域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其中涉及的人物关系网络又有重合之处,值得进行一并考察。
目前为止,已有学者对《风藻饯言集》或“唐人书简”进行过一定的介绍、利用与分析。(4)中文学界对于《风藻饯言集》的主要研究包括:石晓军:《日本园城寺(三井寺)藏唐人诗文尺牍校证》,载《唐研究》第8卷(2002),第109—142页;白化文、李鼎霞校注:《〈风藻饯言集〉校注》,收于[日]圆珍著,白化文、李鼎霞校注:《行历抄校注》,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47—270页。对于“唐人书简”的主要研究参见吴玲:《〈高野杂笔集〉所收唐商徐公祐书简》,载《文献》2012年第3期,第115—121页。不过在史料层面,一些细节如个别事件发生的时间及书信写作的时间、顺序仍值得进一步梳理。在厘清史料细节的基础上,本文还将着重强调加入佛教网络带给海商的收益,以此呈现海商与僧侣密切互动背后的重要驱动力,同时将进一步阐释这一在9世纪中后期发展起来的模式,如何为以后数世纪的中日交流起到奠基作用。
一、《风藻饯言集》中所见入唐日僧圆珍与唐海商集团
《风藻饯言集》是1767年由日本园城寺僧人敬光收集唐人写给日僧圆珍(814—891)的诗文而成。(5)[日]敬光:《〈风藻饯言集〉序》,载《〈风藻饯言集〉校注》,第250—251页。日本延历寺僧侣圆珍于公元853年(唐大中七年,日本仁寿三年)乘坐海商船舶入唐,在唐逗留五年,于858年再度乘商船归日。与留下了知名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日僧圆仁(794—864)一样,圆珍在唐期间同样记有日记,可惜全本已不存。现存的圆珍入唐日记《行历抄》,部分条目由多种史料复原整理而得。(6)[日]圆珍著,白化文、李鼎霞校注:《行历抄校注》,前言第3—4页。《风藻饯言集》中共包含诗16首及书信7封,大多写于858年圆珍返回日本之后数年内,且绝大多数出自唐海商之笔。《风藻饯言集》的留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可以窥探9世纪中后期僧侣与海商互动的真实情境的窗口。同时,由于圆珍在唐行经各地所获得的公验、过所等文件多被保存,再加上他的日记、传记的相关资料,我们得以较为完整地复原圆珍与海商们在不同阶段的交往,以及其关系网络的形成、维系、扩展的过程。
《风藻饯言集》与圆珍的入唐日记及其在唐获得的文件显示,圆珍与一个定期往返于中日之间的海商集团保持了长期而紧密的联系。此集团中的主要人物包括船主李延孝、海商詹景全、李达、蔡辅。圆珍与船主李延孝的结识很可能源于他于853年乘坐李延孝的商船赴唐,而詹景全和李达似长期与李延孝合作,搭乘他的商船渡海,圆珍也因此与这一海商集团熟稔。在圆珍决意入唐求法之时,日本派遣遣唐使一事已趋停滞,故圆珍赴九州大宰府等待商船入唐。(7)[日]佐伯有清:《円珍》,东京:吉川弘文馆,1990年,第43—72页。关于圆珍乘坐何人的商船入唐一事,史料记载中有所分歧。黄约瑟对此点已有考证:他指出许多传记中误记圆珍乘坐新罗人钦良晖的船入唐,而实际上圆珍虽可能852年在九州见到了钦船,但并未登船。(8)黄约瑟:《“大唐商人”李延孝与九世纪中日关系》,第51页。圆珍在大宰府获发的《入唐公验》指其“为巡礼,共大唐商客王超、李延孝等”赴唐,而其在中国福州登陆时获发的公验中亦提及圆珍的一位随从将“随李延孝船归本国、报平安”,再次印证圆珍一行确实乘坐李延孝的船入唐。(9)《入唐公验》《福州都督府公验》,收于白化文、李鼎霞校注:《行历抄校注》,第97—98页。
圆珍在唐五年,其中将近三年在天台山国清寺停留,余下时间他还游历长安,造访洛阳龙门等。(10)[日]佐伯有清:《円珍》,第73—165页;介永强:《日本僧人圆珍入唐求法活动摭谈》,载介永强著:《隋唐佛教文化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240—249页。唐大中十年(856)六月,圆珍在游历之后回到国清寺,并捐资修国清寺大佛殿等。在圆珍回到国清寺后数月,李延孝与詹景全一行人也再次从日本回到中国,并到达了国清寺。据圆珍在写于唐大中十二年(858)的《乞台州公验状》所述,因为日本天台宗祖师最澄在入唐时捐资所建的院舍已毁于会昌灭佛期间,“越州商人詹景全、刘仕献,渤海国商主李延孝、英觉等”“施钱四十千文,造住房三间,备后来学法僧侣”。(11)[日]圆珍:《乞台州公验状》,收于《行历抄校注》,第107页。同参见 [日]三善清行著,白化文、李鼎霞校注:《〈天台宗延历寺座主圆珍传〉校注》,收于《行历抄校注》,第160页。
圆珍或许在乘船入唐时就已与李延孝等人商定,求法后再搭乘李船返回日本。所以856年圆珍游历之后又回到国清寺长住,并且等到了李延孝一行人的到来。858年圆珍携带着在唐朝求得的上千卷经文,乘李延孝的船回到日本,同船还有日后与圆珍交往愈发密切的詹景全、李达等人。
圆珍在日本天安二年(858)六月抵达九州太宰府。詹景全等商人按规定入住博多湾附近的鸿胪馆,而圆珍在附近的寺院等待入京召见。文德天皇在八月十四日即召圆珍入京,但可惜文德天皇在八月二十七日逝世,圆珍则需要在九州等新任天皇再发诏敕。(12)[日]三善清行著,白化文、李鼎霞校注:《〈天台宗延历寺座主圆珍传〉校注》,第165页。在这一段等候的时间中,圆珍与逗留在鸿胪馆的海商往来频仍,《风藻饯言集》中收录的许多诗文即作于这一段时间。
比如,《风藻饯言集》中收入的第一首诗,署名“高奉”所作的《昨日鸿胪北馆门楼游行一绝》即描绘了当时圆珍到鸿胪馆与海商们聚会的情景。“鸿胪门楼掩海生,四邻观望散人情。遇然圣梨游上嬉,一杯仙药奉云青。”(13)石晓军:《日本园城寺(三井寺)藏唐人诗文尺牍校证》,第114页。同可参见 [日]敬光辑,白化文、李鼎霞校注:《〈风藻饯言集〉校注》,收于《行历抄校注》,第251—252页。石晓军已对这首诗进行了详细的校证。这首诗的作者高奉虽未见其他史籍记载,但应为当时往返于中日之间的海商,与圆珍等人一齐乘坐李延孝的船于858年到达日本。诗中提及圆珍时不时会到鸿胪馆,与海商们相聚饮茶。由《风藻饯言集》中其他诗可见,圆珍还会与海商们进行诗文唱和。高奉另有一首诗题为《今月十二日得上人忆天台诗韵和前奉上》,显然是与圆珍唱和之作。(14)石晓军:《日本园城寺(三井寺)藏唐人诗文尺牍校证》,第119页;[日]敬光辑,白化文、李鼎霞校注:《〈风藻饯言集〉校注》,第256页。一起同船抵达鸿胪馆的唐商李达、詹景全、蔡辅也都有对圆珍思忆天台诗作的唱和。(15)石晓军:《日本园城寺(三井寺)藏唐人诗文尺牍校证》,第120—121、124页;[日]敬光辑,白化文、李鼎霞校注:《〈风藻饯言集〉校注》,第257—261页。此外,《风藻饯言集》中还收有詹景全于858年10月11日写给圆珍的一封短笺,邀请圆珍及其弟子到鸿胪馆一起用餐,再次说明那段期间圆珍与这群海商在九州的密切往来。(16)石晓军:《日本园城寺(三井寺)藏唐人诗文尺牍校证》,第127页;[日]敬光辑,白化文、李鼎霞校注:《〈风藻饯言集〉校注》,第262—263页。
圆珍在858年底获召进京。据其传记所载,他于第二年正月十六日获得召见,而其从唐朝带回的两部大曼荼罗像也被呈上御览。(17)[日]三善清行著,白化文、李鼎霞校注:《〈天台宗延历寺座主圆珍传〉校注》,第165页。圆珍的入唐经历,显然在僧俗两界都增加了很高的声望。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858年回到日本后,虽然圆珍未曾再往中国,但借助他在入唐行历中结识的海商集团,圆珍在归国后数十年依然得以保持与中国的联系。
詹景全与李达两人就长期担任圆珍的信使,他们为圆珍送信、购买经书,也负责在圆珍与中国的僧侣间传递礼物。例如,867年詹景全就受温州内道场供奉德圆所托,带给圆珍两铺巨幅净土变。圆珍在唐期间曾面见德圆,欲求灵像,又忧虑无法将众多经书物品一并带回日本,故有数年后詹景全带回净土变一事。(18)[日]三善清行著,白化文、李鼎霞校注:《〈天台宗延历寺座主圆珍传〉校注》,第175页。《风藻饯言集》中收有一封台州开元寺僧常雅写给圆珍的书信,提到从“詹四郎”手中收到来自圆珍的消息与作为礼物的四斤水银,并又托詹四郎带回天台山茶作为回礼。“詹四郎”极有可能就是指詹景全。常雅的信未属日期,不过根据信中的言语及詹景全的动向,日本学者小野胜年推测该信最有可能写于863至867年之间,石晓军也认同这一推测。(19)石晓军:《日本园城寺(三井寺)藏唐人诗文尺牍校证》,第132—133页。
以詹景全、李达、李延孝为中心的海商集团,在长达数十年间频繁往来中日之间。882年圆珍写给唐高僧智慧轮(又名般若斫迦)一封书信,其中清晰体现了这些海商在维系圆珍与唐朝僧侣的往来、推进中日交流中所起的作用。(20)关于智慧轮的研究,可参见Chen Jinhua, “A Chinese Monk under a ‘Barbarian’ Mask: Zhihuilun (?-876) and Late Tang Esoteric Buddhism”,T’oung Pao, Vol.99-1, No.3, 2013, pp.88-139.该文的中文译文版为陈金华:《“胡僧”面具下的中土僧人:智慧轮(?-876)与晚唐密教》,载《汉语佛学评论(第四辑)》(2014),第181—223页。圆珍曾于唐大中九年(855)冬至日在唐长安的大兴善寺见到智慧轮,并“咨承两部大曼荼罗教秘旨”等。(21)[日]三善清行著,白化文、李鼎霞校注:《〈天台宗延历寺座主圆珍传〉校注》,第144—145页。由圆珍这封写于882年的《上智慧轮三藏书》可知,智慧轮曾于唐咸通二年(861)赠予圆珍的八本经书,很可能是托詹景全带回,而收到经书的圆珍即请詹景全于863年送回信给智慧轮。可惜次年詹景全归日本告知圆珍,由于当时中国北方出现交通阻隔,他未能前往长安送信给智慧轮。(22)[日]圆珍:《上智慧轮三藏书》,收于《行历抄校注》,第88—94页。由于詹景全第二年启程回唐比以往早,圆珍未及再次付信给詹景全。而在877年,詹景全再次搭乘李延孝的船从唐前往日本,同船还有逗留唐朝近四十年的日僧圆载(?-877),而该船不幸遭遇海难,詹景全、李延孝及圆载均因此罹难。
李达当时也同在遭遇海难的船上,不过他侥幸得救。882年,正是李达要作为圆珍的信使,送信给智慧轮。(23)黄约瑟在《大唐商人李延孝与中日关系》一文中以为李达与詹景全一同遇难 (见黄约瑟文第56页),但实际并非如此。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想请智慧轮赐《大毗卢遮那经义释》的正本,因日本收藏的这种经书有文句欠缺之处,而圆珍曾在855年面见智慧轮时见到该经书的正本,“铭心不忘”,特地写信相求。圆珍随信附上了50小两砂金,部分作为抄写法文之资。可惜的是,圆珍这封信应无法递交到智慧轮手中,因为据学者考证,智慧轮很可能在圆珍写信的数年前即876年就已圆寂。(24)陈金华:《“胡僧”面具下的中土僧人:智慧轮(?-876)与晚唐密教》,第188、193页。
这封《上智慧轮三藏书》呈现出李延孝、詹景全与李达这一海商集团维持了至少长达二十余年的合作。从圆珍在853年登船前往中国开始,到877年李延孝、詹景全遇难,这一海商团体频繁往返中日之间。正因为他们之间合作稳定、往返基本有定期,所以他们成为了圆珍可以信赖并依靠的、与唐朝沟通的管道。
从圆珍与詹景全、李达诸人的互动中,主要可见的是海商为僧侣提供帮助。不过,海商其实也有试图利用僧侣为自己谋利益的情况。在《风藻饯言集》中,有数首诗署名“大唐容管道衙前散将蔡辅”。石晓军已对蔡辅身份进行辨析,指出蔡辅可能只是在赴日本前在位于岭南的容管经略使或观察使的幕府中任过闲职。由于这很可能是蔡辅在仕途中达到的最高级别,所以他即使赴日贸易时仍念念不忘在姓名前署上该头衔。(25)石晓军:《日本园城寺(三井寺)藏唐人诗文尺牍校证》,第117—118页。《风藻饯言集》中收录的蔡辅的诗大部分被归为“送别诗”,应是写于圆珍在858年底启程上京之际。比如《大德归京敢奉送别诗四首》中,其一写道:“鸿胪去京三千里,一骑萧条骏若飞。执手叮咛深惜别,龙门早达更须归。”(26)石晓军:《日本园城寺(三井寺)藏唐人诗文尺牍校证》,第117页;《〈风藻饯言集〉校注》,第253页。蔡辅在《风藻饯言集》中诗作最多,不过数首送别诗的诗句程式化明显,并且858年后再未见他与圆珍的互动记载,很难推断他与圆珍的情谊是否如诗中所描绘一般深厚。
蔡辅所作的诗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首未被《风藻饯言集》所收录之作。这首诗题为《唐国进仙人益国带腰及货物诗一首》。经石晓军校证后的内容如下:“大唐仙货进新天,春草初生花叶鲜。料知今□(朝?)随日长,唐家进寿一□(千?)年”。落款是“时天安二年十月廿一日大唐容管道衙前散将 蔡辅鸿胪馆书进献谨上”。(27)石晓军:《日本园城寺(三井寺)藏唐人诗文尺牍校证》,第126页。日本学者小野胜年将此诗归入“唐人送别诗”,白化文、李鼎霞的《〈行历抄〉校注》中依样收录。(28)[日]小野胜年:《入唐求法行歷の研究—智證大師円珍篇·下》,京都:法藏馆,1982年,第387页。[日]敬光辑,白化文、李鼎霞校注:《〈风藻饯言集〉校注》,第270页。不过,我认为这首诗并非是写给圆珍的送别诗,而是蔡辅托圆珍呈给新即位的清河天皇的诗。这首诗从内容上而言,并未包含送别之意,反而是可以理解为蔡辅向新天皇呈送了一些物品,并由此表达祝贺与敬意。诗句中的“春草初生花叶鲜”,白化文与李鼎霞的校注中推测可能是指腰带上的图案。我认为这句应恰与前一句“仙货”相呼应,很可能是指草药等药材。当时药材是中日贸易中的常见物品,也很受日本贵族欢迎。而这首诗的落款也比其他蔡辅的诗更为正式,尤其是其他的诗都未曾特别提及诗作于“鸿胪馆”,因为这一信息圆珍十分清楚,并且落款中的“进献”也未出现在其他诗作落款中。同时,这首诗最初并未被园城寺僧敬光收于《风藻饯言集》,也可能恰是因为这本不是写给圆珍的诗作。
蔡辅托圆珍代为向日本新即位天皇呈送诗作与礼物这一举动,恰反映出了海商与僧侣互动中的另一个面向,即海商在条件适当的时候也会寻求僧侣的帮助,并且通常是借助僧侣的社会资源及其与上层权贵人士的联系。时时不忘以“大唐容管道衙前散将”自居的蔡辅,想必会十分期待在新天皇面前留下些许印象,而被召入京面见天皇的圆珍恰好成为难得的、可以联通日本上层人士的纽带。现存史料中没有痕迹可表明蔡辅的这一尝试的后续如何。不过,另有同一时期其他以海商为中心的材料,更为清晰地展示出了海商们如何着意培养与僧侣们的关系,以期在中日贸易中换取一定的便利。
二、“唐人书简”中所见的渡日唐僧义空与徐氏兄弟
被学界通称为“唐人书简”的这一组史料为18封写于9世纪中叶的唐人书信。这18封书信最初附于著名日僧空海的书信集《高野杂笔集》下卷末尾,主要是由唐代僧侣和唐海商写给一名渡日唐僧义空的书信。因为这组书信提供了宝贵的、从海商视角研究9世纪中后期中日贸易的史料,近些年受到中日学者的关注。中文研究中对这组材料进行了重点关注的主要是吴玲的《〈高野杂笔集〉所收唐商徐公祐书简》。(29)吴玲:《〈高野杂笔集〉所收唐商徐公祐书简》,第115—121页。在日文研究中,高木訷元、田中史生等学者均对这组书简进行了校证,特别是田中史生对书简所写年份进行了有力推断。(30)[日]高木訷元:《唐僧義空の來朝をめぐる諸問題》,载《空海思想の書誌的研究 高木訷元著作集4》,京都:法藏馆,1990年,第357—409页;[日]田中史生:《唐人の对日交易——〈高野雜筆集〉下卷所收〈唐人書簡〉の分析から》,载《国際交易と古代日本》,东京:吉川弘文馆,2012年,第153—188页。本文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发掘阐释这组书简中的信息,并由此呈现9世纪中后期中日交流中海商与僧侣的合作互动模式。
这一组书信的收信人义空,是师从杭州海昌院齐安国师的一名禅宗和尚。(31)义空的略传可参见[日]虎關師鍊:《元亨釈書》卷6,《唐国義空》,载《国史大系·第十四卷》,东京:经济杂志社,1901年,第729—730页。据高木訷元考证,唐会昌元年(841),日僧慧萼受当时日本皇太后橘嘉智子所托,入唐邀请得道禅僧回日本传道,而齐安国师推荐了自己的弟子义空。义空遂于唐大中元年(847)与慧萼一同乘坐唐商张友信的船赴日,并在日本受到了皇太后橘嘉智子与仁明天皇的优待。橘嘉智子特地在京都为其创建檀林寺,以义空为开山。(32)[日] 高木訷元:《唐僧義空の來朝をめぐる諸問題》,第385—392页;吴玲:《〈高野杂笔集〉所收唐商徐公祐书简》,第115—116页。关于慧萼入唐与义空返日的行程分析,亦可见[日]榎本渉:《僧侶と海商たちの東シナ海》,第62—65页。
这18封书信,有一半是来自于两位徐氏兄弟——徐公直与徐公祐。徐公直在信中最初署名为“婺州衙前散将”,后为“苏州衙前散将”,有一个与前文提及的蔡辅相类的头衔。徐公直的弟弟徐公祐则是一名频繁往来于中日之间的海商。根据这九封书信的信息拼凑可知,徐氏兄弟与义空的书信往来颇为密切,每次徐公祐赴日都会向义空递送一些礼物,而徐公直甚至把自己的儿子胡婆也送到义空座下修习佛法。“唐人书简”18封书信中,只有编号第4封《唐僧云叙致义空》标明写于大中三年六月七日,及第13封《徐公直致义空》标明大中六年五月廿二日,其余书信只有月、日。因此,对于其余书信的系年,乃至徐公直的儿子胡婆何时抵达日本,学者们曾持不同见解。(33)现有研究对这18封书简采用了一致的编号顺序,本文也采用通行的对此书简的编号顺序。此外,学者们对信中个别字词的辨识有不同看法。因田中史生氏的研究最为晚近、且综合多种勘误,故本文引文以田中史生的录文为准。
田中史生根据书信中的细节,如涉及到的地方官员的在任时间等,将18封书信分为两组,一组写于大中三年,一组写于大中六年。我认为他的分类系年是有理有据、值得信服的,并将田中史生所作的表格翻译附于下。(34)[日] 田中史生:《唐人の对日交易——〈高野雜筆集〉下卷所收〈唐人書簡〉の分析から》,第169页。值得指出的一点,第14封信系年中的“闰十一月”,据学者考证应为“闰十二月”的笔误。距离义空到日本后最近的一个“闰十一月”是887年,而义空可能在856年就已返回中国。而849年恰有“闰十二月”。详细分析见田中史生,前揭文第168页。

书简编号年/月/日写信人收信人写信地备注1大中3/5/27婺州衙前散将徐公直义空唐与2一组2大中3/5/27婺州衙前散将徐公直义空、道眆唐与1一组4大中3/6/7唐僧云叙义空唐10大中3(不详)唐僧法满义空唐3大中3/9/11徐公祐义空日本5大中3/9/13日本僧真寂义空日本11大中3/10/14唐僧无无义空日本15大中3/10/15徐公祐义空日本14大中3/闰11/24徐公祐义空日本13大中6/5/22苏州衙前散将徐公直义空唐16大中6/6/30徐公祐义空日本与17一组17大中6/6/30徐公祐胡婆日本与16一组18大中6/10/21徐公祐义空日本
从这些信件中可见,徐公祐在赴日时还会携带其他人写给义空的信,如在大中三年,徐公祐除了带有兄长公直的信之外,还带着其他唐朝僧侣给义空的信。公祐在到达日本后,通常会写信告知义空,并随信附上礼物。而由于公祐通常会在日本停留一段时间,期间他也会收到义空的复信,并再度回信给义空。公祐在日本停留期间,似也与其他僧侣有交流。如大中三年的信件组中,公祐分别与真寂、无无在非常相近的日期给义空写信,可推测他们的信件很可能是同时被带回给义空的。而第五封真寂的信的內容显示,日僧真寂在大中三年大抵是乘徐公祐的船从唐返日。
徐氏兄弟每次致信义空时都会附上礼物。如在大中三年徐公祐赴日时,其兄徐公直准备了“席五合、沙糖一十斤、蜜五升、靸鞋两量”送给义空,并称其为“当境所出土物”。而徐公祐除了寄送兄长的书信与礼物之外,还自己附送了“茶一斤、白茶椀十口”。(35)“唐人书简”第2封《徐公直致义空、道眆》、第3封《徐公祐致义空》。可见高木訷元,前揭文第365—366页;田中史生,前揭文第160—161页。
徐氏兄弟力图与义空建立紧密联系的最重要举动是,大中三年徐公直送自己的儿子胡婆与公祐一同赴日,去义空座下学法。因为大中三年五月及九月的三封信件中,公直与公祐均未直接提及胡婆之名,故许多学者曾认为胡婆是在之后的旅程中才赴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徐公直在大中三年写给义空的信中有一段附言:“义空和尚侍童。无无和尚言,承要童子,弟子顽愚,幸愿寄于贵国结缘。寔未有所知,望赐驱使,垂流不责。”(36)“唐人书简”第1封《徐公直致义空》。可见高木訷元,前揭文第363页;田中史生,前揭文第160页。而徐公直在大中六年的信中,对义空收胡婆作侍童表示了感谢:“又儿子胡婆,自小童来,心常好道。阻于大唐,佛法襄否,遂慕兴邦。伏惟和尚不弃痴愚,特赐驱使,此之度脱,无喻可陈。”(37)“唐人书简”第13封《徐公直致义空》。可见高木訷元,前揭文第377页;田中史生,前揭文第165页。由此推断,最恰当解释便是,在大中三年时,徐公直就借义空想要侍童这一机会,送自己的儿子胡婆赴日。可能因为胡婆到达日本后就会去京都见到义空,许多事情都得以当面述说,无需在信中多言,使得大中三年的信件中反而未多提及胡婆。
耐人寻味的是,据徐公直在信中所言,他送胡婆去日本主要是由于胡婆学习佛法的信念在唐朝难以达成。这一叙述应是基于会昌(841—846)灭佛而言。但大中六年徐公祐给义空的信揭示出,徐氏兄弟送胡婆到日本似还有其他目的。徐公祐在信中提到,他六月五日从唐明州出发,六月二十日就到达了鸿胪馆。而他写信的主要目的,是想请义空派胡婆到鸿胪馆一趟:
子侄胡婆在京甚烦和尚仁德,家中将得少许衣服及信物来,无好信得附从,伏望和尚垂情发遣。一来已后的不妨驱使。公祐苏州田稻三二年全不收,用本至多,因此困乏。前度所将货物来,由和尚与将入京,不免有损折,今度又将得少许货物来,不审胡婆京中有相识、投托引用处否。望与发遣来镇西府取之。五斤香处置,乞不责下情。限以路遥,未由礼谒。(38)“唐人书简”第16封《徐公祐致义空》。可见高木訷元,前揭文第381页;田中史生,前揭文第166页。
从徐公祐的信中不难看出,虽然公祐以找不到合适的人带衣服及礼物给胡婆与义空为借口,请义空派胡婆到九州取衣物,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公祐希望胡婆可以携带一些货物进京,并协助售卖。公祐在信中说,不知道胡婆是否在京城有渠道帮忙发售货物,但显然,作为一名年轻又资历尚浅的侍童,胡婆拥有合适的人脉与渠道的可能性并不高。这一请求,配合着公祐提到因田产不收而导致的经济困难,更像是面向义空提出的。而信中信息也透露,似乎义空之前也曾在运送货物进京一事上帮助过徐公祐。
公祐的这一请求,本质上是想绕过日本当时对海外贸易的一些管制,以获取更大的利润。当时的日本朝廷享有对海外贸易物品的先买权,并且禁止海商与九州当地的居民随意私下贸易。831年,日本太政官就发布了规定:“商人来着,船上杂物一色已上。”(39)《类聚三代格》卷18,黑板胜美编:《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二十五卷》,东京:吉川弘文馆,1998年,第570页。对于相关规定的研究另可见渡边诚:《平安時代貿易管理制度史の研究》,京都:思文阁出版,2012年,第110—124页。即海商携带的货品要先经过官方拣选、采买。徐公祐的信恰好也反映出,这一政策当时确实是在执行中。在前引信末尾,徐公祐加了一句附言:“家兄亦有状及信物,候官中开库附往。”(40)“唐人书简”第16封《徐公祐致义空》。可见高木訷元,前揭文第381页;田中史生,前揭文第166页。而在三个多月后的另一封写给义空的信中,公祐又写到:“家兄书中有绫一匹,被官中收市出不得,今将百和香十两充代。”(41)“唐人书简”第18封《徐公祐致义空》。可见高木訷元,前揭文第383页;田中史生,前揭文第167页。据徐公直在大中六年给义空的信可知,他附上的礼物包括“越绫一匹、靸鞋一量、沙糖十斤”,(42)“唐人书简”第13封《徐公直致义空》。可见高木訷元,前揭文第377页;田中史生,前揭文第165页。而看起来这其中的“越绫一匹”被朝廷执行先买权收走了,所以徐公祐以香药(应是他带来日本的货物)进行了替代。
日本朝廷在9世纪曾多次下令禁止海商与民众的私下交易。“蕃客赉物私交关者,法有恒科,而此间之人必爱远物,争以贸易。宜严加禁制,莫令更然。”(43)《类聚三代格》卷18,第571—572页。《日本三代实录》仁和元年(885)十月二十日条也提到:“大唐商贾人着大宰府。是日,下知府司,禁王臣家使及管内吏民私以贵直竞买他物。”(44)《日本三代实录》卷48,黑板胜美编:《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四卷》,东京:吉川弘文馆,1971年,第593页。朝廷三令五申恰恰说明了这种海商与民众私下交易的情况时有发生、难以禁绝,而言辞中“必爱远物,争以贸易”“私以贵直竞买他物”皆说明,海商把货物卖给私人会获取更高的收益。而徐公祐希望借胡婆与义空的帮助,把部分货物运到京城直接售卖,应该就是出于此考虑。但这显然是不合规制的,所以徐公祐需要找到可完全信任的人执行,故公祐在信中称难以找到合适的人带衣物进京,需要胡婆前往九州一趟。
到这里我们可以重新审视一下徐氏兄弟把胡婆送去日本学法的缘由。前文提到徐公直在信中称,胡婆“心常好道”但“阻于大唐”,所以送他去日本学法。不过在徐氏兄弟送胡婆去日本时,会昌灭佛已结束三年有余。而且,在大中三年唐朝僧人法满写给义空的信中,特意写到“本国佛法,圣主今已再兴,置寺度僧,倍加严峻”(45)“唐人书简”第10封《唐僧法满致义空》。可见高木訷元,前揭文第373页;田中史生,前揭文第164页。。由此可见,胡婆在唐朝无法修习佛法恐怕不能成为送他去日本的理由。而徐公祐在送胡婆到日本后的下次旅程就试图利用胡婆运送货物进京,所以,送胡婆到义空座下的更重要原因,很可能是由此建立与义空、与日本京城更紧密有效的联系,而本质上是为了给徐氏兄弟从事的对日贸易提供便利。
至于义空最终有没有派胡婆去九州,现存的信件并没有明确信息。在大中六年六月三十日的信件之后,徐公祐十月二十一日又去信给义空,当时胡婆尚未到达九州。公祐在信中又一次提出了请求:“子侄愚昧,在京深蒙和尚赐收教示,甚困心力,反反侧侧。公祐今度所将些子货物来,特为愚子侄在此,欲得看集一转。伏望和尚慈流发遣,暂到镇西府相见了,却令入京侍奉和尚。”(46)“唐人书简”第18封《徐公祐致义空》。可见高木訷元,前揭文第383页;田中史生,前揭文第167页。在这第二封信中,徐公祐对请义空派胡婆来的原因表述得更为直接,即就是帮忙把部分货物运进京城转卖。
不过最有可能的是,义空还是答应了徐公祐的请求,或是以其他方式帮助了徐氏兄弟。因为在此数年后,似乎义空和徐氏兄弟依然保持着联系。前文所述的圆珍在唐期间,曾于大中九年由台州前往长安的途中,在苏州徐公直家养病两个月。(47)[日]圆珍著,白化文、李鼎霞校注:《行历抄校注》,第37页。而《风藻饯言集》中也保留了一封徐公直写给圆珍的短笺,列出了徐公直给圆珍准备的一组礼物,包括两匹绫和20只小碟子。(48)[日]敬光辑,白化文、李鼎霞校注:《〈风藻饯言集〉校注》,第269页。徐氏兄弟是缘何与圆珍建立联系的呢?其实有很大可能是通过义空的介绍。义空于847年到达日本,而圆珍851年才离开京都前往大宰府,所以义空与圆珍两人有颇长一段同在京都的时间。此外,圆珍还在写作中提到过,义空到达日本后,见到日本当时佛教徒的现状后颇为失望:“又本朝沙弥,多无佛法……其得度缘受戒僧尼,只为己活,曾无护法守戒之心,衣色同俗,都无定色。令他客僧义空等,责昔鉴真来此传戒有何轨则,僧头似唐行之与衣,曾无交接,一切行事多与戒背。”(49)[日]圆珍:《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文句合记》卷下末,转引自[日]佐伯有清:《円珍》,第257页。或许也正是由于对当时日本接受禅宗程度的不满与失望,义空在重要的支持者皇太后橘嘉智子去世后,可能于公元856年后离开日本、回到唐朝。
三、利益与信仰:9世纪中后期的中日海上网络
《风藻饯言集》与“唐人书简”难得保留了9世纪中后期往来中日之间的僧侣与海商真实的交往过程。两种材料时期相近,呈现出的僧侣与海商的互动也多有相似之处,可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段的中日海域交流提供重要参考。
在9世纪中后期,遣唐使终止后,频繁往来于中日之间的海商成为维系乃至推动中日交流的,不可或缺又十分有效的纽带。从上文呈现的信息可见,无论是李延孝、詹景全、李达这一海商集团,还是徐公祐,均保持着相当频繁而又稳定的频率往返中日之间。正因为海商们当时的往返日程已较为密集并且稳定,所以他们可以承担起很多贸易之外的交流任务。比如,圆珍得以放心地嘱托詹景全、李达送信,购买经书等,即是得益于当时海商的返程大致可以预期。而徐氏兄弟千里迢迢把胡婆送到日本,也是预备建立长期的联系。
在海商和僧侣的互动中,佛教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虽然表面上看,僧侣求助于海商的时候很多:比如,需要搭乘海商的船渡海、依靠海商传递信息、购买经书等。但文献记载中呈现出的海商与僧侣的关系,无不是海商对僧侣十分敬重,并努力参与佛教相关事业,争取僧侣的欢心。李延孝、詹景全等人在天台山与圆珍会合时,特意捐资建造僧房,以提供住处给像圆珍一样的求法僧侣。在鸿胪馆停留期间,海商们也都积极地对圆珍回忆在唐求法、天台经历的诗进行唱和。而徐氏兄弟不仅多次向义空赠送礼物,更是通过把胡婆送到义空座下当侍童、学习佛法而进一步拉近和义空的关系。在和僧侣的通信往来中,海商们的语气皆十分恭顺,并通常以“弟子”或“俗弟子”自居。而僧侣们的回应也显示出,表达对佛教的兴趣是海商们建立与僧侣的良好关系的便捷途径。僧侣们对于有心向佛的海商们通常会有很高的褒奖。例如,在882年写给智慧轮的信中,圆珍特意表扬了李达“道心坚固”,并指出这是使李达在876年的海难中得以幸存的重要原因。(50)[日]圆珍:《上智慧轮三藏书》,第89页。
海商对于佛教的兴趣,一方面应确实源自信仰的需求。从李延孝与詹景全遭遇海难即可知,远洋航行在当时是风险颇高的活动。海商们愿意搭载僧侣,并在到达一地时拜访寺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寄托了他们对于安全航行的期望。圆仁在他入唐的日记里就详细记述了在航海遇到风暴时,船上的僧人、水手如何祈求佑护。(51)[日]圆仁著,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 年,第3、5 页;另可见Valerie Hansen, “The Devotional Use of Buddhist Art in Ennin’s Diary”, Orientations, Vol.45, No.3, 2014, p.78。不过,海商对于佛教表露兴趣的另一方面原因,也是至今探讨较少的方面,即是僧侣对于加入佛教网络的向往。
在中日间的官方使节外交趋于停滞时,佛教实际上成为连接中日双方,特别是有可能联通到双方统治阶层的有力纽带。无论是圆珍还是义空,都有充足的机会接触到信奉佛教的贵族乃至皇室成员。由于佛教网络跨越海域联结了知名僧侣、重要寺院、以及各个阶层的供养人,佛教网络已不仅仅是传播佛法的管道,而成为蕴含重要的人际资源的网络。本文展示的两个个案,均呈现出了海商试图利用佛教网络的人际资源,以获取更大利益。蔡辅想要通过圆珍向新任日本天皇递送礼物,而徐公祐希望借助义空的特殊地位及人际网络绕过日本朝廷对海外贸易的管制,使自己的部分货品可以更高价位在京城卖出。
在这一时期,佛教网络与贸易网络在地理区域上也有了更显著的重合。9世纪中后期,随着新罗商人在中日海上贸易中逐渐淡出,山东半岛在中日贸易网络中的作用也有所弱化,而长江下游地区在贸易网络中的地位被凸显。本文提到的唐朝商人,都是来自于苏州、婺州、越州等地,而他们交易的商品,如越绫、陶瓷器等,也都产于此地。就如徐公直在送礼物给义空时所称,这些物品是“当境土物”。长江下游同时也是重要的佛教寺院的集中地,日本僧侣造访时,会在此停留较长时间,而被邀请去日本传法的义空和尚,也来自位于杭州的寺院。詹景全在圆珍返回日本后,为其送信、传递礼物,也集中在温州、台州等地。唯一超出这一范围的行程——送信给长安的智慧轮,反而却因为路途不便而未能实现。在日本一方,海商到达的九州北部一带及京城,都是消耗进口品最多的区域,而这一区域同时也是对来自中国的佛法及佛教仪式接受最为积极的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海商对于加入佛教网络的兴趣,在9世纪之后有增无减。僧侣和海商的互助关系愈发紧密,海商更为积极地协助佛教传播,而寺院甚至开始直接参与海上贸易。(52)关于10至13世纪的情况,可见李怡文:《十至十三世纪中日交流中的僧商合作与“宗教—商业网络”》,载邓小南、方诚峰主编:《宋史研究诸层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82—405页。中日之间的佛教网络与贸易网络在之后的数世纪中,进一步地重叠、融合,所形成的“宗教—商业”网络成为联结中日的极为重要的纽带。而这一网络的发端,在9世纪就已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