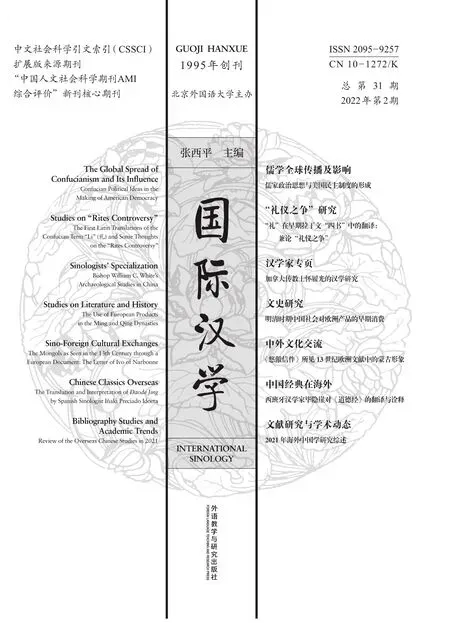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对欧洲产品的早期消费
□ 李 坤
中国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明清社会排斥、贬低欧洲产品。乾隆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回信中所言“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第84页。,便被学者频繁引用,用以说明当时中国社会排斥、贬低欧洲产品。而排斥、贬低欧洲产品的原因,则常常被归咎于明清社会自大保守的文化观念和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
相关研究强调的是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排斥、贬低欧洲产品,不过,忽视了微观层面的欧洲产品消费者,他们作为消费欧洲产品的当事人,应被给予更多关注。而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处于消费欧洲产品的早期阶段,因此,要全面、深入了解明清社会看待欧洲产品的态度,就必须了解欧洲产品的早期消费者及其消费动机。本文考察的时间范围是明末至19世纪初。考察明末至19世纪初的欧洲产品消费,一方面能了解欧洲产品在中国的早期消费情况,另一方面能发现,在中国消费欧洲产品的早期阶段,就存在追捧欧洲产品的现象,就存在促进欧洲产品传播的动力,所以认为明清社会排斥、贬低欧洲产品的观点是片面的。消费视角有助于全面、深入了解欧洲产品在明清社会的际遇。
一、欧洲产品的奇巧特征迎合了明清上层社会尚奇巧之风
在相识之初,欧洲产品是否就具有吸引中国人的产品特征?而中国社会是否本就具有接纳欧洲产品的消费群体和文化?答案是肯定的。明清时期奢侈风气出现了空前的高峰,而在奢侈消费的对象方面,追捧奇巧之物,上层社会尚奇巧之风格外盛行。初次相识欧洲产品时,欧洲产品的奇巧特征正好迎合了上层社会尚奇巧之风。
明末一些上层人士见到欧洲产品的第一眼,就被欧洲产品的奇巧特征吸引,欧洲产品传入之初就受到了一些上层人士的追捧,这可以从来华欧洲传教士留下的中国见闻中看出来。例如,《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1582年两广总督陈瑞听到不用碰它就能报时的钟表时,就特别感兴趣,“请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无论如何病一好立刻就去见他,并把那件新奇的玩意儿(钟表)带去”,这件“新奇的玩意儿”甚得陈瑞欢心,陈瑞批准罗明坚在广州修建房屋和教堂。但后来陈瑞因与张居正的牵连被解职,罗明坚失去保护伞不得不返回澳门。1583年肇庆知府王泮又邀请罗明坚来肇庆,并答应拨一块地修建教堂,罗明坚同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一同前来。罗明坚在王泮指定的修建教堂的地方展示了欧洲产品:“百姓先看到准备送给原长官的玻璃三棱镜,惊得目瞪口呆,然后他们诧异地望着圣母的小像。那些仔细打量玻璃的人,只有惊羡无言地站在那里。随同长官的官员们尤其如此,他们越称赞它,就越引起群众的好奇心。”可见,欧洲玻璃三棱镜和画像之奇引发了中国官员和群众强烈的好奇心。接替陈瑞的新任总督也喜欢玻璃三棱镜,“他很久就想要一个”。当时,玻璃三棱镜受到肇庆官员的追捧,教堂盖好后,官员们常来教堂借玻璃三棱镜观看山河风景,用玻璃三棱镜观看风景的神奇效果吸引了肇庆的官员们。利玛窦在肇庆期间,“在那里接待了异常之多的各个阶层的中国客人,这些来访可能是由收藏的欧洲珍奇而引起的”。②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等译,何兆武校,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50、164、190、202、209页。
可见,一个特别有利于欧洲产品在初始便俘获中国人“芳心”的因素是,欧洲产品奇巧的特征正好迎合了中国上层社会盛行的崇尚奇巧之风。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访华使团副使斯当东(George Staunton,1737—1801)在其访华日记中写道:“这些东西(欧洲产品)初到中国的时候,中国人认为巧夺天工,不惜重价购买。”③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北京:群言出版社,2014年,第418页。
如果说晚明时期部分上层人士对欧洲产品的追捧代表着欧洲产品消费在中国上层社会兴起的源头,那么,进入清代,皇帝对欧洲产品的追捧和使用则是推动欧洲产品消费时尚的“发动机”。巫仁恕(2006)认为,清代士大夫在创造时尚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比起晚明,其重要性已大不如前,宫廷取而代之成为领导流行时尚的推手。④巫仁恕:《明清消费文化研究的新取径与新问题》,《新史学》2006年第4期,第232页。清代宫廷推动着欧洲产品消费时尚,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清代宫廷追捧和消费欧洲产品,成为欧洲产品消费最权威的参照群体,在欧洲产品消费方面存在示范引领作用,上层社会仿效宫廷消费欧洲产品。赖惠敏(2005)的研究就指出,乾隆时期江南社会的精英家庭流行仿效宫廷摆饰自鸣钟、戴表,⑤赖惠敏:《寡人好货:乾隆帝与姑苏繁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0期,2005年,第227页。而且,康雍乾常常赏赐欧洲产品,官员也投皇帝所好搜集欧洲产品进贡,这都会释放消费信息,推动上层社会消费欧洲产品。第二,清代宫廷在欧洲产品生产方面也存在示范引领作用,民间模仿生产宫廷造办处制造的欧洲产品,宫廷影响了中国社会欧洲产品生产,进而带动欧洲产品消费。例如,康熙时期民间模仿生产造办处制造的玻璃鼻烟瓶,⑥(清)王士禛:《香祖笔记》,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年,第256页。雍正时期广州太平门外长寿庵模仿生产造办处制造的黄色珐琅鼻烟壶,并由广东商人将之运到北京贩卖,⑦“内务府总管海望奏请行文广东总督禁止地方制造黄色珐琅器物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故宫博物院合编:《清宫内务府奏销档》,第9册,北京:故宫出版社,2014年,第433页。乾隆时期造办处有匠役偷用造办处的原料烧造玻璃灯售卖。①“总管内务府奏为参奏副催总马兆图私卖玻璃灯等情弊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号:05-0094-051。宫廷造办处制造的欧洲产品是市场模仿生产的对象,宫廷影响并推动了中国社会欧洲产品的生产和供给,而欧洲产品生产的发展和供给的增多为欧洲产品消费时尚提供了基础。
康雍乾追捧欧洲产品,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被欧洲产品的奇巧特征吸引,康雍乾描写欧洲产品的诗,便经常用“奇”“巧”形容欧洲产品。进入清代,欧洲产品之奇巧吸引了皇帝,皇帝追捧欧洲产品的行为又对欧洲产品在上层社会的消费起着示范引领作用,而同时欧洲产品之奇巧特征本就吸引着上层社会。总之,欧洲产品在明清上层社会的消费和传播受到了尚奇巧消费风气的推动。
二、明末至19世纪初上层社会消费欧洲产品的多样化动机
虽然欧洲产品的奇巧特征是吸引明清上层社会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欧洲产品进入中国后,就被上层社会主动纳入其消费文化体系了。消费社会学认为,物一旦被纳入文化体系,就不再是单纯的物,而是文化的载体和表达意义的符号,对物的消费也不单纯是生理性或物理性消费,而是体现了某种社会价值规范,传达了某种社会意义。②王宁:《消费社会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52页。换句话说,消费物,不仅是为了获得物的物理功能和实用价值,也是为了获得物的社会功能和符号意义。利用消费社会学的理论分析明末至19世纪初上层社会对欧洲产品的看法、使用与消费,能从微观视角进一步发现上层社会消费欧洲产品的多样化动机。
1.消费欧洲产品的社会功能和符号意义
明清上层社会使用欧洲产品满足其赠与需要、社会形象需要和时尚需要。
5.1 西宁及以东地区光照强、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夏季气温在22-25℃,总体表现出适宜在该地区园林绿化中推广应用适应性强的月季品种。
1)赠与需要
明末上层人士之间就赠送欧洲产品。藏书家郎瑛(1487—?)的《七修类稿续稿》载,霍都司曾送他一副眼镜。③(明)郎瑛:《七修类稿续稿》,载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534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386页。军事家茅元仪(1594—1640)有诗《千里镜歌贻吴今生》写道,吴今生曾送给他一个千里镜。④(明)茅元仪:《石民横塘集》,载《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10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226页。
文学家顾景星(1621—1687)有诗《玻璃方镜》,下有小字注曰“曹子清赠”,表明曹寅(字子清)曾赠送顾景星玻璃方镜。⑤(清)顾景星:《白茅堂全集》,载陈红彦、谢冬荣、萨仁高娃主编《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第84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236页。《红楼梦》第71回写道,贾母生日,粤将军邬家送来一架玻璃围屏。⑥(清)曹雪芹:《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594页。
陆耀(1723—1785)的《烟谱》曰:“别有所谓鼻烟者,屑叶为末,杂以花露,一器或值数十金,贵人馈遗,以为重礼。”⑦(清)陆耀:《烟谱》,载王德毅主编《丛书集成续编》,第86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第676页。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杨抡(1742—1806)有词《前调鼻烟》曰:“粤海装来,故人多少走书问。玻璃瓶小满贮,紫荷新样好,应许同赠。”⑧(清)杨抡:《前调鼻烟》,载张宏生主编《全清词·雍乾卷》,第10册,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881页。朋友写信希望得到进口鼻烟,词人则答应送给朋友。
上层社会通过赠送钟表维护和编织社会关系。《蜃楼志全传》第1回写道,苏万魁等一众广州行商被新任粤海关监督赫老爷关押,苏万魁为打探消息,将一块上好西洋表赠送给赫老爷的下属杜宠,从此便与杜宠建立了良好的关系。⑨(清)庾岭劳人:《蜃楼志全传》,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6年,第4页。爱人之间也会赠送钟表。乾嘉时期著名文学家乐钧(1766—1814)曾游历广东,他有一首广东竹枝词写道:“君在羊城肯忆侬,寄侬番缎并洋钟。报君土物青铜锁,为锁情关一万重。”①(清)乐钧:《韩江棹歌》,载丘良任、潘超、孙忠铨等编《中华竹枝词全编》,第6册,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7年,第390页。
乾隆二十二年(1757)云贵总督恒文贪污案发,广南府知府汪筠供称,他曾买羽毛纱四件、小呢两身、蓝哆啰呢一疋送给恒文的家仆赵二。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7页。下级官员赠送欧洲奢侈品给高级官员身边的人,这是一种典型的官场投资行为。亲人之间也会赠送欧洲毛织品,士人黄子云(1691—1754)有诗《伏日,泉州族侄植俊至,兼惠哔吱叚,走笔谢》写道,他的侄子曾送其哔吱(即哔叽)。③(清)黄子云:《长吟阁诗集》,载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中国古籍珍本丛刊·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卷》,第56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第765页。
2)社会形象需要
拥有和消费欧洲产品具有展示和提升社会形象的符号意义。《红楼梦》第6回写道,宁国府因要请一个要紧的客,向凤姐借玻璃炕屏。“贾蓉笑道:‘我父亲打发我来求婶子,说上回老舅太太给婶子的那架玻璃炕屏,明日请一个要紧的客,借了略摆一摆就送过来。’”④《红楼梦》,第61页。这个例子可见,玻璃炕屏参与了清代上层社会的消费竞赛,与现代社会的家庭一样,18世纪的家庭也很关心能否获得表明其社会地位的产品,如果得不到,就意味着有可能处在该阶层之下。“要紧的客”来头必定不一般,宁国府想在要紧的客人面前展示和炫耀玻璃炕屏,拥有和使用玻璃炕屏是一种身份诠释方式和提高家庭社会地位的行为。商盘(1701—1767)有诗《咏玻璃屏》写道:“华堂见惯何曾骇,多少人间喘月人。”⑤(清)商盘著,郭杨点校:《商盘集》,第3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689页。看来商盘在大户人家的正厅见惯了玻璃屏。
林苏门(约1748—1809)的《邗江三百吟》描写的是乾嘉之际扬州风土,该书记载,当时扬州“趋时之家”特意将自鸣钟摆放在客厅向客人炫耀:“自鸣钟以定时刻,扬城趋时之家,间亦用之,近日有用闹钟设于厅上者,时刻周流转换,未换之先,隐隐声如击柝,一换则如撞洪钟声。时刻之分,原以钟声之数为定,此钟惟于时刻欲换之际,忽铿铿然如奏乐一般,闹毕即撞,撞亦以数定,厅上乃宾客往来之地,藉以骇人见闻。”⑥(清)林苏门:《邗江三百吟》,卷七《趋时清赏·厅上闹钟》,扬州:广陵书社,2005年,第94页。赵翼(1727—1814)有诗描写自鸣钟:“其初携从利玛窦,今遍豪门炫楼阁。”⑦(清)赵翼:《瓯北集》,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46页。
乾隆年间殷如梅有词《金缕曲鼻烟》曰:“瑞草争相售。笑而今,分明鼻饮,阿谁传授。不用连筒呼复吸,只借玉壶装就。便徹脑,清芬都透。纤手轻轻挑剔起,仗东涂西抹,消长昼。银甲小,愁遗漏。淡巴菰尚名依旧。讶缤纷,千丝金屑,染襟霑袖。忽听时哉争欢羡,座上有人三嗅。”⑧(清)殷如梅:《金缕曲鼻烟》,载《全清词·雍乾卷》,第13册,第7469页。词中写道,对于争相售卖的烟草,现今流行鼻烟,座上有人吸闻鼻烟,引起旁人欢羡,足见鼻烟的炫耀性消费效果。
3)时尚需要
18世纪中国的烟草消费表现出了时尚变化。屈复(1668—1745)有一首北京竹枝词曰:“玉壶细雕镂,雕镂重于钱。天厌相思草,新情爱鼻烟。”⑨(清)屈复:《变竹枝词》,载《中华竹枝词全编》,第1册,第121页。朱履中刊刻于嘉庆二年(1797)的烟草诗集《淡巴菰百咏》曰:“烟草外别有壶烟鼻烟,两种始于京师,今则天下盛行。”⑩(清)朱履中:《淡巴菰百咏》,载杨国安编著《中国烟业史汇典》,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第35页。在扬州,不善吸闻鼻烟的人为追求这股新时尚,也会携带鼻烟。《邗江三百吟》载:“近有一班趋时之辈,本不善吃鼻烟,往往酬应时携一玉壶,以为时尚。”⑪《邗江三百吟》,卷七《趋时清赏·玉鼻烟壶》,第92页。
乾嘉时期部分地区出现了钟表时尚。《邗江三百吟》载,对于西洋表,扬州“趋时人借定时名目,亦多于腰间配带,以为饰观”。林苏门还有一首诗写道:“腰间走表觅知音,委佩垂绅玉与金。贾客近来沽价贵,二分明月要三针。”①《邗江三百吟》,卷七《趋时清赏·带三针表》,第95页。乾嘉之际最受欢迎的时辰表,便是林苏门诗中提到的可报知时、分、秒的三针表,18世纪末英国钟表匠才做出了附有秒针的钟表,乾嘉之际输入中国的三针表,即便在同一时期的英国,也是相当稀有的高级品。②李侑儒:《钟表、钟楼与标准时间——西式计时仪器及其与中国社会的互动(1582—1949)》,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12年,第75—76页。北京也流行三针表。乾嘉时人杨米人有一首北京竹枝词写道:“三针洋表最时兴,手裹牛皮臂系鹰。拉手呵腰齐道好,相逢你老是通称。”③(清)杨米人:《都门竹枝词》,载路工编选《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9页。
乾隆发现当时眼镜非常流行。乾隆有诗《眼镜》曰:“眼镜不见古,来自洋船径。胜国一二见,今则其风盛。”④故宫博物院编:《清高宗御制诗》,第13册,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375页。为了追求社会时尚,北京原本不近视的年轻人也学文人戴眼镜。杨米人有一首北京竹枝词写道:“车从热闹道中行,斜作观书不出声。眼镜戴来装近视,学他名士老先生。”⑤(清)杨米人:《都门竹枝词》,载《清代北京竹枝词(十三种)》,第20页。
2.消费欧洲产品的物理功能和实用价值
明清上层社会还使用欧洲产品满足其娱乐需要和实用需要。
一些欧洲产品具有玩物功能,上层社会用之来娱乐。斯当东在其访华日记中写道:“内装弹簧齿轮,外镶珍贵宝石的八音匣(Sing-Songs),这一类机器售价最高。这些东西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但中国官吏们却醉心追求。这些玩物源源不断地由私商运进中国,值价已达一百万英镑之巨。”⑥《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25页。昭梿(1776—1833)的《啸亭续录》载:“近日泰西氏所造自鸣钟表,制造奇邪,来自粤东,士大夫争购,家置一座以为玩具。”⑦(清)昭梿:《啸亭续录》,卷三《自鸣钟》,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68页。欧洲光学玩具很受上层社会欢迎,特别是千里镜。李渔(1611—1680)在小说《夏宜楼》中写道,对于西洋光学玩具,“凡探奇好事者,皆得而有之”,小说里的主人公吉人是一个旧家子弟,他与几个朋友在古玩铺见一千里镜,试过之后,“甚是惊骇”,“人人要买”,最后吉人买下这个千里镜,竟用它来偷窥大户人家的女孩。⑧(清)李渔:《十二楼》,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0页。
把玩欧洲产品的现象甚至引发不满和担忧。乾隆时人闵华有诗《自鸣钟》曰:“彼何人斯始剏造,徒矜淫巧供豪奢。况此一器百金值,易我菽粟兼丝麻。损将有用得无用,致今识者生咨嗟。”⑨(清)闵华:《澄秋阁三集》,载《四库未收书辑刊》编纂委员会编《四库未收书辑刊》,10辑第2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603页。当时一些人认为中国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可以不需要对外贸易和外国产品,斥中欧贸易是“以有用易无用”,斥欧洲产品为无用之物。
但在日常生活中,上层社会对欧洲产品实用价值和优点的认可非常明显。利玛窦评价中国人:“我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天真的脾气,一旦发现外国货质量更好,就喜欢外来的东西有甚于自己的东西。”⑩《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3页。
随身携带表,可以随时看时间,这是中国传统计时器具无法做到的。曾任刑部侍郎的刘秉恬(?—1800)有诗《时辰表》曰:“游子携以随,时时近征衣。朝士携以随,计刻入禁围。袖里看乾坤,不啻窥日晖。”⑪(清)刘秉恬:《竹轩诗稿》,载《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145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页。相比传统计时工具,钟表的使用不受天气干扰。康熙时人程庭有词《玉漏迟自鸣钟》曰:“偏是泰西一器,总无问,阴晴昏晓。”⑫(清)程庭:《玉漏迟自鸣钟》,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全清词》编纂研究室编《全清词·顺康卷》,第19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1120页。
在《钟 表 与 文 化,1300—1700》(Clocks and Culture, 1300-1700)一书中,卡洛·M.奇波拉(Carlo M. Cipolla,1922—2000)提出,在16—18世纪中国社会,钟表的实用功能并不强,多作为玩具和礼物在上层社会流传。①Carlo M. Cipolla, Clocks and Culture, 1300-1700. New York: W. W. Norton, 1978, pp. 87-90.事实上,明清上层社会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也认可钟表的计时功能,会使用钟表计时。《红楼梦》里宝玉等人常使用钟表,这样可以较为精确地知道自己休息和吃饭的时间。《蜃楼志全传》第4回写道,行商苏万魁之子苏吉士与盐商之女温素馨用钟表看时间,以按时约会。②《蜃楼志全传》,第43页。钟表也用来计时以按时完成工作。沈初(1729—1799)《西清笔记》载,乾隆时大臣于敏中将表置于砚侧,看着表针起草奏章。③(清)沈初:《西清笔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4页。
康熙第十七子允礼(1697—1738)有诗《玻璃》写道,玻璃镜之明净胜过青铜镜:“妍媸同一照,朗彻胜青铜。”④(清)允礼:《静远斋诗集》,载《四库未收书辑刊》,第8辑第29册,第663页。明末清初著名学者、诗人屈大均(1630—1696)有诗《玻璃镜》写道,自欧洲而来的玻璃镜绝对胜过中国的菱花镜:“绝胜菱花镜,来从洋以西。”⑤(清)屈大均著,陈永正等校笺:《屈大均诗词编年校笺》,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249页。宝玉使用玻璃穿衣镜,除了因为它是时尚奢侈品之外,可以想象也因为它比铜镜照得更清楚。
林苏门有诗《玻璃窗洞》曰,玻璃窗虽然“不隔人目”,但“风寒不透”,相比窗纱,玻璃窗不仅能增加室内采光效果,还不阻碍视线:“碧纱隐约护窗棂,中嵌玻璃望更明。冰玉一方秋月炯,相看内外总澄清。”⑥《邗江三百吟》,卷三《俗尚通行门·玻璃窗洞》,第36页。《清俗纪闻》记载,乾隆时期江、浙、闽一带,“窗户上使用明瓦、云母、玻璃,而不使用两面贴纸之纸扉”⑦中川忠英:《清俗纪闻》,方克、孙玄龄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10页。。乾隆时期江南有画舫用玻璃窗取代纱窗。乾隆时苏州才女席蕙文有一首《虎丘竹枝词》写道:“画舫珠簾竞丽华,玻璃巧代碧窗纱。”⑧(清)顾禄:《桐桥倚棹录》,卷十二《舟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62页。
鼻烟具有很好的通鼻效果。浙闽总督高琦之女、被誉为清初八旗第一才女的高景芳有诗《鼻烟壶》曰:“西洋药妙巧,透鼻先熏脑。略吸窍齐通,味辛能去风。腻香匀玉屑,小盖和铫揭。一寸琢玻璃,随身便取携。”⑨(清)高景芳:《红雪轩稿》,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0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63页。《红楼梦》也描写过鼻烟的透鼻功效,第52回,晴雯“鼻塞声重”,嗅了些鼻烟打了几个喷嚏后“果觉通快些”。⑩《红楼梦》,第431页。
欧洲毛织品较厚实,御寒效果好。《红楼梦》里贾府的主人们冬天就穿着欧洲毛织品制作的服装,第51回写道,雪天时大家穿的“不是猩猩毡就是羽缎羽纱”。⑪同上,第423页。乾隆时期浙江嘉兴府桐乡县濮院镇的方志“习尚”条写道,当地用洋呢、羽毛做的冬衣“日多一日矣”⑫(清)杨树本:《濮院琐志》,卷六《习尚》,载《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21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第482页。,可见当地消费者对欧洲毛织品御寒效果的认可。
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中,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在论述“汉族文化中心主义”时强调,汉人对外来事物普遍排斥,⑬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204页。但对于眼镜,使用过眼镜的明清中国人普遍接受它,这是因为眼镜无可替代的实用性。刘廷矶(约1654—?)在《在园杂志》中写道,西洋制造中“最妙通行适用者,莫如眼镜”⑭(清)刘廷矶:《在园杂志》,卷四《西洋制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69页。。
日常生活中眼镜对老人非常实用。明代画家仇英(约1498—1552)的绘画《南都繁会图卷》描绘了南京秦淮河两岸的盛况,画上,闹市中有一位老者戴着眼镜观看杂耍把戏。眼镜对文人而言非常重要。孙承泽(1593—1676)称赞眼镜:“真读书之一助也。”①(清)孙承泽:《砚山斋杂记》,商务印书馆《四库全书》工作委员会编《文津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第289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67页。工作中遇到看字书写的情况,需要戴眼镜。戴震(1724—1777)于1773年被召为《四库全书》纂修官,修书时会戴眼镜。②许苏民:《戴震与中国文化》,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5页。
有学者认为,乾隆在给英王的回信中所言“不贵奇巧”等语,有在外交场合“提虚劲”的意图。③罗志田:《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110页。还有学者认为,“不贵奇巧”等语是乾隆在回击马戛尔尼使团对礼物的过分炫耀,也是乾隆拒绝使团索要贸易特权的外交托词。④张丽、李坤:《乾隆皇帝致英王乔治三世敕书的另类解读》,《广义虚拟经济研究》2019年第4期,第5页。实际上乾隆是很贵欧洲奇巧的,他多次要求粤海关采办欧洲产品,也认可欧洲产品的实用价值。乾隆有诗《自鸣钟》称赞自鸣钟道:“此钟之利贻无穷。”⑤故宫博物院编:《清高宗乐善堂全集》,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288页。乾隆还写有多首《玻璃窗》诗称赞玻璃窗的实用价值,其中一首称赞玻璃窗“内外洞达称我心”⑥同上,第305页。。古代会用贝壳类打磨成半透明的薄片做窗户,乾隆还有诗《玻璃窗》夸赞玻璃窗不阻碍视线,要胜过牡蛎壳的窗户:“虚明兼洞达,牡蛎未堪论。”⑦《清高宗御制诗》,第2册,第123页。乾隆还有诗《玻璃窗》曰:“车窗悬玻璃,障尘胜纱帷。内外虚洞明,视远无纤遗。可避轻风寒,还延暖日曦。惟是听受艰,扬言声似卑。耳属或不闻,目成乃可知。明目信有济,达聪非所宜。致用当节取,格物理可推。”⑧同上,第3册,第309页。乾隆写道,在轿子上安装玻璃窗,在防尘方面胜过纱帷,而且玻璃窗不阻碍视线,还能避寒,可见乾隆对玻璃窗实用功能的认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表述的“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乃乾隆朝处置西学的国家文化政策,⑨刘耘华:《清代前中期东吴文人与西学(下)》,《基督教文化学刊》2013年第2期,第109页。正如乾隆这首《玻璃窗》诗曰“致用当节取,格物理可推”。
三、明末至19世纪初上层社会的消费领域存在欧洲产品的传播动力
欧洲产品的奇巧特征一开始就吸引了上层社会,上层社会盛行的崇尚奇巧消费风气推动了欧洲产品的消费和传播,同时,上层社会逐渐开发出了欧洲产品的多种消费价值,使用欧洲产品满足多种消费需要,上层社会存在的追捧和消费欧洲产品的多样化动机也是欧洲产品传播的动力。
消费者的需求动机可分为社会导向的动机和个人导向的动机,前者侧重于获取商品的符号意义和社会功能,后者侧重于获取商品的物理功能和实用价值。从消费者的需求动机来看,明末至19世纪初,上层社会消费欧洲产品的动机既包括社会导向的动机(赠与需要、社会形象需要、时尚需要),也包括个人导向的动机(娱乐需要、实用需要)。为了满足赠与需要、社会形象需要、时尚需要、娱乐需要、实用需要,上层社会会通过市场的、非市场的途径获得欧洲产品,消费欧洲产品,这无疑促进了欧洲产品的传播,消费欧洲产品的动机,也是推动欧洲产品传播的动力。个人导向的消费动机和社会导向的消费动机均推动了欧洲产品的消费与传播。
明末至19世纪初,上层社会对欧洲产品的追捧和消费发生了两个趋势性变化。第一,上层社会追捧和消费欧洲产品的动机呈多样化趋势,明末上层社会消费欧洲产品的动机较为单一,随着上层社会对欧洲产品的开发和使用,进入清代,上层社会消费欧洲产品的动机更多了,例如,相比明末,进入清代后眼镜还能满足时尚需要。第二,上层社会越来越追捧和消费欧洲产品,这一趋势被身处其中的人清晰地察觉到了,例如,朱履中称鼻烟“始于京师,今则天下盛行”,乾隆称眼镜“胜国一二见,今则其风盛”,赵翼称钟表“其初携从利玛窦,今遍豪门炫楼阁”。
上层社会欧洲产品消费动机的多样化,反映了上层社会擅长在消费领域开发和利用欧洲产品,他们开发出了欧洲产品的多种消费价值,从而满足其多种消费需要。古代中国物质和消费文化发达,滋养出非常善于开发和利用物品的上层社会。将明清上层社会视为保守封闭的文化群体是片面的,他们的消费文化具有开放性,不应该低估他们在消费领域开发和利用舶来品的能力,他们具备娴熟的消费经验和成熟的消费文化,开发出了欧洲产品的多种消费价值来满足多种消费需要。而当欧洲产品能满足上层社会的多样化消费需要时,上层社会更会去消费欧洲产品,也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消费欧洲产品。
明末至19世纪初,就区域而言,欧洲产品在北京、江南和广东的上层社会群体中的消费和渗透最为明显。就产品而言,不同类型的欧洲产品在上层社会的渗透程度不同。有一些欧洲产品,如钟表、玻璃穿衣镜等,价格一直居高不下,主要在各地达官显贵以及经济实力很强的人中扩大传播。在《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的抄家案例中,被抄出钟表和玻璃穿衣镜的主要是各地的高级别官员。有一些欧洲产品在上层社会的传播范围明显扩大了,特别是光学玩具、眼镜、毛织品等,明末主要是达官显贵以及与欧洲传教士交好的士大夫消费这几类欧洲产品,进入清代后,普通士绅、富裕之家也能消费这几类欧洲产品。明末欧洲光学玩具不仅难以买到,而且价格非常昂贵,《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明末肇庆官员只能去教堂向传教士借玻璃三棱镜把玩,瞿太素将利玛窦赠送给他的一面玻璃三棱镜卖出了超过五百金的高昂价格。①《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39页。而到了清初,比利时传教士鲁日满(François de Rougemont,1624—1676)在江南传教的账本表明,光学玩具的价格大大降低了,而且他在江南很容易买到,例如,1674年鲁日满在苏州买了三个取火镜和一个多棱镜,共花银0.35两。②高华士:《清初耶稣会士鲁日满常熟账本及灵修笔记研究》,赵殿红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106页。孔尚任(1648—1718)的《节序同风录》所记大抵以北地风俗为主,书中写道:“九月初九,登高山、城楼、台观……持千里镜以视远。”③(清)孔尚任:《节序同风录》,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104页。明末眼镜“非有力者不能得”④(清)赵翼:《陔余丛考》,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6页。,而“顺治以后,其价渐贱”⑤(清)叶梦珠:《阅世编》,卷七《食货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63页。,在李绿园(1707—1790)的小说《歧路灯》中,河南开封一代的一位普通塾师也戴上了眼镜。⑥(清)李绿园:《歧路灯》,郑州:中州书画社,1981年,第408页。进入清代后,光学玩具和眼镜在上层社会渗透较为广泛,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相关仿制业的发展,而毛织品在上层社会渗透较为广泛,则是由于进口规模的巨大增长。⑦1790—1799年,中国平均每年进口英国毛织品价值高达超过150万两白银(参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0页)。19世纪初,中国进口英国毛织品价值达到鸦片战争前的顶峰,1804年、1806年和1808年,中国进口英国毛织品价值均超过300万两白银(参见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区宗华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卷第458页,第3卷第28、84页)。明末欧洲毛织品极为稀少,到了清代,即使一些很小的物件也有用欧洲毛织品制作的,可见欧洲毛织品使用广泛。例如,清初民间斗鹌鹑时装鹌鹑的口袋有用哆啰呢制作的,⑧《在园杂志》,卷四《服饰器用》,第163页。乾隆时期吸烟盛行,民间的烟荷包有用欧洲毛织品制作的,⑨(清)秦武域:《闻见瓣香录》,载《丛书集成续编》,第24册,第505页。乾隆时期,即使北方偏远地区的低级别官员被抄家,也抄出了欧洲毛织品制作的服装,⑩例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乌鲁木齐各属侵冒粮价案案发,一系列官员被抄家,宜禾知县瑚图里、迪化知州德平、呼图壁巡检吴元、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济木萨县丞伍彩雯、吉昌知县徐维绂等大小官员的抄家财产清单中都出现了欧洲毛织品制作的服装。参见《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第3册,第2253、2248—2250、2290、2301—2302、2332—2340、2345页。嘉庆时期,湖南郴州“哔叽、哆啰相习成风”⑪(清)朱偓、(清)陈昭谋修纂:《嘉庆郴州总志》,上册,卷二十一《风俗》,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391页。。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强调的是明末至19世纪初中国上层社会的消费领域存在欧洲产品传播的动力,是基于上层社会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文化而言的。从消费视角来看,明末至19世纪初中国社会阻碍欧洲产品传播的因素也是很明显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即,广大劳动阶级没有经济能力消费欧洲产品,但这并不能说他们排斥欧洲产品。当消费者买不起某产品时,便认为他排斥该产品,这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购买某产品,与其说他排斥该产品,毋宁说是个人在经济能力有限条件下的理性选择。
四、余 论
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处于消费欧洲产品的早期阶段,很多研究强调明清社会(鸦片战争前)排斥、贬低欧洲产品,但对欧洲产品早期消费者及其消费动机关注不够。本文重点考察了欧洲产品的早期消费情况,特别关注欧洲产品早期消费者的消费动机。研究发现,在消费欧洲产品的早期阶段,就存在追捧欧洲产品的现象和消费欧洲产品的多样化动机,就存在促进欧洲产品传播的动力,明清上层社会及其消费文化推动了欧洲产品的传播。那时欧洲产品在中国上层社会的消费和传播,体现了上层社会开发和使用欧洲产品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而非西方单方面的强加。
中国历代都曾出现奢侈的现象,但是到了明清时期奢侈风气出现了空前的高峰,①巫仁恕:《奢侈的女人——明清时期江南妇女的消费文化》,台北:三民书局,2010年,第3页。这与全球贸易联系更紧密的时代背景下更多且更丰富的舶来消费品的涌入不无关系。欧洲产品被明清上层社会视为奢侈品,欧洲产品迎合、助长了明清奢侈风气,欧洲产品消费是明清奢侈消费的一个表现。欧洲产品消费表明,明清奢侈风气不只是传统奢侈消费的一个更显著的版本,一方面,相比以往朝代的奢侈消费,明清奢侈消费受更广阔的外部世界影响;另一方面,明清上层社会不仅消费传统奢侈品,蕴含新的生产技术和消费文化的欧洲产品成为他们奢侈消费的新宠。
不过,对于欧洲产品在明清消费文化中的角色,以往存在刻板印象。欧洲产品常被认为只是供明清上层社会把玩或收藏的西洋奇巧、珍玩,事实上,特别是进入清代后,很多欧洲产品既被上层社会视为奢侈品,同时也被上层社会视为实用品,上层社会的欧洲产品消费既是奢侈性消费,同时也有明显的实用性消费特征。作为不同于国内产品的舶来品,欧洲产品独到的实用价值得到了上层社会的认可,上层社会在日常生活中积极使用欧洲产品的实用功能。
对于明清社会欧洲产品消费者的角色,以往也存在刻板印象,常常认为他们只是把玩或收藏西洋奇巧、珍玩的奢侈消费者,事实上,他们同时也是消费创新者。所谓消费创新者,即社会上首先采用新产品的消费者群体。②罗格·D. 布莱克维尔、保罗·W. 米尼德、詹姆斯·F. 恩格尔:《消费者行为学》,吴振阳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428页。明清上层社会追捧和消费钟表、眼镜、玻璃制品等欧洲产品,出现用钟表替代传统计时工具,用玻璃窗替代纸面窗和纱窗,用玻璃镜替代铜镜的现象,作为一种事后之见,这是时代的趋势,但明清上层社会的欧洲产品消费行为确有消费创新的特征,他们作为首先采用欧洲产品的消费者群体,推动着中国的物质文明和消费文化变迁,如今,这几种当初来自欧洲的产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已无处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