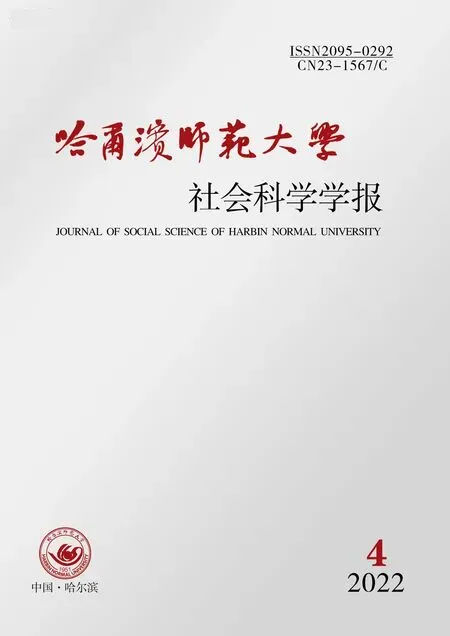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作品性以及权利保护问题
潘一豪,赵理智
(北京外国语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0)
一、问题的提出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领域中的一门重要学科,目的在于开发各种机器与系统,这些机器和系统能够在有限或者在完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其主要任务。在和人工智能“阿尔法狗”的对局中,全球第一围棋选手柯洁也接连被打败。清华“九歌”人工智能已经可以自动生成诗歌,在诗词大会上与选手PK时惊艳四座。人工智能系统,它可以通过对大量数据的分析和复杂的计算,掌握之前只有人类才能运用的围棋或者语言能力,甚至做得比人类更好。
计算机的发展和使用,也带来了很多人们所关心的社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内容便是:人工智能所生成的内容是不是属于作品?如果属于那么著作权是如何归属的?现在的人工智能确实也可以通过预定的流程和计算,或者使用机器学习,制作在表面上和人们创造的产品相近似的内容。[1]比如,德国研发的一种绘画机器人可以为真人绘制素描,如果不说这些素描是机器人绘制的,人们都会认为他们就是画家所画。同样,我国技术人员开发的新闻报道足以以假乱真,使大部分读者都以为是记者所撰写的作品。
二、实务界与理论界关于生成物作品性不同的声音
在司法实务中也会有许多人工智能生成物侵权的纠纷,不同法院的法官对此会有不同的观点。2019年,在北京百度公司诉北京菲林律著作权纠纷一案诉讼中,原告控诉被告在其未经书面授权委托的特殊情况下擅自发布威科先行库生成的文章,损害了其著作权。北京互联网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计算机软件智能生成的文字内容体现了针对相关数据的选择、判断、分析,具有一定的独创性。但是,自然人创作完成应是著作权法上作品的必要条件。计算机软件智能生成文字内容的过程有两个环节有自然人作为主体参与,一是软件研发环节,二是软件使用环节。但软件智能生成的文字内容并未传递软件研发者及使用者的思想、感情的独创性表达,故二者不应被认定为软件智能生成的文字内容的作者。人工智能软件利用输入的关键词与算法、规则和模板结合形成的文字内容,某种意义上讲可认定是人工智能软件“创作”了该内容。但即使人工智能软件“创作”的文字内容具有独创性,也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不能认定人工智能软件是其作者并享有著作权法规定的相关权利。相似的情况还发生在腾讯公司诉盈讯公司侵害著作权一案中。该案中原方告诉记者称,被告并没有权限发表由腾讯机器人公司制作的财经论文,侵犯了其知识产权。法庭经审查后认为,涉案文字已经构成了著作权法中的文字作品。上述两个案件均涉及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构成作品以及该生成物的权益归属问题,两个地方法院却从不同专业角度上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软件著作权问题做出了两个截然不同判决,这至少反映出了当前司法实务界普遍对著作权这一敏感问题存在的一些认识还并不统一。目前,主流观点认为部分人工智能的产物属于著作权保护的作品。对于我国如何能够在软件著作权范畴内依法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的这个问题,学界仍存在着许多相关争议,莫衷一是。就人工智能是否还可依法被司法机关赋予一定法律人格功能的相关争论,也存有“确定说”和“否决说”。“肯定说”借鉴了欧洲议会草案中“电子人”的概念,主张为机器创立独立人格的法律地位。“否定说”强调了“人类中心主义”原则,即认为只有人才具有在法律实践上应有的司法主体地位。在“否定说”的框架下,学界就著作权的归属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熊琦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物是设计师思想与用户自由意志的延伸,在符合独创性要求的前提下,著作权由人工智能的所有者拥有。[2]许春明等则主张,著作权主体为人工智能的设计者或拥有者[3]。
三、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产生过程
可以看出我国学术界存在明显的意见分歧。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搞清楚人工智能是如何生成内容的,为此可以先对比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将一首曲子的五线谱改成简谱,第二个例子是将英文写的小说译成中文。显然,第一种情况形成的不是作品而是作品的复制件,这一过程是复制而不是创作。原因在于五线谱和简谱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对应关系,任何人只要按照规则去做,不出错,结果都是一样的。相关的工作没有给任何人留下发挥聪明才智的创作空间。但英文小说与中文译文之间的文字组合,遣词造句。即使是同一名翻译者,两次翻译同一部英文小说,也可能因为他对原文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以及情绪的变化或者波动发生差异,从而形成不同的翻译。这也说明带有作家个人聪明才智的个性烙印,是作家个性化创造的产物。凡是由算法,规则和模板直接决定的结果,无论算法,规则是多么复杂和先进,甚至他们本身属于具备高度的创造性的发明创造,由此形成的内容都不可能是符合独创性要求的作品。
对于美图软件,它虽然可以将图片处理成印象派等各种绘画风格,而且会使很多人误认为是画家绘制而成的,但这一过程是创作吗?[4]只要对比人的创作就可以得到非常清晰地答案。在画家们看来,要将同一幅照片变成印象派风格的作品,二者并不具有严格的相对关联性。以同一张照片为基准,不同的画家都能够绘画出无数被称之为印象派风格的作品,而尽管每个画家都必须坚持印象派的基本画风,但要保持原图的基本内容,在绘画中也就给作画者们留出了自由发展的空间。作画者往往能够通过自身对原图的认识以及对印象派画风的深刻体会,对颜色,亮度和风格等多方面做出取舍与决定,以表现其自己的思想感情。从而形成的画作往往带有高度个性化的特点,多名作画者在具备同样专业水平的情形下,以相同照片为基准,所绘画出的印象派作品也将会产生巨大不同。当然,不同绘画者也可能基于巧合而画出相似的画作,但巧合在实际中很少发生,原因就在于作品反映个性和情感,而每个人的个性和情感都是不一样的。
采用人工智能技术的美图软件对图像进行了风格变换的结果,本质上是由算法所决定的。该计算可以在分析了数千幅图片之后,确定各种风格间的相应关联,从而让美图软件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图片处理过程。不过,不管这套计算多复杂、优秀并富有了创意,使用同一计算的软件系统通过切换图片设计风格所取得的成绩都不会相差。这也从本质上消除了过程中的创意空间,也消除了数据处理结论具有人性化特征的可行性。所以,由此形成的画面不可能是作品。[5]
同样的道理,在表现形式上最贴近于人体创作的“机器人作诗”不可能达到独创性的要求,机器人创作与真人创作在性质上是不具有可比性的,真人创作随着人的思想,感受和心情是会发生变化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小说的原作家们在因计算机故障或遗忘备份后对丢失的文件手稿等唯一的文字事情深恶痛绝,原文中那些精彩的内容和表述也无法再现,而这些现象也正是作者独创性的表现,这也使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写作有别于严格地根据算法,规则和模板直接生成内容的过程。
“自动媒体创作”也使用了算法模板。这类人工智能创作的关键点就是可以根据某类文字,如经济社会报道,体育运动报道等,研究出针对自身资源进行分门别类的计算方式,然后再把经过运算处理后的自身资料数据分门别类,套进各种系统模块。比如,对NBA比赛进行直播报道的自动撰写软件的内核主要是二样东西:一是上百种模板,这种模版主要是按照数据信息的分类方式和对以往比赛的报道的所使用语言而制定的,类似于具有固定格式,栏目和标题的表单。二是由开发者建立的比分差函数,利用算法对数据信息进行了细分,并填充在具体的模块中。而由此形成的结果也正是由算法和模块所确定的。应用了相同算法和模板的自动写作软件只要获得的数据是相同的,产生的结果就是相同的或者是有限的。准确的说这些作品是计算出来的,而非创作出来的。[6]
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最终成果具有独创性,即使形成过程应用了算法,规则和模板,也应当承认成果是作品。对此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仅仅是以算法,规则和模板为基础进行智力创作,产生了因人而异,反映个性化选择与判断的成果,则该成果当然可以成为作品。比如作家创作小说也有一定的规律、套路和模式,但他们不可能决定小说的内容。从故事情节到文字组合,遣词造句,体现的都是作者个人的聪明才智。由此形成的小说当然是作品。但是,在上面分析的几个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例子中,无论是绘画还是新闻报道亦或者是创作诗歌,都是由算法、规则和模板直接生成的。这里的关键在于,只要算法、规则和模板确定了,所得结果就是唯一或者只产生有限的可能。当然,设计者可能会刻意加入随机因素本质上也是由算法决定的,与创作的思想、情感等个性特征毫无关系。
四、著作权的立法目的以及保护范围
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是鼓励作品的创作,而鼓励创作的方式是通过赋予作者一系列权利,确保他人在利用作品时经过作者许可并向作者支付报酬,从而使作者从创作中获得应有的回报,能够体面地生活,保持继续创作的动力。[7]那么谁能够在这套激励机制中获得动力呢?答案是只能是人。郑成思教授对此指出: 不论何种人持何种看法,在认定版权制度的本质是鼓励用头脑从事创作之人[8]。这一点上,意见是一致的。无论是动物还是机器,都不可能因著作权法保护作品而受到鼓励,从而产生创作的动力。[9]2009年我国《著作权法》 第 2 条将享有著作权的主体限定为“中国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和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无国籍人”, 印证了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人工智能的生成物不能构成作品。
五、关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权利保护问题
虽然说人工智能生成物不属于著作权法中的作品,但是对于其权利的保护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在新兴科技产业中,人工智能智力成果已经在生活与生产发挥重大作用,人工智能的创新与发展引发法律学术界和社会大众以及科技领域人士的重新思考。在现实社会中,在音乐作品、电影作品,电子游戏、电脑软件中,大部分内容是人工智能智力产生的成果。我们还在讨论这些人工智能智力成果究竟是不是作品的时候,市场中大众消费者很久就已经在消费人工智能产生的成果,甚至对这些产品产生了某种依赖,他们并不十分关心这些成果是到底由人来创作还是由机器人创作。关于人工智能的知识产权领域是一项全新的领域,在这其中包含了巨大商业利益,对知识产权领域的贸易具有十分重大影响,如果我们不认可和保护人工智能智力成果的产生的财产利益,将会严重影响人工智能产业的健康以及可持续发展。所以说我们认同人工智能智力成果的法律地位,也是对产业利益进行保护的必然要求。
关于人工智能的生成物有过以下这几种保护的行为模式。第一种保护模式是以合同保护的保护方式,易继明教授也认为,对人工智能项目的最终生成物财产利益在保护体系中的我们认为首先就应该更注重于保护投资人方的自身利益,同时也我们更加需要更重视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项目投资者,设计者方以及项目使用者各方之间相关的权利合同和约定,并且还要根据法律当事人意思表示自治平等的平等原则去确定其权利财产的具体归属问题以及具体解决此类纠纷解决问题的方式[10]。在法律当事人双方没有任何约定效力的实际情况条件下,就更应该注意建立比较合适的诉讼权利的归属法律制度,以此来解决发生在实践中的纠纷。这种模式还具有一个实际上革命性的科技进步创新意义,这种创新模式要求在各方认可现有人工智能智力成果财产权利性质的合理前提条件下,在对人工智能成果投资人、设计者、人工智能所有者之间以及对人工智能作品所有权的最终使用者各方之间进行技术利益基础上有效的技术平衡,通过以合同协议的契约方式来保证在其他各方相对自由平等的合作条件约束下自由约定相关人工智能智力成果权利性质归属义务的契约方式,优先实现对相关人工智能作品的产权归属的问题也进行作了相应制度层面上合理的安排,在一定程度可以减少纠纷,有利于解决实践上的问题。第二种模式邻接权保护模式。 邻接权是广义上著作权的部分,它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狭义的著作权, 其方向不在于保护作品的创造性,而侧重于作品的传播。这也符合人工智能产物的特征,对这种生成物采用邻接权的保护模式更具有可行性。既然我们说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创造性与人类作品相比较来说较低,那么在保护的程度方面也应当随之降低。[11]首先从时间方面来看,邻接权的期限都是比较短的,并且由于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人工智能的升级换代更是频繁,将其保护的期限设定的较短,和科技发展的脚步相吻合。 其次,在权利内容方面,机器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不能够享有人身权。但是我们可以赋予其一定程度的法律人格,可以享有署名权,因为署名权能够实现对不同生成物的产生者,即对人工智能加以区分。对于财产权方面的复制、信息网络传播等权利应当予以保留,财产权利的保留可以视为是对机器的使用人或是研发人员辛勤劳动付出的回报,使其合法权益能 得到法律上的认可和保障,能够更加鼓励其进一步研发、革新。这和合同模式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最后,由于目前邻接权的现有内容还不包含人工智能方面的具体规定,运用表演者权、录音录像制作者权等现有权利来规制也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可以适当地增添相应规定, 使人工智能生成物能够直接通过邻接权的模式得到法律的保护。
六、小结
人工智能可以通过远超人类所及的复杂和精密的计算模仿人类创作的作品,甚至用算法模拟人类创作的过程,一个会弹奏音乐的人工智能有了人的情感,此时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就不再是著作权的归属问题,而是我们是否会沦为机器的工具的问题了。著作权是激励创新,保护智力成果的重要法律制度,但绝不是唯一的法律制度。著作权法有其自身的逻辑和理论,如果抽走了任何作品只能来源于人的创作这块基石,著作权法的大厦将轰然倒塌。对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也许是有必要的,但将该内容认定为作品并提供著作权保护并非明智之举。在未来,需要密切关注人工智能生成物保护的法律需求和事实需要,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生成物在版权保护方面的理论研究和相关法律法规,有效地保证创作者的合法权益,积极推动出版行业在大数据时代有序、健康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