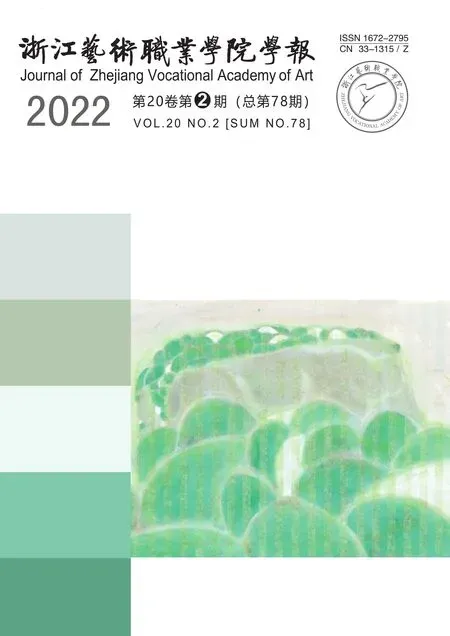怎一个“拟”字了得?!
——从明清女曲家其人其作观照中国女性之独立
郭 梅
一般认为,中国的女性创作自《诗经》 中的许穆夫人始,中经汉唐的蔡文姬和李冶等,到两宋的李清照和朱淑真等,代不乏人。明中期以后,女作家的人数及其作品的数量日益增多,女性文学堪称繁盛,且尤以江南地区为最。值得强调的是,除了继续深耕诗词文赋等传统文体以外,明清才女中还涌现了曲家、弹词家和小说家。其中,以叶小纨、王端淑、吴藻、刘清韵和陈翠娜等为代表的女曲家,用她们的作品和自身遭际写就了一部中国女性的独立心路史。
叶小纨,字蕙绸,江苏吴江县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卒于清顺治十四年 (1657),乃叶绍袁与沈宜修夫妇的次女,嫁曲坛盟主沈璟之孙沈永祯为妻。她诗作极多,晚年汰存二十分之一,编为《存余草》,还留下了我国戏曲史上第一部由女性曲家撰写且保存完整的杂剧《鸳鸯梦》。
叶绍袁和沈宜修分别出自汾湖叶氏和吴江沈氏,俱为书香门第。沈宜修是吴江派魁首沈璟的侄女,叶小纨的两个舅舅沈自徵和沈自晋亦均为吴江派的扛鼎人物。叶绍袁曾在其《午梦堂集》 的序言中如是强调:“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妇人亦有三焉,德也,才与色也,几昭昭乎鼎千古矣”,将女子的“德、才、色”和男子的“德、功、言”相提并论,足见其对女性之“才”的重视和推崇。而沈宜修在孩子一二岁时即口授《毛诗》 《离骚》 和《琵琶行》 等,叶小纨和姐姐叶纨纨、妹妹叶小鸾无不深受影响。
叶小纨的《鸳鸯梦》 作于崇祯九年(1636),不仅“补从来闺秀所未有”,也开创了女性写作戏曲的“拟男”之风,更成为女曲家为实现自己的“鸳鸯梦”“名士梦”和女性人格独立而发出的第一声呐喊。
《鸳鸯梦》 遵循元杂剧“四折一楔子”的体制,也采用元杂剧中较为常见的神仙道化剧形式,写西王母的侍女文琴、上元夫人的侍女飞玖与碧霞元君的侍女茝香,因“偶语相得,松柏绾丝,结为兄弟”,被西王母以凡心稍动为由而谪罚人间,投生于汾水湖滨,分别转生为蕙百芳(字茝香)、昭綦成(字文琴)、琼龙雕(字飞玖)三位书生。蕙百芳于梦中与两位挚友相见,结为兄弟。一年后的中秋佳节,蕙百芳惊闻琼龙雕病逝,吊丧时又接到昭綦成因好友过世悲伤过度一病而亡的噩耗! 他悲痛欲绝,万念俱灰,幸得吕洞宾指点,悟到“人生聚散,荣枯得失,皆犹是梦”,终于与昭綦成、琼龙雕一起重归天庭。该剧首先表现兄弟友情,抒发好友早逝的悲痛:
〔水仙子〕 我三人呵, 似连枝花萼照春朝, 怎知一夜西风叶尽凋? 容才却恨乾坤小。想着坐花阴命浊醪, 教我凤台上空忆吹箫, 只期伯牙尽去知音少。 从今后凄断广陵散, 难将绝调操, 只索将鹤煮琴烧。
〔收尾〕 哥哥, 兄弟! 你原来要辞苦海离尘早, 一灵已往蓬莱岛。 这的是生生死死还同调, 俺可也石上相逢应不杳。
(伤哉志也, 似孤雁鸣空, 不堪嘹呖。)
崇祯五年(1632),叶小鸾在婚前五日去世,年仅十七岁。七十天后,大姐叶纨纨也因悲伤过度而撒手人寰,年仅二十三岁。叶小纨与姐妹间感情极深,常常将伤姐悼妹之情形诸笔端。崇祯八年(1635),叶小纨归宁,路过小鸾生前居住的疏香阁,写下《乙亥春仲,归宁父母,见庭前众卉盛开,独疏香阁外古梅一株,干有封苔,枝无剩瓣,诸弟云:“自大姊三姊亡后,此梅三年不开矣。”嗟乎! 草木无情,为何若是! 攀枝执条,不禁泪如雨下 也》。第 二年,她 又写了 《鸳 鸯 梦》——“蕙”“昭”和“琼”分别是小纨(字蕙绸)、纨纨(字昭齐)、小鸾(字琼章)字号的第一个字,而且琼龙雕十七岁、蕙百芳二十岁、昭綦成二十三岁,也正与姊妹仨在现实中的年龄相吻合。沈自徵在为该剧所作的小序中说:“ 《鸳鸯梦》,余甥蕙绸所作也。诸甥姬皆具逸才,谢庭咏絮,璧月聊辉,洵为盛矣。迨夫琼摧昭折,人琴痛深,本苏子卿‘昔为鸳与鸯’ 之句,既以感悼在原,而琼章陨珠,又当于飞之候,故寓言匹鸟,托情梦幻,良可悲哉!”清代学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谓《鸳鸯梦》 为“伤姊妹而作者”,《吴江县志》 亦载叶小纨“幼端慧,与昭齐、琼章以诗词相倡和,后相继夭殁。小纨痛伤之,乃作 《鸳鸯梦杂剧》 寄意”,可见,《鸳鸯梦》 一直被公认为悼念早逝姐妹的作品。
不过,窃以为,除了哀悼手足,实际上在《鸳鸯梦》 中还深藏着叶小纨自己的“鸳鸯梦”——《鸳鸯梦》 正名《三仙子吟赏凤凰台 吕真人点破鸳鸯梦》,“鸳鸯”既是剧名中的关键词,又是贯穿全剧的线索,最后作者还以“点破鸳鸯梦”结穴,显然大有深意。首先,楔子中就有“并蒂莲”和“鸳鸯”的意象——
(上介) 你看台下一池, 池中莲花盛开,红妆映日, 翠盖擎风。 你看那莲中有一朵并蒂者, 十分艳冶光辉, 更是可爱也!
〔仙吕赏花时〕 这莲呵, 须不是太一飘来海外风, 也不是玉女愁窥华井容。 你看他相倚笑绿波中。 奇怪也! 你看莲花池畔有鸳鸯一双, 游戏于莲蕊之间, 多少和鸣相传! (内作风起介) 呀! 一阵狂风将并头莲吹折下来, 惊得那两两鸳鸯, 冲天飞去, 只有断红零叶, 浮漂碧沼之中, 好是凄凉人也!
盛开的并蒂莲在绿叶的衬托下娇艳欲滴,美不胜收,鸳鸯在满池花叶间欢乐地和鸣—— “和鸣”二字常见于“琴瑟和鸣”,喻夫妻和睦,而“并蒂莲”更是比喻夫妻恩爱。然而无奈狂风吹折并蒂莲,体现了叶氏姐妹各自婚姻的不堪——不愿出嫁的叶小鸾因遭夫家催妆甚急,在婚前五日去世;七十天后,叶纨纨也因悲伤过度而撒手人寰。叶纨纨十七岁嫁给袁祚鼎,夫妻感情淡漠,婚后“七年之中,愁城为家”。她去世后只有婆婆若思夫人携小姑前来吊祭,长婿袁祚鼎竟连奔丧都不愿来,作为父亲的叶绍袁这才意识到爱女的婚姻极其不幸:“岂意荣盛变为衰落,多福更为薄命,眉案空嗟,熊虺梦杳,致汝终年闷闷,悒郁而死。”纨纨的棺木一直停在娘家,直到十年后的崇祯十五年(1642),袁祚鼎才 “迎昭齐之殡,归葬于其新阡”。而叶小纨本人嫁给了母家的表兄沈永祯,婚后“随夫迁居江干,贫不可言”。且其夫早逝,只给当时年仅三十四岁的小纨留下独女沈树荣。
需注意的是,三姐妹的母亲沈宜修拥有美满的知音式婚姻,换言之,叶家姐妹是在父母亲琴瑟和鸣的氛围中长大的,对自己的婚姻自然有着和所有青春女子一般无二甚至更为美好的遐想与期待,如叶纨纨的《菩萨蛮》 就写出了少女的春怨:“关情双紫燕,肠断鸳鸯伴。无奈武陵迷,恨如芳草萋”。而叶小纨未出阁时也曾写过“无端捉得鸳鸯鸟,弄水船头湿尽裙”和“争寻并蒂争先采,只见花丛不见人”( 《采莲曲》 )的诗句,还有叶小鸾题《西厢记》 《牡丹亭》 的诗里有“似怜并蒂花枝好”( 《又题美人遗照》 )之句,无不体现了对真挚爱情的向往。遗憾的是,现实与理想的落差甚巨,纨纨夫妻不睦、小纨盛年寡居,小鸾甚至还未踏入婚姻便早早夭亡。换言之,叶氏姐妹的闺中生活快乐自由,然而出阁后便鸳鸯梦醒,欢愉难再。正如《鸳鸯梦》 第四出所言:“迷途一去不知还,慷慨空教泪暗潸。欲摘荷花寻并蒂,鸳鸯惊起绿波间”,出嫁成了姐妹们一去不返的“迷途”——叶绍袁和沈宜修将长女、三女分别许配叶绍袁的好友之子,将次女叶小纨许配沈宜修的亲侄子,三桩婚事无不门当户对,显然寄予了父母的殷切希望,可惜结果颇不如人意。
明清时女子盲婚哑嫁,能否幸福几乎全凭运气。叶纨纨和叶小纨婚后夫妻感情一般甚至淡漠,纨纨“熊虺梦杳”,小纨也仅有一女,与沈宜修的八子五女形成鲜明的对比。叶小纨为圆自己和姐妹们的“鸳鸯梦”,在《鸳鸯梦》 中特意将三人吟咏之所设于凤凰台:
(行介) 呀! 前面果有高台一座, 登临景色, 恍与梦中相似。 你看台上标题着“凤凰台” 三字, 古人豪吟雄句, 端的是名胜之所。只是孤游无聊, 如何得一二良友, 临风快谈也? (楔子)
(末上) 小生蕙百芳, 得遇文琴、飞玖兄弟, 洵是千古异人。 今日相约游赏凤凰台, 小生索先往, 此时如何还未见到? 正是: 风飘黄叶下, 疑是故人来。
(昭、琼上) (云) 昨日相约茝香, 同到凤凰台玩月, 须索走一遭也。(第一出)
“凤凰台”,典出汉代刘向的《列仙传》,是传说中萧史和弄玉的定情和成仙之地,叶小纨安排主人公在凤凰台欢聚,显然是希冀姐妹仨也能拥有萧史和弄玉般的夫妻恩爱吧!
众所周知,有明一代,对“情”的极致演绎莫过于汤显祖的《牡丹亭》。汤公推崇“至情”,强调“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在剧中安排杜小姐惊“梦”、寻“梦”,继而圆“梦”,对女性命运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改写,在完成这个催人泪下的故事的同时也催生了“女性意识”的萌芽。
“女性意识”是指女性开始关注自身的生存状况,审视女性特有的心理情感和表达自身的生命体验,开始对追求独立人格有清晰的认识和体悟,并拒绝完全接受传统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定义和约束,同时对男权提出一定的质疑和挑战。但封建社会加诸女性的重重枷锁使女曲家们很难直抒胸臆,只得在纸上将自己变成男子,或采用女扮男装的手法,使主人公主动追求爱情和功名的做法合情合理化,这种艺术手法就是“拟男”。叶小纨的《鸳鸯梦》就采用拟男法,在剧中不仅做着希冀婚姻美满的“鸳鸯梦”,还慨叹怀才不遇、壮志难酬,做着更进一步的“名士梦”,渴盼有朝一日自己能身着紫袍、手持牙笏,做出一番惊天的事业来:
〔仙吕点绛唇〕 数载漂蓬, 暮吟朝诵, 空磨弄。 壮志如虹, 命蹇才无用。 哥哥, 我想半生遭际, 真堪叹也! 抵多少贾谊远窜, 李广难封。 可怜英雄拨尽冷炉灰, 休休! 男儿死守酸虀瓮。 枉相思留名麟阁, 飞步蟾宫。(第一出)
从蟾宫折桂到麟阁留影是封建时代所有读书人的最高理想,也是叶小纨的梦想。蕙百芳如是夫子自道:“幼习儒业,博览群书,奈年已弱冠,功名未遂”,在结识昭綦成和琼龙雕两位好友后,又忍不住诉说功名未就的怨气:“ 〔天下乐〕 又有那旅客家乡信不通,孤蓬睡眼瞢,助凄凉月色如水溶。是书生未遇时,伴孤灯一点红,谁如这啸台高耸?”可以说,叶小纨藉《鸳鸯梦》 抒写和实现自己姐妹重逢且各自姻缘美满的鸳鸯梦,以及功成名就的名士梦,就此层面而言,其内涵已超越了《牡丹亭》 的“至情”。可惜,叶小纨能想到的自由和理想的最高境界就是像男子一样蟾宫折桂、麟阁留名,尚未曾真正突破闺阁的限制和束缚。而且在当时的社会里,才女的美梦也最多只能铺陈在纸上,并不可能有机会付诸实现,最终,叶小纨不得不借琼龙雕之口长叹一声:“使我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
必须强调的是,只要社会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才女们的命运也就不可能有大的转折,她们只能一代又一代、一次又一次地,在纸上重复着美好的鸳鸯梦、宜男梦,还有进一步的拟男梦和名士梦——明末清初的叶小纨如是,清末明初的刘清韵亦如是。
相较于只能在纸上描摹美梦建构理想家园的叶小纨和刘清韵——尤其是刘清韵殁于“五四”的曙光前夕,端的令人扼腕叹息——与叶小纨一样生活在明末清初的王端淑和比刘清韵早出生约半个世纪的吴藻,似乎幸运一些,但也只是小幸而已,“拟男”和 “名士”等美梦,她俩也没有机会成真。
吴藻 (1799—1862),字蘋香,自号玉岑子,仁和(今杭州)人,以词名世,有《花帘词》 一卷、《香南雪北词》 一卷,戏曲代表作是独幕剧《饮酒读骚图》 (又名《乔影》 )。
吴藻自幼衣食无忧,受到了良好的闺中教育,长大后又嫁进门当户对的商贾之家。丈夫虽不擅文墨,但并不反对妻子沉醉翰墨书香。她既无经济上的困窘,也可走出家门广交师友,甚至有幸成为名士陈文述的女弟子。吴藻喜欢改换男装,甚至还曾出入青楼游戏人生。她认定是女儿身阻碍了自己追求自由,恨不能真正变成男子:“愿掬银河三千丈,一洗女儿故态。收拾起断脂零黛,莫学兰台愁秋语,但大言打破乾坤隘;拔长剑,倚天外。”可不管她的行为如何惊世骇俗,她的才华如何令不少男性文人激赏,终究无法彻底摆脱闺阁的束缚,而其代表作杂剧《乔影》 便是其自伤之作,主人公谢絮才也显然就是其夫子自道。
《乔影》 写谢絮才自画男装小影一幅,名为《饮酒读骚图》,挂于书房墙上,对像饮酒读《离骚》,自比屈原,慨叹身世:
百炼钢成绕指柔, 男儿壮志女儿愁。 今朝并入伤心曲, 一洗人间粉黛愁。 我谢絮才, 生长闺门, 性耽书史, 自惭巾帼, 不爱铅华。 敢夸紫石镌文, 却喜黄衫说剑。 若论襟怀可放,何殊绝云表之飞鹏; 无奈身世不谐, 竟似闭樊笼之病鹤。
一支〔雁儿落带得胜令北〕 酣畅淋漓地宣泄了她对外部世界的向往和对自由的渴望:
我待趁烟波泛画棹, 我待御天风游蓬岛,我待拨铜琶向江上歌, 我待看青萍在灯前啸。呀, 我待拂长虹入海钓金鳌, 我待吸长鲸贳酒解金貂, 我待理朱弦作《幽兰操》, 我待著宫袍把水月捞。 我待吹箫比子晋还年少, 我待题糕笑刘郎空自豪、笑刘郎空自豪……
在曲中,吴藻借用历史上诸多奇人异士的想象和传说,一口气甩出长达十句的排比句以及一连串典故,以李太白、王子乔、刘禹锡等著名的俊逸神仙、洒落文士自喻,直抒胸臆,气势磅礴,表现出绝对的自豪与自信,表达了渴望发展个性、展现才华、向往极致自由的迫切心情,从中可看出她渴望自由的急切热烈和其本人的豪迈俊爽。
与叶小纨、刘清韵相比,吴藻的反抗意识较明显强烈—— 《鸳鸯梦》 的主人公是男子,叶小纨是假托男性身份与视角去抒写女子心中难以实现的美梦,用的是拟男手法;而《乔影》 的主人公虽披上了男装,但并不避讳女性身份,可谓“半拟男”,是吴藻以女性的视角和身份去体验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从鸳鸯梦、宜男梦到名士梦的各种女儿梦,更能反映女性的真实内心。换言之,出身优渥、个性也较张扬的吴藻,其创作意识较超前、女性意识较激进,其“名士梦”也更高远,或可谓之曰“侠士梦”。
但是,终《乔影》 全剧,谢絮才也只是宣泄愤懑,表达对自由独立的渴望而已,吴藻最终只能让她醉酒下场,却并不能提出走出困境的根本方法。也就是说,“梦”醒后,吴藻发现自己依然身处男权世界,最终选择青灯古佛了却余生。可以说《乔影》 虽然在女性意识上超越了《鸳鸯梦》 等,但也终究只是画饼充饥聊以自慰罢了。不过,从《乔影》 可知女曲家笔下的女儿梦至少已从“山在虚无缥缈间”发展到了“犹抱琵琶半遮面”,而替叶小纨、吴藻部分实现梦想,从“名士梦”逐渐过渡到“侠士梦”的,是女曲家王端淑。
王端淑 (1622—1702),字玉映,号映然子,又号青芜子、吟红主人,浙江山阴 (绍兴)人,晚明文学家、万历年间进士王思任(1575—1646)之次女,丁圣肇之妻。她对中国妇女曲史的重要贡献是所辑录之《名媛诗纬》 中的三十七、三十八两卷收录了黄峨、徐媛、梁孟昭、沈蕙端、郝湘娥、沈静专、呼文如、蒋琼琼、楚妓、马守真、景翩翩和李翠微等明代女散曲家的作品,基本上是我们现在所能找到的明代女子散曲的全部。她还简单记录了每位女曲家的身世,为后人 “知人论世”提供了可能性。
王端淑自小聪慧,颇具男儿气概,王献定所撰《王端淑传》 云:“四岁观剧演善财,效之,以母为观音,叩拜不已……喜为丈夫妆,常剪纸为旗,以母为帅,列婶为兵将,自行队伍中拔帜为戏。”七岁左右便由母亲姚氏教导吟诗作赋,父亲见之笑曰,“汝曷不为女状元”。王端淑有兄弟八人,但王思任独独钟爱端淑,曾言“身有八男,不及一女”。
崇祯七年(1634),王思任到九江赴任,豆蔻年华的王端淑随父同行。当时匪寇成患,父亲坚守不退,危急中欲派人送妻儿回乡避难,但王端淑坚决不从并慷慨陈词:“吾母子宁从父死贼,岂偷生求活耶?”铮铮铁骨,不逊男儿。
王思任将爱女许配丁乾学的儿子丁圣肇。丁乾学是东林党人,被魏忠贤迫害致死。丁圣肇年少时并不懂事,但王思任重然诺不愿悔婚。婚后,王端淑依旧笔耕不辍,丁圣肇为《吟红集》 所作序言云:“内子性嗜书史,工笔墨,不屑事女红,黛余灯隙,吟咏不绝。”他们夫妻和睦,可惜王端淑和刘清韵一样不育。崇祯甲申年(1644),清兵大举入关,丁、王夫妇被战火滞留于浙江衢州。同年春,王端淑主动出资为丈夫纳妾——据其《名媛诗纬初编》 卷十七记载:“陈素霞,字轻烟,南京人,甲申春归夫子,予脱簪环为聘。”陈素霞颇有文才,敬顺端谨,颇得丁圣肇的喜爱,并进而影响了丁圣肇和妻子的关系,王端淑曾在诗中直陈愁苦。
丁家经济困窘,王端淑见丈夫无力养家,毅然走出家门做了闺塾师,同时卖文售画,自食其力,成为当时极少见的职业女性。她在《答浮翠轩吴夫人》 中曾如是描述当时的窘迫:“素守清贫只自知,世人欲杀忌才思……此情愿博芸窗史,故向朱门作女师。”她和吴藻一样,不仅与黄媛介等才女频繁交往,还常与男性文人互相酬唱,不仅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也主导了家庭的人际交往——她曾替丈夫代写了许多诗、书信、墓志铭等,形成“男主内女主外”的模式。其叔父王绍美曾云:“映然子既得使今古闺中人不代女士受贬,又使今古女士不为闺中留恨,厥功既伟,何妨共宝天下乎?”也就是说,她凭借自己出众的才华,在当时的文化现场成功地做到了以“名士”风范气度与男性士人平分秋色。而这,既仰仗其刚强的个性与过人的禀赋,也受益于当时江南地区揄扬才女的浓郁文化氛围。
可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囿于时代的局限,饶是王端淑个性刚强才华横溢,她也始终未曾完全挣脱“拟男”的窠臼而真正赢得经济、政治的独立,并真正得享自由。与仅比她大八岁的叶小纨相比,王端淑之“幸”,或许只表现在她敢于走出家门做闺塾师,而叶小纨寡居后是和舅母李玉照一起生活。但,倘若小纨也无人可依靠不得不选择做闺塾师自食其力呢? 故而,不必说叶小纨、王端淑这样的闺阁弱质,即便是公认侠骨铮铮的革命家秋瑾女侠,在风雨如磐暗夜沉沉的晚清,也只得选择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将一腔碧血洒在古轩亭口,以警醒华夏万民。才女们要真正实现自己的名士梦、侠士梦,必须等待和倚仗时代的巨大变迁,而在江南女曲家中,唯一真正得以拥抱新时代曙光的,是陈翠娜。
陈翠娜 (1902—1968),原名陈璻,字翠娜,又字小翠,别号翠楼、翠吟楼主,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有《翠楼吟草全集》 二十卷。
只比刘清韵晚出生半个世纪的陈翠娜因恭逢沧海桑田的时代巨变,可谓十二万分的幸运。陈栩将爱女嫁给汤寿潜的儿子汤彦耆——汤寿潜是当时著名的社会贤达,曾以领导浙江人民反对清廷借外债筑路而驰誉全国;汤彦耆也并非纨绔子弟,出嫁前,陈翠娜并不曾有抗婚之念,相反,其《闺词·嫁前》 还怀有对婚后生活的希冀:“云鬟乍挽同心髻,笑遣旁人不许看”。可婚后不久便夫妻情感不谐,最终分居。
主动选择与丈夫分居的陈翠娜和仅仅数十年前也是主动与丈夫分居的刘清韵,情况大不相同。陈虽只比刘晚出生五十年,但她却幸运地拥有了天时、地利、人和——在中国女性解放时代大潮的剧烈冲击下,女性逐步觉醒,何况陈翠娜生活在经济文化发达、开风气之先的沪杭地区。换言之,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像陈翠娜这样的知性女子展示才艺提升自我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于是她逐渐成长为现代知识女性,笔下时挟时代风雷,比如〔仙吕入双角套曲〕 《梦江南曲》 就是以1938年日军入侵江浙为历史背景,以对比手法描写江南的昔盛今衰,其中〔山坡羊〕 中的“你看翠生生一行春草,曲湾湾几折红桥,碧沉沉垂柳千条”,与〔沽美酒带太平令〕 中的“俺只见软浓浓媚春光的花草,扑朔朔避生人的鹜鸟,碧晶晶是玻璃碎料,红簌簌是宫墙半倒”,鼎足对的运用娴熟有力,结穴处“险不把一个铁如意敲碎了”一句则心情沉重气势沉雄,似见作者之铮铮铁骨和对祖国对家乡的赤子之心,颇具男儿气概。而在这样的作品里我们还可以看到陈翠娜和其他女曲家最大的不同就是她年代最晚,经历了五四运动和抗日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与叶小纨、吴藻等传统闺秀相比,陈翠娜是现代职业女性,甚至还是著名的公众人物。她经历了近现代的女性解放热潮,笔下也出现了吴藻等所无法企及和描摹的女性立场,如其《题女弟子周丽岚〈诗剑从军集〉 》 便是为女学生奔赴抗日前线的壮行之作,“愁亦醉人何必酒,死能殉国不求名”,在慷慨悲壮中寓有女儿报国不亚男子的豪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木兰从军等历史故事的思想境界。相较于丁玲等用白话文创作的先锋女性,陈翠娜在婚恋题材方面的表现可谓 “特立独行”,其《焚琴记》 《自由花》 等剧作告诉我们,她对爱情既没有浪漫不切实际的幻想,也不过于功利现实或偏重感慨悲叹,取而代之的是她对社会现实深刻清醒的洞察。她对女性的处境和如何自处,也有着与众不同的见解。《焚琴记》 的第十出《雨梦》 强调:“从今参透虚无境,好向那蝴蝶庄周悟化生。吓,愿天下的热中人齐悟省”(〔尾声〕 ),显然是借老庄哲学浇自己之块垒,告诫普天下片面追求自由解放的女子赶紧醒悟过来,尽力保持女性的独立和尊严。换言之,《焚琴记》 认为憧憬纯洁爱情的女性未必都能像杜丽娘和柳梦梅那样终成眷属,其女主人公小玉贵为公主尚不能得享爱情的自由,何况平常女子?! 剧 本文体虽 “旧”,思想却很“新”,具有十分强烈的现实意义。
纵观中国女性文学史和女性戏曲史,才女们往往命途多舛。为什么她们斐然的文采常用于书写自己的凄苦? 为什么她们生命列车的终点多为中年甚至韶年? 是什么主宰了才女的命运? 是性别? 是能力? 是个性? 是经济状况? 抑或是父亲、丈夫的开明程度和生育状况? 王端淑“卒年八十余”,刘清韵享年七十四,算得上寿终正寝。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里,她俩也都比叶氏姊妹幸运百倍,算得上得嫁檀郎。可她俩均不育,还都主动为丈夫纳妾,并因此或多或少影响了夫妻关系。王端淑的闺塾师生涯现在看来也许是她一生的亮点,但在当时这又意味着多少的酸辛无奈呢? 即便王端淑不被迫挑起家庭经济重担,衣食无忧的吴藻不照旧在《乔影》 里长吁短叹么?! 而在经济条件不佳的叶家,沈宜修至少在夫妻关系上是无可抱憾的。还有,刘清韵以为自己一生的不幸皆源于不育,但育有一女的叶小纨不照旧在《鸳鸯梦》 里诉说凄苦么?! 毋庸讳言,与这几位前辈才女相比,陈翠娜是唯一可以“任性”或曰得享自由独立的女曲家——出嫁前她不肯勤习女工,婚育后她也不愿受小家庭的束缚,主动选择分居。在“五四”浪潮中,她保持清醒,不随大流;在白话文运动风起云涌后,她也坚持只用文言写作。但她在形式上与叶小纨、吴藻、刘清韵一般无二的剧本里,我们找不到“拟男”,也找不到“半拟男”! 何也? 正所谓时代潮流浩浩荡荡,为之所裹挟的每个文人,无论才华高低个性强弱出生贫富,都只能在自己所处时代的土壤里勉力绽放创作之花,无一例外! 正如两宋之交的文人,无论男女无论官民无论旧党新党,其创作生涯无不被国破家亡的“南迁”之刀无情地割为两个往往截然不同的阶段。而假设本文提及的所有女曲家都生活在陈翠娜的时代,她们的生命显然将多一些亮色,她们的创作也将更为丰富,而拟男与半拟男手法也会随时代的变迁而被已可以大胆书写心曲的她们所弃捐。可惜,历史无法假设,这次第,怎一个“拟”字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