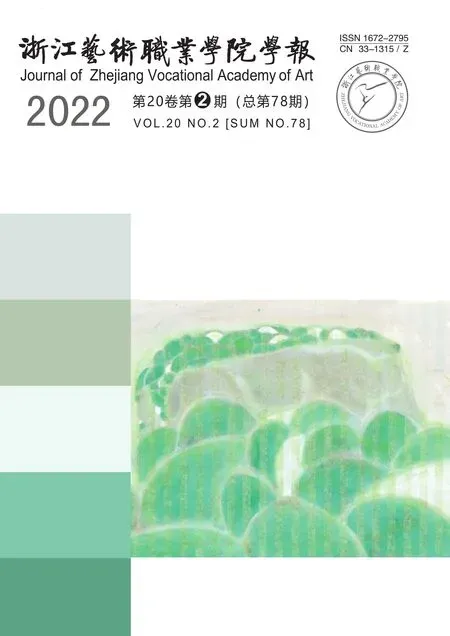信仰之光与古枝新绿
——评原创革命题材现代昆剧《瞿秋白》
张青飞
二十世纪以来,戏曲能否与如何表现现代生活,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重要话题。作为积淀深厚、成熟精致的古老剧种,昆剧如何突破现代戏创作瓶颈,使“百戏之祖”六百余年的古老枝干生发出勃勃新绿,也一直是当代戏曲艺术实践中的一大难题。近年来,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先后完成了现代戏《梅兰芳·当年梅郎》 (2019)、《眷江城》 (2020)、《瞿秋白》 (2021),以成功的舞台艺术实践证明了昆剧现代戏表现现代生活的可能性。尤其是后出的原创革命题材现代昆剧《瞿秋白》,作为难得一见的以昆剧书写红色主题的现代戏,在编剧罗周、导演张曼君及主演施夏明的合力下,在题材把握与戏曲化呈现上均令人耳目一新,散发着鲜活的现代性气息,具有成为昆剧现代戏创作里程碑式作品的潜质,其中蕴含的戏曲艺术实践经验也颇值珍视。
一、实虚互生的结构
作为情节的有机组织和安排,结构在戏曲创作中必然是举足轻重的。杰出的古典戏曲理论家李渔(1611—1680)高举戏曲独立的大旗,首次自觉而鲜明地提出“结构第一”[1]的原则,视结构为戏曲创作的首要命题,标志着古代戏剧理论中结构论的成熟,不仅抓住了戏曲创作的内在规律,也符合古今中外戏剧创作的一般规律。在当代戏曲创作实践中,罗周的剧作多采用 “四折一楔子”结构形态[2],不同于当下戏曲创作中常见的六场、七场乃至更多的场次结构,既具有意味十足的形式感,又逐渐打上了独异的罗氏印记而形成一种稳定的戏曲文体。
昆剧《瞿秋白》 以瞿秋白1935年5月被捕至1935年6月18日慷慨赴义的遭遇为史实基础,聚焦其被羁押于福建长汀狱中的生命最后一个月,以其心灵世界为切入点,书写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不忘初心,舍生取义”[3]的题旨。“戏曲搭架,亦是要事,不妥则全传可憎矣。”[4]全剧为避免拖沓之弊,打破传统传记体的戏剧结构,采用编剧罗周极具个人印记的 “新杂剧”四折结构,由《溯源》 《秉志》 《镌心》 《取义》 四折构成。
与以往不同的是,罗周将昆剧《瞿秋白》 每折剖为“昼”“夜”两部分,看似四折,实际却是由三对昼夜与一对夜昼构成,容量相应扩大了一倍。昼的部分为瞿秋白狱中遭遇,在史实基础上以顺序展开剧情,由宋希濂、王杰夫的 “三劝降”与“秋白之死”构成;夜的部分更能体现剧作家在史实基础上的艺术想象,包括瞿秋白困于囚室的三次“秋白之夜”,即分别与母亲金璇、知己鲁迅、妻子杨之华的三次跨时空会面,以及瞿秋白曾经的学生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在秋白赴义前的灵魂忏悔之夜。昼的“三劝降”,其实是古典戏曲最繁复的“三审三问”的变体,最后取义则是“三劝降”的必然结果;而夜主要择取“五伦”的母、友、妻三伦。剧中四折命名分别对应虚/夜、实/昼、虚/夜、实/昼,虚实兼顾,各有侧重,颇为考究,作者的匠心与妙思略见一斑。
在昆剧《瞿秋白》 每折的内部构造上,罗周充分吸收了规避南戏传奇冗长之弊而产生的折子戏的思维与内在结构方式,借鉴其脉络分明、层层推进的结构形态。如第一折昼的部分由身份点破、主义辩论、信仰坚守三部分构成,层层递进,凸显了瞿秋白信仰的坚定;第二折昼的部分为王杰夫劝降,分三个层次:谈前途、谈时务、谈棋局,步步递进,戏剧性愈来愈强;第三折的夜,分三个层次:盼秋白、梦秋白、别秋白,情感逐步达至高潮;第四折的夜,大致分做何事与如何做两个层次,步步逼向宋希濂灵魂深处。由此,每折内部层次井然、严丝合缝,别具婉转曲折之致。
昆剧《瞿秋白》 不仅每折内层次井然,脉络分明,而且每折昼与夜间互有照应和对比。第二折《秉志》 昼王杰夫言及“那蔡元培受鲁迅之托,在政府会议上,当蒋委座之面再三再四为先生求情”,与夜中上海家里的鲁迅“左等右盼,总无消息”,“救挚友请托枢要”相照应;昼中瞿秋白自评“我本是个小小卒儿,虽不堪大用,也知一步一前,绝无反顾”,夜中评鲁迅“他却愿做个马前卒”,互相照应,也印证了二人志同道合。第三折《镌心》昼中宋希濂言 “这黑布面的本儿,我头一个拜读”,夜中瞿秋白临别时对杨之华说“这黑布面的本儿,你我一人一本”,二者形成对比,在瞿秋白看来宋希濂“毕竟不曾读懂”《多余的话》,只有妻子杨之华才是知音之人。第四折《取义》 夜中宋希濂噩梦不断,“被梦魇百骸皆寒”,而瞿秋白则“一通好觉,直睡到天明”,“偶得一梦”,二者形成鲜明对比。于是每折内部前后贯通、互有关联,对比照应、浑然一体。
全剧不仅每折内部脉络分明、层次井然、对比照应,而且折间更讲究对照与呼应。剧中的夜/虚在整体上作为驰骋想象的心理空间以凸显人物心灵内核,揭示人物心理世界,但四折四夜视角各异,具体叙事功能也自不同。第一折是瞿秋白梦回宗祠之夜,是过去时之夜,追溯其信仰的内在情感动力;第二折的夜不同于第一折全为虚,前部分为鲁迅在上海家里怀想秋白,为虚,后部分为杨之华告知营救失败的消息,为实,内部形成虚实对照,是现在时之夜,凸显瞿鲁二人之志同道合;第三折夜为瞿秋白赴瑞金前与杨之华的分别,是过去时之夜,凸显瞿秋白浪漫之情;第四折夜是宋希濂之夜,其实是梦魇之夜,是将来时之夜,反衬瞿秋白信仰的光芒与力量。四个夜,过去、现在、未来交织,互相对照,颇具同中求异的 “犯笔”之妙。此外,第一折《溯源》 昼为宋希濂审问瞿秋白,而第四折《取义》 夜宋希濂被灵魂拷问,同为受审,但对象不同,巧妙地形成前后对比。
除讲究对照外,昆剧《瞿秋白》 四折间的呼应更为紧密。第一折《溯源》 夜瞿秋白梦回宗祠,“冷潇潇一灵飘荡,行经了长街深巷”,与第四折《取义》 瞿秋白就义前品尝家乡美食,“甜白酒,萝卜干,倒算得在舌尖上回了趟家”相呼应。第二折《秉志》 狱中的瞿秋白在余冰眼中“能吃能睡,写写文,刻刻章,有时还讨酒吃,不像坐牢,倒似度假”,“写文”与第三折《镌心》 昼中宋希濂所说“明知多余,你亦一笔一划,说得明白”的《多余的话》 相照应;“刻章”则不仅与第三折《镌心》 中“我这章儿也刻成了。其下一个心字,其上为无,又多了一点(旡)”,“篆将爱()字两心倾”相照应,也与夜中瞿杨二人“印之在掌,镌之入心”的深情相呼应;“不像坐牢,倒似度假”与第四折瞿秋白视死如归,“工作之余,稍事休息,是小快乐;夜间入睡,安眠无忧,是大快乐;舍生取义,与世长辞,是真快乐”相呼应。第二折《秉志》 夜鲁迅言瞿秋白 “去江西,去瑞金”,可知瞿秋白在从上海赴江西瑞金前特意前来与鲁迅告别,与第三折《镌心》 夜瞿秋白告诉杨之华“临去瑞金之前,我定要与大先生告别”形成呼应。折与折间前呼后应,伏脉绵延,使全剧结构更为浑然紧凑。
由此可见,罗周以细腻文心精心构思与周密经营,使昆剧《瞿秋白》 每折内及折间在联系中皆有照应,草蛇灰线,丝丝入扣,脉络贯通,浑然一体,形成了精妙的实虚互生、时空结合、纵横交织的四折双线结构。这一昼/实、夜/虚的颇具张力的精妙结构,既与古典杂剧、传奇有着深厚渊源,又是作者戏曲现代化的一次成功实践。
罗周“新杂剧体”结构表面与元杂剧结构相似,其实二者有本质区别。迥异于长于铺陈的宋元南戏与明清传奇结构,元杂剧“四折一楔子”结构,简洁清晰,在很大程度上与故事的起承转合相应,然杂剧作家们关注焦点主要在套曲写作,并没形成自觉的戏剧叙事与人物刻画意识。因此,在对古典戏曲两大源头——元杂剧与明清传奇的结构批判接受的基础上,罗周又充分吸收了折子戏的内在结构形态,以杂剧之体与传奇之笔/折子戏来写作,创造出了新型的极具个人印记的实虚互生的“四折”双线结构。这一结构有条不紊,脉络分明,与明清传奇双线结构极相似,但又不失之于松散,使戏剧叙事的张力与戏剧性得以增强。每折昼夜划分,使剧作具有了《牡丹亭》 《长生殿》 “真幻相生”式色彩,古典名剧的华彩似乎得以再次回归。实虚互生的结构不仅是对古典戏曲精神的张扬,也有着极为自觉的现代意识。
这一颇具匠心的实虚互生的双线结构,根源于罗周对瞿秋白的认识。曹禺说:“一个戏的结构,绝不是形式,它是一种艺术感觉,是一个剧作家对人生、对社会特有的感觉。”[5]那么,实虚互生的结构正是罗周基于对瞿秋白战士与文人双重身份的认识而构造的。战士瞿秋白信仰单纯坚定,文人瞿秋白心灵丰富充盈,由此决定了实虚互生双线结构的必然性。在此基础上,罗周在独特而极致的戏剧规定情境中匠心独运、周密经营。剧中的瞿秋白大多时间处于被羁押的囚室中,在这样一个逼仄的现实空间内,在结构上实现传统戏曲时空自由转换的原则显然不易,因此,昼/实部分在结构上以人物活动空间为出发点,接近于话剧块状结构,叙述囚室中的三次劝降与最终就义;而夜/虚部分叙述囚室中的瞿秋白跨越时空与母亲、知己、妻子的悲怆诀别,如夏完淳《狱中上母书》 与林觉民《与妻书》般凄楚动人,既凸显了传统戏曲时空自由的线性结构特征,又为充分发挥昆剧虚拟流动的戏曲化特质提供了用武之地。实的一条线颇似话剧的块状结构,虚的一条线颇似戏曲的自由时空结构,“团块组合”的话剧结构与“点线组合”的戏曲结构在剧作中得以巧妙熔铸,相得益彰。
实虚互生的双线结构增强了剧作的内在叙事张力和戏剧性,既利于作为原创革命题材的现代昆剧《瞿秋白》 在史实框架中展开剧情,又能超越逼仄囚室这一规定情境的束缚,为身困方寸间的瞿秋白心灵的翱翔腾跃与充分展示提供心理空间,从而完成剧作家在历史“不曾触及之处”[6]的探秘寻幽,发现历史人物独特的美学价值。因此,实/昼一条线有利于史实呈现与戏剧性情节推进,虚/夜一条线则如具有华彩的心理乐章,有利于充分开掘人物心理,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使历史逻辑与艺术逻辑达成内在统一。“昼”凸显了瞿秋白信仰的坚定与执著,而“夜”则昭示了瞿秋白对美好的不舍与向往。换言之,“昼”是阳刚的、革命的、坚定的,与瞿秋白革命者气质若合符节;“夜”是阴柔的、温情的、缠绵的,与其文人气质相合。在二者合力下,瞿秋白作为“一个高贵、浪漫、快意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形象”[3]被立体地、真实可感地、血肉丰满地塑造而出。
总之,昆剧《瞿秋白》 实虚互生的双线结构是编剧罗周在把握戏曲内在规律下文心与匠心精妙呈现的结果,在当前现代戏曲创作中颇显精致独异。它既有对杂剧、传奇内在规律的回归与继承,与古典传统血脉相连,又有在革命与超越之中的自觉鲜明的现代意识与创造性转化,在文体上具备了耀目的现代性,构建了一个真与幻、实与虚融为一体、相互映射、互文自洽的审美结构。
二、人物心灵的凝视
戏剧是写人的艺术,人物塑造是剧作主导部分,“一部戏的永久价值在于人物塑造”[7]。在对传统戏曲抒情性体认与把握的基础上,罗周抓住“昆曲经常以浓墨重彩的曲唱,表现人物情感之跌宕、心灵之起伏、个性之张合”的特征,充分发挥昆剧的特长与优势,“以展示人物丰富复杂、独特细腻的情感个性为追求”[8]。因此,昆剧 《瞿秋白》 迥异于以情节取胜的传统戏,避免了红色题材戏剧人物塑造的扁平化、脸谱化之弊,可以说是一部以当代视角开掘革命人物复杂、幽微、细腻的心理,立心铸魂,凝视人物心灵的 “心剧”。昆剧《瞿秋白》 中的人物分两大阵营,一方为瞿秋白、金璇、鲁迅、杨之华,一方为宋希濂、王杰夫、余冰、陈建中,尤以主人公瞿秋白的塑造最为丰满、立体、鲜活,是近年戏曲舞台少见的极富生命力的革命者形象。
全剧从横向分“昼”“夜”两部分,“昼”的部分凸显的是戏剧进程中瞿秋白坚守信仰、铁骨铮铮的革命者形象。瞿秋白自被捕入狱假身份被识破后,先后与宋希濂、王杰夫进行了三次交锋,在这一历程中,瞿秋白作为革命者的心灵得以饱满呈现,信仰的光芒与力量散发而出。在第一次审问时,当身份被点破,面对宋希濂“先生主义,累死英雄”的论调,瞿秋白义正辞严,直接发出“唯一根脊梁,是我主义浇铸”的铮铮宣言,奠定了剧中人的心理基础。
在第二次面对王杰夫巧言劝降,瞿秋白丝毫不留余地直言“这等盛情,我偏听它不进”;当王杰夫劝其“道俊杰,凭风能扶摇,临悬崖,抽身早”时,瞿秋白凛然而言:“时务者,捍卫疆土,抵御外辱;俊杰者,为国为民,虽死犹生。”当王杰夫言及瞿秋白“一直降到个小小的卒子”,瞿秋白昂然自称:“我本是个小小卒儿,虽不堪大用,也知一步一前,绝无反顾,而今过了河,一发不肯掉头。”其信仰坚定无比,一个充满信仰之光的灵魂跃然而出。面对死亡,瞿秋白认为这是对道义的追求,正如“子曰:朝闻道,夕死可也”,“比之傀儡而生,不若快意而凋”。面对王杰夫的威逼利诱,瞿秋白寸步不让,傲骨挺立,最后以饶有趣味、凛然豪迈、蔑视嘲讽的“我便死了,你也输了”的妙句宣告其劝降失败。
当处决令下达后,宋希濂再次劝降,言瞿秋白《多余的话》 “分明还恋此生”,瞿秋白则斩钉截铁地接言“却不叛党而活”,如解剖刀般揭橥自我内心:“文中之倦怠、怯懦、脆弱、消沉,皆我心声,虽经蹉跌,从无改变。共产党员就该不伪饰,不欺瞒,不诓骗,清清白白行事,堂堂正正为人,我若还有半点求生之意,断不写此《多余的话》。”以背面敷粉之法,凸显了一颗信仰坚定、灵魂洁白、人格高贵的革命英雄之心。不同于过往那些仅表达必死之志的绝命书,“它是我临终前无遮无掩、自查自省对我党最后之忠诚”。这是一个信仰所化之人所昭示出的信仰的力量与光芒,其中的赤子之心与人性光辉散发着永恒的艺术魅力与精神力量。
在三次劝降中,剧作家摒弃了空洞的、概念化的口号,以独立精神和个性化思考完成了对人物心灵的凝视与敞开。随剧情步步推进与人物命运急转,从坚守信仰到直面死亡再到剖析灵魂,层层递进,瞿秋白的心灵遂一步步一层层展现而出,张力愈来愈强,展示愈来愈深。在达至末折 《取义》时,剧情虽依史实而写,但在史实框架下对人物心理着墨颇多,节奏则略缓下来。临刑前,面对死亡,瞿秋白一夜好梦,并返身而回集唐诗志梦,对途中街角的瞎眼老乞丐,心生悲悯,“为图天下再无这等可怜人,我等百死何惧,百死何憾”,对途中良辰美景及家乡美酒美食仍挂怀在意、念念不忘。其中体现了瞿秋白浓烈的人间情怀,这个人间是他奋斗的对象,这个人间的美好是他信仰的终极目标。他以豪迈乐观、坦荡淡然的态度面对死亡,“工作之余,稍事休息,是小快乐;夜间入睡,安眠无忧,是大快乐;舍生取义,与世长辞,是真快乐”,是其从坚守信仰到直面死亡再到剖析灵魂的必然结果。
从昼的一条线,可看出对信仰的坚守与对人生的乐观贯穿瞿秋白“生如夏花纷灿烂,死似秋叶意自适”的华丽一生,而夜作为一条情感叙事线,如倒影般凸显了其灵魂的丰富性,呈现了瞿秋白作为革命者的人间情怀。在即将告别人世的某夜,怀着赤子之心的瞿秋白一灵缥缈来至家乡瞿氏祠堂,向母亲告别,不仅凸显了革命者瞿秋白作为人子深情的一面,更为深层的是他将对母亲的爱推及天下千千万万的不幸大众,“遍八方,更有几多骨肉,流离凋亡”,将一己之悲化作为天下劳苦大众谋幸福的内在情感动力,“做那裂空的闪电,惊天的霹雳去了。不见晨曦,誓不归来”,坚定不移的革命者因而被孕育,家国情怀于此也得以统一。第二折《秉志》 中,鲁迅与瞿秋白“同怀共抱”,“文章金石交”,不仅凸显了二人私谊,更揭示出二人友情是建立于找寻光明的伟大目标之上的,与其说是知己,毋宁说是战友。第三折《镌心》 中,瞿秋白与妻子杨之华依依不舍,“只恋着你,傍着你”,凸显了革命者瞿秋白铮铮铁骨下的柔肠,并将个人之爱升华为对国家民族的大爱。
由此,作为人人皆可共情的母子情、知己情、夫妻情是内在统一的,统一于对国家民族的大爱,聚焦于瞿秋白如金石般坚定的信仰,表面写的是幽深的个人情感,内在则是深沉的国家民族大爱,细微的人情世态指向宏大的灵魂描摹,家国情怀得到内在的高度统一。不仅虚/夜中的个人情感是内部统一的,而且虚/夜与实/昼各自对人物心灵的深入开掘也是统一的,二者充满张力,互为表里,统一于瞿秋白对信仰的坚守,对国家民族的大爱。因此,在历时与共时维度的合力下,瞿秋白复杂、幽微、细腻的心理与精神内涵得以饱满呈现,一个血肉丰盈、灵魂高贵的瞿秋白形象呼之而出了。
在对瞿秋白心灵凝视挖掘的同时,瞿母、鲁迅、杨之华的内心也相应得以呈现。瞿母对孩子充满爱与不舍,内心既充盈爱意,又分外坚毅,为了孩子的前途与未来,毅然舍弃生命,舍己为家的母爱在瞿秋白这里升华为对国家的大爱。剧中鲁迅义薄云天,豪气干云,对知己全力营救,与瞿秋白铁骨铮铮的心灵内核相映成辉。剧中杨之华柔情温婉,对瞿秋白一往情深,但又果决勇敢,携手而死亦无怨无悔。三位人物内心既有深情一面,又有刚毅一面,与瞿秋白的心灵气质完全统一。
只有在相互碰撞冲突中,灵魂的成色才更足,灵魂的伟大更凸显。作为瞿秋白曾经的学生,宋希濂在两次交锋中,灵魂受到了瞿秋白伟岸人格的强烈碰撞,其心理也得以深入开掘,避免了扁平化、脸谱化,成为戏曲现代戏创作中少见的灰色人物。作为抗战名将,宋希濂无奈“忍看板荡”,在首次审讯瞿秋白时,便流露出不情愿之态,“男儿合该阵前死,怎叫席间审俊才”,并对瞿秋白狱中生活从优相待。在第二次王杰夫审问瞿秋白时,对所谓被抢了“头功”,嗤之以鼻,其内心对瞿秋白分外敬重。在第三次审讯瞿秋白时,宋希濂自以为读懂《多余的话》,其实根本未懂,原因在于信仰不同,被瞿秋白“临终前无遮无瞒、自查自省,对我党最后之忠诚”所震撼,作为曾经的共产党员其灵魂被信仰的力量与光芒所击中。于是,在瞿秋白临刑前夜,纠结不忍、内心不安的宋希濂“被梦魇百骸皆寒”,如精神崩溃的麦克白夫妇般,最终发出了“1935年6月18日,不是我等处决了他,是他审判了我等,处决了我等”的灵魂哀鸣。与瞿秋白一样,宋希濂的心灵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深刻揭示,只是两者底色不同,一为灰色,一为纯白。
此外,国民党阵营的王杰夫心机深沉、老辣狠厉,余冰愚玩真诚,陈建中谄媚狡黠,也都于有限篇幅中得以表现。作为带有昆丑色彩的陪衬人物,陈建中寥寥几句趣话,“白花花的银子,锃亮亮的车子,高大大的房子,养五六个儿子,换两三回妻子,岂不美哉”,使一个诙谐狡黠的小人物嘴脸活脱而出,并且还以传统戏曲丑角插科打诨的表现形态,点破王杰夫“伊一肚皮的花花肠子”,妙趣横生。余冰虽愚勇讷拙,但对瞿秋白从“心如铁石,顽固不化”“不像坐牢,倒似度假”的懵懂不解,到最后“就冲他这不怕死的劲头,俺也得尊他一声”,为其豪迈气概所折服,从侧面凸显了瞿秋白人格的伟岸之至。
总之,作为“心剧”的昆剧《瞿秋白》 极为注重人物心理塑造,深入揭示人物心灵的真实,不仅洞烛幽微地描摹出了核心人物瞿秋白的心路历程,而且对其心灵进行了贴近人情人性的多维度深入开掘与剖析,使剧作获得了“内在的人情的真实”[9],从而将一位信仰坚定、人格伟岸、灵魂高贵的瞿秋白形象饱满而鲜活地呈现出来,展现了信仰的光芒与力量。这一创作实践既体现了剧作家在对戏曲表现情感的特质体认与把握基础上的“心灵虫”[10]般的文心与匠心,又体现了现代戏曲对“人”的发现与解放的现代精神[11],闪耀着熠熠生辉的现代意识。
三、诗意现代的戏曲化
如果说编剧罗周赋予了昆剧《瞿秋白》 丰厚的文学性与思想性,那么导演张曼君超越文本的二度创作,使昆剧现代戏《瞿秋白》 最终完满实现了既充盈着诗意又洋溢着鲜明现代性的戏曲化。匠心巧思的舞台空间、古典戏曲程式美与现代生活质感熔于一炉的表演、中西合璧富有表现力的音乐,使传统戏曲的简约精神与现代舞台语汇水乳交融,既契合昆剧的雅致诗意品格,凸显了昆剧本体之美,又张扬着立于传统之基的鲜明现代性。
与昼/实、夜/虚的极具张力的精妙结构相应,昆剧《瞿秋白》 整个舞台空间被巧妙地划分为台口左右两侧与中间两大区域。其中台口左侧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代表刑讯室;右侧一桌一凳一张木床,代表囚室,由此营造出了主人公瞿秋白严峻肃杀的现实生存空间氛围。两者作为昼/实故事生活化表演区,一直固定不变,与“一桌二椅”以少胜多、以简驭繁的内在假定性精神相通。舞台中间深处则一分为二凝立着黑白分明的两块巨幅景片,隐喻昼夜、阴阳、生死,蕴含着一种冷峻且异常强烈的对峙感,散发着尖锐的戏剧张力。黑白景片前方作为“黄金演区”,则是夜/虚剧情虚拟化的主要表演区,也是主人公瞿秋白心灵翱翔之所。
不同于传统戏曲上下场门,台口左侧是国民党一方上下场之处,而瞿秋白、瞿母、杨之华、鲁迅的上下场则通过中间白色景片开合来实现。这一新颖的打破传统的上下场门设置,既与双方对立的剧情密切相关,又隐喻信仰之路的大相径庭。黑色景片几乎一直固定不动,而白色景片则通过移动开合,不仅为演员提供上下场服务,还在别母、别友、别妻时,分别扩大了舞台的纵深与表演空间,使瞿秋白的心灵空间显得更为深邃丰厚与浪漫飘逸。
在空灵通透、意蕴丰厚的舞台空间中,曼妙玄幻的光影与明快简洁的色彩在流动中充溢着灵动的戏剧性,凸显着人物丰富的心灵世界,与昆曲擅长揭示复杂、幽微、细腻的人物心理的剧种气质相得益彰,不仅符合戏曲时空自由的美学要求,实现了传统戏曲写意精神的现代张扬,而且注重人物内在精神的外化与传达。随剧情进展与人物心理变化,舞台中的白色景片在光的映照下会相应变化。当瞿秋白斩钉截铁地宣誓“不见晨曦,誓不归来”时,整幅白色景片变为黄色,意味晨曦已现而阳光终会普照而来。景片颜色的变化更多地与人物心理相关。当瞿母义无反顾决定以己命换取儿女前途时,白色景片变为满幅红色,喻示着母爱伟大,人物内心得以视觉化呈现。
剧中以黑白为主色调,在大多情形下,茕茕孑立的主人公瞿秋白身后略显耀眼的白色景片,象征其人格高洁。在截然对立的黑白景片间,略透出一缕耀目红光,隐喻着革命先驱瞿秋白追寻光明的赤诚之心与信仰之光。就义时,瞿秋白玄衣白裤席地坐于白地上,随枪声响起,白色背景变为满幅红色,红英缤纷落下,在黑白对比下,耀目的红色象征换来今日光明的先烈鲜血。在白色、红色成为革命者人格与精神的象征与外化的同时,宋希濂在瞿秋白取义前夜,内心惴惴不安,幕后两块巨幅景片则全为黑色,中间仅有一缕隐约白光,隐喻宋希濂灵魂中的一丝忏悔之意。
除运用颜色与灯光外,还会将投影与剧情紧密结合。当瞿秋白梦回瞿氏宗祠时,白色景片上光影化地再现了灵柩,给人似真似幻之感。当宋希濂受到灵魂拷问时,白色景片上的人影如鬼魅一般,凸显了其内心的压抑与挥之不去的恐惧。白色景片上的投影叠加,丰富了舞台的视觉层次与内涵。
对作为现代戏的昆剧《瞿秋白》 而言,如何在表演上避免程式化与生活化的异质感是一大实践难题。正如罗周所言:“对于现代戏曲创作而言,更大的难度是表演艺术。”[12]昆剧有着谨严深厚的行当程式积累,昆剧《瞿秋白》 正是在行当的程式化规范中完成了角色塑造,使程式化与生活化的表演达成了内在统一。以小官生应工瞿秋白的施夏明,在小生台步的程式化规范中,弱化了动作幅度,放缓了动作节奏,加快了步伐频率,完成了程式基础上富有戏曲韵律的生活化处理。除动作生活化处理外,在凸显昆剧韵味的前提下,对以现代审美衡量而略显拖沓冗长的唱与念,也相应进行了节奏调整与生活化处理。节奏稍快的唱与念不仅未损伤昆曲的绵长韵味,同时也消弭了传统程式与现代生活的隔阂。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昆剧《瞿秋白》 使源于生活的程式再次生活化与适度重构,从而贴近现代戏的内在要求与当下受众审美,形成了新型的现代昆剧表演美学。
在对传统程式进行生活化处理,将凝固化的程式适度生活化的同时,在需放大人物情感的关键处,程式又会被恰如其分地化用。当面对二次劝降时,瞿秋白踱四方步斥责王杰夫,此时人物的得意、豪迈之情与小生行当的潇洒俊逸形象地呈现了出来。在取义前,瞿秋白对人间的眷恋之情,通过施夏明几个轻盈的快趋步恰到好处表现而出,既凸显了传统戏曲程式之美,又与人物内在心境吻合。在创造性化用传统表演程式时,对传统戏曲经典程式也适当吸纳运用。如瞿秋白梦中与母会面,运用传统戏曲虚拟化的两个擦肩而过的程式,不仅符合梦中规定情境,完成了实/昼与夜/虚的转换,也使母子深情得以放大。夫妻二人会面时,呼喊寻觅,面对面却不能相拥,夫妻间缠绵深情得以表现。这些传统程式的恰当运用,使剧中人物的内在情感得以充分展现。
传统戏曲道具作为“技艺化”表演用具,往往以一当十、以虚代实。昆剧《瞿秋白》 的道具使用既符合传统戏曲美学精神,又利于虚拟化表演与情感传达。在充分发挥情绪饱满的唱念的同时,以身段程式较少的正旦应工的瞿母,手持轻纱般的一条手绢,忽而是账单,忽而是红头火柴,忽而是酒杯,以传统戏曲道具的虚拟性消弭了现代戏正旦无戏可作的窘境。杨之华所提装有瞿秋白百万译著的书箱,沉甸甸的,“一字一句,似你一笑一叹”,寄予着她对瞿秋白深深的思念之情。随剧情由实转虚,书箱变为送行的行李,或坐,或托,或两人共提,不但贯通了实虚转换,而且传达出夫妻依依不舍之情。不同于手绢或书箱,剧中的香烟是意象化的,是鲁迅不息战斗精神的象征,既富有昆剧写意韵味,又体现出人物内在精神的独特性。
昆剧《瞿秋白》 的配乐中西合璧,既有传统的笛、笙、琴、胡、鼓,也有提琴、单簧管、长笛、小号、小军鼓等西洋乐器,既有助于充分表现人物情感,又与全剧缠绵哀婉、刚毅铿锵相济的风格相契合。在母子、夫妻见面时,以昆剧传统音乐表现母子、夫妻情的哀婉深切、缠绵悠长;在表现瞿秋白与鲁迅的慷慨激昂及最后取义时,则用小军鼓主奏的节奏铿锵的国际歌。传统昆剧音乐与西洋交响乐水乳交融,使人物情感饱满呈现。
总之,空灵蕴藉的舞台空间、流畅灵动的灯光、熔古典戏曲程式美与现代生活质感于一炉的表演、中西合璧富有表现力的音乐,合力形成了饱满立体的“心象”,实现了“心剧”的舞台呈现与诗性表达,既凸显了昆剧本体之美,又张扬着鲜明的现代意识。面对积淀深厚的古老昆剧,张曼君秉持“退一步——回归戏曲本体的美学思维,进两步——高扬现代观念”[13]的“退一进二”的导演理念,完成了一次极富挑战的舞台新实践,为昆剧舞台创造出了新的现代审美价值,对昆剧现代戏乃至戏曲现代戏舞台新美学的形塑都极富启示意义。
四、结 语
作为红色题材在古老昆剧中的一次弥足珍贵的艺术实践,昆剧《瞿秋白》 展示了革命先驱瞿秋白人格的高洁与心灵的幽微,散发着熠熠夺目的信仰之光,不仅为古老昆剧注入了现代活力,拓展了现代昆剧的实践版图,而且达成了恢宏的红色主题与典雅的昆剧美学的内在完美统一。在对昆剧本体与艺术规律的把握下,罗周完成了结构精妙、意蕴丰厚的具有精神高度的“心剧”,张曼君导演则实现了散发着艺术魅力的戏曲舞台 “心象”赋形,两人以耀眼的主体性合力塑造出了洋溢着昆剧本体之美的现代昆剧新美学。这一成功地融现代审美与古典昆剧为一体的舞台艺术实践,既证明了昆剧现代戏表现革命题材的可能性,又凸显了戏曲现代戏的巨大实践空间与无限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