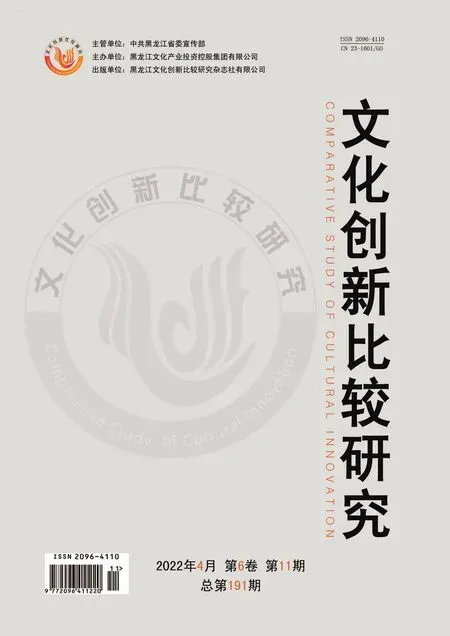脞议西南异味美食及大众认知的转变
——以西南民族地区的“瘪”类饮食为例
唐雨静,蓝斯靖,何锦宸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中国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其中有一道饮食备受争议却流传至今,那就是盛行于西南民族地区的“瘪”。然而在古籍记载当中,中原汉人却是借“瘪”为矛,用以妖魔化西南地区和区域内的各民族,成为一种刻板的污秽食物。目前学界对于“瘪”的研究大都停留在饮食学、人类学、社会学领域[1],很少涉及历史学范围内“瘪”本身及其形象的变革问题。作为“华夷有别”观念重要支撑的“瘪”,一直未被中原主流社会文化所客观接受,现今关于“瘪”的争论亦是如此,网上关于“瘪”的讨论大多还是带有新奇、难以接受等关键词。实际上,“瘪”这一食俗本身的发展变迁、形象的流变转换,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饮食文化“美美与共”的体现。该文将撷取古今相关文献资料和媒体报道,探讨近现代“瘪”的地域分布与历史形象变迁问题,便于拨正刻板印象,以食物为着力点来阐释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西南民族地区的“瘪”类饮食溯源
所谓“瘪”有牛瘪、羊瘪之分,即是利用牛、羊等哺乳动物胃部未消化之物加以肉类、内脏等烹调而成的饮食,又称百草汤。西南民族食用“瘪”的历史悠久,无论是用于治病养生,还是作为调味蘸料,抑或是彰显族群认同,在西南苗侗民族社会生活中,“瘪”的重要性延续至今。
“瘪”类饮食及其衍生物在西南地区已经延续了数百年之久,关于牛瘪的历史记载最早可追溯至唐宋,主要见于《岭表录异》[2]、《溪蛮丛笑》[3]、《岭外代答》[4]、《太平御览》[5]等汉人手记,少量散见于官修文书和诗歌艺术类文集中。唐刘恂所写《岭外录异》[6]将食用牛瘪看作地域特色的饮食文化,并对牛瘪饮食风尚及其具体食用方式进行细节化描述,可以发现在此书中暂无用牛瘪这一异类饮食区分华夷的标志。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中道青羹为异味[7],将“瘪”的饮食文化多样性进行表征,进而通过食用与否展现宾客之间对“瘪”类饮食的态度所产生的微妙心理变化。种种古籍文献之记载都足以证明这一饮食至少在唐宋之际就已经为岭外侗苗边民所食用,或在当时的西南边地生活中是极为重要、极受欢迎的饮食,以至于能被汉文文献记录。但就总体意象而言,这一时期的“瘪”实际上在文献或汉人印象中仍扮演着未开化的族群代表,与西南的瘴、虫等意象共同构造了蛮夷的西南形象。
元明清三代以来,随着中原王朝对西南边缘地区的经营逐渐深入与加强,尤其是明代设军民卫所以来,关于这种对汉人而言属于异类食物的记载渐渐呈现出更广为人知的具体样貌。元代《馔史》、明代谢肇的《文海披沙》及夏树芳的《词林海错》,乃至于清朝文人诗集与地区方志中,皆出现了有关于“瘪”类饮食的记载。这些记载,相较于前代所谓“混不洁以羹”,业已在思维方式上有所改观,食用人群已经不再是被单列为不入朝廷的异族蛮夷,而只是偏远地区的一种族群性的异食爱好,成为展现独特风土人情的一道佳肴。
唐宋以后乃至明清关于瘪的描述,更多反映的是从中原汉人视角出发的一种文化审视,代表着中原传统对西南边地社会的刻板形象认知。即使历代汉人关于“瘪”类饮食的食用记载表现出一定的态度转变,中古社会华夷之辨的话语构建也使得“瘪”无法摆脱这种排斥意味,成为汉文化中区分“我者”与“他者”的精神疆界。但无论如何,牛瘪始终作为西南民族地区特色饮食文化的缩影,留存在历史的长河中。
2 “瘪”类异味美食的时代转身与大众认知的转变
2.1 品味形象:从不洁到美味
“瘪”作为盛行于西南民族地区的一种特色饮食,其制作十分特别,取牛羊胃里尚未完全消化的草料汁水作为烹饪调料,辅以新鲜牛羊肉,或火烹或凉拌,是当地群众款待宾客的上品。这一饮食历史相当悠久,流存至今,在当地社会仍然是代表边地文化的典型意象,在长时间的历史发展中完成了从“不洁”到“美味”的形象转型。
葛兆光先生说过,一种风俗或文化现象在历史文献中再次大量出现的时代,正是其受到主流社会关注和警惕,并对它进行了强烈抵制的时代。而且也只有它成为“异常”时才会被“凸显”出来,为历史所关注,并在史书中被记载下来[8]。在以往的古籍记载当中,中原汉人往往通过“瘪”来妖魔化西南地区和区域内的各民族,成为一种刻板的污秽食物。宋代朱辅在《溪蛮丛笑》中记载:“牛羊肠脏略洗,摆羮,以飨食客,臭不可近,食之则大喜。”生动记录、对比了“瘪”在外人看来的臭不可闻与地方民众所表现出的“食之大喜”。于《太平御览》中,甚至直呼“瘪”为“细粪”,如下文述:“于是烹一犊儿,乃先取犊儿结肠中细粪,置在盘筵,以箸和。”如此这般描述,可见“瘪”在“华夷之间”已然代表肮脏与不洁之代表。作为“华夷有别”观念重要支撑的“瘪”,很长时间内一直未被中原主流社会文化所客观接受,现今关于“瘪”的论争亦是如此,网上关于“瘪”的讨论大多还是带有新奇、难以接受等关键词。实际上,“瘪”这一食俗本身的发展变迁、形象的流变转换,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饮食文化“美美与共”的体现。
在当下信息化程度极高的现代社会,在各方媒体铺天盖地的推广以及游客的猎奇笔记的渲染下,地处偏远的食俗逐渐进入我们的认知图景之中。而牛羊瘪正是在媒体、游客与地方政府的共同助力下,不再作为一种“难登大雅”的奇风异俗,而是被放大为一种民族特色、一个新的旅游卖点,逐渐为大众熟知。在有关“瘪”类食品的各项宣传中,主要运用特色形象操弄以突出牛羊瘪属于西南少数民族分布区域的特征,通过挖掘与牛、羊相关的各色神话传说、自然崇拜等极具地域文化色彩的地方性知识,将“瘪”塑造成代表民族风貌的“奇食美味”。“瘪”的形象再构建与游客在旅游活动进行过程中听闻有关“瘪”的传说有感而发的猎奇心理形成有效互动。于网络热门的猎奇之外,官方宣传系统也将“瘪”作为地域文化宣传的关键内容。在从江县人民政府网站上,就详细介绍了牛、羊瘪,并称其为县境内苗、侗等民族最爱吃的菜肴之一,是侗族筵席上必不可少的主菜。《贵州“牛瘪火锅”》《侗不离酸·爱恨交加百草汤》《苗家“羊瘪汤”的制作》《黔东南吃“羊瘪”习俗探微》等文章也详细介绍了百草汤,即牛、羊瘪汤的制作过程及味道功效。近年来还有相关纪录片如《天下一锅》《沸腾吧火锅》《风味人间》等,详尽地拍摄并介绍了牛瘪火锅,以视频形式更直观地呈现给大众。上述报道在视频文案撰写、影视拍摄方法、后期制作宣传上,无一例外强调“瘪”是一种被地方民众所喜爱的独特食物,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科普大众、去污名化、提升牛瘪正向知名度的作用。
曾经的“瘪”,作为带有鲜明“我者”与“他者”之别以区分人群身份的象征符号,在信息网络媒体与地方旅游文化的催生作用下日渐展现出新的面相。如今,“瘪”在延续其部分原始意义与功能的基础上,由原初的“不洁”转向当下的“美味”,昭示着某种刻板化的观念认知随着时代变迁发生变化,随着西南民族地区与国内其他区域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瘪”正朝着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标识演进,并在此过程中逐渐脱离“不洁”的刻板标识,进而作为“瘪”类饮食分布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代表之一,成为旅游宣传的重要抓手。
2.2 观念嬗变:从有害到健康
于牛瘪而言,大众视角下的“不洁”大抵归因于其原材料及制作方法,对该食俗的不了解也加深了大众的排斥心理,因此牛瘪逐渐沦为污秽有害的食物。然而往时不同今日,牛瘪的做法日益现代化,牛瘪的大众知名度愈发高涨,加之当地符合大众心理的宣传营销,在这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大众认知下的牛瘪渐由有害之物转变为健康饮食。
2.2.1 烹饪及食用方式的转变
就其做法而言,牛瘪的做法及食用方式更贴近现代卫生观念。如今制作牛瘪主要是选用牛腿肉、里脊肉,再加上牛杂碎,倒入经过多重过滤的瘪汁,并辅以辣椒、花椒、葱蒜、香菜、茱萸、陈皮、垂油子等香料高温煮沸。《黎平府志》中就记载有“胡荽芫荽”“木姜”“辣角”“茱萸辣子”“蘹香茴香”等。虽说食材基本不变,但牛瘪的烹饪形式却不断发展,衍生出多样形式,如贵州的“牛瘪汤”,广西的“百草汤”,云南的“牛撒苤”等各具特色的烹饪方式。
就其食用方式而言,《周礼·正义》中记载:“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桂黔地区人民的食俗文化与先辈的一脉相承,承袭了生食风俗,在明清的地方志、竹枝词多有记录。如颜嗣徽《牂牁竹枝词》曰“四山逢逢挝铜鼓,号召宾亲磔生牯”,又有地方记载“腾越处滇省极西南之地,民苗杂居,……披树叶,茹毛饮血,性悍好斗,言语不通,难施化敎。”这些文献说明贵州苗侗居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保留着较为原始的生食状态,五代王仁裕《玉堂闲话》中所记载的凉拌牛瘪就可作为例证。而今在融水、从江等地,人们不再生食牛瘪,而是采用牛瘪火锅、牛瘪粉等多种方式食用牛瘪。
2.2.2 认知深度与偏见程度的博弈
绝大多数情况下,对某件事物认知越深,产生偏见的概率就越小,得益于信息化时代,牛瘪的知名度日益提升。首先是地方旅游中将牛瘪作为地方特色饮食来介绍。在食用牛瘪的主要地区如贵州、广西的榕江、从江、黎平、融水、从江等地大多将牛瘪作为一种特色风情写进当地的民俗志以及旅游期刊中。例如笔者采访的贵州省从江县银谭侗寨的一位担任过导游的老者表示,本地居民皆以牛瘪款待来往侗寨旅游的国内外游客,是当地旅游的一大特色,而居此不远的榕江县更是打出“天下第一瘪城”的称号,吸引游客来访。与此同时,短视频平台的个人展示更是有力拨正了以往对牛瘪的刻板印象。譬如抖音、B 站平台上一批以美食、探店为主的博主,通过制作牛瘪火锅的视频获得上百万点赞,视频观看量更是达到千万以上。
牛瘪这一具有民族特色的异味食品,随着地方旅游以及网络宣传的开发而得到传播,借助地方社会、网络营销以及平台用户的互动得以拨正以往的偏见认知,成为地方文化的典型代表。
2.2.3 宣传形象与健康观念契合
在物质生活愈发丰富的当下,人们在食用各类美食珍馐之际,还会关注食物的健康程度,作为原生态食疗良方的百草汤也因此颇受关注,它的食用功效自然进入大众的视野。
《美味养胃的侗家百草汤》一文指出,被称为侗族“三九胃泰”的百草汤具有清热下火、排毒通便的功效。一些美食网站上也登出牛瘪汤的制作方法,及其具有消炎解表、治疗炎症和感冒的功用。当地在宣传时很好地抓住了“瘪”原生态、绿色环保的特点,迎合了健康饮食的时代需求。从生料取材到熟料入锅的整个过程,“瘪”的绿色、健康则成为旅游宣传、商业销售、食客重视的焦点。而“瘪”类饮食与“百草汤”的联名,将生态与健康的含义赋予了这一看似“污秽”的特色饮食,在倡导绿色生态、食疗养生的今天被更广泛的群体所接受。
综上所述,可简单总结出造成大众认知转变的几个因素:一是由生到熟,食法多元。由生食凉拌生瘪到如今熟食牛瘪火锅、牛瘪粉,牛瘪烹饪及食用方式变化中所折射的,是苗侗人民在近代演变过程里对汉文化、西方文化的摄取和连结,亦是正向引导大众认知转变的最直观因素。二是来往密切,认知加深。认知的深浅与产生偏见的概率成反比,牛瘪这一地处偏远的食俗,在信息化程度极高的现代社会离我们越来越近,这也使得大众对其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三是食材绿色,健康宣传。由于制作牛瘪食材的天然性、绿色性,为当地宣传该食俗提供了基本前提,也得益于近年来人们追求健康饮食的时代需求,宣传迎合需求也促进了大众认知的转变。
2.3 地域延伸:从边地到全国
“瘪”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以苗侗两族为核心代表的特色饮食,生成于特定的自然风貌与人文环境。关于“瘪”的历史记载最早见于唐刘恂的《岭表录异》:“容南土风,好食水牛肉。言其脆美。或炰或炙,尽此一牛。既饱,即以盐酪姜桂调齑而啜之。齑是牛肠胃中已化草,名曰‘圣齑’。腹遂不胀”,容南是容州以南,即今天的广西玉林一带地区。这条记载是唐人关于“瘪”类饮食的唯一叙述,所食地区也仅局限于此。而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中所云:“异味:甚者则煮羊胃,混不洁以为羹,名曰青羹,以试宾客之心。客能忍食则大喜,不食则以为多猜,抑不知宾主之间,果谁猜耶? 顾乃鲊莺哥而腊孔雀矣! ”亦是作者前往岭南观南方民族社会风俗所得,地域范围依然为今天的两广一带。“瘪”类饮食在唐宋流传于岭南地域,中央王朝的深耕使得汉人与南方少数民族接触增多,是以牛瘪的记载见于唐宋士人文集之中,但仍可得知这种奇异的食俗存在于特定的边地社会环境,除岭南以外并不多见。
然而待到元明清三代以来,中央朝廷在南方地区推行土司制度,后又改土归流,对西南边缘地区的经营更加深入,关于牛瘪的记载日渐丰富的同时,记述其出现的地域也较唐宋有所不同。在元明清三代的各类地方志书、医术杂记以及流寓文人的诗集中都有记述牛瘪。不仅在《广西通志》提道“上映土州多狼人,种山猎兽,食生饮血,取牛肠渣滓以为美汁”,而且在《贵州通志》《广东通志》《滇黔志略》都曾记载“瘪”类饮食。除官方记录以外,文人诗集歌咏之词亦不少圣齑身影,有“海错山珍是何物,登筵夸道圣齑香”之赞,又写“彼有人焉兮爱食圣齑,鹣脾象白兮君欲胡为”“山獠各赛偏诸锦,水蜑分尝不乃羹”之事。这些士人下放至云南、贵州、广东、广西任职,将种种见闻所得记入诗文。足以说明“瘪”在西南边地分布范围之广,所起作用之深。从汉人书写的文集志书中,牛瘪的分布地域逐渐从唐宋的局限于两广,地缘延展范围逐渐扩展至桂黔滇粤四省,与今日贵州、广西、云南各地食用牛瘪之地相合不悖。
而从牛瘪的食用人群来说,史书上并未说明是哪些族群食用牛瘪,大多以“蛮”“夷”“獠”“土人”等泛称代指这种奇特食俗的享用者。较早的明确点出牛瘪食用者的是清代士人吴仰贤在其诗《黔中苗彝风土吟》提及圣齑,认为食用牛瘪的主体人群是苗彝之类。而待到民国,随着民族理论的丰富以及民族识别的精准化,有如陈国钧等学者前往贵州调查苗族社会历史时,提出生苗习食牛瘪,“他们杀牛羊时,便剥去牛羊的皮,切肉成薄片放入土钵内,加些辣椒和盐拌匀,然后取牛或羊的别(瘪)和胆水作酱,取生肉片蘸食”。民国出版的《榕江县乡土教材》也记载有:“苗胞食肉常用生食法。购得肉类,即出小刀割成若干小块,放以辣椒,然后更注以汤液。所谓汤液者,牛之小肠内所贮藏得绿色液体也。伊等即用此绿液作调味之用,”更进一步确定食用牛瘪的为苗胞。民国时期的苗胞常常与其他民族混居,牛瘪因此变成一种地区美食,诸如侗族、布依族之类的少数群体也有食用。到这一步,牛瘪已经跨越了原本封闭的边地社会,成为能够传达西南民族鲜明地方特色与审美意趣的地域符号。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牛瘪的食用人群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急速流动起来,较原先固定的乡镇县城逐渐走向了大城市。在迁徙的过程中,牛瘪无疑是被视为一种能够联系故乡的食物,跟随流动的人群走向了更远的地方。在今天一些仍然习食牛瘪的县份里,大多受访者都表示他们不仅在家里爱吃,也会将牛瘪制成易保存的汤料,以方便带去外省,实现了地理空间的跨越。
而从文化领域上,日渐发达的网络世界更是使得牛瘪从鲜有人闻的异味奇食逐渐为人所知。B 站、抖音等视频平台以及各类宣传旅游的传播媒体以奇食为名,大力宣传“瘪”类饮食及其相关食俗,使得“瘪”走入了大众的视野,被更广泛的群体所接纳。不仅如此,从经济销售领域来说,截至调查结束,牛瘪饭店已经开在广东、广西、贵州多省的重要城市,在淘宝、天猫店铺上向浙江、江苏、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销售。牛瘪抓住时代机遇,通过现有的电商贸易网络,以民族商品、特色食物的形式嵌入到各个现代化的大城市,在做到多面盈利的同时,为民族地区经济利益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总之,日益发达的交通建设及网络世界,拓宽了这一异味美食流存的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使其从遥远的边远地区走向了全国,为大众了解西南打开了一扇新窗。
3 结语
长久以来,“瘪”在大众脑海中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认知印象,即在古籍文献中的蛮夷典型,却在近代巨变的历史中逐渐完成了从“污秽野蛮”到“民俗特色”的角色转变。这其中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合力而成。就内部因素而言,“瘪”自身发生了食法的变化,从生食转为熟食的同时产生了不同的食用形式,“瘪”类饮食的卫生化和多元化使其有了更广泛的受众;并且食用“瘪”类饮食的主体民族已经不再被排斥为蛮夷,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观念深入人心,“瘪”作为少数民族同胞的一种文化被欣然接纳。就外部因素而言,西南地区的发达交通促使食用人群流动速度加快,文化交流交往频率增高,“瘪”逐渐走出了封闭的边地社会;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增加了世界了解民俗的窗口,各种媒体对于“瘪”类饮食的宣传拨正了以往的消极刻板印象,大众对于“瘪”的了解是印象转变的重要因素;现代对于健康、绿色的消费观及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更是促使大众认知转变的关键所在。以上种种造就了如今风靡全网的异味美食,大众对此表现出更多的是好奇、尝试与接受。
总而言之,“瘪”作为西南民族地区特有的饮食,其存在本身既是民族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也是各时期社会文化风貌的综合体现,蕴含着丰富的民族饮食文化内涵。从古至今“瘪”类饮食自身及人们对其观念不断变迁,可见中原文化及西南民族文化双方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从边地到全国、从不洁到美味、从有害到健康,“瘪”的转身是人们观念的进步,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体现之一,充分体现各民族文化交流交往交融。
代表原生态、绿色环保的“瘪”迎合了健康饮食的时代需求,各式各样的“瘪”类菜肴满足了各地游客猎奇尝鲜的心理。蕴藏着独特民族文化价值与旅游价值的“瘪”,正从文化层面有力地摆正过去中原人对西南边地及人群的历史偏见,有着文化与经济双重作用。另一方面,不同地区的人群能够相互尊重、包容彼此的习俗差异,平等地交往交流交融,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增强,多元文化的包容与接纳使得“瘪”实现了符号意义的地域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