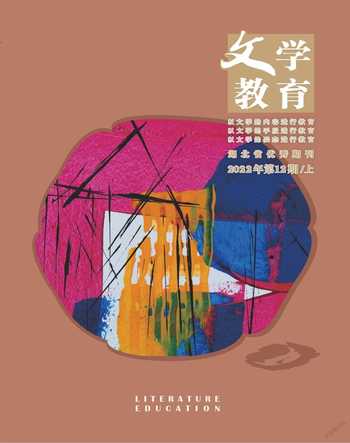论严歌苓《蜃楼》的身体叙述
王忠霞
内容摘要:严歌苓的最新小说《蜃楼》中存在大量的身体描写,作家以身体为切入点,借主人公张明舶的视角展开对于男性和女性的身体描写,其中,男性的身体描写充满了雄性膜拜,弥漫着自恋情结,而女性的身体描写则表现为过度性欲化的特征,充斥着男性的欲望化凝视,是男性欲望在女性身上的投射,有物化女性之嫌。在此基础之上,作家进一步分析了身体叙述的表意价值,通过刻写人物的身体意象、身体图式和身体实践,生动再现了复杂的人性,暴露了人性中的自私和贪婪,作家同时指出,正是父权和男权思想对女性的身体造成严重的伤害,造成了女性的悲剧命运。
关键词:严歌苓 《蜃楼》 身体叙述 表意价值
哲學领域的身体研究转向始自尼采,“身体,从尼采开始,成为个人的决定性基础。”[1]这意味着对于人类意识的拔高和对人类身体的贬抑这一漫长传统逐渐被消解,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的身体标记了他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差异性,哲学研究的这种身体转向对于小说家及其文学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开始在作品中不遗余力地描述人物的身体意像、身体图式以及与身体相关的、源自身体的习惯和爱好,并积极探索身体在人物刻画、情节推进、主题表达等方面的重要价值,可见,身体叙事已经成为文学叙事的重要维度之一。
近年来,随着国内学界对身体研究的持续关注,部分学者尝试从与身体相关的理论角度解读华裔作家严歌苓的作品,从规训理论、身体政治学理论、身体与女性意识的关系等视角评析严歌苓作品中的身体叙事和身体修辞[2]-[13],这些研究从文学与身体的关联出发,探讨了严歌苓作品中身体叙事、身体书写、身体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极大地丰富了作家和作品的研究成果。严歌苓的最新小说《蜃楼》(2021)[14]以上个世纪80、90年代十万人才下海南为故事原型,描绘了主人公张明舶等闯海人闯荡海南的故事。小说延续了作家一贯的对社会中的边缘、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同情,塑造了张明舶、蓝兰、吴玉婷等丰满的闯海人形象,他们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积极融入高流动的群体,在海南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上意欲大展宏图,于是,围绕着他们上演了一幕幕悲喜剧。在小说不长的篇幅中,有关男女人物形象的“身体”描写俯拾即是,作家以她特有的女性的细腻笔触描绘了男女人物的不同身体样态、身体图示和身体实践,涵盖了包括人物的体型、肌肉、头发、乳房等,并将人物的身体感受和心理描写相结合,赋予符号化的身体以丰富的表意价值。
一.身体叙述
(一)男性身体描写:自恋情结与雄性膜拜
文学叙事常常借由文本中某个虚构人物的视角来观察世界,这个人物可以是一个叙述者,或者是一个既在这个虚构的文本中同时又高于这个文本的人物。严歌苓在《蜃楼》中内置了一个旁观者:“我”,一个作家,小说以“我”与已步入中年的主人公张明舶在咖啡馆的交谈开始,全篇以回忆的形式将众人的闯海经历娓娓道来,用他的眼睛还原闯海人群像,其间偶尔穿插“我”(作家)与他的对话。在一次访谈中,严歌苓曾经直言张明舶这个人物塑造难度最大,这是因为小说的叙事几乎全部由主人公的回忆推进,包括人物、情节、冲突、道德判断以及审美等全部是主人公的有限视角,叙述者需要始终潜伏在主人公的内心。[15]这对于一位十分擅长描写女性的女作家来说的确是不小的挑战,但当我们认真细读小说文本,并进行还原性阐释,发现严歌苓无疑是成功的,她精准地抓住了主人公的性格底色,既正直清高,又有些许别扭乖张,其中,正直的性格源于其外祖父母对他从小进行的言传身教,使得他奉行心存善意、吃亏是福以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朴素的生存哲学,清高是因为他的知识分子身份,作为上个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他所接受的高等教育培育了他重义轻利的高尚品质,而别扭和乖张则反映出他隐秘的自恋情结,突出地表现在小说对于他阳刚、健美躯体的毫不吝惜的赞美以及对于其他男性颓败的躯体的无情嘲讽。
历史上对于男性身体的欣赏和膜拜由来已久,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们在创造美术作品和雕刻作品时,常常将男性躯体塑造成赤裸的形象,目的在于突出男性清晰可见的紧绷肌肉和力量线条,这种男性躯体被认为是力量、气势和英勇的象征,张明舶的身体样态恰恰呼应了此种艺术传统。严歌苓在小说中采用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相结合的手法,对主人公张明舶的身体进行了详细的刻写。初次登岛,他还是个初出茅庐、涉世未深的毛头小伙,他身体健壮,性格稳重,行事低调,多次获得雇主的认可和赏识,是大家交口称赞的棒小伙子。参加求职面试,当他“脱下西装,露出肌肉爆满的身子骨”[14],瞬间让雇主眼前一亮,凭借年轻、健康的体魄,他轻松获得了招聘者的青睐,令其他求职者艳羡不已,可见,强壮、健美的躯体是闯海人生存的重要资本。书中还多次提及他的衣着与服饰,几乎每一次出场他都身着紧身T恤,因为这种衣料最容易突出他宽肩窄腰的身材和线条,男性荷尔蒙气息溢于文字之间,就连故事的旁观者“我”也不禁心驰神往,意犹未尽。反观其他男性人物的身体描写,随处可见的文字是秃顶、衰老、颓败、油腻和丑陋,比如中年人王总,在张明舶眼中,这个仅能算个登样的男人,外表平平无奇,一身软肉,乳头凸起,皮下轻度积水,此类身体图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性功能衰退,而那是再昂贵的名牌服饰也无法掩饰的[14]。在王总的“丑的男体”的衬托下,张明舶自诩他是一个拥有“美的男体”的精壮男人,这样一具充满男性阳刚气息的躯体,不仅让其他男性自惭形秽,更让小说中与他产生命运交集的几位女性几乎对他一见钟情,无一例外地渴望以身相许,不求回报,卑微地爱着他,在他落难时用自己的卖身钱接济他,安慰他,帮助他东山再起。面对这些女性的慷慨,他虽偶尔略感尴尬和不安,但最终还是没有勇气彻底拒绝,也没有给予她们同等的情感回报,这种赤裸裸的不对等情感投入将张明舶的自恋情结和雄性膜拜暴露无遗。
(二)女性身体描写:过度性欲化的特征
回顾严歌苓创作的小说,卑微的底层女性人物所占比重较大,这些女性通常被置于对女性非常不友好的极端环境之中,由于政治、历史、社会和经济等多方面原因,她们的生存际遇和命运走向常常存在天壤之别,《蜃楼》中的贵州姑娘蓝兰、浙江女孩吴玉婷、川妹子广玉和云南女孩季小雪等闯海女大抵都属于此类范畴。书中有关她们的身体意像和图式几乎全部通过视觉领域加以呈现,也就是说女性的身体成为叙述者的注视对象,小说循着张明舶的目光,对她们的五官、肤色、头发、身形、甚至乳房等隐秘对象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可以说,女性的躯体几乎从一开始就是男性情欲化的观看对象,充斥着男性欲望的凝视,是男性欲望在女性身上的投射,呈现出过度的性欲化特征,有物化女性之嫌。整体来看,张明舶并非是一个滥情之人,面对几位女性的示好与求爱,他表现得颇为冷静和镇定,严歌苓让他的目光聚焦于这些女性的身体,并将这些身体叙述与他的心理描写相结合,从而为他的情感选择找到合理的解释。
蓝兰有着“一张年轻的小圆脸”、“一条粗壮的腿”、“一具壮实的妇人身体”,她是一个“身上实惠的女人”[14];广玉“白净高挑”,颇有几分姿色,也是一个“从小吃苦,吃苦当饭吃”的能干女人[14];年纪最小的季小雪是一个有着“明亮的大眼”、“腮帮上毛茸茸的”黄毛丫头,她“营养不良的扁平身体”上布满疤癞,让人不禁心生怜惜。[14]然而,这些女子的外形和身体根本不是他张明舶的口味,“让他生出恋情的都是穿超小号衣服的女子,永远在抽条,长不成竹的笋。”[14]比如他的护士对象,相亲时他甚至连小护士的全貌都没有看清,只因姑娘“那一对小辫儿,一双小胖手,暄呼呼的手背上一排酒窝”[14],就首肯了这段恋情。与小婷初识,这个小说中唯一让他魂牵梦萦的姑娘,惊艳了他,小婷到底有多美?广玉第一次看见小婷的一刹那,为她的美丽所折服,小雪只看了一眼小婷的照片便被她的美貌照耀得自惭形秽,张明舶甚至用“西施”这一象征绝美女子的文化镜像来形容小婷,小婷的美不言自明。小婷眼神“明亮干净”,笑起来“无心无邪”,最让张明舶难以自拔的是她那似乎仍在发育中的身体,细瘦笔直,窈窕多姿,“两条细长的胳膊”、“孩子般细弱的肉体”、“孩子一样柔弱”[14],这个爱吃零食、爱睡懒觉的女孩身上释放出一股纯真和蒙昧的气质,激起了他与生俱来的保护欲和雄性怜爱,他不惜放弃知识分子的道德观,在明知小婷被包养的情况下,偷偷与她私会,甚至鼓动她与金主决裂,最终如愿让小婷成为所谓的“他的女人”。上述有关女性身体的描写全部由张明舶的视觉来呈现,带给男性超乎寻常的性快感,表现了他的原始生殖欲望和沖动,同时传递了多层寓意,其中最显著的一层旨在揭示主人公缘何钟情于吴玉婷,归根结底,男性还是视觉动物,女性的性格、能力、品德和灵魂等都不是男性择偶时所看重的因素,女性的身体和外貌才是真正打动男性的焦点。张明舶热恋着小婷,准确来说,他痴迷于小婷的身体和绝世美貌,尽管她好逸恶劳、百无一用、贪恋世俗浮华,不惜丢掉自尊委身他人,张明舶依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恋上了这个终将弃他而去的女孩。
二.身体叙述的表意价值
巴赫金说:“将身体看作一个‘中介,看作一种主体实践和述行行为,视作被生命政治、意识形态、文化话语所构建的一种符码和隐喻。”[16]可见身体在认识世界、社会和人类精神方面的重要价值。身体社会学认为,身体既是一种生物学存在,又具备社会性,身体作为一个客体被它所处的空间、社会环境和文化形态形塑,一个人的身体常常成为一个能指或者是书写信息的地方,被打上标记或符号的形式。小说家在文本中常常借助对身体的刻写与烙印,将身体打造成一个叙述的能指。[17]严歌苓在《蜃楼》中基于对男女两性不同的身体意象、身体图式和身体实践的书写,探讨了身体、文化和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挖掘出人物的身体意像和身体实践背后所传递的表意价值。
(一)深刻再现了复杂的人性
严歌苓在《蜃楼》中的身体叙述,深刻再现了人物的复杂、多面的人性,小说中男女人物对各自的身体观感将他们人性中许多暗藏的、被遮蔽的东西一一揭示,某种意义上说,小说中的人物存在一个相似之处:身体和心灵长期处于冲突的状态,以主人公张明舶的情感故事为例。张明舶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的身上保留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正直、清高和孤傲,在未去往海南之前,他家教良好,过着中规中矩的安定生活,恋爱经历简单,从他和几位女性人物的互动可以看出,他对待感情是十分理性的,在他看来,爱情是神圣的,是两个人彼此心灵与肉体的自然结合,容不得半点玷污,然而这种理想的爱情观真正落到实践中,在他身上渐渐演化为一种表里不一、身心割裂的状态。一方面,他在内心深处是瞧不起蓝兰、吴玉婷和季小雪之类的女性,尽管他十分不情愿承认,他对于她们出卖身体和青春的过往经历十分介怀,他鄙视蓝兰,用最恶毒的言辞嘲讽她挣着不干净的钱,强烈的自尊心和自恋情结使他不愿与之为伍,不愿意轻易接受她的帮助,所以当“我”问他是不是爱过蓝兰时,他表现得非常急躁,对蓝兰用“爱”这个字眼似乎过于轻佻;在他失业之后,他和小婷无力负担高昂的房租,生活过得捉襟见肘,他仍千方百计阻止小婷出去求职,一旦小婷脱离了他的视线,他便反复地在脑海中想象着小婷在鞋店被老板揩油、被试鞋的顾客占便宜的恶心画面,连他自己都不得不承认,“他对小婷是不尊重的”[14],一想到自己的生存依靠的是小婷的卖身钱他便感到无比耻辱,在他看来,小婷不过是一个人形宠物,除了站台、出卖肉体以外她一无是处。另一方面,现实的问题是,他多次依靠这些女性而活下来。面对小婷的不辞而别,他失去了生存的意志,幸而蓝兰收留了他,帮助他走出那段人生中的至暗时刻,让他的躯体有了容身之所,心灵得到抚慰;他尝试拒绝小婷,但他的身体是实诚的,他无法掩饰对于她的欲望,他在理性与欲望之间摇摆不定,两人的交集始于身体的吸引力,然而这种对于身体的迷恋终究败给了残酷的现实,小婷要的是昂贵的翡翠手镯,而小张只能负担得起鲜花和蛋糕,两人在错位的关系中渐行渐远,两人对对方的人生观、爱情观和价值观的嘲弄最终导致两者的决裂。小说中几位闯海人的情感纠葛荒诞不经,男人和女人之间相互征服,相互利用,各取所需,也许这就是人性的复杂之处。
(二)揭露了女性悲剧命运之成因
《蜃楼》的身体叙述不仅表现了人性之复杂,而且揭露了女性悲剧命运之成因,严歌苓认为,正是因为女性的身体受到父权和男权的压迫和双重戕害,造成了她们艰难的生存状况。一方面,女性的身体首先属于原生家庭,然后才是她们自己的,她们肩负着养活原乡亲人的重担,时刻要为原生家庭续命而奉献自己的身体,连同她们的青春一并被那贫瘠的原乡消费着。书中的几位女性都来自乡村,从关于她们家乡的不多的描述中,可以大胆推测出有关她们家乡的图景:经济不发达,思想落后,信息闭塞,并且存在严重的男尊女卑现象,这些女孩们被家人打发到遥远的海南,她们学历不高,没有一技之长,她们只能硬着头皮讨生活,挣扎在社会的边缘,“这样的女孩,心都是穷的,因为她们承载的,不是自己的记忆,更多的是那个饥荒、贫穷的群体记忆,所以她们求富若渴,再富都恐惧穷,于是,都有一颗穷极的心。”[14]另一方面,部分男性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在女性的悲剧中也难辞其咎。吴玉婷与她的包养者之间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利益交换关系,男人提供金钱和奢华的生活,小婷则奉上青春和美貌。不可否认,她爱过张明舶,甚至想过要与其长相厮守,但在现实的苦难面前,她缺乏独立和坚韧,她逃跑了,这段恋情注定无疾而终;广玉,丈夫瘫痪,独自带着三岁女儿在海口打拼,她与有妇之夫徐平搭伙做临时夫妻,可这样有违道德伦常的露水情缘注定是南柯一梦,建筑师随时可以抽身离去,而怀孕的广玉却要承受这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是去是留的艰难抉择,权衡再三最终牺牲掉这个无辜的小生命;蓝兰是个倔强的姑娘,她在历经海南的发端、房产泡沫之后幸存了下来,但她活成了什么样子?多年以后她与张明舶在深夜的大街上偶遇,那个身上实惠的山民女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穿着塑料仿皮高跟鞋、因过度整容而满脸化学胶质的站街女,如幽灵般漂泊在海南的街头巷尾,她的身体变化寓示了女性的身体被出卖,被肆意改造、扭曲和变形;书中最令人意难平的人物是季小雪,这个善于苦中作乐的小姑娘聪明伶俐,“若不是家乡太穷,她会在家乡唱山歌,采茶花,给一个山里的情哥哥去疼去爱……”[14]这是一个被迫堕入苦海的女孩,有着与少女年龄极不相符的圆滑和世故,可她又是一个极其重情义的女孩,她饥肠辘辘时即便仅得了一个椰蓉面包,也要慷慨地与老乡分食。从她初次出现在书中就被白嫖的嫖客打得头破血流,似乎为她的悲剧命运埋下伏笔,她毫无女性意识,对自己的处境没有丝毫的反抗,她甚至拒绝了张明舶和马克的救助,心甘情愿地与那些沉渣苟且偷生,然而她拼尽全力维护的两个老乡,一次次肆无忌惮地逼迫她出卖尚未发育成熟的身体,他们消费着小雪的身体,榨取她身体的剩余价值,甚至利用她的身体玩拆白党行诈骗之术,又恰恰是他们,嫌弃、厌恶小雪的身体,书中有一段描写,当沾有小雪经血的草纸意外飞出,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男性的反应是:“这么脏的东西,碰到哪个,哪个晦气!”[14]即使在她刚刚因为流产手术而不停地出血时,仍然对她拳打脚踢,最终连累她染上毒瘾,客死他乡。这些女性的身心遭受了父权和男权的双重打击,男性的薄情寡义和不负责任,直接导致女性承担全部后果。
身體叙述是现代文学叙事的一个重要策略,作家常常借助于对不同人物的身体进行标记和编码,赋予其不同的叙述功能和表意价值。严歌苓在《蜃楼》中选择身体作为叙述的切入点,着重对男性和女性的身体意象和身体图式展开详尽地刻写,男性身体被塑造为阳刚、气势和力量,充满了雄性膜拜,揭示出主人公的自恋情结,而女性的身体描写则呈现出过度性欲化的特征,交织着男性的欲望化凝视,反映出男性的欲望和幻想,是男性欲望在女性身上的投射。通过身体叙述,作家试图从更深层次来展示人性的复杂、立体和多面,有关人性的评价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论,而应从更加全面的视角予以综合考虑,作家还从两性关系的角度分析了身体的表意价值,探讨了造成女性艰难处境的罪魁祸首恰恰是根深蒂固的父权和男权思想,表现了作家对于女性命运的悲悯之情。
参考文献
[1]汪民安.身体、空间、后现代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3.
[2]郭洪雷,时世平.别样的“身体修辞”——对严歌苓《金陵十三钗》的修辞解读[J].当代文坛,2007(05):94-97.
[3]庞建丽.论严歌苓本土题材小说中女性的身体书写[D].广州:暨南大学,2013.05.
[4]冯梅美.文化规训与话语建构下的主体重塑——严歌苓小说《绿血》《芳华》的身体诗学[J].华文文学,2020(05):71-76.
[5]焦敬敏.论严歌苓小说地身体意像及文化内涵[D].贵阳:贵州师范大学.2007.04.
[6]杨倩.福柯身体思想视阈下的《云图》解读[D].郑州:河南大学.2014.04.
[7]李敏.小说《芳华》的身体叙事研究[J].文化学刊,2019(08):72-75.
[8]胡贤林.荒诞世界的身体镜像——评严歌苓的长篇小说《霜降》[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2(04):14-18.
[9]解孝娟.别样的“身体”写作——论严歌苓的女性书写[J].当代文坛,2012(04):114-116.
[10]张睿灏.论严歌苓小说的身体叙事[D].沈阳:沈阳师范大学,2020.05.
[11]杨超高.论严歌苓《芳华》的身体书写[J].华文文学,2019(03):92-97.
[12]王雪.电影《芳华》的身体叙事之维[J].电影文学,2018(19):99-101.
[13]张春.论电影《芳华》中的身体叙事[J].艺术评论,2018(01):69-75.
[14]严歌苓.蜃楼[J].广州:花城(长篇专号),2021秋冬卷:13页,22页,6页,58页,7页,39页,41页,43页,67页.
[15]刘艳,严歌苓.《蜃楼》:闯荡者的故事和海南岛的时代剪影——严歌苓长篇小说《蜃楼》访谈[J].美文(上半月),2021(11):76-85.
[16](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一卷)[M].晓河,贾泽林,张杰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145.
[17](美)彼得·布鲁克斯.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M].朱生坚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28.
基金项目:1、2020年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研修项目(gxgnfx2020059);2、2020年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社科重点项目:华裔作家严歌苓作品研究(RWSKZ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