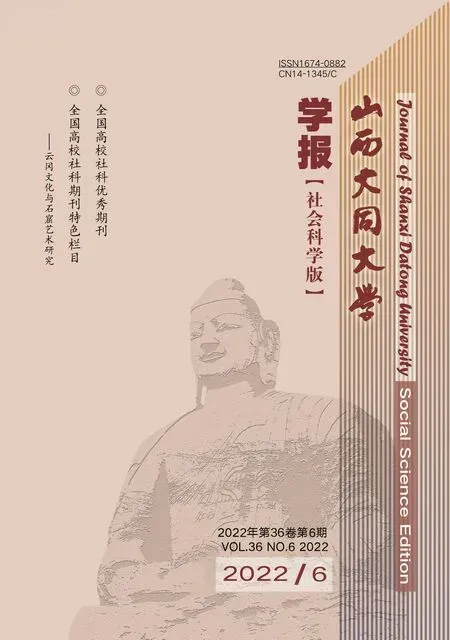大同方言提醒义构式“看+X+de”分析
石孟珂,王跟国
(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山西大同 037009)
现代汉语中有一类词常用来表达提醒、劝阻、警示的含义,如“别、小心、当心、注意”这类词通常可表达提醒义。例如:
(1)你要留意,人言可畏啊!
(2)这么危险的工具,当心别刺到你。
(3)送先生回去,注意保护先生的安全。
(4)母亲一边弯腰捡着,一边嘱咐我要小心别摔着。
这类提醒词通过言者视角表达不同程度的规劝或提醒,是普通话中常见的提醒词。与之相比,大同方言中的提醒结构显得较为特殊。例如:
(5)把书拿上,看忘了的。
(6)水太凉,先别喝,看激着的。
(7)别招她了,看哭了的。
(8)扶着他点儿,看跌倒的。
(9)岔路太多,找人问问,看走错的。
构式是指一个结构的形式或意义不能从其构成成分中得到完全预测。[1](P4)即“一个表达式的意义是将词汇项意义整合进句式意义的结果”。[2](P183)“看+X+的”从组合上已经无法推知整体含义,语义和用法已经独立,基本不需要借助其他成分,这样的结构可以认为是构式。在上述例句中,“看”的词义已经虚化,不再有实在的观察义,变为表担心、提醒的情态义,是话语标记。从整体来看,“看+X+的”构式有提醒规劝的含义,是说话人对当下语义环境的主观判断,表达一定程度的关心,用于会话交际中,具有即时性。
这与另一种普通话中的相似构式很不相同,来看一些表达:
(10)叶月芳说,“现在不好意思承认了,看你脸红的!”(周而复《上海的早晨》)
(11)大帅,看你说的!别说过得惯,我心里可畅快死了。(姚雪垠《李自成》第一卷第二十七章)
(12)你看你蹦的!屋顶要是没盖,你都发射到月球了。(六六《双面胶》)
例(10)、(11)、(12)与大同方言的用法有着明显区别,大同方言提醒义构式的后果是消极的,其后的事件只是言者的主观推测,并未真正发生,是一种事前提醒。而普通话的相似构式所表达的事件已然发生,是事后提醒。此三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看”语义逐渐虚化的过程,而不同虚化程度的“看”也使整个构式义发生了改变。导致两种构式语义上差异的因素——“看”的语法化程度,是一个切入点,或可对大同方言提醒义构式的产生及演变提供一些思路。
如此,我们便先从“看”在大同方言构式中的特征及其对构式整体产生的影响谈起。
一、构式“看+X+的”各构件的分析
(一)“看”的构件特征《说文解字·目部》:“看,晞也,从手下目。”[3](P67)从字形来看,是以手遮目,放眼望去。在有文献记载的最早时期是表示视线的接触或观察,是一种视觉行为,在漫长的演化中产生了许多义项。《现代汉语词典》中“看”的一个义项是:用在表示动作或变化的词或词组前面,表示预见到某种变化趋势,或者提醒对方注意可能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某种不好的事情或情况。[4](P705)
构件“看”是构体的基础,“看”从身体感知类的实词逐渐虚化,新的语义为新的组合方式做了准备。研究大同方言构式,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看+X+的”的提醒意味,此构式义很大程度上是“看”带来的。那么“看”到底对构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此,可以借助信息指向这一理论加以说明。在对否定词的研究中,否定词的“右项原则”,一般用以解释否定范围的问题,从信息流的角度则是在说明语流中信息的传递问题。在汉语尤其是方言中,“右项原则”并不具有很强的普适性,一些否定词的否定的范围还指向“左项”。由此,便可探究一下“看”的语流指向及其功能。
以上述例(5)来说明,可以看到,大同方言构式实际上是一个“半截子话”,由于形式足够简省,其包含的信息也流于言外,只有言语双方都掌握足够信息的情况下才能充分表达。单就构式本身,“看忘了的”可以表达提醒意味,但显然信息不足,不能达到言者想要表达的程度,所以还要再增加祈使性的话语进行补充。言者提醒下的含义是:不想看到“忘了”这一结果的实现。这是在对“看”后可能发生的结果的否定。如此,便得到“看”对右项的作用:言者主观判断下对右项可能发生事件的否定。
在否定可能发生事件的情况下,言者仍需传达一个信息,即如何阻止此结果发生,而祈使性的表达对言语双方最为经济,所以“看”仍有指向左项的信息:提醒听者注意言者想要其遵从的祈使方式。“看”对左项的提醒直接指向了构式外的祈使小句,因此这种提醒的表现甚至不一定要言说出来,仅凭动作也能达到提醒效果。如例(8)“扶着他点儿,看跌倒的”。“看”的语流信息同时指向了左右两项,既有对可能实现的事件“跌倒”的否定,又有希望听者遵从的“扶着他点儿”的提醒。需要指出的是,在同一语言环境下,言者想要否定的事件是恒定的,而“提醒”的方式可以有多种。就如同言者不想让“跌倒”的事件发生,可以说“扶着他”,也可以提醒“慢点走”,甚至仅用手阻拦一下。
上述分析的是“看”的语流信息指向问题,这实际是探究“看”在框架结构中对前后信息的限制。那么仍需讨论的是“看”的语义,尽管构式中的“看”已然不具有实词性的视线接触含义,但其依然有着情态义。高增霞提到,“‘看’由观看义动词发展出了担心—认识情态的标记词的用法。担心—认识情态是一种混合类型的情态:既表现了说话人对所陈述事实状况的确信程度,又表现了他对事情的期望程度,既是认识的又是态度的,是两种情态的混合。”[5](P99)大同方言构式中的“看”基本吻合“担心—认识情态”的特性,不过,若是仅描述此构式中“看”的混合情态,使用“认识—担心情态”更准确,因为“看”首先发挥作用的是言者对当下语言环境进行主观的判断,然后才会根据此判断进行提醒,以警示若不如此可能会引发的结果。
(二)构件“X” 在对构件“看”进行分析后,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构件“X”进入构式的条件,“X”内部结构比较复杂,经过研究,可大致分为简单式、主体式、把被式三类。
1.简单式
简单式并不简单,只是形式上没有其他两类成分多。在调查中发现,“X”可以由动词、形容词和动结式担任。能进入构式的动词都是非自主的变化动词,如“忘”“丢”“哭”等,非自主动词不能单用,后面要加“了”。形容词的用例不多,一般都是体感形容词,如“饿”“激(凉)”“烧(烫)”,后面则要加“着”。
“了、着、过”是具有“体”范畴的动态助词,它们标志着行为动作发展不同阶段的不同状态,石毓智提出关于“了、着、过”的三组语义区别特征,分别是[+实现过程]、[+时段持续]、[+离散性质]。[6](P183)“动词+了”的语法意义为动作的实现过程已经完成。可以看到,整个构式具有未然性,是一种事前提醒,那么为何还能允许实现义标记的进入。实际上两者并不冲突,由于整个构式是主观性的判断提醒,而“看”对右项信息的限制是:言者对可能发生事件的否定。对未然事件的提醒,是否定一个提前态,即把未来已实现的状态拿到现在来否定。如此一来,构件“看”与构式的特征共同对“X”形成了语义压制,要求其必须是实现义,这种实现是主观虚拟的结果。而形容词加“着”却并不是要表现[+时段持续]的语义特征,是要强调性质处于事实状态,仍是为了表明行为动作产生的结果。当“X”为述补结构,如“看跌倒的”,往往是表示行为在某一时刻达到的结果或状态,具有明确的离散性。由此观之,无论简单式的内部结构怎样变化,都被这样一条规则管住:通过一定的语法形式表达实现状态。这是构式语义压制的结果。
2.主体式
前文说到构式在一定程度上要求祈使句的存在,不然构式的提醒义就不太完整,也正因此简单式成为了最精炼的表达。而主体式的作用很简单:引入主体,在可能引起歧义或背景信息不够充足的情况下完善和独立构式。下面仍用“看忘了的”说明,一般而言,提醒功能会更多地用在提醒对方的语境中,在言语双方都知晓提醒的对象时,就不必出现提醒主体。但仍有特例,当言者意在通过他人来提醒自己时,主体“我”就要进入构式中,如:“先把水烧了,看我忘了的”,还可说“看他忘了的”(“他”多为虚指,没有明确的指代对象)。
3.把被式
把被式在构式中的使用频率也很高,下面是具体用例:
(13)看把手割了的
(14)看把孩儿饿着的
(15)看把我踩着的
(16)看让抓了的
(17)看让哄了的
以上“把”字句的语义可以理解为,某一行动带给或将要带给B 的结果,这在时相中可以理解为:从当前态向未来虚拟态的变化。例(13)“看把手割了的”,体现的是当前未割伤的状态很可能会“滑向”一个割伤的状态,而是否真的能到达割伤的状态,在构式中是没有体现的。但在此要强调的是,“把字式”只是能够体现状态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却不是“把”带来的,后文会对此进行解释。
大同方言构式是处于当下会话环境所使用的提醒话语,所以信息的传递与接收者始终是言语双方,提醒人永远是言者,提醒下行为的行使人永远是听者,但事件的受事却可以变化,由于构式经常是提醒听者规避某个事件,有时就会产生听者与受事是重叠的错觉。而实际上,听者并不总是受事。把被式在构式中真正起到的作用是:引出明确的受事,消除歧义。例(14)“看把孩儿饿着的”,把字式将事件的受事“孩子”引入构式中,明确了受事的归属。若使用简单式“看饿着的”,而前面的祈使小句又没有任何提示的话,很容易将受事与听者结合在一起,造成混淆。
(三)“的”的构件特征 下面来讨论构式中“的”的功能。目前学界对“的”的研究已经十分充分,总体来说“的”具有两种功能:“的1”表达结构关系,“的2”仅有语用功能。根据前文的例句可以看出“的2”出现在句子的末尾,起到煞尾的作用。下面通过对比研究讨论大同方言构式中“的”的功能:
A组
a 别哭了 别哭了的
b 别摔了 别摔了的
c 别忘了 别忘了的
A组以提醒词“别”为例,在例句不加“的”的条件下,句子a、b、c 分别表示已然事件、已然未然皆可、未然事件,“的”进入结构之后,提醒义加强,句意变为了只能表达未然事件。
B组
a 看哭了的?看哭了
b 看摔了的★看摔了
c 看忘了的★看忘了
B 组是大同方言构式,若将构式中的“的”去掉,大部分是构式不成立的,“看哭了”可以说,但也是表达一个已然性的事件。那么经过A 组和B组的对照,是否可以假定“的”有控制事件已然和未然的功能呢?情况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再来看前文提到的普通话中的相似构式:
C组
a 看你脸红的 ?看你脸红
b 看把他给忙的 ★看把他给忙
c 看把你积极的 ★看把你积极
C 组构式都表达已然的情况,且去掉“的”基本上不能说,a 例“看你脸红”在特定语境下勉强可以表达,但可能只用于回话,如:“你盯着我看什么呢?看你脸红”。如此,通过以上三组用例的对照已经能得出一些结论了:
①“的”字并没有控制已然未然事件的功能,在构式中事件是否处于已然或未然的状态是构式及其构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②以上用例中的“的”不是一个结构助词,而是起到煞尾作用的语气词,其表达一种主观的确认态度和肯定的语气。
③在构式这种极为凝练的结构里,去掉“的”就不能表达,说明“的”起到重要的完句作用。
张伯江、方梅认为句子的焦点分为常规焦点和对比焦点。[7](P66)在交际过程中,不同概念的认知状态是不同的,旧信息在前,新信息在后。常规焦点一般位于句末,且不需要添加标记成分。而对比焦点的预设与实际情况不同,需要添加标记成分来强调。构式“看忘了的”常规焦点是“忘”,“的”的加入产生了对比焦点(言语双方心理预期的对比),前文提到过,构式要求“X”是实现义,言者通过对可能发生结果的否定进行提醒,“的”表达确认态度,而态度的确认恰好是结果的浮现。但是,仍要强调的是,言者的主观态度及其态度下所认定会发生的虚拟结果绝非“的”的功劳,是构式本身和各个构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构式“看+X+的”的来源
大同方言构式“看+X+的”具有很强的能产性,内部结构也比较松散。对比普通话中的相似构式,我们有理由思考两种构式间的联系,它们是否具有承继关系,还是在演化过程中有了分叉,很值得研究。
(一)“看”的主观化与语法化 经过前文的讨论,可以发现构式中“看”的功能极大影响了构体特征,若要对构式的来源作一番解释,首要问题是“看”在演化过程中出现了怎样的变化,对构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可以肯定的是,“看”在语义演变的过程中出现了义位增加,说话人主观态度融入词义中且逐渐固定下来。也就是,“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信仰、立场、态度和感情,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记。”[8](P268)“如果这种主观性在语言中用明确的形式来编码,或者一个语言形式经过演变而获得主观性的表达功能,则谓之‘主观化’。”[9](P3)对于主观化是否为语法化中语义演变的机制,学界颇有争议,本文对此不做讨论,仅从语言事实角度探讨“看”出现主观性后对构式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看”在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
(18)梁车新为邺令,其姐往看之,暮而后,门闭,因逾郭而入。车遂刖其足。(《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当时的“看”并非“以视线接触”的意思,而是“探望、拜访”之意。从战国至两汉,实际上“看”表示“以视线接触”的用法极少,一般都用“视”来替代:
(19)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听,目所欲视,口所欲尝,虽殊方偏国,非齐土之所产育者,无不必致之;犹藩墙之物也。(《列子·杨朱》)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看”的使用频率才有所提高。唐朝是“看”词义发展的重要时期,除了“看望、观看”之意还发展出了“眼看着、转眼”和“估计、料想”的义项,如:
(20)老僧看他有分。(《五灯会元》卷十三)
(21)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唐·杜甫《绝句》)
(22)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唐·李白《书怀赠南陵常赞府》)
以上几例的“看”出现了主观评价和估量的词义,说明“看”在演变过程中逐渐主观化,已经不仅是客观而具体的动作,其中还夹杂了言者的主观态度。
(23)刘起庆用兵,一夕逃遁,您看我家用兵有走的么?(《大宋宣和遗事·亨集》)
这一例出自宋元时期的一部讲史话本,在当时的书面语中,已经有了“看”类词语充当插入语的情况,这是演变中重要的一环,说明“看”已经有了结合特定结构的能力。
元明清时期,随着大量白话文的出现,“看”字已经彻底取代了“视”字,成为了使用频率极高的词。其中,“看”字在四大名著中得到了广泛运用。
(24)你倒是去罢,这里有老虎,看吃了你!(《红楼梦》第二十八回)
(25)那和尚那里走!仔细看打!(《西游记》第二十二回)
这里“看”便有了明确的提醒之意。“看”发展到明清,现代汉语中的义项基本上已全部出现。
(26)一个人不能去,看掉在沟里头。(老舍《龙须沟》第一幕)
(27)快吃罢,看冷了啊。(巴金《寒夜》第二十二章)
“看冷了啊”和方言中提醒义构式已经极为相似了,整个表达的功能也基本一致,就是缺少了具有完句功能的“的”。
语法化的过程遵循由具体到抽象,由实词到功能词演变的规律。诸多学者也对“看”从实义动词到情态动词乃至变为话语标记的机制做出解释。但对此变化,仍应从隐喻入手。目前学者们将“看”的隐喻机制解释为由视觉域向心理域的投射。本文在此尝试提出另一种看法。前文梳理“看”字语义演化过程中提到,“看”在一段时期使用频率提高,逐渐吸收了“视”的词义,主要释义也变为了“以视线接触人或物”。在“看”最初仅涉及具体事物时,视线的发出与最终的落点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距离,视觉上的看便具有了空间属性,正是空间上的距离提供了时间上的长度,另外由于“看”这一动作的持续性,也为时间域的心理投射提供了准备。“看”能够带有时间性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基于使用频率提高和语法成分不断结合逐渐“浮现”出来的。功能主义者Paul Hopper 最早提出了“浮现语法”,其观点是把语法看成是动态的、在使用中所形成的趋向结构。[10](P139)“看”字的这种变化要得益于唐宋诗词中的大量使用。下面仅举一例来说明:
(28)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唐·孟郊《登科后》)
诗词中语词的结合创新,意象累积的背后是语言概念的整合与结构的重新分析。“一日看尽长安花”中“一日”和“尽”给整个诗句赋予了“时间性”,而“看”作为动词在其中仿佛也被时间拉长了。这是语境给句内成员增添的“假象”。而“浮现义”正是源于此种“假象”在大量用例中固定下来为人潜在地接受的含义。如沈家煊先生指出的,“意义的产生并不仅仅是语法的、结构的、规约的某种形式,意义的生成来自于形式后面的认知操作,这些认知操作是以形式为有形锚定的概念整合,概念整合生成的浮现结构所带来的浮现意义是从形式后面增生出来的,不是字面的意义,而是大于形式的附加意义。”[11](P6)
如此,再来看本文提到的两个相似构式,就很容易明白。下面用图示说明:

箭头所指的方向表示“看”在时间域的指向,它们都是从当前出发,分别指向了过去和未来的时间。时间上的延伸在构式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变化过程”。“看把孩儿饿着的”体现的是言者视角下“孩子”会由当前状态的一端“滑向”另一端“饿”,是状态的衰退,并会衰退到言者认为可能达到的极点上。“看”的时间性恰好契合了构式整体展现出来的“向坏”的过程。由于状态衰退的结果已经由言者虚拟地判断出来了,听者便不用花费时间去思考状态变化的结果,这是潜藏在深层结构中的语用因素。
但仍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其时间性是在语境或构式中浮现的结果,它潜在地依附于特定的结构中,并有条件地激活。“看”本身并不能区分过去和未来,即已然和未然。我们想要证明的是“看”在语义演变的过程中增强了主观性,在用法与频率逐渐丰富和增加的基础上浮现了“时间性”,这为构式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由于构式是一个连续演变的结构,难以划定其形成的准确界限。只能说,“看”是构式形成的前提,一旦构式初具特征,构式义的形成与发展就是构件合力的结果。
(二)构式化与构式压制 构式语法认为一个构式的产生和凝固有着漫长的过程,构式的产生、形成、发展的阶段之间界限模糊,难以细致切分。这是由于构式化总是伴随着语法化,在语言演变道路上纠缠不清。Diewald 和Smirnova 提出过四个语法化阶段,分别为非典型语境、关键语境、隔绝语境、范例化。[12](P146)实际上,也可将其看作是构式化的阶段,第一、第二阶段为先构式化构式演变,第三阶段为构式化本身,而第四阶段为后构式化构式演变。后构式化意味着已然成形的构式可能还会出现形式和意义的淘汰与缩减。那么,我们便循此尝试说明构式“看+X+de”的构式化过程。
上一章梳理“看”的语法化过程中提到,主观化可能是导致结构重组的重要原因,“看”进入了特定结构与人称代词连用,出现了“X 看”和“看X”的用法,其主观性即情态义与此结构共变,这符合语言或者狭义来讲符合构式化的核心原则:形式与意义的整合统一。可以说,“看”前加人称代词这一使用方式,为“看”的主观化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动力依据,现代汉语中的“X 看”类插入语或许便由此而来。在宋代,出现了“看+NP+V”的结构:
(29)放宽心,以他说看他说。(《朱子语类》卷十一)
之后,“看”进入结构的用法逐渐增多,到了明清时期有了“看+NP+V+的+X”的用法:
(30)沙僧道:“你看师父说的话。”(《西游记》第二十三回)
清末,“看+NP+X+de”的结构首次出现:
(31)看他年纪轻轻的,什么干不得,偏要做贼,还要偷宝灯。(《七侠五义》第六十六回)
将“看”进入结构的发展脉络大致梳理就会发现问题:照此脉络形成的结构并非本文讨论的大同方言构式,而是与之相似的普通话构式。确实,在前文讨论“看”的时间性便有所提及,其时间性既可指向过去也可指向未来。在“看”形成特定结构并逐渐构式化的过程中,指向过去的时间性具有绝对优势,这可能是由于已经发生的事情更易观察,在人的心理认知层面能留下痕迹。而将来时所指都是未发生的事情,人们对其判断、推测和征询往往就会具有很高的主观性。“这也就是将来时标记易于进一步发展出表达各种认识情态的用法,具有估计、预测等主观估价功能的原因。”[13](P77)所以,提醒标记的“看”是主观程度更高的、语义更虚的用法。
这并不是说大同方言构式没有原型,它的先构式化演变应源于“看”首次在结构中浮现出未来的时间性。根据已收集的文献资料,我们认为这一变化始于明清,明清小说的口语化对语言结构产生了极大影响,随着“看”使用频率的提高,特别是离开书面语进入到交际用语中,其词义进一步虚化,演变成表提醒的话语标记,实际上“你看”就已经具有了提醒标记的意味,而明清小说中的用法“看吃了你”正是由此发展而来,它逐渐摆脱了前面的傀儡主语,继承了“看”作为提醒标记的功能,形成了结构的重新分析。
至此,或可猜测本文讨论的大同方言构式与普通话相似构式并非由一条脉络发展而来。普通话构式是“看”的主观化逐渐增强,其内部结构逐渐扩张,最后稳固下来的结果。
于是就有了一系列构式扩张的痕迹:
X看 看+NP+V 看+NP+X+de 看把NP+X+de
功能学派认为,句式实例的产生是通过概念结构的类比映射及概念和语言的整合完成的。“看”作为提醒标记进入一定的结构,产生了“看吃了你”“看冷了啊”的用法,大同方言构式应是从此类用法中映射而来的。由于语料有缺失的可能,不能保证在此类用法之前没有其他结构出现。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相比过去的时间,“看”指向未来的时间性浮现得更晚,而“看”成为提醒标记是虚化程度极高的表现,结合一定的结构就更需要演变的时间。照此,也许可以旁证大同方言构式“看+X+的”的原型结构未出现或没有机会出现更多的结构扩张或紧缩,早期出现的简单式已然具有了很高的自足性。也因构式是一个“半截子话”,它总是做小句的后半段出现在会话中,无论构式内部怎样扩张,单独使用总是显得信息不足,未能达到提醒目的,所以总是需要前加一个祈使句以完整会话目的。这就限制了构式内部构件的数量,既然增加成分也不能完全表达含义,让构式内部的信息足够凝练就成了目的。
构式“看+X+的”已经由简单式发展出主体式和把被式,因此,可以认为其构式化阶段基本完成,而继续发展可能就会脱离构式的限制,变成普通结构,继而再经历结构的淘汰和紧缩,循环往复。
三、结语
本文对大同方言提醒义构式“看+X+的”进行描写和溯源,探究构式的构件特征,注重解释语义—形式对子的整体性。在搜集语料的过程中,笔者发现“看+X+de”结构在多地方言中均有出现,且具体形式不一。但是各地方言的用法基本区别在于结构内部成分的多少,也即整个结构的紧凑和松散问题。另外还发现各地方言中此用法煞尾的“de”有很大区别,如张家口县城地区使用“咧”,山西榆次使用“唠”等。由于缺乏更多的语料,难以对此现象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希望在今后语料充足的情况下能对此现象研究得更加深入、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