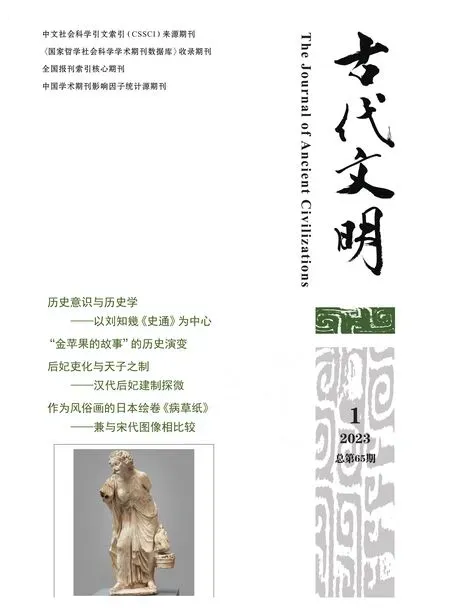《大清通礼》纂修新探
贾安琪
提 要:《大清通礼》成书于乾隆朝,由礼部礼书馆与通礼馆接续完成纂修。礼书馆纂辑的《大清通礼》以五礼为结构形式,以现行章程为主体内容,通过“考证”“正俗”条目的设置,标举鉴古宜今、整齐风俗的礼典特色。但是,这一编次体例在通礼馆开馆后被修正。通礼馆仿照杜佑《通典·开元礼纂类》体式,以“合于今制”为标准,采用现行仪注重新编纂《大清通礼》。这使《大清通礼》在形式、体例上与《大唐开元礼》一脉相承,礼典的教化与规范功能被进一步突出。乾隆朝确定的通礼传统在道光修礼时得以有效延续,但受到当时礼学界复兴古礼思潮的影响,道光《通礼》呈现出与乾隆《通礼》“虽有古制,概不摭拾”所不同的礼制趋向。德宗季叶,为配合预备立宪,礼部设立礼学馆重修《大清通礼》。但礼学馆以维护礼教为己任,并未对旧有礼制做出根本变革,显然难以应对清末时势之困。
“自古帝王经国治世之典,莫大于礼。”1清高宗敕撰:《清朝通志》卷36,《礼略一》,台北:新兴书局,1963年,第6939页。自西晋《新礼》之后,国家制定并颁行礼典作为君臣庶民礼仪教化的行为规范,成为中国历史的一大特色。清朝统治者也注意到了礼在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在历代礼书与《大清会典》的基础上纂修《大清通礼》,作为清朝礼法之轨式。
关于《大清通礼》的纂修情况,学界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尚存诸多问题有待深入挖掘。首先,关于《大清通礼》的纂修机构存在礼书馆与通礼馆两种不同观点,2参见彭孝军:《〈钦定大清通礼〉修纂考述》,《保定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林存阳:《三礼馆:清代学术与政治互动的链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51页。孰是孰非有待考证。其次,学界对《大清通礼》编次体例的认知局限于现存的《通礼》文本,但该书的编次体例在成书过程中并非一以贯之,其变动原因令人深思。其三,现有研究重点考察乾隆朝《大清通礼》的制定过程,对《通礼》的修订情况缺乏关注。笔者将结合相关档案史料,对上述问题逐一分析。
一、从礼书馆到通礼馆:《大清通礼》纂修机构之变迁
乾隆元年(1736)六月二十三日,乾隆皇帝颁布编修礼书1礼书泛指记录礼仪制度、礼仪活动以及礼制议论的典籍。国家礼典、私家仪注、三礼经传等皆可囊括在内。《大清通礼》是清代的国家礼典,在其未被赐名之前,朝野多以“礼书”代称。的上谕,正式拉开了纂修《大清通礼》的序幕。上谕中系统总结了历代公私礼书及《大清会典》在化民成俗方面的适用缺陷,并对礼书的纂辑做出具体指示:“应萃集历代礼书并本朝《会典》,将冠、婚、丧、祭一切仪制,斟酌损益,汇成一书,务期明白简易,俾士民易守。”2来保等:《钦定大清通礼》卷首,《上谕》,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第2页。上谕颁布后,礼部随即着手开展修书工作。
对于《大清通礼》的纂修机构,学界存在歧见。林存阳教授认为,《大清通礼》由大清通礼馆纂辑;3参见林存阳:《三礼馆:清代学术与政治互动的链环》,第151页。而彭孝军则称清廷专门开设礼书馆纂修《大清通礼》。4参见彭孝军:《〈钦定大清通礼〉修纂考述》,《保定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二者所附的纂辑《通礼》大臣官员职名相同,却对《大清通礼》的纂修机构得出不同结论,不免令人疑惑。结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观点皆存在偏颇。实际上,乾隆朝《大清通礼》的纂修经过了礼书馆纂辑与通礼馆重订两个阶段。
乾隆二十一年(1756),《大清通礼》纂修完竣。大学士兼管吏部事务傅恒等人在会议礼部请求议叙《大清通礼》修书人员的题本中,对《通礼》的纂修过程述之甚详。兹摘录于下:
准礼部通礼馆咨称:恭照乾隆二年礼部钦奉上谕开馆纂辑《大清通礼》,于乾隆十年告竣,共计《通礼》三十三卷附以《通例》十七卷,进呈奏明,交内翻书房翻译,武英殿刊刻。嗣因乐章章名有经乐部更定,又书内引用典礼不合及仪节内有与见行不同者,经臣等奏准,重加校正。十二年二月奉圣谕:《通礼》一书俟礼部《会典》进呈之日,随同呈览,钦此……今计纂就吉、嘉、军、宾等五礼,共五十卷,节次随同《会典》进呈,业经完竣。臣等见在缮写全书以备进呈。谨案乾隆十年书成,荷蒙皇上命名、锡序,以光盛典。今是书既经重订,将原赐序文进呈,或仍用原序,或载锡宸翰之处,伏候命下。臣等同原奉上谕,冠诸篇首,恭呈御览。请交内翻书房翻译,武英殿刊刻,以便颁行。5傅恒等:《题为会议礼部通礼馆奉旨纂辑大清通礼业经完竣例准议叙礼部员外郎永柱等员事》(乾隆二十一年八月十四日),吏科题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2-01-03-05340-006。
由该史料可知,在高宗上谕颁布的次年,礼部即奉旨开馆纂辑《大清通礼》。该书于乾隆十年(1745)告竣,由乾隆皇帝赐名、赐序,并交与内翻书房翻译,武英殿刊刻。但是,因为乐章章名需经乐部更定、书内引用典礼不合,以及一些仪节与现行规范不同的缘故,该书并未立即刊刻颁行,而是经礼部奏准之后,重加校正,至乾隆二十一年告成。如果仅就这份题本的题名及内容来看,由礼部通礼馆奉旨纂辑《大清通礼》,事毕后,也是通礼馆提出议叙相关官员。如此看来,通礼馆应当是《大清通礼》的制定机构。但若结合其它史料,《大清通礼》的纂修机构实可进一步探讨。
乾隆十年七月,大学士兼管吏部尚书事张廷玉在议叙礼书馆效力官员的题本中记录了礼部纂辑礼书的经过。“礼书馆具奏内开:伏查乾隆二年八月内,臣部遵旨开馆纂辑礼书,随经陆续纂就吉、凶、军、宾、嘉五礼并《通例》共五十卷,业已进呈完毕,经臣等奏准,奉旨交武英殿刊刻颁行在案。”6张廷玉等:《题为礼部礼书馆纂修礼书告成分别议叙效力各官事》(乾隆十年七月二十三日),吏科题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2-01-03-04332-015。对比傅恒题本中所称“乾隆二年,礼部钦奉上谕开馆纂辑《大清通礼》,于乾隆十年告竣……”7傅恒等:《题为会议礼部通礼馆奉旨纂辑大清通礼业经完竣例准议叙礼部员外郎永柱等员事》(乾隆二十一年八月十四日),吏科题本,档案号:02-01-03-05340-006。可见张廷玉这份题本中所提到的礼部于乾隆二年(1737)八月奉旨开馆纂修的礼书就是后来的《大清通礼》。但是,据张廷玉所称,礼部礼书馆是当时礼书的纂修机构,而非傅恒题本中提到的通礼馆。《大清通礼》的纂修机构究竟为何?
乾隆五年(1740)闰六月,兵科掌印给事中吴元安曾奏请将现修礼书中民间日用之礼先行辑出,每年与时宪书一并颁发。1参见吴元安:《奏为遵旨请修便民之礼书事》(乾隆五年闰六月十八日),朱批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01-0050-004。奏折中直接引述了《大清通礼》卷首收录的高宗诏修礼书的上谕,可见吴元安所说的现修礼书即为《大清通礼》。同年七月,鄂尔泰等人对吴元安的建议做出答复时谈到了纂修礼书的工作进程,“礼臣于开馆之后,先资载籍以稽于古,复取文案以参于今,后又覆准原任佥都御史陶正靖条奏,传令直省在京官员并候补、候选人等,各将该籍地方民风土俗灼见悖礼伤化者,据实开送,以凭集议”。2鄂尔泰等:《题为汇编礼书宜简明事》(乾隆五年七月十六日),礼科题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2-01-005-022728-0005。文中虽然没有直接指明礼臣所开之馆的名称,但是提到了陶正靖的建议。陶正靖在《考祀典正礼俗疏》中表达了其于礼书馆效力行走一事,“窃臣于上年七月,奉旨兼礼书馆行走。臣分修祭礼,已次第具稿交送部臣”。并针对正俗一条,提出“请敕该部通行各衙门,传知属员并候选进士、举贡,凡本处习俗悖理伤财之事,许据实开送到馆,部臣纂修官会同商酌”。3陶正靖:《考祀典正礼俗疏》,载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卷55,《礼政二·大典上》,台北:世界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412—414页。与前引鄂尔泰的表述相吻合。可见,当时《大清通礼》的制定工作系由礼书馆负责。
然而,礼书馆修书工作只维持到乾隆十年。根据张廷玉题本,乾隆十年五月,礼书馆书成议叙在馆效力官员的请求已经被乾隆皇帝批准,这标志着当时礼书馆的修书使命已经完成。受史料所限,礼书馆纂修、提调、收掌各官难以考证。但从张廷玉题本中所列誊录、供事名单来看,在礼书馆供职的一等汉誊录任麟书、陈令言、郑㪱,一等汉誊录、翻译卢焜,一等供事甘时敏、张际熙等人,4参见张廷玉等:《题为礼部礼书馆纂修礼书告成分别议叙效力各官事》(乾隆十年七月二十三日),吏科题本,档案号:02-01-03-04332-015。与《大清通礼》书中所载并不相同。礼书馆分修祭礼的陶正靖也不在《大清通礼》纂辑官员职名之中。由此可见,最终版本《大清通礼》所记载的纂修人员与礼书馆修书人员已是两套人马。礼书馆在乾隆十年书成议叙后,事毕则撤,并没有再负责后续重订工作。
礼书馆撤馆后,礼部重新开设通礼馆对礼书馆所修之礼书重加校正。根据《钦定大清通礼》所附纂修官员职名来看,新成立的通礼馆由来保、陈世倌、王安国、嵩寿4人担任总裁。提调、纂修、收掌及誊录人员皆由礼部满汉司员、笔帖式及儒士、书吏内选派。通礼馆人员构成如下表一。
此外,按照清代修书机构命名的惯例,通礼馆也应当是礼书被赐名为《大清通礼》之后才诞生的机构。而按照傅恒表述,该书于乾隆十年书成后才蒙皇上命名、赐序。综合傅恒及张廷玉的题本,通礼馆的设立时间应该在乾隆十年七月吏部议叙礼书馆效力各官之后,乾隆十二年(1747)二月奉旨《通礼》随同《会典》进呈之前。
综上,乾隆朝《大清通礼》的纂修由礼部礼书馆与通礼馆接续完成。乾隆二年八月,礼部钦奉上谕开设礼书馆负责礼书的纂修工作,乾隆十年纂修完竣。但该书未及颁布,便由礼部奏请,重加校正。由于礼书馆事毕撤馆,礼部成立通礼馆重订《大清通礼》,至乾隆二十一年告成。5这里的告成系指《通礼》成书时间。根据《国朝宫史》记载,直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大清通礼》才校刊完成。参见鄂尔泰、张廷玉等编:《国朝宫史》卷26,《书籍五·典则》,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42页。
二、从鉴古宜今到合于今制:《大清通礼》编纂体例之厘定
纂修《通礼》,发凡起例尤为重要。乾隆元年颁发编修礼书的上谕后,礼部曾会同总理事务王大臣酌拟条例六则,具体规划这部礼书的编纂体例。其内容如下:
其一,以风化之原,始乎朝廷,达乎里巷。本朝制作隆盛,礼教详明,宜悉遵《会典》兼查取各衙门案卷敬谨编录,掌之有司。其臣民以下之制,别为卷帙,以便颁行。

表一:纂辑《大清通礼》大臣官员职名1参见来保等:《钦定大清通礼》卷首,《职名》,第5—6页。
其一,以冠婚丧祭人道之大端,至宫室车服及一切往来之礼,织悉烦多,俱宜一并厘正。今拟以吉、凶、军、宾、嘉五礼为纲,钜细条目,次第类从。
其一,以编次体例先举现定章程为本文,次详其揖让升降为仪节,又次为考证,又次为正俗。
其一,以臣民以下章程固不容踰,而满汉仪节不能尽同,宜举其大凡,示之模范。
其一,以考证一条推本三礼经传、历代典章及先儒说礼之文,撮其精要,删其繁冗,以示鉴古宜今之意。
其一,以五方风气各殊,民生异俗,惟是淫靡积习,悖礼伤化,有必不容不革者,正俗一条,详切分疏,严为防范。2鄂尔泰等:《题为汇编礼书宜简明事》(乾隆五年七月十六日),礼科题本,档案号:02-01-005-022728-0005。
从上述条例可以获知,礼部规划的这部礼书在结构形式上仍然延续了历代相承的礼典传统,以吉、凶、军、宾、嘉五礼为纲,对相关条文进行分类编辑。其创新之处体现在内容编排方面,通过“考证”“正俗”条目的设置,彰显鉴古宜今、训民正俗的礼典特色。
张文昌先生曾对中国古代礼典编纂模式进行总结,提出自西晋《新礼》以来,中国古代五礼礼典大要分为两种编纂模式:一是以《大唐开元礼》为代表,节录当代仪节文字,以凸显礼制的规范性与完整性;一是以《太常因革礼》为代表,标举典礼仪制的前后变革,强调礼制的沿革性与修正性。3张文昌在系统梳理了唐宋礼书的编纂与运作模式的基础上,提出唐代礼典发挥“今王定制”原则,注重现行仪制的规范作用;宋代礼典则恪守先王之道,在礼典体例上多表现“因革为礼”特色。参见张文昌:《制礼以教天下——唐宋礼书与国家社会》,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2年,第228页。后世礼典的制作,多本于这两种传统。就礼书馆规划来看,清廷制定这部礼典,有兼综二者、超越前代的雄心壮志。一方面,以现行章程为本文,列明仪节度数,体现当朝礼典的规范效力;另一方面,通过“考证”一条的设置,叙述三礼经传、历代典章,及古今议礼言论,作为当代礼制之参考与补充,体现“沿革”精神。而《太常因革礼》等记述变礼的礼典,多标举典礼仪制在当代的因革损益,并不博览远搜,征之古礼。这使得礼书馆纂辑的这部礼书较之前代礼典在内容上更为丰富。更别具一格的是,针对汉唐以来,国家礼典缺乏的庶民之礼,礼部专设“正俗”一条,严加防范民间悖礼伤化、费财无益之事,用以推行教化,整齐万民。
因为所涉内容太过庞杂,增加了礼书馆的工作难度。乾隆九年(1744),礼部因所呈礼书屡有错误,被皇帝多次下旨斥责,其主管官员任兰枝等人也受到处分。1参见《清高宗实录》卷222,乾隆九年八月丙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60页;《清高宗实录》卷231,乾隆九年十二月己巳,第981页。在当朝礼典中阐发经义,记述礼制渊源与历史变迁,也在无形中削弱了礼典的规范与教化功能。为何礼书馆仍然大费周章,采取这一编次体例,笔者推测,其原因有三:其一,清代为异族统治,记述礼制因革可以构建清礼与儒家礼制的渊源关系,借此凸显王朝统治的正统性;其二,通过梳理礼制的历代沿革变化,以古礼为参照,以鉴古宜今;其三,作为有清一代第一部国家礼典,被朝野上下寄予厚望,礼书馆充分揣摩圣意,尽量满足高宗上谕中的期许,故而事无巨细,以期尽善尽美。诚如吴元安奏折中所称:“臣窃见礼臣汇纂礼书,迄今三载,尚未告成。意在博览远搜,期于尽善;溯源竟委,钜细兼收。洵盛世之典章,熙朝之令甲矣。”2吴元安:《奏为遵旨请修便民之礼书事》(乾隆五年闰六月十八日),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01-0050-004。
但是,这一原定体例并未呈现于刊行的《大清通礼》之中。礼部通礼馆在重订《通礼》时,除更定乐章及与现行法律不合之规条外,亦请旨对礼书体例进行变更:
臣等恭承谕旨,奏请依仿唐《开元礼纂》规模,采取见行仪注,准五礼篇目另加编纂。至原定通例,杂记朝会、卤簿、祭祀、祝版、玉帛等类,其间贵多贵少,不能悉称,应请分见于各礼中,其通例名目统在就删之列等因,奏准在案。今计纂就吉、嘉、军、宾等五礼,共五十卷,节次随同《会典》进呈。3傅恒等:《题为会议礼部通礼馆奉旨纂辑大清通礼业经完竣例准议叙礼部员外郎永柱等员事》(乾隆二十一年八月十四日),吏科题本,档案号:02-01-03-05340-006。
从史料来看,本次重订对《大清通礼》的改动如下:其一,明确编纂模式。《通礼》仿照唐《开元礼纂》规模,选用现行仪注另加编纂。其二,删除通例名目。相关内容分见于各礼之中。其三,调整五礼篇目次序。将五礼顺序由原先的吉、凶、军、宾、嘉,改为吉、嘉、军、宾、凶。改变书稿编次体例系属修书过程中的重大变革。在《通礼》书成待刊之际,礼部借重加校正之机,如此大刀阔斧的调整《通礼》编排,必然经过了慎重的考虑。但是,上述引文中,仅简单交代了删除通例的原因,对于书稿编次体例的变化并未解释。以下笔者结合《通礼》凡例及相关史料对其原因略作分析。
其一,《大清通礼》依仿唐《开元礼纂》规模,更符合乾隆皇帝“明白简易,士民易守”的形式要求,也更适应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据《大清通礼》凡例,“《开元礼纂》见于杜佑《通典》,而修史者采之《唐书》,今仿其式”。4来保等:《钦定大清通礼》卷首,《凡例》,第7页。由此可知,引文中提到的唐《开元礼纂》指的是唐代杜佑《通典》中的《开元礼纂类》。《开元礼纂类》系杜佑抄撮《大唐开元礼》而成。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评价:“其讨论古今,斟酌损益,首末完具,粲然勒一代典制者,终不及原书之赅洽。”5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136页。可见《开元礼纂类》基本涵盖了《大唐开元礼》的主要内容,并较原书更为精简。通礼馆纂修官员在重订《大清通礼》时择取《开元礼纂》作为仿效对象,与《大唐开元礼》编纂模式反映的礼典性格息息相关。《大唐开元礼》著于盛唐,以“今王定制”为指导原则,注重现行仪制的规范作用,以展示国家统治力量。6参见张文昌:《制礼以教天下——唐宋礼书与国家社会》,第228页。其每项仪文俱系现行规条,以便于行用。与之相对,礼书馆所纂的《通礼》文本,遵循“本文(现定章程)—仪节—考证—正俗”的编次体例。虽然以现定章程为主要内容,规范当代仪制,但因为兼顾礼制因革、礼经礼论,致使内容繁复,重点模糊,反而难以达成高宗简明易守的形式要求。诚如吴元安质疑中所称:“若又博综百代,义蕴未免宏深;遍采诸家,篇牍不无繁重。即刊于学宫,购求仍为匪易;纵讲于乡约,顷刻亦觉难通。”1吴元安:《奏为遵旨请修便民之礼书事》(乾隆五年闰六月十八日),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01-0050-004。作为清廷颁布的首部礼典,《大清通礼》肩负着建构王朝礼制,教化天下臣民的重任。打击僭礼违制行为,整饬社会不良风俗,更是乾隆皇帝即位之后重点关注的对象。为了更好地维护统治秩序,礼典的规范性与实用性自然成为清朝统治者的首要考虑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延续《开元礼》的形式与功能,更有利于实现清朝统治者总一海内、整齐万民的治理目标。
其二,《大清通礼》的体例变化是配合《大清会典》结构调整的内在要求。根据傅恒上呈的题本可知,礼部奏请仿《开元礼纂》规模改纂《通礼》是在乾隆十二年奉旨,“俟礼部《会典》进呈之日,随同呈览”之后,2傅恒等:《题为会议礼部通礼馆奉旨纂辑大清通礼业经完竣例准议叙礼部员外郎永柱等员事》(乾隆二十一年八月十四日),吏科题本,档案号:02-01-03-05340-006。乾隆朝编修《大清会典》的结构调整或许对《大清通礼》的编纂体例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有清一代,共纂修5部《会典》。在乾隆朝以前,《大清会典》的体例结构与《明会典》相仿,典例并载,收录现行规条与旧行事例。但是,乾隆十二年二月,高宗对《会典》的纂修下达的指示显示了他对旧《会典》体例的不满。“原议旧仪,连篇并载,徒为炫目,反掩正文。其他讹误多端,繁简未当,俱宜更正,以示宪章。”3《清高宗实录》卷284,乾隆十二年二月丙寅,第703页。总裁张廷玉领会圣意,请求“于朝庙典礼各定为一仪,于官司事例各定为一则,化参差之迹,成画一之规。书成以后,如间有因时损益之处,系畸零节目,止于则例内增改”。4《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首,《张廷玉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页。随着清朝统治者将《大清会典》与《大清会典则例》相区隔,《会典·礼部》仅规范现行仪制,《会典则例·礼部》则记述礼制沿革。礼部通礼馆重订《通礼》时适逢《大清会典》纂修,礼部尚书、通礼馆总裁王安国亦担任会典馆总裁。在这种情况下,通礼馆很有可能迅速捕捉到了乾隆皇帝的意图,为迎合圣意,改弦更张。对此,《大清通礼·凡例》透露出一些蛛丝马迹:一是强调“礼时为大”的编纂原则,不再叙述古制。凡例曰:“是书皆取见行仪注辑定,其非皇朝成式,虽有古制概不摭拾,至合于今制者存之。”5来保等:《钦定大清通礼》卷首,《凡例》,第8页。二是明确《通礼》仅载现行规条,不再记录本朝已行之旧典,“所有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已行旧典,年月次第另详《会典》,兹不备载”。6来保等:《钦定大清通礼》卷首,《凡例》,第8页。这都与高宗对《会典》仪文指示高度统一。《通礼·凡例》中还多次表示,《通礼》与《会典》相表里,要与《会典》吻合,以昭信守。随着《会典》体例变更而调整《通礼》的体裁亦在情理之中。
综上,通过此次体例调整,可以看出礼部在领会圣意的基础上,对《大清通礼》的定位与功能更加明确。即以《大清通礼》作为天下法式,规制朝廷仪制及官民生活,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在此过程中,礼典的教化与规范作用被进一步突出,详载行礼仪节、合乎人伦日用,以此弥补《会典》调整范围之不足,并起到羽翼《会典》的功能。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道:“自朝廷以迨于士庶,鸿纲细目,具有规程。事求其合宜,不拘泥于成迹;法求其可守,不夸饰以浮文。与前代礼书铺陈掌故,不切实用者迥殊。”7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2147页。
三、通礼传统与时宜权变:《大清通礼》的续纂与重修
“礼,时为大”是儒者制礼的基础理念。8郑玄注,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卷32,《礼器第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960页。制定符合时措之宜的礼仪制度,避免国家礼典成为僵化的教条也是朝廷修礼的直接动因。自乾隆朝编修《大清通礼》之后,有清一代曾两次对《通礼》进行修订。二者皆在不同程度上对乾隆朝确立的通礼传统进行调整,以适应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的现实需求。
(一)《大清通礼》在道光朝的续纂
《大清通礼》纂修完成后,主要颁在礼部供其行用,1参见王昶:《与汪容甫书》,载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卷2,《学术二·儒行》,第131页。这显然难以达成统治者淑世牖民的治理目标。为了更好地发挥《通礼》的教化功能,嘉庆二十三年(1818)八月,仁宗下旨“著武英殿按照省分各印给一部,各该督抚派人祗领,照刊流播。俾士民共识遵循,用昭法守”。2《清仁宗实录》卷345,嘉庆二十三年八月戊子,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66页。
针对仁宗推行《通礼》的举措,河南道监察御史朱鸿指出,《通礼》纂修至今已六十余年,现行规条多有遵奉增改之处,应酌加辑后,再行颁发。鉴于本次修订《通礼》是在原书基础上增改,朱鸿提议由礼部则例馆一体修辑,无需另行开馆。3参见朱鸿:《奏请酌修通礼一书事》(嘉庆二十四年六月初三日),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2160-015。朱鸿改正颁行的建议受到仁宗重视,命大学士会同礼部具体讨论修书事宜。礼部表示,将于《礼部则例》修订完竣后增修《通礼》,以便查照新定则例修改《通礼》内容。4参见穆克登额等:《大清通礼》卷首,《奏疏》,清道光四年刊本,日本内阁文库藏,第1页b。不过,朱鸿提出由则例馆纂修《通礼》的建议未被礼部采纳。吏部尚书文孚在议叙礼部修辑《通礼》当差供事的题本中称:“其通礼馆供事黄鹤鸣、张坤、潘甲三名,声明俟《通礼》告成另行鼓励。”5文孚等:《题为会议礼部修辑通礼成书所有当差供事请照例议叙事》(道光五年二月十八日),吏科题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2-01-03-09574-018。这表明纂修《通礼》的供事黄鹤鸣等人系于通礼馆当差办事。《福建通志·梁章钜传》也显示,道光初,梁章钜曾担任大清通礼馆纂修。6参见梁章钜:《楹联丛话》附录,厦门:鹭江出版社,1996年,第356页。由此可知,道光《通礼》仍由礼部开设通礼馆负责编纂。
道光四年(1824),《大清通礼》修订完成。新修订的《大清通礼》在整体上延续了乾隆《通礼》的礼法架构,按照原书体例,将历年以来著为定制之规条,分门别类增入4卷。全书共计54卷,又称《续纂通礼》。本次修订内容包括如下方面:其一,补充原书礼制记载的缺漏。如增补旧《通礼》未载之冠服制度、奉恩将军昏礼、致祭堂子之礼。其二,更正原书礼制的错误。如对照《会典》修改不合今制的卤簿、乐悬及历代帝王庙列祀位次,调整镇国将军以下谕祭之礼。其三,增补原书刊行后的新颁仪制。如增纂授受大典及太上皇三大节庆贺仪,以明确太上皇在礼仪秩序中的地位及待遇。除此之外,通礼馆还围绕礼部职掌,在嘉礼中补充了一些与科举、教化相关的事务性规定,如“宗室乡试”“宗室会试”“朝考”及“宣讲圣谕”等,7参见穆克登额等:《大清通礼》卷首,《续纂凡例》,第1—10页。使《通礼》内容更加完善。经过调整的《续纂通礼》在贯彻乾隆《通礼》确立的体裁与架构的同时,受到当时“以复古为职志”“回向经典”的礼学风气影响,8按照经学史观点,清朝是经学复盛时代。对于当时的学术研究特点,梁启超总结指出:“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9页;张寿安也提出,清儒形成“以经典为法式”的学术风气,学者转向经典考古寻求解方,借考证进行经典新诠。参见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6页。亦呈现出与乾隆《通礼》不同的礼制趋向。
道光《通礼》在内容取舍方面,以古礼为参照,具有复古倾向。凡例曰:“谨照《会典》全书细加核对,并参考礼经及《皇朝礼器图》《文献通考》各书,逐条更正。”9穆克登额等:《大清通礼》卷首,《续纂凡例》,第1页a。礼部尚书穆克登额也表示:“礼贵准乎人情,法当权于古意。”10参见穆克登额:《奏为纂辑通礼其服制一门酌修数条分别开明事》(道光四年七月十八日),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2550-037。礼部对经书古意的刻意强调,较之乾隆朝以“合于今制”为取舍准则,“其非皇朝成式,虽有古制,概不摭拾”的修礼立场大异其趣。11来保等:《钦定大清通礼》卷首,《凡例》,第8页。修礼期间甚至出现仪文制度互异时,根据古礼裁断改正的现象。如对于祭器内簠簋之实,古礼以簠盛稻粱、簋盛黍稷,而《会典》及《通礼》原书与古礼互异,最终礼部选择依据与古礼记载相吻合的《礼器图》对二者进行改正。12参见穆克登额等:《大清通礼》卷首,《续纂凡例》,第3页a。清末礼学馆评价道光《通礼》时也指出,“道光礼有依据古制,而与今不合者”。1《礼部奏礼学开馆酌拟凡例进呈等折》,《政治官报》,宣统元年闰二月初六日,第505号。这都显示出道光《通礼》复古的一面。
道光修礼博采儒臣之议,礼学家及其礼学见解在修礼过程中得到重视。北岳之祭,自明嘉靖以后,向在浑源,乾隆《通礼》所载亦同。清初大儒顾炎武曾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作《北岳辨》一文论证宜在曲阳。道光修礼时,经过诸臣讨论,最终听从顾氏之说对《通礼》进行修改。2参见张锡恭:《茹荼轩文集》卷2,《修礼刍议一》,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8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6页。此即礼臣采纳学人之说修改现行制度的例证。礼学名家胡培翚的学术观点也影响了道光《通礼》的编纂。《与费耕亭论继父服书》中提到,通礼馆纂修官费庚吉在修书时本欲删去继父之服,但胡培翚认为礼之继父与世俗所云嫁母之夫迥殊,不赞同费庚吉的做法。他指出,“先圣之制此礼,诚非苟然已也。今若必削其文,既恐无所劝,而孤寡苦于无依;又恐失之偷,而背义忘恩者众。请于继父同居及先同居后不同居者,仍存其服。而于继父下注曰:‘夫死妻稚子幼,其子与所适者,皆无大功之亲,而所适者又为其子立庙祀先,乃得为继父。’”3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4,《与费耕亭论继父服书》,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38册,第58页。胡培翚的建议被费庚吉所接受,“为同居继父”及“为不同居继父”服制最终在道光《通礼》中得以保留。4参见穆克登额等:《大清通礼》卷52,《凶礼》,第4页b—第5页b。另据《仪礼正义》记载,道光四年诸臣会议《通礼》各条时,内阁中书汤储璠曾就其礼学主张向胡培翚请教,5参见胡培翚撰,段熙仲点校:《仪礼正义》卷22,《丧服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447页。这也印证了胡培翚曾深度参与道光礼的纂修一事。
尽管在礼学思想渗透下,道光《通礼》并未像乾隆《通礼》一般极力突出礼典的规范性格,但是学界“以复古为职志”的思潮对道光修礼的影响也不应该被过分突出。整体而言,《续纂通礼》仍是清朝统治者在《通礼》原书体例的基础上,立足于以《会典》为主的现行仪制,对国家礼典进行修订的纂修活动。道光《通礼》对古礼的复兴主要体现为礼学考证后对现有制度的完善。
(二)《大清通礼》在光宣之际的重修
清廷第三次纂修《大清通礼》是配合预备立宪的现实需要。清廷立宪上谕发布后,考虑到礼教乃朝廷立国之根本,法制更张,礼制不能不因革损益,光绪三十二年(1906)九月,云贵总督岑春煊奏请编订变政后士庶通行之礼以养成民德。6参见《云贵总督岑春煊奏请修明礼教折》,载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74—977页。岑春煊此议与以溥良为首的朝廷礼官意图于清廷维新之际厘定礼制的想法不谋而合,旋即得到了礼部与学部的鼎力支持,请求在礼部附设礼学馆详慎编纂,并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迅速拟定了礼学馆的修书宗旨与章程。其中明确提出应以《大清通礼》为宗,以吉、凶、宾、军、嘉五者为纲,分类编纂;择取外务部、学部、陆军部所掌与之关涉者,依类编入。7参见《礼部奏筹办礼学馆大概情形并拟定章程折(并清单)》,载《大清法规大全·吏政部》卷20上,《内官制一》,台北:考正出版社,1972年,第718页。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清廷对礼学馆修书一事做出指示,“著即照所拟行,该部堂官务当董率在馆人员参酌古今,询查民俗,折衷至当,奏请颁行”。8《清德宗实录》卷575,光绪三十三年六月辛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03页。正式拉开了修订《大清通礼》的序幕。宣统元年(1909)闰二月,礼学馆正式开馆,并制作《重修〈通礼〉凡例》,作为修礼章程。根据礼学馆上呈的凡例内容来看,共计19条。其中,第一条与第三条是关于重修《通礼》的宗旨与原则类的规定。明确礼学馆以《通礼》为主,会通礼教与宪制的编纂方针,并宣示皇帝拥有议礼之权。其余诸条,则主要从修明礼教与配合立宪两个方面对《通礼》内容进行具体规划,参见下表二。
如表二所示,在礼部拟定的凡例中,有13条内容着眼于修补乾隆、道光两朝《通礼》中疏漏、错误及不合时宜之处,以保存礼书定制。如补充乾隆、道光礼所缺之冠礼及皇帝春秋阙里释奠孔子之礼;厘定旧《通礼》所载直省不经之祀;简化官民相见礼等。虽然礼学馆在修礼过程中试图结合西方思想文化,将“化除满汉畛域”的平等思想渗入,但对旧有礼制的逐一考订、详加论说仍是修明礼教的重心所在。3凡例明确表示,凡道光礼一时疏误者,悉详加校正;凡引据未确者,皆为更正。参见《礼部奏礼学开馆酌拟凡例进呈等折(并清单)》,《大清法规大全·礼制部》卷7,《礼学馆》,第38—41页。

表二:重修《通礼》凡例条目分类1本表中所用编号系笔者根据礼学馆所呈凡例之排列顺序自行标注。相关内容参见《礼部奏礼学开馆酌拟凡例进呈等折(并清单)》,《大清法规大全·礼制部》卷7,《礼学馆》,第38—41页。
凡例中关于配合立宪的制度设计共计3条,主要通过在《通礼》原书基础上增设篇目的方式谋求与宪制会通。其一,模仿宋代《太常因革礼》以《开宝通礼》为主而记其变的编排方式,在旧《通礼》的基础上增设“新礼”“废礼”两篇,以便增入与宾礼、军礼及学礼相关的新式礼仪,保存与废止科举考试相关的旧礼。其二,仿效江永《礼书纲目》,在五礼之外增加“曲礼”一门,遵照《会典》、则例及新修的宪法、法律,将相关民事法律制度增入,并纂辑各家正俗之说以及礼器图、丧服图等,以便民间诵习。其三,书成之后将关涉士庶民礼条目另行刊布,以便单行。4参见《礼部奏礼学开馆酌拟凡例进呈等折(并清单)》,载《大清法规大全·礼制部》卷7,《礼学馆》,第38—41页。礼书馆的修礼规划在体例上虽未延续道光礼在《通礼》原书基础上全面续修增辑的撰作模式,却仍未脱离传统礼制的框架,重修《通礼》主要是结合立宪改革内容对礼仪制度进行局部调整。
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之下,《大清通礼》的修订并不顺利。一方面,礼学馆看重的查访风俗一事并没有得到各省的重视和支持。截至宣统元年十二月,各省汇辑的礼俗表并未一律送部。加之民礼条目需与民法相互订正,民礼纂修进展缓慢。另一方面,对于亟需编入《通礼》的宾礼、学礼、军礼篇目,外务部、学部、陆军部也一再拖延。礼部不得不勒令各部速行编送,以便《通礼》能如期告成。5参见《礼部奏礼学馆办理情形并详拟分年办法折》,载《大清法规大全·礼制部》卷7,《礼学馆》,第42页。但颇为遗憾的是,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清廷覆灭,这部被清廷寄予厚望的《大清通礼》也没有编纂完成。对此,陈宝琛感慨道:“政体既变,侍郎挂衣冠去,馆员亦云散,而委盈尺垂成之书于官寺,其为灰尘、为蠹蚀,无从闻问。”6陈宝琛:《沧趣楼文存》卷上,《曹君直礼议序》,载氏著:《沧趣楼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99页。
结合礼部拟定的《重修〈通礼〉凡例》与现存的《通礼》稿本残卷来看,这部《大清通礼》在宪制方面建树不多,而在礼仪细节的考订上颇为用力。这一方面归因于清廷意图保存国本,以礼教范围宪制的政治立场。礼学馆纂修官张锡恭对慈禧太后立宪方针阐释道:“夫列邦之良规曰兼采,中国之礼教曰无违,则注重在礼教可知也。”7张锡恭:《茹荼轩文集》卷2,《修礼刍议三》,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86册,第17页。另一方面也与清廷拟定的修书人员资质不无关联。礼学馆纂修官员的选拔与乾隆、道光修礼时相比,具有鲜明特色。原本熟悉政务的礼部官员不再担任修书之要角;取而代之的是调取精通礼学、素著望闻的硕儒到部专任编纂之事,并采访各省官绅熟精礼学者为顾问。8参见《礼部奏筹办礼学馆大概情形并拟定章程折(并清单)》,载《大清法规大全·吏政部》卷20上,《内官制一》,第718页。对此,当时新闻报道评价:“今者奉旨设立礼学馆,由是好古儒臣,运经硕子得以发抒蕴蓄。”9《选谕·议礼篇》,《申报》,1907年8月30日,第2版。以陈宝琛、张锡恭、曹元忠等为首的秉承礼制传统的儒生成为修礼团队的主流。但是,这些精通礼学的儒臣士子受自身学术背景所限,坚守经书文本与亲亲尊尊的礼秩基石,将救亡图存的希望寄托于对《通礼》文本的考订与诠释之上,并排斥馆中变乱旧章的行为,1参见曹元弼:《诰授通议大夫内阁侍读学士君直从兄家传》,载曹元忠:《笺经室遗集》卷首,民国三十年吴县王氏学礼斋铅印本,第2页b。最终致使《通礼》在保存礼教与配合立宪一事上轻重失衡。此外,礼部“分修书行政为两事”的管理方式,2参见《礼部奏礼学开馆酌拟凡例进呈等折(并清单)》,《大清法规大全·礼制部》卷7,《礼学馆》,第37页。将礼学馆修书与礼部的行政事务相剥离,也在无形中淡化了礼学馆编订《大清通礼》的行政实用色彩。重修《通礼》日渐成为礼学家为保存古学而精研礼书的议礼治学之作,与行政实践相去甚远,这显然难以实现清廷配合立宪的编修目的。
四、结 语
礼,时为大。面对不同社会情况,朝廷致力于通过国家礼典的制定解决不同的社会问题。作为清朝开国之后的首部礼典,乾隆朝《大清通礼》的基本任务是在延续前朝礼法架构基础上,完成符合清朝特性的礼制建构,进而实现统治者淑世牖民的治理目标。因此,历经礼书馆、通礼馆两任编纂机构寻绎,乾隆《通礼》在编纂模式上最终选择遵循《大唐开元礼》的制礼传统,将现行仪制定于一尊,以突出当朝礼典的教化与规范功能。这既是清朝统治者礼法体系建构的内在要求,也是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经过调整之后的《大清通礼》,标举明白、简易,士庶易守之礼典特色,在功能上弥补了《大清会典》调整范围的不足,为朝廷礼仪教化的推行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撑。
《大清通礼》既是清朝礼制法律形式的集中体现,也是三礼经制度化的产物。衔接学术与政治,沟通理想与现实。受乾嘉以来复兴汉礼思潮的影响,道光朝续纂《通礼》也在制礼思想及具体内容上做出调整,以回应学术与社会实践产生的相应问题。光宣之际,中国社会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以及制度思想的多重挑战,出于保存国本的现实考虑与养成民德的长远考量,清廷在推动制度变革、社会转型的同时,希望重修《大清通礼》以重构社会秩序。但是,礼学馆纂修官员的整体思路仍然延续过去的礼制传统,被清廷寄予厚望的《大清通礼》亦随着清朝的覆灭而败于垂成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