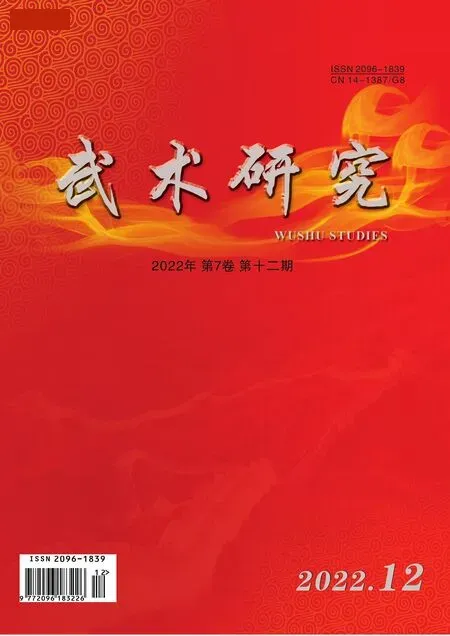近代社会转型中我国传统武术的嬗变分析
曾丽春 吴宝升
温州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0
1 前言
传统武术衍生于农耕文明,派系种类繁多。历史变革,时代迁移,一切生活需要,渐次递变,于是由前传后的传统武术,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传统体育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形成了以儒家“天人合一”和“气一元论”为哲学基础,以保健性、表演性为基础模式,以崇尚礼让、宽厚、平和为价值取向的体育文化。在外在形式上主要以健康长寿为终极目的的养生和以保身护体、技击与套路相结合的武术为一体的内外合一,整体圆融、稳定而丰实的结构体系[1]。那么,作为中国传统体育极具代表性的项目——传统武术,在鸦片战争后的近代社会转型中产生了何种变化?传统武术又如何突破传统文化的稳定结构,适应时代的变化发展?窥一斑而知全豹,处一域而观全局。本文集中关注的是鸦片战争后国门被打开后的中国,其社会转型的渐进发展对传统武术产生的具体影响,试图厘清绵延几千年的传统武术在1840-1937年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自身的转变状况,以期为当今社会转型中传统体育活动适应时代发展的生存演化提供经验启示。
研究主要选取了洋务运动(清朝统治阶级的自救运动)、甲午中日战争(回光返照帝国的重创)、辛亥革命(社会结构的重新构建)以及“土洋体育之争”(中国体育的发展道路)这四个代表性事件,从具体的社会历史出发,既是纵向上随着时间推进社会转型变化的深入成像,也是横向上综合深入考虑政治改革、战事动乱、社会革命、思想革新的重点聚焦,推敲传统武术的时代性与流变性,分析社会转型的渐进发展对传统武术产生的具体影响。
2 近代社会转型与传统武术嬗变
封建社会专制行政之网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形成了一个自洽的封闭系统。中世纪的幽灵消失后,资本主义的“浪潮”从西欧向世界扩张,受这股势力影响,中国运行了几千年的自洽封闭系统也开始向新的社会形态转变。在传统社会中,人们从事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生产,以家庭为中心承担特定的角色,以地缘、亲缘为人与人之间的主要联系纽带。鸦片战争后的中国,西方列强的侵入、西学东渐的思潮以及资本主义的产生和社会转型,使中华民族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转型将原先的秩序打乱,支持传统武术开展的社会结构被破坏,新生的社会结构尚未成型。牵一发而动全身,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其政治生活的革新,社会思潮的变化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传统体育活动。
2.1 洋务运动:传统武术裂变伊始
一个民族的独立首先是民族精神独立,在外来文化入侵时,人们会情不自禁地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理论来抵御外来文化的入侵。在洋务运动中,西式体育和传统体育活动二者同时在国人生活中并立,因西方体育是伴随着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炮舰进入中国的,所以人们以传统观念来审视西方体育时,或者敬而远之,或者不屑一顾[2]。在文化观念的偏差上,传统武术与西式兵操,传统体育与西式体育的对擂揭开序幕。
2.1.1 底层大众的生存需要:民间传统武术螺旋式上升发展
在混沌的局势中,清王朝行政管理的执行力开始下降,禁武令的执行管理因社会形式的复杂性未能自始至终贯彻实现,辅之以西方侵略者夹带着西方文明的进一步入侵,民族危机加剧。民族矛盾的加剧激化了国内阶级矛盾,在社会底层的大众,因缺少生存生活资料,不能同商贾官吏一样可以依靠金钱权力换取平稳安定的生活,只能寄期望于习练传统武术,以达自保,在混乱的社会中以求容身之所。各地农民运动的上演就为传统武术活动的展开提供了畸形的历史轨迹。1841年,广东三元里人民的英勇抗英斗争掀开了中国人民反帝运动的序幕,为了在复杂动荡的社会下安身立命,许多矿工、纺织工及其它行业的工人都组织有武馆,工余时间常请武师到馆教授武艺[3]。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在当时的民间严禁习练拳术的社会背景下,太平军对军事训练有着足够的重视,促进了农民的习武活动。军中许多名将都是精通武艺的好手[4]。随着义和团的发展壮大,清政府害怕其以武力威胁乃至更替政权,便施强制手段以期禁武。当时社会人民,颇以武为危事而咸怀戒心。然武术在中国相沿成风,官府虽施强制手段,依然不能制止[5]。在浩浩荡荡的农民革命的新局势中,其社会大背景的禁武并未割断传统武术的生存命脉,也未在战争与革命的炮火中销声匿迹。虽有不少武术名家殁于革命暴乱斗争之中,但传统武术命脉一直系于农民大众之中。农民大众成为传统武术的主要根基力量,成为燎原星火的点燃者,在战争中,传统武术其中于民间呈螺旋式上升发展趋势。
2.1.2 上层阶级引入西式兵操:未触及传统武术根基
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侵入中国,审时度势后,国人将目光投向了西方的“技巧”,纷纷投身借“西法以自强”的活动。在“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下各精英人物深信“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此纷纷探索和利用西方近代新式体育。从曾国藩建立湘军,李鸿章设立淮军,左宗棠创办福建船政学堂,再到张之洞兴办两广水陆师学堂,这些在当时具有先进思想的精英人物都看到了西方的先进利器和西洋体操的军事价值,且纷纷将西方兵操体育引入自己阵营之中[6]。在浓厚的军事烙印之下,以期驱侮自强的国人毫不犹豫地将西方的所有一并拿来学习。此时,国人对西方体育存在一定的认知偏差。于军队开展的“兵式体操”,在王维泰看来不过是我国古代舞蹈遗留下来的锻炼方式。“体操者实非西法,乃我中古习舞之遗意,而教子弟以礼让之大本也。”[5]作为政治变革的产物,此时西式兵操仅是一种达成强兵御侮的手段。这种自上而下的器物改革并未触及传统武术根基,故当火器未盛之时,武术实为军中之操法,及改习外国兵操,仍不弃武术[5]109。这场关于西方器物学习的改革并未对我国传统武术产生较大影响,但是传统武术也开始由辉煌走向没落,艰难地走向了转型之路。
2.2 尚武思想:传统武术在价值审视后消沉
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军落败,这极大地刺激了国人,中国先进分子纷纷试图求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之道。梁启超在其著作《中国之武士道》中就大声疾呼中国应提倡尚武精神,“今者爱国之士,莫不知奖励尚武精神之为急务”[7]。乙巳四月初三日《时敏报》登载的题为《论尚武主义》一文,即阐明“旷观古今之历史,横览中外之大势,见夫国家忽兴忽亡,忽强忽弱,而究其所以致此之由……在乎民质尚武与否而已。盖民质者,国家之要素,社会之基础,兴亡之根源,而国家所赖以成立也。民质能尚武,则其国强,强则存;民质不尚武,则其国弱,弱则亡。英、法、德、美何以强?强于民质之尚武也;印度、波兰何以亡?亡于民质之不尚武也[8]。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各仁人志士在思考和对比中将目光转向日本,得出的共识是:日本之所以能摆脱积贫积弱的处境,与“富国强兵”之国策有关。中国欲救亡图存,唯有学习日本和西方,提倡尚武,重视体育[9]。据此,近代中国人开始从更深的层面接受西方体育和认识西方体育[10]。在此情形之下,政府改练新军,学校增设体操一科,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5]。“嗣科举既各省遍设学堂,武术遂弃而不用,各处之武学馆亦列入天演淘汰之列。北京一隅仍多派各门武术专家,但传授生徒不能如前之自由,较之前之盛况相去远矣,军事上,绿营裁撤,各军队均改外国操法不复专事武术;在民间集团多用火器,各省镖局亦不负往昔之盛。各富商巨绅响之须延武士保护者,今亦自置火器,不负专恃武术。”[5]甲午一役极大地挫伤了传统武术在官方及民间的正统地位,辅之以1901年清政府颁布的废除武举制政策,中国习武(传统武术)之风江河日下、日暮途穷。同时,在各精英人士的疾声呼吁及政府的合力之下,整个社会形成尚武风气,但此尚武亦非“传统武术”之武,它泛指的是涵盖传统武术在内的身体锻炼活动方式。主要是通过期望国人通过身体锻炼增强身体素质。西式体育“尚武之风”悄然“潜入夜”,割据中国体育土壤,传统武术渐入消沉。
2.3 辛亥革命:国术日益趋重,期待传统武术奋扬民志
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成立,国人亦重体育,各界人士,竞尚各种体操,各种运动,嗣渐多趋重我国固有之武术[5]。西方国家入侵所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迫使中国人开始接受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在争取民族独立时代命题下,民国时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被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楔入,得出了“发展我国体育,不可不从我国实际出发,注意国情”的结论[11]。在此思潮下,以国术(武术)为代表的传统体育项目开始受到关注。国人寄希望于国术,以期通过习练国术达到民族自强的目标。提倡国术者指出,国术乃我国固有之体育,适合我国国情,尤其在民族危机的时候,国术乃救国之利器,因此,提倡国术为当务之急。“壬子癸丑学制”(1912-1913)后,武术以合法的方式进入学校并成为体育教学内容[12]。李芳宸先生在其国术馆的讲话上指出“我为救济民族的衰落起见,设立国术馆。这并不是无故消耗政府的钱财,而是希望达到强国强种的目的,奋扬民志的皓的。因为国术与民族之存亡,是有密切关系的[13]。这实际上是把传统武术等同于“工具”,希望传统武术成为武装自己的刺刀,提倡国术就是希望能让身体增强战斗力,去实现强国救种的目的。在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的近代体育的回合较量之中,一方面,在社会结构转型下的西方体育以其独有的特征传入有深厚文化传统积淀而又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最终扎根,并且为人民喜闻乐见;另一方面,对于衍生于中国土壤的传统武术在面对社会转型之下的起承转折,更多表现为思想上的沉浮。而传统武术在当时承担的并非作为体育项目强身健体的功能,更多的是承载着国人期待崛起的强烈自尊之心以及肩负着民族振兴的光荣使命。这种国粹主义思想在一定情形下推动了传统武术的繁荣。
2.4 东西体育之辩提供多元视角——在对立中走向前进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并没有完成两种不同性质社会之间的过渡,社会混乱,军阀割据,多元思想林立。中国体育的体育发展道路问题的讨论,从1914年将马良创编的《中华新武术》引入国民教育体系中起这种争议就已初见端倪。1932年,中国人第一次参与奥林匹克运动会后,“土洋体育之争”西方体育(由欧美传入的近代田径和球类运动项目)与东方体育(以武术为代表的中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争论达到了高潮。发表在《大公报》上的《今后之国民体育问题》呼吁,“请从此脱离洋体育,提倡‘土体育’!中国人请安于做中国人,请自中国文化之丰富遗产中,觅取中国独有的体育之道。”认为应当舍弃西洋竞赛运动的方法,从此不必参加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5]。这篇社论引发了学界就今后中国体育道路问题的深刻讨论。吴蕴瑞就此社论发表了《今后之国民体育之我见》回应了关于摒弃洋体育的观点,并且认为今后国民体育途径,主要是看它是否能适应个性,适应社会。各种体育都有自身独特的用处。“故今后欲适应环境,为捍卫国家计,宜训练智勇兼备之士,养成跑跳奔攀之技,然此端赖游戏器械田径运动等有养成之,绝非土体育单独所能奏效。”[5]过去的信仰又或者说是意识形态似乎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化的浪潮下失去了有效的解释力,因此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动摇,或者说是怀疑。这种思想在土洋体育之争中显现出来。当然,这场论争更进一步地加深了国人对土洋体育各自特点和实质的认识,为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的初步融合提供了思想基础,使“洋”体育更好地走进中国,也为中国的“土”体育走向世界创造了更好的条件[10]。同时,在这期间所谓的“土体育”,也抓住了发展契机,与西方体育的对话让传统武术更深切地扎根中国土壤,从当时诞生的武术社团组织就可见一斑。根据习云太的《中国武术史》记录的在册的民国时期的武术社团组织共49个,除去1914年之前成立的武术社团组织以及部分没有确切成立时间的武术社团,在东西体育之辩思想浪潮中共衍生武术社团组织35个。总体而言,民国年间不同思潮的激烈交锋以及连年战火等,影响了武术的发展。但这一时期的武术,仍呈发展趋势。在“土洋体育”之争的论战中,人们对传统武术的认识逐渐深刻,传统武术的科学化阐释也渐进开展。

表1 民国时期部分武术社团组织
3 结语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在面对内忧外患的情形之下,呼声“政治救国”“实业救国”“体育救国”,实际上是希望借助某种工具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而“体育救国”中体育的目的,无外乎是由民众健康扩大到复兴民族。可以说,救国的思潮一直充斥着整个中国近代史,当体育救国兴盛时,国术与国民健康的关系,舶来的体育与国民健康的关系,中国体育与舶来体育之间的关系,就展开在民众眼前,对于它们的讨论也变得热切。从洋务运动的“借西法以自强”,甲午海战失利后直接将“救亡图存”与“体育”相勾连,辛亥革命提出国术为救国利器,最后的东西体育之辨,这种将民众健康亦或是体育置于急功近利的荫蔽之下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一斑。实际上,这种体育工具化的思想也维系着传统武术的生命活力使其能够完成时代浪潮下的蜕变。传统武术的发展态势是否可以看作就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对抗之间的结果?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东方国家变得更加西方化还是更少西方化,抑或是两者相互矛盾的交织?这些问题很难一言以蔽之,在不同的社会,乃至同一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答案都有所不同。正如中国近代历史上两次不同性质的思想争论一样,维新派与封建顽固势力的论战,保皇派与革命派的论战,这些势力新旧更替,势力变化,角色转换。而传统武术的繁荣,与对抗之间的结果息息相关,当此思想兴盛时传统武术繁荣,彼思想兴盛时,传统武术蛰伏。
当然,今日之中国已然是世界之中国,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儒学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正在有力地回应“西方文化霸权”。传统武术,或者是传统体育的背后文化意识形态如何保持自我的独立性,才是传统武术不断推进,适应民众需要,满足社会大众的情感的重中之重。不可否认的是,传统武术在转型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问题,直至今日,传统武术的现代化转型依然没有完成,但文化的交流绝非简单的文化单向移植,人类历史的前进也离不开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对于传统武术亦或是传统体育而言,拥有文化输出和文化健全机制,方能获得文化补偿,赢得空间上的扩展和时间上的延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