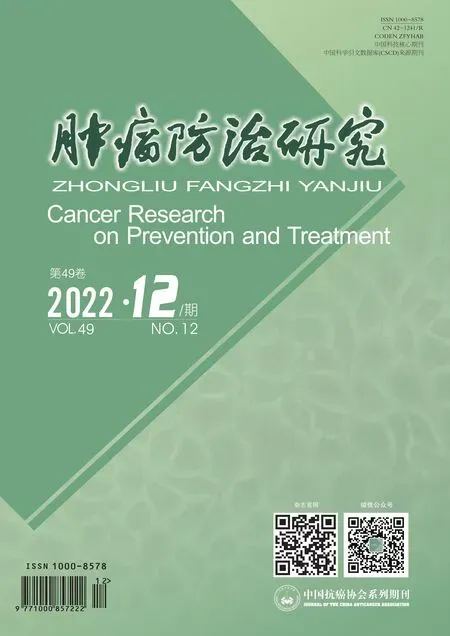炎性反应参数评估壶腹癌预后生存的研究进展
陈瑞秋,张志磊,贾聿明,彭利
0 引言
壶腹癌是一种相对罕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约占所有胃肠道恶性肿瘤的0.2%~0.5%,在壶腹部周围肿瘤中占6%~17%[1]。从解剖学方面看,其位于胆总管和胰管汇合处的远端,即瓦特(Vater)壶腹部。与其他壶腹周围恶性肿瘤相比,壶腹癌由于胆道梗阻引起的黄疸症状出现较早,疾病发现及时,从而预后相对较好。一般情况下,早、中期壶腹癌最佳治疗方式为根治性手术切除,通常采用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或Whipple手术)[2]。尽管根治性切除后壶腹癌相对于其他壶腹周围癌预后较好,但部分患者预后效果却要比预期的相差甚多。并且近几十年来,全球壶腹癌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从而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3-4]。炎性反应因子和免疫细胞在肿瘤的发生发展和患者的预后生存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大量研究报道证实,免疫反应影响肿瘤发展的所有阶段,包括起始、侵袭、促进、恶性转化和转移[5];免疫细胞浸润于肿瘤内并与癌细胞相互联系,控制肿瘤生长[6]。近年回顾性研究数据证实,生物标志物与壶腹癌的发生、发展以及预后具有一定的密切联系[7]。其中,淋巴细胞与单核细胞比率(lymphocyte to monocyte ratio,LMR)、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NLR)和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率(platelet to lymphocyte ratio,PLR)等已被广泛研究,并被用作壶腹癌预后的预测指标[8-9]。然而,由于这种疾病相对罕见并且研究数据有限,同时血源性生物标志物可能会受到阻塞性黄疸和胆管炎等共存疾病的影响,导致这些生物标志物对壶腹癌预后生存的预测作用仍然存在争议[10]。在此,本文就部分炎性反应参数对壶腹癌预后生存的预测价值进行概述。
1 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
血小板通过释放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激活多种信号通路进而刺激血管生成,最终导致肿瘤的生长和进展[11]。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platelet derived growth factor,PDGF)作为血小板α颗粒的组成部分,在正常细胞增殖的调节中起着关键作用,同时作为病理性细胞生长的介质,以自分泌或旁分泌的方式在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12]。除了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血小板还会生成其他多种类型生长因子,包括转化生长因子β和血小板衍生的内皮细胞生长因子等,它们对于肿瘤生长和进展同样具有促进作用[13]。目前炎性反应参数已成为多种恶性肿瘤的研究热点,其中PLR具有简单、易获得且可行性高等特点,因此被广泛用于探究多种肿瘤的预后评估和监测。中国一项关于71例胰十二指肠术后壶腹癌患者的研究中,PLR数据统计最佳截断值为226.83,其中高风险组(PLR>226.83)中位生存时间为24个月,低风险组(PLR≤226.83)中位生存时间为48个月,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Cox回归模型多因素分析证实,PLR(P<0.001,HR=3.001,95%CI: 2.264~3.978)为胰十二指肠术后壶腹癌的独立危险因素,根据χ2检验对PLR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PLR越高,胆红素(Tbil)数值相对越高,淋巴结转移比例越高(P<0.01),而与肿瘤的分化程度和分期无明显的相关性。进一步将胆红素与PLR进行危险分层,结果表明Tbil/PLR越高,分化程度越低,分期越晚(P<0.001),逐步验证分析后证明了PLR对壶腹癌预后评估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14]。与此同时,日本学者对该国当地医院的42例根治性切除术后壶腹癌患者进行了数据统计分析,曲线下面积(AUC)=0.744,证实了术前PLR对于根治性切除术后壶腹癌患者具有一定的预测性能[8]。该研究数据PLR最佳的截断值为211.7;在高风险组中(PLR>211.7),PLR越高,复发率越高(P=0.01),同时高风险组1、2年无病生存率(disease-free survival,DFS)分别为57.1%、28.6%;低风险组(PLR≤211.7)1、2年DFS分别为81.5%、70.2%。PLR>211.7的患者2年内复发风险明显高于PLR≤211.7患者(P=0.005)。将PLR与肿瘤标志物(tumor markers,TMs)进一步预后分层分析,第一组(低PLR、TMs)、第二组(高PLR或高TMs)和第三组(高PLR、TMs)1年DFS分别为92.3%、71.4%和42.9%,2年DFS分别为84.6%、52.4%、14.3%(P<0.003)。目前对于壶腹癌术前PLR最佳截断值的判定仍缺乏共识。
上述研究表明,PLR对于根治性手术切除的壶腹癌患者预后评估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但尚未得到共识,其主要原因是缺乏更多样本基线资料验证分析,数据研究范围较为局限,同时相关回顾性研究未纳入随机对照试验进行内、外部验证,缺乏一定的严谨性和说服力。未来还需进一步优化统计学应用方法、完善基线资料、扩大研究范围以及纳入随机对照试验组,支持和验证PLR对壶腹癌患者预后生存的预测。
2 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
以往研究表明,多种恶性肿瘤中高NLR与较差的生存率相关,但NLR与患者预后的确切关系仍不清楚[15]。其中一个假设认为:NLR升高的恶性肿瘤患者往往伴有相对的淋巴细胞减少症,因此恶性肿瘤表达出较弱的淋巴细胞介导免疫反应,从而增加肿瘤的复发率[16]。此外,循环中性粒细胞含有并分泌大量循环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在肿瘤发展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中性粒细胞计数升高为肿瘤生长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从而有助于肿瘤的发生和进展。另一种假说认为:当中性粒细胞激活后,其在调节T细胞活化的同时,抑制细胞毒性T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从而建立了免疫抑制环境,加快了肿瘤进展[17]。血液常规实验室检查即可获得NLR,其低成本、易获得、简单、可动态监测等特点近年来也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青睐。多项研究证实,NLR可作为多种消化道恶性肿瘤预后的预测指标,且具有切实、可行的预测能力[18]。同样,NLR也是壶腹癌患者预后评估及诊疗后监测的重要指标。日本东京慈惠会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纳入了37例根治性切除术后壶腹癌患者,以NLR=3作为最佳截断值,将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及NLR进行了DFS和OS的单因素、多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结果证实,影响DFS的独立危险因素为局部淋巴结侵犯、术前胆道引流,然而NLR并无统计学意义;NLR(P=0.026,95%CI:1.245~34.134)和局部淋巴结侵犯是影响OS的独立危险因素。同时根据NLR截断值分为两组:NLR≥3和NLR<3。结果可见NLR越高,肿瘤浸润(P=0.007)越深以及术前胆道引流(P=0.006)比例更多[19]。在此研究中,虽然数据显示NLR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但是多因素分析中NLR可信区间太大,导致NLR虽然具备一定的预测能力但预测精确性很低,从而缺乏一定的严谨性和可信性;另一方面,研究数据样本太少,后续还需进一步扩大样本纳入量进行验证。Demirci教授团队[20]针对NLR对根治性切除术后壶腹癌预后分析进行了更为全面的研究,结果表明NLR是影响DFS(P=0.041,95%CI: 1.027~3.696)和OS(P=0.001,95%CI: 1.747~8.360)的独立危险因素,NLR<3壶腹癌患者3、5、10年的DFS(P=0.041)和OS(P=0.001)明显低于NLR≥3的患者;NLR越高,患者预后复发时间和生存时间越短,预后越差,且根据数据结果可见预测准确性较为可信、样本量较以往相关回顾性研究多。
尽管多项研究证实,NLR越高,壶腹癌患者预后越差,但大多数研究缺乏内、外部验证,研究过程及统计学方法不够全面和严谨;其次,受到区域性的影响,数据样本具有局限性,现有文献尚未综合各地区基线数据进行随机对照分析。对此,未来需要大量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对照研究证据进一步支持和深入探究NLR对壶腹癌患者预后的预测性能及精确性。
3 那不勒斯预后评分
近年来,营养状况和免疫状态作为宿主相关因素,在预测各种癌症的术后疗效方面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控制营养状况(CONUT)评分[21]、预后营养指数(prognosis nutrition index,PNI)[18]和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lasgow prognostic score,GPS)[22]成为了恶性肿瘤的重要预后指标。其中Galizia等[23]提出了那不勒斯预后评分(Naples prognostic score,NPS)是一种基于血清白蛋白和总胆固醇浓度、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率(NLR)和淋巴细胞与单核细胞比率(LMR)综合得分计算出来的新评分系统,反映了患者的全身炎性反应情况和营养状况。已有研究证实,NPS评分在食管癌、结直肠癌、胃癌、胰腺癌等消化道恶性肿瘤的预后评估中具有较为精确的预测性能[24-27]。然而,目前对于接受胰十二指肠切除术(pancreato duodenectomy,PD)的壶腹癌患者,NPS与短期和长期预后之间的相关性尚不清楚。最近,国内有研究纳入404例符合标准的壶腹癌患者,结果表明全身炎性反应评分(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core,SIS)、CONUT、PNI、营养风险指数(nutritional risk index,NRI)和NPS中,仅NPS为影响PD术后壶腹癌患者OS(P<0.001,HR=3.067,95%CI: 2.203~4.274)和无复发生存时间(RFS)(P<0.001,HR=2.732,95%CI: 1.972~3.774)的独立危险因素。NPS越高,胆红素、CA19-9、CA125浓度越高,术前胆道引流比例越高,预后越差。同时NPS与术后并发症密切相关(P=0.038)。NPS越高,胰瘘发生率(P=0.004)、腹腔脓肿发生率(P=0.024)和肺部感染发生率(P=0.002)越高,术后住院天数(P<0.001)越长。根据各预后评分系统生成的时间依赖性ROC曲线,NPS评分的预测能力持续优于其他评分系统,并且其5年后的预测性能几乎等于TNM分期;同时研究表明高NPS与根治性切除术后壶腹癌患者预后呈负相关[28]。
目前在壶腹癌方面的相关NPS评分研究相对较少,且大部分为回顾性、单中心、观察性研究,受试者选择偏倚不可避免,未来需进一步挖掘和研究。
4 γ-谷氨酰转肽酶为基础的炎性反应参数
血清中γ-谷氨酰转移酶(γ-Gamma glutamyltransferase,GGT)是一种广泛分布于腺体和导管上皮细胞表面的膜蛋白酶,主要由肝脏分泌产生[29]。据研究表明,GGT对多种消化道恶性肿瘤预后生存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由于在多种其他疾病和条件下(如肾功能不全、糖尿病、胰腺炎、心肌梗死、肥胖和酒精摄入)血清GGT水平均会升高,因此其缺乏一定的特异性[30]。对于GGT与癌症之间的关系,有学者假设了一种潜在的机制[31]:其作为谷胱甘肽(glutathione,GSH)代谢的关键酶是细胞的主要抗氧化剂,主要催化降解细胞外的GSH,在中和活性氧化合物和自由基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并且GGT为细胞防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GGT和GSH被用来抵抗氧化应激。肿瘤细胞中GGT水平升高可产生活性氧化物质(ROS),促进肿瘤进展。目前以GGT为基础的炎性反应参数在肝胆系统恶性肿瘤的研究较为广泛。近期一项研究证实,GGT与血清白蛋白的比值(glutamate-transpeptidase to albumin ratio,GAR)是影响肝切除术后肝内胆管癌OS(P<0.001,HR=1.655,95%CI: 1.286~2.129)和DFS(P<0.001,HR=1.524,95%CI: 1.219~1.906)的独立危险因素[32],同时GAR越高,肿瘤体积相对越大(P=0.002)、数量相对越多(P=0.032)、淋巴结转移(P<0.001)、神经受侵(P=0.021)比例越高。另外,多种炎性反应参数,如血清白蛋白与GGT比值(AGR)、GGT与氨酸转氨酶比值以及GGT与淋巴细胞比值(GLR)等,对肝胆系统恶性肿瘤的预后生存均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以往的回顾性研究[33-36]已进行过分析和验证。最近,有学者提出将CA19-9与GGT进行比值来优化胆系恶性肿瘤预后评估的精确度[7]。CA19-9作为胆系恶性肿瘤诊断的首选肿瘤标志物,是评估患者复发及远期预后的重要指标,但极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导致血清CA19-9水平异常升高[37]。同时,GGT是反映胆道梗阻及肝损伤最敏感的一种肝酶[29]。鉴于此,通过CA19-9/GGT不仅能通过GGT对血清中CA19-9浓度进行校正,提升评估根治性切除胆系癌症患者术后远期生存的能力,而且是一种新的、易获得的、更加具有潜力的预后指标。
令人遗憾的是,目前以GGT为基础炎性反应参数在壶腹癌预后生存评估方面的研究尚未发现,其在肝胆系统恶性肿瘤预后生存分析方面的作用为壶腹癌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性和研究方向。未来可针对CA19-9/GGT,以及以GGT为基础的炎性反应参数进行深入挖掘,纳入大量基线数据进行分析和考证。
5 全身免疫炎性反应指数
炎性反应与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以及预后密切相关,一方面,大多数恶性肿瘤通过诱导转录程序募集白细胞、表达促癌趋化因子和细胞因子以及诱导血管生成,从而触发内在炎性反应。其中最常见的免疫细胞是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umor associated macrophage,TAM)和T细胞,两者对肿瘤生长、侵袭和转移以及血管生成起到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肿瘤微环境有助于促炎介质和信号通路中信号分子的增加,从而刺激血管生成同时促进肿瘤活跃程度[5]。
近年来,全身免疫炎性反应指数(SII)被用作癌症患者预后评估的重要生物标志物,并已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预后参数[38]。SII作为一种基于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和血小板计数的新型炎性反应生物标志物,特点是术前易于获得、经济快捷和可持续动态监测。中性粒细胞可以通过促进CD8+T细胞活化来帮助肿瘤淋巴结转移;此外,中性粒细胞可通过分泌内皮生长因子促进局部环境血管的形成和肿瘤的远处转移[39]。肿瘤细胞激活血小板,形成适应的微环境,从而保护肿瘤细胞免受宿主免疫系统的影响[40]。相反,淋巴细胞参与免疫监测以抑制癌症进展,高淋巴细胞计数可能会导致癌症患者产生强烈的免疫反应。因此,SII被定义为中性粒细胞×血小板/淋巴细胞,用于反映癌症相关炎性反应状态和宿主免疫[41]。研究表明,与其他炎性反应指标相比,SII在预测消化道恶性肿瘤患者生存率方面是更为客观、可靠的预后指标[42]。高SII与较低的OS密切相关(HR=1.86,95%CI: 1.57~2.21,P<0.001),且SII评分系统高于截断值的壶腹癌患者表现出较差的DFS(P<0.001)。近些年多项研究证实了围手术期SII在预测肝癌、肝内胆管癌以及肝外胆管癌的预后疗效方面均有所建树[43-45]。在肝胆系统恶性肿瘤患者中,高SII与分期较晚和预后生存较差有关,但对辅助治疗受益相对较大。并且与PLR、NLR等炎性反应标志物相比,SII可能是更好的预后评价指标。此外,SII对肝癌免疫、靶向治疗效果评估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然而,SII在壶腹癌预后疗效方面的预测价值鲜有报道,未来还需对SII在壶腹癌预后评估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6 结语
总之,尽管许多炎性反应指标预测壶腹癌预后价值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进展,但是部分炎性反应参数尚未在壶腹癌患者中得以研究和验证,例如CA19-9/GGT、AGR、GAR和SII等。同时,由于壶腹癌的罕见性导致研究数据有限,从而缺乏大量的研究证据对炎性反应指标给予一定的考量和深入探究。另外,炎性反应指标易受混杂因素的干扰,例如慢性炎性反应、药物作用、免疫性疾病等,导致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误差性以及炎性反应指标的最佳截断值也稍有差别。多种因素的干扰、样本量少是目前学者们在壶腹癌预后分析研究中尽可能去解决的问题。尽管样本量有限,但基于近几年对消化道恶性肿瘤相关炎性反应指标的研究结果,未来应当尝试各种炎性反应指标对壶腹癌的预后价值评估;同时需要尽可能提供样本量较大的、多中心的临床研究提高预后评估的精确度,从而降低纳入研究的偏倚,为临床研究提供更科学严谨、可信准确的循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