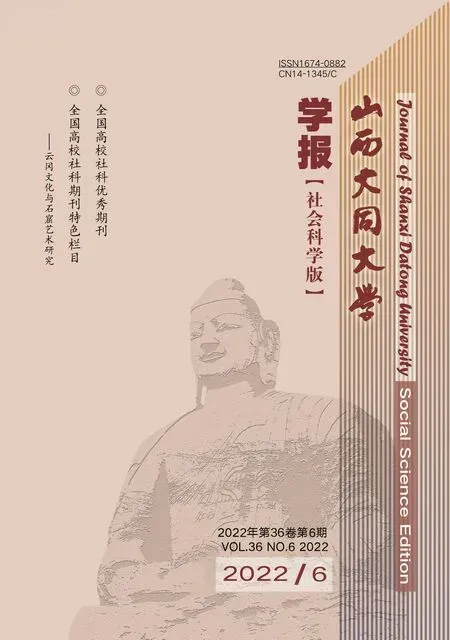从“接受”的缺席看《百鸟朝凤》中民俗的自然消亡
沈松钦,刘可文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作为首个摘获鲁迅文学奖的贵州作家,肖江虹的作品聚焦贵州山地的独特风俗,他将贵州特殊的风俗世界深情地融入到作品。从《百鸟朝凤》和《家谱》,到《喊魂》和《当大事》,再到“民俗三部曲”,民俗书写逐渐成为肖江虹文学创作的风向标。肖江虹凭借《百鸟朝凤》走进文坛,2009 年《百鸟朝凤》改编为同名电影后让贵州这位青年作家在文坛出名,因此,大量的文学评论围绕肖江虹《百鸟朝凤》中的民俗研究、电影改编以及叙事张力等方面展开。关于《百鸟朝凤》中民俗消亡的原因,学界也都一致从宏观上归因于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的冲击,认为这是传统和现实相抗争的结果。但是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说,《百鸟朝凤》想要阐明的是:传统技艺的消亡是“接受”缺席的结果。在考量民俗传承问题的时候,首要思考的是传承的必要性,现在是否还有人愿意听唢呐、还有人愿意传承民俗,如果没有,那么传统技艺的消亡便是新时代的生活常态。
一、《百鸟朝凤》中“接受”的缺席
小说《百鸟朝凤》聚焦贵州省修文县农村一支民间唢呐乐班的发展际遇,以前半段的“传”与后半段的“承”共同见证唢呐逐渐消亡的过程。主人公游天鸣从11 岁开始学习唢呐到28 岁唢呐班彻底解散,17年的时间,由于“接受”的逐渐缺席,唢呐这一传统民间技艺从中心走向了边缘,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因此,唢呐作为一门表演艺术,在社会语境中缺少接受者的期待和接受语境,其消亡就成为必然。
(一)接受语境的缺席 从人类学的视角看,表演理论强调对表演语境的关注,美国民俗学家鲍曼认为口头表演是一种交流模式,它强调观众的参与性,并重视特定文化背景下交流的情景化语境。唢呐作为一种口头表演艺术,在相关的语境中发生,并传达着与该语境相关的意义。唢呐的表演语境主要由外在的自然环境和人物的内心世界组成。
在《百鸟朝凤》中,唢呐是肖江虹安排的一个象征符号,这个象征符号作为叙事主体存在,社会环境主要为它服务。肖江虹将自然景物的盛衰与唢呐的兴亡相勾连,达到景与人事的完美融合。在唢呐班“传声”那天,无双镇的自然环境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传声”那天之前,“柔软的河湾”“坚实的山丘”“袅袅的炊烟”共同勾勒着无双镇的诗意与美好。但是,随着唢呐逐渐淡出乡村的舞台,“天边的冷月”“冬天的寒风”等意象频繁地出现在文本中,给游天鸣带来了沉重的心理焦虑,成为作者抒发悲情的载体。“猝然而至的交接像一场成人礼,从那天起,我眼里的水庄褪去了一贯的温润,一草一木都冰冷了,那些整日滑上滑下的石头也变得尖锐而锋利。”[1](P37)外在环境的变化牵扯着游天鸣内心的变化,游天鸣的心里开始为唢呐的未来担忧,无双镇的人们也开始将目光从唢呐身上转移,游天鸣内心对于唢呐的“期待失落”逐渐浮出水面。
游家班成立后共出了三次活,从这三次出活的“接受”来看,受众的“期待失落”越来越明显。“小说的沉重与其说来自人物的命运,不如说来自正在被消解的乡村历史传统与文化,包括它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2]肖江虹将唢呐艺术的逐渐消亡看作是一场“雨的预谋”,游家班的第一次出演的时候,天气是“乌云密布的,太阳带晕”,第二次出演天气是“干旱,月亮带晕”;第三次的天气则是“一场连绵不绝的细雨了”。[1](P46)从乌云到细雨,从太阳到月亮,无双镇的唢呐和天气一样慢慢地走向了沉重和衰亡。民俗表演的情境语境通常和物质的场景因素相连接,物质对无双镇的入侵加快了唢呐接受语境的变化。游天鸣与师兄弟们接的第一单活是毛长生家,毛长生是水庄第一个穿牛仔裤和夹克的人。在葬礼上,水庄的毛长生出手非常阔绰,不仅大鱼大肉地招待乐师们,结束的时候还给他们塞了很多钱。“众声喧哗”的现代化生活方式消解着人们的理性精神,当游天鸣和唢呐班子第二次接活时,游天鸣的内心愈加惶恐。硕大的院子,没有人将目光聚焦唢呐,一支西洋乐队将无双镇村民的魂全部勾走了。第三次出活的时候,游天鸣眼前一黑,倏然将“百鸟朝凤”这首曲子忘了,焦三爷用沉重的膝盖折断了那把专吹“百鸟朝凤”的唢呐,也就是从那一刻起,唢呐艺术的接受语境永远地消逝了。从担忧到惶恐、再到眼前一黑,游天鸣心理上的变化折射了唢呐的最终命运。作者肖江虹用唢呐连缀的是整个传统社会和价值世界,这个世界的结构在现代社会的冲击之下悄然发生了变化,西洋乐器的音符“搅乱了某种既定的秩序,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些莫名的东西在暗暗涌动着,像夜晚厨房木盆里那团搅和完毕的面团,正悄悄地发生着一些不为人知的变化。”[1](P48)无双镇的村民以前对唢呐有多期待和热爱,现在就有多么疏离和陌生,正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所说:“真正毁掉我们的,恰恰是我们无比热爱的东西。”[3]
(二)观众审美的缺席 唢呐作为一门表演艺术,“它召唤观众将自己的经验融入作品中来,在交互对话中生成审美的意境,达成作品意义的塑造。”[5]唢呐表演既是一种交流方式,也是一个展示的过程,参与到唢呐演奏过程的受众也是创作中的一环。因此,表演的基本要素,即参与者、表演者和观众缺一不可。缺失了观众的参与,唢呐这门传统技艺自然就会走向消亡。
唢呐艺术作为中华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一定群体成员生活中,最基础的,也是极重要的一种文化。因为世上没有比民俗文化,更为广泛地紧贴群众生活、渗透群众生活的文化现象了。”[4](P218)在这个群体社会中,人们拥有的交流资源不同,受到的知识熏陶和现代化冲击的程度也不一样,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得不到统一和实现,观众就会逐渐逃离这个有一定距离感的民俗表演。表演的框架要求表演者和观众有共同的说话方式、知识和才能,否则,表演就成为无本之源。在《百鸟朝凤》中,接受者年龄的断层给西洋乐器和传统唢呐之间的对照提供了事实性依据。在游家班第二次出活的时候,西洋的吉他和流行歌曲引起了木庄年轻人情感上的共鸣,当乐队“唱到自己熟悉的曲子时还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哼。”[1](P50)而上了年纪的老人则将愤怒挂在了脸上,为灵堂里的逝者抱不平。对于那个阿婆来说,在逝者的葬礼上呈现出这番热闹非凡的场景是不合时宜的,这是对逝者的不尊。但是对于接受了新时代潮流的年轻人来说,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因此,当社会上大部分人的审美发生变化,并且在同一个社区中人的交流资源和审美认知产生差异的时候,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就不会均衡地发展。这样看来,由于交流资源的差异,表演者和观众的审美观念和共情节点不同,那些触碰不到心灵和抵达不了内心的声音,人们就不愿与之共情,这时候,“接受”的缺席就成为必然。
关注表演艺术中接受主体的变化,我们可能会找到人类社会何以达成的原因。将《百鸟朝凤》中“接受”的缺席进行横向研究,我们能从中窥见到无双镇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游家班第一次出活是四台唢呐,正式出演的前一天晚上还有预演,寨邻将游天鸣家的院子塞得满满的,乡亲们都在关心和谈论着这次盛大的仪式;第二次出活的时候,游家班出活的是八台唢呐,但是这远盛于四台的表演不仅没有预演,连观众的视听都从唢呐身上移开了。“从我们进马家大院起,好像就没有人关注过这几支呜呜啦啦的唢呐。”[1](P43)尽管大师兄将两个眼珠子都要吹出来了,院子里也没有人将目光转向这支凋零的队伍。但是唢呐作为一种交流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表演者要对观众承担展示自己交流技巧的责任。”[5]所以游天鸣和师兄们继续瞪大了眼睛吹,向空荡的肚子里灌了一大瓶烧酒,将腮帮子高鼓,游家班的乐师们试图用这样的方式使交流的相关技巧和效果得到观众的品评。但是他们没想到,卖力的呜呜啦啦换来的只是满眼的鄙夷和不屑,就连游天鸣也没想到,这次的冲击会来得如此迅猛和强烈。
二、“接受缺席”后民俗的自然消亡
(一)传统文化变成一纸遗产 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历史的见证,是国家文化的深厚积淀。唢呐作为一种波斯乐器,在唐代通过西域传入中原。在元代,唢呐在官方的推动下流布于中国全境,随着“王化进程”和全国各地的移民流入贵州,并在各族群间流传开来,在各种婚丧嫁娶仪式上被吹奏。《百鸟朝凤》中的唢呐是丧葬场合的专属,吹唢呐这种传之久远的民间艺术,已超越了娱乐化的作用,其深刻意义是它在葬礼上对远行故者的一种人生评价——道德平庸者只吹两台,中等的吹四台,上等者吹八台,只有德高望重者才有资格吹“百鸟朝凤”。
《百鸟朝凤》曲谱扉页上的几句话生动地显示了这首曲子承受者的品行和权威,“《百鸟朝凤》,上组诸般授技之最,只传次代掌事,乃大哀之乐,非德高者弗能受也。”[1](P60)综观整篇文章,游家班一共出了三次活,其间有逝者的孝子请唢呐班吹“百鸟朝凤”,但是都被拒绝了,只有火庄的窦老支书才是有资格承受这首曲子的人。火庄相对水庄和土庄来说,“火庄一直落在后面,房屋还多是拉拉杂杂的茅草屋,道路也没有其他几个庄子来的宽敞。”[1](P59)火庄的村民卖的鸡蛋货真价实,价格和质量都符合市场价值,成为整个无双镇信赖的对象。诚恳淳朴的火庄孕育出了德高望重的老支书,窦老支书“去过朝鲜,剿过匪,带领火庄人修路被石头压断过四根肋骨。”[1](P59)在窦老支书的葬礼上,寨邻们挤满了窦老支书家的院子,满怀期待地等着“百鸟朝凤”的响起。可是,这门传统的表演艺术却被无双镇唯一的传承者忘却了,游天鸣的忘却让无双镇这个古老的传统以一种非常丑陋的形式完结了。连绵不绝的群山被突如其来的沉默撕得粉碎,村长带着省里面派下来挖掘和收集民俗文化的工作人员,想听一场完整的唢呐表演,但是二师兄的中指断了吹不了唢呐,唢呐在四师兄的手中也只闷哼了一声就结束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实践和意识节日等,作为口头表演艺术的唢呐,最终由活生生的表演艺术变成了冷冰冰的一纸遗产。
(二)口头表演走向僵化文本 表演在本质上可被视为和界定为一种交流方式,它要求通过表演自身来研究口头艺术。相较于通过文本来探究口头交流本质来说,人们在特定的语境中,依赖一定的表演进行交流更有意义。《百鸟朝凤》中的唢呐在文中既是指民族音乐这一实体,也是对民族精神和文化价值的虚指。这个众望所归、最出名、最受人尊敬的“百鸟朝凤”,最后却变成了唢呐班子的葬歌,从活生生的口头表演艺术变成了失语的固化文本。演奏“百鸟朝凤”需要表演者、参与者和观众的有效互动,“百鸟朝凤”的传承者,也就是吹奏这首曲子的人因为次代传承而显得非常稀罕,能够吹上“百鸟朝凤”则被视为祖上的一种荣耀。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百鸟朝凤”这首曲子的表演者与接受这首曲子的逝者具有同等的地位。“百鸟朝凤”的权威性和罕见性让它在无双镇村民的心中镀上了一层珍稀的光环,寨邻观众的倾听以及对此次吹奏的品评共同构成了“百鸟朝凤”这一完整的表演结构。游天鸣第一次和师傅去金庄出活的时候:“一直在院子里劳作的人群过来了,没有人说话,目光全在师傅的一支唢呐上。渐渐有了哭声,哭声是几个孝子发出来的。没多久,哭声变得宏大了,悲伤像传染似的,在一个院子里弥漫开来,那些和死者有关的、无关的人,都被师傅的一支唢呐吹得泪流满面。”[1](P24)现在“百鸟朝凤”的“接受”的缺失,这一完整的表演秩序被打破,于是,唢呐这一表演艺术从此就成为一堆文字组成的一串概念。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当表演由口头变为文本存在以后,“文本自身成了分析的基本单位和讨论的出发点。”[5](P7)后世唢呐的研究者通过被抽象化了的文本来探究以口头交流为主要属性的唢呐表演,在文学人类学家看来,这无疑是一种退步,这并非是唢呐表演的直接产物,而是另外一种交流模式的呈现。
三、“缺席的在场”:游本盛的坚守和付出
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孕育出了多种多样的文化个性,在每一种文化的背后,都有一段可歌可泣的历程,或是多年沉淀的文化底蕴。就唢呐而言,它已经在华夏大地传承了数百年,成为那个时代人们劳作与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社会潮流的发展必然会给这些传统技艺带来一定的冲击,因为接受这些新事物的主体,他们也出生在新时代,在心理和情感上更能够与新兴的事物产生共鸣。正如新事物、新思想终究会取代陈旧的习俗,成为下一个时代的引领一般。诚然这个时期会有一批坚守的艺人,他们为了不负前人的嘱托,历经苦难,苦苦坚守传统文化的传承精神并诚恳地付诸行动,《百鸟朝凤》中的游本盛就是作者要着力表现的这样一个人。他的人生故事是暗藏在小说中的一条或明或隐的线,虽说作者对这个人物的着墨不多,看似可有可无,实则关键,成为小说“缺席的在场”者。
(一)在代际叙事中传承唢呐艺术 肖江虹说:“我真正要写的,既不是德高望重的焦师傅,也不是一力传承的游天鸣,而是一辈子没吹上唢呐的父亲游本盛。”[6]显然,《百鸟朝凤》最突出的人物是父亲游本盛,游本盛是中国式父母的生动缩影,他的身上有着农民的局限性,虽然小时候没有当上唢呐匠,但他将自己未实现的梦想寄托在儿子游天鸣的身上,于是代际叙事在《百鸟朝凤》中展开,贯穿了整个故事的发展脉络,小说的前半部分是“传”,后半部分则是“承”,这两个阶段都有游本盛对儿子的期待和希望,他希望儿子将“百鸟朝凤”传承下去,将无双镇真正的唢呐班子传承下去。小说紧扣个人体验和家族情感,将家族的代际传承在游本盛父子身上呈现出来,给予读者一定的温情。
在《百鸟朝凤》中,游天鸣小学时经常逃课导致成绩不佳,当老师向游天鸣的父亲反映情况后,他的父亲竟然对此满不在乎,因为他要让儿子成为乡村的唢呐匠,这才是他对游天鸣的期望和打算。游本盛是小说中对唢呐抱有最高热情的人,但他却是一生都与唢呐无缘的人。游本盛自己没有当上唢呐匠,一心要送儿子去学唢呐,他将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寄托在了儿子身上。从送儿子游天鸣去学习唢呐,到焦师傅“传声”游家班成立,再到游家班彻底散伙,这个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农民都未缺席,甚至希望在自己的葬礼上能够听到四台的唢呐,“对于水庄的游本盛来说,没有唢呐的葬礼是不可想象的。”[1](P66)在唢呐面临着绝境之时,游本盛感到十分怨怒,于是他将这种怨怒转化为对儿子的责备。在游家班散了之后,游本盛的心中还没有真正放弃对唢呐的敬意,所以游本盛把自己治病的钱给了游天鸣,希望游天鸣能够再次将唢呐班组合在一起,将唢呐这门技艺传承下去,但是他最后的希望在师傅和师兄们的现代化心境中成为了泡影。小说的后半部分,游天鸣的父亲就像深秋的落叶逐渐腐烂。水庄的冬天不像往常一样下雪,反而下起了冰。稻谷返青后遭遇干旱,庄稼都烂在了地里。故事的结尾,游本盛也没了却一生的心愿,他的葬礼没有四台的唢呐,只有呼啸的风在送终。这个从泥地里钻出来的农民,生前还没来得及听儿子吹“百鸟朝凤”就又钻进了泥土。
(二)在代际传承中坚守匠心精神 游本盛是作者在小说中着力塑造的一个人物。首先,游本盛是“百鸟朝凤”唯一的受者和听众,是他死后游天鸣在他的坟头为他吹的;其次,游家班解散之后在火庄和水庄成立的唢呐班子在游本盛看来都是不正宗的,他只认水庄游家班的唢呐。小说最后部分,民俗文化的工作人员来到游天鸣家做调查时也坦然“我们听过了,他们那个严格说起来还不能算纯正的唢呐。”[1](P70)由此看来,这位扎根在水庄一辈子的男人,有着对唢呐深厚的热爱和了解。焦三爷在游天鸣忘记“百鸟朝凤”后就放弃了挣扎,到城市后在师兄的厂当了保安,在“接受”的缺席之下,焦师傅的放弃是当代社会生活的常态。但是游本盛的这份坚守却是至死不渝的,他毕生都在维护和坚守着唢呐这门传统技艺,这是一种匠心,一种精神。正如作者肖江虹所说的,在匠心和匠气面前,不论是文学创作还是传统技艺表演,需要的都是一颗匠心。《百鸟朝凤》中唢呐艺术的挽歌,也是一曲唱给坚守艺术文化和理想人的热烈赞歌,是唱给游本盛最真切的赞歌。
在乡村文明与都市文化碰撞的过程中,家族宗法制和等级伦理观念下产生的“权力意志并没有妥协和再造”。[7]肖江虹曾在“2018 绍兴文学周第五届青年作家、批评家主题峰会”上表达自己对民俗的看法:“那天我在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上发言讲了一个老唢呐匠,我觉得他完全是哲学家出来的,我问他,你唢呐也不吹了,有一天你的唢呐肯定不在了,你死了这些东西就消失了,怎么处理?然后他说,唢呐可以没有,但是曲子是死不掉的,这个调子是在的。”[8]外在的凋敝始终动摇不了人心和人性中兼顾的东西,善意和伦理依然存在。小说是以一位乞丐吹奏《百鸟朝凤》结束,“百鸟朝凤”的结局是悲凉的,但也能从中窥见出几丝希望,底层的人民也在坚守唢呐这门传统技艺。民俗的核心是人类的精神世界,而肖江虹正是用关怀人类精神的情怀对传统民俗进行再造,让其小说中的民俗传递出与人类精神的共通之处。当前这个信息超速发展的时代,丰富的社会生活给予文学创作很大的自由度,但在书写生命的过程中,艺术创作都应该是有温度的,艺术创作的温度应该体现在对于社会的宽容以及对这个世界、对艺术的敬畏之心。在敬畏心、敬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消失之前,新的事物就诞生了,这种精神的东西会附着到下一个即将诞生或已经诞生的载体上,这是人类历史滚滚向前的发展实质。传统文化因其超强的生命力,即使形式不断消逝,但精神层面的气质会附着延续到其他事物上,一直留存下去。小说里唢呐消失了,但它的内核——传统文化精神层面的东西一直都在,并且在未来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最后都会依附于人与人的关系中,将传统文化代代相传。
结语
肖江虹通过《百鸟朝凤》表达了对传统民俗艺术现状与前景的思考,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唢呐作为一门表演艺术,在“接受语境”和“接受主体”缺席后,唢呐的消亡属于生活的自然常态。观众和读者都是新时代的“产物”,新兴的东西更能引起“接受”的共鸣。消亡后的传统技艺变成了一纸遗产,由生动的口头表演艺术变成了僵化的文本,失去了其表演的生机与活力。在肖江虹看来,唢呐这一民间传统技艺虽然消亡了,但是精神层面的传统是很难被消灭的,它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成为“缺席的在场”,一直留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