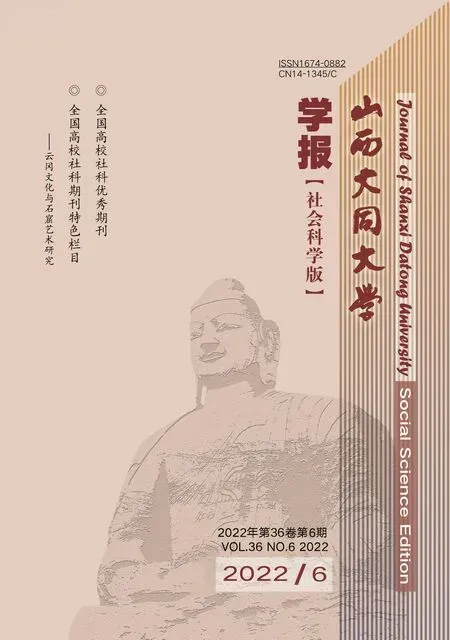论铁凝小说的民俗书写
贾博然,薛文礼
(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山西大同 037009)
民俗可以被描述为一种长期生活在历史语境下的文化事项,而创造并沿袭这一文化传统的社会群体在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回放、演习这种流行风尚,并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赋予民俗以文化权利。民俗因此成为追溯历史语境的重要符号,尽可能地展现、复刻存在时期的社会风貌。而作家群体拥有将客观真实转化为内在真实、将生活与艺术无限叠加的能力,他们发挥艺术手法,在不同时空的视野下演绎民俗的发生与进行。在这种可以预见的行为路径中,民俗成为铁凝不断书写的文化素材与灵感来源,民俗的意义与范畴在真实与虚幻的交接下得到充分扩展。
一、铁凝小说的民俗建构形式
(一)民俗文本的呈现 20 世纪60 年代末70 年代初,民俗学界产生并兴起了“表演理论”的学派与方法。民俗在其中存在一个文本化的过程,进而动态表演民俗,“将民俗事象形塑为文本的大部分编创过程可能在表演中重述它之前很久就发生了。……是一次话语的实现,一个将一段口头表达展演——包括再生产——为文本的实际过程。”[1]与表演理论不谋而合的是,文学作品中同样存在民俗的文本化问题。无论是文学的民俗化,还是民俗的文学化,作者与读者实际上是共同参与到民俗表演中去,民俗表演也藉由作者之手传递到读者——即接受者的手中。
铁凝的文学创作也基于此。每一次落笔都会创造一个不尽相同又暗藏逻辑关联的文学世界。文学世界一头连接着现实,另一头连接着虚幻,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小说将真实与虚假糅合在同一场域,围绕共同的主题及文化心理在人物行为的特殊化上进行习惯性界定,期间诞生了文化与个体的双向互动。可以说,挖掘文本中描述或隐含的民俗文化及民俗事象,是理解作者潜意识透露或主观传达的族群观念(也被称为集体意识)的认知实践,也是读者建立深层文化情境的有效方式。民俗表演的文本化,使我们可以基于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来围观民俗意义重现的可能。
在铁凝的多部小说作品中都能觅得民俗的踪影,其中包括以《麦秸垛》《棉花垛》《青草垛》《笨花》等为代表的乡土性质文学,和以《玫瑰门》《大浴女》等为代表的城市题材小说。而她更早时期的创作文本和涵盖众多主题的短篇小说中也不乏民俗文化的隐现。在大多数情况下,民俗常常被铁凝使用在小说中人物的生活里,因为民俗的参与使文本不至于脱离现实而产生文化真空的窘境,小说的背景环境也因此变得更加生机盎然。
民俗会作为文化载体和价值符号存在于作品当中,但有时出现的大段民俗情节只是为了填补叙述空白或增添故事趣味,而非真正传达背后的文化观点。如《笨花》里描写掌管下雹子的雷公、雷公娘娘及他们在人间的助手活犄角,“民间有雷公驱车下雹子的图画:雷公长着一张“雷公嘴”,像秃鹰,直眉立目的;雷公娘娘和地上的女人没什么区别,梳着高头,穿戴也飘逸,举镲打闪时扭着腰身。活犄角则是一副村夫野叟的打扮,裸着胳膊,高挽着裤腿。有的人家把这画贴在家里当故事看。”[2](P144)从叙事功能的角度来看,这部分有关民间传说和民间信仰的书写实际上在文本中并没有发挥太重要的作用,雷公、活犄角等角色是为奔儿楼娘的不幸际遇做了铺垫。而铁凝不仅在小说中加入这部分刻画,更是进行了长达数百字的描写介绍。这既是铁凝对民俗文化的主观张扬,也是民俗话语的一次实现,充分演绎了传统社会中民俗之美和文化之魅。
(二)民俗情景的再现 作家对民俗的态度不同于民俗学家,他们未必要仔细钻研某一民俗现象或民俗观念的形成原因、流传模式,甚至对民俗的书写往往表现出一种无意识的状态。无论作家是否主动触碰民俗边界,文学都与民俗产生了难解难分的密切联系。现实生活是创作的根基,铁凝汲取充分的生活养料来构建独属于她的文学秘境,民俗化的时空场景始终贯穿小说内里,民俗化为内在的精神特质存在其中。作品中涉及到了社会关系、生产生活、语言艺术、仪式信仰、心理观念等众多民俗文化类别,展现出别具一格的民间色彩。铁凝在描述民俗场景时兼顾真实叙述与审美取舍相统一,将民俗描写包裹在层层深入的人性探寻与精神追求当中,以达到契合共生的理想状态。她的小说创作从某种意义上再现了当时社会的历史风貌,同时也赋予了民俗文化新的时代意义。
民俗在学界一般被分为四大类型,分别是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和语言民俗。农民们田间劳作的场景、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美食、居住院落的建筑特征,这些与人民日常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活动都属于物质民俗。铁凝的物质民俗书写主要体现在生活场景中的衣、食、住、行等活动。以《玫瑰门》为例,出现了焦圈、蜜麻花、炸酱面、萨其玛、火烧等许多烙有地方印记的风味吃食,老北京的气息扑面而来,将人们拉入当时北京的社会生活场景中去。
社会民俗书写更多体现在人生仪礼和岁时节日上,《笨花》中向文成成亲、奔儿楼娘去世、取灯去世等婚姻丧葬仪式描写详尽,村子的人情往来、观念习俗也交代得十分清楚,繁杂的仪式中暗含着当地人们的传统文化心理。铁凝借约定俗成的仪礼风俗区别小说人物的性格观念,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环境,深入探讨当时的社会观念与人性纠葛。
精神民俗包含民间艺术、民俗信仰及民间哲学伦理观念等内容,是民俗心理经验在人们精神活动中的具现化表达。《木樨地》中多次提及到大秧歌——一种民间戏曲,包括里面的坤角大绿菊化装、上台表演等情景。大秧歌是民间艺术的地方形态,具有当地浓厚的文化特色和审美趣味。《笨花》中讲解了兆州四月庙会的由来,盖因企求火神不要降灾当地,隐含着劳动人民的朴实愿望。这些无一不反映了民间审美意识和地域文化对民风民俗的影响。
语言民俗在铁凝的作品表达中最为细琐,也最为平常。人们日常对话、交流离不开语言的帮助,而民间语言最能反映人们思想感情、生活习惯。受地域文化及生活环境影响,铁凝的作品中多出现冀中及北京一带方言,如闺女、老冒、张八儿等称谓语,还有一众活泼有趣的俗语、歇后语,如不到火候不揭锅、老鼠咬茶壶——满嘴的瓷(词)儿等。这些通俗易懂且带有丰富感情色彩的民间语言为小说叙述增色不少。
二、铁凝小说的民俗心理成因
(一)文化心理的语境生成 民俗书写的缘由、民俗事象的发生、民俗文化的表征,都与作者的文化心理息息相关,而作家的民俗文化心理又为文学作品民俗化呈现提供必要的支持与期待。“民俗在反映人生的文艺作品中,它不是镶嵌于人生的简单饰物,而是沉淀于人物内在的心理结构,又显现于人物外在行为方式的永恒伴侣。”[3](P82)可以说,文本的民俗记号既体现了作者的文化心理展演,又给予了作品人物以行为规范和思想依托。在脱胎于社会群体意识的共同文化心理作用下,个人经历为同一文化语境背景下的民俗书写提供了同中之异的可能。
以铁凝所处的文化语境来论,地域文化、社会规范、文学风向等因素共同塑造了她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细腻的文化心理。铁凝亲切地称冀中平原为“青纱帐”,[4](P26)这片地界包容了她人生起起伏伏的体验与情感,让她沉下心去体会生活的本真。一部作品是否真实,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看作家是否真正深入了解文化模式和参与所描述的生活。铁凝清楚这个道理,并深以为然,高中毕业后毅然放弃留在城市的机会,凭借一腔热血和对文学的极度喜爱及自信,离开家人下乡去做知识青年。冀中独有的地域文化赋予铁凝扎实的泥土芳香,使铁凝在乡下生活中不自觉地接纳当地地域文化的给予和馈赠。如果没有下乡锻炼的经历,铁凝断不能写出如此真实动人的乡土小说。
个体生活的历史中,首要的就是对他所属的那个社群传统上手把手传下来的那些模式和准则的适应。[5](P2)在农村,粮食是活着的根本,土地是农民的根基。这种观念潜移默化影响了铁凝的小说创作,她的多部作品都是以庄稼、植物命名的,有“三垛”系列、《那不是眉豆花》、《笨花》等。《麦秸垛》里写搂麦子这段,“脱粒机吐出了新麦秸,杨青就拿筢子搂。新麦秸归了堆,有人用四股杈垛新垛。新垛越垛越高,两个半大小子不住在垛上跳腾,身子陷下去又冒上来,冒上来又陷下去,垛心眼看实着起来。”[6](P159)铁凝将北方农村生产生活的日常行为生动地展示在读者眼前,民俗氛围也在这一字一句地文化背景中得以充分流露。
中国传统文化传承数千年,无论是观念思想,还是寄托人民希望与祝福的民俗仪式,都在历史滚滚车轮的裹挟下流传至今。铁凝同其他人一样,也写文化、写现实,与别人不同的是,她并未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文化现象,大肆批判一些长期浸染在落后文化中的人的思想行为。对铁凝而言,接受这种文化遗传的不完美,并如实展露在作品当中,才是她应该做的。《笨花》钻窝棚的风俗、《小黄米的故事》黄米姑娘们的生活、《闰七月》七月姑娘的遭遇,铁凝以客观的视角书写女性群体行为,剖析这些行为背后女性群体有关欲望、人性、道德的多重纠葛,并以此反照社会现实。
(二)民俗创作的自觉意识 民俗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算作历史遗留物,它偏离正统史书记载,隐没在无数人家的寻常生活中。古代专有一种官职为稗官,他们的工作是搜集街谈巷语、风土人情,以供皇帝省览。“稗官野史”一词由此而来,并逐渐演变为小说这一创作体裁。因为正史的缄口,有关民间文化的历史想象也顺理成章地流传了下来。小说家们把民间传承的传统文化放置到不同的文学时空,利用文化差异与时空重叠建构出民间想象的文化回环。
社会、时代的规范框架限制了人的思维范围,个人意志的自由性又使主体个性化得以凸显。铁凝的文学观念与写作风格一方面受到当时社会环境和文艺理论的影响,一方面又与强烈的自我意识脱离不了干系。铁凝执意下乡的举动不能不说是为了贴近文学而选择深入生活,因为当时文学界认为生活才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大环境为铁凝的人生道路提供了指向牌,而她热爱文学的心和体悟生活的情才是作品洋溢着真实可爱的魅力所在。观其作品,独属于她的人生碎片闪烁其间,那是她饱有真情的生活片段在写作中自然而发的自由情感,是个体意识在当下社会环境里的变相突围。
小说创作的内容书写往往会与审美风格的变化保持相对一致的方向。铁凝的文学历经多个时期,从稚嫩走向成熟,风格由《哦,香雪》时期的清丽纯净到《玫瑰门》时期的冷峻自省,再到后期的凝练沉稳,一步一印,随着自身审美观念的变化和思想的深拓挖掘而呈现不一样的文学动态。随着风格的演变流动,不合时宜的写作材料也理所应当随着作品的性情变化而消减隐身。正如其他构建素材一般,民俗事象的出现顺应了故事走向、节奏、风格及旨意的安排,在小说体系架构过程中发挥或大或小的文学作用。在承认这一点的基础上,反过来说,契合的民俗精神决定了民俗的被使用权,而从这种民俗精神中可以反观铁凝形而上的美学思考。
个体思维的活跃性使铁凝善于自然地进行民俗书写,把各种不同属性的民俗事象合理运用。写乡土小说,就讲农民的吃穿住行,讲他们如何种地、做饭、消遣娱乐;写城市小说,就讲市民的吃穿住行,讲他们的买卖、潮流、时代文化;写乡村和城市之间流动的小说,就利用民间风俗观念的不同来体现城乡之间的文化差异。女作家及女性主义作家是铁凝身上的一个重要文学标签,她始终坚持在女性意识关照的书写维度里思考女性的生存困境并追寻其存在意义,因此在很多具有女性意识的小说里都出现了女性生命状态的民俗事象。通过分析铁凝的众多民俗书写,可以发现铁凝的民俗心理是带有一股“野性”力量的,这种“野性”恰恰是个体自觉意识的主观表现,压抑的现实社会与带有赤裸欲望和蓬勃生命力的民间文化碰撞出矛盾而和谐的生命之花。
三、民俗写作下的精神探寻
(一)对人类世界的深切关怀“当我看到短篇小说时,首先想到的一个词是景象;当我看到中篇小说时,首先想到的一个词语是故事;当我看到长篇小说时,首先想到的一个词是命运。”[7](P188)铁凝这样定义小说。文学是深入铁凝心灵世界的一扇窗,透过小说这一介质可以观察到铁凝内敛沉稳的表象下涌动着无数滚烫的情感脉流,她在作品中始终传达了对人类精神归宿的无尽追求和对世界的大的热爱。
以铁凝的写作来算,她实在不算十分高产的作家,但经年累月的文字也令其对小说这种独一无二的写作方式深有体悟。铁凝第一篇小说《会飞的镰刀》开启了她的文学大门,从中不难看出她初出茅庐的稚嫩思想,但瑕不掩瑜,人物交往过程中细腻自然的情感表达令整部作品在当时的文学环境中脱颖而出,呈现出纯真质朴的独特气质。故事讲述了学农的城市女学生们与当地农村男孩发展出的珍贵友谊,一把“会飞”的镰刀牵动了所有可爱人的心。镰刀不仅是女学生与男孩之间友谊的见证物,也是农村民俗生活的重要意象。这把带有乡土气息的民间物件由此承载了纯粹真挚的情感回忆,成为联通民俗与情感的媒介符号。在那个思想压抑的特殊时期,这部作品的出现表明铁凝人文主义色彩的文学追求。
真、善、美,是铁凝创作路上不断执着的文学底色。《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村路带我回家》等作品都具有真淳和谐之美的情感倾向。《砸骨头》虽是一部短篇小说,里面传递的情感却格外厚重、热烈,小说提到居土村有一种特别的民俗活动——砸骨头,当地男人们发生矛盾争执时就采取这种方式进行宣泄、解决。故事中“砸骨头”的场景十分震撼,当两个男人赤膊上阵,晃动着身体拼命砸向对方,这一瞬间涌动着源自灵魂的极致冲动。这是肉与肉之间的搏斗,是骨与骨之间的交锋,是生命与生命之间无声的呐喊。“砸骨头”这类民俗仪式代表了人们面对原始欲望的真实自我。
铁凝一直坚持文学要有捍卫人类精神健康和心灵高贵的勇气和能力。在铁凝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大芝娘这类善良、宽厚、勤劳的女性形象,她面对生活带给她的苦难挫折没有自暴自弃,而是转化为了对其他人的关爱之情。大芝娘出生在受传统思想洗礼的农村,生儿育女的传统观念深深影响了她的人生认知,她在与丈夫离婚后仍跑去丈夫工作的城市找他,自此有了女儿大芝。大芝娘对孩子的疯狂执着显得不可理喻,偏偏这种不可理喻下埋藏着一位伟大母亲的天然渴望——对生命的纯粹希冀。人类只要保持心灵的高贵,就不会被世界打倒,生活可以磨难你,但永远不能玷污你。铁凝以理性的目光注视人类社会,对人类世界的深层关怀铺就了她作品永恒不变的情感底色。
(二)对生命个体的动情书写 铁凝不是被生活琐碎蹉跎麻木的木头人,她理智又浪漫、敏感又沉着,面对社会百态、人性复杂有着出乎常人的冷峻,而观其作品又能发现其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炙热情愫。多年的下乡经历使她变得坚韧而宽和,农村比之城市更接地气的乡野生活使她善于捕捉自然的细微波动,而源自原生家庭的审美培养和艺术领悟令铁凝对生命的发生、消逝更易触动。至少在她的思想中,生命是伟大和值得眷恋的。每一个生命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但生命开始之后的历程则是由自己内心来引导,欲望的自我掌控和放纵也由此成为造成个体命运差异的重要因素。铁凝的作品背景往往离不开光怪陆离的社会状况,文中个体命运的波折起伏也率以为常,人性叵测是她经久不衰的中心话题。或冷目、或诘问、或赞美、或感慨,铁凝以真实的笔法讲述世俗故事,用自由的方式释放自己的内心话语。
女性是铁凝着重描写的创作个体。“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着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8]生命的诞生是由女性孕育出来的,女性因而具有男性没有的独特生命张力。《孕妇和牛》是铁凝继《哦,香雪》后又一性灵之作,自然、人、动物在她的娓娓叙述中呈现出一派宁静、温暖的诗意画面,而背后透露出的家庭状况、民间观念和风土人情也委婉构建出一种和谐生命的存在关系。孕妇因孕育着生命而格外可爱,她与同样怀孕的黑牛行走在平原上,温情与希望始终环绕在这份自然美好的氛围下,营造了天人合一的审美意境。“这是一篇快乐的小说,温暖的小说,为这个世界祝福的小说”[9]汪曾祺曾大力赞美这篇小说,从他的话语中不难发现铁凝对生命和谐的精神追寻。从《哦,香雪》到《玫瑰门》《大浴女》,铁凝笔下的女性形象出现了由纯净、质朴向世故、扭曲的变化过程。香雪、安然、司猗纹等人物性情命运的不同恰恰反映出铁凝面对复杂社会矛盾与女性生存困境时产生的深刻反思。
无数生命个体共同构建了庞大复杂的社会,文学创作中的生命书写仅仅揭开了世间百态的冰山一角。死亡是所有生命的最终归途,但它有时也被认为是另一种新生。铁凝的小说中存在不少有关“死亡”的篇目,如《丧事》《明日芒种》《青草垛》等,死亡的仪式、禁忌、信仰传说在纷纷杂杂的言语中透露出头脚。《丧事》中提到了一种民间独有的“抓土竞赛”——“做儿媳妇的,谁要先跑到家,把土放进瓦罐,谁就会有吃不完的粮食。……虽然一把黄土从未给人带来任何幸福,可穷人还是这样虔诚地希望着。”[10](P69)死亡仪式却传递着与之完全相悖的生命意义,这是民间观念饱含希望的一粒播种,是活着的人与死去的人之间不必言说的情感反哺。生命和希望由此循环不止,生生不息。铁凝用心倾听社会的心跳,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交互碰撞中勾勒生命本质。
综上所述,铁凝小说的民俗书写,表现了时代背景下的社会百态,并通过民俗表象透视其文化意义,继而追寻人生与社会的终极奥义,达到真实与艺术的高度契合。民俗与文学共同指引了作品的情感趋向和价值取向,小说中民俗场景的再现以一种特殊的符号意义深度参与社会生活,推动人们重新关注传统文化。铁凝在创作时取材于生活,把展示社会人生百形百态作为主要内容,将人的生活故事和时代背景结合在一起,通过对普通人的人生展示挖掘人性和心灵的力量,从而具有了现实主义的“对人类大的体贴和爱”。[11](P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