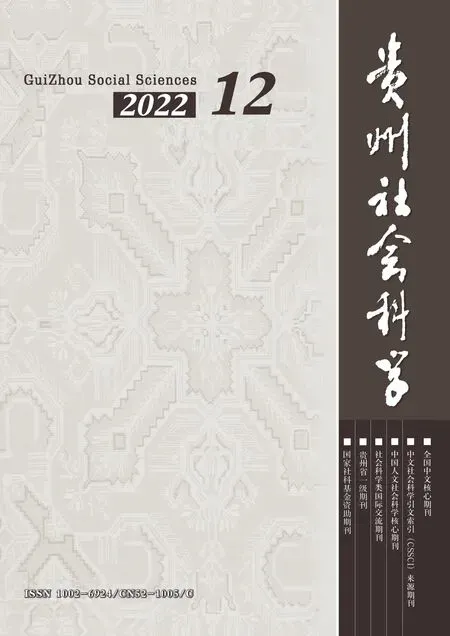仙传与升仙图:宋代“仙人接引”模式的文本建构与图像表达
熊 明 宋 昭
(中国海洋大学,山东 青岛 266100)
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为诱化人心、稳定社会,对道教进行整饬并纳入其社会治理体系加以提倡,至北宋太宗朝,道教趋向复兴并持续整个两宋时期(1)北宋道教具有唐代道教那种明显的官方性质。宋初,太祖、太宗倾向于儒释道三家并尊的格局,宋太祖注意到道士的政治作用,对道士加强管理和控制;宋太宗崇重宗教更甚,进行大修宫观、广招隐逸、推崇黄白金丹、搜集刊正道书等活动;至真宗“天书下降”“神人降言”“封禅泰山”“祠祀汾阴”“朝谒太清宫”,达到北宋第一个崇道高潮。详见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2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第526-575页。。道教追求长生不死、羽化成仙,与之相伴的是古老的神仙信仰在整个社会也得到更广泛传播。人们普遍相信灵魂飞升、长生不死之说,这在两宋从士林到民间的日常生活中有充分的体现。其中,道教自身的神仙谱系建构与教外文人的传记写作,促成仙传的大量出现;而在民间,升仙图成为墓葬墓室壁画营构的重要部分。仙传与墓室壁画升仙图,看似毫不相干,但在两宋道教于士林与民间广泛流行的背景下,却呈现出互渗相参的显著特征。考察宋代墓室壁画的升仙图,可以发现,升仙图所绘实即仙传中的升仙过程,是将仙传中的升仙过程形象化、艺术化,而“仙人接引”正是二者共同的核心与重点。
尽管文学与图像的表达范式有着各自长期形成的自洽体系,但宋代仙传与升仙图体现的多维度的互渗相参现象,给我们研究文本与图像共生关系提供了鲜活的案例。而目前已有的宋代道教相关文献与图像研究(2)参见邓菲《多重祈愿——宋金墓葬中的宗教类图像组合》,《墓室壁画研究》2019年第6期;黄士珊,杨清越《图像与灵应:宋代佛教和道教绘画艺术》,《美成在久》2015年第2期。,对仙传与图像中“仙人接引”这一显著情节却鲜有关注。潘诺夫斯基提出,文学研究可以借助其他艺术探究文本的内在含义,如他所言:“研究政治活动、诗歌、宗教、哲学和社会情境等方面的历史学家也应该这样利用艺术作品。人文科学的各个分支不是在相互充当婢女,因为它们在这一平等水平上的相遇都是为了探索内在意义或内容。”[1]12-13由此,通过分析“仙人接引”模式在宋代仙传中的文本建构与墓室壁画升仙图中的图像表达,可以探析其形成过程、模件表征及其现实隐喻,总结文本与图像之间以及更深层面的文学艺术与宗教体系、现实秩序之间的互渗互参机制及其发生。
一、宋前“仙人接引”母题溯源
汉末道教兴起之前,神仙信仰早已在中国存在并流行,道教形成后,神仙信仰被纳入道教体系,成为道教的重要内涵,证道成仙也成为道徒的终极目标。升仙过程便成为道教经典书写的重要内容,并作为一个一以贯之的母题,出现在道教的各种叙事中。
先秦时期,随着人们思维方式的转变和认知能力的提升,人们在体会到生命美好的同时,也产生了对死亡的恐惧,逐渐认识到生老病死的既定规律,萌生了渴望长寿、长生的念想,所以《诗经》有“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2]587“乐只君子,万寿无疆”[2]615之语。然而,再长久的生命终究难逃消亡,如果肉身得以永久保留、灵魂不灭,那么这种对死亡的恐惧便可消解。《释名·释长幼》则曰“老而不死曰仙,仙,迁也,迁入山也。故制其字,人旁作山也。”[3]从乞求长寿到肉身不死,“仙”的概念基本具备。但先民们认为仅靠自身的力量达成长生的目的遥不可及,只有神话中的神人才具有长生的能力,因此他们向神祈求,但人神相隔,于是就产生了“巫”这一媒介,《国语·楚语》中就记载:“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4]认为“巫”有连通天地的作用,其职能就是沟通人神。从“仙”的定型到“巫”的生成,神仙信仰于此萌蘖。其后老庄道家哲学以及邹衍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给神仙信仰提供了理论基础,神仙信仰由此得以建构并迅速传播。
秦始皇接受邹衍“五德终始说”,并开始了大规模的求仙活动,访仙山、求仙药,希求长生不死。至汉代,昆仑、蓬莱等仙境传说不断被完善,神仙信仰方兴未艾。武帝宠信方士,立五祠、建甘泉宫,修造蓬莱、瀛洲等“人间仙境”。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白日飞升难以企及,只能寄望于“神仙”显灵将其带离人间,即使在生时不能实现,也渴望死后能够升仙,因此墓室画像砖、壁画中出现了西王母、羽人、方相氏等符号式神仙或仙物。西王母崇拜可追溯至商代,汉代则出现了大量相关艺术品,西汉洛阳卜千秋墓壁画中,西王母庄严端坐于山巅,在幽冥世界静待朝拜,一人持节乘灵兽面向西王母而来,诉说了墓主死后进入仙境拜见仙人得以成仙的祈愿。汉哀帝建平四年祠西王母,传书曰:“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5]西王母不仅是成仙的象征,更被赋予了无限的权威,可使人长生不死。《汉武故事》《汉武内传》中直接记有西王母下降会汉武帝的求仙故事:“唯见王母乘紫云之辇,驾九色斑龙,别有五十天仙,侧近鸾舆,皆身长一丈,同执彩毛之节,佩金刚灵玺,戴天真之冠,咸住殿前。”[6]王母乘辇携众仙显灵,“仙人接引”的情节开始显露。
除西王母外,汉代墓葬艺术中还盛行“羽人”图绘。“羽人”延续了“鸟夷”“鸟羽”“鸟图腾”的文化脉络,在汉代宗教礼仪的影响下演变成人身羽翼的形象。《论衡·道虚》讲凡人升仙:“好道学仙,中生毛羽,终以飞升。”[7]身生羽毛即可飞升成仙。长沙砂子塘西汉墓漆棺,彩绘二羽人端坐于巨磐之上,羽人作为仙人的象征,有引导亡者灵魂升天的意味。此外,这一时期方相氏作为引导升仙的媒介也出现在墓葬艺术中。《周礼·夏官司马下》记方相氏职责:“大丧,先柩,葬使之道。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驱方良。”[8]826即引领道路和驱疫辟邪。汉代,方相氏起初用于贵族送葬仪式,其后民间出现了替亡者开路的“险道神”即方相氏的遗制。河南南阳辛店熊营画像石墓东西两墓门,分别绘有“蒙熊皮”“执戈扬盾”[8]826的方相氏,将其绘于连接阴阳的石门之上,意为墓主引路者。文学作品也逐渐出现神仙以特定之“物”接引凡人进入仙境的情节,如《列仙传·邗子传》记载有主人公邗子因寻犬而误入山中仙洞之事:“邗子……行度数百里,上出山头,上有台殿宫府,青松树森然,仙吏侍卫甚严,见故妇主洗鱼,与邗子符一函并药,便使还与成都令乔君。”[9]“犬”成为邗子进入仙境的引导。
随着道教的兴起,神仙信仰被纳入道教系统,成仙也成为道教修行的终极目标。至魏晋南北朝,道教鬼神观念影响下的仙传及志怪小说中,接遇仙人也成为其中的当然情节。西晋王浮《神异记》“虞洪”条云:“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吾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蚁之余,不相遗也。’因立奠祀。后令家人入山,获大茗焉。”[10]叙虞洪入山采茗遇仙之事。《搜神记》所记东晋“胡母班”遇仙事特详:“胡母班……曾至泰山之侧,忽于树间逢一绛衣驺,呼班云:‘泰山府君召。’……遂随行数十步,驺请班暂瞑。”[11]胡母班求见泰山府君,由绛衣骑士接引而入,同样是神仙前来接引的程式,足见仙人接引模式渐趋成型。南朝刘义庆《幽明录》“刘晨阮肇”条:
……便共没水,逆流二三里,得度山,出一大溪。溪边有二女子,姿质妙绝,见二人持杯出,便笑曰:“刘、阮二郎捉向所流杯来。”晨、肇既不识之,缘二女便呼其姓,似如有旧,乃相见而悉。问:“来何晚耶?”,因邀回家。[12]
故事以“忽复去,不知何所”暗示刘、阮成仙飞升的结局,透露通过“仙人接引”进入仙境可致精神超越和肉体永恒的范式。同一时期,在墓室壁画中,“龙”和虎等作为特定意涵的“符号”开始出现,如北魏画像石棺龙、虎升仙图,呈现的是以瑞兽龙、虎驮载墓主升仙之状。汉代兴盛的羽人形象此时也发生了新变,随着道教的走向成熟,羽化升仙观念褪色,羽人也逐渐脱去鸟形,基本与世俗人物形象无异。如南京灵山南朝大墓的羽人图像,不见羽翼仅头部装饰羽毛,体现出接引者逐渐向神仙转变的趋向。
佛道两教的争竞在初唐十分激烈,但在吕纯阳沟通禅宗身心性命之学与道家修炼生命之术后,至五代宋初,佛道二教在交流互鉴中体现出融通趋势,敦煌地区出现了一批引路菩萨接引亡者的壁画,所谓“引路菩萨”即“引导临终者去路之菩萨。其名号末见诸经典,系唐末宋初,与净土教之流行共同兴起之民间信仰。”[13]“引路菩萨”形象出现于唐末宋初,显然是受佛教净土宗影响,壁画所呈现的意涵,有接引亡魂前往西方净土世界之意。莫高窟五代第六一窟佛传故事送殡图中,引路菩萨手持引魂幡,就具有接引亡魂往生的信仰意义。在佛教图像中引路菩萨出现前后,道教图像中也出现了仙人接引亡灵升天的形象。不同的是,佛教“引路菩萨”是为超度亡灵,而道教仙人接引亡灵则是为还虚升仙,升登天国得以长生不死。
早期先民基于对生死离别的认知,通过“巫”与上天神人沟通,希望能够实现生命永恒,由此萌生出朴素的神仙信仰,先秦的方士借助人们渴望长生、自由飞升的欲望,结合老庄、五行之说,丰富完善了神仙信仰的理论与实践。汉末兴起的道教将神仙信仰纳入自身体系,道教的教义教理,无论何种道派,其终极目标均指向生命不死、灵魂飞升,向信众鼓吹得道升仙之旨。形之于文本:人们潜意识幻设偶遇仙人、经过其接引进入神秘仙境而得以成仙,长生不死,并在仙传与小说中逐渐完善和细致化。形之于图像:从西王母、羽人、方相氏的显现再到祥瑞动物、天人接引,人们设想升仙过程时,总需要特定神仙或仙物作为媒介的引导,至唐末“引路菩萨”的出现,为宋代墓室壁画“仙人接引”图式的生成完成了最后的铺垫。
二、宋代“仙人接引”模式的定型
唐五代以来,随着道教的传播发展,神仙传记与仙道小说的造作成为道教经典书写的重要方式,且二者相互交叠,相通与共同之处甚多,比如主题,二者都多集中于求仙、寻仙、长生之事,且对仙境的描绘与夸耀必是重要内容。而其中关于如何进入仙境,又是必不可少的情节,仙传与小说创造了颇具异想的特殊方式,李丰楙曾总结唐五代小说中进入仙境的方式,他概括为误入型、探求型、引导型三种,并指出,与小说相比,仙传中叙写游历仙境,进入方式则多为引导型,且有导乘工具如船、犬、龟等。[14]
至宋代,这种引导模式逐渐由动物转变为仙人,且逐渐趋向程式化。析读宋代仙传,我们发现其描绘的“升仙”过程,大致可分为前后相续的三个阶段:首先,神仙下降宣诏;其次,凡人准备飞升;最后,仙人下降接引,配合华丽隆重的场面描写。可简化为“仙人宣诏—凡人受诏—仙人接引—凡人飞升”,我们将这一程式化的情节概括为“仙人接引”模式。白玉蟾《旌阳许真君传》描写许真君飞升的过程,细致形象,将这一程式体现得十分清晰、完整:
至孝武帝宁康二年甲戌,真君一百三十六岁,八月朔旦,有云仗自天而下,二仙乘辇,导从甚都降于真君之庭,真君降阶迎拜,二仙曰:奉玉皇命,赐子诏。……至日中,遥闻音乐之声祥云弥望,须臾渐至会所,羽盖龙车,从官兵卫,仙童彩女前后导从。……乃揖真君升龙车,命陈勋、时荷持册前导,周广、曾亨縿御,黄仁览与其父族侍从,吁烈与毋部从,仙眷四十二口拔宅同时升举,鸡犬亦随逐飞腾。[15]
许逊真君飞升前,二仙下降宣告玉皇大帝诏命,表彰其在人间功德,后天降异兆,仙童彩女持幡来迎,仪仗华美,场面绚丽。从玉皇的诏命到众仙的引领,其内在逻辑俨然为得道升仙需经过上天认可,经由仙人的迎接,才能最终飞升。这种情节模式在众多的仙传中反复出现,又如沈庭瑞撰《华盖山浮丘王郭三真君事实》“二真君实录”条记载王、郭二真君飞升事:“晋元康三年二月一日,王、郭二真亦在山北玉亭馆奉玉皇诏命上升,乃留言乡人……言讫,王驾青鸾,郭乘白鹤,仙乐仪仗前迎,霓旌灵官后拥,冉冉上升。从辰至巳,祥云彩霞,移时望之,方没所属。”[16]王、郭二位真君,受玉皇大帝诏命后,同样经仙仗灵官持幡接引,得以证道飞升。廖侁《南岳九真人传》:“邓真人,讳郁之……以梁天监十一年壬辰十二月三十日,有八真人乘云车羽盖降于室中,即前得道升举者八真人也,于是日揖郁之就自然石坛同升霄汉。”[17]张某撰《唐鸿胪卿越国公灵虚见素真人传》:“至六月三日,甲申日中时分,真人化剑为尸,云舆造门。天钧拥户,彩云缭绕,香气缤纷,迎侍而去。京城之人咸见院中有青烟直上,与天相接,终日不灭。”[18]虽描写简略,但仍不脱神仙侍者下降接引的模式,也完全遵循“仙人宣诏—凡人受诏—仙人接引—凡人飞升”的基本模式。
道教认为神仙可以摆脱肉体的桎梏,以神魂不灭、肉身不老实现永生。凡人想要达到生命的永恒,就要借助飞升的方式成为神仙。宋代仙传对仙人、仪仗和诏书的描写都将飞升场景的自然要素神化,这些要素因此具有了一定的“神性”功能,“仙人接引”情节作为飞升故事中必要的一环也被赋予特殊的内涵和意义。
宋代道教的流行,造成神仙信仰的进一步下移(3)真宗导演“天书”“圣祖”下降等实践,在他当政期间,奠定了道观祠禄制度,使道教业已形成的官方祠祀性质更加普遍化、完备化。徽宗全面崇道,并一度废佛,其崇道活动有“宠任道流,大兴符箓”“奉神仙,夸祥瑞,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兴宫观、铸九鼎”“设立道学制度,提倡学习道经”“增置道官、道阶和道职”“广开入道之门”。详见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二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91-630页。,渗透到从士林到民间的社会日常生活之中,除了道教自身谱系建构中的经典造作以及教外文人的仙传书写之外,“仙人接引”模式也在民间墓葬墓室壁画的营构中以图像的形式呈现出来。亦即仙传描写的“升仙”故事也被纳入了墓室壁画的表现主题之中,在墓室壁画中出现了特殊的“升仙图”。由于壁画所处“场域”限制,无法完全展示文本故事描述的全过程,而故事进行中总有特定的瞬间可直达其叙事内核,那么这种“瞬间”便成为图像所要截取的画面,引领“观者”以有限的图像,“复原”文本故事的过程。就此而言,单个图像便具有了某种概括性与象征意义。
考察宋代墓室壁画升仙图,“仙人接引”情节便是其提取的“升仙”故事的核心和重心,是“升仙”故事的概括性和象征性的图像表达。如河南省登封市黑山沟北宋李守贵墓《持莲仙女图》《仙人击钹图》《持幡仙女图》《导引图》[19]137-140、新密市平陌村宋墓《“四洲大圣度翁婆”图》《仙界楼宇图》《升仙图》[19]150-152、济源市东石露头村宋墓《持幡仙人图》[19]165、登封市高村宋墓《升仙图》[19]168等,图像所描绘均为仙人下降迎接墓主人升仙的过程。其中,平陌村宋墓壁画以多幅具有连续性的组图来表现“升仙—长生”全过程。墓室东北壁上部,蒸腾的祥云掩映华丽的石桥,桥上共八人,作前行状,最前梳高髻侍女手捧仙气方盒,后一女子神情肃穆执幡相随,再后二人为墓主夫妇,两人毕恭毕敬合掌于胸前,墓主身后另有一执幡女子侧首与身后二小童交谈。在仙人接引行过云桥后,墓主二人进入仙界,壁画也过渡到《仙界楼宇图》[19]151,图像正中屋宇林立,四周祥云环绕,一派仙境气象,亡者或得道之人通过仙人的接引、持幡女仙的护持,渡过仙桥,飞升仙宫,便进入了天宫洞天实现了永生。图像的叙事性描绘,从人世到仙境,实现了“长生”信仰的视觉化、图像化转变,于是“‘死亡’不再是一瞬间的事情,而表现为一个持续的过程。”[20]
升仙图中仙女一般脚踏祥云,图中云气呈花头状,与仙人侧身朝向一致。祥云代表了升仙长生的媒介,也是神仙形象的固定图式。《庄子·天地》云:“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21]《论衡·无形篇》云:“图仙人之行,体五毛,臂变为翼,行于云。则年增矣,千岁不死。”[22]皆提及仙人伴祥云的固定模式。另桓谭《仙赋》论及升仙:“仙道既成,神灵攸迎。……出宇宙,与云浮,洒轻雾,济倾崖。观沧川而升天门,驰白鹿而从麒麟。”[23]从人世升仙转向仙境长生,无论是仙人乘于白云亦或是行于云气,“云”已然是神仙形象的视觉基础,也是升仙、永生的叙事性表达,并与仙女形象一道,共同构成了墓主从现实世界到天国仙界的“桥梁”。
就宋代墓室布局看,升仙图大多位于墓室的最上方,墓室中层部分则描绘其他内容,如平陌村宋墓绘有闵子骞、鲍山、王祥、赵孝宗孝行图,下层则为夫妇对坐、梳妆等日常生活场景。这些壁画的布局象征了墓主所处的“宇宙”,他们心中的宇宙图式天在上,地在下,按照这种逻辑,很显然,最上方的“升仙-长生”图绘才是整个墓室空间构造的重点与目的所在。人们对长生的深切渴望,生前无法如愿以偿,死后就以墓葬为阈界,试图于此实现灵魂的升华。世俗图、孝行图、升仙图相组合,由下及上,从现世到仙境,完成了死者肉身与魂灵“长生”的转化。
仙传与升仙图各自通过符合自身艺术规律的书写方式,完成“仙人接引”模式的文本建构与图像表达,并各自在书写实践中实现模式化定型。在“仙人接引”情节的文本建构和图像表达中,仙人们扮演着沟通上天和凡世的媒介角色。凡人必须要通过仙人的接引才能进入仙境,这代表神仙世界对其的承认和接纳。由此仙人也被赋予了连通天地的祥瑞含义,因而仙人实际上也有了显著的工具性,这也显露了神仙信仰的巫觋底色和传统。
仙传对“仙人接引”模式的文本建构和升仙图对“仙人接引”模式的图像表达,是宋代道教文化在从士林到民间各社会层面的一种特殊反射和投映。对读宋代仙传与墓室壁画升仙图,不难发现,仙传文本书写的形象意旨,“就在图像内部,当它们显得最彻底地缺场、隐藏和无声时,也许就在图像的最深处”[24]。同样,升仙图背后的意涵,也完全可以在仙传文本的故事叙述与情节建构之中找到答案。因而,将二者对读,实现图像形式与文本语义的互释,无疑可以更好地理解与探寻深藏在它们背后共同的文化机理。
三、作为“模件”表征的诏书与灵幡
以“仙人接引”模式为中心,宋代仙传飞升故事,大致按照“仙人宣诏—凡人受诏—仙人接引—凡人飞升”的情节程式展开。在这一程式中,仙人宣诏与凡人受诏具有标志性。相对于传记以文本呈现出的完整始末和诏书意涵的明确性,升仙图由于受空间限制,则大多以仙人形象及其所携仙物来表达这一程式。升仙图中仙人手执灵幡的形象,可视为仙传中接引意涵的形象化表达。仙传文本中仙人所持“诏书”与升仙图中仙人所持“灵幡”,也成为各自书写范式中的标志性“模件”(4)雷德侯在《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与规模化生产》中提出了一组概念—模件“module”、模件体系、模件化,针对中国艺术中的模件体系进行了考察和讨论。他认为:“中国人在历史上很早就开始借助模件体系从事工作,且将其发展到了令人惊叹的先进水准。他们在语言、文学、哲学还有社会组织以及他们的艺术之中,都应用了模件体系。”详见雷德侯,《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与规模化生产》导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也就是说,诏书与灵幡,是仙传与升仙图“仙人接引”模式中具有特定象征意义的道具,更是仙传文本建构与升仙图图像表达中的标志性符号。
(一)诏书
诏即帝王颁布的以命令为主的下行公文“(王)命为‘制’,令为‘诏’。”[25]“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渊嘿黼扆,而响盈四表,唯诏策乎!”[26]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在宋代仙传中,玉皇大帝作为天界权威,其诏命也具有同样的功用,得道者是否可以升仙完全取决于玉皇的征召,因此诏书具有了聚神属性,成为仙传中不可缺少的道具性物件。白玉蟾《逍遥山群仙传》“沛郡施岑乡关壮士”条:“宁康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晨,见东方日中,有一童子乘彩云、执素策、驱苍虬降其所居,宣玉帝诏,遂御苍虬乘云去。”[15]“钟离嘉”条:“是年十月十五日日中,碧霞宝车自天来迎,公阳拜诏,升车而去。”[15]关壮士、钟离嘉皆在得到玉帝诏命后而飞升,只有经过上天的承认,才能获得正统合法的神格。具体而观,玉皇大帝的诏书同皇帝的诏命形式内容如出一辙,白玉蟾《旌阳许真君传》:“真君俯伏以听,乃宣诏曰:上诏学仙童子许逊,卿在多劫之前,积修至道,勤苦备悉,经纬愈深,万法千门,罔不师历,救灾拔难,除害荡妖,功济生灵,名高玉籍,众真推仰,宜有甄升,可授九州都仙太史兼高明大使,赐紫彩羽袍,琼旌宝节,玉膏金丹各一合。诏至奉行。”[15]同时期宋高宗有《李若水赠观文殿学士诏》:“故吏部侍郎李若水,忘身为国,知死不惧,忠义之节,无与比伦。达于朕闻,可特赠观文殿学士,与子孙恩泽五人,赐其家银绢五百匹、两。”[27]两篇诏书,皆用骈体书成,首先讲明被赐诏人的身份,其次表彰其功德,最后进行封赏,这无疑反映了诏书效应的共通性。回归到诏书内容本身,这一隐喻更加明确。许逊飞升前玉皇诏命的重点是对许逊的善行进行罗列和嘉奖。此外,宋徽宗也对许逊有所加封:“繇魏迄晋,嗣休炳灵,赈乏蠲疴,一方攸赖;剪妖馘毒,三气获分。……荐降嘉祥,聿彰幽赞;襘禳响答,民物阜宁。宜极徽称以昭严奉,谨遣朝奉大夫充集贤殿修撰,知洪州、军州管干学事、兼管内劝农使、充江南西路兵马铃辖护军,赐紫金鱼袋,王勇上尊号曰:神功妙济真君。”[15]以褒奖许逊功德为始,继而进行册封。
在民间信仰中,玉皇大帝是统摄“天”的象征,玉皇大帝通过下达诏命来册封新的神灵,代表天界对新神的认可,其作为天界的至尊,是现世皇帝在超自然领域的镜像,这种超凡的权威结构,明显是以凡世的制度结构和文化心理为当然基础。宋代人均以科考中举为人生目标,其在当世的孜孜以求迫使他们幻想在黄泉下也依旧显贵,于是彼岸世界成为现世官僚制度体系的拟像。无论是仙传中凡人飞升还是现世中帝王维护统治,上天的指示作为一种准入形式,在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诏书作为仙传中“仙人接引”情节的模件构成,是确定仙人身份的权威性表征,隐喻了神仙信仰中普遍存在的同现世相似的制度结构和文化心理。
(二)灵幡
“幡”通“旛”,《释名·释兵》云:“旛,幡也。其貌幡幡然也。”[28]《说文解字·部》云:“旛,幅胡也。”[29]孙诒让《九旗古谊述》认为《说文》所谓的“旛胡”亦即“旐旆”的别名[30]。其本源可以追溯到《礼记·檀弓上》:“孔子之丧,公西赤为志焉:饰棺、墙,置翣设披,周也;设崇,殷也;绸练设旐,夏也。”[31]公西赤在布置孔子葬礼时遵照夏礼设计了装饰有白绸和长练的旐旗,是丧葬礼仪秩序的必备。宋代道教认为灵幡与儒家经典中的旌旗形制相近,故有时借用“旛”字名之。如《召魂咒》:“阳神返风生,阴灵逐我幡。魂魄承符召,急速赴灵旛坛。阳神返汝残,阴灵来我幡。北斗天蓬敕,玄武开幽关。三魂无散失,七魄莫倾残。乘此金符力,摄汝赴灵旛坛。愿承无上道,证汝升仙班。”[32]灵幡召魂,使亡灵齐聚于灵旛坛,从同样具有聚魂功效来看“灵旛坛”即“灵幡坛”,可见宋代对两种不同来源的旗幡已多有混同,将儒家旌旗与道教灵幡在名称上杂糅到了一起。与儒家旗幡礼仪之用相似,道教之“幡”常用于斋蘸科仪,不同的灵幡适用于不同的科仪,其中迁神宝旛,据《上清灵宝大法》记载:“绛缯七尺,或四十九尺,造旛一首,以朱砂、雌黄合研,书日月斗形于旛首,书旛名于旛身。左手书三天内讳,右手书三天隐讳。亡魂睹此,则得罪障解脱,神迁南宫。”[33]亡魂见此灵幡即得以解脱,飞升成仙,仙人接引或用此幡。
仙人显灵下降总是持幡而来,灵幡成为仪仗中显著的标志,是身份、权力与秩序的体现,宋代墓室壁画升仙图引入灵幡,无疑是一个聪明且恰当的选择。灵幡在升仙图中被固定为“仙人接引”模式中的必备“模件”,如李守贵墓《持幡仙女图》《导引图》[19]139-140、平陌村宋墓《升仙图》[19]152、东石露头村宋墓《持幡仙人图》[19]165所示,画中仙女皆梳花髻侧身呈前行状,或俯视下方注视墓主、或前后导从簇拥亡者,双手持幡立于身前,灵幡直立高耸,幡首作三角状、幡身作矩形状、两角下垂飘带、矩形底部携尾带,幡带迎风飘扬,正是主动接引之意。壁画用简洁的造型描绘出这些女仙形象并凸显灵幡的象征意义,体现亡灵“接引—长生”的轨迹,也是“长生”信仰的情境化描绘,具有强烈的宗教涵意。
墓葬文书从战国时期起就与丧葬仪式密不可分(5)关于此点来国龙有详释,见来国龙《战国秦汉“冥界之旅”新探:以墓葬文书、随葬行器及出行礼仪为中心》,《人文论丛》2009年卷,第151-186页。,汉代文人或士吏有专书简册随葬的习俗,如磨咀子汉墓中以简册随葬。以简策向地下的世界昭示墓主人生前的身份和荣耀。借官方文书以告幽冥世界,也有引路效应。这种墓葬文书展现了对诏令神圣性的崇拜心理,和世俗诏书具有共同功用。对照宋代仙传中升仙的文本建构与升仙图中升仙的图像表达,不难发现,仙传中详细呈现的玉皇诏命,在升仙壁画中完全隐退。由于图像无法完整、精确地展示上天的诏命,且图像的主人公也不是得道高人或王公贵族,因此无法获得上天的册封,于是图像中仙人手持的灵幡作为准入规则的外显特征,替代和凝聚了诏书的指示性功能。灵幡的作用是引导游荡的亡灵,虽然在神仙信仰中得道之人可以升仙长生,但人们对幽冥世界的未知性仍怀有恐惧,于是在“招魂”观念的促使下,不得不借助灵幡以聚魂魄,引领亡者去往仙界天国。基于雷德侯“模件化”的理论,模件体系由可灵活替换的内容组合而成,对于“仙人接引”叙事体系而言,无论是仙传中的诏书,还是升仙图中的灵幡,作为模件的显性意义和指向,无疑是可以实现互释的,其背后实际上也暗示了升仙叙事中存在着现实秩序机制的规范和限制。尤其是道教灵幡在定格过程中又受到儒家旌旗制度的影响,因而它们无疑也是墓室壁画空间秩序的重要表征。
四、“仙人接引”模式的现实隐喻
分析和解释艺术作品,潘诺夫斯基提出了三个解释层面,即前图像志描述、图像志分析和图像解释学解释[1]3-13,上文所论述的墓室壁画的“仙人接引”模式,以及“飞升成仙”的秩序机制,即第一、二个层面。而要实现对仙传与升仙图“仙人接引”模式的融通互释并发现其背后的现实隐喻,还需要将“仙人接引”模式置于其原本所在的文本和图像体系中才能实现。
宋代仙传在描写“仙人接引”前常常刻画传主飞升之前的人间历程,其中浓墨重彩加以描绘的是那些传主的积德行善之事,这些善行作为“仙人接引”发生的前事前因,最终成为其日后升仙的必备条件。以南宋《西山许真君八十五化录》为例,“化录”或有教化之意,其中“择地化”条云:“乡里化其孝友,交游服其德义。”“德政化”条云:“视事之初,戒吏胥去贪鄙,除烦细,脱囚挚,悉开谕以道……其听讼,必先教以忠、孝、慈、仁、忍、慎、勤、俭,近贤远奸,去贪戢暴,具载文诫,言甚详悉,复患百里之远难以户晓,乃择秀民之有德望与耆老之可语者委之,劝率,故争竞之风日销,久而至于无讼。”“赈乏化”条云:“先是岁饥民无以输租,郡邑绳以法,率多流移。祖师乃以灵丹点瓦砾为金,令人潜瘗于县圃。一日,籍民之未输者咸造于庭诘责之,使服力役于后圃,民钁地获金得以输纳,遂悉安堵。”“平疫化”条云:“属岁大疫,死者十七八。祖师以所授神方拯治之,符呪所及,登时而愈。至於沈疴之疾,无不痊者。传闻他郡病民相继而至者,日且千计,於是标竹於郭外十里之江,置符水于其中,俾就竹下,饮之皆瘥。其悼耄羸疾不能自至者,汲归饮之,亦获痊安。”[34]
此四条,皆叙许逊于凡间所行善举,但无论是“德政”还是“平疫”,其所体现的精神显然是儒家的,指向儒家的人格完善和事功理想。道教也通过这种方式,将自身浸入或融入既存俗世的社会主流伦理秩序之中,从而建立起与俗世的一致性宗教伦理秩序。又如《黄鹿真人传》云:“是时世道多尤,盗贼蜂起,岁仍荒歉。仙女为捐所有,垦开荒芜,疏凿淤塞,播种以时,使民无艰食之患。”[35]如此行善四十余年,乃有神仙下降告其功业渐成。仙传通过建构羽化飞举故事向世人许诺:信奉其教、多行善举即可升仙,长生不死。在弘道之外,也以此归化民众,提升道德,助益建立和维持现实社会政治与道德伦理秩序的稳定。当皇权无法解决天灾人祸时,民众就会对神灵产生期待,道教借仙传神化这些代表伦理标准的人物,塑造新的神灵,这些神灵也由此被赋予了相应的伦理责任,参与到现实政治与道德伦理秩序的建立和维护中来,并鼓励人们遵守政治与道德伦理规范。在许真君、黄鹿真人这些百姓熟悉的神仙身上,实际上也凝聚了统治者的政治与道德伦理要求,通过这种方式,道教在宗教层面为现实政治与道德的伦理秩序进行了背书。
宋代仙传通过提供符合世俗社会主流价值判断的成仙故事,助力现实秩序的建构和维护,墓室壁画升仙图则以空间布局来表现和实现这一目的。宋代统治者偏崇道教,并试图将道教活动控制在朝廷认可的标准体系中,促使百姓的宗教实践接受官方的规范和管理。这种做法确实促进了符合统治者要求的政治与道德伦理秩序的传播和推广。已出土的宋代墓室壁画中的升仙图,墓主人多为社会中下层的地主或商人即是证明。河南省登封市黑山沟村北宋李守贵墓,墓室东北壁壁画[19]141,下方为王祥行孝图,上方为持莲仙女图。墓室东壁壁画[19]142,下方为孟宗行孝图,上方为击钹仙人图。另有西壁壁画,下方王武子(妻)行孝图;西北壁下方为董永行孝图;北壁下方为丁兰行孝图。墓室上方升仙壁画的南壁上部是引导图,东南壁上部是持幡仙女图。统观整个墓壁,行孝图均位于墓壁拱眼处,在整个墓壁下方,升仙图则均位于墓壁上方,全壁将儒家孝行故事和道教仙境纳入一个图像系统中,在生与死、实与虚的时空结合里,显示出明确的伦理秩序。从下方的孝行图到上方的升仙图,壁画的排列顺序体现出宋人的神仙信仰观念,即只有在现实世俗生活中尽孝行善,死后才会有仙人接引前往仙境,最终实现不朽。从凡人到神仙,由现世飞升仙界,以孝行作为得道升仙的必备条件,以仙人接引作为仙界准入的必要仪式,墓主人在这一过渡性空间里实现了其飞升成仙的祈愿。这一组壁画证明,道教实际上是以将普世性的亲情善行与自己的修行目标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对现实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宣扬。
宋人对死后世界的想象,除道教美学和现实社会儒家政治与道德伦理文化的映照之外,也有着佛教美学的印记。南宋梁楷《道君像手卷》[36]图中地狱业火燃烧,牛头首领带鬼怪前来追击,一位士大夫装束的人物脚踏祥云上升,被天尊接引离开地狱。手卷聚焦于画面右上角,以道教神仙救苦天尊(6)救苦天尊即太乙救苦天尊,是专门拯救堕入地狱之人的神仙,受苦受难者只要祈祷或呼喊天尊的名字,便能得到救助。下降为重心,天尊端坐于五色莲花座,头绕神光,与地狱的可怖形成鲜明映衬,预示天尊成功拯救受苦灵魂脱离炼狱。有关太乙救苦天尊的形象“在造型上,观音持杨柳和净瓶在太乙救苦天尊之前,是佛教影响道教的关系;在神格上,道教用杨柳和净瓶驱邪治病的做法影响到了观音,是道教影响佛教的关系。”[37]展现“仙人接引”场景的同时,另隐含着佛教教义的基调,体现了佛道二者的相互影响。又如上文所举平陌村宋墓壁画,在墓主人夫妇升入仙境后,其后紧跟有《四洲大圣度翁婆图》[19]152墓主人另受到“四洲大圣”(7)“四洲大圣”也作“泗洲大圣”即僧伽和尚,是中亚何国人。公元661年左右来中国,他被视为观音化身,有消灾解难、治水、祈雨、护城、护航、治病救人等功绩。的接见和度化,关于“四洲大圣”,洪迈在《夷坚志·张次山妻》中载有其事:“妻曰‘每日受苦如此,须请泗洲大圣塔下持戒僧看诵《金刚经》,方免兹业。’”[38]张次山妻后由经文资荐求助“泗洲大圣”得以投生。在这一故事里,“泗洲大圣”成为接引人们脱离地狱苦海的人物,张次山妻在得到其度化后转世,这与佛教“轮回”的教理相吻合,“轮回”在某种意义上也实现了长生,“僧伽崇拜以孝为先……正体现了三教合一的特色”[39],墓主或其后代修墓之时无意识地吸收不同文化,无论是儒家的人格完善与事功理想还是佛教的度脱地狱,都与道教升仙长生的最终目的相一致。另一方面,图像构成的多宗教蕴含也为宗教文化的融通提供了佐证。
具有“历史时间”性的宋代仙传与墓室壁画升仙图,是以回顾式的眼光对历史的重构,其本质是社会性和政治性的。[39]宋代道教的教内秩序树立,表现出对本朝官僚体系的积极模仿,统治者也赋予道教宗教仪式和宗教实践合法性和权威性。作为一种辅助力量,道教因此得以参与到国家思想文化以及现实社会生活制度规范的型塑过程之中,在现实政治与道德伦理秩序的推广与巩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仙传以飞升成仙来解释生命不死,劝导行善积德,在升仙过程的程式化书写中,以特定的细节突出“仙人接引”仪式,其目的在于增强道教神仙信仰的权威性,并使之合乎现实社会的礼仪与法度,由此证明和宣示现实伦理秩序的合理性。壁画升仙图则借助空间布局,选择并呈现“仙人接引”场面,同时通过引入特殊的物象,实现了对“仙人接引”的视觉化转化和塑造,同时,也印证了这种秩序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并深入人心。潘诺夫斯基认为,图像第三层面“揭示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阶级、一个宗教和一种哲学学说的基本态度,这些原理会不知不觉地体现于一个人的个性之中,并凝结于一件艺术品里”[1]5。仙传与壁画升仙图借助文学与视觉艺术的转换和互动,实现了宗教文化的兼容并包。
总之,宋代仙传与壁画升仙图对“仙人接引”情节的书写与呈现,无疑有着共同的文化心理,在不同层面展现了宋代神仙信仰的历史图景,而通过二者的对读,也可以略窥文本与图像之间以及更深层面的文学艺术与宗教体系、现实秩序的互渗相参机制及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