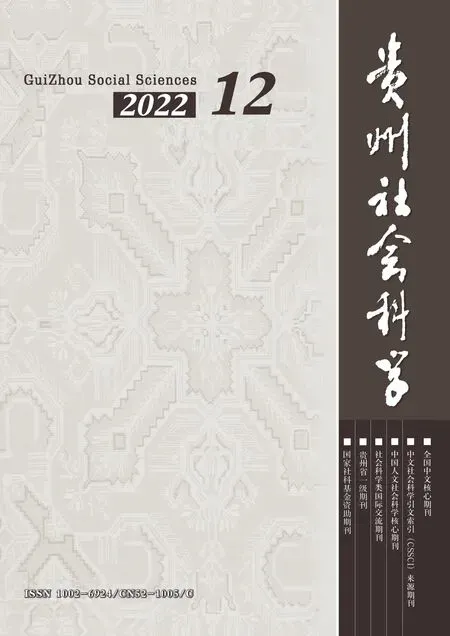清代清水江中下游的乡村治理
——以制度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张 旭 王砚旭 龙昭宝
(1.贵州民族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2.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
清水江中下游曾是重要的林区,在明代中后期皇木采集的推动下,林业开发在清代迎来鼎盛时期。从逻辑上而言,清水江中下游林业经济的兴盛必须以稳定的社会为坚实基础,离不开乡村治理。关于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费孝通先生认为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法律是无从发生的,[1]指出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持是通过“礼治”来完成。[1]49-50其实,丰富的民间文献表明,费老所言的“礼治”只是乡村社会秩序建构的一大路径,除此之外还有制度,在少数民族地区尤其如此。在已有的研究中,规约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为学者所强调,就这一领域而言,除此之外还有官府颁行的禁令、法规以及民间社会的其他制度,但为学界忽略。清水江中下游通过制度开展乡村治理的历史背景是什么,有哪些制度类型,官民之间形成怎样的互动?本文对前述问题展开探讨,意在抛砖引玉。
一、乡村治理的历史背景
连接湖广与云贵地区的黔中通道东段为舞阳河和清水江的上游,是明朝重点经营的区域。位于舞阳河南侧的清水江中下游以及都柳江流域爆发的局部动乱时常对交通干道造成严重冲击。自洪武年间开始,明朝通过屯军和建立政区的手段对清水江中下游实施管控。清朝建立政权后通过军政手段继续加强统治。在此背景下,清水江中下游经济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时存在多种引发社会失序的因素。
(一)明清王朝不断加强军政管控
明朝建立政权之后,面临的是土司林立、动乱频发的状况。土司虽然被朝廷赋予治理边远地区的权力,但有的土司缺乏治理能力,甚至成为祸源之一。基于此,明清王朝一方面延续元朝的制度任命土司治理地方,另一方面安插卫所、设立政区不断加强管控。
1.任命土司。元朝在清水江中下游南侧设立的土司有潭溪、八舟、洪舟泊里、曹滴洞、古州八万、新化、湖耳、亮寨、欧阳、中林验洞、赤溪楠洞、龙里、福禄永从等,其中古州八万长官司还短暂升为军民总管府。[2]125-128洪武三年(1370)正月庚戌,分据于清水江中下游的13个土司归顺明朝。明朝任命其为蛮夷长官司,授其原职,先令辰州卫统领,后改隶同年三月设立的靖州卫。[3]4明朝还根据治理需要任命和废除一些土司,新设的土司有西山阳峝蛮夷长官司(位于今从江县西山镇顶洞村),[3]130遭废的长官司有铜鼓、五开洞、上黎平、诚州富盈等处。[2]128西山阳峝蛮夷长官司的设置表明国家统治力量从清水江中下游拓展到都柳江中游。清代康熙元年(1662)六月曹滴洞遭改土归流,[4]15其他土司因能受朝廷约束而延续至清末。清朝在雍正初期通过军事手段开辟“苗疆”之后,任命一批熟悉地方社会、掌握民汉双语且“征苗”有功的“通事”为土弁管理少数民族村寨,分土千总、土把总之职,据《黔南职方纪略》记载,土千总22人、土把总16人。[5]364-375关于土弁的形成,卢树鑫认为时贵州地方政府出于治理“苗疆”的需要,在朝廷不再设立土司的背景下违例授予通事土弁职衔,遂使通事的身份经由在官人役转变为如土司般的世袭职官。[6]通过委任土弁,国家控制力量不断向清水江与都柳江的交界区延伸。
2.屯军设堡。为镇压洪武十一年(1378)六月,[3]16洪武三十年(1397)三月爆发的农民起义,明朝先后设立有五开、铜鼓两卫,其间又设中潮、铜鼓、新化、亮寨、黎坪守御千户所。[3]60此外,在清水江下游的北面,明朝分别于洪武二十年(1387)、三十年(1397)设天柱及屯镇汶溪守御千户所。[2]1570-1571这些卫所分成许多屯堡,如楔子般插入清水江中下游。据乾隆《开泰县志》记载,五开卫管辖16所、380个屯堡。[7]53万历二十五年(1597),明朝裁天柱守御千户所而设天柱县,隶湖广靖州直隶州。[8]这也是清水江中下游裁所设县之开始。清代康熙及雍正两朝,明朝设立的卫所逐渐被裁革或者改设为县,五开、铜鼓两卫于雍正七年(1729)分别被改设为开泰、锦屏两县。虽然裁卫改县是清朝的一项“去军事化”改革,但屯军制仍被延续下来。据《黔南识略》记载,开辟“苗疆”之后清朝在清水江中游及都柳江中上游设有9个卫,分成120个屯堡,[5]90、93-94、106、117、121、181-182其中清水江中游分布有5卫、57堡,足见清朝对此区域的重视。
3.设立政区。大量土司及卫所的设置为明朝设立府、县级政区提供了较好的人文基础,契机源于思南、思州两大宣慰司长期的相互仇杀。永乐十一年(1413)二月,明朝将此两大宣慰司废除后设立贵州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在清水江中下游设立黎平、新化两府,原隶于卫的土司改为府管辖。[3]140-141由于地方狭小和人口少,明朝于宣德九年(1434)十一月裁掉新化府,将其辖境并入黎平府。[3]243正统七年(1442),福禄永从蛮夷长官司李瑛无子嗣而族人争袭,朝廷将其设为永从县(今黎平县永从乡)。[7]255这是侗族聚居区改土归流之开始。雍正七年(1729),清朝在清水江中游及都柳江中上游设立古州、清江、台拱、八寨、丹江、都江6个厅级政区以及凯里分县(隶清平县),实现了对这一区域的完全管控,[5]180、106其中清江、台拱位于清水江的中游。设立政区之后,明清王朝设立府学、县学、卫学、社学、义学等机构开展儒学教育,开科取士,以此为纽带让不同文化传统的群体产生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
(二)社会失序
明清王朝通过军政手段对清水江中下游实施管控,推动这一边地的经济社会获得发展的外源性动力。屯军使得大量土地得到开发,多种经济作物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得以引进和推广。清水江及都柳江航运的开通不仅使内地的粮食、布匹、食盐、铁器等货物进入贵州,也使边远地区的木材、茶油、桐油等农特产品远销闽浙一带。大量汉民通过屯垦、经商以及逃荒的形式迁入这一区域,和苗、侗等民族杂居于一起,社会生活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发生变迁。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基于良好的社会环境,违法乱纪、偷盗抢劫、失信违约、欺诈拐骗、传统婚俗等是引发社会失序的重要因素。
1.治理阶层违法乱纪现象突出。在国家力量加入之前,清水江中下游的社会治理主体分为土司、寨老和普通民众。明清王朝设立卫所以及政区之后,社会治理主体增加了地方官吏。这些多样化的群体既是社会秩序的建构者,也是社会治理的对象。此后,因为有了国家的赋权,土司、官吏、头人等群体构成了地方社会的治理阶层,违法乱纪之行为构成了社会失序的一大因素,主要体现在多收赋税、勒索财物、滥派徭役等方面。嘉靖十三年(1534),贵州巡抚王杏在奏疏中指出土司及下属盘剥百姓的多种方式以及引发“田土荒芜”“地方疲惫”之严重后果。[9]乾隆元年(1736),贵州学政邹一桂在《奏苗民被欺积怨折》中向朝廷反映贵州少数民族承担沉重徭役、乡绅强占田产、官兵低价勒买苗货、汉民共同压低本土货物而哄抬外来商品价格的现状。[10]229治理阶层违法乱纪之行为在民歌中也有所反映,例如侗族古歌《讲到天下大乱》描述有贪官污吏及土司“糟蹋地方”的恶行。[11]清代著名侗族歌师陆大用(生活于黎平县肇兴侗寨)编有《乡老们吃钱过份》《头人不好》等歌谣揭露乡老、头人“专讲大话,吓唬老百姓,……践踏粮食,……糟踏良民”之现象。[12]治理阶层的违法乱纪使得地方动乱时有爆发,为势使然,正如邹一桂所指出的那样:“且思苗性虽顽,亦属人类,其感恩蓄怨之心,岂必尽无,方其受欺之时,则隐忍而不言,或言之而莫理,积之日久,乃一发其胸中之毒,此亦事势之必然者”。[10]229-230
2.民间社会偷盗劫掠行为时有发生。清水江中下游位于湘黔两省交界区,国家控制力量薄弱,亦为内地犯罪汉民逃匿之所,民间社会的偷盗、劫掠行为时有发生,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的建构,地方志及文人著作对此亦有记载。万历年间郭子章所著《黔记》记录黎平府洪州一带侗族有偷盗、抢劫的行径,“峝人,性多忌喜杀,……在洪州者尤犷悍,地肥多稼,而懒于耕作。惟喜剽略,寻常持刀,铤挟驽矢,潜伏陂塘,……又四方亡命倚为逋薮,往往为之乡导,分受卤获,饥愈甚。故黎平之盗,洪州为最多”。[13]2627-2628流传于清代中后期的“百苗图”描述有清水江中游少数民族劫掠的社会生活:“(黑生苗)在清江境内。[性情](情性)凶恶。访[知]富户所居,则勾连恶党,执火持镖刃而劫之。”“(黑山苗)台拱、古州、清江有之,……[不事耕作,每]以掳掠致富。”“(黑脚苗)在清江、台拱。……出入三五成群,持标带刀,以抢劫为能[事]。”[14]劫掠团伙社会危害性巨大,历来是官府严厉打击的对象,雍正初年清朝开辟“苗疆”主要基于这样的考量。
3.姑舅表婚习俗引发社会冲突。姑舅表婚是一种姑之女嫁给舅为媳的婚俗,普遍流传于西南地区,在黔东南的苗、侗民族传统生活中被称为“还娘头”。姑舅表婚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质,因违背女性意愿和以钱财作为补偿,故而时常引发社会冲突。流传于黔湘桂边区的侗族款词《出娘舅银款》认为姑舅表婚理所当然:“你是我们的姑血表婚。娶你是理所当然,娶你不能有半句怨言,娶你没有半文身价钱。……表哥断腿断脚你都要嫁,表哥眼瞎耳聋你也要回舅家。”[15]苗族歌谣《哭诉“还娘头”》却控诉姑舅表婚的强制性:“我是笼里鸡,要宰全由人;……舅家那娃崽,塌鼻扁嘴唇;呆头又呆脑,象鬼不象人。……娘亲你是人,不如鸟兽心——硬逼女儿我,还你舅家门!”[16]若姑之女不嫁给舅家,或者舅家没有适龄的儿子,必以一定的钱财作为补偿,名为“外甥钱”,如清人李宗昉的《黔记》载道:“姑之女必适舅之子,聘礼不能措则取偿于子孙,倘外氏无相当子孙抑或无子,姑有女必重赂于舅,谓之‘外甥钱’,其女方许别配。若无钱贿赂于舅者,终身不敢嫁也”。[17]298光绪十四年(1888)十二月立于锦屏县彦洞乡瑶白村的《婚俗改革碑》记录有舅家多索钱财以及郎家借贷、出售田产结亲的现象,“惟有总甲等二寨,养女出户,舅公要郎家礼银二十余金。出室受穷,舅公反富。倘若郎家穷困,并不积蓄,势必告贷;告贷不能,势必售产”。[18]41这些资料表明,舅权在婚姻中具有极高的权威性,这使得姑舅表婚习俗产生束缚女性婚姻自由、贫女不敢嫁、婿穷舅富等社会问题。
二、乡村治理的制度类型
无论是对王朝国家还是对民间社会而言,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是共同的诉求。针对不法之徒劫掠财物、农民起义等群体性事件,王朝国家首先采取军事镇压手段,以防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显然,这一举措治标不治本,无法改变局部动乱频发的现实。基于此,针对不同主体,王朝国家和民间社会通过制度来加强乡村治理,旨在消除引发社会失序的因素。诺思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形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主要作用是“通过为人们提供日常生活的规则来减少不确定性”。[19]3-4他关于制度的正式规则以及非正式规则的两大分类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一)正式制度
正式制度是政府或一些社会组织制定的法律、法规、规则以及经济主体之间签订的合同、协议等,具有成文性和强制性。诺思称之为“正式规则”,涉及的内容有政治(和司法)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19]56针对引发清水江中下游社会失序的问题,清朝从严以治吏、木材贸易、婚俗改革等三个方面制定制度,民间社会在从事山林、土地等不动产交易以及股份分配、家产析分时也签订有契约。
1.严以治吏制度。官吏的违法乱纪行为是诱发农民起义、影响国家长治久安的主要因素,中国历代王朝通过制度来严以治吏,清朝也不例外。清朝以《大明律》为蓝本制定清律,于顺治三年(1646)颁行第一部法典《大清律集附律》。为解决律与例之间的冲突,符合新的统治需要,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对此部法典作了重大修订,最后由乾隆帝亲自厘定,定名为《大清律例》,于乾隆五年(1740)颁行天下。此外,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朝编制的会典中也有治吏的制度。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基础上,清朝针对贵州地方官吏的各种违法乱纪行为颁发禁令。从目前搜集到的资料来看,最早的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十一月,云贵总督蒋陈锡严禁潭溪土司重征滥派。禁令刻于石碑,至今存放在黎平县岩洞镇述洞村独柱鼓楼旁。[18]65针对全省各地的官吏违法现象,乾隆二十七年(1762)六月,云贵总督吴达善颁行十七项禁令,(1)一是严禁滥派夫马,巧设名目折收银钱;二是采购日常各种物资须按市场价用银两现买现卖,不得向汉、苗民众摊派,或者折价而中饱私囊;三是征收屯饷银两时只能增加一层火耗,统一标准,由民众自行缴纳,严禁多加火耗,勒索票钱;四是监狱所需的各项材料要在市场购买,不得在民间社会摊派;五是征收粮赋或者折算其他物资时,要用官府统一颁发的斗斛,让民众自己缴纳,不能用市斗测量以及勒索钱票;六是汉、苗等民众入城出售鸡、柴火以及蔬菜之类,文武官弁以及士兵不得强行索取,或者压低价格强买;七是处理诉讼纠纷时,官差下乡不许勒索鸡、酒等物资以及鞋脚钱、马钱及铺堂使费;八是文武官员以及士兵路过驿站时不得征用民夫和摊派火把,而驿站负责人更不能私自外出,令妇女承担差使;九是汉、苗民众改用米谷来代替屯饷时,要自己亲自缴纳,不许由户首粮差代办,以免被对方勒索侵占;十是采买仓粮兵粮,要对制定的价格进行公示,严禁克扣和额外征收;十一是田地卖了赋税也要跟着变动,不能再向原田主征收赋税;十二是征收粮食用于铺仓库用的竹席由官方购买,不得向民间社会摊派;十三是缴纳库粮雇佣民夫,每天要给费用,不得征用民夫;十四是修缮城墙时要雇佣民夫,不得折算成银两而由偏远山区的民众缴纳;十五是地方官所需的竹子、木材等物资,要在市场购买,不得向民间摊派;十六是修理旗杆以及所需麻绳之类,木材由官府购买,不能在民间征收;十七是修缮公家修建的馆舍时,费用由官府承担,不能向民间摊派。开泰县知县费履祥将其刻于石碑立在衙署前。[7]372同治、光绪两朝,贵州也颁行有关于严以治吏的制度。立于今剑河县南哨乡翁座村的《例定千秋》碑是贵州巡抚曾璧光于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二十一日签署的关于社会治理的法规,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十日又加以重申。[18]17光绪五年(1979),贵州巡抚岑毓英颁发“严禁加收钱粮以苏民困事”的禁令,如今在锦屏县固本乡新民村仍立有刻有此类内容的石碑。[18]37道光十六年(1836)六月十四日,黎平知府张锳综合以往贵州省颁发的严禁土司贪赃枉法的禁令,重新对所辖土司提出要求,严禁这一地方势力集团裁决民间纠纷和代缴赋税。[18]55
2.确立“当江”制度。雍正七年(1729)清水江航运的开通激活了这一流域的林业开发,地方社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维护不同主体利益的制度也逐步得到建立。清水江中下游的木材贸易存在两个重要的地理空间:一是“山上”空间,林农之间以及与“山客”(本地木商)开展林木及土地交易;二是“江边”空间,“山客”将木材采运到清水江边卖给“水客”(外地木商)。在“山上”空间中,民众之间的木材、土地交易通过契约来确定权属关系。在“江边”空间中,因涉及销售点、运输等环节以及不同群体,木材贸易过程中存在的利益冲突只有地方政府的强力介入才能解决。凭借河道平缓、便于泊木之条件,隶属锦屏县的茅坪、王寨、卦治三寨逐渐形成重要的木材交易市场(民间文献称之为“当江”(2)“当江”是指当地民众作为中介联系买卖双方、促进交易,提供食宿以及看守、扎排等服务性工作。),当地民众利用掌握民汉双语的优势开店接待“水客”,联系“山客”,收取中介费,而食宿、看守、扎排等环节也是他们获得收入的重要渠道,因此也就有了前述三地与坌处等下游村寨的“当江”之争。因天柱县通过黎平府的道路经过茅坪、王寨、卦治三地,三者的“当江”之争和承担的夫役不均密切关联。嘉庆三年(1798)至十一年(1806)是“当江”之争的第一阶段。官府为平衡茅坪、王寨、卦治的“当江”之利和夫役,确立了三地“轮流当江、分年歇客”的核心制度。[20]这一制度自然引起坌处、清浪、三门塘等下游村寨的持续不满和挑战,因此“当江”之争的第二阶段是咸同—光绪年间,背景是清水江中下游通过组建团练来对付咸同之乱,经费源于抽取木材交易的厘金。基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兼顾沿江村寨的利益,天柱、锦屏两县建立起了内、外“三江”(3)茅坪、王寨、卦治居于中游,被称为“内三江”。坌处、清浪、三门塘居于下游,被称为“外三江”。共同“当江”的制度,对各村寨从事木材交易的事项都作了具体规定,民间称之为《内外三江木材商场条规》。[21]
3.姑舅表婚改革制度。针对引发社会冲突的姑舅表婚习俗,官府逐步对其改革,从历时性来看,先是限定“外甥钱”的数额,其后是禁止姑舅表婚。锦屏县敦寨镇平江村《恩德》碑立于康熙二十九年(1960)七月十五日,刊载的内容是云贵总督、都察院、黎平军民府以及亮寨长官司联合颁发的关于社会治理的告示,涉及摊派、治安、文教、婚姻、丧葬等方面,其中涉及到姑舅表婚的是规定赔偿舅家“礼银三两五钱”,要求“不得勒借”。碑末刻有潭溪、新化、亮寨、湖尔(耳)、欧阳五个土司。此碑表明官府至少在康熙朝后期已介入民间婚姻,来自上层的力量通过土司阶层向下层社会渗透。[22]虽然有了国家的介入,但由于文化传统的惯性,该婚俗并未得到遏制。乾隆五十六年(1791)孟冬月,应文斗、尧里村民姜廷干、李宗梅等人关于革除姑舅表婚的要求,黎平府颁发告示,内容刻于石碑,名为“恩垂万古”,碑文写道:“凡姑亲舅霸,舅喫财礼,掯阻婚姻,一切陋俗,从今永远革除。如有违示者,众甲送官治罪”。此外还对聘礼、认舅家亲礼钱、嫁女首饰所有权、请媒、二婚礼等都作了具体规定。石碑末尾刻有文斗、茂广、岩湾、加池、张化、平鳌、尧里、扒洞、格翁、践宗、堂东、培亮、里夯等寨101名头人的名字。[18]22-23这些信息表明官府推行的姑舅表婚改革制度通过众多头人向边远地区扩散,前述村寨位于清水江中游的南岸,因此从地理空间来看,婚俗改革仍是局部性的。同治三年(1864)及光绪二年(1876)先后任黎平府知府的徐达邦、袁开第分别颁发有婚俗改革的告示,其中袁开第在《禁革苗俗告示》中要求辖境内“舅家不得强娶外甥女、勒索财礼”,违者“按例究办,决不以苗俗曲宽”。[23]
4.契约制度。“契约”在中国古代语义中有“约束”之意,经历了刻木为符到文字书写的发展历程。当文字契约在历代王朝的主导下逐渐变成规范化和程式化的时候,少数民族由于没有掌握汉字而仍停留在符契的阶段,刻木为契的习俗在《后汉书》以降的汉文典籍中多有记载。湘黔边区土著民刻木为契的汉文献记录始见于宋人朱辅著的《溪蛮丛笑》中:“刻木为符契,长短、大小不等,冗其旁多至十数,各志其事,持以出验,名木契。”[24]明代随着屯军戍守、设立政区以及学校教育在清水江中下游的渐次实施,大量汉民与苗、侗民族杂居,汉字契约逐渐被人们接受。中华法系的契约制度有买卖、借贷、租佃、典卖等类型,其中以买卖、借贷契约为主。[25]从已有的资料来看,清水江中下游留存于世的时间最早的土地买卖契约是锦屏县铜鼓镇九南村的《吴王保石榴山冲荒地卖契》,时间为明代嘉靖三十五年(1556)十一月廿三日。[26]99清代随着木材贸易的兴盛,民间社会每年立下的买卖契约数量,吴振棫在《黔语》中描述为10万余份:“商贾骈坒,赍刀布而治质剂者,岁以数十万计”。[17]386-387光绪《黎平府志》记载的资料显示鼎盛时期杉木的年销售额达“二三百万金”,在盗伐严重的情况下仍可卖“百余万”。[27]大量白银在清水江中下游的流动也带来了山林、田土的大量交易、租佃以及借贷、典当活动,契约种类不断增多。较之一年一季的稻谷种植,杉木从幼苗到成材至少需要20年才能砍伐出售,周期长,许多杉山由多户人家合伙经营,故而民间社会又出现了杉山分股或白银分红的契约。这是一种新的契约类型,是林业开发的特定产物,和其他类型的契约共同作为一种制度规范着人们的经济行为。
(二)非正式制度
非正式制度是指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约定俗成的具有约束作用的行为规范或者做法,亦可称为“非正式规则”。和成文性、强制性的正式制度相比,非正式制度主要以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形式存在,富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而且有的非正式制度并不具有强制性,而是从心理层面对民众产生影响。结合相关史料,清水江中下游代表性的非正式制度可归纳为村规民约、“中人”调解以及神判。
1.村规民约。村规民约是村民结合实际情况共同制定和用于自治的行为规范。结合民族性、地域性、口头性之特质,把村规民约纳入非正式制度更为合适。早期的村规民约主要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人们集众宣讲之后在现场埋下一块石头作为凭证。苗族《议榔词》说道:“立根石柱一尺高,栽根石柱一抱大。议榔在石柱下,榔规就付(附)在石柱。议榔在石柱,榔规就留在石柱。议榔在石柱上,榔规才不变动。议榔在石柱上,榔规才不遗失。”[28]不仅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村规民约,而且同一民族不同群体制定的规约也有所区别。黔湘桂边区侗族传承于世的作为整个款组织的口头规约共有18条,通常称为“六面阴规”“六面阳规”“六面威规”。“六面阴规”是对重罪处以极刑的处罚条规,“六面阳规”是对轻罪的处罚条规,“六面威规”是属于一般的礼仪规范和道德要求,具有劝勉、告诫的性质。苗族的榔规涉及治理盗贼、窝藏罪犯、偷砍林木、偷放田水等多个方面,对违反榔规之人予以相应处罚,轻者遭受不同数额的罚款或者驱离,重者则被剥夺性命。明清时期,民人掌握汉字之后,把口头传诵的规约编成条款刻于石碑,目前学界搜集到最早的为侗族款约系从江县增冲《万古传名》碑。此碑立于康熙十一年(1672)七月初二日,内容涉及治理偷盗、婚姻关系、婚恋出轨、田地买卖、山场纠纷、恃强横行、内勾外引、失火烧屋或坟地等,共有12条,大部分规约都有具体的处罚金额,只有“山场纠纷”“田土买卖”两项以捞油锅为最终解决办法。[29]3-4
2.“中人”调解。针对群体之间的冲突,贵州各民族也采取中间人调解的方式化解矛盾。苗、侗民族的“中人”调解习俗在明代贵州弘治《贵州图经新志》中已有记录,调解人分别被称为“行头”“乡公”。苗族的“行头”用木筹记事,多次奔走和听取矛盾双方的意见后才确定处理办法。侗族宰杀牲口召集众人,推选公认的“乡公”说和,当事人互相辩争,负者对胜者进行财物补偿,与对方饮血酒,立下誓言。[2]122在黔东南苗族传统社会里,调解之人被称为“理老”,解决纠纷时把道理蕴含在具有神话性质的案例中讲解,以案说理。在侗、苗、汉等多民族杂居的社会中,调解之人被称为“中人”,调解纠纷之后要求当事人立下合同或合约。目前学界搜集到最早调解纠纷的文书为锦屏县敦寨镇九南村的《寨市乡陆勇等立断事合同》,时间为明代嘉靖二十五年(1546)九月二十九日。[26]451清代,中人参与到了山林、土地、屋基等不动产的交易之中,名字作为见证者写于契约上,调解买卖双方之间的权属纠纷,故而文书中多写为“蒙中劝解”“从中劝解”“请中理论”之语。从一些具体案例来看,在中人的调解之下,当事人通过写下“清白”文书的方式来表示矛盾已化解。例如,搜集于锦屏县河口乡文斗苗寨、立于乾隆五十年(1785)六月二十日的“范振远、姜士朝清白合同”记录的是中人调解纠纷的文书。缘由是锦屏县河口乡岩湾寨的范振远砍伐地名叫“皆烈”的林木,文斗寨的姜士朝前来争夺。二人请来中人姜弘运、姜廷评判处理。中人经过调查核实,发现范、姜二姓都参与了林木的购买,提出的处理意见是:一把山地分成两股,范、姜二人各占一股;二把山上未砍的老木分成四股,范、姜二姓分别占一、三股;三是姜士朝先年栽下的嫩木权属归他,而今后范振远在权属自己的山地栽杉时前者不得阻挠。这些处理意见得到范、姜二人的认可,他们共同立下“清白”文书,“今恐无凭,立此合同,各执一纸为照”。[30]231-232
3.神判。神判是人们借助神灵的力量判断疑难案件的一种文化习俗,可分为“捞沸判”“铁火判”“能力判”“人体判”“人血判”“人头判”“饮食判”“灵物判”“煮物判”“鸡卜判”“起誓判”等。[31]在诸多类型中,“捞油汤”是最常见的一种,做法是当事人用手在滚烫的油锅或者沸水中捞起预先放入里面的物件,不被烫伤者被认为清白无辜,反之则被判定为有罪并向胜者赔偿财物。此种习俗不仅在清人方亨咸著的《苗俗纪闻》、陆次云撰的《峒溪纤志》有简要记载,而且在民间文献中也有体现。搜集于凯里市凯棠乡的《捞油锅理辞》叙述了此种裁决纠纷的来历以及做法,用于烧油锅的物质有牛油、小米、蜂蜡。[32]13-32捞油锅势必造成极为严重的烫伤,搜集于黄平县谷陇镇的《捞油锅理辞》表明理老并不主张。如果当事人执意要通过捞油锅来解决纠纷,理老们作为证人,监督裁决方式的公正性,严禁作弊,希望雷公、龙王护佑受冤者不被烫伤以及威慑和惩罚作恶者。[32]33-51侗族款约表明捞油锅是最终的裁决方式,立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七月初三日的从江县《高增寨款碑》规定:“议山场杉树,各有分界,若有争执,依据为凭。理论难清,油锅为止。”[29]2
三、乡村治理中的官民互动
上文的多种制度类型表明清代清水江中下游的乡村治理呈现出多元化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都存在一些不足,亦有难以管控的领域,这也为官民互动提供了良好契机,认知及实践层面分别表现为相互接受和利用。
(一)官方对民间自治传统的认可与利用
从发生学角度而言,非正式制度的产生早于正式制度,这些约定俗成的做法在乡村社会国家化的过程中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与利用。从历史进程而言,明朝在贵州各地设立的府、州、县级政区的职能只是征收赋税而不处理民间纠纷,“郡邑治民,……民即苗也,……郡邑中但征赋税,不讼斗争,所治之民,即此而已矣”。[33]少数民族之间矛盾的解决也不诉讼于官,即便诉讼于官也不依据明律,“凡几要约,无文书,刊寸木判以为信,争讼不入官府,即入亦不得以律例科之”。[13]2619-2620“亦不得以律例科之”的现象说明官府处理民间纠纷依据的是村规民约,体现出官方“因俗而治”的策略以及对民间自治传统的认可。这些举措延续至清代,并得到了进一步弘扬。康熙四年(1665)七月,贵州总督杨茂勳向朝廷提出“安边境之道”的措施,认为贵州为少数民族聚居地,言语不通,不知“理义”,仇杀之事常发,因此治理的举措与内地有所区别,针对劫掠财物的团伙通过军事行动予以剿除,针对群体内部“相互仇杀”之事则“止须照旧例”,由头目讲明曲直,或偿命或用牛羊、人口赔偿,根据自治传统处理,并在官府里备案,“申报存案”。[4]19这一建议一方面体现出地方官员利用少数民族文化传统来治理乡村,另一方面体现出官方对民间纠纷并非放任不管而是开始介入,较之明代有所变化。针对偷盗之事件,贵州巡抚王燕于康熙四十年(1701)十月向朝廷提出“分而治之”的建议,即“熟苗”(承担赋税、徭役的少数民族)为盗则按照“汉法”处置,而“生苗”(未承担赋税、徭役的少数民族)则按“苗蛮侵害地方旧例处分”。[4]55按“汉法”处罚犯罪“熟苗”表明清朝运用国家法来治理乡村,但也带来诸多骚扰而引发社会矛盾,对此,乾隆帝于乾隆元年(1736)八月初一日作出“嗣后苗人一(切)争讼之事,俱照苗例完结,不必绳以官法”的谕令。[10]212这一谕令是国家层面对少数民族自治传统的高度认可,为后者在民间社会的延续以及发挥治理作用提供了合法性,各地民众因时、因地制定出繁简不一的村规民约,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制度文本。
村规民约的治理对象为地方民众,实施主体为“通事”、头人等群体。实施主体的贤良与否影响到村规民约的权威以及治理成效。乾隆三年(1738)七月二十八日,贵州总督兼管巡抚事务的张广泗在《革除苗疆派累厘定屯堡章程》奏折中提出了慎选“通事”、签立头人的举措。“通事”乃谙熟民汉双语以及道路交通之人,凡官府委派的招抚民众、宣扬政策、征收钱粮、查缉罪犯等事务皆由他们完成。其时,一些奸顽之辈借机勒索食物、银钱等,导致地方动乱发生。在民间纠纷“俱照苗例完结”的背景下,张广泗建议加强遴选“通事”,只委任对方翻译民语而禁止到村寨去勒索民众,允许民众到衙门来处理纠纷,若对方有“从中把持蒙蔽”之举即从严处罚。头人即村寨中明白事理、懂得汉语且有较强领导力之人。张广泗认为开辟“苗疆”之时那些凶狡强悍的头人已被剪除,留存下来的为安分之人,原属本寨自立之寨老,并无责任意识,可根据传统习俗推选出一至三名良善守法者作为头人,官府与其签立责任状,由后者来约束民众,不许为非作歹、劫掠仇杀、私造军器、招纳匪人等。如头人能够认真履行职责,地方社会稳定,官方予以适当奖赏以示鼓励,反之则与犯罪团伙一起处置,另行推选。“是亦同内地设立乡约保正之类,庶责成耑而苗人不敢滋事矣。”[10]240-241通过加强对“通事”、头人的管控,王朝国家的统治力量向边远山区渗透。
(二)民间社会对国家力量的认同与借助
王朝国家作为秩序建构的主体之一,民间社会对此经历了从排斥到认同和借助的过程。从刊刻于康熙十一年(1672)七月初三日的从江县《高增寨款碑》的序言来看,民间社会处理矛盾的一般步骤是先由家族长辈调解,若是还未能解决的再请乡正、团长处理,并不容许横蛮无理控诉至官府,“决不容横行无理,奔城具控,咬情生事”。[29]1这一规定表明乡村社会希望把问题化解于群体内部,对国家力量的介入持有排斥态度。类似的规定在黎平县竹坪村的《款禁碑》中也有所体现,该碑立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二月初五,涉及13个村寨,核心内容是禁止偷盗,处罚的措施是“捆绑款上,立即打死”,同时规定不许赴官、动凶和隐匿抗违,违者遭受同样的处罚,“同治罪”。[34]75且不说凡是偷盗即遭死罪之规定的严酷性,就“不许赴官”之规定即表明一些地方并不希望受到官方干预。然而,村规民约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甚至有横蛮者并不遵守规约,因此一些村寨把“送官治罪”写入村规民约中,对国家力量呈现出认同态度,借助后者来增强款约的威慑力。从现存的碑刻资料来看,“送官治罪”的缘由各有不同。一是恃强不接受规约。立于嘉庆四年(1799)梅花月(腊月)的锦屏县鹏池村《禁条告白》碑记录的是一个叫“沟盘下”的地方多次跌倒耕牛,众人规定不许砍树,违者罚银三两;如有恃强不服者,则报官处置。[30]297立于嘉庆十七(1812)五月吉日的锦屏县瓮圭村《小江放木禁碑》严禁通过河道运木以免损坏农田,违者“照木赔偿”,而“恃强不服,送官究办无虚”。[30]297二是不履行规约。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二月谷旦的锦屏县章山村《万古碑记》禁止砍伐、破坏风水林,违者一方面要补栽树苗作为赔偿,另外还有“罚钱拾三千文”。不履行此规定者则报至官府处理,“违者禀官究治”。[30]266三是情节严重的盗窃案件由官府处置。黎平县纪堂、弄邦以及从江县登江、朝洞等侗寨于光绪十八年(1892)七月初八日刊立的《永世芳规碑》共计24条,内容涉及衙门公务、禁偷、禁赌、砍伐古树、拐骗、婚姻、丧葬、诉讼、诬陷等多个方面,对盗窃的规定根据情节严重与否来作相应的处罚,半路劫掠的是送官治罪,而偷杉、茶、棉花以及鸡、狗、蔬菜的分别有不同数额的罚款。此外,该规约对赌博烂棍“罚钱十二千文,违者送官治罪”。[34]71显然,此条款意在处罚不履行规约者,和前述的第二点相同。
固然村规民约在社会秩序建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但在问题不得解决的前提下,一些地方存在械斗现象,这也是官府不乐见的,因此要求人们诉讼于官,通过衙门来裁决纠纷。康熙三十六年(1697)三月十日的《永远碑记》记录的是黎平府颁发给平鳌村民的告示,除了明确该村承担的“烟火银六两”之外,还要求人们通过官府来化解矛盾,“今尔等愿归府辖,凡一切斗殴、婚姻、田地事件,俱令亲赴府控告,不得擅自仇杀”。[30]280在日常生活中,时人诉讼于官的情形有三:一是利益共同体错综复杂,当事人就纷争事实各执一端,难辨是非;二是涉及的利益巨大,无法在头人、寨老的调解下达成一致;三是一方当事人恃强欺弱,拒不执行调解协议,一再拖延,甚至一开始就排斥调解,导致矛盾不断升级。从学界搜集到的民间文献来看,民间社会诉讼于官的领域主要是山林以及婚姻。山林纠纷的主要表现是或产权不清,或强行砍伐,而婚姻纠纷主要是姑舅表婚。针对山林纠纷,官府通常不会主动搜集证据并严格按照清例做出明确裁决,而是寄希望于中人调解或者凭据契约管业。针对婚姻纠纷,官府的处置是或革除姑舅表婚,或限定“外甥钱”的数额,或者下不为例。显然,诉讼于官是一件财力耗费甚巨的事情,对此人们深有感触,希望通过规约或调解来化解纠纷。锦屏县启蒙的《因时制宜》碑立于光绪十一年(1885)十月二十二日,系流洞、寨母等10个寨子的48个寨老同立,涉及700余户,内容是对传统婚俗中的种种积弊进行改良或革除,共有8条款约。人们之所以立此规碑,是因姑舅表婚引发冲突而诉讼于官,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第婚姻六礼之例,创自先人,而姑表分财之规,不无陋弊,或藉此而赖婚枉利,或因此悬搁终身。以至内怨外旷,覆宗绝嗣,因此构讼经官,倾家荡产,呜呼殆哉,祸甚烈也!”[34]74一份未署时间的文书记录有经历咸丰、同治两朝动乱之后锦屏县文斗苗寨重新制定的自治规约,共有9条,其中一条是通过调解来化解纠纷,原因是当地事无巨细都诉讼于官,“我团中每因婚户、田土、银钱、细故,动辄兴词告状,以致倾家荡产”。[30]175针对此种情况,地方乡绅规定当事双方设一宴席,请头人、寨老“据理劝解”,如有不服再请团首调解,决不允许刁蛮扰公,否则“立即联名禀官重究”。此外,在其他规约中,如有违者则报官处置。固然,人们通过村规民约来构建乡土秩序,但“禀官重究”之语表明到了清代中后期,民间自治还是在国家治理框架之下完成的。
综上所述,清代清水江中下游林业经济的兴盛离不开乡村治理。明清王朝加强军政管控以及社会失序构成乡村治理的历史背景,官府和民众是乡村治理的两大主体,通过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来构建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在乡村治理进程中,官民形成较好互动,民间社会自治传统因官府的认可及利用获得了合法性,而国家力量也通过民众的认同与借助向边远山区扩展。乡村治理使得清水江中下游的国家化得到不断推进,促进这一区域的内地一体化发展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