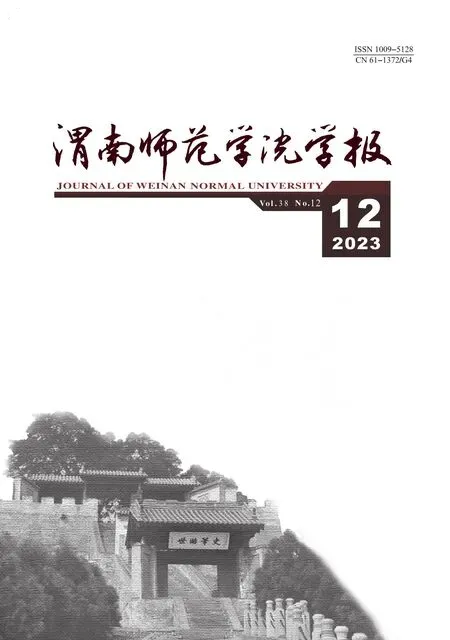有为而作,探本求真
——读可永雪先生《〈史记〉人物论》《〈史记〉中的再创作选评》
任 刚,蔡静波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文教学院,西安 710100)
一生挚爱着《史记》、年过九旬的可永雪老师仍然笔耕不辍。2021 年以来,他又出版了两部有关《史记》研究的大作:《〈史记〉中的再创作选评》(中央民族出版社2021 年6 月版)、《〈史记〉人物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年7 月版)。这两部著作都着力于《史记》人物的研究,是近年来《史记》研究中特色鲜明、不可多得的成果。二书倾注可老师一生的心血,有内在关联,可以看作可老师研究《史记》人物的总结性著作。笔者以为,这两部著作可以归结为研究《史记》人物的两个心得,或者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物本身的研究,一个是人物形象的成因。二者相辅相成,有逻辑关系。
一、有为而作
有时我们觉得历史沧桑,古今分明;有时我们又分明看见日月星辰亘古不变,人事往往重演。历史的变与不变,使得历史具有了价值。古圣先贤认识到了历史的重复性,认识到了历史经验教训的价值,因而非常重视历史记载。中华民族黄帝时就设置了史官,专司其职,地位崇高。杜预《春秋序》曰:“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1]1703以实录为前提,历史事件的人物、地点、时间记载分明,有的记载具体到某一时辰,充分体现出史官对历史的责任心、使命感。此种责任心、使命感成为史官基本的职业道德,亘古未变。
司马迁家族乃重黎之后,源远流长,“世典周史”[2]6331,“世主天官”[2]6380。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司马迁父子对史官职责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其使命感、责任心也更加强烈。“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兴败成坏之纪”,撰成三千年通史——《史记》,其“述往事”的目的就是“思来者”[2]6445。因此,《史记》是历史的书,同时也是现实的书,具有永久生命力。具体可以从两个方面说:一是司马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纵观三千年的中华史上的兴衰成败,使得《史记》虽然下限在汉武帝时期,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有较强的中华民族缩影的性质;二是《史记》中的人物是一个个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真实人物(《五帝本纪》所载传说历史,司马迁也认为是真实存在过的)。诗人气质的司马迁具有洞彻人心、人性的天赋,他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研究十分细致,既有宏观背景的考察,也有微观的体贴,能够进入历史人物的心理和情感世界。他对历史上的兴衰成败虽然有时归结于天,但他从来也没有忘记人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他主要的、很大程度上,把兴衰成败归结为人为因素,甚至归结于历史人物的心性和性格。因此,《史记》人物,多有个性。从男到女,从老到少,从“大人物”到“小人物”,从传说中的“五帝”到汉武帝时期,《史记》所载人物皆然。个性鲜明,成为艺术形象,甚至成为符号,影响深远。可以说,《史记》展现了民族性,是一部中华民族“心灵史”。司马迁父子融通古今,黜陟幽明,《史记》对现实的观照、对后世的借鉴作用,自不待言。
可永雪老师一生研读《史记》,《史记》人物又是他关注的中心、用力最多的兴奋点,其所著《〈史记〉人物论》可谓抓住了《史记》的核心所在。《史记》既然是以人为中心的史书,《史记》人物自然是研读《史记》者最关心的内容,也是最能引起读者感慨和共鸣的部分。这种共鸣从《史记》传播的时候就开始了,晚司马迁五六十年的扬雄就有评论。两千多年来,有关《史记》评论,人物评论当居首位;但《史记》人物研究的专论很少,许多真知灼见,都是三言两语、点点滴滴的心得体会;专书更是少而又少。自20 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来,可老师不断有《史记》人物研究论文发表,得到学界的普遍重视与认可,其成就与特色,拙作《名山之宝谁识得——可永雪老师的〈史记〉文学研究》[3]曾有分析。笔者捧读此书,认识益深,感慨益多,益觉其当下价值的可贵。可以总结为:立足书本与现实,在“知人”与“识人”上用力,以期有益于现实人生,体现出司马迁天人古今的视角。归结为一句就是:要《史记》为我们做人做事提供参考。
其一,有针对性地精选人物。《史记》中个性鲜明的历史人物不下百人。可永雪老师所关注的历史人物一定比较全面。但是《史记人物论》所论仅仅三十多人。这说明此书绝非泛泛而论,而是经过精心筛选的。夏商周三代选了虞舜孝亲和吴太伯让国,春秋时期只选了管仲、鲍叔牙、骊姬、伍子胥四人,战国时期选了聂政、赵武灵王、孟尝君、范雎、田单共五人。事实上,我们知道,《史记》所载春秋、战国时代的比较生动、典型的历史人物也很多,但是可老师都没有选。可老师并不一定以《史记》着墨多少为原则,也并没有完全从人物形象的生动与否为出发点(比如太伯让国,《史记》并没有写多少事情,人物形象也并不十分鲜明),那可老师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筛选呢?我们从可老师自己写的《〈史记〉人物论·前言》可以找到答案:“《史记》,都是从一篇一篇的人物传记开始。写《史记》的文章都是随感、随笔式的,当年随读、随写、随发,并没有个总体规划,……不过回过头来再看,篇目当中,虞舜孝亲、太伯让国、管鲍知己、骊姬害申生、万石君一家谨小慎微等等,题题都关系到或离不开中国人与中华民族思想道德中的美德、恶德或弱点——都与人民大众的精神生活密切相关,可以视作中华民族人性的一个枝叶或侧影。……是有感而发,有话要说,有实际内容。”[4]“有感而发,有话要说,有实际内容”何尝不是司马迁父子选择传主的标准?何为“有感而发”?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听到、感觉到某些生活事实而有所感,这些都是一些活生生的现实中的人和事,而这些人事与《史记》的某些人事有了关联。于是,《史记》里的人和事就有了生命。不读书的樊哙有担当。“樊哙这个人物,不止在鸿门宴上给读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就是后来排闼进谏的行动,也具有动人的光采,那‘排闼直入’的气象,至今还使人想到,他率绛、灌等大臣进去之后,那门准还是忽闪忽闪的。”[5]两千多年来,被樊哙推开的那扇门,似乎还在开合中向后人昭示着樊哙的担当、汉高祖的从善如流、对后人的警示和启发。因为有感而发,就有话要说,因此,可老师说的虽然是《史记》人物,其因缘媒介却是现实的人事。于是在《〈史记〉人物论》中就有了现实的内容,在现实中看到历史人物的影子,与现实生活相对照映衬。这样的扎根于现实的人物研究,具体、生动、深刻,可以给后人启发。后世从《史记》得到做事做人的借鉴,数不胜数,这才彰显出司马迁和《史记》的价值。这样研究《史记》人物是条正路,真正做到了客观、全面、深刻。以李斯为例,可老师肯定了李斯的旷世奇才,也指出其极端自私的品质,从而避免了一般偏重于品德恶劣的片面性。最理想的择人标准是德才兼备,才是不可或缺的。但一般来说,人才不是才高于德,就是德高于才,皆有所偏。李斯属于才高于德一类,才偏高德偏弱,导致德才分裂,致使把一己之利置于天下安危之上,名为秦相,实则秦贼,宁愿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这样客观、全面、深刻的分析,有现实意义。因为站得高看得远,所以立场客观,是非分明,行文自然娓娓道来,激情内敛,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这样的人物研究,不仅读懂了《史记》,读活了历史,还通了古今,悟出了人生。司马迁父子有灵,何其欣慰!
其二,对人心、人性、民族性的探讨。可老师“有感而发,有话要说,有实际内容”更深层的是对人心、人性、民族性的探讨。司马迁是天才作家。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他能够洞彻历史人物的“为人”(某个历史人物是什么人)。司马迁从前代著作中借用了“为人”一词,并有意识地在《史记》中大量使用,据统计有一百多次;而不书“为人”,而实际上表达同样意思的例子更多。这充分说明,在写《史记》的过程中,司马迁对历史人物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说,《史记》是司马迁研究历史人物的结果,《史记》成为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应该与此直接相关。正因如此,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判断十分准确,《史记》对历史人物的品评往往成为定论。司马迁对人性有着十分深刻的了解,所以《史记》才有那样的影响力。以人的本质善恶论人,是《史记》核心的、重要的特点,先做人后做事是司马迁一贯的原则。论事功,商鞅对秦国乃至中国有再造之功,但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并不高,原因是商鞅是一个“天资刻薄人”。相反的,伍子胥的事功虽无法和商鞅相比,但司马迁对其雪耻评价极高:“弃小义,雪大耻”,何为“小义”?何为“大耻”?如果以伍子胥做人做事轨迹探讨的话,我们就会得出与传统观念完全不同的结论:君臣之义为“小义”,不能为父兄报仇、使恶人得到应有的惩罚为“大耻”,雪大耻即为“大义”。伍子胥胸中的一团烈火就是要烧尽肆意作恶的坏人。所以,伍子胥复仇是天下人的事,不是区区小家的个人恩怨,是为“大义”。除恶之义比君臣之义显然要重要得多,所以相比之下,向来被奉为天的君臣关系,就成了“小义”;而如果君本身就是恶之源的话,那就更应该大张旗鼓地除掉除尽。古有借交报仇,伍子胥很可能也想过此事,所以养着专诸;但伍子胥之仇,非专诸之力可报。他复仇的唯一途径就是先隐于野,然后借国报仇。司马迁极力渲染、发挥伍子胥历经艰辛、隐忍十数年,兴吴强吴,借吴报仇,鞭尸三百,终于伸张大义。《伍子胥列传》是《史记》少有的酣畅淋漓之文,展现了司马迁的人性观。《孟子·离娄下》:“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6]2726论述了君臣关系,比齐景公与孔子讨论的“君不君臣不臣”,更加明确。《孟子·尽心下》:“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耳。”[6]2774这仿佛是伍子胥复仇的量身定做,尤其切题。《伍子胥列传》赞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2]3852与孟子的思想一脉相承。《〈史记〉人物研究》挖掘了司马迁和《史记》里的这种对民族性人心、人性的认识,使我们看到中华民族的“心灵史”“人的赞歌”[7]5。
此外,有意识地解决《史记》人物形象研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发表自己的一家之言,也是本书亮点。《史记》中最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无过于楚汉战争,最复杂、精彩的人物形象无过于刘、项二人。对此,历代相关的议论精彩而多,似乎人人有心得,但是没有一篇全面讨论的文章(指现代学术意义上的集中全面的分析论文),虽然原因是复杂的,但分析刘、项的难度也是客观的。《霸王的悲剧——项羽论》《高歌唱大风——刘邦论》二文从历史进程、社会发展的高度落笔,有高屋建瓴、刚健纵横的大气象,都是刘、项人物研究中不可多得的好文、奇文,放在整个《史记》研究史上的刘、项形象研究中,不仅毫不逊色,而且有个性、有立场,特色鲜明耀眼,充分显示出可永雪老师对《史记》、对历史、对人生的全面关照与深刻理解。这样的文章不是靠读死书读出来的,是立足于现实,在贯穿古今、纵横万里、俯瞰人生的视野下,立足于人心人事,在宏观把握与微观体察的反复转换、贯通后的创作。二文既有对文本的深入全面的理解把握,也有对现实社会、人生的深入关照,学以致用,少学究气,贯穿着可老师《史记》人物研究“有为而发”的一贯精神。
二、探本求真
《〈史记〉中的再创作选评》是可永雪老师从史源学角度研究《史记》人物的专书。在考察《史记》材料来源的基础上,把《史记》文与原材料文进行比勘,分析司马迁对原材料文的加工改制。20 世纪80 年代可老师就想把《史记》的史源做一个彻底的清理;20 世纪90 年代发表的《史记上溯性比较论说》(《天人古今》1994 年1 期),可老师提出《史记》上溯性比较研究的思路并设计了具体方案。此书即是四十多年来这个想法的尝试。笔者有如下几点体会:
第一,这是可永雪老师自20 世纪80 年代初到现在,对《史记》上溯性比较研究的成果结晶。
《史记》成书是一个把经传子史等各种性质不同、体例各异的著作,按照司马迁自定的体例,融会于一炉的过程。据统计,司马迁所据书达106 种之多,而实际上多于此数。这是前无古人的壮举,也是千古文章的盛事。郑樵《通志·总序》赞《史记》为“会通”之作。但“会通”是一个非常复杂对史料鉴别、取舍、增删的过程,绝不是简单地抄录。在“会通”的过程中,司马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史记》上溯性研究也因此产生。
扬雄许《史记》为“实录”[8]163,又斥其“以多知为杂”[8]413。班彪父子也是既赞司马迁为“良史之才”,又责其“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9]1325等不足。今天看来,这都是有见地的观点。此后,《史记》的史源学研究进一步展开。“三家注”可谓这方面第一次集中的研究,注释中有较多《史》文与原材料异同的比较及其得失的说明。《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四“类书类”著录南宋倪思《迁书删改古书异辞》十二卷:“以迁史多易经语,更简易为平易,体当然也。然易辞而失其义,书事而与经异者多,不可无考,故为是编。经之外与他书异者亦并载焉。”[10]431可以看出,此书当是一部专门研究《史记》采用前人材料、语言等问题的著作,可惜亡佚,其详难知。明代凌稚隆《史记评林》在前人基础上,对《史记》与其所依据材料的异同得失多有比勘说明。清代考据成风,相关研究更多,如钱大昕《史记考异》、王鸣盛《史记商榷》、崔适《史记探源》等。其中成就最大者为《史记志疑》,梁玉绳将司马迁援引参考的材料与《史记》印证,以见《史记》史实可靠与否。这些著作的成就主要在史实考订上。
近现代以来,这一研究沿着古人的路子,继续推进。特点有二:一是见解散见于注释中。如日本人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此书在基本竭尽《史记》材料出处的基础上,于注释中也涉及上溯性比较的说明。此外,《史记》取材诸书如《尚书》《国语》《左传》《战国策》等的注释中,也有《史》文与其素材异同的说明。二是《史记》与其素材诸书关系的宏观探讨,并有专书出版。如刘师培《司马迁〈左传〉义序例》《司马迁述〈周易〉义》(《刘申叔遗书》凤凰出版社1997 年版)、阮芝生《太史公怎样收集和处理史料》(《书目季刊》1974 年第7 卷第4 期)等。特别是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 年版),对司马迁使用的各种典籍,加以探讨,对考察《史记》上溯性研究很有参考价值。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史记》上溯性研究又一次受到重视,研究向更加深细迈进。如台湾有顾立三《司马迁撰写〈史记〉采用〈左传〉的研究》(台湾正中书局1980 年版)、古国顺《〈史记〉述〈尚书〉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5 年影印版)、周虎林《〈史记〉著述的过程》《司马迁与其史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 年版);祖国大陆有陈桐生《〈史记〉与今古文经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年版),赵生群《〈史记〉编撰学导论》(凤凰出版社2006 年版)等,研究者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主要从宏观上探讨《史记》取材方式,较前人成果更加细致深入。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以编年的方式对战国史料进行了全面的罗列、分析,不仅使《史记》战国史源一目了然,也对研究史上一些有争论的疑难问题的解决有帮助。韩兆琦《史记笺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新材料,于注释中也涉及较多上溯性比较。日人藤田胜久结合出土文献,从《史记》原始史料的性质,探讨《史记》史源。出版的专著有:《〈史记〉战国史料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版)、《〈史记〉战国列传研究》(日本汲古书院2011 年版),是对《史记》战国史料的别开生面的研究。
值得重点提出的相关论文是孙钦善、易宁等的文章。孙钦善《〈史记〉采用文献史料的特点》(《文献》1980 年第2 期)以《史》文与原材料对比,全面说明司马迁采用史料的特点。例证典型而又高屋建瓴,从内容到思路、方法都可目为相关研究的经典文章。易宁《〈史记·鲁周公世家〉引〈尚书·金滕〉经说考论》(《中国史研究》1998 年第3 期)、《〈史记·殷本纪〉释〈尚书·高宗肜日〉考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4 期)、《〈史记〉载“高宗亮阴三年不言”考释——兼论司马迁叙史“疑则传疑”》(《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6 期)等文章,都从具体事例探讨司马迁对史料的采用,可以视为《史记》上溯性研究的典型案例。
从史源学视角考察《史记》文本特色,是认识《史记》文本特征的恰当切入口。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出,哪些是司马迁在前人基础上的加工改制,其加工改制的结果如何等等。说白了,可直接看出《史记》中,哪些是司马迁自己的,哪些是别人的。这无疑是理解《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最直接明了的方式。
可永雪老师的相关研究立足于前修时贤的研究成果,开辟出自己的路子,其特色就是在对读、比勘《史记》文与原材料的基础上,再分析其异同的实证研究。在1980 年《语文学习》(上海)第4 期发表了《〈史记〉〈战国策〉对照举例》[11],详细分析《史记》文与《战国策》原文的关系;在《史记上溯性比较论说》(《天人古今》1994 年1 期)一文中可老师提出《史记》上溯性比较研究的思路并设计了具体方案。《〈史记〉文学性界说之实证》[12]对照了《战国策》有关甘罗的故事和《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中的甘罗故事,通过对比《战国策·秦策五·文信侯欲攻赵以广河间》“文信侯叱去曰”[13]459与《樗里子甘茂列传》“文信侯叱曰:‘去!’”[14]2319说明,如果司马迁不是处于“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的状态,是不会注意到人物口吻的细节,自然也写不出这样与造化争奇的句子。这些表面看起来的一字之差,似乎区别不大,仔细分析却神态迥异的例子,很能表现出《史记》文与原材料文的异同。以往学者遇到类似问题,一般都以为是《史记》流传过程中传抄所致。经过可老师的分析,让我们感觉到有些可能是传抄所致,有些可能不是。之后可老师又有系列专论,如《〈吕氏春秋〉与〈史记〉关联微探》[15](署名洁芒)、《〈国语〉八论》[16]、《〈史记〉与〈国语〉的上溯比较研究》[17]等。可见可老师对上溯性比较研究,既有具体方案的设计,也有大量的具体实例支持,思路系统、成熟。此书便是可老师多年相关探讨的小结,也是可老师研究初衷的体现。
第二,可永雪老师在史源学比较的基础上,提出“再创作”理念。
《史记》所依据的主要原材料,如《国语》《左传》《战国策》等皆为集文史于一身的名著,却无“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之誉;《史记》得此殊荣,其故何在?我们以为其重要原因在于司马迁在使用材料的过程中进行了文学创作。因为这些文学创作以一定史料为基础,与一般天马行空的文学创作不同,可老师将其名为“再创作”。
从《史记》研究史看,文学再创作也受到研究者的注意。如《史记会注考证》常以诸如“史公以意敷衍”的话,说明《史记》文与原材料文的异同,但仅仅是点到为止,而不作具体分析。钱钟书《管锥编》在分析实例的基础上,以“笔补造化”等语评价《史记》的文学价值,指出《史》文与原材料文的不同。实际上,学人对《史记》中的文学创作认识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发现《史记》的文学性质。《史记》具有十分浓郁的文学性,但《史记》一直是以史学成就引起人们的重视。对其文学性质的认识相对较晚。真正现代意义上对《史记》文学书写的认识应该在宋代。《史记评林·高祖本纪》引南宋魏了翁评论高祖还乡:“后世为史者,但云‘还沛置酒,召故人乐饮极欢,足矣。看他发沛中儿,教歌,至酒酣击筑,歌呼起舞,反转泣下,缕缕不绝。古今文字淋漓尽致,言笑有情,安可及此!”[18]148-149魏了翁清楚地指出一般的历史书写和文学书写的区别。之后,学人们将这种现象叫作“增润”“意趣”“以意敷衍”“附会”“笔补造化”等。
第二阶段,将《史记》的文学性质定性为文学创作。元明清以后,随着戏曲、小说的日趋繁荣,学者们对《史记》的文学创作有了更深的认识,并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代表人物有李开先、茅坤、金圣叹等。如茅坤论述《史记》写人时说:“今人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若此者何哉?盖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故也,而固非区区字句之激射者也。”[19]196《史记》的艺术魅力源于“盖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即司马迁对所写的历史人物了然于心,所以笔下可以自由挥洒(“肆于心”),茅坤强调的是《史记》有些内容生成于文学创作状态之中。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学来,虽是史公才高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却不然,只要顺着笔性写去,削高补低都由我。”[20]29金圣叹真不愧是天才文学批评家,眼光独到,理论色彩浓郁,表述准确生动,认定虽然“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但有没有阻止司马迁的“顺着笔性写”。这是人们熟知的层次更高的“戴着脚镣手铐舞蹈”,这实际上就是可老师提倡的“再创作”。此外如周亮工、姚苎田、郭嵩焘等也多有极好的分析。
第三个阶段,《史记》文学研究的开启。现代学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史记》文学创作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最有代表性的是鲁迅先生《汉文学史纲要》概括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是可与《离骚》并列的诗,标志着现代学人对《史记》文学创作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之后,李长之先生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具有评传性质,其最大贡献是对司马迁的诗人气质(此前人们皆以史家看司马迁)、《史记》的抒情性作了前所未有的剖析论证。从而开启了《史记》史学研究之外的文学研究。之前,《史记》文学研究一直附属于史学研究,至此,《史记》文学研究成为独立的研究方向。这也是当代《史记》研究的主要方向。
上述对《史记》文学性的认识概括起来有三点:(1)司马迁在写《史记》的过程中常常处于文学创作状态,从而创造出文学作品。(2)《史记》文学创作生成的方式是“以文运事”。(3)司马迁的诗人气质、不凡的阅历使《史记》成为文学作品。这些是可永雪老师提出“再创作”理念的基础。
20 世纪80 年代,可永雪老师《从〈伍子胥列传〉看〈史记〉再创作的特点》[21](署名洁芒)提出了《史记》的“再创作”。他认为《史记》里有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作与一般的创作不同,是在相关传世典籍基础上的创作,所以叫“再创作”。这个理念契合《史记》的实际。《〈史记〉文学成就论稿》(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1 年版)专设一章,结合一些典型案例,从何为再创作、再创作的基本面貌、主要特点三方面进行论述。《〈史记〉中的再创作选评》脱胎于以上诸相关研究而独立成书,所重在《史记》文本与其史料文本的比勘对照,可以看作《史记》再创作研究上的奠基之作。
“再创作”是文学创作中的普遍现象。“再创作”简明准确地概括了《史记》中的文学创作特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司马迁编撰《史记》的基本方法,“再创作”在司马迁撰写《史记》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是《史记》的成书方式。这一概括既有其历史渊源,也有理论色彩,准确地解释了《史记》的文学性及其来源。《〈史记〉中的再创作选评》,虽是“选评”,但因其所选典型,有代表意义,再现了《史记》的“再创作”特征。另外,此书直观的体例给人的启发是多方面的,如上溯性研究之外,还可以从语言学、训诂学、史学等等不同学科得到启发。
“再创作”提出于20 世纪80 年代,之后可老师又多次发表文章论证分析,在公开场合也屡屡倡导呼吁。但是,无论从司马迁的夫子自道,还是从《史记》的客观实际看,“再创作”是《史记》里的客观存在,相关研究源远流长,是不容忽视的。学术研究本可以多种多样。与上述史源学研究成果相比,《〈史记〉中的再创作选评》路子独特,是有特色之作,是可老师的“《史记》文学论”[22]184,如果后有继者,则此书具有开创之功。
三、如何评价《史记》的写人成就
《〈史记〉中的再创作选评》《〈史记〉人物论》是继承与创新的结晶,促人思考、给人启发。《史记》人物研究是可永雪老师主要的学术成就与贡献所在,这方面的评价已经不少。最关键的问题是:站在学术研究的高度,从学术发展的视角看,可老师的研究能给我们什么启发?《〈史记〉人物论》是沿袭传统而来,其主体来自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成就在学术界早有公论;《〈史记〉中的再创作选评》发轫于20世纪80 年代,但成于近年,可谓最具创新价值,是可老师一生学术的新高度。如果我们把两部著作结合起来看,前者可以看作是后者的基础,后者可以看作是前者的深化。这深化表现在诸多方面,其核心是:《史记》人物成就怎么来的?可老师的结论是:司马迁站在巨人肩膀上取得的。既然如此,这里是不是就存在“巨人”的成就和司马迁的成就的区分问题?也就是说,巨人的成就在哪里,司马迁的创造在哪里,是需要说明的。这也是可老师研究“再创作”的目的与基本思路,《〈史记〉中的再创作选评》就是这个思路指导下的“选评”。所以叫作“选”,乃非全体之谓,可能离“全体”还差得远;“评”乃谓研究还处在探索阶段。对此,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理解:一是研究不易,有难度,难度不仅仅表现在工作量大,更难在高下优劣的品评。第二,这种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应该有很大的研究的空间。第三,只有“再创作”的问题彻底清楚了,即清楚了“巨人”者何在,司马迁者何在,真正的《史记》文学成就才算彻底搞清楚了。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审视一下当下相关的认识,就会发现其模糊性。以写人成就为例,准确地说,《史记》的人物基本上是在前代及当代相关著作、史实的基础上写成的。也就是说,《史记》的写人成就并不是司马迁的独创,而在大量已有成果以及现实基础之上而成,司马迁创造之处,可老师名之曰“再创作”。先秦人物且不说,就是当代的人物,也是如此。比如最著名的项羽、刘邦等形象,最著名的“鸿门宴”等故事,就是在陆贾《楚汉春秋》基础上写成的。因此,准确地讲,我们说项羽、刘邦等形象是司马迁塑造的,就失之笼统;说他们是司马迁在陆贾《楚汉春秋》基础上塑造而成的,才是准确的。但是,目前论述到《史记》的写人成就时,往往不提前人的成就,从而造成错觉,以为《史记》的人物形象是司马迁一人之功。这显然是一种误导,是一种不负责甚至不科学的说法。影响比较大的若干文学史及其相关论著,一般都是从写人成就、语言特色等方面大谈特谈《史记》的文学成就,可以说是抓住了《史记》文学成就的基本方面。但这些书没有“《史记》成就怎么来”的思路。有鉴于此,笔者认为这类教材即使不做专门小节,也至少应该有一定篇幅的相关说明。说明要有总说、有举例、有总结,要以给读者留下较深印象为原则。
《〈史记〉的再创作选评》虽然选定篇章有限,但通过它设定的体例,就把什么是司马迁自己写的,什么是承袭前人的,很直观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把这个问题解释得清清楚楚。这样做的目前学界还只有九十老翁可永雪老师一人而已。可见其学术研究的“求真”精神,老当益壮,老而愈健。
可永雪老师笔耕不辍,对此二书付出的辛劳巨大。《〈史记〉人物论》虽在已有成果上修订而成,但也吸收了新成果、新体会,有的是近年成篇的。上溯性比较研究在《史记》研究诸子目里相对较难,工作量巨大而细致,费时费力,短时间内难以奏效。按照可老师的思路与研究方法,通过《史记》文与原材料文的逐字逐句的对照比勘,比较出《史记》文与原材料文的异同,由此看司马迁的“再创作”。
艺术来源于生活,没有对生活的观察体验,就不能很好地理解艺术。艺术又高于生活,没有对艺术的深入了解,就悟不出艺术反映生活的深广度。可永雪老师认为,在《史记》中,司马迁有两种身份:有时是一丝不苟的历史学家,有时又是充满诗情和想象力的文学家,集历史学家和诗人于一身。[12]《史记》是“实录”,而司马迁在“实录”的过程中往往带着理想,进入历史人物的心理世界,《史记》又超越“实录”,成为艺术。因此《史记》既忠于现实,又具有历史穿透力。可老师是通过对生活的深入体察,有为而发,准确地把握了《史记》在“实录”和艺术上的成就。《史记》的成就是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取得的,不了解何为前人的成就,何为司马迁的成就,也就不能很好地把握司马迁的创造力和《史记》的思想、艺术方面的高度;只有对前人的相关成就了然于心,才能看出司马迁的创造,才能看出《史记》的成就。从这两方面看,可老师研究《史记》之路,可以概括为“有为而作,探求本真”,将读书与生活相关联,用书本观照现实,用现实读懂书本,这很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