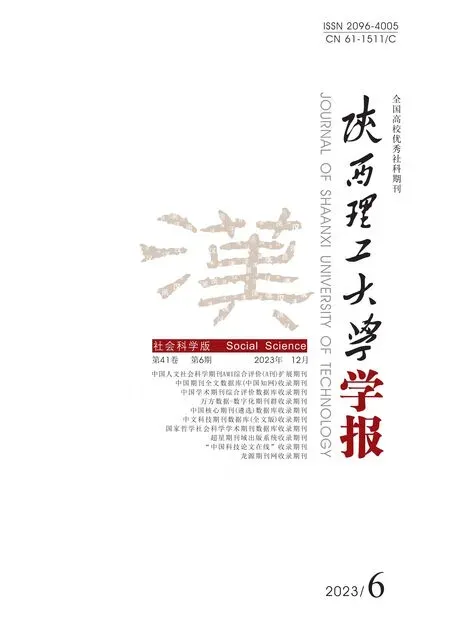“圣人礼禁”与“身国同构”
——《管子》身体政治论研究
杨滢桐, 刘耘华
(1.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234; 2.复旦大学 中文系, 上海 200433)
《管子》是指导君主治国理政的重要著作,内容丰赡,主要论述了君主设立官职、建立法度的具体措施和礼仪行禁。《管子》论政以“身国同构”为主要内容,属“身体政治论”[1]341范畴。已有学者对此做出解释,如张丰乾将《管子》中的身体与国家置于“身、家、乡、国、天下”的关系序列中思考二者之间“不可为”的界限[2]、来永红则以《管子》为例论述道家心、身、国同治的思想[3]。遗憾的是,这类相关研究重视对理论、现象的分析,对《管子》中“身国同构”的特点及实现路径却未作深入阐发。
《管子》身体政治论以“身国同构”为基础和主要内容,在身与国通过类比建立起的同构关系基础上制定政治政策。“身国同构”在天人感应背景下进行,以圣人身体为核心、以“圣人礼禁”为主要手段。但“圣人礼禁”具体如何加强“身国同构”,以及在此过程中身体这一概念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则是本文需要探索与回应的相关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可以还原出《管子》“身体政治”理论中身体如何同政治发生联系,并进一步思考身体参与政治后依然得以保持自身独立意涵,却将政治赋予了身体化色彩的原因。
一、 “圣人礼禁”:身体与空间的交织
“礼禁”意为礼仪与禁制,“礼”指“礼制”“礼节”与“礼义”[4]74。《管子》主涉“礼制”(张连伟[5]与郭丽[6]所论《管子》的“礼”实为“礼制”)。《管子》将“礼”与“法”结合,以“法”的形式固定礼仪的具体要求,因此《管子》中的“礼”强调制度的制定与遵守。与“法”结合的“礼”与“禁”实为一体两面,例如“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7]4004,就指出“礼”有禁忌义但此义隐而难见。因而,《管子》论“礼”有并重“禁忌”义、偏重实用且兼顾制度风俗的特点,本文以“礼禁”指称。
《管子》中提到的“礼禁”既用于圣人也用于普通百姓,兼有本义及引申义[8],其中更侧重于强调用于普通百姓的实践意义。因《管子》“君王南面听天下”之要旨,在具体论述中,“礼禁”以圣人为线索,规范圣人行为并以圣人的行为为标准规范民众行为,所以“礼禁”其实是“圣人礼禁”。“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9]7说明“礼”的意义指向行动。而“禁”即禁止,表示行动的暂停,“礼”与“禁”都是对身体动作的规范,所以“圣人礼禁”是对圣人身体的规范。就此意义而言,“礼禁”是身体性的概念。在《管子》中,圣人的行为以天人感应为背景,圣人的目的是汇通天人,“圣人礼禁”的目的也是加强圣人与宇宙的感应,这种感应是身体性与空间性的结合。
(一)以身体为中心的空间与作为普遍空间的“宇”
“圣人礼禁”作为身体性的行为之所以能加强圣人与宇宙的感应,缘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空间”概念是身体性的。空间封闭循环,无绝对坐标和维度,处于变化之中。各种学说在空间中建立坐标系,多数时候,坐标系的“中点” 以“说者的眼界为起始点”[10]126。也就是说,在身体出场前,空间无中心,没有绝对固定的“中”的概念及由它划分出的维度。于是空间以身体为中心构建,“切分空间这一循环的事物依靠判断坐标。先民的空间坐标是人的身体,人以自己的身体为中心感受和判断空间”[11]。具体而言,可以依据“说者”或“说者”的对象(通常是统治者)的身体为中心构建出一个相应的空间坐标。在说者的论述中,空间是一种位置关系,它强烈依赖语境赋予的“中心”,也随语境而变动。
不同的语境产生诸多不同的空间,这些空间以共同想象的更大普遍空间——“宇”为最高规范。《淮南子·齐俗训》曰:“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12]798,可见“宇”的范围更加广阔并且有一个隐含的中心。“宇”的存在确定了“东南西北”的定义——“人们最早就以日出日落为判定东西方向的依据……后来又以星辰来判别南北方位,天空中一切都在向左旋转,但有一个永恒不动的地方,那里的一颗星辰就是北极星,当然相反的方向就是南方”[13]22。通过观察“宇”,先民确定了判定方向的普遍标准,以在“宇”中位置恒定不动的北极星固定了“宇”的方向划分逻辑,“宇”被认为是最普遍意义上的空间。对“宇”的认识深刻影响了人们对身体性的空间的认识,进而影响了其对其他概念的认知。
(二)空间性的圣人建筑与政令
“圣人礼禁”涉及服饰、居住、饮食、政令颁布及方向,在《管子》中《幼官》《四时》《五行》等篇目的具体论述中均体现出先民对空间性的重视。
《幼官》以文字性的图示反映“圣人礼禁”的具体细节。对《幼官》题义,何如璋等学者认为,“幼官”是“玄宫”的误传[14]104,本文采此解。另一解释指出“幼官”是祭官,“幼官图”是为官方祭祀及相关生产、政教活动而绘制的图式[15]33-40。这两种解释都说明了“幼官”于祭祀、政教和天人感应的重要性。玄宫是宇宙形式与政治人事结合的典型,玄宫的选址、朝向都模仿宇宙,它因是圣人居所而与政治联通,并在后续实践中形成了有象征意义的传统。《幼官》这一题目喻示了圣人建筑与政治密切关系。
《幼官》文本主要体现了政令与空间的关系。马思劢、郭鼎玮指出《幼官》的文本结构可分为内外两层, 其中最早的文本被分为四部分以与四时相配[16],内外两层文本又共用一个框架,即“中、东、南、西、北”。作为一篇旨在为统治者提供政令指导以规范民众生产的文章,《幼官》采用一种空间性而非与生产关系更为密切直观的时间性的划分标准,这看起来与文章主旨有所偏离。
事实上,《幼官》的这种将时间与空间做出明确对应的论述方式传递了更丰富的信息。就文本内容而言,《幼官》明确地以春夏秋冬为时间节点并以此作为指导民众生产和规范君主行为的原则:
“春行冬政,肃。行秋政,雷。行夏政,阉。十二,地气发,戒春事。”“夏行春政,风。行冬政,落。重则雨雹。行秋政,水。十二,小郢至,德。”“秋行夏政,叶。行春政,华。行冬政,秏。十二,期风至,戒秋事。”“冬行秋政,雾。行夏政,雷。行春政,烝泄。十二,始寒,尽刑。”[17]130、133、135、137
结合《幼官图》,这些时间节点与方位一一对应:除了中方图,东南西北方图各对应春夏秋冬四季。通过以春夏秋冬为基点的四分,《幼官图》详述了与具体日期对应的农事政令,《四时》中也出现了类似情况。时间节点由空间转化,这是“观象授时”观念的表现。中国的四时依空间(天文)而定而非更大的时间概念:“帛书下文言四子‘步以为岁’,也以步算之法度四时。故步即步算,‘步数’意即步算天数。天数即历数,乃周天度数……”[18]20。“观象授时”概念对农业的影响非常深刻,空间的划分使时间的划分成为可能,也使因时而作的农业成为可能。
(三)服饰:模仿宇宙的身体的外延
服饰是身体的外延,文明时代的服饰是文化与身体的交互界面,既是身体的又是文化的。服饰是皮肤之皮肤,是身体的表达与外显,是“礼禁”作用于身体的结果,是文化化的身体。
作为圣人身体的外延,圣人服饰与季节的联系非常紧密,间接呈现出空间性。在《幼官图》中,这种表现尤为明显——在中、东、西、南、北方本图中分别出现了对时节的说明和对圣人服饰的颜色要求。同时,《管子》认为旗帜也可作为君主服饰的延伸:“选为都佼,冒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威也”[17]542。君主服饰的颜色与旗帜颜色一致(中方本图未提及),同样是东—青、西—赤、南—白、北—黑。这样的规定应是受到四方神信仰的影响,先秦有“五方木”,是代表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的神木,四神正是其中的青、赤、白、黑四木,即代表东、南、西、北四方的木神[11]。《管子》文本中的“黄后”“青后”“白后”“赤后”“黑后”指黄帝、青帝、白帝、赤帝、黑帝[14],分别对应五个方位圣人服饰的颜色。同时,《管子》中也有颜色与空间直接联系的例子,如《轻重己》:
“冬尽而春始。天子东出其国四十六里而坛,服青而絻青……春尽而夏始。天子服黄而静处……秋至而禾熟。……西出其国百三十八里而坛,服白而絻白……秋尽而冬始。天子服黑絻黑而静处……”[17]1111-1116
虽然夏季服黄的规定与《幼官》和四方神略有出入,但总体而言依旧属于这一体系。这种对应关系的形成可能与上古先民对空间颜色的直观感受有关:日出东方天空青紫、正午偏南太阳赤红、傍晚太阳西斜时阳光泛白、太阳沉落后一片黑暗[11]。种种对圣人服饰颜色的规定都暗示着圣人身体的政治意味。圣人身体与宇宙的联系依靠各种经验性的传统理念,又在对规定的重复遵守中不断加强。圣人身体与宇宙的关系既是历时的又是共时的。圣人建筑和政令颁布也昭示出明显的空间性,它们的共同意义来源是宇宙,圣人身体是将宇宙与政治、人事联系起来的枢纽。
①类比推理是指根据两个或两类对象在某些属性上的相同, 推断出它们在另外的属性上(这一属性已为类比的一个对象所具有,另一个类比的对象那里尚未发现)也相同的一种推理。具体可参见刘畅的《心君同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种原型范畴分析》一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二、 “圣人礼禁”对“身国同构”的具体摹写:多重回返的机制
圣人身体在天人感应的背景下与政治互动,巩固“身国同构”。《管子》通过“圣人礼禁”摹写“身国同构”,这是一个涉及宇宙、圣人身体、圣人建筑及政治的多重回返的复杂机制,其目的与结果是巩固圣人的权威。
“联系性思维方式”[1]314是“身国同构”实现的前提之一。中国思想自古以联系性思维理解事物,事物与事物之间总是通过各种方式连结,所有事物都处于复杂交织的关系网络之中,所有的网络最终都可回溯至宇宙。对作为普遍规则的宇宙的摹写是“身国同构”的背景和前绪。“构成天、人的诸多因素之间,常常是通过类比的方式而建构其关系(共时的空间并列关系)的。”[19]类比思维与阴阳思想、《管子》气论结合,影响了《管子》的政治理论。“类比推理”①实现了身国同构的前绪及过程:通过增加、重复、强调“身”与宇宙在某些具体属性上的相同,使“身”获得来自宇宙的神圣性与权威,“国”通过模仿“身”间接获得权威。这一过程中礼禁是重要的实施手段,礼禁确认和展现了圣人观察、体验“天”的结果。
(一)圣人身体空间向宇宙的嵌合
《管子》认为,圣人通过自身修炼使气存于身体,由此,圣人身体获得在人世的至高权威。相应的,圣人身体空间也天然保有权威。对圣人而言,修炼是将自身空间尽量延展,以拓展至宇宙的范围,将自身空间嵌合进宇宙。《管子》指出要将身体修练至“穷天地,破四海”的境界才能称为圣人。“穷天地,破四海”指自身空间的延展,贯穿这一过程的是精气——精气起初在身体内部,通过圣人的修炼蕴养,外放后到达更广阔的范围。与此一致的还有《心术下》提出的“神莫知其极”。“神”是精气的一种形式,圣人修炼后的“神”,由圣人发出,带上了圣人的属性。“神”能认识到什么程度,圣人身体空间就能延展至什么程度。《内业》云:“人能正静,皮肤裕宽,耳目聪明,筋信而骨强。乃能戴大圜,而履大方,鉴于大清,视于大明。敬慎无忒,日新其德,遍知天下,穷于四极。”[17]726首句强调身体对修炼的重要性以及修炼对身体的要求。第二句表述圣人参于宇宙,具有体察万物和道的能力。第三句描绘圣人持续修炼,将身体空间延展至宇宙边缘的状态。圣人身体空间构建之初是纯粹躯体性的,它以圣人身体为中心。在修炼过程中,具有精神与躯体双重属性的圣人身体逐渐被赋予空间认知能力。圣人的“神”体察到的范围都成为圣人的身体空间。通过提高“神”的认识能力,圣人身体空间得以延伸。身体空间构筑之初依赖于可触形体,在修炼过程中又转变为识知空间。随着圣人的修炼,圣人身体空间获得神圣性。
(二)空间性的“身国同构”:以圣人建筑为中介
“圣人礼禁”是对有限时间与空间的延伸,目的是调整自身位置以适应天地[20]278。圣人身体通过改变服饰及行为以模仿宇宙。关联性思维通常在宇宙领域与现实秩序方面构建起系统的对应关系,例如人体本身、政治身体与宇宙身体之间……[21]1。对先民而言,宇宙以及它所包含的星辰位置关系等是天道最直接原始的体现。以北极星为中心划分出的东西南北四向及据其衍生出的历法对古人的农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古人对天象物宜的观察逐渐秩序化为一种理性的认识,这种理性的认识直接反映于政治人事。圣人希望通过摹写宇宙获得神圣和权威,从而使他的身体空间也保有权威,然而圣人身体空间注定无法长久地保有这种权威。宇宙的权威在于其固定性,而宇宙的固定性在于中心即北极星的固定(这种固定不指作为实在的永恒不变,而指位置关系的固定,即它对于观测者而言位置是固定的)。但这里我们所指的身体必定是活动的——这是圣人得以遵守礼禁的前提。于是,一方面圣人需要活动身体以遵守礼禁;另一方面,正是身体的活动使圣人无法摹写宇宙的固定性致使他无法长久保有权威。“动”意味着变化,也与君主所期望的自身政权的恒久相悖。为了调和这个矛盾,明堂、玄宫等一系列圣人建筑被引入了摹写系统。
圣人建筑建造之初便因其与圣人的密切关系而初具权威。也就是说,圣人建筑是对圣人身体空间的转喻,这是“身”与“国”最初的同构(1)王健文认为“国君一体”的完整意义在时空两重意义的交叠之上,其中作为其时空意义的“诸侯世”依赖于政治家族的血缘。具体可参见王健文《国君一体——古代中国国家概念的一个面向》一文,摘选自杨儒宾编《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气论及身体观》,巨流出版社,1993年版,第241页。但这方面观点在《管子》中并无表现。。“国君的宗庙的空间象征意义,又扩而及于国……国君以国为体,是在空间上构成的一体关系”[22]113,通过转喻,圣人身体空间与宇宙的同构关系固定下来了。圣人生命短暂,圣人建筑则成为较为长久的政权象征。此消彼长之下,圣人建筑获得更多权威。圣人通过与普遍宇宙建立同构关系而获得的正当性与权威连同身体空间至圣人建筑的转喻一起被转移了。至此,政治本身比圣人获得了更多的权威——虽然这个权威的获得大多来自圣人的身体行动。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圣人所期望的。在此状况下,圣人想要保持自身的权威并分享政治累世沉淀的权威只能同时摹写宇宙和圣人建筑,约束自己的行为,这就是“圣人礼禁”的作用。
(三)“身国同构”的具体实现方式:政治对圣人身体的摹写
“身国同构”的另一种实现方式是通过国家政治摹写圣人身体,这是具体、显象的实现方式。诸子思想都有政治目的,皆是为了实现对人民生产生活的整体安排,这种整体安排不仅是社会的,而且是宇宙的[23]12。在《管子》中,这种“宇宙的”整体安排通过摹写圣人身体实现。政治对圣人身体的摹写主要在于官职的设立和政令颁布。“身”是一个意涵丰富的“象”,当它与“国”相联系时,含义向躯体倾斜。“国”的概念在身国同构中也向“身”靠近。《说文》训“国”:“国,邦也,从口从或”[8]129。段玉裁云:“周礼注曰。大曰邦。小曰国。邦之所居亦曰国”[24]277。而“邦之所居亦曰国。此谓统言则封竟之内曰国曰邑……古者城所在曰国、曰邑。而不曰邦。邦之言封也”[24]283。可知“国”是一个地理空间层面的概念,邦所统治的版图为国。在《管子》中,“国”又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的概念被论述,它在参与论述之初即同时带有空间性与政治性。
《管子》中国家与身体的同构关系主要落实于国家对圣人身体的摹写与同构。政令摹写的直接对象不是天道而是圣人身体。圣人的权威来源于其唯一的、直接摹写天道的权利。政令不能越过圣人与天道直接联系,否则这将是对圣人权威的瓦解。政令与天道的联系依赖作为介质的圣人,三者共同形成了一个权威的转移链条。
《管子》认为,君臣应各有其分,主张圣人无为的同时认为臣子必须尽职,这种观点的表达依靠对圣人身体的比附。将心与国君做比是中国传统思想中常见的现象。《管子·心论》详述了“心”统领身体的稳固权威,指出承担大部分工作的各器官应服从心的统治、辅助心管理身体。通过类比,《管子》提出对圣人与臣子的要求,并以身体的康健类比国家的治理状况。《管子》的“身国同构”思想以身体类比国家、政治,着重强调了官的地位与作用,同时表达了君主无为的政治思想。
在“身国同构”机制下,国对身的影响是回返的。在圣人身体与国家的同构关系中,礼禁不仅规范着圣人身体也在类比中被迁移至政治。《管子》指导圣人通过礼禁确立社会层级,如“是故能象其道于国家,加之于百姓,而足以饰官化下者,明君也。能上尽言于主,下致力于民,而足以修义从令者,忠臣也”[17]498。被严格规定的社会层级,从上至下依次是君主、官爵、民众。这种划分与《管子》中按照与天道的亲疏关系对身体各部分的等级划分一致。心统领身体,四肢五官是身体的重要部分,地位次心一等,皮毛则少有谈及,地位最次。圣人与天道联系最紧密,居最上等,官爵次之,居次位,以此类推。这种等级划分的意识来自于宇宙。“作为‘空间’的宇宙,在殷周人心目中投射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深层意识,即以中央为核心,众星拱北辰,四方环中国的‘天地差序格局’”[13]53,所以它成为被大多数人认同的普遍意识。在生活中,这种普遍意识是隐形的。因为圣人强调自己对宇宙的唯一解释权,所以他以自己的身体为模板将这个等级意识显现出来以供政治模仿并建立法度。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是“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17]623其中所提及的“道”的根本是来自于宇宙的权威。
《管子》将等级视为统治的必要手段。对等级的遵守突出表现在服饰上。《管子》对不同等级的社会层级规定了不同的服饰规范,如“度爵而制服……衣服有制,宫室有度……散民不敢服杂采,百工商贾不得服长鬈貂,刑余戮民不敢服絻……”[17]63-64于是,《管子》的政治策略又回到了身体层面。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复写的主体是民众的身体。与圣人的身体不同,民众的身体是被支配的对象,它被定义为最边缘的环节,但实际上,正是通过对民众身体的支配,圣人的权力得到巩固。
这一过程造成双向的影响:一方面圣人以自身身体为模版制定政策、划分等级,使社会中的所有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另一方面民众、官员对这种等级的遵守使这一等级划分更加牢固。摹写圣人身体的政治礼禁的制定与被遵守带来了回返的影响,使居于等级最上层的君主获得了权威。
三、 政治视野下的圣人身体:枢纽与复合
“从角色理论而言,个体的人可分属于自然、社会关系及政治社会等单位……但由于对‘身’的过分强调,‘身’就不仅表现为政治的枢纽,同时也是自然和人伦等一切外在世界的枢纽,即在‘身’之中体现主、客的同一律。”[25]192-193圣人身体是自然社会与政治社会的桥梁,处于“天—人—政治”关系网络的枢纽位置,同时也是宇宙、理想身体与政治摹写对象的复合体。在《管子》构建的整体宇宙图式中,圣人身体不再是被支配的个体,而成为了唯一积极的主动者、一切具体行为的起点。
“人能偶天地,故能参天地。偶者成对也。人如何与天地成偶,乃因人副天地之数与象。而所谓‘副’,用现代的语言来讲,可说人是天地的一个副本。”[22]31这种对应依赖于身体的空间性,身体的空间性在于身体的“形”。《管子》不仅借助“形”描述外于“身体”的他物,也同样用它指示身躯。前者的相关论述展现出《管子》对“形”的认识依赖于视觉与空间,如《管子》将“形”与“色”连用以描述视觉层面的事物的外形。后者主要用于区分完备的身体与肉体。这反映出《管子》对身体的认识:身体与“形”的关系复杂,它既不是完全的“形”,也无法脱离“形”而存在,在“形”层面与宇宙应和的身体是身体作为宇宙副本的基础。天地贯通一气,则万物同宗,肉体由形气生成,才有了身与宇宙相类的可能,这是《管子》论“身”的思路。先天精气降于身体形成心,心能吸引后天精气继续修炼,人与天地同构,所以人能参悟天地,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后续论述得以成立。
《管子》提及了两种“身体”,普通人的身体和圣人身体。圣人身体以普通人的身体为基础修炼而来,这种修炼兼顾肉体与精神。《管子》对修炼论述颇多,认为在修炼中作为“道”的具象的“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精存自生,其外安荣……心全于中,形全于外,不逢天灾,不遇人害,谓之圣人”[17]726。“精”既是普通人修炼成圣人的法门,又体现着圣人的状态。这里的“精”具有自我生成的能力,身体对于“精”而言并非必要,但“精”对于修炼中的身体则至关重要,它不仅是“全心”也是“全形”的条件。结合对“精”的定义——“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17]721,可见,无论是具体修炼方式还是圣人礼禁的要求,相较于“道”,“身体”处于被动地位。圣人身体的意义在于它在被动的基础上获得了主动性。这种主动性肇始于修炼之初。普通人的身体已经完备康健,所以修炼之于身体并非必须。圣人身体的出现始于向更高等级的“道”的追求,这一追求是人企图超越自身、追寻永恒及未知的主动表现。这一主动是一种“动”姿,圣人身体的后续修炼是这一动姿的彰示。动姿让人不再受制于躯体,它让人向世界表达意向,动姿的发出使人拥有了灵性。
圣人身体是兼具躯体康健完备、精神自由通达的身体。“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17]729修炼的对象是储存“精”的心和形气生成的肉身,目的是使二者完备,达到“全心全形”的状态。圣人身体同时又是贯通的身体,是先天精气与后天精气相贯通,进而与“道”互通的身体。“精”进入人体有两种情况:其一是先天的精气在人的孕育期已进入;其二是后天进入身体的精气,《管子》称为“精”和“神”,它们是修成圣人的关键和评判标准。“‘洁其宫,阙其门’:宫者,谓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宫’”[17]632,说明“心”只有“神”入驻才能产生“知”,进而才能“明”。获得了更高级的思维能力,达到“明”的境界的身体可以体知“道”并影响外界。圣人是《管子》构建的一个与“道”互通的理想个体,圣人的修炼不能是完全内向性的,而是需要发出行动、与“道”互动,彰显出自身主体性的。修炼使身体不断向世界的最高规律“道”靠近,这样的身体是天人感应的完美体现。“气”在身体与宇宙间建立了通道,通过它,圣人身体可以不断扩展,身体与宇宙构建起动态双向的互通。贯通的身体让人不再与世界有截然的划分,宇宙成为与人息息相关的宇宙,人成为与宇宙互通的人。
圣人身体是政治权威的身体。不重视血缘的线索,《管子》主论对圣人行为的要求,将身体修炼、道德修养和政治治理等要求与圣人权威绑定。这种观点将作为宇宙副本的身体与理想的身体、政治权威的身体与人的思想相结合,展现了《管子》独特的思想脉络以及对圣人的约束。因为圣人同时是政治上的理想君主与肉体、精神修养上的理想人格的结合体,所以其中一方面的实现必然要求其他方面的实现。把理想人格与理想君主的要求拉入同一逻辑链条,使统治者的修养与其权威性结合,就可督促统治者重视自身修养。这一逻辑的组合方式是空间性的而非时间性的,也即圣人权威的获得方式是空间性的。以此体现出《管子》对统治者能力德行的高要求,与它不重视以血缘为线索的“诸侯世”的“身国同构”倾向相吻合。
“身国同构”是《管子》身体政治思想的重要表现,礼禁是具体实施手段,礼禁的对象与主体都是圣人的身体。圣人通过遵循礼禁增加自身与宇宙(天道)的类同点以获得神圣性和权威,同时又因自身的“动”的特点无法固定这种同构关系,转而引入圣人建筑,圣人建筑于是与圣人一同获得权威。圣人通过修炼,将以自身身体为中心构建的空间扩展并嵌入宇宙,同时,在行为、服饰等方面模仿宇宙获得权威。圣人颁布政令使政治模仿自身身体,在圣人身体与国家之间建立起又一个同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政令与国家因为模仿具有权威的圣人身体而获得正当性,同时,对模仿的强调回返地增强了圣人身体的权威。《管子》将宇宙与政治人事通过圣人身体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多重回返、相互呼应影响的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圣人以身体出场,承担了中介及桥梁的作用,它的权威也来自于此。《管子》的身体政治思想清晰且明确,在这一思想中,君主、官员和民众都有整饬的秩序,都能找到自身的位置,并且这一切秩序都以宇宙为稳定的思想基础。可以说,《管子》的“身国同构”思想是天人感应思想的一部分,在这部分中,身体展现了先人对更高境界的追求,是人自由、主动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