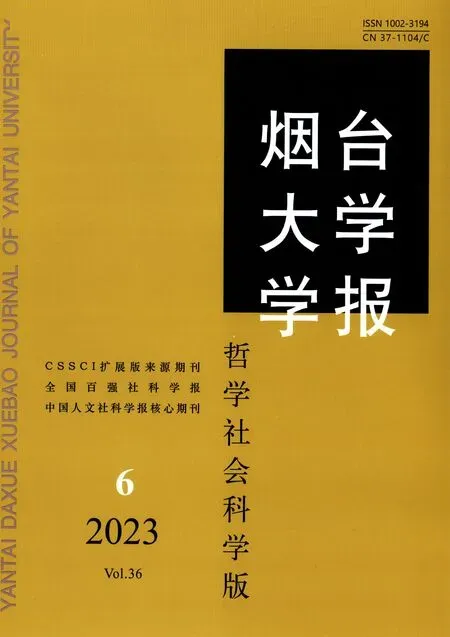明清民国黄河流域水土流失治理的认知与实践
——从阎绳芳到阎锡山
周 亚
(1.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2.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119)
黄河流域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中游的黄土高原又是黄河流域水土流失的主要地域。应当说,在人类诞生之前,该区域的水土流失就已存在。人类诞生特别是进入全新世以来,随着人们改造自然能力的逐渐增强,水土流失也相应加剧。对此古人早已有所认知,从西汉的张戎,到北宋的沈括,再到清代的胡定,都已认识到黄河中游水土流失导致了黄河泥沙的增多。近代以来,随着水土保持学科的发展,对于黄河流域水土流失的认识更趋学理化、科学化,并且形成了一套成系统的治理方略。(1)参见李荣华:《民国时期水土保持学的引进与环境治理思想的发展》,《鄱阳湖学刊》2016年第6期;杜娟:《民国时期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的路径与成效》,《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1年第3期。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措施,植树造林成为透视水土流失治理的一个有效视角。因此,考察历史上森林植被的变化情况就成为黄河流域水土流失及其治理史研究的重要方向。
史念海先生把历史上黄土高原森林的破坏分为四个阶段: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明清以来时期。其中,明清以来森林的破坏最为严重,“这一时期,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黄土高原森林受到摧毁性的破坏,除了少数几处深山,一般说来,各处都已达到难于恢复的地步”。(2)史念海:《论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生态平衡的失调及其影响》,《生态学杂志》1982年第3期。这客观上反映出研究明清以来黄河流域水土流失及其治理问题的重要价值。数十年来,学界围绕这一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基本厘清了六百年来黄河流域特别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原因、阶段和整体特征以及治理的组织、方法等,对区域人地关系的认识也不断深化。(3)相关论述可参见李荣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水土保持史研究综述》,《农业考古》2020年第6期。同时,也应当承认,以往研究尚存在若干不足:一是重古代轻近现代,特别是缺乏将明清以来整体贯通起来的研究,这就很难从长时段的视角考察其变化趋势;二是个案研究不足,近年来学界虽然逐渐重视这一研究方法,但就黄河流域的广大区域而言,相关个案研究仍不充分,对区域经验的挖掘仍有较大空间;三是学科融合不够,水土流失和治理问题是兼具自然、人文两大系统的研究,缺乏任何一个面向的观察,都将造成整体上的认知偏差;四是重实践轻思想,更缺乏对二者关系的探讨,难以深刻理解不同时代水土流失治理背后的逻辑及其演变。鉴于此,本文从黄河中游的一个小流域切入,在长时段的视野下探讨地方官员水土流失治理的认知与实践,进而揭示治理实践背后的文化逻辑。
一、昌源河与镇河楼
昌源河是汾河的主要支流之一,发源于黄河中游地区,源头位于黄土高原东部太岳山脉孟山头南麓的平遥县北岭底村,流经平遥县、武乡县、祁县,在祁县原西村汇入汾河,全长87千米,流域面积1029.7平方千米,其中位于上游平遥、武乡的流域面积为286.3平方千米,其余的均在祁县境内。昌源河上游为土石山区,中游流经丘陵山区,下游进入太原盆地,其主要支流有滹溪河、乌马河、阎灿河、王贤河等。昌源河多年平均径流量为3901万立方米,最大洪峰流量1740立方米/秒(1977年7月6日),清水流量为0.298立方米/秒,枯水季节最小流量仅0.01—0.02立方米/秒。昌源河流域区内的降水量由上而下依次递减,上游为510.7毫米,中游为467.7毫米,下游为437.8毫米,且季节分布极不均匀,主要集中于夏季的几次强降水过程,而多年平均蒸发量为1575毫米。(4)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祁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60-63页。昌源河河床平均纵坡6.86‰,其中子洪水库以上山区河段平均纵坡9.1‰,以下的平原河段平均纵坡3‰,贾令桥以下平均纵坡1‰,全流域侵蚀模数887吨/平方千米。(5)晋中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晋中市志》,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53页。夏季的集中降水、蒸发量远远大于降水量、下游纵坡的骤然降低等因素,使该区不得不同时面对“水多”“水少”“淤积”等几大问题,也要面对如何在不利条件下开发有限“资源”的河流。总而言之,昌源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是比较脆弱的。
明朝初年,朱元璋“遍诣天下,督修水利”,(6)《明史》卷八八《河渠志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7册,第2145页。祁县亦在昌源河下游开渠灌溉。据《祁县志》记载:“洪武二年(1369年),自昌源河引水灌东西营、西高家堡三村田。”(7)乾隆《祁县志》卷二《山川》,乾隆四十五年刻本,第十八页b。当时共开渠五道。此后,昌源河下游的水利开发活动日渐活跃,引水量逐渐增多,以致渠道变为河道。《大清一统志》载,侯谷水“北出为昌源渠,绕县东北,又西南入平遥县界”。(8)道光《大清一统志》卷七二《太原府》,道光九年木活字本,第十六页a。这说明,昌源河祁县河湾村以下河道即是昌源渠。
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汾河在太原盆地中部向东改道后,昌源河亦受影响改道。昌源河从河湾村向北改道后,经东六支、刘家堡等村,到贾令镇和丰泽村附近又分为两支。一支由贾令镇西北流,即今河道;另一支入平遥县后在净化村西汇入汾河,是为“沙河”,(9)康熙《祁县志》卷一《舆地志》,康熙四十五年增修本,第十页b。但此支后来逐渐湮废。(10)汾河灌区志编纂委员会编:《汾河灌区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水利之兴固然值得庆幸,而河流改道之害及对其原因的认知,更能引发人们长久的思考。明嘉靖年进士、祁县人阎绳芳的《重修镇河楼记》就记载了正德至嘉靖年间昌源河上游的环境变化所引发的下游水患及应对之策,其文曰:
祁之东南有麓台、上下帻诸山。正德以前,树木丛茂,民寡薪采。山之诸泉,汇而为盘陀水,流而为昌源河。长波渀湃,由六支、丰泽等村经上段都而入于汾。虽六七月大雨时作,为木石所蕴,放流故道,终岁未见其徙且竭焉。以故从来远镇而及县北诸村咸浚支渠,溉田数千顷,祁以此丰富。嘉靖初元,民风渐侈,竞为居室,南山之木,采无虚岁,而土人且利山之濯濯,垦以为田,寻株尺蘖必铲削无遗。天若暴雨,水无所碍,朝落于南山而夕即达于平壤矣。延涨冲决,流无定所,屡徙于贾令南北,坏民田者不知其几千顷,淹庐舍者不知其几百区也,沿河诸乡甚苦之。是以有秋者常少,而祁人之丰富减于前之十七矣。於乎!河之为害有如此哉?贾令镇中街旧有楼,宣德间镇人以斯有驿署而鼎建之,壮并峙之观也。迨嘉靖丙申,驿署迁于县城中,而斯楼亦颓敝弗振。镇人阎邦瀛、袁尚清乃倡众而更修之,经始于丙辰夏六月,落成于戊午冬十月,翚飞鸟革,金碧辉煌,巍丽实倍于前矣。然集财于众而弗私,励事于久而匪懈,二人之志亦殷矣哉!县令李公春芳喜斯楼之新也,乃名之曰“镇河”。盖以天下之势有轻重,而理有相轧,风水者之所常谈,君子亦习之而不置也。自今观之,楼其峙于北,壮主之势厚重而不迁乎?河其环于南,丽客之形悠然而循轨乎?主客既分,轻重斯别,河水泛滥之患将为楼所轧而保其必无矣。李公命名之义,固冀斯民之免昏垫而复于丰富也,用心亦仁矣哉。虽然楼镇之家文物衣冠,通今学古者济济辈出,行将陟云霄、腾事业,炫光闾里,与斯楼并高于千仞,则河水之流声又于我祁而增美矣,岂独使无冲决之害而已哉!(11)阎绳芳:《重修镇河楼记》,康熙《祁县志》卷七《艺文志》,第三十七页b-三十九页a。
在以上这篇碑记中,阎绳芳通过对昌源河流域正德、嘉靖两朝的对比,分析了从“溉田数千顷”到“祁人之丰富减于前之十七”这一巨大变化背后的原因,即上游森林的砍伐和土地的无限制垦殖。他已认识到森林植被在水源涵养上的重要作用,但与这一科学的环境认知背道而驰的是,阎绳芳认可的解决之道却交给了下游的“镇河楼”。
二、明清时代的整体认知与“偏方”实践
昌源河流域的地势东南高、西北低,由山区丘陵逐渐过渡到平川。其中上游地带山川广布,主要包括祁县东南部的小麓台山、南原、伏罗领、上帻山、下帻山等,还有平遥东部的超山、麓台山、紫盖峰、万松岭以及武乡的胡甲山等。祁县古八景中的麓台龙洞、昌源春水、高峰积雪、帻山晚照等,都是对昌源河上游景观的写照,这些自然景观也常常成为诗人赞颂的对象。元代王恽曾作《过麓台山》,诗中有“阴壑气蓊郁”,(12)王恽:《过麓台山》,乾隆《祁县志》卷一五《艺文志》,第二页a。说明当时麓台山上林木葱郁。元代诗人杨正芳的《周党墓》中也写到,“上有古松树,清荫被祁里”,(13)杨正芳:《周党墓》,乾隆《祁县志》卷一五《艺文志》,第三页a。表明这里曾古木参天。明代刘铣在《麓台龙洞》中写麓台山“南望层峦倚翠台”,(14)刘铣:《麓台龙洞》,乾隆《祁县志》卷一五《艺文志》,第十五页b。可知麓台、帻山所在的昌源河上游当时植被茂密、生态良好。与之相应,明嘉靖以前也少有昌源河流域大饥、大旱、大水的记载。明人武尚綗在《昌源春水》中写到“溉良田兆岁安”,(15)武尚綗:《昌源春水》,《乾隆《祁县志》卷一五《艺文志》,第二十四页a。这可与《重修镇河楼记》中的“灌溉田数千顷”(16)阎绳芳:《重修镇河楼记》,康熙《祁县志》卷七《艺文志》,第三十七页b。相呼应,大抵反映了昌源河较为稳定的流量所带来的民生之利。
对此,阎绳芳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注意到,在正德以前,昌源河上游一带树木丛茂,砍伐柴薪者甚少。山上诸泉汇而成河,为下游水利开发提供了充沛的水源。夏季虽有暴雨,但并未形成洪灾,祁县民人因此而富足。阎绳芳分析了背后的原因,即大雨被“木石所蕴”,这样河水就可以“放流故道”,从而不会出现迁徙和断流的现象。现代生态学研究表明,森林土壤不仅能在降雨特别是暴雨出现时吸收贮存水分,而且在降雨停止后还具有水分保持能力及多余水分的排出能力。前者可以减少地表径流,防止土壤被侵蚀,削弱洪峰;后者可以含蓄水源,延长洪峰历时,补充地下水。(17)王海帆:《生态恢复理论与林学关系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22页。古今对比可以发现,阎绳芳的分析是极为科学的。
从嘉靖朝开始,昌源河流域的人地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阎绳芳观察到,民众在上游山区砍伐森林、开发田地的活动日渐增多,即便“寻株尺蘖”亦被“铲削无遗”,幽幽青山变为濯濯童山。由于丧失了森林涵养水源的功能,每遇暴雨便很快形成洪峰,当洪峰到达盆地时常常冲破河道,出现“流无定所”的情况。河流在贾令南北不断改道,以致冲坏民田几千顷,淹没庐舍数百间,秋田往往得不到保证,沿河百姓的收获受到极大影响。
阎绳芳的论述揭示了明代中期昌源河流域人地关系变化的内在机制,在他看来,正是上游人类活动的加剧导致森林覆被减少,从而引发水土流失,最终导致下游洪水灾害频发,以此构建了一个“人类活动—覆被变化—水土流失—洪水灾害”的关系链条。在这个链条中,阎绳芳把上游和下游放置于一个系统中进行考察,说明其具备了全流域的整体认知,散发着朴素的现代流域学的理论光芒。
毋庸置疑,阎绳芳关于昌源河的“诊断”是正确的,但他开出的“药方”却是以楼“镇”河,希望以此断绝水患的影响。从今人的视角来看,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既然明知顽疾所在,何以不对症下药,从上游的根源处解决问题,而非得在下游着手建一座“无用”的楼阁?这里不免有头痛医脚之嫌。我们认为,阎绳芳并非不懂得应当努力保护上游的森林,甚至通过植树造林恢复生态,但是在当时的制度环境下,要开展任何有组织的所谓“保护”活动,恐怕都只能是天方夜谭。
治本无方,治标无妨。沿河村庄纷纷在河道两旁筑起堤堰,以“堵”的方式防范洪水。但这都是各自为政,并没有统一的规划。对于官方而言,镇河楼的重修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或可视作治理昌源河的一剂“偏方”。
碑文详细记录了镇河楼修建的来龙去脉。镇河楼所在之贾令,明洪武年间设驿站,名“贾令驿”。(18)康熙《祁县志》卷二《建置志》,第二十六页b。政治军事地位的跃升,必然要求有相应的建筑与之匹配。先是在中街建楼,宣德年间又“鼎建”了镇河楼的前身,于是形成二楼“对峙”的壮观之势。嘉靖十五年(1536),驿署迁入县城内,贾令地位的下降导致了楼宇的颓敝不兴。二十年后,贾令镇人阎邦瀛、袁尚清倡议重修,毕两年之功,得以“金碧辉煌,巍丽实倍于前”,县令李春芳给焕然一新的楼阁赐名“镇河”。应当说,镇河楼的命名并非李春芳一时兴起的随意之作,而恰恰反映出昌源河下游的洪水以及河流改道带来的危害成为其辖境内一桩极为棘手的大事。嘉靖十五年贾令驿署迁移的直接原因便是“六月大水坏驿舍”,(19)高叔嗣:《新迁贾令驿碑记》,康熙《祁县志》卷七《艺文志》,第四十二页b。这一细节虽未出现在阎绳芳的碑记中,但他对于事情的本原应当是谙熟的。进一步说,阎绳芳在碑文中对镇河楼意义的阐发,亦可看作是他和李县令在这一问题上共同的意志表达。
镇河楼得以出现的核心支撑理论就是风水学说。风水是古人的环境观,是“天地人合一”的体现,极为讲究等级秩序,上尊下卑,上下分明。在阎绳芳看来,镇河楼与昌源河的位置关系,正是楼峙于北为主位,河环于南为客位,轻重有别,客不犯主,客位的河水会被主位的楼所制服。除了主客相轧,高大的楼宇本身也有改造不利风水的功能,这就是风水学中的“宝塔镇煞法”,即俗语所谓“宝塔镇河妖”(风水学认为河水泛滥成灾是由于河流中的妖气所为)。(20)李计忠:《周易环境与建筑》,北京:团结出版社,2010年版,第100页。只不过,这里易塔为楼,但功效应是一致的。阎绳芳认为,镇河楼的功能远不止于此,它还护佑着一方百姓,使这里人文昌盛,“炫光闾里,与斯楼并高于千仞”。同时,镇河楼使昌源河复归固定河道,成为一条水声潺潺的悠然之河、景观之河,为祁邑“增美”。总之,阎绳芳从绝河患、昌人文、美环境三个方面阐述了镇河楼的功用,在他的世界观中实现了天地人的和谐统一,也在昌源河的“病症诊断”和“药方开具”上实现了逻辑自洽。
显然,如果没有其他配套治理措施,除了在人居环境的美化上具有一定价值外,镇河楼几乎不能起到什么实际的治河之用,顶多只能是心理上的慰藉。但是,这并不妨碍后来者的认知承继,甚至是罔顾事实地执着坚守。
到了清代,昌源河的人地关系依旧延续着明代中期以来的格局,清初“山竭采樵,泉多塌隐。潦则河涨,田多冲没;旱则涸槁,苗无以兴”。(21)⑦ 康熙《祁县志》卷一《舆地志》,第十二页b、第十二页b—第十三页a。顺治九年(1652年)夏,冰雹和长达四十天的连阴雨给当地造成巨大损失,“河溢,田庐漂没,山陵荡徙,林木摧拔”,“山禽死者无算,拥流而下”。(22)康熙《祁县志》卷八《杂纪志》,第六十六页b。可是,乾隆时期再次重修镇河楼时,碑文中却说:“自斯楼成而河患遂息,镇河楼之所系岂不重哉?”(23)⑥ 渠殿飏:《重修镇河楼记》,乾隆《祁县志》卷一二《艺文志》,第二十九页b。碑文作者是乾隆间举人渠殿飏,亦为地方文人。他在发表该言论之前,还专门回顾了镇河楼的渊源和阎绳芳的碑记,应当说,对于阎氏的论断,渠殿飏断然不会置若罔闻,关于河患史实的记载不会视而不见,只是在当时条件下他与阎绳芳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心灵寄托。他同样从风水的角度指出,镇河楼之修建可凝聚气脉,“祁邑钟灵毓秀,人文蔚起,未始非镇河楼之力也”。(24)⑤ 渠殿飏:《重修镇河楼记》,乾隆《祁县志》卷一二《艺文志》,第二十九页b。
这种认知与实践上的“偏离”恐怕是当时的一个常态。因为在同一方志文本中,也有关于治河方略和具体实施办法的讨论:“宜严山禁以毓灵秀,浚昭余以广水利,增支渠筑堤防以弥河害。修樽节教养之政,开育材富民之源,岂非今日所当讲求者乎!”(25)③ 康熙《祁县志》卷一《舆地志》,第十二页b、第十二页b—第十三页a。论者指出,应从开源和节流两方面做起。所谓开源,就是在上游封山育林以治其本,同时在下游修筑河堤、疏浚河湖、增开渠道,治标与兴利并举;所谓节流,就是要养成俭朴节约之风,以减少对资源的攫取。这一“药方”显然更符合科学视野下的治理方案,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作为阎绳芳应发而未发的另一个“镇河”之策的表达。
应当看到,其他地区的官员和民间社会也有切实有效的治理之举。如山西省河曲县令曹春晓发布的《劝民种树谕》曰:“若尔村落居民,或岭脚山,或田头地角,凡不可耕作之处,悉行栽植,审土性之所宜,勤加培护,乡邻互相戒约,毋得砍伐损伤。十年之计树木,百里之地成林。”(26)同治《河曲县志》卷八《艺文类》,同治十一年刻本,第三十九页b。陕西省靖边知县丁锡奎不仅带头种树,还编写劝民种树的俚语,鼓励民众植树,其言曰:“靖边人,听我说,莫招贼,莫赌博。少犯法,安本业,多养牲,勤耕作。把庄前庄后,山涧沟坡,多栽些杨柳榆杏,各样树科。”(27)丁锡奎、白翰章等:《靖边志稿》卷四《艺文志余》,光绪二十五年刻本,第四十九页a。民间社会也通过制定乡规民约并树立碑石,以此禁止破坏森林植被。(28)何满红:《明清山西护林碑初探》,《文史月刊》2007年第1期。反过来讲,劝谕和禁令的背后往往是严峻现实的写照,其实际效果却是很有限的。同时,也不能认为所有的官员都有这样的认知水平和实践能力,明清时代人们的环境意识和治理实践仍是个体的、局部的。(29)王社教:《清代西北地区地方官员的环境意识——对清代陕甘两省地方志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期;王晗:《清代基层官员的环境感知与地方治理——基于陕北黄土高原的考察》,《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三、民国时期的科学认知与“急方”实践
中华民国建立后,正式开启了现代国家制度的建设,明清时代综合性的机构组织和全能型的官僚队伍,逐步被科层化的行政机构、专业化的行政管理和技术化的文官队伍所取代。这一转变带来的结果,就是分化出一系列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自上而下地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这对环境认知的深化及向实践的转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南京临时政府设有实业部,分管农务、矿务、工务、商务四司,其中林业归属于农务司。北洋政府时期,实业部分解为农林和工商两部。山西于1913年成立山西省山林总局,次年被撤销。1917年,阎锡山将山林总局从巡按使公署划出,设技正、技术、庶务等职。1918年山林总局又改称大林区署,管理山西全省林业事宜,并在阳曲、五台、宁武、大同、蒲县、长治等县设立6个小林区署,管理和开发88个县的林业资源,(30)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山西通志》卷9《林业志》,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53、154页。这奠定了这一时期山西林业管理的基本格局。
阎锡山极为重视植树造林,并把其列为“六政三事”的主要内容之一。省政府直接领导指挥大林区署,大林区署发布公文往往以省长名义行之。小林区署直接奉从大林区署的指令,进行采籽、育苗、植树、护林等各项工作。各大、小林区署的工作规划、人事安排、业务总结、报告等重要资料皆备案于阎锡山处。省政府始终强调,造林是林业的中心任务,必须抓紧抓好。(31)李三谋:《民国前中期山西的林业活动》,《古今农业》2001年第1期。为此,阎锡山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向全省推行。
由下页表1可知,这些法律法规涵盖了组织机构、林权登记、树籽采集、植树造林、育苗、管理保护、人才培训等各个方面,既有突出的政府主导性,又彰显了民众的参与性(除要求每人植树一株外,(32)《种树简章》,1917年11月12日,《林业史志》编写组编:《山西林业史资料(初稿)》第二编《民国时期的林业》,1984年,第39页。还成立村级林业促进会,由各村20岁以上无外出和残疾的男性组成,(33)《修正林业促进会简章》,1919年12月2日,《林业史志》编写组编:《山西林业史资料(初稿)》第二编《民国时期的林业》,第10页。动员基层社会植树造林);既注重树籽采集和育苗,又注重具体的植树造林;既重视前期植树,也重视后期管理;既重视植树活动本身,又重视对相关人才的培养;既有奖励,也有惩罚。可以说,法规之结构堪称完备。
这套制度体系以无差别的方式传达给下级行政部门,各县相应出台各自的法规条文,如1923年的《阳曲县上兰村北山造林办法》,1923年的《沁源县第二区聪子峪公议处办砍伐损坏森林简章》,以及《五台县保护森林暂行办法》《五台县奖励人民造林暂行办法》《浮山县承领河滩造林章程》等。(34)《林业史志》编写组编:《山西林业史资料(初稿)》第二编《民国时期的林业》,第109-115页。祁县也于1929年拟定了《昌源河岸造林办法》,并呈送省政府。省农矿厅还对其中的第六条内容进行了修正。(35)《指令祁县政府呈拟订昌源河岸造林办法文》,《农矿季刊》1929年第3期,“林务”第40页。这说明,在科层式的管理体制中,下级与上级的意志必须保持一致。进一步说就是,下级不能存在独立于甚至有悖于上级的意志表达。具体到本文所论的环境意识,省府的一系列法规文件是祁县方面相关认知的直接来源,必须无条件接受,虽然可以根据地方特色在具体办法上有所出入,但总体精神上始终是统一的。
从当时情况来看,这一时期的环境认知一方面继承了前代的基本思想,另一方面把现代科学理论贯穿其中,彰显了时代的特色。1919年,山西省长阎锡山为配合在全省推行分区造林办法而发布布告,其中阐发了他关于水土流失和植树造林的看法:
究竟为什么要做造林呢?概括言之,就是“兴利去害”四个字。我们山西本来是表里山河的地方,群山环围,万壑奔流,每遇大雨,那无数的河流便挟泥带沙一齐下注,往往盈堤泊岸,弥漫无际。就最近的事实说,上年夏秋之间,淫雨连绵,太榆汾孝等二十余县,先后俱遭水患,房屋也坍塌了,田禾也淤没了,人民食宿露处,流离失所。这种巨灾,你说可惨不可惨呢。究其最大的原因,实由于宁朔一带,山势陡峻,土质复又轻松,无固结的力量,所以桑于、滹沱、汾水各河,遇着山水暴发,卷土刷沙澎涨齐来,不但本省受害,而且直隶境内河流,凡河源出自山西的,也都泛滥了。要说防御的法子,再没有比造林好的。因而各河源流如果有了树木,散落地上的枝叶,就渐渐成了层积,河水经过的时候,自然挟沙的力量,流动的速率,都可减少。而且藉那根株引导泥土浸渗起来,也就不怕弥漫了。大家试想这造林的事,岂不是为你们去害吗。至于荒地荒山,据最近调查,各县有的地方很多,但是满目童秃,概无树株可言,这不是放弃天然的美丽么。单就美国说,每一亩的森林,年可得美金十三元,合中国银元二十元。本省长时常向美国人谈询,这是很靠得住的。近来我们中国的木料,到处都比从前贵了几倍,你们还不赶紧趁官厅提倡造林的机会,将所有的荒山设法整理,一面广培树苗预备栽植么。比如现在着手,到十年二十年长成以后,都是合抱参天的森林。间伐销售,每年平均收益不只二十元,比较平常农产物利益,是格外丰厚的。大家再仔细想想这造林的事,不是为你们兴利吗。况且一方面为自己兴利除害,一方面还可以替直隶防河,你看这关系有多么重大呢。所以本省长不嫌繁琐,特将分区造林的意思讲说一番,甚愿你们互相劝告,总要人人了然于心,大家勉力群起办理。赶到数年以后,枝叶发达起来,那就是享受富裕康宁幸福的日子。万勿稍从观望,辜负殷殷告谕的苦心。特此告示。(36)阎锡山:《布告沿河各县分区造林办法领切实办理文》,1919年1月5日,《林业史志》编写组编:《山西林业史资料(初稿》)第二编《民国时期的林业》,第64-65页。
在布告中,阎锡山从当下的水害现象切入,分析了背后的原因,他认为由于地表没有植被覆盖,疏松的土质一遇暴雨,便会“卷土刷沙”,形成泛滥之势。他进而号召民众植树造林,“藉那根株引导泥土浸渗起来”,以除水害。这一认识与阎绳芳、渠殿飏几乎毫无二致。也就是说,关于水土流失的基本性质问题,从明代到民国时期数百年间,至少在官方群体中,这一知识是得到传承的。民国时期的超越表现在两点:一是将除弊与兴利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是阎锡山布告内容的一体两面,尤其在兴利方面,他借鉴美国的经验,对造林的获利情况进行了数据表达,较有说服力。二是将山西的植树造林上升到国家层面——“可以替直隶防河”,这显然更具全局意识。当然,这与他所处的身份地位密不可分。
在阎锡山之外,一批技术型官员得以上任,他们将近代水土保持的科学理念渗透到法律法规中,使这一时期的环境认知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人才选拔上,当时的法规规定,充任署长、技士、指导员、技术员等职,须为“国内外林学专科以上毕业,得有毕业证书者”;充任技手等职,须是“本省甲种林科及林业传习所毕业,服务林业机关二年以上者”。(37)《山西省林业人才训练办法》,《林业史志》编写组编:《山西林业史资料(初稿)》第二编《民国时期的林业》,第93页。受此影响,专业知识能直接体现在植树造林等法律法规中,如在太行山的森林保护法规中,就明确记载“林地倾斜在二十度以上者,不准开垦,以免土沙流失”。(38)《修正太行山森林保护办法》,《林业史志》编写组编:《山西林业史资料(初稿)》第二编《民国时期的林业》,第83页。这里对山地坡度与水土流失的关系给出了准确的数字标准,是从传统时代定性认识到近代试验分析得出量化认识的一个重大转折。(39)近代水土保持学的奠基人罗德民曾于1924—1926年与金陵大学中国师生组成团队,在山西不同流域开展了径流实验,观测并比较森林覆盖率与坡地保水量的关系,得出系列定量数据。他认为,山西省90%的地区为坡地,且平均坡度在20度及以上,这种情况使土壤侵蚀更易发生。参见穆盛博:《林地、军阀和浪费的国家:20世纪20年代的跨国网络和资源保护学》,高冠楠、贺咪咪译,《社会史研究》第14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
与上述认知相并行的,是法规的实践,可分为执法行为和守法行为两大类。前者主要针对政府而言,包括政府对法规的宣传,对下级机关和民众的指导,以及对各项工作的监督考核等。后者包括各行政机关团体的法律遵守和普通百姓的法律遵守两方面。应当说,作为“六政三事”的核心内容,各级各地政府和基层百姓进行了广泛的实践,(40)相关内容可参见阎锡山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各类刊物,如《山西村政旬刊》《山西省政府行政报告》《山西建设》《实业部月刊》等。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特别是在荒山造林方面,成果较为显著。1915年山西仅有国有林百余亩,地方公有林35万多亩,私有林地37.85万亩,总数为72.88万亩。(41)农商部总务厅统计科编纂:《中华民国四年第四次农商统计表》,上海:中华书局,1918年版,第226-227页。“六政三事”实施后,仅1920年就造林12.45万亩,(42)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山西通志》卷9《林业志》,第214页。到1931年时,全省共有森林面积达到1456.58万亩,(43)《林业史志》编写组编:《山西林业史资料(初稿)》第二编《民国时期的林业》,第123页。是原来的约20倍,达到了民国时期山西林业发展的顶峰。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不足和局限所在。第一,官方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人民群众参与度不足。据时人观察:“民国八年晋省曾定三十年间造林一万八十二万余顷之计划,惟其事之进行原冀人民自动着手办理,收众擎易举之效。乃五六年来各县种树造林之作业,仍藉官厅督促,始有每年人植一株之成绩。而各村所立林业促进会等,大半名不符实,虽有少数人为零星片段之栽植,而于省政府原定巨大之计划相距不啻天壤。”(44)《山西林业调查录(二续)》,《中外经济周刊》1925年第141期,第20-21页。第二,经费缺乏,人才不济,从而导致执行不力。因财政困难,1932年将原八个林区署合并为四个。时人说:“太原第一林区所造之人工林一片,余等参观见其所造之榆林,因气候土质不宜,生长不旺,推究原因,实由选择树种不当所致。又见所栽植之侧柏、刺槐,生长颇盛,惜因修理不善,打枝欠妥,亦不能得良好成绩。由此可见林区成绩之一斑矣。”(45)贾之亮:《山西林业之概况》,《农铎》1933年第66期。这反映了政策法规执行过程中重数量而轻质量的问题。第三,实用主义的时代局限。前文已及,在阎锡山的布告中,明确论述了植树造林有着两方面的功能——除弊和兴利。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应对水土流失和经济不振的一个“急方”,虽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当1932年山西开始建设同蒲铁路时,南段铁路的枕木、电线杆等建筑材料大部分取自太岳山区,导致该区发生了严重的森林破坏情况。(46)翟旺、米文精:《山西森林与生态史》,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271页。先造林,后毁林,阎锡山实用主义价值观指导下的治理实践注定只能成为一时之举。
四、结 语
明清时期,以阎绳芳、渠殿飏为代表的士大夫群体,揭示了昌源河水土流失的基本原理,也给出了相应的治理措施,从“诊断”到“开方”,其认知水平都与现代意义上科学的水土保持理论相接近。但是,地方社会并未“照方抓药”,而是开出了一剂“偏方”,就是以风水学说中的镇煞之法来对水土流失进行治理。应当说,这是时人的一个无奈之举。因为无论是从制度、经费还是人力、物力上,根本不具备进行广泛社会动员以开展水土保持实践的条件。现实情况难以改变时,只能用风水方法加以“补救”。这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与士大夫之于水土流失的认知是毫不违和的。应当指出,这一文化兼具建设性和破坏性。前者告诉人们,无论何事何时何地,都有努力的空间,所谓亡羊补牢,犹未晚矣,体现了主观能动性的一面;其破坏性在于,既然认为补救措施是有用的,就片面夸大它的功能,以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放大了被动性的一面。
民国时期,现代国家制度的建立推动了行政管理的专业化和文官队伍的技术化。随着近代水土保持科学理念和技术的发展,明清时代水土流失治理的“定性”描述进入现代科学实证研究的“量化”认知阶段。细分的专门化行政管理在科层式政治制度的加持下,无差别地渗透到各级机关,使水土流失治理的认知在政府及相关部门中实现了自上而下的意志统一。新的变化一方面扫除了传统思想的桎梏,使水土流失及其治理问题回归到事物本身;另一方面,也为自上而下地进行水土流失治理实践提供了保障。在阎锡山的治理逻辑中,“兴利”被放在与“除弊”同样重要的位置,植树造林成为一种资源再造工程。这一“急方”固然在短期内取得一定成效,但终是权宜之计,当需要服务于经济建设时,森林又会被无情砍伐。这看似是一个植树与毁林之间的“悖论”,实际上却是实用主义价值观下的主动选择。
认知与实践是一对重要的哲学概念,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同时也受到历史环境和具体条件的制约,呈现出时代性、区域性、民族性等特征。本文的研究表明,无论明清时代的士大夫群体,还是民国时期的政府官员,其关于水土流失治理问题的认知,都是在各自世界观或信仰基础上形成的,相应的实践活动也不能脱离更不能超越其所处的时代。不同时期的治理实践均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也有诸多不足,体现了其有限性的一面。在今日黄河流域水土流失的治理中,一方面应当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另一方面更要结合区域内具体的生态和社会环境,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