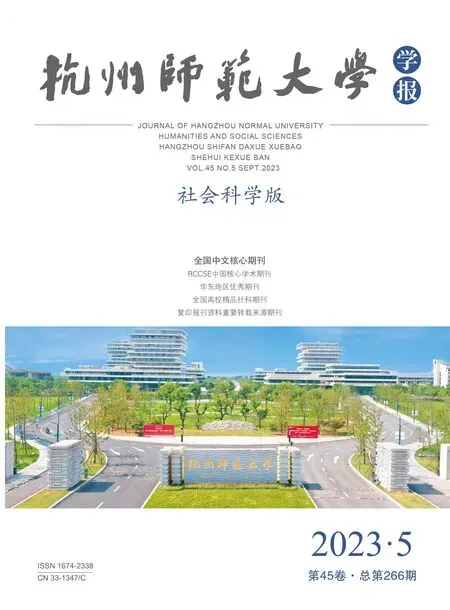论语言与文本
聂珍钊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东 广州 510420)
讨论什么是语言的问题,离不开讨论什么是文本的问题。语言和文本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语言不是文本,也不等同于文本,但是它们紧密结合在一起,相互依存,不能分开。如果要弄清楚什么是语言的问题,首先需要梳理语言与文本的关系,讨论语言与文本的性质,分析各自不同的特点。在《普通语言学教程》里,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为了说明语言的问题,讨论了语言的定义及其特点、能指与所指及语言符号的构成,也讨论了文字以及文字同语言的关系等诸多问题,然而很少涉及文本的讨论。正因为索绪尔忽视了文本在语言构成中的关键性作用,尽管他做出了重要努力,却始终无法把语言的问题解释清楚。同索绪尔相比,巴特(Roland Barthes)显然注意到文本对于符号及语言的价值,提出“文本”概念,并在《从作品到文本》一文中对“文本”做了全新的解释和分析,建构了自己的文本理论。巴特的“文本”理论不仅对于语言学和符号学具有重要启发意义,而且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分析和解读文学的崭新视角。
一、语言之源
自巴特以来的文本研究表明,文本为语言学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为解决语言的定义问题找到了一条新路。
语言是什么?目前有多种解释,如“语言是一种表达思想的符号系统”[1](P.15)。“语言是一种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重要的思维工具。”[2](P.11)“语言是人类社会中一个最重要的工具或手段。”[3](P.10)“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意义结合的词汇和语法的体系。”[4](P.11)“语言是一种复杂的符号系统,是人类进行社会交际思维认知的工具。”[5](P.2)“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交际工具和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不但是交际的工具,而且也是思维的工具。”[6](P.34)以上提到的种种观点,大体代表了目前有关语言定义的解释。如果对其进行归纳,可以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语言符号论,一类是语言工具论,一类是符号工具结合论。第一种观点把语言看成表达思想的符号,第二种把语言看成交际的工具,第三种是前两种结合在一起的折衷主义观点。从本质上看,无论哪一种观点,都是从语言的功能出发理解和解释语言,都是把语言看成表达思想的工具。
显然,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不能解释什么是语言的问题,因为作为工具的语言必须是具体的实体,是可以感知并能够发挥作用的媒介,例如钢笔是书写的工具,文字是记录的工具,眼镜是阅读的工具,电灯是照明的工具,无论钢笔、文字,还是眼镜、电灯,我们都能对这些工具有一个具体的把握。语言作为记录思想的工具也好,或者作为进行交际的工具也罢,不仅语言是什么样的工具我们无从把握,即使我们能够把握工具,但是仍然不能解决工具表达的语言是什么的问题。
那么,索绪尔把语言看成表达思想的符号系统是否可以解释什么是语言的问题呢?表面看似乎有理,其实不然。索绪尔简单地在语言和符号之间画上等号,把词和词汇看成语言符号,因此语言就在逻辑推理下等同于文字。索绪尔特别强调了语言的音响形象的本质特征,也特别说明语言不能等同于文字。按照索绪尔的理解,文字就是语言符号,语言符号等同于语言,因此文字本身就是语言。尽管把文字看成语言的一部分是后来语言学界的一个重要观点,但是这个观点使坚持文字的价值在于表达语言的索绪尔陷入自相矛盾之中。从索绪尔的自相矛盾中,我们仍然可以抓住问题的实质,那就是文字作为工具表达的语言是什么。因此可以从中看出,索绪尔没有解决的问题同其他观点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一样的。
归根结蒂,所有的问题仍然是语言是什么的问题。无论索绪尔还是巴特,他们都认为有一种语言存在,这一点几乎是所有的人都认同的,但是这种语言是什么?在哪里?这些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究其原因,这是在探讨什么是语言的问题时,我们忽略了一个与语言密切相关的问题,即文本的问题。只有把文本的问题同语言的问题、符号的问题、文字的问题等结合在一起时,我们才有可能打开思路,真正解决什么是语言的问题。
二、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巴特把符号看成语言的源头,认为只有符号才能说明语言的问题,并通过对符号价值的强调不断消解作品概念的价值,把文学理论的研究聚焦到文本概念上,从而开启了从“作品”研究转向“文本”研究的时代。巴特在其重要论文《从作品到文本》《作者的死亡》等论文中系统深入地讨论了从作品到文本的转向,对文本概念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解释。应该说,文学理论界有关文本研究的潮流,最初是由巴特引领的。
早在巴特之前,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即作家的价值已经遭到质疑。正如巴特所说:“在法国,可以说,是马拉美首先充分地看到和预见到,有必要用言语活动本身取代直到当时一直被认为是言语活动主人的人;与我们的看法一样,他认为,是言语活动在说话,而不是作者。”[7](P.296)马拉美(Stephane Mallarme)已经认识到同文本的价值相比,作者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要。在文学批评传统里,对文本的理解是从寻找作者的写作动机以及分析写作过程开始的,“批评以在作品中发现作者(或其替代用语:社会、历史、心理、自由)为己重任:作者一被发现,文本一被‘说明’,批评家就成功了”[7](P.300)。但是,马拉美认为没有作者并不影响阅读和分析文本。
在作家同文本的关系方面,不仅马拉美在消解作者的重要性,而且超现实主义和语言学也同样如此。超现实主义打碎了作品中作者头上的神圣光环,把作者从文学创造者的神坛上拉了下来。语言学强调言语活动只认识“主语”而不认识“个人”,作者在作品中的地位变得无足轻重。同文本相比,作者离我们更远了,而这正是作者价值消减的结果。用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话说,“疏远作者”的结果是导致文本建构以及阅读过程中的作者缺席。只要文本形成,或者说只要作者完成了文本的建构,作者就不再是文本的组成部分,而是从文本的阅读和理解中退场,而其身份转变成了普通的读者。此前作者对于理解文本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不可缺少的,而现在作者同文本的关系似乎可以完全斩断了。没有作者,并不影响我们阅读和理解文本。作者死了,但是新的读者产生了。所以巴特说:“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之死为代价。”[8](P.148)
什么是文本?巴特解释说:“现在我们知道,一个文本不是由从神学角度上讲可以抽出单一意思(它是作者与上帝之间的‘讯息’)的一行字组成的,而是由一个多维空间组成的,在这个空间中,多种写作相互结合,相互争执,但没有一种是原始写作:文本是由各种引证组成的纺织物,它们来自文化的成千上万个源点。”[7](P.299)巴特的这种解释还不足够让我们完全明白什么是文本。他在“从作品到文本”一文中又说:“与作品的概念相反——一个长期以来乃至现在还在以一种被称为牛顿主义的方式进行思考的传统概念——现在对新客体有了一种需要,它通过放弃或颠倒原有范畴来获得。这个客体就是文本。”[9](P.86)但是,巴特也意识到文本这个概念很时髦因而遭到质疑,所以他对文本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首先,文本在性质上不是一个时间概念。“文本应不再被视为一种确定的客体。 尝试作品与文本在材料上的区分可能是徒劳的。人们必须特别小心地不要说作品是古典的而文本是先锋派的。区分它们并不在于用现代性的名义来建立一张粗糙的图表然后根据作品所处的年代顺序位置来宣布某些文学作品在现代性之‘ 内’,另一些则在‘ 外’ 。一部非常古老的作品可能就是‘某种文本’,而许多当代文学作品则可能根本不是文本。”[9](P.87)
其次,文本是一种话语存在。关于作品与文本的区别问题,巴特解释说:“作品能够在书店,卡片目录和课程栏目表中了解到,而文本则通过对某些规则的赞同或反对来展现或明确表达出来。作品处在技巧的掌握之中,而文本则由语言来决定:它只是作为一种话语(discourse)存在。”[9](P.87)从巴特的解释中可以看出,作品主要是文学的形式,也可以说是文本的形式,而文本则是作品的话语,是作品的意义。作品是“文本想象的产物”[9](P.87),文本是创作活动中的体验,是超越作品形式的内容部分。
最后,文本有多种形式。在《S/Z》一书中,巴特提出了“可写文本”和“可读文本”两个相对的概念。巴特认为:“在今天可被写作(被重新写作)的东西,即可写文本(scriptible)。”巴特解释说,可写性文本就是正在写作中的我们:“可写性文本,就是无小说的故事性,无诗歌的诗意,无论述的随笔,无风格的写作,无产品的生产,无结构的结构化。”[10](P.154)归根结蒂,可写性文本就是可以重新改写的文学作品。通过对文学作品的改写,批评家可以对作家创作的作品任意分割和解读,重构与原来作品意义不同的文本。通过对文本的改写,读者和批评家也就从文学的消费者变成了文学的生产者。由此可见,巴特的可写性文本并非指文本自身,而是指对文本的重构。正如巴特所说,“可写性文本是一种永恒的现在时”[10](P.153),如此一来,创作作品就不再是作家的专利,作者将从历史的神坛上被推倒,将由读者和批评家取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特宣称作家死了。
什么是可读性文本?巴特说:“可以被阅读但不可以写作的东西,即可读文本。”[10](P.152)巴特把任何可读性文本都称作“古典文本”[10](P.152),它们构成文学庞大整体的产品。可读性文本与可写性文本相对,是可写性文本的等价。巴特认为文学存在的问题是读者同文本的分离,因此需要改变读者只是文学消费者的状况。他说:“因为文学工作(文学就像工作)的赌注,是使读者不再成为消费者,而是成为文本的生产者。文学机制在文本的制造者和使用者之间、在其主人和其顾客之间、在其作者和其读者之间,保持着一种无情的分离状态,我们的文学正具有这种特点。于是,这种读者便陷入一种无所事事、不闻不问和总之是严肃的状况:他不去自己发挥作用,不去充分地接近能指的诱惑力和写作的快乐,他天生只有接受或拒绝文本的可怜的自由:阅读仅仅是一种公民投票。”[10](P.152)因此,面对着可写性文本,便建立起它的等价,即它的负向的和反作用的价值可读性文本。可读性文本也是作为消费对象存在的文本,与之相对的是作为写作活动或创作实践存在的可写性文本。巴特把文本分为可写性文本和可读性文本,其目的是要打破读者和批评家与作者之间的界限,认为作者并没有最终完成文学的创作,而要读者和批评家作为作家参与到文学的创作中来,把文学创作继续下去,创造新的文学价值。
巴特提出可写性和可读性文本后,似乎觉得并没有将文本解释清楚,于是又提出多元性文本问题。多元性文本就是“能指的银河系,而不是所指的结构;它无开头而言;它是可换向的;我们可从许多入口进入文本,而没有一个入口可断言是主要的;它所调用的编码无穷无尽,但均难以确定(其意思从不只依赖一种决定原则,甚至是靠偶然性);意思系统可以从这种绝对多元的文本中获得”[10](P.156)。巴特认为,作品是一元论的,有来源和影响,而文本则是多元的,不仅有多重意义,而且是对意义本身的穿越和超越,是意义的爆炸和发散,因此作品和文本的区别也在于文本的多元性。巴特企图从传统的文本理解中解构文本,寻找文本的多元意义,这是他为建立新的解构主义的文本理论做出的努力。
三、远非完成的任务
巴特继承和发展了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提出可写性文本、可读性文本等概念解释文本和建构其文本理论,但除了说明文本形式的多样性特点和增加了文本理论的复杂性外,并无助于说明什么是文本。尽管巴特从多个方面解释文本或界定文本,但他始终无法把文本的概念解释清楚。
巴特有关文本的解释和定义总是模糊的、充满矛盾的,并最终陷入文本神秘主义的泥淖。他虽然从多个方面对文本做了大量解释,但实际上并未真正实现其建构文本理论的目标。他是建构文本理论的开创者,但是他并未收获到文本理论的成熟果实。正如他强调文本的多元意义一样,他对文本的多元解释增加了文本理论的矛盾性。巴特对文本的解释可以给我们许多有意义的启发,但是他的解释并不成功。原因就在于他扩大了文本理论的范畴但是缺少了逻辑论证。尤其是他对同一概念的多元性解释,增加了我们理解同一概念的难度,有时甚至让我们无所适从,不知究竟应该按照他的哪一种解释理解他的定义。
例如,在巴特的文本理论中,他认为“文本是文学作品的现象表层,是进入作品并经过安排后确立了某种稳定的且尽量单一意义的语词的编织网”[11](P.297)。但是,文学作品的现象表层是文本并不能让我们真正理解什么是文本,因为文学作品的现象表层是文本的表述只是一种同义反复,尽管表述的字面不同但是语义却是相同的,其结果是我们仍不能理解什么是文本。由于文本的定义不够清晰,所以巴特又解释说,文本不是作品,它是“作品平凡但必要的支柱”[11](P.297)。文本不同于作品,它“在作品中担保所写之事,汇聚了种种保障功能,一方面,保障书写文字的稳定性和持久性,以纠正记忆之脆弱和不准确性;另一方面,保障书写文字的合法性,因为它是毋庸置疑的不可磨灭的痕迹,保障作品作者有意加入其中的意义”[11](P.297)。从巴特的表述中有一点是明确的,即文本不是作品。那么文本是什么呢?尽管巴特指出了它的作用与价值,但是对于究竟文本是什么的问题,我们仍然不得要领。
为了把文本的问题解释清楚,巴特显然做出了巨大努力。为了能够理解文本,他从多个角度对文本进行解释,尤其是企图借助符号学理论解释文本。[11](PP.297-298)他借助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文本理论解释文本,认为文本是一种把能指和所指连接起来的表意实践。他说:“文本概念意味着书写信息被结构成符号:一方面是能指(即字母及其联结成语词、语句、段落、章节的物质性),另一方面则是所指(即具有原初性、单义性和终结性语义),后者由承载该语义的符号之间的关联决定。经典意义上的符号是一个封闭音位,它关闭、终止语义,阻止其动摇、分化、萧蔓延;经典文本的道理相同,它关闭作品,把作品拴在它的文字上,束缚在它的所指上。”[11](PP.297-298)在巴特的解释中,文本似乎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正如他所说:“文本即写成之文字。”[11](PP.297)但是,他似乎又对自己的这个观点进行了否定。他说:“我们不能把文本概念局限在书面文字(文学)内。”“所有表意实践均可能产生文本:绘画实践、音乐实践、影视实践等。”[11](P.304)因此,“文本永无完形,它处于种种规约无限的互动之中,而不停靠在作者某种‘个人’行为终结的港湾”[11](P.304)。在巴特的理解中,文本既不是作品,也不是文字,也不是符号。文本就像树木,树木是时刻更新的事物,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文本也同样如此,处在不断的变动中。
巴特还通过同作品的比较解释文本。他说:“一部作品是一件完成物品,可以计算页码,可以在图书馆的书架上占据位置;文本则是一个方法场。因此,人们无法(至少正常地)计算文本的相关数据,人们最多只能说,在某部作品中,有(或没有)文本:‘作品捧在手中,文本寓于言语中’。”[11](P.303)在巴特看来,文本只能在其成义的过程中,即在“某种工作中、生产中,才能被感知”[11](P.303)。因此,巴特还提出现象文本、基因文本、互文性等概念,以此说明文本理论“试图从编织过程中,从规约、格式、能指的交织中发现编织物”[11](P.303),即文本。
显然,巴特对文本的解释越多,我们从中得到的启发也多,但是对于文本的理解没有变得更清晰,而是变得更糊涂。可以说,巴特自己已经陷入了他为自己设置的文本解释的陷阱中了。他在《今日神话》中解释文本的意义时,曾把文本解释为“神话”。巴特认为,“神话是一种言语”[12](P.92),“是一种意指方式,是一种形式”[12](P.90)。巴特根据他的神话逻辑指出:“既然神话是一种言语,那么,一切便都可以是神话,因为神话归属于一种话语。”[12](P.92)巴特尽管在神话——话语——文本之间建立起一条通道,把神话同文本联结起来,文本既可以是言语,也可以是语言或者其他的东西。总之,文本似乎不在现实中,而变成了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变成了没有实体的可以任意解说的抽象概念。
巴特对文本的解释不能尽如人意,我们既不能从他的解释中领悟文本的定义,也不能消除心中有关文本的疑惑。巴特对文本的解释不仅纷繁复杂,而且没有抓住要害,忽视了对文本的形态、功能、作用机制等基本问题的解释。建构新的文本理论是巴特远非完成的任务,但是他的研究和解释为我们进一步探讨文本的问题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当我们关于语言的定义、符号的研究以及文学理论的讨论面临窘境时,文本可能就是一把万能的钥匙,帮助我们打开一扇新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