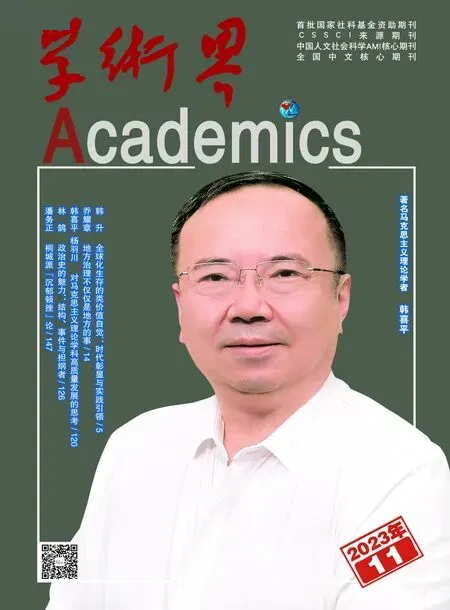桐城派“沉郁顿挫”论〔*〕
潘务正
(安徽师范大学 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安徽 芜湖 241000)
杜甫是桐城派最推崇的诗人。桐城诗人观念中,杜甫之前的《诗经》《楚辞》、汉魏、阮籍、陶渊明、谢灵运、谢朓、鲍照等,都是为他的出现而作准备;在他之后,韩愈、苏轼、黄庭坚、陆游等都逃不出他的影响。杜甫之所以“冠绝古今诸家”,“只是沉郁顿挫,奇横恣肆,起结承转,曲折变化,穷极笔势,迥不犹人”,〔1〕首要因素为“沉郁顿挫”,其他“奇横恣肆”等均是由此而形成。桐城派论诗文讲究文法,而最主要的文法,就在于此,方东树说:“专讲文法,以顿挫沉郁为主。”(第534页)姚莹也说:“古人文章妙处,全是沉、郁、顿、挫四字。”〔2〕以“沉郁顿挫”评杜诗盛行于明清时期,其中桐城派之论最为典型,使用频率极高,视其为杜诗成就的不二法门。桐城派根据诗学发展的趋势,赋予“沉郁顿挫”新的内涵,使之进一步经典化。
一、“沉郁顿挫”与桐城派诗文反俗化倾向
桐城派重视“沉郁顿挫”的文法,不仅是对杜甫的推崇,还有其更为深刻的用意。姚莹在阐释“沉郁顿挫”之特点时,特别指出与之相反的四种弊病即“浮、率、平、直”,并说:“文章能去其浮、率、平、直之病,而有沉、郁、顿、挫之妙,然后可以不朽。”〔3〕方东树也说:“诗文无顿挫,只是说白话,无复行文之妙。……非苦思不能避滑易轻浮。”(第533-534页)也就是说,“沉郁顿挫”被重视,是用以纠正诗文创作中出现的“浮率平直”或“滑易轻浮”之病,更进一步地说,即“说白话”的“弊端”,也就是以之抵制诗文的通俗化倾向。
一般认为,中唐以降,中国古代社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即唐宋转型,文学在思想、语言、文体等方面表现出有别于以前的特质。其中,随着市民阶层的崛起,正统文学出现通俗化的趋向,此自白居易开其端,苏轼、杨万里承之,明代的公安派、清代的性灵诗派是最为典型的代表。为反驳此种风气,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倡复归唐诗,回归传统诗歌“意与境谐、情与景会”的美学境界,前后七子继承严羽之论,力倡诗文复古运动;〔4〕清代馆阁及桐城派对这种风气更是极力批判,并为此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可以说,中唐以后,古代诗文的发展,贯穿着雅正传统与通俗传统的对立及统一。抵制诗文的通俗化倾向,是桐城派首要的任务,诸多文学主张都是为此而提出,“沉郁顿挫”得到他们空前的重视,也是出于这一文学思潮。
桐城派批评文学史上开通俗化之趋向的作家及流派。方苞反对种种语体进入古文,而这些语体,不同程度地与古文的通俗化趋向有关,比较明显的如小说家体、语录中语,其他如诗歌中的“隽语”、南北史中的“佻巧语”,亦是与通俗化有联系,〔5〕涉及到的流派及作家有公安派、黄宗羲、钱谦益等。至于诗歌领域,则一直追溯到中唐的白居易。姚鼐编纂《今体诗钞》,意在“正雅祛邪”,于白居易五七言律诗仅收13首,远不及杜甫的220首,姚鼐解释道:“香山以流易之体,极富赡之思,非独俗士夺魄,亦使胜流倾心。然滑俗之病,遂至滥恶,后皆以太傅为藉口矣。非慎取之,何以维雅正哉?”〔6〕所谓“滑俗之病”,就是“老妪能解”的通俗化倾向,为从源头上遏制此种风尚,不惜少选白诗,以维持雅正。姚鼐对李白之诗评价很高,其弟子方东树虽于白亦无间言,但对其可能造成的俚俗诗风心存忧虑,故云:“太白岂非作祖不二,大机大用全备?世人不得其深苦之意,及文法用笔之险,作用之妙,而但袭其词,率成滑易。此原不足为太白病,但末流不可处,要当戒之。”(第20页)担心“末流”只是袭取其浅近的诗语而形成“率成滑易”的诗风,故主张于李诗要谨慎效法。“杜韩苏黄”是桐城派最为敬仰的四位诗人,但对于苏轼,在推崇的同时,也于其诗风有所警惕,方东树云:“东坡下笔,摆脱一切,空诸依傍,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能为一大宗;然滑易之病,末流不可处。故今须以韩、黄药之。”(第43页)东坡“摆脱一切,空诸依傍”的诗风,在其自身本不是问题,但末流效之,易成“滑易之病”,故亦慎学。诸大家之外,如姜夔“字句率滑,开伧荒一派”(第19页);如吴莱,“立夫伧俗,乃开袁简斋、赵瓯北、钱箨石等派,不可令流毒后人。……此种粗才,惊俗眼而已。求其以古人深韵,不复可见”(第342页),等等。在评价前代诗人诗风时,时刻不忘排斥“流易”诗风,力图从源头上杜绝通俗化的倾向。
不难发现,桐城派反对流易诗风,有现实针对性,在明末清初,是针对公安派;在乾嘉时期,则是面临着以袁枚为核心的性灵诗派的冲击。尤其是后者,姚鼐与袁枚差不多同时,其崇正黜邪之追求,明显是有感于袁枚诗学的社会影响。〔7〕方东树时期,性灵诗风盛行一时,所以方氏集中笔墨抨击之。袁枚诗与白居易浅近诗风相近,据他所称是无意相合;有鉴于此,姚鼐少选白诗,而方氏则于《昭昧詹言》中未设专条讨论白诗,这与乐天的诗史地位完全不符。又,方氏于吴莱之诗一再批判,就是觉得其诗为“俗调”“伧俗”,开袁枚、赵翼、钱载之“俗派”(第343、344页)。对于赵、钱二位,方氏并没有集中笔墨,只是于吴莱诗略一及之;而于袁枚之诗风,则深恶痛绝。他不点名地批评道:“如近人某某,随口率意,荡灭典则,风行流传,使风雅之道,几于断绝。”(第17页)其人之诗“随口率意”,断绝风雅之道,且“风行流传”,造成的社会影响极大,由其所言,一看便知锋芒所向。方氏又说:“近世有一二庸妄巨子,未尝至合,而辄矜求变。其所以为变,但糅以市井谐诨,优伶科白,童孺妇媪浅鄙凡近恶劣之言,而济之以杂博,饾饤故事,荡灭典则,欺诬后生,遂令古法全亡,大雅殄绝。”(第33页)近世这一二位未尝至合先求变的“庸妄巨子”,除袁枚之外,当然还包括袁宏道。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诗学祈向,与提倡由模拟以至新变的桐城派不侔,故自钱澄之、方文、潘江等人以来,桐城诗人重“苦吟”以避之。而到了乾嘉时期,通俗化潮流的主将变成袁枚,且其与公安派诗学有一定的关联,故方东树连类而及,对这几位“庸妄巨子”极尽讽刺之能事。
在针砭制造通俗诗风的诗人同时,桐城派也竭力抉发反俗化诗人的诗学贡献。对于李商隐,桐城派评价并不太高,但姚鼐却比较推崇,尽管其诗亦有“僻晦之敝”,但因其“近掩刘白”,以“太过”之“用思”来“矫敝滑易”,所以推为“诗中豪杰士”,充分肯定其诗学贡献;又如黄庭坚,其诗“刻意少陵,虽不能到”,但其“兀傲磊落之气,足与古今作俗诗者澡濯胸胃,导启性灵”;〔8〕方东树也说:“寻常人胸臆口吻中当作尔语者,山谷则所不必然也。此寻常俗人,所以凡近蹈故,庸人皆能,不羞雷同。如山谷,方能脱除凡近。”(第314页)所见与其师相同,由是黄庭坚得以与李、杜、韩、苏并列为桐城派尊崇的诗人。唐代以前诗人中,只要是能药浅俗之病者,桐城派都以之为师法对象,如谢灵运之诗“下字成句”“无一字轻率滑易”,故“须以康乐为法”(第136页);鲍照诗“涩炼典实沉奥,至工至佳”,“诚为轻浮滑率浅易之要药”,称其诗风为诗学史上之“大变格”,杜、韩“皆胎祖于此”(第172页)。陶渊明之诗“直书即目,直书胸臆”(第97页),方氏提醒学诗者,“若不先从鲍、谢入手,而便学此,未有不失之滑浅庸近,如今凡俗所为者也”(第108页)。正因如此,学诗以二家“为之的”,于谢取其“华妙章法,一字不率苟随意”;于鲍取其“生峭涩奥,字字炼,步步留,而又一往俊迈”(第168页)。甚至谢惠连之诗亦非齐梁以下“浮靡轻滑熟懦之可及”(第158页),而被桐城派所看重。至于韩愈,方东树说:“今且以鲍、谢、韩、黄为之祈向,可以已轻率滑便之病”(第135页),也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可以看出,桐城派推崇的诗人,大多是因其诗风有功于抵制俗化倾向。
在下字、用典、造句、谋篇等方面施加用心皆可以避免平直浅率之弊,其中最重要的无疑就是杜诗“沉郁顿挫”之文法。黄庭坚之诗不如杜甫、韩愈者在于“无巨刃摩天,乾坤摆荡,雄直挥斥……沛然浩然之气”,不过其“沉顿郁勃,深曲奇兀之致,亦所独得,非意浅笔懦调弱者所可到也”(第226-227页),以“沉顿郁勃”与“意浅笔懦调弱”的俚俗诗风相对,用意甚明。谢惠连诗“故为顿挫往复”,也是“避轻便滑利顺直无留步之病”的有效手段(第158页)。不难发现,在桐城派看来,“沉郁顿挫”是救治诗风俗化的灵丹妙药。
二、人格:立诚尽怨
“沉郁顿挫”虽被方东树看作文法,但其并非仅为形式上的指称,而是关合着诗人的道德品质、学养境遇等多方面的因素。清人何日愈云:“子美以学力胜,故语多沉郁。”〔9〕桐城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构成“沉郁顿挫”的诸多成分,姚莹说,《楚辞》《史记》、李杜诗、韩文皆有“沉郁顿挫之妙”,究其根底则在于:“此数公者,非有其仁孝忠义之怀,浩然充塞两间之气,上下古今穷情尽态之识,博览考究山川人物典章之学,而又身历困穷险阻惊奇之境,其文章亦乌能若是也哉?”高尚的襟怀、浩然的正气、广博的学识及坎坷的经历是“沉郁顿挫”之妙形成的根本原因,此虽被桐城派视为文法,但却包含着人格意涵在其中,而非仅为表现内容的形式;相反,如果“不求数公之所以为人”,而“惟求数公之所以为文”,则“罕有及数公者”,〔10〕这种文法不能只从外在寻取,而要深入内里去学习。
雅俗诗风与两个阶层划上等号:高雅诗风属于正统士大夫阶层,而俚俗诗风被划为市民阶层,二者的区别在于胸襟学识的高低差异。方东树说:“夫人亦孰不各有其胸臆,而不学则率皆凡鄙浅俗。”(第52页)俗派诗“凡鄙浅俗”,品味不高,其根源在于“不学”,此论大概承其师姚鼐,而矛头主要指向公安派及袁枚为代表的性灵诗派。姚氏有诗与其弟子陈用光云:“我观士腹中,一俗乃症瘕。束书都不观,恣口如闹蛙。公安及竟陵,齿冷诚非佳。古今一丘貉,讵可为择差。”〔11〕指出公安派、竟陵派之“俗”,皆由束书不观而致。三袁之师李贽《童心说》认为后天的“闻见道理”遮蔽先天的“童心”,书读得越多,经历越丰富,闻见越广博,越会成长为一个“假人”,因此提倡“绝假纯真”,保持“最初一念之本心”的“童心”;公安派的性灵说脱胎于此,他们排斥正统观念重视的胸襟、学识与阅历等,在其肯定的“性情”中,包括为理学家所不齿的男女之情。袁枚性灵诗学与公安派乃“古今一丘貉”,袁氏虽并不完全反对知识,但毕竟知识不占其诗学的主导地位。并且,其学习的对象亦非前代的文学遗产,而是身边的普通人:“少陵云多师是我师,非止可师之人而师之也。村童牧竖,一言一笑,皆吾之师,善取之皆成佳句。”〔12〕其所师亦是“绝假纯真”的“童心”之人。正因如此,他亦被视为胸襟学识低下者。
如果按照诗学传统来划分,性灵诗风源于《国风》传统,桐城诗派则出自《雅》《颂》传统。前者是“全乎天者”,后者是“因人而造乎天者”,一重天赋,一重工夫。前者“成于田野闺闼、无足称述之人,而语言微妙,后世能文之士,有莫能逮”,此重性情之真;后者“文王、周公之圣,大、小雅之贤,扬乎朝廷,达乎神鬼,反复乎训诫,光昭乎政事,道德修明,而学术该备”,此重道德之善。在姚鼐看来,前者“偶然而言中,虽见录于圣人,然使更益为之,则无可观已”,仅凭天赋,只是偶有佳作;而后者为“儒者之盛”,“兼《雅》《颂》,备正变,一人之作,屡出而愈美”,〔13〕依仗工夫,就会与日俱进。两相比照之下,自可看出《雅》《颂》传统高于《国风》传统。
《雅》《颂》传统特别重视胸襟与工夫,即所谓“道德修明”“学术该备”。方东树云:“大约胸襟高,立志高,见地高,则命意自高。讲论精,功力深,则自能崇格。读书多,取材富,则能隶事。闻见广,阅历深,则能缔情。”(第381页)所言胸襟、读书、阅历之功用,与姚莹相同,方宗诚观点亦与之一致。他以曾子“出辞气,斯远鄙倍”为文训,说“能不鄙倍,文章之能事毕矣”,为文关键在远离“鄙”与“倍”。所谓“鄙”,即“说理论事言情,稍涉于粗陋伧俗浅近肤泛,皆鄙也”;所谓“倍”,即“稍涉于支离偏辟浮伪淫遁,皆倍也”。要做到不鄙,必须“胸襟真开阔,知识真高明,闻见真广博,气象真涵养,而又能泽之于古”;要做到不倍,必须“学问真笃实,性情真不偏,气质真不驳,好恶真不乖戾,而尤能审之于理”。“鄙”与“倍”虽在辞气层面,属外在的表现,但其“工夫全在心地根本上做”,〔14〕只有胸襟、识见拔出流俗,方能远离鄙倍。
“心地根本”中最重要的一项是“立诚”,方东树说:“要之尤贵于立诚。立诚则语真,自无客气浮情、肤词长语、寡情不归之病。”(第381页)“立诚”与“胸襟”有必然而内在的联系,不诚之人自然无胸襟可言。“立诚”“胸襟”是“本领”,是文章的根本。朱熹云:“文章要理会本领。”此“本领”谓理。〔15〕所以作诗文与修身为一事:“诗文与行己,非有二事,以此为学道格物中之一功,则求通其词,求通其意,自不容己。”古今人作诗文之不同,就在于此:“古人皆于本领上用工夫,故文字有气骨。今人只于枝叶上粉饰,下梢又并枝叶亦没了。文字成,不见作者面目,则其文可有可无。”(第2页)有本领的文章就有气骨,无本领的文章不见作者面目,此不仅是古今之别,也是雅俗之异。古今诗人中,杜甫能综贯《国风》及《雅》《颂》传统,“其才天纵,而致学精思,与之并至,故为古今诗人之冠”,〔16〕杜诗才、学、思并至,宜其为古今第一诗人。而最主要的,则是其诗是“立诚”的体现,方东树云:
诗以言志。如无志可言,强学他人说话,开口即脱节。此谓言之无物,不立诚。……屈子则渊渊理窟,与《风》、《雅》同其精蕴。陶公、杜公、韩公亦然。可见最要是一诚,不诚无物。诚身修辞,非有二道。试观杜公,凡赠寄之作,无不情真意挚,至今读之,犹为感动。无他,诚焉耳。彼以料语妆点敷衍门面,何曾动题秋毫之末。(第2-3页)
屈原、陶渊明、杜甫、韩愈之诗,皆以立诚为主。杜甫将修辞与立身打并为一体,因此其诗不管何种题材,即使是应酬之作,也能感动人心。其诗之“沉郁顿挫”,与学识、阅历密切相关,亦与此胸襟即“立诚”融为一体。在理学家看来,胸襟虽是得之“天命之性”,但也通过后天的博学、阅历、践履而获得提高,方宗诚释“诚”为“实”,“实体诸心、实践诸行、实验诸事之谓诚”。如果不学,则胸襟猥琐,格调低下,是为不诚;经过学习、游历不断提高胸襟,以至于立诚。不诚则所出之辞为“巧言”,立其诚“则言皆根心而生,始无浮伪之弊”,〔17〕诗文方能“沉郁顿挫”。
一部杜诗,其核心就是“沉郁顿挫”,这是由杜甫“立诚”即天性之近“怨”所决定。陈式云:
古人著一书,必有一书之义。诗虽前后为时不一,而综其生平,亦从来自见。公初献赋之言曰:“臣作述虽不足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给,扬雄、枚皋之流,或可跂及。”沉郁顿挫,公已全乎为怨矣。公稷、契自命之才,年四十,自叙文章,即一归沉郁顿挫,毋亦性与怨近,天故穷之,使尽怨之极致乎?文章不怨不奇,屈原、司马迁其明征也。予于公诗,总主于寻味出“沉郁顿挫”四字。〔18〕
陈式这段话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沉郁顿挫”为杜诗“一书之义”,贯穿一部杜诗始终,其著《问斋杜意》,意在寻味此四字;二是杜甫以稷、契自命,其胸襟高广,故自四十岁时为诗已归“沉郁顿挫”;三是“沉郁顿挫”的核心是“怨”,与杜甫之天性契合,天使之穷,以尽其怨;四是敢怨之诗文才能奇,屈原、司马迁之文因怨而奇,杜甫是他们最好的继承者。总体来说,“沉郁顿挫”的情感核心为“怨”,此即“立诚”的体现。曾与陈式共同讨论杜诗的钱澄之,所见亦相近,他说杜诗“慷慨悲壮,指陈当世之得失,眷怀宗国之安危,一篇之中,三致意云”,〔19〕“指陈得失”与“眷怀宗国”就是“诚”“怨”的体现,此是“沉郁”的内涵;“一篇之中,三致意”的反复申述,此为“顿挫”的表达。只有“沉郁”,才不致平直,故“顿挫”;只有“顿挫”,才不致浮率,故“沉郁”。吴闿生评《述怀》云:“此等皆血性文字,至情至性郁结而成,生气淋漓,千载犹烈,至其顿挫层折行气之处,与《史记》、韩文如出一手。”〔20〕“至情至性”的“血性文字”以“顿挫层折”的方式呈现出来,此种观念与“发愤著书”的精神实质相近。〔21〕
桐城派思索俗体诗“凡近滑易”产生的原因,归结于胸襟凡俗、学识浅陋、闻见狭窄、经历匮乏,形之于诗文,容易走向轻佻滑易,与“沉郁顿挫”相反。因此,要救治其病,必须脱略凡近。方东树云:
古人论文,必曰:“一语不落凡近。”此数百年,小家不能自立,只是不解此义。而其才力功夫,学问识见,又实不能脱此。以凡近之心胸,凡近之才识,未尝深造笃嗜笃信,不知古人之艰穷怪变险阻难到可畏之处,而又无志自欲独出古今,故不能割舍凡近也。凡近意词格三者,涉笔信手苟成,即自得意,皆由不知古人之妙,语云:“但脱凡近,即是古人。”(第240页)
所谓“凡近”,就是“人人胸中所可有,手笔所可到”者(第239页),意、词、格三者一落“凡近”,就不能入古,只有摆脱“凡近”,方能独超众类。方氏评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云:“起四句沉着顿挫,从肺腑流出,故与流利轻滑者不同。”(第404页)出自真性情的诗句,断然不会“流利轻滑”,而是“沉郁顿挫”,后者是根治前者之弊的有效手段。思想阅历的积淀不仅表现在诗文的内容之中,也蕴含在形式之内。姚鼐说:“夫道有是非,而技有美恶。诗文皆技也,技之精者必近道,故诗文美者命意必善。”〔22〕既然“技精近道”,那么技艺之美对应着道之是,技艺之恶对应着道之非。由诗文之美即技艺之精,就可以看出诗文形式之近道,形式如此,“命意之善”即内容之近道就更不用说。“沉郁顿挫”无疑属于“技之精者”,“凡近浅易”无疑属于“技之恶者”。去恶而存美是诗人的追求,因此,只有臻于“沉郁顿挫”,方能扫除“凡近浅易”的俗体诗,这是桐城派力倡“沉郁顿挫”的精神内核。
三、表述:高古厚重
诗文的俗化,在表达方式上呈现出浓厚的口语化色彩。老妪能解的白居易之诗已肇其端,宋诗的日常化写作,且以文为诗,诗歌表达的通俗化逐渐明显;理学家重道而轻文,索性以语录体传道,风气延展,明代性气诗公然以俚俗之语为之。公安派注重向民歌及通俗小说学习,袁宏道《听朱生说水浒传》诗云:“少年工谐谑,颇溺《滑稽传》。后来读《水浒》,文字益奇变。《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23〕其爱好从《史记》转向《水浒传》,语言也随之发生变化,所谓“奇变”,无疑就是以白话入诗文,这是晚明“尚奇”的风气所致。袁枚取村童牧竖之语为“佳句”,其诗风如姚鼐所说“灶下媪通情委曲,砚旁奴爱句斒斑”,〔24〕老妪与书童都能理解喜爱的诗句,定当俚俗平易。通俗化的诗风获得更为广泛的接受群体,占有巨大的文化市场,这是正统文人所无法接受的,必然出手抵制。
桐城派是反对诗文俗化的中坚力量。他们认为俗体诗语言表述与口语无二,一泻无余,缺乏厚重之感。姚范云:“凡文字贵持重,不可太近飒洒,恐流于轻利快便之习。”又说:“凡文字轻利快便,多不入古。才说仙才,便有此病。李太白诗、苏东坡文,皆有此患。”〔25〕语言表达的“轻利快便”,与“贵持重”而生成的高古厚重之风不同。个性飘逸洒脱者如李白与苏轼,诗文语言也不免有此风。方东树称此言为“精识造微之论”(第15页),对姚氏之论深表赞同,并认为“此自宋人习气,时代使然”(第43页),反复指出:“宋以后不讲句字之奇,是一大病。”(第16页)又说:“南渡以后,冗长纤琐。”(第43页)口语表达来不及润色剪裁,故繁琐冗长;语意语序清楚明白,流于“轻利快便”。虽然他没有明说是何种时代因素所致,但不难理解其与趋俗的时代思潮密切相关。黄庭坚作诗“以俗为雅”,就是要调节雅俗之间的矛盾;姜夔力求“摆落一切,冥心独造,此与山谷同恉”,不过仍难免除此病,其《昔游》诗形容大风逐浪为“如飞鹅车炮,乱打睢阳城”,前句完全是口语的表述,因此方东树批评其“已开俗派”(第43页)。公安派及袁枚为代表的性灵诗风,无疑与宋以来的俗化诗风一脉相承。
“轻利快便”的诗风,是用意、用法与选词造句的结果,方东树说:“不知用意,则浅近;不知用法,则板俗;不知选字造语,则滑熟平易。”(第14页)故此,他们除了从胸襟学问上加以纠偏之外,还从文法上进行救治。方氏云:“自赵宋后,文体诗盛,一片说去,信手拉杂,如写揭帖相似,全不解古人顺逆起伏、顿断转换、离合奇正,变化之妙矣。”(第54页)所谓“文体诗”就是“以文为诗”,此与桐城派所讲的“以文为诗”不同,后者主要是以“文法为诗”,而前者是以散体文之表述方式为诗。由于忽略文法,诗文趋于口语化,故方氏又说:“古人之妙,只是能继能续,能逆能倒找,能回曲顿挫,从无平铺直衍。”(第107页)有顿挫自然高古,无顿挫就成口语,“诗文无顿挫,只是说白话”(第533页)。顿挫能避免平直之病,如陶渊明《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一直叙去,而时时顿挫开合,笔势起跌,无平直病”(第105页),杜甫《因许八奉寄江宁旻上人》“只是顿挫,不直率联接”(第412页)。白居易虽开俗派,但其《西湖留别》一诗“用笔用意,不肯使一直笔,句句回旋曲折顿挫,皆从意匠经营锤炼而出”,而刘禹锡、柳宗元则“但放笔直下”(第430页),就难免平直之病。苏轼《次韵述古过周长官夜饮》也是“太快,无顿挫”(第448页),陆游之诗“时有轻促而乏顿挫曲折”(第420页)。可见,“沉郁顿挫”之法可避免“浮率平直”之弊,姚莹分析道:
沉者,如物落水,必须到底方着痛痒,此沉之妙也,否则仍是一浮字。郁者,如物蟠结胸中,展转萦遏,不能宣畅;又如忧深念切,而进退维艰,左右窒碍,塞厄不通,已是无可如何,又不能自已,于是一言数转,一意数回,此郁之妙也,否则仍是一率字。顿者,如物流行无滞,极其爽快,忽然停住不行,使人心神驰向,如望如疑,如有丧失,如有怨慕,此顿之妙也,否则仍是一直字。挫者,如锯解木,虽是一来一往,而齿凿巉巉,数百森列,每一往来,其数百齿必一一历过,是一来凡数百来,一往凡数百往也;又如歌者,一字故曼其声,高下低徊,抑扬百转,此挫之妙也,否则仍是一平字。文章能去其浮、率、平、直之病,而有沉、郁、顿、挫之妙,然后可以不朽。〔26〕
与有的学者视“沉郁”为情感,视“顿挫”为文法不同,桐城派以“沉郁顿挫”为具体的四种文法,与“浮率平直”一一相对。根据姚莹的描述可以看出,后者重在线性流动的时间性,一往直前,从而给人以“轻佻”的浮光掠影之感;而前者重在纵深挖掘的空间性,螺旋下潜,从而给人节奏舒缓的厚重之感。由此,前者被塑造成纠正后者之弊的最佳文法。杜甫《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虽“衔接承递一串”,看似轻便,却“不伤直率”,关键在于“笔笔顿挫”(第410页)。只有在章法上讲究顿挫,才能无直率之弊:“大约诗章法,……真意贯注,一气曲折顿挫,乃无直率死句合掌之病。”(第412页)
“沉郁顿挫”之法往往在文中关键处使用,改变诗文平顺风貌。方宗诚云:
古人之文,无论叙事议论,长短繁简,皆有一意义贯乎其中,或在首作提掇,或在中作关键,或在后作结束,或在言外,令人想象而得之,以此意义为主。至其文之开合反复,沉郁顿挫,皆无非发明此意义,所谓要也、玄也。〔27〕
陈式与方东树都主张一书有一书之意义,一篇有一篇之意义,而一篇之意义,方宗诚认为可以通过“沉郁顿挫”之文法发明,如其论《尚书·梓材》“引养引恬”一句云:“此是文中一上下关键、极沉郁顿挫处。”〔28〕方东树在分析前人之诗时,往往点出顿挫之所在。其在诗之开篇者如曹植《杂诗》:“‘高台多悲风’二句,兴象自然,无限托意,横着顿住。‘之子’四句,文势与上忽离。‘孤雁’二句横接。‘翘思’句接‘离思’。‘形影’句,双结雁与人作收。文法高妙,宋以后人不知此矣。”(第77页)所谓“横着顿住”就是顿挫,此诗首二句写高台所见之景,而三四句则转到怀念远别之人,与开篇不接,直到第七八句“孤雁飞南游,过庭长哀吟”才又与首二句相接。这种“高妙”的文法,宋以后通俗化诗歌中少见。杜诗“往复顿挫”“为起句宗法”(第167页)。结尾顿挫者如鲍照《代白纻舞歌辞四首》其三结尾之“凝华结藻久延立,非君之故岂安集”,此二句“换意换笔,顿挫收”(第349页)。当然,顿挫之法多用在一篇之中间位置,起到关键作用。如鲍照《代东门行》起八句说将别之情,“一息不相知,何况异乡别”二句“顿住,最沉痛”(第179页)。也有句句顿挫者,如黄庭坚《道中寄景珍兼简庾元镇》“句句顿挫,不使一直笔顺接”(第453页)。
“沉郁顿挫”改变平直的表述顺序,形成章法的断裂。姚范云:“老杜自称其长,谓沉郁顿挫。所谓顿挫者,欲出而不遽出,字字句句持重不流。”〔29〕俗体诗欲出即出,毫不拖泥带水;而杜诗则与之相反。欲出即出者,则不免轻利快便;而欲出不出者,使得句子或段落之间产生裂缝,由“流利”变为“顿折”。顿挫之法即为断法,方东树云:“古人无不断之章法,断则必顿挫。”(第180页)“断法”深得桐城派推崇,方氏就说文法“以断为贵”,“逆摄突起,峥嵘飞动倒挽,不许一笔平顺挨接”(第10页),打破平顺呆板的表达顺序,是“意接而语不接”(第94页)。对于断法的领悟,方东树颇为自负,他说:“布置章法知断,今世无人知之,明代诸家亦不知,惟我知之。”(第337页)其实明人亦非无知之者,何景明就说过:“仆尝谓诗文有不可易之法者,辞断而意属,联类而比物也。”〔30〕将“断”视为不二之法门;胡应麟赞《青青河畔草》之妙“独绝千古”,就在于“语断而意属”。〔31〕方氏之目无明人,实可见出其自鸣得意处。断法源自宋人,朱熹发现欧阳修之文“有断续不接处,如少了字模样”;〔32〕苏轼文法《檀弓》,也着意于此(见下文)。桐城派之论断法,当受宋人的启发。
如果说“直说直叙”是“凡近”之习的话,那么“沉郁顿挫”之“断”就制造出“高古”之风,此亦与俚俗诗文大异其趣。“俗人接则平顺騃蹇,不接则直是不通”(第28页),一篇之中若有一两行五六句“平衍騃说,即非古”(第26页),“平顺”“平衍”即“凡近”;“语不接而意接”的断法则“血脉贯续,词语高简”(第28页)。欲避免“轻便滑利顺直无留步之病”(第158页),追求高古厚重,则需改变通常的口语表述习惯,简省冗长纤琐的表达成分,方能呈现出奇崛孤傲、曲折瘦硬之貌。方宗诚赞叹《尚书·多方》“文亦极其沉郁顿挫”,所以如此者在于平直语序的改变:“‘刑殄有夏’以下,原可以接入‘乃惟成汤’,而中间忽插入‘惟天不畀纯’一节,文便沉郁。‘弗克以尔多方享天之命’以下,原可接入‘惟我周王’,而中间插入‘呜呼!王若曰’六节,文便沉郁。此可悟文字不可直说直叙。”〔33〕由于忽然插入某些句子,打破直说直叙的表述节奏,自然“高简”。姚范推崇西汉之文“莽苍”,韩文“文法硬札高古”,〔34〕只有“莽苍”“硬札”,才能“高古”。断法是此得以形成的关键。方东树对高古之诗人推崇备至,他说:“汉、魏、曹、阮、杜、韩,非但陈义高深,意脉明白,而又无不文法高古硬札。其起处雄阔,擘头涌来,不可端倪;其接处横绝,恣肆变化,忽来忽止,不可执著,所以为雄。”(第33页)凭空而起,无端而接,戛然而止,如此“恣肆变化,忽来忽止”,乃无“浮率平直”之弊,造就“高古硬札”之风。他推崇的曹操、阮籍、鲍照、杜甫、韩愈、黄庭坚诸家,无不是善用“沉郁顿挫”之法形成高古厚重诗风之人。
四、风格:刚柔兼济
桐城派论诗文重刚柔相济之美,姚鼐主张“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但这种状态只有圣人能做到,一般人或偏于阳刚,或偏于阴柔,他倾向于前者:“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35〕其弟子吴德旋亦云“文章之道,刚柔相济”,〔36〕管同则说“与其偏于阴也,则无宁偏于阳”,〔37〕各得其师一面。姚门弟子总体来说尚刚,方东树说“诗文第一笔力要强”(第29页),“诗以豪宕奇恣为贵”(第28页),都是推崇阳刚之美。当然,如果阳刚阴柔只有一端而没有另一端,那就会“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阉幽”,成为“无与于文”〔38〕一族,他们所尚的阳刚,包含阴柔成分在内。
在桐城派中人看来,俚俗诗风弊端之一就是阴柔无力。方东树说:“篇短语无多,若截不断,则相承一片,直滚顺放。譬如乘马下坡,前面又无多地,岂不迫促跼步,无驻足分。尚有何势?尚有何奇?何处见用笔?将使题分不得尽,况求异观。”(第215页)用虚字亦容易“截不断”,导致无气:“好用虚字承递,此宋后时文体,最易软弱。”(第19页)诗文如果如流水般顺承直下,则会无势无奇也无气,有阴柔而无阳刚,属于“柔者至于颓废而阉幽”之列。“相承一片”即平笔、顺叙、直写,由上句而能推知下句,缺乏回旋的余地,气势难以振起。方宗诚推崇《孟子》之言“不喜用直笔,不喜用顺接笔”,〔39〕因为“用顺笔则平弱矣”。〔40〕如《公孙丑》“不动心”章中,“不动心有道乎?曰:有”以下,原可直接“我知言”二句,不过这样一来就“平弱无力”;又可直接“昔者曾子”一段,“然尚觉平顺无势”。〔41〕顺承相接则文气不足,这与崇尚阳刚之美的桐城派大异其趣,故遭到他们的批评。
“沉郁顿挫”之文法因顿断而打破平直的文序,摆脱软弱之病,形成诘屈动荡的文势。方东树说:“短篇尤在有丘壑,截得断。断愈多,愈便用奇,愈斩峭,愈见笔力。”(第215页)“截得断”就是顿挫,诗中顿挫越多,文势越不平,越奇绝,诗风就越斩截有力。旧题苏武《骨肉缘枝叶》“用笔转换顿挫,峥嵘飞动,后惟杜公有此”;又《结发为夫妻》“行役”四句顿挫,“古人笔力必写到十分极至处,此最见力量。沉郁顿挫,后惟杜公有之”(第63-64页)。只有用笔顿挫才能“峥嵘飞动”,才能“最见力量”。诗如此,文亦是如此,方宗诚分析《孟子·滕文公》“有为神农”章之顿挫,认为前段辨许行,于“恶得贤”之下,若直入“有大人之事”数节亦可,然觉平直无势力,少精彩。故先用种粟、织布、釜甑诸喻,挑剔诘难,腾挪顿挫,以逼出陈相“百工之事不可耕且为也”一句,然后出“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乃有力,以下畅发乃有势有神,故文字必先蓄势。“当尧”以下数节,虽畅发,然每节下必有停蓄顿挫,下文又提起,又停顿,无一直说下之理。〔42〕口语表达受限于时间的流动性,因此前后顺承,一气直下;而书面语则不受表达时间的约束,可以颠倒前后语序,激起读者的注意力,扫除昏昏欲睡之感,精神为之一震,气势由此而生。吴闿生评《孟子·公孙丑》篇“孟子将朝王”章云:“笔笔顿挫,最见英伟雄厚之气。”〔43〕行文处处顿挫而造就《孟子》之文的气势。相反,如果气势不足,很难形成“沉郁顿挫”之风。方贞观对杜诗多有批评,尤其是夔州以后诗,“气势多散慢,意义有重复,少波澜,不精紧,无顿挫沉郁之致”,〔44〕无气势波澜就乏“沉郁顿挫”,二者之间的关系不言而喻。
俚俗诗风的另一种弊端就是过于阳刚。宋人倡导儒学刚强有力的人格精神,且主张以文为诗,诗文崇尚雅健,〔45〕然过分追求劲健又易于粗豪。在方东树心目中,苏轼之诗“气势紧健,锋刃快利,但失之流易不厚重,以此不及杜、韩”;后世学苏者,“但得其流易之失矣”(第24页),此失即雄直之病,气势如果不加收敛控制,令其毫无阻碍地喷涌而出,则会变得“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在他们看来这也是俗体诗一弊。而挽救之法,亦推“沉郁顿挫”。苏轼可能已经意识到自身诗风的问题,故教学生师法《檀弓》“或数句书一事,或三句书一事,至有两句而书一事者,语极简而味长,事不相涉而意脉贯穿,经纬错综,成自然之文”〔46〕之文法,有意识地以“事不相涉而意脉贯穿”的断法顿挫文势。桐城派与之相近,方东树云:“诗文贵有雄直之气,但又恐太放,故当深求古法,倒折逆挽,截止横空,断续离合诸势。”(第222页)又说:“(文法)秘妙,尤在于声响不肯驰骤,故用顿挫以回旋之;不肯全使气势,故用截止,以笔力斩截之;不肯平顺说尽,故用离合、横截、逆提、倒补、插、遥接。”(第214页)如果仅用平笔、直笔,有阳刚而乏阴柔。平直的语序难以有笔法变化的余地,而“沉郁顿挫”的截断之法,生成巨大的回旋空间,如此,离合、横截、逆提、倒补、插、遥接等文法的运用,才能节制气势。
顿挫之法束住雄直之气,不使其全部释放出来。方氏云:“气势之说,如所云‘笔所未到气已吞’,‘高屋建瓴’,‘悬河泄海’,此苏氏所擅场。但嫌太尽,一往无余,故当济以顿挫之法。顿挫之说,如所云‘有往必收,无垂不缩’,‘将军欲以巧服人,盘马弯弓惜不发’,此惟杜、韩最绝,太史公之文如此,《六经》、周、秦皆如此。”(第24页)雄直导致气势“太尽”,“沉郁顿挫”之法则注重收敛气势,借用美学术语来说,“盘马弯弓惜不发”近似“包孕性顷刻”的美学追求,即不使气势达到顶点,在接近巅峰的时刻适当收缩,如此才不会一泻千里。谢惠连《西陵遇风献康乐》其三中三四句“悲遥但自弭,路长当语谁”就是“折洗顿挫以束之”(第158页);刘琨《重赠卢谌》诗中“中夜抚枕叹,想与数子游”二句“顿挫束上”(第66页),均是有意收缩气势。气势被束缚住不得直接喷涌而出,反而制造出一种特别的“张力”,杜甫《暮归》诗云:“霜黄碧梧白鹤栖,城上击柝复乌啼。客子入门月皎皎,谁家捣练风凄凄。南渡桂水阙舟楫,北归秦川多鼓鼙。年过半百不称意,明日看云还杖藜。”此诗起四句情景交融,后四句叙情,欲南渡而不能,思北归亦不成,人生尽是失意,只能徒留此地杖藜看云,方氏说其“一气顿折,曲盘瘦硬。而笔势回旋顿挫阔达,纵横如意,不流于直致,一往易尽”,由于笔势的顿挫,使得精神鼓荡,臻至刚柔相济的化境:“是乃所以为古文妙境,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矣。”(第415页)杜诗“沉郁顿挫”成为桐城派的典范,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种文法可以锻造出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的审美极境。
“沉郁顿挫”为断法,但断中有连,而俚俗诗风则连中无断。连中无断则气或偏于阳刚,或偏于阴柔;而断中有连则刚柔相济。汉魏诗人之作“大抵皆草蛇灰线,神化不测,不令人见。苟寻绎而通之,无不血脉贯注生气,天成如铸,不容分毫移动。”(第27页)所谓“草蛇灰线”,与归有光评点《史记》所用的“峰断云连”意近,也就是方东树所云“语不接而意接”,涉及章法与气脉的关系。不接之语为“章法”安排,相接之意为“气脉”运行,断法造成章法上表面不连贯,但其题旨归宿则是“血脉贯注”,前后一气相通。“诗文以气脉为上”,又离不开章法:“气所以行也,脉绾章法而隐焉者也。章法形骸也,脉所以细束形骸者也。章法在外可见,脉不可见。气脉之精妙,是为神至矣。”(第30页)气脉隐而章法显,气脉的运行掌控着章法的布局,章法是气脉的形骸。“语不接而意接”的顿挫之法,就是句断,“不将两句合一意,使中相连,中无罅隙,含蓄成叶子金”(第410页),似断而实连,断的是章法,连的是气脉,“沉郁顿挫”之文法将气作为脉隐藏在章法之内,气便成为“潜气”,在断裂的章句之间通过“内转”的方式得以运行,从而造就刚柔相济之美。与之相反,“俗人先无句,进次无章法,进次无气。数百年不得一作者,其在兹乎”(第30页),一味顺接则无法调控阳刚阴柔的力度,丧失中和的美感。雅俗之别,关键在于是否明了诗文的“沉郁顿挫”之法。
桐城派推尊六经及汉魏诗,“沉郁顿挫”之法“非解读《六经》及秦、汉人文法,不能悟入”(第27页),杜甫本来用此四字指称以扬雄为代表的汉大赋之特征,桐城派则将其源溯至六经及汉魏诗,并在后代诗人诗作中揭示这种笔法。方氏称曹操《苦寒行》为“用笔沉郁顿挫”,“气真而逐层顿断,不一顺平放,时时提笔换气换势;寻其意绪,无不明白;玩其笔势文法,凝重屈蟠,诵之令人意满”,断中有续,真气弥漫,由此赞其为“千古诗人第一之祖”(第68页),此亦是杜诗之“沉郁顿挫”所自出。经典作家之外,凡是章法有“沉郁顿挫”之妙的诗人均得桐城派推崇。姚鼐评李颀《寄綦毋三》云:“往复顿挫,章法殊妙。”〔47〕方东树对此有深刻的领悟,他说:
起二句叙事,已顿挫入妙。三四复绕回首句,更加顿挫。第四句含蓄不说出,更妙。五六大断离开,遥接第二句。七八又从题后绕出。大约有往必收,无垂不缩,句句接,句句断,一气旋转,而仍千回百折,所以谓之往复顿挫也。此为正宗,若杜公、山谷,四句兀傲,一气浩然者,亦当以此法求之。否则恐流于滑易,不得归罪杜公、山谷也。(第391页)
李诗云:“新加大邑绶仍黄,近与单车去洛阳。顾眄一过丞相府,风流三接令公香。南川粳稻花侵县,西岭云霞色满堂。共道进贤蒙上赏,看君几岁作台郎?”此诗首联、颔联、颈联、尾联无不顿挫,即所谓“往复顿挫”,虽千回百转,仍一气旋转,是为“潜气内转”。此被桐城派推为正宗,杜甫自不必说,黄庭坚也由此得到姚鼐、方东树等的大力推崇。相反,缺乏“往复顿挫”,就有可能“流于滑易”。在点明“沉郁顿挫”之法时,桐城派往往顺带着以“滑易”诸弊作为对照,此法被他们确立为抵制诗文俚俗化的有效手段。
五、结 语
中国古代社会中,长期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是文言文化,正如彭亚非所说:“在中华文明这一文化系统中,相对于民间文化或社会生存文化而言,文言文化确实就是一种高高在上的、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的文化。”〔48〕而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壮大,诗文的通俗化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口语文化挑战着文言文化。面对这种趋势,士人阶层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他们绝不允许口语文化威胁自身的地位,必然强化文言文化,反对民间文化。
桐城派将“沉郁顿挫”塑造成抵制诗文通俗化的重要手段,在人格修养上区分其与通俗文化之间的雅俗之别,在语言表述、章法安排上提倡高古厚重而贬斥凡近浅易,审美风格上崇尚刚柔相济而批评偏刚偏柔。他们将“沉郁顿挫”与本派的审美追求结合起来,进一步凸显其特点,以经典文法对抗诗文的通俗化。“沉郁顿挫”这一文法之中,蕴含着深刻的文化意涵:它是衡量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分界线,是崇雅而黜俗的不二法门,雅俗之别被浓缩在这一文法之上。
注释:
〔1〕〔清〕方东树著、汪绍楹校点:《昭昧詹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379页。注:由于文中引用此书较多,为避免注释繁琐,皆随文注出页码。
〔2〕〔3〕〔10〕〔26〕〔清〕姚莹著、欧阳跃峰整理:《康輶纪行》卷一三“文贵沉郁顿挫”条,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75、376、376、375-376页。
〔4〕参见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1-41页。
〔5〕〔清〕沈廷芳:《隐拙斋集》卷四一《方望溪先生传书后》,《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9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39页。
〔6〕〔8〕〔47〕〔清〕姚鼐编选、曹光甫标点:《今体诗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3-4、233页。
〔7〕参见潘务正:《姚鼐与袁枚诗学关系考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9〕〔清〕何日愈撰、覃召文点校:《退庵诗话》卷一,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页。
〔11〕〔24〕〔清〕姚鼐撰,姚永朴训纂、宋效永校点:《惜抱轩诗集训纂》,合肥:黄山书社,2001年,第252、465页。
〔12〕〔清〕袁枚撰、王英志编纂校点:《随园诗话》卷二第四则,《袁枚全集新编》第八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7页。
〔13〕〔16〕〔22〕〔35〕〔38〕〔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9-50、49、84、48、48页。
〔14〕〔17〕〔27〕〔28〕〔33〕〔39〕〔40〕〔41〕〔42〕方宗诚:《论文章本原》,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六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650、5650、5617、5640、5645、5661、5668、5673、5682页。
〔15〕〔32〕〔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论文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320、3308页。
〔18〕〔清〕陈式:《问斋杜意》卷首《读杜漫述》第六则,康熙二十一年(1682)陈氏侧怀堂刻本。
〔19〕〔清〕钱澄之撰,彭君华校点、何庆善审订:《钱澄之文集》卷一四《叶井叔诗序》,合肥:黄山书社,1998年,第259页。
〔20〕吴闿生:《古今诗范》卷四,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0年,第47页。
〔21〕关于“沉郁顿挫”与“发愤著书”传统之关系,参见王南:《“沉郁顿挫”论》,《文学遗产》1993年第4期。
〔23〕〔明〕袁宏道著、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18页。
〔25〕〔29〕〔34〕〔清〕姚范:《援鹑堂笔记》卷四四《文史·谈艺》,《续修四库全书》第114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12,114,113、111页。
〔30〕〔明〕何景明著、李淑毅等点校:《何大复集》卷三二《与李空同论诗书》,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576页。
〔31〕〔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第34页。
〔36〕〔清〕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21页。
〔37〕〔清〕管同:《因寄轩文初集》卷六《与友人论文书》,《续修四库全书》第150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30页。
〔43〕高步瀛集解、吴闿生评点:《孟子文法读本》卷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中文系,1979年,第14a页。
〔44〕〔清〕方贞观:《方南堂先生手批杜诗》第六册“扉页”,〔清〕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金陵叶永茹刻本。
〔45〕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25-333页。
〔46〕〔宋〕费衮撰、骆守中注:《梁溪漫志》卷四,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97页。关于宋代“文法《檀弓》”的研究,可参看聂安福:《宋人“文法〈檀弓〉”说解读》,《文学遗产》2010年第2期。
〔48〕彭亚非:《中国正统文学观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