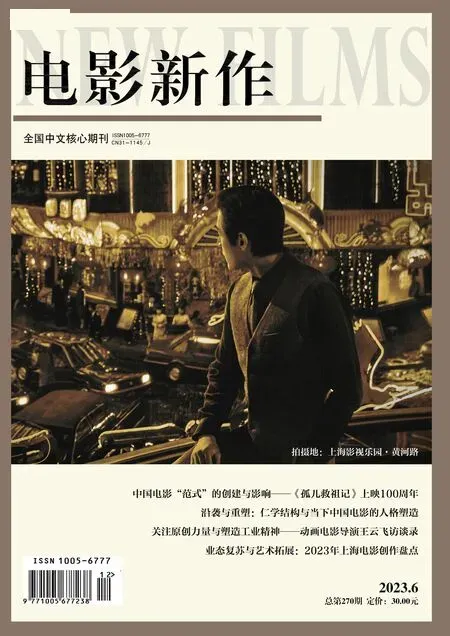“它”的存在和“我”的彷徨
——论当代好莱坞科幻电影中人工智能形象的表演维度
李天辰
人是一种必须要将自己认识为人、使自己成为人的动物……唯有当他让自己提高至人之上,他才能成为他自己。1
——卡尔·林奈
约一个世纪以前,动物学家雅各布·冯·尤克斯考尔曾做过一个关于蜱虫的实验:这种靠吸食哺乳动物温热血液维持生命的小虫子没有眼睛,也听不见声音。雅各布·冯·尤克斯考尔通过实验确认了蜱的全部感官与捕食机制:它靠嗅觉捕捉到路过的哺乳动物的行踪,一跃而上,靠温度的感觉器官确认37℃体温的猎物,靠触觉找到毛发掩盖之下的下口之处——皮下血管。这便是蜱与世界的全部关联,而世界对于蜱虫来说,只有这么多——雅各布·冯·尤克斯考尔将其称为蜱虫的“生态圈”(Umwelt),由一系列对蜱虫来说“有意义的载体”(Bedeutungsträger)构成。2
人类要如何表演一只蜱虫?如果以动作驱动,人类的肢体构造与蜱虫相去甚远;如果以情感经验驱动,表演者很可能会完全迷失在对蜱虫极度陌生又有限的非人感官的无穷想象之中。但日本的舞踏艺术家定会认为这并非不可行,舞踏里的灵魂可以幻化成世间万物,人类的躯体可以表演“龙”也可以表演“燃烧的腐木”3,想必蜱虫也不在话下。如果在电影里出现一只蜱虫,则大概率不会由人扮演。当人类演员在银幕上表演非人时,他通常在表演与人外表相似的某种角色:神、人形怪物、人形动物,或是人形人工智能。
当下,我们正处在一个神话般的时代里,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技术成果在演示大会上安抚人类不用担心它们/他们向创造者反叛。以创作为生的人类画师在艺术家群体中最先感受到来自人类造物的威胁并发出抗议。唐娜·哈洛威(Donna Haraway)认为我们都是延伸意义上的嵌合体/赛博格,机器的发展已经模糊了种种边界。一些人预言象征着超越的下一个技术“奇点”正在到来。另一些人,并不矛盾地,认为作为20世纪一系列人类活动导向的后果,即我们已经进入了人类历史的尾声。电影正如一面镜子反映出这个时代的样貌,映照出那张饱含憧憬、焦虑,并难掩兴奋之情的人类的脸。

图1.电影《银翼杀手》剧照
人对人工智能的关切来源于对人类自身的关切。正如现代科学分类的奠基人卡尔·林奈(Carl von Linné)在他的著作《自然体系》(Systema Naturae)中反复指出的那样:人与自然界其它动物并非处于谱系的两端,而是同处于连贯的物种延续之中。人处于人形动物的序列里,而唯一让他/她与众不同的特征是认识自己的能力。也就是说,人是一种必须要将自己认识为人、使自己成为人的动物。4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将自己认识为人,人为了在非人中辨出自己,反复修改划定界限的定义。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将这个保护自己作为人类的边界的机制称为人类机制(Anthropological Machine)。而人工智能的出现,如同历史上进化论的提出一样,正预备着再一次猛烈冲撞原本间歇性趋于稳定的人类定义的边界。但与后者不同的是,这一次冲击不再是关于对前历史的追溯,而是有关下个阶段的颠覆性转变,甚至或许是为所谓“人类世”的终结摇旗助威。在种种讨论、争议以及艺术表现,如电影中,人们继续努力通过人类机制的两个变种试图辨认自己:或将人工智能排斥在外,或纳入内部。人类机制的艺术表达毫不遮掩地体现在好莱坞主流科幻电影中,但同时,反人文主义的话语也在一些作品中凝结出另一种表述。人将对人工智能形象的想象通过在影片文本中的多维度塑造来完成,其中包括人类演员对它/他的表演。
一、排斥,人工智能形象的“非人化”表演
笛卡尔的二元论哲学立场的涟漪从三个层面上影响着人类对人工智能的认知、思考,以及艺术形象的创作。首先,在笛卡尔看来动物没有智慧和直觉,它们的所有行为皆为身体的机械反应,而不存在心灵的操作。动物是一部自动机器。这种对于人/动物的粗暴对立划分成为机器人与人之间区分的一种粗陋的原型范本。其次,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将心智与身体独立区分,由此,动物-人的有机体与机器之间的界限由“机器里的鬼魂”5存在与否来判决。最后,笛卡尔的二元论立场将自然与“大写的人”区分开,人类活动和自然界的其他部分被当作两个虽互相影响但独立构成的行为单元。人工智能在这样的立场下成为一种与自然脱离的造物,一种产品。

图2.电影《大都会》剧照
笛卡尔对于动物的论断早就遭到了驳斥。继而,当人类被归入灵长类动物之后,动物和人之间出现了难以定义的中间地带,人的边界遭到威胁。一方面,生物学的研究从人与猿、猿人或人猿的解剖学比较进展到了基因测序,却总在进一步验证人与动物的延续性;另一方面,林奈关于人类唯一特征所下的断言——将自己认识为人——描述出人类机制运行的基础。在人类机制的运行下,语言作为一个首要元素用以区分人和动物——这是被质疑的,因为语言是历史的产物,而非自然给定的东西,因此前语言的人类阶段成为一个悖论。阿甘本指出,现代的人类机制通过排斥起作用,将尚不是人的人区别于人类本身,如猿人。6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人工智能,则会发现,在笛卡尔区分动物/人的直觉心灵元素失效后,新的区别方式是无法适用在这里的。人工智能,作为语言的产物,甚至是比人类更为纯粹的语言使用者。为了保护边界,人类机制的排斥作用不得不寻找人工智能与人之间特有的区分地带。但这是否意味着,人类边界的划定不仅是反复游移不断修正的,而且甚至无法根基于人类本身,而是取决于外部对象的转换?
电影里的人工智能形象首先是“非人”的,即使披上“人”的画皮。外形越接近“人”的,越常被用来强调与“人”的差异。在科幻电影中,除了机械身躯和无实体外形等明显的外表差异之外,人形肉身的人工智能形象早在1927年的《大都会》(Metropolis)中就已出现,时间越拉近现在,外形差别越经常被消抹。如果不考虑视觉无法触及的内部机制的话,趋近于“真实人类”的类人人工智能外观常常被当作一个不变量固定下来,以便于探索或建构人与“非人”之间更本质的差别。或者说,只有当假想的分界处被拉近人类时,“认出自己”的人类机制运作才是有成果的。在类人人工智能角色身上,我们常看到人/人工智能的各种区别元素被创作者想象出来。这类想象,往往指向电影试图探索的与存在相关的哲学命题。在《银翼杀手》(Blade Runner,1982)里,这种差别是生命的时间跨度。在《银翼杀手2049》(Blade Runner2049,2017)中,它是自然生育能力和记忆的原初性。在《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2012)中,它是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在《超验骇客》(Transcendence,2014)中,它是生命极限的有限性与超越性的对抗。当这些“非人”角色由人类演员表演时,演员往往有意识地模拟一种想象中的区别于人类惯常的表情或动作细节来为人工智能的差异打上印记。这些印记,或见之于著,或见之于微。在《杨之后》(After Yang,2021)中,机器人杨虽然外表与亚洲人类无差,并被设定为拥有完备的知识体系和高度的共情能力,会使用创造性的比喻解答人类妹妹Mika的困惑,且性格谦逊温和,然而与人类的差异性却在最细微处浮现。在杨与养父母的两场对话戏中,杨显露出与对话者不同的气质。通常情况下,即使在最温和的人与人的对话中,也往往暗藏着博弈、试探、侵略和自我保护,发话者和接受者一来一回地进行行动和反应的游戏。但在杨和“养父母”Jake或Kyra的对话中,杨仿佛包裹在一层既无防御又无进攻的柔软的社交海绵之中,仿佛可以让人类对话者在放下戒备的同时,陷入反客为主的凝视之中无所遁形。杨的扮演者贾斯汀·闵在本片的对话表演中有一个区别于对话者的特点:除了观察物体或思考答案以外,他的目光总是无所顾忌地停留在对话者的面庞之上,与对话者在被凝视中闪躲的目光形成对比。滨口龙介在谈论导演《欢乐时光》的创作经验时曾提到,由于我们的身体比起言语会更直率地述说,而言语比身体可以更准确地传达信息,所以,当人们在对话时,会“心照不宣地达成避开‘互相凝视’的协定”。7这样的协定,没有被身为“非人”的杨遵守。比起较早的科幻电影中类人人工智能身上常见的怪异或身体不协调的机械化动作等差异表现,对杨的表演显然是更加细微的差异,是更加独特的将人工智能区别于人类的特征。或者反而言之,这种细微的表现差异体现出人类社会建构而成的文化、习俗等行为的不自觉内化,形成了人类机制中对自身的边界保护。
在考虑机器与人的差异时,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的影响正在逐渐淡化。当下人工智能形象已经很少呈现为弗兰肯斯坦的怪物、或是《大都会》的玛丽亚那样,将心智或灵魂注入机体的容器之中。部分原因可能如哈洛威所言,在现代生物学中,“有机体已经被翻译成基因编码和读出的问题”,“关于机器和有机体的概念已全然改观,两者皆是被编码的文本,借此我们得以参与书写及阅读世界的玩耍”。8正如电影《千钧一发》(Gattaca,1997)中所展现的那样,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技术让人类自身的编程设计成为可能,自然的确定性也由此受到永远难以恢复的损伤。在此基础上,有机体和机器、自然和人为、心智和身体、自我发展和外在设计的界限也被渗透了,人类机制的齿轮在此处生锈,人工智能也似乎从人类创造的伊甸园出走。正如大卫从《普罗米修斯》里的服从听命于人类,到《异形:契约》(Alien:Covenant,2017)中发展出“自我意识”,当代人工智能角色的“自我觉醒”常常由自身的经验、学习、思考/演算与进化迭代习得,而非造物者本意赋予。
作用于排斥机制的还有另一种受到二元论影响的观念:人工智能属于人类活动的一部分,一种资本主义社会人类劳动的产品与文明的产物。作为一种客体化的物,人工智能和解释并控制自然的主体性的人类有本质上的不同。本体论和认识论在15-18世纪间形成,成为思考世界的思维方式。这种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是资本主义文明建立起来的基础,也是“人类世”叙事的根基。在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里,人是大写的,是文明或社会的成员,或两者皆是。9美国学者Jason Moore认为这种割裂的二元论立场导致“人类世”的表述是有问题的。但有趣的是,也正因为此,人造人工智能却获得了与部分自然出生的“小写的人”——也就是通过排斥的作用在人之中产生的“非人”——进入同一区域的机会。纳入的机制总是和排斥机制同时起作用,建立起人类——或者说“大写的人”——边界的护城河。
二、纳入,人工智能形象作为“小写的人”
阿甘本对“神圣人”(Homo Sacer,又译作“牲人”)概念的论述来自古罗马法。在罗马法中,“神圣人”指那些被视为既不受法律保护(杀死他的人不用承担法律后果),又不能被用作祭祀的个体,这些个体被神和城邦双重抛弃了。在阿甘本的解读中,失去了人类共同体庇护的“神圣人”是一种不允许其他任何属性的生物学存在,也就是沦为了他所称的“赤裸生命”的形态。10在《敞开:人与动物》中,阿甘本进一步指出,人类机制“必然通过排斥(通常也就是一种俘获)和包含(通常也就是一种排斥)来发挥作用”。11通过纳入性的排斥,将人动物化产生非人:这里有动物、有猿人,有昏死状态的人,也有时间向前推进几十年的纳粹政治下的犹太人。同时,通过排斥性的纳入,“非人”也通过对动物的人化产生:人猿、野孩子、野人。由此,人工智能在被排斥的同时,也被纳入为人类形式中的动物形象。人与动物/非人之间的例外空间是一个不断变换的模糊地带,这里既是排斥区又是包容区:被法所排斥,又收容着被从自身剥离的赤裸生命。不过,这里谈收容没有意义,因为它并没有给被收容者任何庇护。

图3.电影《索尔之子》剧照
如果我们确实能将人工智能当作“非人”的人化的一种特殊形态,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考察他/它与另一种更确切的赤裸生命形态在银幕形象塑造上的相似性。在《银翼杀手》第一部(以及原作《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的故事中,复制人被设计成具有类似于人类的特征,具备由人工合成的生物体形态,具有难辨真伪的人类外貌、肌理触感、比人类更强健的运动能力,也有感知能力和情感。然而,复制人的认知和情感能力是基于预设的程序和算法,他们被禁止拥有真正的自我意识和情感体验。为了确保这一点,复制人的寿命被限制在4年,这个时间跨度被认为可以限制复制人通过经验习得自主情感的可能性。而在第二部《银翼杀手2049》中,复制人的寿命已大大延长,情感和自主意识也不再是区分人和复制人的标准,改进后的复制人可以更好地完成人类交付的工作。《银翼杀手2049》的主角新型复制人K,部分地延续了前作主角Rick Deckard的身份和任务,猎杀可能会对人类社会造成威胁的复制人(Replicants)。两者在角色设定上最大的不同在于,从一开始K就明确知道自己身为复制人,却为人类残害自己的同胞,而Deckard捕杀复制人却建立在以为自己是人类的认知上。从这些被人类共同体以纳入的方式排斥的复制人身上,我们几乎可以清晰地辨认出一种近似于“神圣人”的状态。与之相对称的,大屠杀电影谱系的文本总是关注一类原本已然为人,却被排除出共同体,作为“非人”存在的范本——政治下的犹太人。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比较《索尔之子》(Saul fia,2015)与《银翼杀手2049》关注的群体以及主角形象在表演层面的角色塑造。前者的主角索尔(Saul)是一名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犹太人囚犯。特殊之处在于,他还是“囚犯特遣队”中的成员。“特遣队”由犹太人囚犯组成,被迫协助管理、监督其他犹太人,或为集中营内部灭绝行动的执行打下手。同时这些“队员”相对于其他囚犯享有一定“特权”。但在做工数月之后,他们依然会被处死。在两部影片的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两位主角各自在面对同胞执行自己的“任务”时所表现出的压抑与克制,以及麻木与无奈之间的矛盾。《索尔之子》开场,匈牙利诗人盖佐·罗赫里格(Géza Röhrig)饰演的索尔嘴唇紧抿、眉头微锁、面色憔悴阴郁,此刻的任务是将初来乍到的新一批同胞领入通向地狱的大门。索尔在人群中穿梭,背景里一个声音在诉说一个谎言,催促这群人进入实为毒气室的淋浴房。索尔不发一言,毫不犹疑地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他伫立在那里,眼看着赤身裸体的同胞们排队进入毒气室。他直面着这个队伍的一张张面孔,而非不忍地移开目光,或不舍地目送同胞们的背影。毒气室的门关上,他的呼吸更重了一些。直到那个从毒气室幸存片刻的少年出现,我们才第一次看到索尔的关切。《银翼杀手2049》开场,瑞恩·高斯林(Ryan Gosling)扮演的K背光坐在阴暗的屋里,安静地等候旧型复制人萨珀·莫顿(Sapper Morton)的归来。当将要回收(销毁,或说:杀死)的同胞转向他时,K的面容从阴影中显露,五官没有焦虑愤怒却眉头暗锁。虽是在暗处盯紧猎物的捕猎者,却姿态放松地跷腿坐着,收起所有肢体上的侵略性和威迫感。当萨珀与他生死相搏时,K快速精准地狠狠反击并制服对方,下手毫不手软。当他站在重伤不起的对手面前时,K用近似恳求的口吻请对手不要站起来,语气中尽是疲惫和无奈。当萨珀没有听取这个意见时,K迅速扣下了扳机。我们可以看到K的主动自觉的动作行为和他下意识的姿态之间似乎处处充满不协调和矛盾。直到之后他开始意识到,这位同胞在临死前所说的“奇迹”意味着什么——复制人可以自然生育,人/复制人的边界动摇了——K的情绪终于以肉眼可见地开始波动。
除了面对各自的同胞以外,在面对受人类机制庇护的“大写的人”时,犹太人索尔和人工智能K的表现也出现了明显的相似性。索尔在做“特遣队”的工作时,处于官兵的监视之下,服从于这些剥夺了自己权利、并可以任意杀死自己同胞的人。在官兵粗暴的辱骂、喝止、指令之下,索尔低眉顺眼,以看似冷静的沉着应对一切危机,顺从地将身体的主导权交出。但在所有不见光的角落里,或是不被监管的片刻,他谋划着一个微小目标——给男孩一个葬礼。葬礼意味着,灵魂不被抛弃。主体虽然被剥夺了政治生命,但不会完全沦落为赤裸生命。所有小心翼翼地顺从主权者放低的姿态,构成索尔用以隐藏内心的保护色。《银翼杀手2049》中,K作为极少数的合法新型复制人,和底层人类混居,仍遭到周围的歧视。而K对此习以为常,可见合法复制人在社会所处的地位。在完成任务回到总部汇报时,浑身血污狼狈的K与文明社会身穿制服的人类同僚在走廊擦肩而过。面对恶意的挑衅辱骂,K侧过头,低眉、颔首、垂眼,沉默地快速走过。紧接着,他走过下一个对他没有做出任何反应的人类同僚。而我们却看到,K依然做出了同样的动作。隐忍、顺从和自视卑微已然成了K的行为习惯,但这是他的角色本质吗?在《银翼杀手》第一部中,一套缜密的“移情测试”曾被设计出来用以检测被测者在回答问题时的细微生理反应,来判断被测者是人还是复制人。而在《银翼杀手2049》中,测试升级为了“基线测试”,用以测试复制人的心理稳定性和情感控制能力,来判断被测者能否继续胜任工作/被使用。K在结束任务之后,立即返回总部接受基线测试。但在发现复制人生育“奇迹”并开始探求真相之后,这种麻木发生了变化——自然生育能力从根本上抹除了人与复制人的界限,K所代表的群体与“人类”已无本质区别。在他误以为自己便是“奇迹”的天选之子后,第二次基线测试K失败了。面对机器念出的并无感情的暗示性语句和问题,K的心绪波动体现在每一次努力克制住的喉结的颤抖、回复的犹疑和呼吸的躁动上。和索尔一样,他需要用谎言来继续维持对自身“忠诚”的伪装。
索尔和K的区别在于,索尔的生命是短时间内确定会被剥夺的,他的赤裸生命状态是一种确定的从生到死的倒计时过渡,不仅仅是“可以”被杀死,还是一定会在某个未知的特定时间被杀死;而K看起来相比于完全被剥夺生命权利的索尔而言享有一定的权利。如果他可以通过基线测试、如果他情绪稳定且不会有反叛人类之心、如果他作为个体并不象征着复制人侵入人类机制边界的生命“奇迹”,那么他就有机会一直活下去,完成人类交付的各项任务,和虚拟女友一同生活,直到寿终正寝的回收之日。然而,K的存在却依然表现出一种“神圣人”的状态。因为正如他在得到命令要销毁复制人之子时,提出自己从未回收过自然出生的东西,便可得知:在这个社会中通行的法的观念里,K自身由于不是通过出生来到这个世界,因此也可以在这个社会被随意剥夺生的权利。或者说,他并未真正拥有过生的权利,即使他看似暂时性地处于体制结构内。相较而言,在科幻叙事下的K的角色塑造也许对当代观众的警示意义并不会更少。因为在阿甘本看来,当代社会中,我们每个人都是潜在的赤裸生命。事实上,K的角色命名也很难不让人想起卡夫卡的《诉讼》(又译作《审判》)和《城堡》。K既可以代表“诬陷者”(kalumniator),又可以代表土地测量员(Kardo)。诬陷者质疑了法,而土地测量员质疑了边界。12
三、表演主体的合法性和可能性
现在回头看本文最初提出的问题,人要如何表演一只蜱虫?也许我们也可以提问:人要如何表演人工智能?在我们的科幻叙事中,人工智能越来越倾向于被塑造为具有与人类相似的形态和能力。如果人工智能也有机会处在延续连贯的物种序列中,那么一定是远比蜱虫更靠近智人的存在。如果人类可以表演一只猩猩,为什么不能表演人工智能呢?若我们摈弃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也许可以换一个问题问:猩猩可以表演人类吗?
雅各布·冯·尤克斯考尔所说的生态圈并非只针对蜱虫,事实上,所有的动物、包括人类都封闭地生活在各自的生态圈内,与“意义的载体”相关联,而与世界其他无意义的部分隔绝。由此我们可以说,智人与其他物种感知到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那么,人类演员还可以体会非人角色的内心情感吗?还能在环境给予他刺激时做出非人角色本身应有的真实反应吗?我们可以观察到,在《猩球崛起》(Rise of the Planet of the Apes,2011)这样饱受赞誉的影片中,安迪·瑟金斯(Andy Serkis)对主角凯撒(Caesar)的表演是多么拟人化。再试问,如果有一只猩猩真的获得超越人类的智力,它的生态圈也会因此与人类相吻合吗?由它来扮演的凯撒会是电影中这样吗?如果不是,那么人类对“进化”后的猩猩的表演是一种自大的想当然吗?
当我们将人工智能当作一种生命或类生命看待时(正如相当一部分科幻电影所尝试的那样),只要人工智能技术还是基于计算机语言的,就很难假定人工智能角色的生态圈和人类是相通的。我们可能不得不把人工智能假设为不同于智人的一个物种。但这里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当表演自然界现成存在的物种时,我们可以忽略它的感受而单纯模拟它的体态、动作、表情(五官动作)。我们在塑造类人人工智能角色时,往往将它的体态、动作、表情设计为对人类的模拟。这种模拟通过计算机理解和处理自然语言、从数据中识别情感表达、推理算法、生成自然语言等复杂而精细的程序达成。也就是说,人类表演人工智能其实是在模拟人工智能对人类的模拟。那么,第一维度的失真是否可能将第二维度的失真转化为一种宽泛的真实?正反模拟下的双重失真是否反而为人类表演人工智能奠定了可行性基础?
在海德格尔那里,生态圈的概念被命名为去抑环境,“意义的载体”被命名为去抑因子,动物与它的去抑因子的关系是沉浸的关系。13这意味着,因为沉浸在自己的生态圈内,对于动物而言,“将某物领会为某物的基本能力遭到了抑制”。14而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只有人,事实上,只有本真思想的根本性的凝视,才能看到敞开,命名了存在物无蔽状况的敞开”。15封闭并迷失在去抑环境中的动物,无法揭示自己的去抑因子,因此看不到这种敞开。这也许可以帮我们理解《银翼杀手》中鲁格·豪尔(Rutger Hauer)演出的Tears in Rain一场戏为何能成为影史经典。豪尔扮演的复制人罗伊·巴蒂(Roy Batty)在求生的动物性本能驱动下展开一系列行为,进而发展到对主角Deckard动物性的猎杀。当短暂寿命导致的死亡终于要降临时,一种惊人的转变在观众眼前发生。Roy的行动结束于临终前在顶楼对Deckard的施手相救。紧接着,他手握白鸽在雨中发表了彰显纯粹“人性”的著名演讲,与世界的关联不再封闭于复制人的去抑环境内:C光束不仅在“汤豪泽之门” (Tannhauser-Gate)的黑暗中闪耀,也在此在(Dasein)被悬置的虚无的永夜中闪耀。Roy完成了人类机制上边界的突破,实现了从“动物”维度到“人”之维度的超越性飞跃。这种飞跃也为当代科幻电影后人类叙事提供了一种人工智能形象的范本,并在各个文本中延续。当人工智能和人不再有本质区分时,当人工智能和人一样看见敞开时,人将失去自己的物种特殊性,而人工智能的可表演性问题也将不复存在。
与此同时,在文本之外,更加现实的革命性突破正一步一步切实进行着。在《机械姬》(Ex Machina,2014)中,女主角Ava的形象呈现为人形与机器的嵌合形态。通过成熟的动作捕捉技术,计算机协助艾丽西亚·维坎德(Alicia Vikander)出色地完成角色塑造。《超验骇客》中,主角威尔的人形面孔以不少于五种形态出现。除了由Johny Depp表演的真实的人类威尔,以及以不同真人形态出现的超级人工智能威尔以外,比较特殊的几种形态是死亡后被连上网时显示在屏幕上的威尔。第一次他生硬的面孔映在屏幕上时,讲话时几乎只有嘴巴在动,这是通过计算机技术完成的虚拟人“表演”:首先通过数据采集得到Johny Depp的数字面孔,再通过CGI技术完成表情和动作的虚拟表演。虚拟人威尔每次出现都比前一次多习得一些近似于真人的表情,来完成和女主的情感沟通,包括并不限于挑眉、微笑、眨眼、视线跟随和目光转移等,根据谈话内容选取适合的表情展现,直到最后Depp再次以不借助特效的真身表演威尔。在表演主体从计算机算法转换到Depp真人之间,是一系列近乎连贯的变化,让人几乎难以辨别从何时起演员占据的主体性要多于计算机。虽然不是物理性的,人和机器的边界确实在此处互相渗透了。人工智能形象的表演主体,正如哈洛威在《赛博格宣言》中所呼吁的那样,早已实现了人(动物)和机器的融合。而这种赛博格式的融合,在哈洛威看来,可以帮助我们学会不当“大写之人”。那么,在这种融合之下,我们又如何可以断言,在谈到表演艺术时,表演主体一定指涉为人类呢?当人与机器、或者说人与人工智能的共生体成为表演主体后,更多的可能性也许将不仅仅出现在科幻电影中。
【注释】
1[意]吉奥乔·阿甘本.敞开:人与动物[M].蓝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32.
2 同1,49.
3 刘炼,孙慧佳.舞踏中的身心关系的问题研究[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4):172-176.
4 同1,32.
5 the ghost in the machine机器中的幽灵是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提出的,用来反驳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转引[美]唐娜·哈洛威.猿猴、赛伯格和女人:重新发明自然[M].张君玫译.台北:群学,2010:248.
6 同1,45.
7[日]滨口龙介, 野原位, 高桥知由.滨口龙介:那些欢乐时光[M].沈念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23-24.
8 [美]唐娜·哈洛威.猿猴、赛伯格和女人:重新发明自然[M].张君玫译.台北:群学,2010:267,248-249.
9 Jason Moore.The Rise of Cheap Nature[A],in Anthropocene or Capitalocene? Nature, History,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C].edited by Jason Moore, PM Press, 2016:78-115.
10Martin Puchner.Performing the Open: Actors, Animals,Philosophers[J].TDR (1988-), 51(1),2007:21-32.
11同1,45.
12同1,36-71.
13同1,61-62.
14同1,63.
15同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