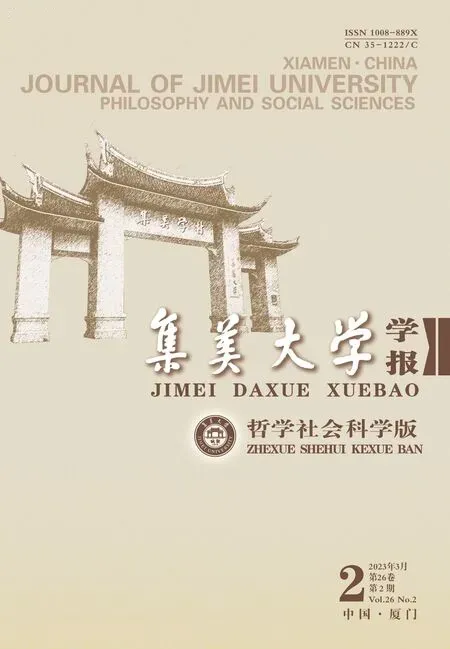黄檗宗与普度文化对日本送船民俗的影响
——以“舟子流”为例
林 涛,黄燕青
(集美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一、引 言
2020年,以福建为实施主体的“送王船”民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值得关注的是,此次“送王船”民俗的入选是中国和马来西亚共同申报的成果。换言之,“送王船”民俗的入选本身体现了中国海洋文明以移居华侨为载体,进入东南亚文化场域并且实现域内域外共同融合兴盛的过程,是文明互鉴、民心相通、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典范之一。与妈祖文化类同,“送王船”文化研究成果集中于华人文化圈,但是这一文化习俗在海外非华人受众的跨语境传播的发掘、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话语模式建构方面的学术研究还比较少。黄燕青、任江辉的《中国海洋民俗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及影响——从“彩舟流”到“精灵流”》一文着眼于日本长崎的盂兰盆节庆习俗“精灵流”,讨论了“送王船”民俗于江户时代在日本延伸为华侨华人圈里的“彩舟流”,后融入现代日本九州地区的“精灵流”习俗,从而建构独特话语体系的过程[1],该文为本研究奠定了阶段性的基础。
本研究的着眼点,首先在于空间设定,选择了日本岩手县盛冈市的“舟子流”习俗为对象,在空间路径上自临近中国的九州“窗口”一跃纵深至日本本州岛腹地的东北地区;其次,围绕“舟子流”习俗的研究,多散见于日本的本地乡土人士撰写介绍节日风俗的科普书籍之中,本研究则是去芜存菁;最后,围绕普度文化或者福建黄檗宗在日本的传播研究,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民俗学界皆存在着大量的研究积累,而新史料的发现与挖掘将有助于这一研究的持续深入。基于此,笔者拟从文化人类学、传播学角度进行探讨,结合黄檗宗这条中华文明传播线索,发掘新史实,展现“彩舟流”习俗跳出华侨华人圈、进入地域性的话语体系的高层,并成功根植于日本民众内心世界的过程。站在更为宏大的视角而言,时至今日,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深入人心,然而往朝鲜半岛、日本的东北亚航线尚未获得足够关注,研究成果有限。本研究聚焦中华元素在日本、尤其是日本东北地区的民俗仪式之中的传播,旨在弥补该项不足,也具有开拓性的价值。
二、盛冈“舟子流”概况
“舟子流(funekkonagashi)”是每年盂兰盆节(即农历八月十六日)盛行于日本东北地区北上川流域、岩手县盛冈市等地的送船仪式。其仪式仪轨与中国东南沿海的“送王船”民俗相似。该活动以当地寺庙为举办主体,以村落街町为单位,各派一条龙船,全市共十余条龙船参与。举行活动之际,由仅身着“裈”(即满裆裤)的十余名青壮年男子抬着一艘约五六米长的木制龙船在村落内巡游,船上载着写有“南无阿弥陀佛”与村民们过世亲人名字的“万灵供养塔”。到了黄昏时分,众人将龙船抬至北上川河中,点燃龙船“化吉”,以水火净化的方式送亲人亡魂往西方极乐净土,表达对故人的思念之情。
“舟子流”源于享保年间(1716—1736年)岩手名刹大慈寺在河岸举办的“施饿鬼”法事,迄今约400年历史[2]55。明治时代之后,每逢战事天灾,均行慰灵法事,如今该仪式在保留最初的“万灵回向”功能的基础上,还出现了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等一般性俗信功能。“舟子流”由“盛冈舟子流协赞会”组织开展,下辖28个村落团体,各村落街町的町内会(类似居委会)会长领导,町内青年会为执行主体。与最初纯粹的民俗仪式不同,现在仪式举行之后常伴随举行烟花大会,与长崎地区的“精灵流”相同,这一活动逐渐演变成振兴当地经济的旅游资源,由最初的小范围民俗仪式扩大为宗教法人、信众、区域内外一般民众以及当地行政部门共同参与,兼具仪式感、娱乐性、神秘性、传承性的一项综合性活动[3]。
三、“舟子流”的中华源流考
据笔者考证,“舟子流”仪式的产生与中国福建传入日本的佛教黄檗宗有密切关联。具体而言,黄檗文化直接奠定了“舟子流”仪式的参与主体、核心内容、基本目标,从而令普度文化在日本东北地区得以扎根、发展起来,成就了如今的“舟子流”仪式。
日本黄檗宗的创始人是来自福建福清的高僧隐元隆琦。明末清初之际,隐元主持临济宗寺院黄檗山万福寺17年之久,对闽浙佛教的兴盛做出了巨大贡献。1654年,应长崎华侨多次恳请,隐元禅师东渡日本,进驻长崎唐寺兴福寺。次年,隐元受请住持长崎崇福寺,后又前往大阪、京都、江户等地弘法。1661年,在德川幕府支持下,隐元在京都宇治开辟新寺并任住持,命名黄檗山万福寺,以示不忘祖庭[4]。京都万福寺的开创,标志着来自中华的临济宗黄檗派在日本落地生根,日本禅宗新兴宗派——黄檗宗由此成立。
黄檗宗自创立时期到1745年的不足百年期间,在日本各地迅速发展起来,寺庙数量增加到1 043家,在禅风思想、戒律清规、法式仪轨、教团组织、丛林制度等诸多方面深刻影响了日本佛教界。以隐元为代表的一批僧侣在东渡日本之后,不仅在佛教思想,还在文学、语言、建筑、雕塑、印刷、音乐、医学、茶道、饮食、绘画、书法、篆刻等方面,将明清文化融入日本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化形态,称之为“黄檗文化”[5]。
提到“舟子流”仪式的来由,日本东北地区保留了一个统一说法,涉及本地的重要历史人物——幕子公主,且存在着以“墓碑”为代表的不少历史文献资料的支撑,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与实存性。相传南部藩(岩手县原所属藩国)第四代藩主行信公第七女幕子公主在14岁的时候嫁与骏河守护(今静冈县)毛利高久。两年后离异,改嫁和泉地区的陶器藩(今大阪府)第四代藩主小出重兴,而后不幸丧夫,且因无后导致陶器藩领地被朝廷收回,藩国就此灭亡。万念俱灰之下,幕子公主回到盛冈落发出家,因仰慕黄檗宗佛寺——大慈寺的异国情调和历代住持的崇高品德,选择了皈依黄檗宗,得号“光源院”。大慈寺第四代住持万睿和尚受其委托,在北上川舟桥下举行大规模的“施饿鬼”仪式以积阴德,成为如今“舟子流”的原形。文化12年(1815),津志田的名妓大时小时前往盛冈游玩之际,不幸覆舟落水,双双溺亡,为纪念亡者,“舟子流”活动规模得以扩大[2]55。
不过,在探究“舟子流”的地方根源的同时,还不得不提到黄檗宗、“彩舟流”的问题。承前所述,大慈寺内伫立着约2米高的花岗岩墓碑,即幕子公主的墓碑。大慈寺因为南部藩的庇护,后逐渐发展为寺领63石、下属寺庙十余家的大寺院,日本第十九任首相原敬死后也葬于该寺。大慈寺前身为宽文13年(1673)建立的草庵,创建者德真道空和尚曾跟随黄檗宗大本山京都万福寺第二代住持木庵性瑫长期修行。木庵性瑫(1611—1684)为黄檗三杰之一,福建泉州晋江人氏,俗姓吴,隐元禅师之法嗣。大慈寺山门建筑模仿长崎崇福寺的龙宫形山门而建,保留了唐寺的明显特征,寺内至今可品尝和京都万福寺一样的中国“精进料理”和“普茶料理”[6]。历史传承由此可见一斑。
依照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收藏的《彩舟流唐船图》(天保15年,1884),该图记载:“惣乘组灵二百八人”“灵祭执行,南京兴福寺,福州崇福寺,漳州福济寺”等文字。由此可知,“彩舟流”是由唐寺僧侣主持的佛教活动,其目的是为了祭奠客死扶桑的华侨灵魂[7]。事实上,隐元禅师东渡日本之后,先后住持兴福寺、崇福寺,两座唐寺皆为“彩舟流”活动的主办寺庙。而后,隐元开创京都万福寺,在1664年隐退,由木庵性瑫继任住持职位,一直到1680年[8]。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梳理出兴福寺、崇福寺—京都万福寺—盛冈大慈寺的一条潜在脉络。
与黄檗宗、“彩舟流”一样,普度文化也成为“舟子流”的文化溯源之一。承前所述,长崎唐三寺、京都万福寺每年皆会举行大规模的普度活动,以超度祖先灵魂及各方孤魂野鬼。时至今日,两地寺庙依旧保持着中元节期间举办普度的中国文化传统[9]。中国普度文化传统,历史上始终保留着“烧法船”的基本环节。清人得硕亭《草珠一串》留下了一首咏京城中元节放河灯的竹枝词:“御河桥畔看河灯,法鼓金铙施食能。烧过法船无剩鬼,月明人静水澄澄。”[10]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中元普度也依然保留“烧发船”“施饿鬼”的习俗,把为过世亲人准备的纸扎灵位、纸扎贡品和路边祭拜孤魂野鬼的贡品一并放入名为“发船”的体积庞大的纸扎船上,再由法师诵经后,将纸扎船焚化,象征“发船”已载往西方极乐世界[11]。作为长崎华侨祖籍地之一的福建漳州,在宋朝时期就在普度中引入了烧法船的环节,且一直延续至今[12]。作为京都盂兰盆时期的代表景观,京都万福寺举办的“黄檗山川施饿鬼”已经成为日本俳句中表示秋天的“季语”,入选日本俳句季语词典。不仅如此,万福寺还同时举办“水灯会”,在宇治川浅滩上浮起小船,一边诵经一边漂流莲花形状的灯笼[13]。
由此可以推测,大慈寺德真道空在万福寺跟随木庵性瑫修行期间,不仅接受了黄檗宗的教义,同时作为实践者也参与了这样的法事活动。因此,德真道空在盛冈建立草庵,将黄檗文化带到日本纵深腹地的东北地区之后,也在地方政权高层的支持下,确立起了与地方风俗相结合的民俗活动,从而进一步让这一时期处于先进地位的中华黄檗文化深入到日本民间,积淀而为厚重的地域化的历史。“舟子流”习俗就是在这样的宗教流派的传播、“彩舟流”习俗的传承、地方文化建构的过程中得以树立起来。
四、“舟子流”的文化传播特征
(一)保留仪式的基本特征
德奥传播学派“文化圈”学说的代表人物格雷布内尔指出,文化圈的研究要建立在“形的标准”和“量的标准”之上。“文化圈”“信仰圈”“祭祀圈”的学说未必适用于本研究,但是该标准却可以提供一定参考。该标准站在基础的角度制约主观判断的偏颇,要求观察相互符合的事物特征,而非是事物发展的必然形成的结果,也不被材料或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所决定的现象[14]。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跳出历史经纬,站在比较文化学的立场,就中国东南沿海“送王船”、日本“彩舟流”与“舟子流”的仪式仪轨进行比较性的研究,以站在实证的立场来探究中华文化元素在日本的传播。
顺便提一下,明治维新之后,长崎“唐馆”荒废,华侨迁移,日本政府颁布了禁止“彩舟流”习俗的法令,因此,探究“彩舟流”与“舟子流”的问题,只能依旧那一时期画师的图绘或者少量的文字资料,由此而尝试发现一点蛛丝马迹。但是,较之这样的三元比较的视角,或许在此将传承至今的中国东南沿海“送王船”和日本盛冈“舟子流”的仪式仪轨进行比较的话更为有效真实(见表1),且我们亦可以在造龙船、迎接亡灵、绕境、烧船与宗教法事等主要环节找到东亚内部文化传承的潜在线索,更可以由此而论证出文化的传播、仪式的构筑绝不是来自突发性的创造。

表1 中国东南沿海“送王船”和日本盛冈“舟子流”的仪式仪轨对比(1)表中“送王船”仪式以笔者田野调查的厦门漳州地区为依据。
就仪式的理念而言,仪式是文化的纪念碑,是最能够体现人类本质特征的行为方式与符号表达。仪式不是日记,也不是备忘录,它的支配性话语并不仅仅是讲故事和加以回味,而是一种将想象中的虚幻世界进行模拟的实践,它通过一系列象征性行为将两个世界连接在一起。“在仪式中,生存世界与想象世界借助单独一组象征性符号形式得到融合,变成同一个世界”[19]。“送王船”作为关涉“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被纳入世界非遗名录,成为了中国海洋文化的代表之一。
“舟子流”应该说也是如此。依照实地性的考察,“舟子流”的龙船造好之后,由当地孩童悬挂千羽鹤、代表五色莲花光的五色纸幡、灯笼假花等,形成一系列图像符号。而后举行备点心、点灯笼、跳三飒舞,以迎接亲人“御灵”来临,在龙船前举行“入魂”仪式等一系列行为之后,由寺庙僧侣做法事,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阿弥陀经》,以一种“符号语义情景”营造出神秘庄重的氛围,让民众感觉“连接了阴间的亲人”,呈现出一种“符号语义信息”。在村民轮流烧香祭拜、“拉近了阴阳之间,祖先与子孙之间的距离”之后,便开始抬着龙船绕境。到了黄昏时分,各地区龙船齐集于明治桥下河边,再由僧侣举行法事,之后村民轮流抬龙船至河中,使用松明火把点燃。龙船四周铺好的杉叶燃烧发出的声音和鞭炮声汇聚成了送灵挽歌,杉叶焚烧的浓烟和龙头中暗藏的烟火相互渲染,恍如隔世。在一派庄严肃重的气氛中,人们祈求亲人顺利到达西方极乐净土。
就此而言,中国东南沿海的“送王船”,日本长崎地区的“彩舟流”“精灵流”以及盛冈的“舟子流”,皆借助龙船化吉、亲人亡灵升华来渲染一种庄重的仪式,并将之作为现世的人界与亡者往生的西方极乐净土之间的联系纽带,带有极为神秘的人文色彩。
就仪式的实施而言,正如法国著名人类学家涂尔干所言:“仪式首先是社会群体定期重新巩固自身的手段。当人们感到他们团结了起来,他们就会集合在一起,并逐渐意识到了他们的道德统一体,这种团结部分是因为血缘纽带,但更主要是因为他们结成了利益和传统的共同体。”[20]在整个仪式的实施过程中,不仅血缘的认同、地域性的认同或者“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
日本盛冈“舟子流”在这一点上最为显著,彰显出一种不同于男权中心主义的既有观念,呈现出一种多元参与的范畴。具体而言,一方面,我们可以认识到,“舟子流”保留了过去的僧侣主持法式、民众参与、政府支持的固化模式;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找到一种全员参与的价值体现,也就是男丁抬龙船,妇女近旁推车后勤,孩童持五色纸幡护驾,从而体现出这一“舟子流”礼仪的极为独特的“社会性”理念。
事实上,这样的一种独特的形式,我们亦可以在中国东南沿海“送王船”的民俗之中找到一点踪迹。中国东南沿海“送王船”是以妇女持扫把为王船开道为先,男丁们抬王船,孩童坐“蜈蚣阵”跟随之后,从而构成整体性的绕境队列。这样的共通性或许也映证了一种社会性,即“既是讯息得以在空间传递和发布的过程,又是从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是共享信仰的表征”[21]。
(二)符合国情的历史演变
站在地理空间的视角,文化传播是由文化输出地向四周扩散,根据传播途中信息递减的一般规律,离文化输出地越远的地方越无法保持文化原形。当一种文化元素传播到另一个地区以后,它就不再是原来的形态和含义,而是在传播和采纳过程中被修改,因此,两地文化只有相似处,完全相同的文化十分少见[22]。文化传播之际的变形或转向,产生的不仅是一种新事物,更可能是一种主流性的而非细枝末节的事物。一言蔽之,新形成的文化可以成为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可以成为取代过去的新主流,并构成新的文化传统。
中国东南沿海“送王船”和日本盛冈“舟子流”的最大区别,应该就是“送王船”的仪式之中出现了“代天巡狩的王爷”,实现了“由鬼到神”的转变[23]。根据刘枝万的历史考证,“王爷”的身份功能实现了由最初的“厉鬼”到“瘟神”“海神”“医神”“地区神”,再到最后的“万能神”的转变[24]。“王爷”的登场及功能的不断扩大,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民众需求的扩大。换言之,即便不涉及文化的传播,文化现象自身也会不断变化。文化在传播过程中,讯息量难以保持不变,也必然因为传入地的外界环境、气候人文环境的不同而被迫做出演变。这样的演变既符合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也是事物持续生成的必然。本研究论述的送船习俗,或许正是因为实现了受众(受益面)的“他者”向“自我”的转变,才得以不断延续(见表2)。
由此可见,送船民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以普度文化这样的宗教意义为核心,通过确定仪式的实施目的、实施主体、参与者的位置,逐渐实现了自“他者”到“自我”的转变,最终演变成神灵登场的格局,亦通过“参与者共鸣程度”的把握,从而确立起了以受众覆盖范围为指标的民间信仰。就此而言,文化传播之际外界环境的变化,既可能造成文化仪式的外在变化,也可能反衬出“源文化”的根源所在,进而还可以倒映出“源文化”是否进化缓慢或者停滞不前的自我反省。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中元烧“发船”、祭祀过世亲人和路边孤魂野鬼的活动,也体现出中国文化走到域外之后不断“演绎”的不同阶段。日本盛冈“舟子流”则是更多地保留了中国东南沿海“送王船”的基本仪式,可谓是中国东南沿海“送王船”民俗文化在域外的活化石。

表2 各个送船民俗的“他我”转变
不过在此也需要提到一点,即“舟子流”的仪式也并非一成不变。“舟子流”的游行人员,戴有头绳,身着日本特色的满裆裤,凸显出日本地方特色;在迎接亲人灵魂回家的环节,跳的是极具本土特色的三飒舞,也彰显出日本的地方特色;“舟子流”在日本传承之际,不仅自身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而不断经历着变革,还应对外界环境的变化延续着整个礼仪;为了应对严重的老龄化带来的青壮年人口比例下降的问题,号召子供会的孩童参与活动;在龙船制作过程中,让孩子们参与制作一艘小型龙舟、折纸鹤、制作五色纸旙、撰写愿望语等,为培养继承者做准备。不仅如此,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少数女性参与抬龙船的新动向。一言蔽之,“舟子流”在日本的传播,事实上绝不是映证所谓日本化、中国式这样的大逻辑,而是不停地走向仪式的在地化,始终在为了这一仪式的延续而不断地选择了更加优化、更为契合的外部环境。
五、结 语
文化的传播、演绎与涵化,“媒介”必不可少。两个不同文化的集团,在持续的、直接的“接触”之后,彼此激活双方文化的内在因子,使之在一定条件下进入亢奋状态,结果必然造成双方或者一方在文化形态、文化组织、文化指针上出现变化。无论是直接采借,还是传播演绎,媒介皆不可或缺。
中国东南沿海“送王船”在海外的传播,与福建移民的海外迁徙密不可分。一方面,华人移民固然是一大主体,黄檗宗的文化力量也不可忽视;另一方面,移民移神(信仰)并举是海外华人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普度文化更是成为一种重要信仰。在此,黄檗文化、普度文化就成为“送王船”的海外传播,也是日本“彩舟流”或者“舟子流”得以形成的重要媒介之一。尤其是黄檗文化在日本可谓是自上而下、风靡一时。这是一种极为高效有力的文化传播媒介,既为文化传播本身的深入民心提供了制度保障,又为后世学界进行传播媒介的考证提供了较为可信的考证材料。“舟子流”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性的强大力量引导下,经历了以普度文化的普遍性洗礼,进而经过了“彩舟流”这样的既有文化的传承,从而实现了自“他者”到“自我”的重大转变,从而得以在日本东北地区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致谢:感谢漳州市开发区保泉宫程国民先生、厦门市海沧区水美宫蔡通行先生等在笔者进行田野调查之际提供的资料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