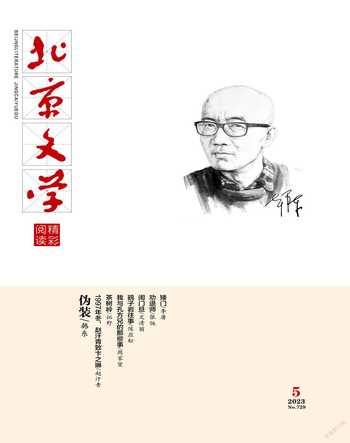一次去伪见真的文学实践
何平
即使不热衷于考据,不去做细密的考小说的“本事”,稍微了解一点世纪初南京文艺生活,或者只是百度下小说里引用的诗歌,比如《愿景》《三个肉月亮》,我们也能知道《伪装》的“南都”即南京,“明月”即南京文艺圈名人吴宇清。
吴宇清是诗人外外的原名。说他是诗人,其诗名生前不彰,虽然他自己印过一本诗集《洞》。小说《伪装》里换作《窟窿》。类似的替换,无所不在地侵入到小说《伪装》,暧昧现实和小说、纪实和虚构的边界。语言制造的幻景成为另一现实,缔造的是一个自定义的现实。事实上,当现实通过语言的制造和现形,对韩东而言,小说之现实一种,肯定不是简单复刻或者仿真。
回到外外的诗集《洞》。在我们这个辽阔的文学国度,有过自印作品经历的写作者太多太多。而外外之所以是“诗人外外”,因为有一本诗集《我将成为明月的椅子》和诗集出版前后在网络媒体空间流传的数十首诗歌,而且这些诗歌得到包括北岛、韩东、于坚、翟永明、宋琳、尹丽川、巫昂等在内的38位成名诗人的诚实推荐。诗集在豆瓣读书也有8.2的评分。
“2017年9月26日下午3点,吴宇清从28层的高楼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个事实的描述,来自吴宇清去世后的第二年2018年11月,当时还很有影响的非虚构平台“正午”,李纯那篇流传甚广的报道《一个叫吴宇清的男人决定去死》。韩东小说《伪装》也是从明月的自杀开始写起的。
《一个叫吴宇清的男人决定去死》有关于韩东的段落:
诗人韩东第一次读到了吴宇清的诗。他们是多年的朋友,但韩东从没见过他的诗。他先是震惊,而后愧疚——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的“视而不见”,可能是诗人所能犯下的最不能弥补的错误之一。他说,“一个人的天才直到死时才被人发现,尽管是身边的人,惭愧,不安。”
韩东参与了外外遗作《我将成为明月的椅子》的编辑、整理和出版,他将“天才”的称号赋予外外。这是韩东的“视而见”,虽然这种“视而见”是在外外去世之后的后知后觉。季羡林有一篇著名的散文,题目叫《赋得永久的悔》。对一个写作者而言,生者对死者的“悔”可以借由文字不断地释放和疏解。现在的问题是,韩东在吴宇清去世五年多以后写一篇四万五千字的小说仅仅是“悔”吗?这首先得从《伪装》写了什么去想。
《伪装》用一句话可以概括:南都(南京)青年文艺圈和文艺青年明月的文艺生活。当然,如果更准确一点,应该是南京边缘或者非主流青年文艺圈和青年文艺生活。边缘和非主流不需要多作解释,我们回忆下上個世纪末韩东们的《他们》大概就能体会。“他们”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南京有全国影响的诗人和小说家群体。《他们》是他们编辑的民间刊物。那时候,韩东和他的朋友们大多三十岁盈余四十岁未满的年纪。追随“他们”的年轻人则是更年轻的大学生们,像李樯和李黎等不过二十岁出点头。
那是一个青春期荷尔蒙勃发的南京青年文学时代,但《伪装》不是韩东对自己参与制造的曾经的文学黄金时代的咀嚼式的怀旧。怀旧所包含的黄金时代的丧失有时候只是一种自我神话的话术。韩东自动屏蔽了去往上个世纪文学黄金时代的通道,直接切入世纪初的黄金时代之后。他写南京文艺生活用的是类似巴尔扎克写巴黎的“风俗研究”。庆总、诗人老秦、《南都晚报》的副刊部主任鲁南、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王峰和林元忠这群人,他们进入到21世纪,不过是20世纪南京文艺时代的剩余物。《我们》杂志、如梦令酒吧、“我们”写作网以及诗人之间的交游和嘻乐貌似还在时代的延长线上,甚至叙述城市青年文艺生活不能或缺的“男女”也依然如故。比如《伪装》明月和齐齐、小瞿疑似的谈恋爱,鲁南和魔女贝贝网恋以及老秦和齐齐夜聊等等,就像小说写到的:到处寻寻觅觅,就像一匹发情的骡子。筹办“我们写作网”时鲁南尤其积极,为建立一个能够独立发表作品的园地只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大概是想借办网站和女网友勾兑。鲁南周围充斥着文学女青年,但他总觉得网上的更胜一筹,至少更新鲜更不可预料。实际上我们都抱有类似的心态,但如果说到心情的迫切,肯定非鲁南莫属。
交游几乎每天都在南都(南京)发生,但不限于。小说至少写到扬州、深圳和北京,所交往的也都是在文艺男女之间。从现实中上个世纪“他们”文学时代转场到小说的“我们”文学时代,韩东没有点明,但南京青年文艺生活事实上正经历着风流云散的时刻。但一个时代的落幕却成为《伪装》“地下音乐之父”和买单王明月纵情文艺纵情声色的时代。除了地震局的本职工作,明月的日常生活几乎跨界游走在所有文艺领域:听说他在艺大(南都艺术大学)兼职代课,讲授电影写作,也就是写剧本。我真不知道他在这方面还有研究,但也不奇怪,明月就是一个文艺青年,有关文学艺术的一切、方方面面他都来者不拒。音乐、诗歌、文学、电影,现在是电影写作,再加上他当电台节目主持人时锻炼出来的口才,我觉得明月是完全可以胜任的。这也让我想起另一个问题,就是明月的收入。经那次在深圳向姐提醒,我开始担心起这个买单王的日常开销。看来他除了本职工作,这些年一直都在兼职(干音乐节目DJ亦是兼职),多了一份兼职在他也是顺理成章的。
“我们”写作群声名鹊起,已接近巅峰。这个判断在小说能够确定的文学事实好像就是这一伙儿人的带头大哥,比如鲁南和老秦出书变得容易,而且“接近巅峰”所耗尽的过去文艺黄金时代残存的能量。然后,接踵而至的则是“气氛大不如前”。还不只是气氛。“以前,这个圈子是以鲁南为核心的,我在一旁辅佐之。现在圈子的核心仍然是鲁南,明月从旁辅佐。以前,我们的圈子主要还是谈诗歌文学,男女是附带话题,而现在基本上没有人聊文学,话题一转就奔下半身去了。”如此看,《伪装》确实是一部罗曼蒂克消亡史,但韩东的《伪装》不是挽歌。
罗曼蒂克消亡殆尽之后,时代仍然滚滚向前,《伪装》明月的文艺生活从一小撮人的厮混扩张到书店这个公共空间。这或许就是我们今天很多文艺从业者向往“破圈”:明月从担任这帮人的主持开始,后来竟成了先锋的第一主持人,或者首席主持,绝对是首选的主持人或者是主持人A角。主持内容也不再限于诗歌、文学,一切和文艺有关的书籍出版举办活动时都少不了明月。影视、艺术、音乐,历史、建筑、哲学,甚至美食和旅行,明月无所不通。
如果小说至此作结,无非是我们时代无数类似明月的或大或小的文艺达人的变形记。小说写:“明月的这身装扮很像一个艺术家,当然是被我们这帮人瞧不上的艺术家。他再也不是一个文学青年,拿腔作势,不伦不类,已经完全找不到北了。”由此,《伪装》俨然要通向议论今不如昔“批判现实”的小说。然而,《伪装》并没有。小说写到此,一切都是《伪装》的“伪装”。
以明月跳楼自杀为界,小说接着写。自杀前,活在我们中间的明月只是明月的“伪装者”。自杀成了明月伪装脱落,真身现形的时刻。鲁南读到了一家微信公号上刊发的明月的诗,惊为天人。“这怎么可能呢,他怎么可能写成这样?这明月写诗吗?写过诗吗?”明月已婚,妥妥的一家三口,卻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未婚青年。明明是一个极具天才的大诗人,却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文学青年,情调兮兮得不行。明明是一个厌世者以致最后跳楼自杀,却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快乐的白痴……吴宇清(外外)的诗集《我将成为明月的椅子》出版,韩东写道: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外外热衷于谈论文艺并不是为了混世,他的诚恳在偏见下反倒显得虚假。有时外外也想聊点深入的,但无人接茬,因此就算有这样的想法,他也只会三缄其口。没有人觉得外外是一个可以讨论严肃话题的对象。我们对外外的忽略是双重的,既忽略了他的写作,也忽略了他在圈子里以特有方式的存在。作为一个诗人,外外于是便成了这样一种隐者,隐于圈子的最核心区域,并非隐于市井,更非山野或者庙堂。经过近20年如此这般的时光,连他也将自己骗过了。
在这里,“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我们”是一个复数。这个复数是韩东这个“我”在其中的复数。如果意识到在词与物,在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上韩东对中国当代文学所作的贡献,韩东之“从来没有想到”的主语,是一个对日常生活比绝大多数人甚至绝大多数写作者有洞悉和澄清能力的诗人。以此观之,韩东写《伪装》可以理解为一次自我反省和批判。这种反省和批判是对世俗生活无所不在的人和人的默契和隔膜,也是对诗人感受世界的可能和局限的提醒。我们常说“文学是人学”,所谓“人学”说到底是以自我之生命理解他者之生命的去伪见真的“人之学”。对诗人和小说家而言,人之学不一定是知识,而是顿悟的一刻。小说《伪装》写到这一刻的降临,在明月之前一起去扬州:
站在木楼梯上我看见了楼下的明月。他坐在一把靠背椅上,怀抱一把吉他拨弄着。低头且抬头,目光和我相遇,又低下了头,兀自吟唱不已,乃至于绵绵不绝……
明月坐过的那把椅子上已经没有明月了,也没有其他人。那把椅子上放着一把吉他,感觉上是那吉他自己发出了声音。我看明月,再看楼下的椅子和上面的吉他,来来回回看了好几次,乐声和吟唱终于停止了。
小说的这一刻还有更昭然若揭的,比如明月和老秦互换电脑,比如明月自杀前的电话。或许溢出《伪装》文本的审美意义,我们熟悉的那些人中间,有多少人曾经向我们显形他们的渴望被看见、渴望被听见。即便止于小说《伪装》,渴望被看见的是诗和才华,渴望被听见的是无法承担的隐痛之后微弱的呼救。这是非虚构如此发达的时代,我们仍然需要小说的理由;也是已经有了《一个叫吴宇清的男人决定去死》,韩东还有写《伪装》的自信和勇力。
特约编辑 蓦 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