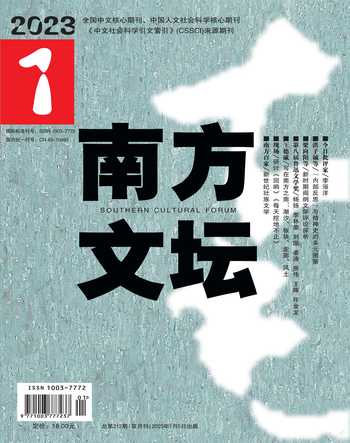观照历史、文化与生命的“根性写作”
刘铁群 王丹

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观念转型以及90年代文学桂军的“边缘崛起”,新世纪的广西文学呈现出多民族文学多元共生、文体丰富的新局面①。其中,壮族作家的散文创作也在时代的潮流中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态势。从创作队伍来说,新世纪以来从事散文创作的壮族作家梯队整齐、力量壮大。生于1930年代的韦其麟、凌渡依然在坚持笔耕,生于1950年代的冯艺、庞俭克、黄佩华、岑献青和生于1960年代的严风华、石一宁、凡一平、牙韩彰、黄鹏、黄少崇、蒙飞、透透等作家还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生于1970年代的陶立群、罗南、黄土路、梁志玲、韦露、廖献红等作家的散文开始走向成熟,生于1980年代的黄庆谋、黄其龙和生于1990年代的廖莲婷等新生力量也显示出良好的创作势头。从作品数量来说,几代作家携手共进,持续发表新作,同时推出了大量的散文集。在1999年出版的《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散文卷》中,共收录新世纪以来的散文56篇,其中壮族作家的散文13篇,接近四分之一。从创作特质来说,新世纪以来的壮族散文延续了壮族作家自觉的民族意识,立足民族土壤,拥抱民族文化。同时,也具有开阔的胸怀和开放的视野。2007年,壮族散文家冯艺在《根性的写作》中提到,民族文学的“根性”来源于自己民族的文脉,“真正的少数民族作家,他的笔下,永远流淌着母体的血脉和浓浓的原乡况味”,“这是一种根性的写作,他们的根扎在民族母体里”②。从本质上说,新世纪以来的壮族散文创作正是一种“根性写作”。民族根性是深潜于少数民族作家意识中的身份认同与民族自觉,是一种可勾连历史记忆与写作主体的文化质素,也是理性反思下回望民族与自我的某种诗性思考。在全球化、城市化、多样化等特征显著的新世纪,民族之“根”更需要扎根在特定时代的文化土壤之中,立足当下,以一种发现、发展和审视的眼光拥抱现在和未来。正如冯艺所说,民族文学的妙谛是“民族根性和与时俱进的大胸怀交融糅合”③。新世纪的壮族文学在中国多民族文学繁荣共生的背景下,正以一种自觉扎根民族母体、竭力重续民族血脉、积极拥抱现代文明的与时俱进的姿态和“大胸怀”持续在文坛深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相比于小说,壮族散文以某种“真实”的倾向和抒情的方式试图抵达民族的根脉,对山海文化性格与民族历史记忆、“那”文化浸润下的土地意识和“麽”文化陶染下的万物有灵等民族历史、伦理和文化质素进行理性的审思与诗性的思考,发掘了壮族散文与一座山、一条河、一棵树或一朵花坦荡于穹庐间的同脉共生的民族气质。这种立足民族传统,观照历史、文化与生命的“根性写作”,显示了新世纪壮族作家深入多彩地域和民族根性中汲取创作养分的文化自觉。
一、山海文化性格与民族历史记忆
八桂多山多水,山河相间,居于其中的壮族常被冠以“山地民族”的称谓。事实上,广西不仅处于珠江水系中的西江流域,桂东南与广东珠江文化一衣带水,桂南还有海岸线和边境线,也可以说是一种准海洋文化。正如严风华在专门介绍广西世居民族的散文集《壮行天下》中提到:“一片土地,如同身軀;一片海洋,如同血液。身躯有了血液,才会变得鲜活,脸色才会红润。广西有山有海,山海相连。从山到海都是壮族的家园。也就是说,壮族拥有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拥有了丰富的山地资源和海洋资源。更重要的是,拥有了海洋一样的博大、宽容、开放、开拓的性格。这是我们壮族生存的根本。”④正是千百年来与山峦海河的共处,壮族人民不仅获得了刚毅、坚韧、宽容的山地秉性,也拥有了开放、拓展、进取的海洋性格。这种性格在民族融合、多元共生的新世纪背景下赋予了文学创作以一种面向历史、奔赴未来、海纳百川的“根性”。
这种“根性”集中体现在广西当代小说和历史文化散文之中。与小说创造诡谲多变的异度空间不同,新世纪壮族作家的历史文化类散文立于山海民俗的现实空间里抒情达意,思绪纵横古今中外,如江河湖海般气魄宏大,同时重视历史遗忘的焦虑和危险,在故事和传说中捕捉即将逝去的一些细微的、可能的真实,以抵抗记忆的程式化消散和无根的现实隐痛。牙韩彰散文集《屈指家山》中的“八桂文化名山寻访系列”和“回望家山系列”散文以真挚的感情、淳朴的笔触和趣味的意兴将珍藏在故乡和心中的山、景与历史捧在读者面前,并道出了他的忧虑:“一个没出过名人的家族或村庄,最后的结局,必然是默默失语于时间的长河而无声无息,外人既不知其来路,更不知它将要走向怎样的未来。”⑤诗人黄鹏的散文集《气象家园》用强烈的情感守护以花山骆越文化为根脉的民族文明,反思当下商业浪潮对民俗文化和风土人情的侵蚀。他呼吁关注本民族失落、寂寞的文化:“与其热衷于仿古建造,与其崇媚他地他国的文化文明,不如回过头来关注我们寂寞的文化文明,不如认真审视一下我们是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文化文明的。我们应该相信,神州大地上人和一个民族创造的文化文明,其价值绝不会低于其他地方的古迹,都是值得全民族共同守护、视如明珠的。”⑥蒙飞的《花山蝴蝶飞》以虔诚的心态回顾花山的历史文化,寻找壮族的精神家园:“我已是多次前来拜谒花山了,带着一个壮族赤子的虔诚之心。每次前来,心灵都获得一次洗礼和升华。在民族坦荡赤裸的图腾面前,我感受到来自心底的震撼。感觉到自己的灵魂在颤抖,在燃烧。随着拜谒次数的增多,我一次比一次坚信,呈现在我面前的赭红色花山壁画,就是壮族先人热血澎湃的心脏,就是壮族先人的心血之作。”⑦历史文化类散文的持续繁荣展示了民族作家以历史为根基、以本民族文化为根柢、以个体认知为依托的“与时俱进的大胸怀”。
冯艺的散文集《红土黑衣——一个壮族人的家乡行走》《沿着河走》《除了山水还有什么》在文化历史题材的书写中时常感叹历史余痕逝去的悲哀,袒露历史记忆遗忘的焦虑。在《红土黑衣——一个壮族人的家乡行走》中,冯艺将壮族民族风情和故事融入一幅巨大的历史素描中,把吊脚楼、山歌、花山崖壁画、壮锦、绣球、三月三、天琴、红水河等壮族标志和苏元春、陆荣廷、孙中山、莫氏土司、张天宗、瓦氏夫人等历史人物悉数数来,以发现的眼光、行走的姿态构建了历史记忆中的现代民族风景,守护文化根脉的同时不断提醒失去历史记忆和反思意识的危险。冯艺感叹道,失去历史深刻性的人们“普遍缺乏记忆的真髓、血性与骨质,缺乏知觉、沉痛和耻辱感,更缺乏灵魂的拷问,矫饰、轻浅、单薄、圆滑,不仅不能解释已经发生的历史,而且造成历史真相的模糊、残缺、流失甚至是常识性颠覆”⑧。冯艺的历史文化散文不断确认直面历史的重要性,重申历史记忆对民族文学的“根性”塑造,具有一种史诗般的气魄。瓦尔特·本雅明认为,“历史地描绘过去并不意味着‘按它本来的样子’(兰克)去认识它,而是意味着捕获一种记忆,意味着当记忆在危险的关头闪现出来时将其把握”⑨。冯艺的散文不拘于对历史事件本身的认识,试图捕获一种历史主体的记忆并用于还原多维视角的真实,这是一种开放的、进取的、直面历史与现实的文化态度。历史与记忆在冯艺的散文相伴而生、相辅相成,记忆则具有了通向过去、未来和自我的可能。《沿着河走》和《母亲记》都将家族记忆与浩荡的历史相勾连,试图在历史的总体性中发掘某些幽暗的悲哀。在冯艺的散文中,个体的记忆和历史是同脉共生的,人就是历史本身,个体的经验世界深深地扎根在历史长河之中。冯艺散文正立足于现实的“当下性”,沿着经验世界的长河奔向想象世界的海洋,探寻一种保留复杂性和反思性的整体性书写。在遗忘的焦虑和记忆的寻真之外,冯艺的散文还具备一种积极发掘和建构中华民族精神的“大胸怀”。在《古老运河的娃娃们》中,冯艺在苏北运河边想起了抗战时期由一群娃娃组成的“新安旅行团”。娃娃们一路南下,以多种艺术形式组织青少年,动员民众,宣传抗日救亡,在桂林文化城中留下了多篇剧作,也在南宁昆仑关血战前线为将士们演出,他们“用脚步度量着生命的意义,也在社会中学习成长”。冯艺感叹道:“少年的前途是浩荡无涯的,少年的锤炼也是不可限量的,中国的未来,不正是靠着这样一代代古老运河的娃娃们吗?”⑩这种“向上,向大千世界,向远方”的力量,正是民族的未来,中国的未来,是值得被铭记和发扬的中华民族精神。
在山河湖海和历史记忆中穿行的还有石一宁、严风华、黄佩华、黄土路等。石一宁关于履痕心绪和寄情哲思的《凌云行思》《北海的风》《上林忆想》等散文以强烈、自觉的民族主体意识介入历史记忆,呈现出一种心怀天下、品味历史、拥抱现实的广阔风貌。严风华散文集《壮行天下》《龙州记忆》《总角流年》,黄佩华散文集《生在平用》,黄土路散文集《谁都不出声》等,都有不少篇章着力书写壮乡的风土地貌、历史余痕和个体与历史的同脉共生,在不放弃历史总体性的态度之上,将强烈的主体嵌入时代的轨道,追求一种更具有“汇通性”的整体性。沿着文化寻根的脉络和视角,新世纪壮族散文用山海一般宽广的视野立足现实,用强烈的主体意识挖掘历史断裂中的真实,虽然在历史地标和故事的选择上略有重复,但仍切合了新世紀文化的总体要求,对广西文学的文化根脉进行了再次确认,也重塑了新世纪民族文学情感的重量和质量。
二、“那”文化浸润下的土地意识
人类在历史长河中与土地早已结下不解之缘,以“土地”为中心意象的文学往往负载着人类对自然的原始态度和想象。壮族古代创世史诗《布洛陀》歌颂的是河谷中法术高强的“智慧祖神布洛陀”改天造地、安排山川的功绩。作为壮族原始宗教“麽教”的主神布洛陀,传说中是珠江流域的原住民,是稻作民族的人文始祖。在“创世女神麽渌甲”神话中,人和万物皆生于泥土,泥土对人具有本质性意义。因此,“壮族将自我的根性定义为大地——泥土”,“泥土成为了壮族人的根性以及审美生发的元点”11。据现有材料可知,壮族先民为适应亚热带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点,较早掌握了将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的技术,是我国最早创造稻作文明的民族之一,从而形成了以“那”文化为中心的民族文化体系12。“那”[na2]是壮、傣、布依等民族语言中的“水田”之义,壮傣语系的民族地区有许多地名都冠以“那”字。正如张声震所言:“壮族及其先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据‘那’而作,凭‘那’而居,赖‘那’而食,靠‘那’而穿,依‘那’而乐,以‘那’为本的生产活动模式及‘那’文化体系。”13可见,在壮族的世界里,土地具有至高的神性,不仅是灵魂的栖息之所,还对民族的成长和归宿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难怪冯艺在《红土黑衣——一个壮族人的家乡行走》的序言中盛赞岭南地区红土地的热烈豁达、执着阴柔和美丽神秘:
红土地是什么?是边地,南国;是丛林密,绿意翠;是白云飘,山峰嗥;是糍粑和土酒;是“呢的呀”的歌声;是铜色的脸膛;是纯朴的个性。无论多么悠长的目光总会被留下来,多么狂烈的风行至此都只能低吟浅唱。可无论是土生土长的,还是流浪迁徙的人,硬是要在红土的胸脯上安家落户。从红土地望出去是一望无际,而有拘有束。向后望是群山包围的内地,如此的安稳、踏实和放松。所以壮族人非常坦荡、憨厚、可爱。但又有阴柔的一面,这个阴柔不是忍气吞声,不是怯怯懦懦,不是畏畏缩缩,而是有很高的智慧含量和文化的积淀。为了大局,为了国家的和平精神,体现了红土文化中的化解力量。14
冯艺对土地的崇拜可以说正处于“那文化人地交往模式”15中的“依生阶段”,即展现的是土地对人的本源意义以及人的主体性生态智慧的初步萌发,彰显了冯艺真挚的人文思考与执着的“根性写作”理念。
严风华在散文集《壮行天下》里也表达了壮族“那”文化对土地的崇拜。“‘那’,在壮话里是‘田’的意思。可以说,在壮族人的心目中,田地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是恩泽他们的生命之源,丰润无比。于是,他们总是很喜欢将‘那’字给地方冠名。如‘那劳’、‘那马’、‘那堪’等。似乎只有这样,田地才如同神灵,无处不在。这是壮族特有的文化现象。”16严风华的另一部散文集《一座山,两个人》写自己在广西一个边境小镇与一位老伯一起建造了一间简陋的瓦房,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回到山脚下过“结庐在人境”的乡野生活。文中温厚踏实的乡野土地是与城市车水马龙、灯红酒绿和钩心斗角的土地相对存在的。《地气氤氲》讴歌地之大、地之厚、地之灵气,赞美土地的善良、平实和宽容。《土地的颜色》惋惜曾经富足、自然的水田景色的消失,感叹土地与农民生活之间相互照映的微妙关系的不复存在。《游戏》中的“我”因被停职而回到山里,老伯安慰道:“干不干也无所谓,亚伯这里有地,可以种红薯、玉米,饿不死。”老伯用土地为“我”壮胆,“我第一次真正地感到,我与老伯,似乎都是为对方而生的。我们已经成为一种亲缘关系,没有任何虚假的成分。……在这座山里,我对老伯和土地,开始产生了依赖”17。严风华通过在陌生的山下开辟自己的心灵休憩寓所体现出的主体性,以及在与自然、老伯、乡民们的交往中将“地缘”转化为了“亲缘”从而达到一种主体间的伦理交往模式,体现的是壮族“那文化人地交往模式”的全阶段,即一种既彰显个体与自然、他人的主体性地位,又与群体共生,进一步生发出某种相互认同、融合乃至整合的文化意义。可以说,《一座山,两个人》汲取了壮族稻作文化中实践性、创造性和融合性的民族伦理,与布洛陀不断开辟、不断创造的精神实质隔空呼应。若不解严风华为何执着于开辟一个主体性的乡野寓所,可从其散文集《总角流年》中窥得一二。在散文集中,严风华用“少年目光”回望了自己的故乡龙州,书写了满是创伤的家族故事和备受歧视的童年记忆。土地承载了家族之累,乡野也曾是被放逐的心酸场域,人与土地的紧张关系使人一直处于无根的漂浮感之中。是故,被壮族血脉中的土地意识召唤的严风华,同样被土地所带来的创伤记忆所缠绕,使其散文具有了复杂的寻根意识和乡野情怀。
同样被土地意识所缠绕的还有韦其麟、黄土路、凡一平、黄庆谋和陶丽群。韦其麟的《季节》以地之子的真诚书写了壮家子弟与家乡土地的血脉相连:“生命的源本都孕育于这大地山河,大自然有无限的魅力,深沉、朴重、博大、仁慈、宽容而亲切,永远对人们毫不吝惜地给予。”18黄土路的《故乡的草味》《谁都不出声》《想念菜地》《河岸人家》《父亲传》等散文都重视故乡那片土地作为“根”的价值意义。在回答庞白关于“根”和故乡情结的问题时,黄土路说:“我重视你说的这个‘根’的东西,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大,心里越来越有着一种恐慌。”19对土地和“根”的焦虑,使黄土路虽向往沉默,但依然在静默中思考和回望。黄庆谋在《河流牵着村庄奔跑》中也强调故土家园是割不断的根:“我的影子后就牵着一条河,同时,河流之后就牵出了我的村庄,不管我是站着躺着,不管我是睡去醒来,我的村庄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舒展它的容貌。”20天地浩渺无边,无论“我”奔向哪里,身后的河流永远牵着我的村庄奔跑。凡一平的“根”是他在“上岭村系列小说”中不断汲取创作源泉的故乡上岭村。当凡一平以小说家的眼光和视角审视着故乡上岭村,故乡的“根”则多了一份羁绊与复杂性。正如凡一平的散文集《掘地三尺》的书名一样,凡一平渴望掘地寻根,不仅在地理上掘出《卡雅》中广西巴马山区长寿村“卡雅”的原始和美丽,还在创作中掘出故乡、历史、土地、人文和伦理更深刻的价值意义。与上述作家相比,陶丽群《忧郁的孩子》《乡村系列》《锄记》《一生一世》《凛冬》等散文中的土地是冰凉潮湿的。土地承受着乡土的四季转圜、悲欢离合与人情冷暖,承载了乡土女性的创伤体验与心酸悲哀,涵括了布满扭曲和荆棘的陈年往事与家族秘史。在《锄记》中,锄头连接了农民与土地,不仅是农民田野劳动的重要工具,甚至成为农民四季劳动行为的外化具象。锄头无数次挖开又缝合田埂的豁口,“成全一片稻子走向成熟,成全一个家庭的丰衣足食”21。《凛冬》中的老者说出了对土地朴素而深刻的认识:“一个人要想在一片土地上站稳脚跟,就得在里头埋进血泪。没有哪一片土地会白白让人从她的胸膛里拿到果实,土地从来不欺负人,但也从来不任人宰割。”22对土地的开掘与耕种、顺从与征服,仿佛是人们在生活中对自我伤疤的撕扯与弥合。人如同植物般依赖土地又用自己的根开掘土地,在自然界中倔强地生长。土地也如一片精神旷野,承受农民创痛的同时给予着他们抵抗虚无的力量。陶丽群还在散文创作中锄开了童年记忆的“土”,翻出了家族秘史的“根”。《乡村系列》《一生一世》等散文从家族女性的心酸怨怼中发掘了乡土系统的创痛与悲哀,同时寻找着自我的某个神态、某种“隐秘的惯性思维”,甚至那些“凝视世间万物时双眸流露出的悲悯或哀愁”的根源,显现了一种敏感、执着与深邃的乡土情结和土地意识。
三、“麽”文化陶染下的万物有灵
与壮族“那”文化相辅相成的,是以万物有灵观念为核心的自然崇拜、以布洛陀和麽渌甲为始祖的神话体系和以鸡骨巫术占卜为基础的壮族原始宗教——“麽”教。“麽”[mo1]的状语意义为喃诵经诗、通神施法,“麽”文化也是在壮族古代巫文化的土壤上生发形成的。受到“泛神论”的影响,壮族“麽”文化把水、火、土地、山、树、花等自然物升格为有人格化的神,形成了诸如花图腾、蛇图腾、鸟图腾、稻谷图腾等图腾崇拜,认为人有灵魂,世上万物同样也有灵魂23。这显示了壮族先民对世界的原始想象,寄托了其借助神力调解人与自然、社会之关系的企盼。相传,“布洛陀”在壮语中除“通晓知识和法术的长者首领”等含义外,还有“一棵绿色的神树”的说法,主要源于壮族人民对神树的崇拜24。壮族从土地认同衍生出来的对“祖宗神树”的认同,是通过树作为土地与人类的双重表征来展现壮族内部继嗣链和民族分支状态的。在壮族民间故事“祖宗神树”中,祖先们为解决人口拥挤让大家到各地寻生路。他们商议到山上种木棉树、榕树和枫树,作为子孙住地的标志,并对儿孙说:“凡是你们走过有这三种树任何一种树的村庄,请你们进去问一问,一定住的是壮族同胞。”25这种以树作为宗族标志的传统在中国文化中也由来已久,如《论语·八佾》“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尚书·逸篇》“大社为松,东社为柏,西社为栗,北社为槐”,集中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同区域和谱系中族群分支繁衍的生存智慧。壮族对木棉树、榕树和枫树等植物的认同与崇拜,体现了壮族先民对“根”的维护和巩固;壮族“麽”文化陶染下万物有灵的“泛神论”思维,也在民族集体意识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韦其麟、冯艺、严风华、黄佩华、黄土路、石一宁、罗南、陶丽群等作家的散文时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出现树的形象,或揭示壮族文化传统,或回忆壮乡童年旧事,抑或寄托情思愿景。冯艺的散文指出“壮族人崇拜树木”,展现了与此相关的民风民俗和知识分子的生态意识。严风华在散文中强调人与树之间天然的默契,植物有时也会给人以指引和庇佑。石一宁的《上林忆想》从徐霞客在广西上林考察的故事为思想契机,思绪发散至上林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砍伐山林的行为,反思了现代人自然观念和历史意识的匮乏。在韦其麟的《乡情》中,树是他与故乡情感的精神纽带。在失眠的长夜,他沿着榕树、芭蕉、簕竹走进故乡的怀抱,安然入睡。在武汉大学的图书馆,独坐思乡之际,他写下了“绿绿山坡下,清清溪水旁,长棵大榕树,像把大罗伞”。韦其麟以一棵榕树描画出故乡村庄的实景,以此开篇,写出了惊艳文坛的《百鸟衣》。在黄土路笔下,树是通向童年壮乡的重要记忆线索。《从一片枫叶上回家》《山里花开》《逃跑的榕树》《父亲传》等散文中的红枫林、木棉花、大榕树、黄皮果树等,使作者在家园故土的荒芜巨变中让远去且模糊的壮乡面目重新清晰起来。而黄土路笔下的许多城市人则像是被移植进城市中的树,根在乡野却身不由己,只能沉默地守望记忆中的乡村。黄佩华《寄树》书写的壮族独特的“寄树”仪式,是“麽”文化中深受壮族人民信赖的古老传统:如果一个孩子生下来体弱多病,可以寄一棵生命力强的大树,意味着二者命运绑定、同根共生。父亲为“我”寄了村边的一棵大榕树,全家人郑重其事地在树下举行了仪式。诸多仪式环节使“我”与榕树产生了某种“通灵”,不管身在何处,时常惦念家乡的大榕树。就此,人与树产生了某种伦理关系的缔结,人与自然在相互照应的关系中彼此建构,体现了壮族原始宗教的基本特性。
人与树木在某种强韧、奔腾、活跃的原始生命活力之间的契合,以及壮族“麽”文化陶染下的万物有灵,在罗南的散文集《穿越圩场》中有较为集中的展现。《穿越圩场》自觉地抱持壮族文化之根,力图从自我的童年秘境中发掘民族独特的文化根脉和原始信仰,以及在现代性规则和现代化进程冲击下的乡土存在状态。罗南笔下的逻楼镇山逻街呈“丫”字形,“丫”字交叉处有一棵三人合抱粗的大古榕,“街头街尾家家户户全都是沾亲带故的亲戚,像一棵错节盘根的老树结出的果”,而世居在这片土地上的壮族人作为世居民族的骄傲“渗进一辈辈壮族人的血液里,长成了一种气质,一种气势,像地底盘缠的根,像石缝间攀缠的根”26。在《娅番》中,作者以树比喻家族系统,“就像一片林子总会有一棵最老最大的树,一番的家族就是山逻街最老最大的树”。在《水之上》中,百乐街的人“不愿意把根须伸进别人的泥土里,与别人的根须纠缠不清”,即使要整村搬迁也要住到离百乐街最近的地方,保留原始的语言和习惯。罗南笔下像树丫和树根的山逻街、像树种子的百乐街、像藤一样的娅番、像一棵“斜长的树”的我,以及像树一样从四伯父心底悄然长出的对朵仪的感情、像挑剔的女子一样的“坏脾气的草药”、被具象化为“断肠草”的毒药等形象,使她的散文雾气氤氲、草木葳蕤、生机盎然,意象丰润奇异、诡谲多变,极具植物灵气。这种壮族文化自有的族群模式、文化观念及呈现方式抵挡了来自自然界和其他族群等力量的冲击延绵至今,也孕育了“麽”文化中以植物或物种来观照人类万物的审美倾向,使世界万物有机地成为一个有“灵性”的整体。
除了树,壮族作家的散文中还有不少花的意象。花在“麽”文化中也是一种具有根本性的原始意象。在壮族民间信仰中,“创世女神麽渌甲”生于大地的一朵花,是掌管生育的女神——花婆。“壮族女巫认为,世间凡人,在世行善者,死后经超度,其灵魂升入天堂后,由掌管天国花园的花王圣母安附在36个花园里任意一朵花的花蕊上,待凡间的信男善女向花王圣母‘求花’,花王圣母便将花赐给他们,让升入天堂附在花朵上的灵魂重新投胎面世。人从天上来,回到天上去,再从天上来,如此循环反复,轮回不止。”27“麽”文化中的花能打通生死,因此花婆的权力可以覆盖三界,围绕花婆的一系列仪式则显示了壮民族对生死的理解和对来世的寄托。黄少崇的《花婆的春天》从自己的成长经历书写了对花婆文化的理解。“我”童年时跌下床或生病,祖母就抱着我喃喃自语:“布伢保佑。”“布伢”在壮语中就是花婆。当“我”明白了花婆对壮族村寨的意义,理解了壮族的生殖崇拜和生命信仰,“我”的灵魂震撼了。壮族人生活在亚热带,阳光灿烂,四季花开,花开花落就像生命的轮回。“花婆形象的出现让壮族先民在生命繁衍方面有了某种强劲的生命依托,由此产生了顽强的生育欲望和生殖能力。”三月三花王节,妇女们怀着无限的希望到鳌山庙拜花婆,然后唱着“待得春来花繁茂”踏上回家的路。壮族人的春天就是“布伢”的春天,“布伢”的护佑让壮族人坚信即将迎来的春天一定“春情四溢,春光无限,春花遍野”28。罗南的散文也书写了花婆文化。《豁口》《药这种东西》等都提到了巫师说死去的孩子会变成花母娘娘的一朵花,重新投胎到阳间,于是亲人们四处寻仙问神,找能超度亡灵的麽公作法。“麽”文化是在古代巫文化的土壤上生发形成的,那些古老的、模糊的、虔诚的、有关生老病死的仪式和方术,在罗南的散文中与植物相伴相依、相辅相成,將壮民族的某种缺席的悲伤转化为当下在场的祈愿,展示出壮族人植根大地、野蛮生长的根性。同时,罗南也写出了这种古老文化弥合现实心灵缺位的失效时刻,即便如此,罗南笔下那一声声响亮的“朵梅”、壮家女子独特的哭唱、妙趣横生的骂街、从青涩到强悍的娅番、盘根错节的亲缘关系和爱恨情仇等,都展现了山逻街人民在苦难中如植物般的韧性和汹涌澎湃的生命力,作者是用一种植根壮族文化的诗性思维呈现自我的童年秘境、观照民族的独特根性。
相比之下,陶丽群散文中的民族意识则沉潜在更隐秘的“泛神论”思维之中,这体现在她创造的诡妙意象上。如“屋后的菜园子”里的蔬菜灵性地显示了家庭的人员存续情况;锄头与人达成了某种身体的一致与平衡,产生了精神乃至灵魂上的契合;土地则和人一样有脾性,能与跟自己对着干的庄稼人闹别扭……在《凛冬》中,一个名叫“凛冬”的活物游走在乡野荒原之上,它的原型似乎来源于四季中的冬季,但它却意指凛冽的死亡。它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选择,谨慎地对生死进行确认,不错误地带走一个人的生命,并对死者保有基本的耐心和尊重。在面对逝去的老人时,凛冬留足时间给老人的遗体完成“落地”仪式,并跟随代表逝者“灵魂”的“影子”穿越土地和记忆,耐心地等待躯体的最终“盖棺”,才将“影子”带走,完成自己的使命。“凛冬”这一具有审判意味的死亡形象表面冰冷凛冽,内心却秉持着一种朴素的、灵性的人文关怀和悲悯意识,是作者对死亡的诗意刻画与大胆想象,显示了其“万物有灵”的“泛神”思维与人本主义的“神性”思考。
经过了时空历程下山峦海河的熏陶、“那”文化的浸润和“麽”文化的陶染,新世纪的壮族散文仿佛也成为一个汲取天地万物之灵性的“活物”,它穿山越河、纵横古今,在旷野大地上恣意奔跑,也不惧扎根泥土,顽强地在雨露风暴里生根发芽。这种被民族文化熏染的“根性写作”本身具备了不同于他者的生命力和异质性,在文学的世界中已经“活”了起来。批评家张燕玲指出,广西少数民族作家根本无须标明自己的族属,“民族文化的异质性已经深入作家骨髓,作品自然就会透出独特的边地民族文化的异质性,形成独特的审美特征”。同时她也強调:“民族文化的异质性,必须与人类文明融合,才可能走向世界。因为在民族差异性与独特性中,探求人类所共有的普遍性才是民族文学的优势之所在。”29期待新世纪的壮族散文创作能进一步在民族差异性与独特性中探求人类共有的普遍性,发挥优势,守本逐新,再结硕果。
【注释】
①黄伟林:《广西多民族文学六十年》,《广西文学》2018年第11期。
②③冯艺:《根性的写作》,载《沿着河走》,作家出版社,2012,第145、145页。
④16严风华:《山海之间》,载《壮行天下》,广西民族出版社,2010,第29、26页。
⑤牙韩彰:《面对故乡,我只有谦卑和低语》,载《屈指家山》,广西民族出版社,2019,第91页。
⑥黄鹏:《关注寂寞》,载《气象家园》,广西民族出版社,2019,第201页。
⑦蒙飞:《花山蝴蝶飞》,《南方国土资源》2009年第1期。
⑧冯艺:《月为谁清明》,载《红土黑衣——一个壮族人的家乡行走》,青岛出版社,2007,第106页。
⑨瓦尔特·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载《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267页。
⑩冯艺:《古老运河的娃娃们》,《人民文学》2021年第7期。
11翟鹏玉:《那文化生态审美学:那文化人地交往模式与壮族生态审美理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第31、28页。
1213张声震:《壮族历史文化与〈壮学丛书〉——〈壮学丛书〉总序》,《广西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
14冯艺:《序言》,载《红土黑衣——一个壮族人的家乡行走》,青岛出版社,2008,第3-4页。
15翟鹏玉:《那文化生态审美学:那文化人地交往模式与壮族生态审美理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那文化人地交往模式”分为依生模式、竞生模式、共生模式和整生模式。依生阶段强调“土地对于人的本源性意义”,以及地对人在生产方式上的初步创造;竞生模式强调“人定胜天”的竞争意识和人的主体性地位;共生模式侧重主体间的自然共生,也表现为家族、族群或政治、经济、文化意义上的共生;整生模式是共生模式的高阶阶段,“主要表现为那文化对国家制度的认同与民族经济文化的融合,以及那文化区的民族认同与文化整合”。四者具有历史和逻辑的演化过程和层级递进关系,“始终贯穿着那文化的主体民族——壮族的生态审美理性”。
17严风华:《游戏》,载《一座山,两个人》,漓江出版社,2013,第93页。
18韦其麟:《季节》,《广西文学》2008年第11期。
19黄土路:《与庞白扯散文(代后记)》,载《谁都不出声》,金城出版社,2014,第160页。
20黄庆谋:《河流牵着村庄奔跑》,《广西文学》2010年第3期。
21陶丽群:《锄记》,《广西文学》2018年第3期。
22陶丽群:《凛冬》,《广西文学》2021年第5期。
2327黄桂秋:《壮族麽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第196、69页。
24刘婷:《壮族布洛陀文化的当代重构及其实践理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第34页。
25蓝鸿恩搜集整理:《神弓宝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第43页。
26罗南:《穿过圩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第51-52页。
28黄少崇:《花婆的春天》,《广西文学》2009年第8期。
29参见张燕玲在《扎根民族沃土,共攀文学高峰——新时代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研讨会纪要》上的发言,《南方文坛》2020年第6期。
(刘铁群、王丹,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