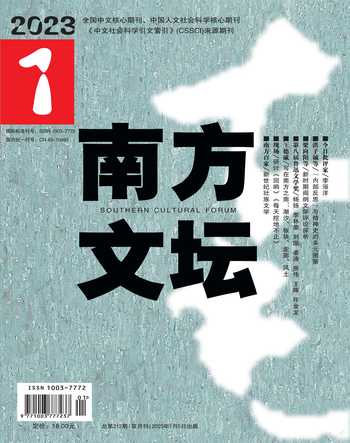新世纪以来“山水诗”的几副面孔
一、沈苇:西域归来,重新发现江南
此岸,彼岸;彼岸,此岸
揭谛,揭谛,波罗揭谛……
——沈苇《骆驼桥》
沈苇有着三十多年的西域生活经验。面对离居已久的江南故土,他将如何审视这个“新的沉潜着的世界”?从其2018年底以来的写作中,我们发现其用了两种非常重要的方式来处理这一题材,一是以西域视角重新发现江南,一是将“当代性”与“江南性”相结合,以当下来回应传统。
以西域的视角重新发现江南,是沈苇后期写作的一项重要使命。如其所言,他要用一粒沙、一片沙漠和海市蜃楼的眼光来重新发现江南的山山水水①。这是一个相互对应和相互映衬的世界,它帮助我们打开了另一重观察江南的视角。对于这一点,沈苇的内心是清晰的。在《关于水的十四种表达》中,诗人开篇即是这样的陈述:“三十年干旱西域/运河一直在你身旁流淌/——这昼夜不息的运命之河!”短短的三行诗,既简洁又有力地将诗人一生中的两个栖息地很好地关联在了一起。其实沈苇回到江南之后的写作,一直都是围绕着这两个命运之地在展开。
在诗集《诗江南》的写作中,他的这种理路也很清晰。典型的诗作,如《骆驼桥》即是如此。骆驼桥本是诗人故乡湖州的名胜,然而诗人并不直写“骆驼桥”,而是将其当作一个“点”,“向东”写到“湖州城外/钱山漾的地下世界/碳化的丝、桑园、孤独的高秆桑/王大妈的面、淤泥里不腐的檀香木……”,“向西”则借助“骆驼”的意象尽力向曾经熟悉的地域拓展:“骆驼的肉身已是合金/从荒寂到繁华/一条黄沙路似乎没有尽头/仿佛你凌乱一脚/就踏入了西域的隐喻。”一如作者所说:“骆驼桥,只是一个水乡隐喻/一次与远方的对话和关联。”沈苇懂得,唯有如此,才能对江南有一个独到的新发现。唯有如此,他写出的江南才是他自己的江南,而不是别人的江南。因为江南的传统,尤其是江南诗歌的传统在很多人的血脉里都有。而西域对照下的江南写作,只有他自己有。当然,反过来推想,江南视野中的西域,不也是不一样的西域吗?这一点也只有沈苇有。沈苇在《关于水的十四种表达》的末节说:“一切都散失了/只剩下了水与沙/帕斯说的‘两种贫瘠的合作’/和‘强盛’。”看起来,这的确是“两种贫瘠的合作”。不过对于沈苇而言,这一类写作却是“强盛”的。
沈苇进行江南写作时产生的另外一种反思也值得重视。他深知,江南是一个大主题,也是一个大传统,今天的江南写作,无论你采取何种方式进行传统转化,都摆脱不了“当代性”这一主题的渗入。为此,必须在写作中将“江南性”和“当代性”结合起来,“换言之,要置身纷繁复杂的现实,回应伟大悠久的传统”②。这是一个看起来司空见惯但却非常有警惕性的思考。为此,我们有必要来审视其诗集的开篇之作《雨中,燕子飞》。因为这首诗是奠定其“江南性”和“当代性”相结合的典型写作范例。在这首诗中,江南传统里的“燕子”与“当代性”结合得相当紧密。如“在雨中飞”的燕子,“备好了稻草和新泥”的燕子,“在雨中成双成对飞”的燕子,“逆着水面这千古的流逝和苍茫”的燕子,都是江南传统里的燕子。然而这燕子又是21世纪的燕子:“燕子在雨中闪电一样飞/飞船一样飞,然后消失了/驶入它明亮、广袤的太空。”在诗人的笔下,这只燕子具足了现代性和当代性。所以,这21世纪的燕子亦是21世纪的江南,是21世纪的“新山水”的一部分。它与我们的时代密不可分,与时代之中诗人的内心密不可分。诗歌是诗人内心世界的投射,透过诗歌中的数行描述,我们可以非常真切地体会到这一点:
燕子领着它的孩子在雨中飞/这壮丽时刻不是一道风景/而是词、意象和征兆本身/燕子在雨中人的世界之外飞/轻易取消我的言辞/我一天的自悲和自喜/燕子在雨中旁若无物地飞/它替我的心,在飞/替我的心抓住凝神的时刻
不过,对于诗人沈苇而言,江南在他的内心中经历了一个“反复”的过程,虽然三十年西域生活之后重返江南的他意欲“用无言的、不去惊扰的赞美/与它缔结合约和同盟”(《雨中,燕子飞》),但毫无疑问,他必须“再一次重建自己内心”(《驶向弁山》),因为“再次归来”,他所置身的江南已发生了世纪性的变化。
沈苇对自己的写作是警醒的,在大量的江南诗歌写作中,他“将自然、人文与‘无边的现实主义’相结合”,形成一种“并置”和“多元”的效果③。套用卡林内斯库的观点,沈苇以他的“混血写作”和“综合抒情”创造出了文学艺术通过浑融既有的趣味范型获得发展的新模式。这是他在当代山水诗写作上的贡献。
二、大解:燕山与太行之子
当我抬起头来 感受体内的震颤
总会有一种力量 穿越心灵
——大解《眺望》
大解生长于河北地界。而据说,河北是中国唯一兼有高原、山地、丘陵、平原、湖泊和海滨的省份,或许正是如此丰富多彩的地貌特征,为大解进行诗歌写作提供了肥沃的地理养料,从而使其“山水诗”具有了不同于他人的独特风貌。
从具体的地理形势看,河北东临渤海,北负燕山,西依太行。应该是很小的时候,大解就对山水有了情感,故而在大量的诗歌写作中,他总是会将山水付诸笔端。检视诗人1990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诗歌》,我们发现其中写及“山”“水”的诗句居然有一百处之多。而出版这部诗集的时候,诗人只有二十四岁。在这部诗集中,诗人对于山水的认知和思考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深度与高度,比如《深山》一詩中说:“依旧是山 见证着我们/依旧是水 流去了又回来/我们一次次走出自己。”进入21世纪,尤其是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及其以来的十余年光阴,是大解在山水诗写作上力量迸发并产生高质量作品的一个阶段。如2007年创作出的《山的外面是群山》《这是一条干净的河流》《大河谷》《河套》诸诗,已经展示出诗人独到的山水视野。不过,这些诗篇大多以诗人的故乡(如村庄、河流)为背景,展现生于斯长于斯的乡人生活,同时融入个人对这种生活的一种省思或考量,时而也生出一种淡然、哀婉的乡愁。相对而言,这一类诗歌的视野还较为窄狭。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瞬就到了2009年。这一年是大解山水诗创作的一个转捩点,因为这一年的6月25日,诗人创作出其名作《燕山赋》。2010年又创作出《山顶》,2011年则有《夜访太行山》和长诗《江河水》。如此,一个宏大而开阔的山水诗视野便横亘到了世人面前。如《燕山赋》的开篇:“田野放低了自己 以便突出燕山/使岩石离天更近。”这是一个恢宏的开篇。然而如果你认为诗人会沿着这样的思路一直透视燕山,你就大错特错了。大解的山水诗写作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密切关注山水与人类相存相依的辩证关系。故而,无论他将山水写得如何繁复,如何高远,最终都要回降到人类生存的基点来做题材处理。故而诗人接着写道:“山顶以上那虚空的地方/我曾试图前往?但更多的时候/我居住在山坡下面?在流水和月亮之间/寻找捷径//就这样几十年?我积累了个人史/就这样一个山村匍匐在地上?放走了白云。”在《山顶》一诗中,诗人也如是说:“燕山是这样一座山脉 山上住着石头/山下住着子民 中间的河水日夜奔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诗人面对宏大叙事的一种姿态,他知道自然山水固然重要,但最有温度的依然是大山里的万家“灯火”,最有生命力的依然是那些“继续劳作和生育”的延续着血脉的人们:
燕山有几万个山头撑住天空/凡是塌陷的地方 必定有灯火/和疲惫的归人/他们的眼神里闪烁着光泽/而内心的秘密由于过小 被上苍所忽略
我是这样看待先人的 他们/知其所终 以命为本/在自己的里面蜗居一生/最终隐身在小小的土堆里/模仿燕山而隆起
外乡人啊 你不能瞧不起那些小土堆/你不知燕山有多大 有多少人/以泥土为归宿 又一再重临
——大解《燕山赋》
诗人首次正面触及太行山的詩篇,大概是2004年5月创作的《车过太行山口》。此诗写诗人于傍晚时分坐车经过太行山口的情形,短短十七行诗将旅途所见所感一一呈现,尤其是其中写到的“震撼”场景及诗人反应,既给诗人自己也给他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许正因为此,诗人此后写下大量有关太行山的作品,如《太行山已经失守》《太行游记》《夜访太行山》《蚂蚁奔向太行山》《太行山里》等。与我们前面述及的情形类似,诗人亦不是为了展现太行山而写太行山,在诗人的骨子里,人事与山的关系依然是诗歌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故而在这些书写太行山的诗篇中,诗人或写“太行山失守”给村庄带来的“灾难”,或写游宿太行而产生的冥想,或写潜入太行夜访故人而感受到的“隐秘的力量”……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大解在其山水诗写作中一直潜藏着一个“史”的意识,这让其诗歌蔓延出一种厚重的力量。2013年诗人曾创作出长篇叙事诗《史记》,近三年来又别有匠心地挥洒出叙事诗《太行山》和《燕山》,这些叙事诗与此前述及的有关“燕山”和“太行山”的诗篇一起,将诗人的“个人史”“村庄史”以及“山水史”完美地呈现了出来。当然,诗人的这些努力,也使其个人在建构“太行山”和“燕山”史诗精神中的形象逐渐丰富和伟岸起来。在叙事诗《燕山》中,诗人曾虚构出一个胡须雪白、灵魂透明的长老形象,这位老者是燕山的长子,是他从远方带回了火种。“他必须存在,且不能死去。”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他的身上肩负着神圣的使命。“一个生于燕山的人,必须认命。”与这位长老一样,大解的身上似乎也肩负着一种责任,那就是:他必须从诗人的身份出发,完成自己作为“燕山与太行之子”的使命。
三、雷平阳:沉默于云南的山水之间
——许多年了,我就这么
来往于苍山和怒江,鸡骨支床
像一个停不下来的信徒
——雷平阳《信徒》
雷平阳在随笔集《旧山水》的自序中曾坦言:“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山水间的行吟诗人,热爱山水,也能从山水里得到教育和安慰。”④尽管这里所说的“那时候”是指写作“旧山水”的2000年前后,但是我们分明能发现“山水诗”在其一直以来的写作中占有非常大的分量。尤其是2009年以来,其出版的诗集大多以带有“行旅”之意或者与“山水”有关的名字命名,如《云南记》《出云南记》《基诺山》《雨林叙事》《悬崖上的沉默》《山水课》《大江东去帖》《我住在大海上》《送流水》《鲜花寺》等。此外还有大量寄意“山水”的散文和随笔作品,与其大量的山水诗歌相呼应,这使得我们完全可以将其视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山水诗人。
雷平阳为云南昭通人,故其耳濡目染的首先是云南的山山水水。如有一段时间,他常常寄身滇南山中,生活中发生的一些情事使其与山水、密林、寺庙等多了一层亲近关系。故其诗篇中与这些事物有关的文字也逐渐增多。大概是受到“父亲西游”等情事的影响,他的心境有些散淡,对于人事也逐渐看开。一如他在《本能》一诗中所写的那样:“沉默于云南的山水之间/不咆哮,不仇视,不期盼有一天/坐在太平洋上喝酒。”为此,他这一时期的山水之作,大多呈现一种平淡孤立的心境,即使看到绚烂之极的桃花,他也安之若素,只将一些淡淡的思绪流露(《狮子山的桃花》)。不过,一旦触及生死问题,他的内心会突然警觉与清醒起来,典型作品如《昆明,西山道上》《乌蒙道上》《过怒江》《狮子山下》《过云南驿》《过哀牢山,听哀鸿鸣》《布朗山之巅》《怒江上》等,都是如此。事实上,雷平阳在其诗歌中用大量的内容谈论生死,已成为其诗歌的一大特色,故而其山水诗也“不能幸免”。中国的古典山水诗也谈论生死问题,不过只是一种偶然现象,从未这么普遍。通过对这一传统方式的打破,雷平阳的诗多给人一种启发式的感召,尤其是那些将个人代入进行生死体验的诗篇,如《无定河》。此诗虽非写在云南山水中的体悟,但基本延续了他写作的一贯风格。而且,其所写还多与地方文化甚至异域文化相关,这让其与生死相关的山水诗带上了一层地域文明的色彩,如《基诺山上的祷辞》《穿着袈裟的江》《布朗山的秘密》。
与此相关,雷平阳在诗歌中对“故事”倾注了大量心血。如其所说:“云南南方山水里所发生的旧传说和新故事,它们一旦来到我的记忆中,来到我铺开的稿子上,就会成为我饥饿的灵魂无限迷恋的食物。”⑤故而,雷平阳的山水诗与滇南的故事、传说构成了一种十分紧密的互文关系,这种略带偏嗜特征的创作已经成为他建构诗歌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创作中,他频繁地透过故事、传说来记录彩云之南的轶闻逸事和人文历史,为其诗歌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当然,这一类书写有的是片段化的,只是选择故事中的部分情事入诗,如《鹧鸪》《过澜沧江》;有的则有非常细节化的描述,而且整体突出,给人一种高强度的叙事感,典型的诗篇如《访隐者不遇》《狮子山中》,亦且后者的故事采取倒叙方式,新颖而深刻,建构巧妙,别具匠心。将故事打并入诗,既是他的一种兴趣,也是他的一个愿望,他希望自己“记录下来的场景和故事,能成为时间的骨头和血液”⑥,当然他希望自己的诗歌也是如此。不过,这种书写有其危险性,如果处理不好,会使诗与故事之间的张力被破坏,但雷平阳成功地开拓出了一片新天地。
雷平阳的山水诗中,也有清新恬淡、风趣自然的一类,如名作《山中》《伐竹》即是。不过,其造诣最高的则是一系列山水长诗,如《怒江,怒江集》《昭鲁大河记》《大江东去帖》《春风咒》《渡口》,这些诗篇有的集中于写云南山水,有的则突破了云南的地域局限,通过叙述、抒情、议论、铺陈等多种表达方式,运用起兴、象征、隐喻、烘托等表现手法,将山水史、村庄史、个人史,甚至坟典奇秘、传说逸闻打并入诗,发展出一种山水叙事诗的新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讲,雷平阳的叙述超越了语言和叙事本身。他以一种超拔的眼力来窥视目击到的山水,使山水既呈現出本来的灵性,同时又赋予山水一种文明的面目。他以自己的文本实验,让隐藏在山水之间的秘史得以在人间持续,也使山水更加接近文明的真相。正如其《怒江,怒江集》的开篇所宣示的那样:
悬崖卷起波浪/天空发出声响/帝王的人马,浮雕于河床上/子嗣绵长啊。自由而哀伤
这既是对人类历史与文明的判断,也是对人类历史与文明的一种感伤。从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雷平阳笔下的山水怎么可能会是纯粹的山水呢!
四、孙文波:置身在语言的山水中
语言的山水不同于自然的山水,
在一段陡坡上你种植了世界观;
花花草草。非常哲学地开放
——在山顶放眼远望,大地的苍茫,
正对应心灵的苍茫
——孙文波《登首象山诗札之一》
2012年孙文波出版了诗集《新山水诗》。与众多写当代山水诗的诗人不同,孙文波依然沉浸于冥想,这让其山水诗一度处于语言的幻象之中。“我的想象,不过是依附在语言的皮肤上。”(《咏古诗·忆江南》)这是他对诗歌的一种创造。当自然的山水与人之冥想合一,中国的道家所倡言的“天人合一”的景观便时常呈现出来。虽然孙文波的诗歌中,道家思想并不明显,但多年来的蛰居生活,山水的灵性与诗人之性灵的融合,使其后期诗歌写作表现出一种大成气象。尤其是2008年以来的山水诗写作,孙文波通过浑融的方式给诗歌注入了“源头活水”,使当代山水诗有了更加丰盈、更加灵动的血脉传承。
“语言的想象奔驰着”(《咏古诗·忆江南》)。的确,在孙文波诗歌中,他之语言的想象一直奔驰着。尤其是对山水的想象,更是充满活力。在其《新山水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咏古诗·东山》《咏古诗·忆江南》这样的诗篇,很显然,诗人举着“咏古”的“招牌”,这暴露了他的创作意图。诗人并非为了山水为写山水,而是借由山水中的经典意象来翻新“古意”,或者借古讽今,这一类诗歌与前人的“怀古诗”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后来诗人所写的《登首象山诗札》系列让我们看到了真山水的影子。但很明显,诗人仍然不是为山水而来。“登山,不是为了看风景,也不是/为了锻炼身体。登山,是寻找一首诗。”(《登首象山诗札之三》)他要实现他作为诗人的角色。于是,在诗人的眼中,大地、落日、山鸟、岩石、天空、积雪、荆棘、苔藓,无不成为他触发联想的媒介。但孙文波诗歌的触发机制与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所说的“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的机制完全不同。刘勰所说,偏于外物对内心的兴发感动,而孙文波的诗歌建构大多以思理发端,然后借助外在的山水风物,一步步激发联想的潜能,以“思”贯穿全篇。可以说,整个过程几乎都是“冥想”和“想象”占据主导地位。正如诗人所说,诗歌虽然以“山水”为对象,但着力点并不在状述山水,也非单纯地如古人“借景抒情”,而是深入地探究人与世界的关系,到达对生命的理解,或由此进入与文化传统的勾连⑦。很显然,孙文波的这种写作构成了当代山水诗与古典山水诗的极大不同,也是他的山水诗之所以独绝的地方。
《新山水诗》的命名取自集中一首同名诗。此诗为诗人所偏爱,是其向华兹华斯致敬的作品。华兹华斯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后来遁迹于英国的昆布兰湖区和格拉斯米尔湖区,是“湖畔派”三诗人之一,也是其中成就最高的诗人。尤其是他的“山水诗”,如《丁登寺旁》,在后世备受推崇。在自然山水的书写上,华兹华斯实现了艺术上的革新。故孙文波以“新山水诗”为题,显然有向华兹华斯的“山水诗”致敬的意图。在此诗中,孙文波仍然以冥想和凝思的方式与华兹华斯展开时空对话,共同探讨“化身山水的能力”,以“思无邪”的方式重新取得与自然的关系,最后回归“教诲”,体认出“山水就是大道”的意义。
最后,不得不说一下孙文波的诗集《长途汽车上的笔记》。此集中的三首曾经收入《新山水诗》。如其所言,此集虽冠以“笔记”之名,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旅行笔记。此部长诗集,共十一首,前后贯穿。其中有两首被付以“感怀、咏物、山水诗之杂合体”的副标题,六首被付以“咏史、感怀、山水诗之杂合体”的副标题,可见诗人并不满足于传统意义上的羁旅写作范式,而是试图采用浑融古典的方式来实现“人面对山川、河流、现实、历史时的种种思考”,孙文波自认“这是一部具有开放性的作品”⑧,运用的写作手法如“戏剧化、抒情意识、哲学沉思”等也极具现代性。不过从“山水诗”的角度而言,它与传统的咏物、咏史纠合在一起,仿佛使山水诗失去了主导地位。其实,认真研究孙文波的作品就可以发现,即使他不辅以这样的副标题,其“沉思”的层次感、包容力、纵深性也都会将咏物、咏史、感怀的内容涵盖。孙文波一直沉浸于对语言复杂性的追寻,他认为这是当代诗的必然要求,只有复杂的语言才能处理和解析越来越混乱的人类世界:
我知道我/还会在语言中浪迹一生。有时候一个词是一堵墙,/有时候一句话是一条河,有时候一首诗/是一座山。我必须面对它们,或者,穿过它们。
——孙文波《长途汽车上的笔记之十》
2022年6月15日,深圳
【注释】
①②③沈苇:《西域归来,重新发现江南》,载《诗江南》,中国言实出版社,2021,第3-4页。
④⑤⑥雷平阳:《旧山水》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第1-3页。
⑦孙文波:《新山水诗》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第216页。
⑧孙文波:《长途汽车上的笔记》后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
(赵目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教育学院。本文系深圳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圳文学研究中心科研成果和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校级科研项目“中国当代诗歌与古典诗学资源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