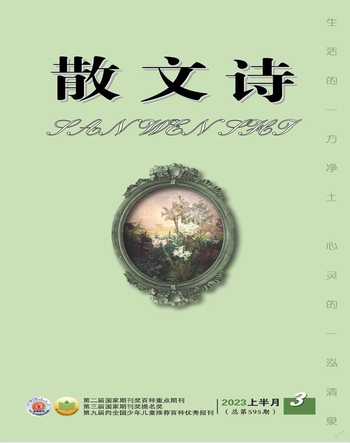新诗谱(节选)
胡亮

鲁 迅
鲁迅的天才既见于小说,又见于杂文,还见于新诗。先生的文学身份,小说家也,杂文家也,却很少有人称他为诗人。即便有人称他为诗人,大抵也便归入次要诗人、其他诗人或业余诗人了。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就有什么样的前提——比如,《野草》是诗集,散文诗集,还是局部意义上的杂文集、寓言集或短篇小说集?文类不同,仪式感各异。诗有诗的仪式感,杂文有杂文的仪式感,小说有小说的仪式感。《野草》所收录的24篇“文本”,只有一篇——亦即《我的失恋》——混仿了古典诗和新诗的仪式感,其余23篇则具有其他文类的仪式感——比如《过客》,盗用了独幕剧的仪式感;《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混仿了杂文和短篇小说的仪式感。那么,鲁迅自己是如何定义《野草》的呢?“一本散文诗”。这本散文诗,出现了内乱——短篇小说揭竿,杂文称雄,独幕剧夺权,旧体诗通敌,新诗会不会告急或逊位?换句话来说,其他文类会不会构成对新诗的僭越?作者,普通读者,都不会费心于这个问题;只有新诗本位主义者,战战兢兢,给出了一个答案——作者首先展现了新诗的天才,同步展现了杂文和小说的天才,然则,作者无意于勘定散文诗或其他文类的边界。先来读《我的失恋》:“爱人赠我金表索;/回她什么:发汗药。”再来读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前者是对后者的“滑稽模仿”(parody),甚至步了“原韵”,似乎既有新诗的仪式感,又有古典诗的仪式感,以至于错综成一种“提前的后现代主义”。鲁迅曾用“打油”,救活自己的旧体诗;难道要再用这招,救活自己的新诗吗?提出这个问题,应当自罚三杯。鲁迅何许人也,岂会轻薄如此?在这里,必须讲个小故事,以便打通大关节——《我的失恋》原投《晨报》,受阻于刘勉己,结果未能过审;转投《语丝》,经手于孙伏园,很快顺利发表;《语丝》其时正在连载《野草》,将刊出《影的告别》《求乞者》,临时插入《我的失恋》。这样,历史开了一个不算小的玩笑——《野草》中仅有的“分行作品”,只是计划外的楔子;作者原拟全部以“不分行作品”,来建构和呈现他的“新诗形象”。甚至就连《我的失恋》,也自相矛盾地表达了对“分行作品”的不信任。此诗有个副标题“拟古的新打油诗”,皮里阳秋,就出示了两种不信任——对旧体诗的不信任,对新诗的不信任。鲁迅自己怎么讲?“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干了。”鲁迅的“新诗”,或“分行作品”,除了一首见于《野草》,还有10首未见于《野草》。来读发表于1919年的《他》:“大雪下了,扫出路寻他;/这路连到山上,山上都是松柏,/他是花一般,这里如何住得!/不如回去寻他,——阿!回来还是我家。”暂时不谈“新我”,先要埋葬“旧我”,这里面,既有悲剧性,又有痛快感。与其把《我的失恋》,不如把《他》放进《野草》。可以这样讲,《他》,《野草》,还有《写在“坟”后面》,共同建筑了一座“大坟”,当年废名先生也曾注意及此。行文至此,不免引出两个话题。其一,“野草”之前已有“野草”。此话怎么讲?《野草》,明显有其“上游文本”。比如鲁迅的《寸铁》,第3段言及“钉杀耶稣”,就是《复仇(其二)》的“上游文本”;鲁迅的《自言自语》,第2篇言及“火的冰”,就是《死火》的“上游文本”。《寸铁》和《自言自语》,均发表于1919年;而《野草》开篇的《秋夜》脱稿于1924年,最后补写的《题辞》脱稿于1927年。其二,“鲁迅”之前已有“鲁迅”,此话怎么讲?鲁迅,明显有其“祖述作家”。比如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裴多菲(Petofi Sándor),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厨川白村,长谷川如是闲,以及比鲁迅更年轻的徐玉诺。蛛丝马迹,皆有铁证。李欧梵先生甚至还有新的发现——鲁迅的惊悚之句,“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很像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的腥膻之诗,“他蹲在地上,/手里拿着他的心,/并且吃着”,只不过,前者想吃出却没有吃出味道,而后者一口吃出了味道。啥味道?苦味道!除了厨川白村,還有小林一茶,明里暗里,或都加持过《野草》。先说厨川白村——鲁迅曾中译《苦闷的象征》,作序云,“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完全可以视为《野草》的艺术自释。要知道,鲁迅一边写《野草》,一边翻《苦闷的象征》,在很大程度上而言,前者力践了后者的美学思想。此种“广义的象征主义”,生根于《呐喊》,抽枝于《彷徨》,开花结果于《野草》,终由现实小说的“偶然的装饰品”,演变为散文诗的“不可或缺的面孔”;正如“提前的后现代主义”,生根于《野草》,开花结果于《故事新编》,终由散文诗的“偶然的装饰品”,演变为反历史小说的“不可或缺的面孔”。再说小林一茶——冯余声曾英译《野草》,鲁迅作序云,“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缘的惨白色小花,当然不会美丽”,完全可以视为《野草》的灵魂提纲。这句话,就化用自小林一茶的俳句:“我们在世上,/边看繁花/边朝地狱行去。”然则,当“繁花”换成了“惨白色小花”,“地狱”换成了“废弛的地狱”,小林一茶——以及其他“祖述作家”——又怎么笼罩得住鲁迅的脱颖?看看吧,诗人已经建立了《野草》的空间轴:地狱-人间-天堂;同时建立了《野草》的时间轴:过去-现在-将来。在谈及“地狱”的时候,诗人自视为“小花”;在谈及“小花”的时候,诗人自视为“地狱”;诗人既想为“小花”浇水,又想与“地狱”偕亡。如若偕亡,谁来浇水?此种“地狱-小花悖论”,又时常落实、分解或转化成“死亡-存活悖论”“绝望-希望悖论”“黑暗-光明悖论”“冰-火悖论”“杀戮-拥抱悖论”“投枪-无物之阵悖论”“空虚-充实悖论”或“失语-说话悖论”……正如李欧梵先生所说,“他的多种冲突着的两极建立起一个不可能逻辑地解决悖论的漩涡”。来读《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来读《墓碣文》:“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来读《题辞》:“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可见《野草》也者,既有抒情之诗,又有叙事之诗;既有独白之诗,又有杂语之诗;既有写实之诗,又有记梦之诗;既有玄学之诗,又有寓言之诗;既有绝望之诗,又有极乐之诗;既有唯美之诗,又有审丑之诗;既有象征之诗,又有解构之诗。要讲文体家,无论当时,还是如今,鲁迅都可以说是顶级文体家。他的神鬼难测的斑斓,来源并服务于一颗“最痛的灵魂”,这颗最痛的灵魂恰是那个时代的“最真的黑暗”。难怪鲁迅写信,对许广平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总之,《野草》提供了“一种诗的现代性”,而且这种诗的现代性几乎同步于全球(比如,参差同步于《荒原》),所以,笔者不得不服膺于张枣先生的金口玉言:“中国现代诗之父其实是鲁迅,而不是胡适。”
胡 适
下面的说法并非故意耸人听闻,而是为了揭开真相——白话诗或新诗的策源地,不在北京,不在中国,而在绮色佳(Ithaca)。这座小城,位于纽约州凯约嘉湖的南岸。康乃尔大学位于绮色佳,而哥伦比亚大学位于曼哈顿。1910年,胡适就读于康乃尔大学;5年后,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1915年8月到9月,胡适与几位朋友,包括任叔永、陈衡哲、梅光迪、杨杏佛、唐擘黄,都聚在绮色佳消夏。他们时常一起讨论,“从中国文字问题转到中国文学问题”。9月17日,梅氏将往哈佛大学,胡适赠诗云:“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20日,胡适将往哥伦比亚大学,赠绮色佳诸友诗云:“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针对这个论点,梅氏致信胡适:“诗之文字(Poetic diction)与文之文字(Prose diction),自有诗文以来,(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不能不说,梅氏有理。1916年4月12日,胡适写出《沁园春 誓诗》:“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6月,胡适回到绮色佳,再与诸友热议,决心“用白话作文、作诗、作戏曲”。7月8日,绮色佳诸友覆舟于凯约嘉湖,虽然有惊无险,却也狼狈不堪。任氏为作四言长诗《泛湖即事》,“言棹轻楫,以涤烦疴”,“猜谜赌胜,载笑载言”,云云。胡适认为,任氏所用,死字也,死句也。孰料梅氏不平,来为任氏助阵。26日,胡适致信任氏:“吾至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8月23日,胡适写出《朋友》,后来改成《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此诗旨在悲叹绮色佳诸友之失和,个人之落单,以及文学革命之高处不胜寒。此诗写得颇为低回,字里行间,并没有“吾志决矣”的大无畏。1917年6月1日,胡适写出《文学篇 别叔永,杏佛,觐庄》:“前年任与梅,联盟成劲敌。与我论文学,经岁犹未歇。吾敌虽未降,吾志乃更决。暂不与君辩,且著《尝试集》。”在此前后,胡适已有理论结晶。1916年8月19日,他提出“八事”(或亦可称为“八个不”):“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将对仗”,“不避俗字俗语”,云云。12月,胡适《藏晖室劄记》抄来《印象派诗人的六条原理》,并留下一条旁注:“此派所主张与我所主张多相似之处”。“印象派”(Imagism),今译作“意象派”。“六条原理”,亦即“六个不”,提出者乃是庞德(Ezra Pound)。胡适留学美國,正值意象派风行。何谓意象派?在庞德或蒙洛(Habrriet Monroe)看来,意象派不过是“中国风”的替换词。意象派引入中国古典诗,居然领跑了美国诗复兴运动。胡适私淑美国意象派,回来却掐断了中国古典诗。胡适领衔的白话诗运动,庞德领衔的意象派或美国诗复兴运动,几乎造成同样显豁的“诗歌史分野”。这段“影响与回流”的公案,无论如何,都算得上是文化交流史上的奇谈。1919年10月,胡适写出《论新诗》,此文核心术语“新诗”,或来自美国诗复兴运动中的“New Poetry”。如果不是这样,难道,是来自杜甫的“我有新诗何处吟”或“老去新诗谁与传”不成?胡适向来看不起杜甫;更何况,杜甫所谓“新诗”,本是指“新出的诗”,而美国新诗运动所谓“新诗”,才是指“出新的诗”。不管怎么样,自此以后,“新诗”逐渐替代了“白话诗”——这两个术语并不能随时互换,白话诗以白话写成,残留有古典诗的句法,或可视为古典诗与新诗之间的过渡形态。1920年3月,胡适出版《尝试集》,这是中国文学史上首部白话诗集。该书分为两个部分,正文《尝试集》,附录《去国集》。《去国集》所录作品,多为骚体、古风、歌行或长短句,此类诗体的相对自由,很显然,比律诗和绝句更加接近新诗的绝对自由——这就是钱锺书先生所谓“旧学而强欲趋时”。《尝试集》所录作品,多为白话诗,然则从《蝴蝶》以降,前面15首都是白话绝句、白话歌行或白话长短句,直到第16首《老鸦》才勉强算是新诗——这就是钱锺书先生所谓“新学而稍知存古”。正所谓:一脚踩上古典诗,一脚踩上香蕉皮。先来读有名的《小诗》:“也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几次细思量,/情愿相思苦!”再来读更有名的《希望》:“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好。”《希望》后来改为《兰花草》,经张弼和陈贤德作曲,银霞和刘文正传唱,早已流行于整个汉语世界。但是,这两件作品,都是白话诗而非新诗。胡适认为那首《关不住了》,算是新诗成立之纪元。然而,此诗乃是译作而非原创,其作者乃是蒂丝黛尔(Sara Teasdale)——这就像是一个隐喻,暗示了白话诗或新诗的“原罪”:从零传统,到反传统。那么,《尝试集》可有一首像样的新诗?有,来读《梦与诗》:“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1922年,胡先骕发表《评<尝试集>》:“胡君但能作白话而不能作诗”,“是胡君者真正新诗人之前锋,亦犹创乱者为陈胜吴广,而享其成者为汉高,此或《尝试集》真正价值之所在欤。”胡适岂无自知之明?胡先骕两万言的长文,说来说去,约等于胡适8个字的自我总结:“提倡有心,创造无力。”后来,胡适还曾出版《尝试后集》,不过是自证了一句预言:“我或终归老于文言诗国”——此语出自《五年八月四日答任叔永书》,亦即《尝试集》增订四版的《代序》。话说当年梅光迪入哈佛大学,师从白璧德(Irving Babbitt),胡适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John Dewey);白璧德倡导新人文主义思想,杜威则倡导实用主义哲学,两者的对峙,被其弟子分别引入中国,终于导致了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的对峙。梅光迪与胡先骕,均为学衡派的大将;胡适,则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当年所谓对峙,到了如今,完全可望“化干戈为玉帛”——只有这样,才有枯树开花、死灰生火的可能。
(连载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