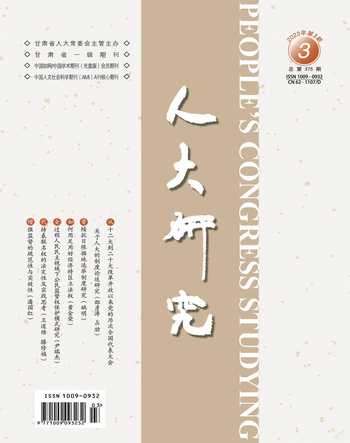如何用足用好经济特区立法权
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备案审查实践以及法院的适用法律实践对特区法规的审查体现出了比较宽容的态度,这种态度为大湾区经济特区用足特区立法权创造了很大的法律空间,但在依法改革意识日益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只有尽量严守法律边界、依法规范行使特区立法权,大湾区经济特区的法治创新才能真正行稳致远。
经济特区立法权是依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专门赋予经济特区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在经济特区适用的专门法规的权力,其本质是经济特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在遵循宪法并且不违背法律和行政法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性法规的具体规定进行变通的权力。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予经济特区立法权的目的在于让经济特区在推进经济和法治改革创新方面可以“大胆地试,大胆地闯”[1]。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需要进行大量制度创新,并且这种创新又涉及极为复杂的法律问题的背景下,深圳和珠海市拥有的特区立法权可以说迎来了大显身手的新的历史性机遇。
中央有关大湾区政策性文件对特区立法权在大湾区建设中的作用寄予了厚望。2019年8月发布的《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特别要求深圳“用足用好经济特区立法权”;2021年9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也同样提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应“用足用好珠海经济特区立法权”。由于经济特区立法权的行使在法律上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地方,因此如何在大湾区建设中用足用好特区立法权仍然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拟在分析特区立法权法律限制以及审查特区法规实践的基础上,探讨用足用好特区立法权所存在的法律空间及其面临的法律挑战。
一、特区立法权的法律限制及审查实践对特区法规适用的可能影响
(一)特区立法权的法律限制
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授予经济特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特区法规的授权决定以及《立法法》的有关规定,经济特区在行使特区立法权首先存在的一个明确限制是,不得违背宪法的规定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不过对于哪些规定属于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这个问题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法律适用者的具体解释。特区立法权行使面临的第二个限制是,在立法范围上要受《立法法》第八条有关法律保留事项条款的限制。不过,对《立法法》第八条的法律保留事项本身也存在较大的解释空间,对于“民事基本制度”“诉讼和仲裁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等含义的不同解释会直接影响特区立法的内容和范围。
除了上述两个限制,2015年修订后的《立法法》规定的程序限制也可能会对特区立法权的行使内容产生较大的影响。《立法法》第九十八条第五项规定,“经济特区法规报送备案时,应当说明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出变通的情况”。在《立法法》修订前,经济特区在对特区法规报送备案时,并没有义务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说明其对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作出变通的情况,因此除非进行仔细审查,否则即便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无法直接知道特区法规是否作出了变通规定,也无从知道哪些条款做了变通。对于法官和其他特区法规的适用者来说,一般只有在具体案件中发现特区法规与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有冲突时,才能发觉是否存在变通。对于2015年《立法法》第九十八条第五项的不同理解可能会对特区法规的适用产生不同的影响。如果将此要求理解成特区法规变通条款的认定要以特区立法机关备案时明确的说明为限,那么就意味着那些在备案时未予说明但与法律和行政法规发生冲突的特区条款将不再具有适用上的优先性[2]。但如果不这样理解,那么无论特区立法机关是否在备案时对变通情况进行了说明,特区法规与法律、行政法规相冲突但又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时,特区法规中的冲突条款都具有适用上的优先性。
(二)特区立法变通权的实践及其对特区立法的影响
目前,国家法律对于特区立法权有一些限制,但这些限制会对特区的立法创新构成多大的障碍还需要通过实践进行检验。此外,目前对于特区立法权的理解还存在某些不清楚的地方,对此也只能通过法律适用实践寻找答案。对特区法规进行监督的渠道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负责对经济特区法规进行备案审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另外一个就是负责适用特区法规的法院。
1.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特区法规的备案审查实践
自2000年《立法法》施行以来,法规备案審查制度已经日益成为确保法律统一性的一个基本制度。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备案审查的程序、回应性、透明度和力度等方面都存在严重不足,因此即便出现涉嫌违反法律规定的特区法规,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不一定能有效的处理。例如,1982年国务院《公证暂行条例》实际确立了公证自愿原则,但1999年《深圳经济特区公证条例》却对抵押等八类事项都要求必须进行公证。《深圳经济特区公证条例》2001年修订后仍保留了四类强制公证事项。2005年《公证法》只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公证的事项,有关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公证”。尽管如此,《深圳经济特区公证条例》直到2017年才取消了大部分强制公证事项。很显然,该特区法规有关强制公证的规定实际上涉嫌违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但却长期得不到有效纠正,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备案审查程序也未能有效地发现这个问题。
近些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规备案审查的意愿和力度都有所加强。目前可以查询到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经济特区法规备案审查的案例主要有两个。(1)《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与《物权法》关于业主大会及业主委员会职责范畴的规定冲突问题(2017年审查案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规审查备案室在经过审查后确认不存在抵触情形。(2)《深圳经济特区食品安全监督条例》与《食品安全法》有关职业打假条款的冲突问题(2018年审查案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规审查备案室在审查后确认两者确实存在冲突,但认为特区法规第九十七条属于立法变通,且“不存在超越经济特区立法权限、违背法律基本原则问题”[3]。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特区法规的审查实践可以看出,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特区法规是否可能违背法律和行政法规基本原则问题进行了审查,但迄今没有特区法规因违反上位法而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撤销的案例。
2.法院对特区法规法律冲突的适用实践
法院对特区法规的适用主要看它们如何处理特区法规与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法律冲突,尤其是对特区变通立法的认定方面存在争议的领域是如何处理的。从现有司法案例看,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法院系统曾在具体案例中以特区法规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拒绝予以适用,也未发现因特区法规规定的事项超越《立法法》第八条法律保留条款而不适用特区法规的情况。
我们再看看法院理论上对立法变通条款认定方面存有争议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的。从理论上来说,特区立法变通权的行使应该是立法者有意识的一种行为,即通过有意识变通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相关条款达到创立有别于国家制度的经济特区制度。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特区立法变通的条款只有在与法律和行政法规相冲突时才具有适用上的优先性。这就意味着一个先于法律和行政法规制定的先行先试特区法规生效后与后来制定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相冲突时,特区法规并不应享有适用上的优先性,那些无意制定的冲突条款也不应具有适用优先性。按此理论,2015年《立法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对于特区人大常委会报送特区法规备案审查时要求其说明立法变通的情况后,法院对于特区法规变通条款的认定应该以特区人大常委会自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变通情况说明为准。不过对于法院来说,这种理论上合理的推理在实践中存在一定的困难,虽然我们通常可以从某个条例是否冠以“经济特区”名称来判断法规是不是特区法规,但特区法规本身一般都不会直接明示该特区法规是否有变通规定以及对哪些条款做了变通。虽然现行《立法法》要求特区人大常委会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说明变通情况,但到目前为止,对这种变通的情况说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未对外公开,因此法院实际仍然无从知晓特区法规的变通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也不能判断出哪些变通条款属于特区立法者明示的变通,哪些属于因为疏忽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与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冲突。
但从法院有关特区法规适用的判例看,法院总的倾向是,只要在审判中发现经济特区法规与法律或行政法规相冲突都一律以特区法规有权变通为由适用经济特区法规,不管是因特区法规未及时修订,与后来通过的法律或行政法规相冲突的情形,还是因特区立法者無意疏忽导致的法律冲突,都一律统一优先适用特区法规。在《立法法》出台前,有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贤成大厦案”[4],它涉及1995年《深圳特区企业清算条例》这一特区法规与1996年《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这一行政法规之间的法律冲突。尽管该特区法规被经济特区自身视为一种先行先试性立法而不是变通类立法,并且在与之相冲突的行政法规出台后也没有进行修改,但无论是深圳中院还是广东省高院最终都认定《深圳特区企业清算条例》具有优先于行政法规的适用性。在2015年《立法法》修订后的“谭安利诉深圳公安局案”[5]中,当法院发现2014年《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证条例》第十九条与2015年国务院《居住证暂行条例》第二条冲突时,法院也同样认定《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证条例》“作为特区立法,可以对上位法做变通规定”,尽管在《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证条例》制定时,其所谓要变通的国务院《居住证暂行条例》根本不存在。
二、“用足特区立法权”的法律空间
中央希望地处大湾区节点城市的深圳和珠海能够用足用好特区立法权,对于大湾区的经济特区城市而言,用足特区立法权就意味着在推进制度改革创新的过程中,如果有需要,首先就应尽量利用经济特区立法权这一立法特权和法律利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优先选择行使特区立法权而不是寻求全国人大常委会等主体授权
在深圳和珠海这类经济特区需要实施与现有法律、行政法规以及省级地方性法规不同的制度时,通常可以选择两种途径来处理,一种是直接寻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或者省级人大常委会的授权,一种是直接行使特区立法权。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前一种授权方式具有较强的政治和法律权威性,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政治和法律上的争议,对于试图获得中央对特区特定制度改革支持的经济特区而言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某些问题。但这种方式的弊端是比较费时,并且还不一定能够成功。在改革具有很大实验性和不成熟性的情况下,中央往往会因为谨慎不能及时作出决定。直接行使特区立法权最大的优势是特区可以根据本地制度变革的现实需要直接对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进行变通,而不必像大部分其他地区那样必须依赖上级机关的法律授权才能进行制度改革,因此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便利性。但行使特区立法权也有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就在于它无法对涉及法律和行政法规基本原则的事项进行变通,也无法对《立法法》第八条规定的属于法律保留事项进行变通。在大湾区建设的背景下,用足特区立法权就意味着经济特区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应大胆地优先选择行使特区立法权,而不是寻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或者省级人大常委会的授权。
(二)特区立法权对于可能涉及特区立法权限制的事项也存在一定的行使空间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无论是深圳还是珠海行使特区立法权都要受到法律和行政法规基本原则的限制,学术界的通说认为还要受到《立法法》第八条法律保留事项的限制。因此,对涉及法律和行政法规基本原则的事项,经济特区原则上不宜变通;对于《立法法》第八条法律保留事项的问题,在国家法律没有规定之前特区不宜进行先行先试性立法,在国家法律对这些事项进行规定之后,经济特区原则上也不宜进行变通。但这并不意味着特区立法权遇到此类问题就完全无所作为了。事实上,即便是面对这些问题,特区立法权仍然存在一定的行使空间。原因主要在于对于何为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原则以及法律保留事项本身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和解释空间,更为重要的是,迄今为止法院的司法判例尚未发现根据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或《立法法》第八条对特区法规进行审查的实践,也从未有司法判例以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为由拒绝特区法规的适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备案审查实践也未有以特区法规超越立法权限为由否定特区法规适用的例子。这种司法实践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备案审查实践至少表明,司法机关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特区立法的实践总体抱有一种非常宽容的态度,这种态度固然容易导致对越位特区立法的纵容,但也会对经济特区大胆通过行使特区立法权进行制度创新起到很大的激励作用。深圳特区的特区立法可以说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目前法律适用机关对特区立法采取的宽容态度,最终取得了较大的改革成就。
(三)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改为省级管理不妨碍合作区充分利用珠海特区立法权
根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后改为直接由广东省管辖,理论上此后横琴合作区将由广东省政府和广东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的机构通过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合作区的事务进行直接管理,部分事项将通过广东省政府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共同组成的合作区管委会发布规范性文件进行管理。尽管如此,横琴合作区既不太可能也没有必要完全排除珠海市地方性法规、特区法规、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适用。对于横琴合作区来说,珠海市拥有的比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和广东省政府更具优势的特区立法权可以成为推进横琴合作区制度改革与创新的法律利器。
广东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1981年1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广东省、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所属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的决议》,也拥有一定程度的经济特区立法权。在横琴合作区改为直接由广东省管辖后,由于合作区在行政区划上仍隶属于珠海经济特区,因此广东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通过行使长期搁置的经济特区单行经济法规立法权为合作区制定单行经济法规,并可以对法律、行政法规进行必要的变通。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广东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仅仅限于“制定经济特区的各项单行经济法规”,因此广东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就经济特区可行使变通权的立法范围不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直接赋予经济特区的特区立法权宽泛。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横琴合作区而言,在推进合作区的制度改革时充分利用珠海经济特区立法权比使用广东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经济特区经济单行法规制定权具有更大的优势。
三、“用好特区立法权”的法律与政治边界
如果说用足特区立法权意味着大湾区经济特区要充分利用有利于制度改革创新的特区立法权这个法律利器,而用好特区立法权则意味着大湾区经济特区在利用特区立法权进行制度改革创新时,要充分注意特区立法权在法律、政治和技术上的一些边界和限度,确保特区立法权的行使做到法律上合法、政治上稳妥,最大限度地降低通过特区立法权进行制度创新的法律和政治风险。
(一)注意特区立法权边界,尽量减少合法性争议
如前所述,可能涉及特区立法权行使合法性争议的问题主要存在于是否违背法律、行政法规基本原则,是否违反《立法法》第八条法律保留条款,以及是否存在特区法规非明示变通条款这三个方面。从确保特区立法权合法性的角度看,法律、行政法规明确确认的基本原则就不应进行变通,对于法律、行政法规虽然没有明确确认但从法律、行政法规整体进行解读可能涉及基本原则的问题,也要尽量避免变通;对于《立法法》第八条确认法律保留事项,如果法律未予规定,经济特区也不应予以先行先试,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制定法律,对这些事项也要尽量避免变通,因为如果予以变通,从严格意义上说,就相当于在特区法规中制定属于法律保留的事项;对于2015年《立法法》第九十八条第五项规定的备案审查时的变通情况说明要求,为了防止法律适用争议,经济特区应该在特区法规立法时尽量明确予以变通的条款以及所变通的法律或行政法规条款。
当然,上述三个限制都有比较明确的法律依据,但又不同程度上存在模糊或者不确定的一面。很多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本身并不是特别明确,对这些原则的解读也可能会出现较大的分歧,这就使得特区立法是否突破了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此外,2015年《立法法》第九十八条第五项的规定是否就意味着对特区法规变通条款的确认是以特区人大常委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明确说明变通的条款为限的问题,迄今在法律上也没有明确的答案。更让问题复杂化的是,有些经济特区尽管事实上并没有有效地遵守特区立法的法律界限,但这些涉嫌越界的行为实际也从未得到有效纠正。就深圳经济特区而言,除了前述《深圳经济特区公证条例》涉嫌违反行政法规和法律基本原则外,2020年8月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也涉嫌违反《立法法》第八条的规定,因为个人破产制度显然属于《立法法》第八条规定的“诉讼和仲裁制度”,该特区立法显然就对法律未予规定的事项进行先行先试立法了。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特区如何对待这种“立法创新”就成为一个需要特别慎重对待的问题。
(二)尽可能争取权威部门支持,确保特区立法权的行使具有政治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主要是指得到上级权威机关以及社会公众的认可。对于特区立法机关而言,行使特区立法权的合法性一般情况下应是首先要考量的内容,但也应该承认,在中国当前的语境下,政治合法性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比法律上的合法性还要重要。具有法律合法性的特区立法不见得能够获得上级政府或者社会公众的认可,但在具有政治合法性的情况下,有时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法律合法性上的不足。深圳市2020年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在很大程度上就反映了这种情况。该特区法规虽然涉嫌违反《立法法》第八条,但深圳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该特区法规却并非没有政策依据。2020年10月中央发布的 《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就明确规定,要“推进破产制度和机制的综合配套改革,试行破产预重整制度,完善自然人破产制度”。这份经过深圳市和国务院充分协商的政策性文件虽然在法律上完全无法作为深圳市对个人破产制度进行特区立法的合法授权凭据,但在政治上却从国务院到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都视其为深圳市进行先行先试立法的通行证。
从现实层面言之,经济特区要确保特区立法政治合法性,除了要争取特区所在市公众及各部门的支持外,最重要的是需要尽量就制度创新问题事先与上级权威部门尤其是中央各部门进行充分的沟通,哪怕这种沟通在法律上并没有必要。事实上,在大湾区法治建设中,深圳和珠海在进行与大湾区制度创新的有关特区立法时基本上也遵循了这个模式。例如,尽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已经明确政策规定,并且对这个领域的法律、行政法规进行变通在法律上并不会遇到特别大的合法性争议,但珠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在2019年9月制定《珠海经济特区横琴新区港澳建筑及相关工程咨询企业资质和专业人士执业资格认可规定》之前,除了广泛咨询了港澳相关机关和组织的意见外,仍“分别赴全国人大常委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省人大常委会、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就主要制度请示汇报,得到支持和指导”[6]。
当然,对于任何改革创新而言,没有任何风险的决策是很少存在的。大湾区法治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法律问题,大湾区经济特区要发挥特区立法权的法治创新功能,既需要体现对法治精神的尊重,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发扬其曾经拥有的开拓和冒险精神。相信这也是从中央政府到社会公众对大湾区经济特区的普遍期望。
注释:
[1]《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摘要》,载《当代经济》2012年3月上。
[2]参见黄金荣:《大湾区建设背景下经济特区立法变通权的行使》,载《法律适用》2019年第21期,第76页。
[3]两个案例可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备案审查室编著:《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案例选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0年8月版,第6-8、33-35页。
[4]该案详情可参见《案件聚焦:历时10年的“贤成大厦案”尘埃落定》,http://finance.sina.com.cn/g/20040411/1040712627.shtml,2022年7月20日访问。
[5]“谭安利诉深圳公安局案”的案情可参见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6]朱仁达:《开展创新性立法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法治保障》,载《人民之声》2021年第7期,第13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法学博士)
——基于合成控制法的分析
——评《中国经济特区四十年工业化道路: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