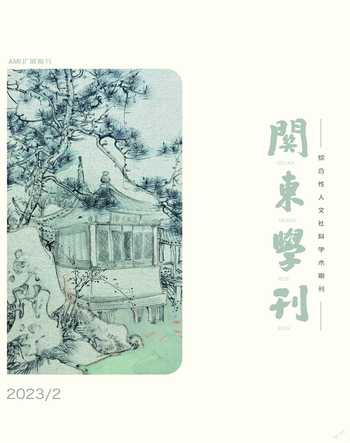土地·花生米·帽子
范家进 王天愉
[摘 要]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生动真实地为读者呈现了一幅苏南农民在特殊历史转折时期的生存图景。“土地”“帽子”“花生米”三类日常物象在作品中反复出现,作者将这三类物象放置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赋予不同的意义,或表现政策变化,或隐喻经济变迁,或凸显官民关系;并通过主人公陈奂生与这三类物象的情感纠缠,描写和刻画陈奂生这类农民的坎坷命运和复杂的文化心理性格,探索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
[关键词]“陈奂生系列”;乡村主人公;文化心理;高晓声
[基金项目]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当代乡土小说中主人公的变迁(1949-2019)”(20BZW166)。
[作者简介]范家进(1963-),男,文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王天愉(2001-),女,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学生(杭州 310018)。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关注建国以后中国农民和农村的发展,成为不少作家不约而同的自觉选择。因“右派”问题被遣送回家乡接受长期“改造”的高晓声就是其中突出而醒目的一位。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复出以后,他的主要精力和笔墨都用来描写中国农村和农民,并以表现农民在衣食住行方面的艰辛坎坷经历而引起文坛震动。在他创作活跃期里,不仅陆续推出了由多部中短篇小说构成的“陈奂生系列”(1991年12月上海文艺出版社以长篇小说形式出版《陈奂生上城出国记》;2001年作家出版社四卷本《高晓声文集》中也歸入其中的“长篇小说卷”,但少数篇目亦在“短篇小说卷”或“中篇小说卷”中重复出现),也留下了带有浓厚自叙传色彩且不在此系列中的长篇小说《青天在上》。限于篇幅,本文只简要论述和分析“陈奂生系列”中的乡村主人公形象所蕴藏的文化心理内涵及其意义。
从《“漏斗户”主》到《出国》,“陈奂生系列”包括七部中短篇小说,相对完整地记录了改革开放后十多年时间里一个普通苏南农民的命运沉浮与传奇。小说主人公是像大地一样朴实而平凡的中年农民,年龄上与高晓声大致相当。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改造”生涯中,作者与他笔下的人物朝夕相处、休戚与共,故而在这些人物身上蕴涵着作家的深层寄托。高晓声说,他“要启发农民的自我认识,认识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作用、责任,认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认识自己的历史和现状……使(农民)自己不但具有当国家主人翁的思想,而且确确实实有当国家主人翁的本领。”
高晓声:《开拓眼界》,《小说林》1983年第7期。】他笔下的陈奂生虽然只是一个人,但其背后站着的是一群“陈奂生们”,他们有类似的性格,面临着相同相似的境遇,甚至经历着大体相近的命运曲线。
据当代哲学家李泽厚的分析,文化心理结构“是专门属于人类的,由文化而历史地积淀而成。它表现为认识的时空直观和知性范畴,也表现为自觉的道德律令”,它“并非先验的理性,而仍然是由人类长久历史积累沉淀所造成”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312-313页。】。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其心理特征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承载着沉重的历史重负。作者在“陈奂生系列”的写作中使用了多种艺术手法,不过有三类具体的乡村日常生活物象出现得较为频繁,即“土地”“花生米”和“帽子”。它们在不同的中短篇中先后出现,凸显了不同时代的发展症候,作家进而挖掘了它们所隐含的不同社会现实,显示了乡村主人公独特的文化心理和性格。于是,物象同时成为意象,能指背后蕴蓄着丰富的所指。本文将以这三类物象为聚焦点,解读其背后的隐喻意义,尝试对陈奂生的文化心理及性格构成进行一些探究。
一、土地:农民的牵系和羁绊
西谚曰:人来自尘土,又归于尘土。中国社会从秦汉开始就有祭祀土地神或社神的习俗,历代皇帝在夺取政权后也往往会举行相应的祭祀仪式,并留下地坛之类的遗址。更不用说改朝换代一般都与土地的争夺有关。可见土地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性。人们在土地上生产粮食、放牧牲畜、修筑道路、建造房屋,甚至去世后也被大地所接纳和收留。尤其是农民,甚至把土地当成自己的命根子,哪怕远走他乡,也有揣一把故土放在怀里的习俗。到了当代中国,这种心理仍然顽强地延续着。“土地、土地,种了几十年田的庄稼人充分懂得它的好处,为它喜,为它愁,为它笑来为它哭,它是社员心头一块肉”
高晓声:《陈奂生上城出国记》,陆文夫、费振钟主编:《高晓声文集》(长篇小说卷),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第384页。】。自然,土地也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和改革历程中最敏感的神经,牵一发而动全身,无论是大起大落的巨变还是适度调整的改革,都会对数亿农民产生重大的影响。置身历史大潮中的陈奂生就像小小的一叶扁舟,在时代的飓风大浪里经受着他个人无法掌控的剧烈颠簸和摇晃。
“陈奂生系列”中的打头篇是1979年5月发表在《钟山》上的《“漏斗户”主》,作家笔下第一次出现了一位劳动特别勤快、力气大、食量也大,在公社化年代无论如何也吃不饱的、土头土脑的当代中国农民陈奂生的形象。作品中写到,“文革”中,由于政策的严重束缚,陈奂生空有一身力气,可还是落下了一顶难堪的“漏斗户”主帽子,因为他总是背着一身“粮债”,像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每一年都在为一家人如何填饱肚子而发愁,日子过得很是凄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业农村政策出现了相应的调整,生产队出台了激发农民积极性的新措施,陈奂生很快摘掉了有辱尊严的“漏斗户”帽子,秋收后“一共分配到三千六百零五斤粮食,比去年的二千二百五十九斤多了一千三百四十六斤”
高晓声:《“漏斗户”主》,陆文夫、费振钟主编:《高晓声文集》(短篇小说卷),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第62页。】!他转眼就从缺粮户变成了“余粮户”。农业政策一调整(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陈奂生得以当上“六亩三分田王国的国王”,同样的土地,却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
正如当地谚语所说:“种大田藏死钱”。虽然通过家庭土地承包,陈奂生一家解决了基础温饱,但和村里其他聪明的“钻尖货”相比还是拮据得很,他离真正意义上的“致富”还相距很远。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年事渐高的陈奂生发现自己挑不起种田大户的担子了,“产量逐年降低,收入逐年减少”
高晓声:《陈奂生上城出国记》,陆文夫、费振钟主编:《高晓声文集》(长篇小说卷),第450页。】,生活反倒又显得日渐困难起来。因为固守土地,仅靠农耕,在从集体承包的有限土地上,陈奂生难以实现农民身份的蜕变。在小片承包土地上从事单一经营,也注定了难以真正走上致富之路。而如何摆脱土地的束缚,对于陈奂生这一代农民来说,确实说得上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数千年代代相传的“土地情结”,又怎能轻易从他们身上消除。
为此,作家有意识地表现了陈奂生命运中出现的几次“离土”的机会以及他本能般的选择结果(反而都是加深了只有靠种田才能生活的想法)。
第一次是队办厂(当时称社队企业)的厂长想让陈奂生凭着他与地委书记吴楚的私人关系去当采购员。这次采购给陈奂生带来了六百元的奖励,这以当时农民的生活水准及物价来衡量,简直近于“天文数字”了;但除了欣喜之外,陈奂生却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与困惑之中,“他认定这一笔飞来横财不是他的劳动所得,他拿了,却想不出究竟有哪些人受了损失”
高晓声:《陈奂生转业》,陆文夫、费振钟主编:《高晓声文集》(中篇小说卷),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第140页。】,他竟比以前更“沉默”了。多亏小学教师身份的堂兄陈正清的一番话,既让他认清自己的性格特点,也解除了他对新政“包产”的担忧与恐惧。这之后,陈奂生反而铁了心,认定自己不适合通过偶然认识的官场人物大把捞钱,而是“从此与工厂脱钩,在村里包产种田”
高晓声:《陈奂生上城出国记》,陆文夫、费振钟主编:《高晓声文集》(长篇小说卷),第401页。】。
第二次是家庭副业的选择。“社队企业办得红火的一些苏南农村,集体主义传统相对深厚,农业机械化也实现得最早;由于社队企业和家庭副业转移了农业人口和剩余劳动力,每个家庭只留少量口粮田,其余的土地交给几个专业户规模经营。农民的收入已经主要来自社队企业(乡镇企业)和家庭副业。”
闫作雷:《“陈奂生”为什么富不起来?——兼论“新时期”农村题材小说中农民的致富方式(1978—1984)》,《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但无论是养德国毛兔还是地鳖虫,陈奂生都不是那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精明人,他总是比别人慢半拍或是更多拍,总是跟不上形势,等到他眼红别人的收益时,市场不是饱和了就是跌价了。他的思维在旧有的习惯性故道上缓慢滑行,不舍得投资本钱,也不知“性价比”为何物,“一年復一年,奂生夫妻俩仍旧认为要吃鸡、鸭、蛋,非从小养大它们不行”
高晓声:《陈奂生上城出国记》,陆文夫、费振钟主编:《高晓声文集》(长篇小说卷),第419页。】,从未想到自家鸡生的蛋其实是“花费了五个蛋甚至十个蛋的钱才有自家鸡生的一个蛋,是一个吃不起的金蛋蛋”
高晓声:《陈奂生上城出国记》,陆文夫、费振钟主编:《高晓声文集》(长篇小说卷),第420页。】。
这里体现出陈奂生对商品经济的迟钝。他不会别的营生只会种田,包产后,他甚至干得比以前更勤快,把自己所有精力都投到田里。“包产以后,队里不论哪一家,都不像集体劳动那样,天天下田。有的是巧安排,有的是懒安排,有的甚至已经不放在心上,准备赔产,他们忙于赚大钱,不在乎田里的收成了。只有奂生,全力以赴,一心扑在禾苗上,弄得田里没有一棵杂草,田四周刈得干干净净。”
高晓声:《陈奂生上城出国记》,陆文夫、费振钟主编:《高晓声文集》(长篇小说卷),第 页。】此时的陈奂生已经将自己束缚在那一小方分散的土地上,简直有点“万般皆下品,惟有‘种田高”了。对于不懂多种经营的陈奂生来说,种地是他最为信赖而贴心的“舒适圈”,只要“六亩三分地国王”的安稳梦还能做下去,他就愿意继续维持现状。而他也不会预感到作为“死守小块土地的传统农民”
闫作雷:《“陈奂生”为什么富不起来?——兼论“新时期”农村题材小说中农民的致富方式(1978—1984)》,《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维持现状的美梦是维持不了多久的。
《出国》篇算是他可以与土地脱离的第三次机会。见识到与苏南农村迥然不同的西方花花世界后,照理本应该对陈奂生改变固有观念有所触动和启发,但出国后陈奂生种种让人哭笑不得的表现随处印证着他对田地的“钟爱”已经融入了他的骨髓。当陈奂生到艾教授家代看房子时,被告知除了看管屋子还需要适当修剪草坪,他不禁暗忖:“那么大一块土地不种菜,让荒草占据了,还要花时间修饰它。”
高晓声:《陈奂生上城出国记》,陆文夫、费振钟主编:《高晓声文集》(长篇小说卷),第520页。】实在心痒难耐的陈奂生未经主人允许,找到一把亮锄就“用双手捏着,一口气锛脱了大约一个平方米的草坪”。后来他被告知修复一平米草皮竟要几十美金时,陈奂生震惊得合不拢嘴。“草坪补好了,陈奂生的心上却被划出了一条痕”
高晓声:《陈奂生上城出国记》,陆文夫、费振钟主编:《高晓声文集》(长篇小说卷),第531页。】,这道深痕划出了中西文明的巨大落差,尤其是传统农业文明和现代工商社会之间的巨大缝隙。从这之后,陈奂生对早早回家的念头变得空前强烈和执着,“金窝,银窝,毕竟不及家中草窝”
高晓声:《陈奂生上城出国记》,陆文夫、费振钟主编:《高晓声文集》(长篇小说卷),第532页。】,对西方现代化社会及其生活方式的强烈“排异反应”,愈加把他推回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生活习惯和心境之中。只有在那里,陈奂生才能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心安理得之所。
这三次主观或客观上对土地脱离的尝试反而让陈奂生与土地靠得更近,对于他这代农民而言,确实是终身无法脱离土地而生存下去。他对土地近乎贪婪的渴望无形中也阻碍了自己以别的方式发家致富的可能性。随着周围其他人,特别是年轻一代致富途径和手段的日益丰富,进城打工或经商,已经是他儿女辈所要谋求的生存道路了。土地既是对这代农民的养育和承载,也构成了对他们的终身束缚和羁绊,这不仅是身份和生活道路上的,也是心理和灵魂意义上的。从这里,也印证着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
二、花生米:乡村经济变迁的晴雨表
在陈奂生个人和家庭命运起落的故事里,花生米是苏南一带农村经济的“晴雨表”,也是改革开放对我国农民物质生活带来不同影响的最直观表现。
陈家村一带不出产花生,文化大革命时期花生竟被称作“贵公子”,加上商品经济不发达,花生显得又贵又俏,“比肉价还高得多,哪一家待客用花生米做下酒菜,陈家村上的人会当一件新闻传开去”
高晓声:《陈奂生上城出国记》,陆文夫、费振钟主编:《高晓声文集》(长篇小说卷),第407页。】。而《包产》篇中,花生虽然没这么紧俏了,但还是作为一份用心的礼物在“人情”交往间流传。陈奂生在当采购员时无意中出手相助过的个别外省农民,经过包产的新政策生活条件有所好转,“念着旧情,找上门来,送了奂生五斤花生”
高晓声:《陈奂生上城出国记》,陆文夫、费振钟主编:《高晓声文集》(长篇小说卷),第392页。】。陈奂生在钞票的诱惑和社队企业厂长好言好语的温情攻势下,又被怂恿着再去找已升官的地委吴书记那里走走“后门”。如何给吴书记送点伴手礼呢?陈奂生思来想去,“想起吴书记下酒爱吃花生米,便把外省人送给他的那五斤花生拿出来剥光了壳,用塑料袋装了带走,既不显眼,也讨得吴书记喜欢”。这两次“送礼”的花生米虽然都并不特别贵重,但毕竟都出自送礼人的真情实意,都尽力投对方所好,也自认为所送礼物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
但想不到花生的身价在包产后不久就一落千丈。陈奂生的妻子张荷妹有一次兴致勃勃地给外甥张坤大炒来一碗花生米做招待,却被告知说,“这样东西,三年前头是宝贝,两年前就普通,到一年前头,就不上台盘了”
高晓声:《陈奂生上城出国记》,陆文夫、费振钟主编:《高晓声文集》(长篇小说卷),第415页。】。从把花生米当“稀罕物件”到相互赠送再到“早就过时”被嫌弃,花生米在农民日常生活中地位的转变,足以让人感受到中国农村经济在短短数年间的快速挺进步伐。
当然,陈奂生一家对花生米很快失宠“过时”的不解与困惑,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像陈奂生这样的农民们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的被动迷茫与一时难以应对。作者借乡村年轻人张坤大之口说出了这代父辈农民的心理现状:“这两个老实人包种了几亩田,埋头死做,旁的事情全不晓得,社会变起来快得打呵欠割舌头,样样都像花生米一样调整位置,舅舅舅母哪里弄得明白!”
高晓声:《陳奂生上城出国记》,陆文夫、费振钟主编:《高晓声文集》(长篇小说卷),第415页。】现代化意味着商品经济的大流通,意味着各种时尚的轮番登场和退场,意味着城乡居民“喜新厌旧”的消费需求得到充满尊重和认可,而在“公社制”下被束缚了大半辈子的老一代农民,怎能不在这样的全新商品经济大潮中晕头转向、无所适从?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如何适应时代列车的飞速运行,如何及时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与内在理念,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和社会课题。高晓声在“陈奂生系列”中的描写与表现,显示出他对中国农民文化心态的独特的情感体验以及与众不同的关注视角。
三、帽子:有形的和无形的
帽子是“陈奂生系列”中频繁出现的另一重要物象和意象。穿衣戴帽,是劳动人民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常生活事务,但在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小说里,“帽子”则被赋予多重意涵,作者借助这一日常生活细节,进一步描绘和开掘陈奂生这代农民的具体生存质量及深层心理意蕴。
在陈奂生的命运沉浮经历中,他曾依次被戴上过三顶帽子,既是实体意义上的,又是象征隐喻性的。
陈奂生最早的一顶帽子是“漏斗户”。虽然是公社制下的一位极为卑微的农民,可他最初被扣上这顶帽子时心中仍然忿忿不平,暗自思忖道:这顶帽子不是“富人嘲笑穷人,地主嘲笑农民”吗?“共产党的干部,能这样看待困难户吗?我种了一世田,你倒替我定了个‘漏斗户的罪名。你就只晓得我粮食不够吃,却不晓得我一生出了多少力!”高晓声:《“漏斗户”主》,陆文夫、费振钟主编:《高晓声文集》(短篇小说卷),第55页。】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屡经磨难,被压在最底层的普通农民更是雪上加霜、温饱难求,即使进入当代中国,这种状况的实质性改变也是一再遭受种种阻碍。在实际生活处境的刺激下,陈奂生会自发地产生这一类隐藏着的愤怒与不平,但时间长了,这种“忿忿”的棱角也易于被自己和家人的饥饿消磨殆尽。他变得越来越沉默和木然,外界压力也让他逐渐形成了单一、短视的线性思维方式——从前是只想着填饱全家人肚子(粮食)一件事,到了改革开放时代也还是只知埋头种田而不知变通,以至错过了一些可以适当改变命运的机会。
此后的一顶帽子是一顶实体的冬帽,也是《上城》一文中的核心故事线索。当地农业生产实行“三定”办法后,陈奂生终于得以解决初步的温饱问题。但日常零用还是十分拮据,陈奂生需要在农业劳动之余,连夜去县城的小火车站做点小买卖(出售自制的一种面食产品——油绳),打算用赚来的钱买一顶帽子过冬。但陈奂生上城之后却阴差阳错,遭遇一系列尴尬事件:突发感冒在火车站候车室躺下睡去,关心民生的县委书记出差途中发现了这位他认识的老实农民,委托司机将发烧的他送去县委招待所过夜……,醒来的陈奂生发现遭遇空前人生大尴尬与大损失!因为他在百货公司看中的一顶帽子需要二元五角,但他在迷糊中被送来住宿的、生平从来没有资格进入的高级招待所却索价五元一夜!陈奂生不禁哀嚎:“我害怕困掉一顶帽子,谁知竟要两顶”!一夜房价就抵两顶帽子的县委招待所是他万万消费不起的(不是县委书记的小车星夜送来,他也根本无权靠近),“他一个农业社员,去年工分单价七角,困一夜做七天还要倒贴一角”
高晓声:《陈奂生上城》,陆文夫、费振钟主编:《高晓声文集》(短篇小说卷),第186页。】。所以忍痛付了钱的陈奂生再次回到房间,内心感受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推开房间,看看照出人影的地板,又站住犹豫:‘脱不脱鞋?一转念,愤愤想道:‘出了五块钱呢!再也不怕弄脏,大摇大摆走了进去,往弹簧太师椅上一坐:‘管它,坐瘪了不关我事,出了五元钱呢。”
高晓声:《陈奂生上城》,陆文夫、费振钟主编:《高晓声文集》(短篇小说卷),第186页。】
作家对人物这些行为和心理细节的想象与挖掘,来自于他长期被“改造”过程中对农民的极度了解和熟悉,以及对这种精神创伤的沉痛感受和体验,也深刻揭示了主人公现代主体意识的蛰伏和不健全。反观他未知房价前對生平头一次进入的“高级房间”的珍惜和小心翼翼,其实是隐含着一种类似于刘姥姥进大观园式的“奴才的珍惜”或畏惧。无论是脱了鞋在油漆过的房间地面上行走担心把地面弄脏,还是不敢坐大皮椅(沙发),“怕坐瘪了弹不饱”,其实都源于一种与生俱来的自卑;因为长期以来的日常生活轨迹中,他这样的农民根本没资格进入这样的招待所,他已习惯性地将自己放置在一个极度卑微低贱的地位上,不可能、也不敢具有自己也是这些社会公共产品的“主人”意识。但既然让他承担了劳动七天还要倒贴一角钱的超常利益损失,他又要不管不顾地、泄愤般地试图从心理上把意外遭受的亏欠找补一点回来。
而陈奂生的第三顶帽子是地委书记吴楚亲手送给他的,兼具实体和象征意义。在《转业》一篇中,吴书记看陈奂生头上的帽子旧了,说自己有一顶买大了点的帽子可以送给他,“吴楚拿了一只崭新的呢帽走进来,笑着说:‘你看,我嫌大。他往头上一套,果然遮到眼睛上。脱下来戴到奂生头上去,恰是正好”
高晓声:《陈奂生转业》,陆文夫、费振钟主编:《高晓声文集》(中篇小说卷),第121页。】。高晓声曾在《谈谈有关陈奂生的几篇小说》中讲到设计这个情节是为了显示“群众是大头,干部是小头”
高晓声:《谈谈有关陈奂生的几篇小说》,《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3期。】的寓意。但在陈奂生的日常生活世界里,他一直是把这种关系颠倒着看的:在他心里,国家就仿佛是个大家庭,生产队长是“爹”,大队长是“爷”,公社主任是“祖爷爷”,吴书记的辈分就不知比自己高出多少了,真是当成太祖太宗都不为过!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就习惯于把关心普通民众疾苦的各级官员视为“青天”,陈奂生的文化心理结构不能超过这种集体心理定势的平均数。所以高晓声在《谈谈文学创作》中不无沉痛地感慨道:“他们的弱点确实是很可怕的,他们的弱点不改变,中国还是会出皇帝的。”
高晓声:《创作谈》,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第60-61页。】
作家在塑造陈奂生这个形象时,还特别关注伴随在他艰难物质生活进程中的无形的“帽子”——心理和精神上的某些根深蒂固的“旧习”和惯性。譬如误打误撞住了一夜“高级旅馆”后的面子问题,作家最后设计了“精神胜利法”作为他的精神避难所。回家的路上,陈奂生盘算着各种自我宽解的说辞和借口,或者是“这等于出晦气钱——譬如买药吃掉”
高晓声:《陈奂生上城》,陆文夫、费振钟主编:《高晓声文集》(短篇小说卷),第186页。】,或者跟村里人说,是吴书记看得起他才请他去住……总之,是不让自己在乡民面前丢脸,要让其他人也觉得他即使花了五块冤枉钱也能算“值透”。作家在设计和表现这些细节时,笔下其实隐含着读者不易察觉的苦涩和沉痛
对此,笔者在专著《当代乡土小说六家论》第六章中有过论述,此处不再展开。参见范家进:《当代乡土小说六家论》,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185-229页。】。
四、填饱了肚子以后
因政治运动而被贬入底层“改造”了二十多年的高晓声确实是最了解当代中国农民的作家之一。故而他笔下与作家大致同龄的陈奂生身上汇聚着当代农民的诸多复杂意蕴。陈奂生身上有着人们通常所乐于称道的当代中国农民的品质:勤劳踏实、老实肯干、淳朴善良、对党员干部始终敬畏而顺从,甚至常常受了欺侮也不知道反抗。我们的主流话语里,会习惯性地以“贫下中农翻身做了主人”来表述农民在新社会中的地位,但具体到陈奂生这个主人公身上,他始终处于社会的边缘,不曾把自己视为“主人翁”。他不光是不敢求,甚至连想都不敢想。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心理积淀,使得陈奂生习惯了以颠倒关系看待官与民。譬如说,通用的话语表述是人民已成国家的主人,但陈奂生却本能般地将县委书记(后来的地委书记)吴楚视为自己的上帝,主人和人民公仆的关系完全倒置。“四人帮”被粉碎后,他摘掉了“漏斗户”主的帽子,显然是新国政的受益者,但他事实上也仅仅只是填饱了肚子,内在心理和精神上的更新换代还无暇提上议事日程。基本温饱解决以后该怎么办?他确实还来不及加以细心谋划。“‘兜肚里有了钱,还怕不会过日子吗?他们不承认‘有了钱确还有一个‘怎样过日子的问题要解决。他们自以为想过了,自以为解决了,其实完全没有。”
高晓声:《陈奂生上城出国记》,陆文夫、费振钟主编:《高晓声文集》(长篇小说卷),第433页。】小农经济的生产者们长期为“肚皮”奔波,能将自己和一家人的温饱问题大致解决,就足以花费他们的九牛二虎之力。在此基础上的精神提升和拓展,显然还需要假以时日。
在这些中短篇小说里,作家一再表现了陈奂生权利意识模糊、只知道“荫下饭”好吃、乐于做“跟跟派”的心理习惯。日常生产与生活中长期缺乏必要的自主性和主动权,慢慢地,他们几乎成了“只管做,光用手,不动脑的产粮机器”
范伯群:《陈奂生论》,《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1期。】。一旦需要他独当一面独立判断时,他反而更加六神无主手足无措,甚至对“自主权”产生反感和抵触情绪,只求有别的力量来代他“做主”。在陈奂生的心理世界里,似乎待在枷锁里才能获得他所需要的“自由”。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陈奂生这种文化心理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历史和社会原因,是政治、经济、文化多种因素杂糅所造成。作家也曾描写过陈奂生身上一些初步的自尊意识、自主意愿,陈奂生并非生来就不愿“当家做主”。譬如当初,陈奂生对口粮的分配政策就抱有诸多怀疑,曾发问:“为什么牵涉到了一批人的问题反而不去努力解决?”
高晓声:《“漏斗户”主》,陆文夫、费振钟主编:《高晓声文集》(短篇小说卷),第53页。】他甚至想拜托小学老师陈正清给报社写信反映自己长期辛苦劳动却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但陈正清却告诉他:“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根本就没有你说的这种事实”,“凡是事实,都要能证明社会主义是天堂”
高晓声:《“漏斗户”主》,陆文夫、费振钟主编:《高晓声文集》(长篇小说卷),第58页。】,这给陈奂生兜头浇了一盆冷水。面对铁桶一般严密的媒体舆论,他只好认输,一腔愤懑之气化为一声哀叹。自己和一家人的肚饥问题,足以让他所有的“热血”都凉下来。对于饿着肚子的人来说,“主人”的字眼和意识,确实都太奢侈了。
于是,“再饿一年看”成了他的口头禅。面对无法躲过的天灾,“忍”和“熬”虽然显示了“陈奂生们”的某些坚毅品格,但同时也何尝不是一种逆来顺受的天性。正如高晓声在《且说陈奂生》一文中所说:“他们甘于付出高额的代价换取极低的生活条件,能够忍受超人的苦难去争得少有的欢乐。”
高晓声:《且说陈奂生》,陆文夫、费振钟主编:《高晓声文集》(散文随笔卷),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第403-404页。】已成定势的习惯性文化心理让陈奂生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他越自卑就越没有抗争的勇气,越怯于抗争就越自卑。遇到种种挫折,他总是习惯性地责怪自己,而不敢睁大眼睛去打量那些给他带来种种压迫和阻碍的力量和人物。即使在城里花了冤枉钱反倒怪自己没有提前买好帽子做好自我保护,怪自己“受不起这么高级的关心”……高晓声确实太了解当代中国农民了,他深知“当家作主”对陈奂生们是一件多么艰难的历史使命。
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土地”“花生米”“帽子”,作家在三类世俗物象中浓缩了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后期间的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变迁,并通过陈奂生这个普通苏南农民的坎坷经历和命运,展现了中国农民在时代巨变中的悲欢离合和文化心理变迁。通过“陈奂生系列”及同时期的另一些作品,高晓声表达了对中国农民在物质生存条件得到基本改善后,如何进一步提升其思想境界与精神生活的深沉忧思。时至今日,它仍然是作家们需要认真面对的严肃的时代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