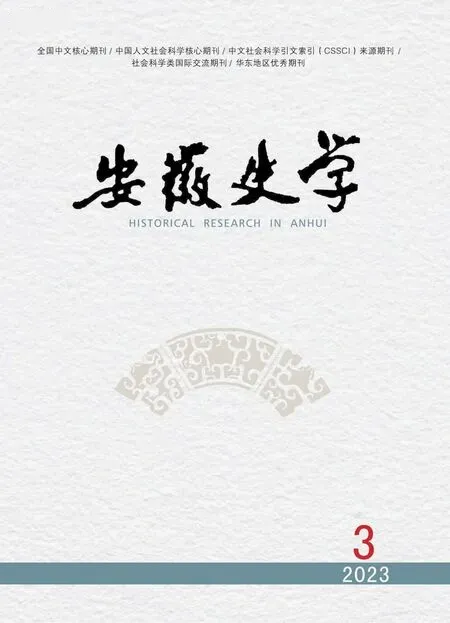胡适与民国时期的中华文化外译
雷炳浩 马会娟
(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北京 100089)
谈到胡适,人们往往关注其引入西学之功,盛赞其为影响我国近代知识分子心灵的三位杰出翻译家之一(1)转引自陈瑞山:《胡适与严复》,《翻译学研究集刊》2018年第22辑,第172页。,对他的翻译思想、翻译作品、翻译影响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2)相关研究成果如李红绿、赵娟:《胡适翻译思想探析》,《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09年第2期;张少鹏:《早期创造社与胡适的翻译论争》,《安徽史学》2009年第6期;雷炳浩、马会娟:《胡适与早期社会主义文献的翻译》,《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22年第3期,等。遗憾的是,他在中华文化外译方面的贡献却鲜有学者论及。(3)本文中的中华文化外译主要指中国古代典籍和传统思想文化的对外译介,不包括胡适对自己作品的翻译,也不包括他人对其作品的翻译。胡适作品的英译比较复杂,笔者拟另行撰文论述。作为所谓“全盘西化”(4)胡适曾明确表示自己赞成、支持全盘西化,但同时指出因为文化固有的“惰性”,文化改造最终会走向折衷,见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2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55页。因此,有论者认为,“从文化改造的方法、手段上说,他的确是全盘西化论者;而从文化改造的结果上说,却又是道地的中西文化交融论者”,见杨林书:《试析30年代胡适文化观的矛盾》,《安徽史学》1993年第4期,第68页。的主要代表,胡适在自己的中文著述里对中华文化多有批评,且常常言辞激烈、不留情面,这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似乎是他不太可能助力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但是回顾胡适的一生,可以发现中华文化的对外译介构成了他翻译活动的重要一环,他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所做的努力受到了不少国外学者的赞赏。(5)Bertrand Russell,“Early Chinese Philosophy”,The Nation and the Athenæum,Vol.33,No.25(1923),p.778;范劲:《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汉学对胡适的接受》,《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5期,第94页。有鉴于此,本文利用胡适档案、日记、书信等材料梳理他与民国时期中华文化外译活动之关系,揭示其文化外译活动的意义,以期为当前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启示。
一、亲身从事中华文化外译实践
留美期间,胡适即注意到美国民众对中国社会的深深误解,“此邦(指美国)人士多不深晓吾国国情民风……盖恒人心目中之中国,但以为举国皆苦力洗衣工,不知何者为中国之真文明也”。(6)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3册,第78页。为了消除这种误解,胡适在努力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积极通过翻译向美国民众介绍中国。
(一)留美期间的汉诗英译
关于胡适的诗歌翻译,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尝试集》上,着重探讨其英诗汉译对中国白话新诗产生的影响,忽视了他留美期间即开始的汉诗英译对其文学革命思想的重要意义。通过检索胡适档案,可以发现至迟到1914年他已经开始尝试将汉语文言诗翻译成英语白话诗。这年11月6日,他在致美国友人韦莲司(Edith Clifford Williams,1885—1971)的信中谈及自己为其收集中国有关月亮的神话一事,并翻译了一首中国诗。(7)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虽然这首译诗没能保留下来,但我们至少可以知道胡适已经开始了汉诗英译活动。
1914年12月3日,胡适因对英美世界翻译的《诗经·木瓜》不甚满意,遂自己动手翻译:原文: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译文:Peaches were the gifts which to me you made,/ And I gave you back a piece of jade—/ Not to compensate/ Your kindnesses,friend,/ But to celebrate/ Our friendship which shall never end.(8)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1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年版,第555页。1917年1月12日,胡适又将杜甫的一首绝句翻译成英文:原文:漫说春来好,狂风大放颠。吹花随水去,翻却钓鱼船。译文:Say not Spring is always good,/ For the Wind is in wild ecstasy:/ He blows the flowers to flow down the stream,/ Where they turn the fishman’s boat upside down.(9)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2册,第459页。此外,在担任《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编辑期间,胡适还翻译了杜甫的《兵车行》,发表于该刊第10卷第3期。(10)Suh Hu trans.,“The Song of the Conscript”,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Vol.10,No.3(1914),pp.139-140.这是胡适少有的公开发表的汉诗英译成果。遗憾的是,鲜有学者论及该诗的翻译。胡适档案中保存有他英译《兵车行》的打字草稿,内容与公开发表版本略有不同,另附有他英译杜甫的另外两首诗《新安吏》和《石壕吏》(11)“The Song of the Conscript by Tu Fu (712-770 A.D.)”,台北胡适纪念馆藏,馆藏号:HS-NK05-197-012。,显示了这一时期胡适对杜甫诗作的重视。
(二)作为学术研究和公共演讲工具的翻译
除了早期的汉诗英译,胡适此后很少直接进行汉语作品的英译,更多的是将翻译作为一种工具以服务其学术研究。1926年,胡适赴欧参加会议期间结识了很多著名学者,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Eugène Pelliot,1878—1945)就是其中之一。交往过程中,胡适得知伯氏正在修订美国学者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1882—1925)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便提醒对方注意元稹的《〈白氏长庆集〉序》(12)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9册,第136页。,后来更将该序翻译后寄给伯希和。(13)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4册,第623页。此外,胡适还在自己的英文写作和研究中广泛征引与翻译中国文献以证明自己的观点。比如,他在自己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中就译介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很多理念。他的学术翻译活动得到了国外学者的重视,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曾指出胡适翻译的古代中国文本精确可靠,任何外国人都很难赶得上。(14)Bertrand Russell,“Early Chinese Philosophy”,p.778.
早在留美期间胡适即开始有意识地通过公共演讲传播中华文化,以纠正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偏见。七七事变之后,胡适应蒋介石邀请出任驻美大使,任内四年(1938—1942)是他集中向美国政府和人民介绍中国的时期。在对美外交方面,胡适认为“无关战事的讲演比直接的宣传为更有效”(15)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7册,第534页。,因此便充分发挥其优势,旅行数万里,演讲百余次。(16)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7册,第511页;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73页。他的演讲涉及中国历史、文学、哲学等多个方面,翻译并介绍了很多中国思想文化术语。比如,在1941年所做的“民主中国的历史基础”演讲中,为了证明民主在中国有其思想渊源,胡适翻译、介绍了孔子的“有教无类”“苛政猛于虎”,孟子的“民贵君轻”“性善论”等思想。(17)Shih Hu,“Historical Foundations for a Democratic China”,in Anonymous ed.,Edmund J.James Lectures on Government (2nd series),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41,pp.53-55.这种将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民主观念结合起来的做法,显然比简单的政治说教更容易让美国民众接受,使他们意识到中美两国处于同一战线上,从而唤起他们对中国抗战的理解和支持。有学者指出,美国民众对中国抗战的态度由二战初期的全无了解、漠不关心转变为后期的同情与支持,胡适在其中起了相当作用。(18)周质平:《胡适的情缘与晚境》,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228页。胡适日记中的一些小事足可证明这一点:1938年2月他在华盛顿演讲,一名雇役拿了三块银元给他,希望捐给中国以作救济;同年3月31日他在费城演讲时,台下的几位老太太都感动落泪了。(19)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7册,第476—477、517—518页。
二、赞助中国人的中华文化外译事业
除了自己身体力行,积极进行中华文化的对外翻译,胡适还通过提供资金支持以及专业指导等方式赞助了一系列中国人的中华文化外译活动。
(一)胡适与熊式一的中华文化外译
熊式一是与林语堂并称海外的双语作家,在英语世界撰写并执导戏剧的中国第一人。西方文化界有“东林西熊”的说法,美国文化界佩服林语堂,青睐其《京华烟云》,英国文化界佩服熊式一,钟爱其《天桥》。(20)转引自马会娟:《熊式一与中国京剧〈王宝川〉的文化翻译》,《外语学刊》2017年第2期,第86页。作为中华文化外译的杰出代表,熊式一对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考察其中华文化外译活动,可以发现胡适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熊式一早年就读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文科,毕业后先后任教于北京、上海等地多所大专院校。当时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西滢有意聘请他担任欧美近代戏剧的正教授。遗憾的是,当时的教育部门此前早有规定,无留洋经历者不得担任英文系正教授。在得知熊式一没有留洋经历后,陈西滢只好作罢。这件事深深触动了熊式一,使他产生了留学英伦的想法。但是他的家境并不好,妻子当时尚未大学毕业,两人还有五个孩子需要抚养。为了筹措给妻儿的教养费以及自己的留学经费,熊式一不得不将自己所著译之书稿尽数出售。(21)熊式一:《八十回忆》,海豚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当时接受熊氏所译英国戏剧家巴蕾(J.M.Barrie,1860—1937)剧本的正是胡适领导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胡适虽然认为他译得并不好,未能把握巴蕾语言的风趣幽默,仍同意买下他的译稿,让他用这笔稿费作为去英国留学的路费。(22)刘靖之主编:《翻译论集》,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年版,第65页;《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七次报告》,1932年,第33页。正是有了这笔费用,熊式一才得以负笈英伦,师从英国著名戏剧专家尼科尔(Allardyce Nicoll,1894—1976),在后者的建议下翻译中国戏剧,最终凭借《王宝川》的翻译和舞台演出一炮走红。
(二)胡适与梅兰芳访美演出
20世纪30年代梅兰芳的访美演出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由于资料所限,已有研究往往将演出的成功归因于京剧独有的东方文化魅力、梅兰芳个人的表演艺术以及“梅党”成员所做的巨大努力,但是当我们将目光转向胡适档案等历史材料时,却可以发现京剧这一所谓“旧文化”在美国获得巨大成功的背后隐约闪现着胡适等“新文化”知识分子的身影。
梅兰芳访美能够成行,由胡适等人共同创办的华美协进社功不可没。(23)参见李庆本、李彤炜:《谈华美协进社在梅兰芳访美演出中的作用》,《戏剧》2018年第5期;陈倩:《华美协进社与中国戏曲的跨文化传播——再论梅兰芳访美之始末》,《中国文化研究》2021年第2期。华美协进社成员积极参与了梅兰芳赴美的组织和策划工作,是梅兰芳成功访美的重要推动者。成员姚昌复不仅翻译了《霸王别姬》《宝蟾送酒》《武家坡》等经典剧目,撰写了商业味浓厚的宣传册,而且根据西方文化的特点,在具体翻译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戏曲进行改编,成功调动起美国观众的兴趣和好奇心。(24)陈倩:《华美协进社与中国戏曲的跨文化传播——再论梅兰芳访美之始末》,第176—177页。成员张彭春在梅兰芳访美之前就承担了撰写相关介绍、协助翻译资料等重要工作,后来更被剧团礼聘加盟,成为梅兰芳访美期间所有剧目与演出安排时最依赖的顾问。(25)傅谨:《梅兰芳与新文化》,《文艺研究》2014年第5期,第92、96页。华美协进社创始人之一、胡适的老师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更是梅兰芳访美活动的美方赞助人之一。
作为旧剧改良的倡导者和新式戏剧的引进者,胡适积极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梅兰芳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太真外传》是梅派艺术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梅兰芳访美演出期间的一出重头戏。该戏由齐如山为梅兰芳量身打造,写作过程中齐如山即多次致信胡适,请求其帮忙修改。(26)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8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391—394页。访美前夕,梅兰芳曾至上海,向胡适了解美国的风土人情、观众的喜好和习惯以及剧场的真实状况等。大至整个出访的演出策略,小至演出剧目的安排、角色的搭配等,胡适都积极为之出谋划策。胡适后来曾谈道:“他(梅兰芳)每晚很卖气力的唱两出戏,招待我们几个人去听,给他选戏。那时一连看了好多夜。”(27)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补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5年版,第417页。梅兰芳还多次致信胡适,希望他能够利用闲暇时间,将《太真外传》翻译成英文和日文。(28)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第488—489、490页。
为了支持和宣传梅兰芳访美演出,胡适专门写了一篇名为《梅兰芳和中国戏剧》的英文文章,收入华美协进社早期成员梅其驹(Ernest K.Moy,1895—1957)所编《梅兰芳太平洋沿岸演出》一书。在该文中,胡适一改新文化运动初期对中国旧剧的猛烈批判,持笔相当公允,间或有溢美之词,认为梅兰芳受过中国旧剧最彻底的训练,具有非凡的艺术才能,“连那些最严厉的、持非正统观的评论家也对这种艺术才能赞叹不已而心悦诚服”。(29)梅绍武:《父亲梅兰芳》上册,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82—183页。
1930年1月18日,梅兰芳从上海乘船赴美,胡适到码头为其送行。对胡适的鼎力相助,梅兰芳深为感激,赴美途中致信胡适:“在上海,许多事情蒙您指教,心上非常的感激的!濒行,又劳您亲自到船上来送,更加使我惭感俱深!……晓得您一定关怀,所以略此奉闻,并且谢谢您的厚意!”(30)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册,第488—489、490页。
综上所述,胡适在梅兰芳访美活动中所起作用巨大,无怪乎有学者称其为“梅兰芳接通西方主流文化的通行证”。(31)傅谨:《梅兰芳与新文化》,《文艺研究》2014年第5期,第92、96页。
三、助力汉学家的中华文化外译活动
胡适对中华文化外译的另一贡献是借助与海外汉学家的交游为他们的中华文化外译提供指导和帮助。
(一)胡适与韦利的《西游记》英译
英国汉学家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的《西游记》节译本《猴》是《西游记》影响最大的英译本,1942年由英国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至1965年已出至第七版;1943年又由庄台公司在美发行。(32)严苡丹:《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中国古典文学英译研究——以〈西游记〉韦利译本为例》,《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1期,第261页;葛桂录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的英国之旅》,大象出版社2017年版,第223—224页。1926年胡适赴欧参加会议期间结识韦利,此后两人保持了长期联系。在《西游记》的翻译和出版方面,韦利曾多次得到胡适的帮助。
韦利很早就注意到中国古典小说的版本问题,1941年曾致函胡适,表示自己正在以亚东版《西游记》为底本进行翻译,但是听说孙楷第在日本发现了一些明代版本,因此想请教明本与亚东版所据清本是否存在很大差异。(33)“1941年8月19日Arthur Waley致胡适函”,台北胡适纪念馆藏,馆藏号:HS-JDSHSE-0367-011。该信只给出了具体日期,并没有提供准确年份,但是根据现有资料推断,该信应作于1941年。韦利最终选择以亚东版为底本进行翻译,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该版本是在胡适指导下出版的,并附有胡适所作之序。(34)Arthur Waley trans.,Monkey,George Allen &Unwin Ltd,1942,p.10.
在翻译过程中,韦利还采纳了胡适的研究发现。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当时学界很有争议。为了说明这一问题,胡适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最终形成了《〈西游记〉考证》一文,收录于1924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胡适文存二集》。(35)竺洪波:《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112页。1926年访欧期间,胡适曾将《胡适文存二集》赠予韦利。韦利看起来毫不费力,几天之内就都看完了。(36)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4册,第569页。韦利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胡适的研究成果,接受了吴承恩为《西游记》作者的观点,并在译本序言中简要介绍了吴承恩的生平以及小说的演化历史等问题。
胡适对韦利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底本的选择和作者的考证上,更体现在故事情节的采摭和诠释上。韦利之前的《西游记》英译本多注重挖掘《西游记》的宗教内涵。比如,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在翻译过程中就以基督教教义比附佛教主张,用基督教甚至伊斯兰教的术语来置换儒释道三教的概念,其后的海耶斯(Helen M.Hayes,1906—1987)则注重将小说中有关宇宙生成的观念与基督教、伊斯兰教进行对比。(37)竺洪波、王新鑫:《域外汉学中的〈西游记〉叙述》,《文艺理论研究》2021年第1期,第22页。胡适不赞同对《西游记》的这种宗教解读,认为《西游记》并无“微言大义”,只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38)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册,第689页。韦利最终接受了胡适的游戏说,在译本中尽量淡化原作的宗教意味,删除了与“修心”有关的重要情节(如浮屠山玄奘受《心经》一事),不译宣扬佛教思想和渲染佛教法力的情节,剔除了与五行炼丹有关的内容。(39)吴晓芳:《中国古典小说英译研究的底本问题——以〈西游记〉为中心》,《中国比较文学》2021年第4期,第106页。
韦利《西游记》英译本在英出版之后,又由庄台公司(40)该公司以出版与中国有关的作品闻名,曾出版赛珍珠的《大地》及《水浒传》的英译本。在美发行,发行过程中也得到了胡适的大力帮助。1942年10月26日,庄台公司主席沃尔什(Richard J.Walsh,1886—1960)致信胡适,希望他能为韦利译本撰写介绍并提出一些修改意见。胡适不仅欣然应允为韦利译本撰写介绍,而且将其与中文版《西游记》进行比对,发现了译本中的一些错误,然后将介绍和修改意见一并寄给了沃尔什。在与韦利联系不便的情况下,沃尔什与赛珍珠(Pearl S.Buck,1892—1973)进行商议,采纳了胡适的部分建议,对译文进行了修改。(41)“胡适、Richard J.Walsh往来书信”,台北胡适纪念馆藏,馆藏号:HS-JDSHSE-0366-019、HS-JDSHSE-0366-020、HS-JDSHSE-0113-017、HS-JDSHSE-0366-022、HS-JDSHSE-0366-023、HS-JDSHSE-0366-024、HS-JDSHSE-0366-025、HS-JDSHSE-0366-026。在庄台公司的宣传打造和胡适的支持背书下,韦利所译之《西游记》在美国同样获得成功,庄台公司还趁势出版了据此译本改编、面向青少年的插图版《西游记》。
(二)胡适与词的翻译
1933年,英国约翰·默里公司出版了由坎德林(Clara M.Candlin,1883—?)翻译的《风信——宋代诗词歌谣选译》(以下简称《风信》)一书。该书出版之后广受好评,不仅多次重印,而且迅速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其所据底本正是由胡适编选、商务印书馆1927年发行的《词选》。(42)刘宏辉:《论胡适〈词选〉的海外传播》,《国际汉学》2021年第1期。
《风信》共选译了20位词人的作品,这些词人全部收录于胡适所编《词选》,包括向镐、朱敦儒等其他选本很少收录的词人。《风信》中词人的排列顺序,也与《词选》完全一致。64首译词中,除了误作陆游词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外,全部收录于《词选》。此外,《风信》一书的编排体例也与胡适《词选》相似,同一词人的词作前面均附有词人小传,这些小传也直接节译自《词选》。
胡适编选的《词选》代表了他对词史的见解,所选的词“大都是不用注解的”。(43)胡适选注:《词选》,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11—12页。而《风信》的选译情况大体上也能反映《词选》的选词标准。《词选》选录最多的是辛弃疾、朱敦儒和陆游的词,分别为46、30和21首。三位词人的词作同样为《风信》选译最多,分别为9、6、5首。(44)虽然《风信》名义上选译了陆游的6首词作,但是《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并非陆游所作,因此该书实际选译陆游词作5首。
胡适还专门为这本译著撰写了序言。在序文中,胡适首先称赞了坎德林的选译,认为“这本选集里收录的60余首词作都是词中的典范”,然后介绍了词的起源、词与诗的区别以及词的发展历史。(45)Shih Hu,“Foreword”,in Clara M.Candlin trans.,The Herald Wind:Translations of Sung Dynasty Poems,Lyrics and Songs,John Murray,1933,pp.27-29.这篇序言与胡适《〈词选〉序》大旨相同,但并非后者的直接英译,《〈风信〉序》主要面向英语读者,内容更加简单、浅显。
四、胡适中华文化外译活动的意义和启示
晚清以降,中国多次受到西方列强的欺凌,国人的文化自信遭到沉重打击,所谓“以吾数千年之旧文明当之(西方新文明),乃如败叶之遇疾风,无往而不败衄,于是睡狮之梦醒矣”。(46)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9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65页。在这一背景下,无数先进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复兴,于引进西学方面用力甚勤,而为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殚精竭虑者却寥寥可数。胡适的中华文化外译活动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显得更加珍贵,其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胡适的中华文化外译活动对其文学革命思想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胡适的文学革命思想并不是回国之后凭空产生的,而是他留美期间就开始苦苦探索的中国文艺复兴之路。留美七年是胡适“一生思想和志业的定型时期”(47)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7页。,在此期间的中英文转换活动使他认识到中文白话的可能性与生命力,其汉诗英译就是最好的证明。将汉语文言诗翻译成英语白话诗涉及两道翻译流程,首先是将汉语文言诗翻译成汉语白话诗的语内翻译,然后是将汉语白话诗翻译成英语白话诗的语际翻译。“将诗意表达为汉语的两种不同方式,先文言,后白话,是一种诗的语言的新感受;把整齐的五律转换为长短不一的白话诗句,更是一种诗体观念的冲击。”(48)李丹:《胡适:汉英诗互译、英语诗与白话诗的写作》,《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第92页。这一语内翻译过程正是一种白话诗的思维训练。此外,在将汉语白话诗转换为英语白话诗的语际翻译过程中,虽然也有韵律、音步等的限制,但是形式更加自由,句式可以长短不一,成为胡适后来构建汉语白话诗“诗体大解放”理论的一块基石。
其次,胡适的中华文化外译活动增加了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和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早在留美期间,胡适即开始有意识地通过演讲和写作等活动纠正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偏见。受邀担任驻美大使后,胡适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不可能仅由外交活动促成,因此对美外交的重点在于建立和增进中美之间的了解和信任,“使美国政府人民,明瞭我国待援情形及抗战决心”。(4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1页。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胡适开始了其跨越美加的演讲之旅。演讲中,胡适充分运用他对美国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和社会心理的了解,采取了符合美国听众接受习惯的表达形式。他的演讲让美国人民及时地、较为清楚地了解到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况和中国政府对于抗战问题的立场,认识到中国人民的持久抗战对于制止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战争,维护美国在中国和亚太地区的利益有着重要意义,从而援助中国的抗战。(50)朱文华:《胡适评传》,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273页。胡适在美国的演讲和活动还引起了日本政府的警觉。“日本有人提议,为抵消胡适在美国的影响,日本应派三位干员到美国去。”(51)耿云志:《胡适与抗战》,《安徽史学》1989年第1期,第60页。当时杨鸿烈也从日本写信给胡适说,“在日本人眼中,先生是他们的‘侵略主义’的大对头”,“先生在美的一言一动,日本的报纸都详为揭载”,“或以为先生们善于为有组织的宣传……故使美国排日的空气甚为浓厚”。(5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75—376页。
除了争取美国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以外,胡适中华文化外译活动的更大意义在于促进了中华文化在不利形势下的对外传播。近代以来,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原因,国人的文化自信遭到了沉重打击。为了解决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纷纷负笈海外,学习、接受、引进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在这一背景下,为中学西传殚精竭虑者却寥寥可数。民国时期在中学西传方面,胡适可谓有先开风气之功。他充分利用自己学者和外交官的双重身份,在欧美大学、学会和科研机构竭力宣传中国文化。同时与海外汉学家展开平等交流,为他们的汉学研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并对他们的研究成果提出批评和指正。海外汉学家因为与其所在国家的读者处于同一文化体系中,更了解本国人民的需求,在中学西传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胡适通过为这些文化传播者提供帮助,推动了中华文化在西方的广泛传播。
那么胡适为什么能够实现中华文化在不利形势下的对外传播呢?他的中华文化外译为何能在西方世界获得成功呢?弄清楚这一问题无疑对当前的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熟稔中英两种语言文化的学者习惯

除了研读古书,胡适在上海读书之时,即开始“专读英文算学”(55)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册,第211、44—52、66页。,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留美之后,胡适没有放松自己的语言训练,“数月以来之光阴大半耗于英文”(56)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1册,第148页。,并通过英文演讲提升自己的表达能力,到美国仅三年就已演说70余次。(57)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3册,第78页。留学归国后,胡适在用中文著述的同时坚持用英文写作和演讲,这种训练使他养成了熟悉英语语言文化的学者习惯。罗素曾指出,胡适对西方哲学的精熟好像是一个欧洲人,英文写作之佳则和多数美国教授没有分别。(58)Bertrand Russell,“Early Chinese Philosophy”,p.778.林语堂也称赞胡适写的英文比他的中文还漂亮。(59)林语堂:《胡适之》,新绿文学社编:《名家传记》,文艺书局1934年版,第211页。熟练掌握中英两种语言文化是准确翻译中华文化的必要条件。在当今时代想要找到一个像胡适那样熟练掌握中英两种语言文化的学者也许并不容易,我们可以采取合作翻译模式,将熟练掌握中英两种语言文化的学者(而非仅仅熟练掌握中英两种语言)共同纳入到翻译模式中来,在保证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用英文进行准确表达。
(二)顺应目标语读者阅读需要的翻译策略
胡适在用英文进行写作和翻译时有着明确的读者意识。韦利曾指出,胡适非常了解西方人,知道他们需要什么。(60)Arthur Waley,“Arthur Waley Writes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Hu Shih’s Genius”,The China Press,1927-10-02,pp.3-4.李又宁也指出,同为胡适自传的中文《四十自述》和英语《口述自传》也因读者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前者“只写到胡适1917年回国,是为中国读者写的”,后者的读者是“美国大学中国研究的学生。《口述自传》涵盖了胡适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学术生活,强调了胡适的学术训练、研究方法和学术写作”。(61)转引自郑澈:《中国学者走出去的策略——以胡适英语著作发表为例》,《中外文化与文论》2016年第3期,第372页。可见,胡适写作时是有着清晰的读者意识的,针对不同读者采取不同的写作策略,从而使自己的著述产生最佳的传播效果。明确的读者意识同样体现在胡适的中华文化外译活动中。比如,在梅兰芳访美活动中,胡适向其介绍了美国的风土人情、观众的喜好和习惯以及剧场的真实状况等,并在出访的演出策略、演出剧目的安排、角色的搭配等方面提出了建议。前美国文学翻译家协会主席、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高级翻译学院教授陶忘机(John Balcom,1956— )认为,在将中国文化翻译成英文的过程中,根据读者的需要和期待对原文做出一定程度的改写是非常必要的。(62)John Balcom,“Translating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in Susan Bassnett &Peter Bush eds.,The Translator as Writer,Continuum,2006,p.128.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持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中国文化不仅要走出去,更要走进去、走下去。如何走进去、走下去,了解目标语读者的阅读需要正是一条重要途径。
(三)借由学术交游形成的人际网络
胡适能够成为民国时期中华文化外译有力推手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他与国际汉学界频密的学术交往。(63)参见桑兵:《胡适与国际汉学界》,《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他与国际汉学界的这种密切关系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助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国际汉学界在翻译中华文化时愿意接受胡适的批评指正、指导帮助。1914年8月2日,胡适偶然读了《皇家亚洲学会杂志》所刊英国汉学家翟林奈(Lionel Giles,1875—1958)的《敦煌录译释》一文,发现翟氏的译释“讹谬无数”,于是摘其谬误,作一校勘记寄去。(64)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1册,第431—432页。1915年2月11日,他收到皇家亚洲学会书记寄赠的杂志若干份,知道翟林奈已自认其误,并重新译过。(65)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2册,第38页。其次,胡适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翻译比较容易得到国外学者的接受。1922年6月28日,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为文友讲解《易经》的哲学,大旨用的就是胡适的解释。(66)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3册,第650页。罗素也对胡适翻译的中国古代哲学赞赏有加,认为他的翻译精确可靠。(67)Bertrand Russell,“Early Chinese Philosophy”,p.778.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由国内学者发起的文化外译活动难免会因为不了解国外需求而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而海外汉学家因为与其所在国家的读者处于同一文化体系中,更了解本国人民的需求,在中学西传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加强与他们的合作可以有效避免水土不服情况的发生。
结 语
民国时期,各种西方思潮疯狂涌入中国,但是这股热潮的背后也潜藏着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涓涓细流。在民国时期中华文化的对外翻译方面,胡适有先开风气之功。遗憾的是,他的这种努力往往被其介绍西学方面的光芒所掩盖。本文利用胡适档案、日记、书信等材料从三个方面梳理了胡适与民国时期中华文化外译活动之关系。胡适的中华文化外译活动发生在西学势强、中学势弱的历史背景下,因而更加难能可贵,在胡适文学革命思想的形成以及增进西方国家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希望能够呈现一个更加完整的胡适,同时为当前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