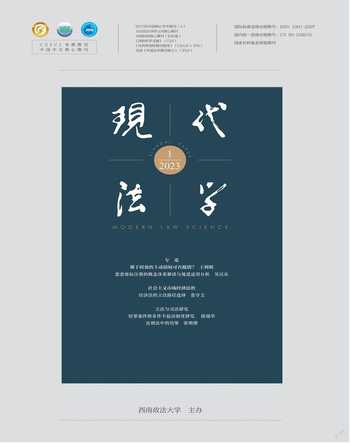经济法的立法路径选择

摘要:在法治建设的新时期,经济法的立法路径如何选择,事关整体法治的完善和发展。经济法的立法路径可分为两类,即集中立法路径(包括法典化路径和统合立法路径)和分散立法路径(包括分领域、分行业的单行立法路径),两类路径皆有其必要性、合理性和局限性。基于我国经济法立法的需要与可能,目前应兼顾各类路径的优势,将统合立法与单行立法有机结合,从而形成相互协调的多元立法路径。为此,既要基于各具体领域、行业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加强个别立法或单行立法,又要推进统合立法,不断提升立法层级,增强立法的协调性和系统性,从而持续提高整体经济法立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其多元调整目标。经济法的立法路径选择,不仅涉及经济法的立法理论、法治理论或运行理论,也与经济法的本体论、价值论、规范论、范畴论等密切相关,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为经济法立法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并推进经济法学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经济法;立法路径;法典化;统合立法;分散立法
中图分类号:DF41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23.01.09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迅猛发展,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已进入新阶段。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需要着力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由此,对经济法立法提出了更高要求。近年来,在多个部门法领域盛倡法典化的背景下①
,基于经济法对国家治理和整体现代化的重要影响,如何选择经济法的立法路径,已成为广受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
法律和法律秩序是实现“发展”“转型”和“善治”变革的重要因素。参见[美]安·赛德曼、罗伯特·鲍勃·赛德曼、那林·阿比斯卡:《立法学理论与实践》,刘国福、曹培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经济法作为发展促进法,对于实现上述“发展”“转型”和“善治”等目标尤为重要,这也是国家立法机关大力推进经济法立法的重要原因。
经济法对于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具有特殊功用,对其立法路径如何选择,不仅事关我国立法体系的重构和完善,影响经济法执法和司法活动的走向,还会涉及国家与国民、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等多种重要关系的调整。同时,经济法的立法对于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尤为重要,直接影响国家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参见张守文:《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经济法补缺》,载《现代法学》2018年第6期,第54-63页。因此,对其立法路径的选择不可不察。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形式意義上的经济法立法体系日臻完善。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属于经济法的法律已有80余部,立法数量在七大部门法中位居第二位。
由于经济立法具有综合性和复杂性特征,在一部法律中往往涉及多种部门法规范,对相关法律的部门法归属有时难以截然划分。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中,如果依据严格的经济法理论,可能还存在本应属于经济法的法律被归入民商法或行政法的情况。即使如此,也并不影响对“经济法立法数量较多”的判断。如此众多的单行立法表明,经济法调整的具体领域存在较大特殊性、差异性,由此使经济法在立法路径上有别于传统民法、刑法等部门法。
与上述形式意义上的立法体系相对应,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法体系包含了大量经济法规范,这与各类主体经济活动的广泛性、复杂性以及经济法调整的必要性、回应性直接相关,使经济法的立法层出不穷,且不断推陈出新。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经济法立法路径是否合理,应当如何改进,涉及的法治问题及其背后的规律等,都需要进一步总结和提炼。
目前,受到普遍关注的经济法立法路径,可大略分为两大类,即集中立法路径和分散立法路径。前者包括高度集中的立法路径(法典化的路径)和适度集中的立法路径(统合立法的路径);后者包括分领域立法的路径和分行业立法的路径,强调应基于各领域、各行业的特殊性,推出单行立法,从而更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上述立法路径均有其存在理据,需要梳理和辨析其利弊得失,据此作出研判和选择。
面对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对经济法治建设提出的诸多新要求,基于经济法领域既有立法的大量积累,以及立法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问题,应结合新时期经济法立法的时代使命和未来发展,对经济法的立法路径作出理性选择,以回应科技革命、经济发展、法治建设等需要,并明确经济法立法未来的发展方向。
鉴于此,本文拟着重探讨经济法的立法路径选择问题,通过对集中立法路径与分散立法路径的梳理辨析,探讨依循各类路径进行经济法立法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局限性,并由此提出应结合现实需要与可能,将统合立法的路径与分领域、分行业的单行立法路径结合起来,从而确立相互协调的多元立法路径。本文试图说明,鉴于经济法立法范围广阔、规范对象复杂多变,不宜仅选取单一立法路径;只有确立相互协调的多元立法路径,才能有效回应现实经济社会发展对法治建设的多方面需要,并由此深化经济法的立法理论、法治理论或整体运行理论研究,从而为经济法的各类立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二、集中立法的路径
集中立法的路径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法典化路径,一类是统合立法的路径。对于究竟应按照前一类路径,一步到位制定或编纂法典,还是按照后一类路径,通过持续的统合立法不断实现立法优化,确实需要审慎选择
经济法统合性立法应规避法典化的封闭性与滞后性,吸收分散立法的实践导向和回应性功能,努力寻求一种渐进式、开放式的经济法立法体系化路径。参见刘凯:《法典化背景下的经济法统合性立法》,载《法学》2020年第7期,第100-112页。,这其实也是科学立法的重要要求,会直接影响立法的科学性、合理性。
事实上,对法典的形式与功能、法典化的具体路径等,人们尚存在诸多不同理解。通常,狭义的法典化路径,是将制定或编纂法典作为直接目标。
经济法学界对此已有较多研讨,参见程信和:《经济法通则原论》,载《地方立法研究》2019年第4期,第54-129页。统合立法的路径,则强调制定或编纂法典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只有持续推进不同层次的统合立法,才能为法典的制定或编纂奠定基础。因此,如果将统合立法作为法典化的一个阶段
经济法法典化中的“立法整合”,需要在内外两个层面展开。“立法整合”不仅是经济法法典化的基本路径,还是经济法面对“法的整合时代”的有效回应。参见焦海涛:《经济法法典化:从“综合法”走向“整合法”》,载《学术界》2020年第6期,第54-67页。,则两类立法路径都可能被归入广义的法典化路径。
“法典化是一个宽泛的术语”,因而往往会存在很多争议,“法典化的主要目的是在它所指涉的法律领域创造一份独特的文件”“提供一个反映该领域规制之全貌的文本”。参见[英]赞塔基:《立法起草:规制规则的艺术与技术》,姜孝贤译,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第308-309页。考虑到现实的立法需要与可能,下面将着重从狭义角度讨论法典化路径,并将其与统合立法的路径相区别。
(一)法典化路径
从我国民法典的立法历程看,在大量既有立法的基础上编纂法典,而并非追求从无到有地直接制定法典,是我国推进法典化的基本路径。对此,有必要从整体立法发展的视角,审视法典编纂的相关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长期将立法活动分为法律的“立改废”三大方面,近年来又强调“立改废释纂”五个方面,体现了立法内容和立法方式的发展。但无论如何发展,法律的“立改废”始终处于基础地位。例如,在“立”的方面,我国一直重视经济法领域重要法律的创制,归属于经济法部门的法律数量持续增长。在“改”的方面,鉴于经济法各主要领域的法律已相继出台,结合现实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及时修改既有立法,已成为经济法立法的重要方向。尤其是2013年以来,结合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国家力推简政放权、减税降费、优化营商环境等,对相关经济立法已作大范围修改。
例如,2018年10月26日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十五部法律的决定》、2018年12月29日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等四部法律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五部法律的决定》、2019年4月23日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等八部法律的决定》等,都涉及经济法领域大量法律的修改。在“废”的方面,我国重视对不合时宜的规章、行政法规甚至法律的废止或清理例如,在经济法领域,行政法规是重要的法律渊源,因此,国务院对行政法规的废止或清理尤为重要。参见2020年至2022年期间国务院多次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其中涉及大量经济法领域的行政法规。,不断吐故纳新、推陈出新,使相关立法能更好地回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要,从而有效解决各类新问题。
在持续强化法律“立改废”的同时,依据2014年作出的“法治决定”
即2014年10月23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法律解释进一步受到重视,由此提升了“释”在立法活动中的地位。由于多年来国家立法机关的立法解释相对较少,而国家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大幅增加,因此,如何构建合理的法律解释体系,有效配置相关解释权,已成为需要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
上述法律“立改废”的持续推进,以及一定数量法律解释的积累,为法典编纂创造了重要条件。但是否要编纂法典,是重要的立法路径选择问题;同时,是否要在各部门法领域全面进行法典编纂,更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随着《民法典》编纂的完成,行政法、环境法等领域也开启了法典编纂的准备工作,有人由此认为我国的法制建设已进入“法典化时代”。但对于经济法立法是否应采行法典化路径,一直存在不同认识,对此,至少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法典化路径并非各国的普遍选择。近代以降,各国对于应否以及如何推进法典化,始终未能形成共识。例如,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大陆法系国家,曾在法典化方面表现突出,先后制定了民法典、商法典等,但在立法过程中亦曾有大量争论,特别是萨维尼等学者的观点至今仍令人深思。
“立法者在变更现有法律时,或会受到强有力的国家理性的影响”,这在是否实行法典化路径方面体现得更为突出。参见[德]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如果说对于较为成熟的民法等领域的法典化尚且有大量不同认识,那么,在其他立法领域应否制定或编纂法典,更会存在诸多意见分歧。因此,在作为现代法的经济法领域,对于应否制定经济法典存在不同声音,可谓非常正常,更何况对于在21世纪是否仍要制定或编纂法典,本来就存在较多争论。
第二,经济法的法典化缺少可借鉴的资源。从法制发展史看,在经济法领域,世界各国几乎都没有专门的法典,只有捷克斯洛伐克(现已分为两个国家)曾于1964年制定过经济法典,但其内容早已不适合今天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1964年,捷克斯洛伐克曾在计划经济时期制定过经济法典。参见《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法典》,江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同一时期的苏联也曾着手起草经济法典,但最终未能出台。
1969年,苏联科学院曾委托经济法学者起草《苏联经济法典》(草案);1985年,以拉普捷夫为首的委员会完成了《苏联经济法典》(草案)的起草工作,但最终未能提交立法機关审议。参见何勤华:《20世纪外国经济法的前沿》,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84-593页。在经济法产生较早的德国等欧陆国家,虽然有制定法典的传统,但也未曾制定经济法典,其背后的原因和立法规律尤其值得深入探究。
各国经济立法的历史表明,制定或编纂经济法典基本没有可借鉴的国际经验,只能从我国实际出发,结合立法现状和立法理论,特别是相关经济法理论来展开制度设计。
早在1979年就有人提出,条件成熟时应制定一部较为完备的经济法典。参见齐珊:《经济法是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法律部门》,载《法学研究》1979年第4期,第15-16页。但那时经济法理论研讨刚刚开始,还不能支撑经济法典的制定。与民法基本规则较为统一、便于借鉴国外立法资源不同,在经济法领域,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经济生活复杂多变,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政策性、国别性、差异性突出,经济法的立法必须依据本国实情,而无法简单借鉴或平移国外立法经验和制度。由于制定或编纂经济法典缺少可借鉴的资源,我国是否要“独树一帜”地编纂经济法典,其理论准备和立法准备是否充分,现实需要是否迫切,国家立法机关是否有意愿推动等,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三,不能将成文法与法典、法典化完全等同。经济法是经济宪法的具体化,其调整将直接影响国民的基本权利,因而在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方面都要遵循相应的法定原则。基于法定原则在经济法领域的特殊重要性,各国都重视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法立法。即使是英美等判例法国家,也同样存在大量经济法方面的制定法或成文法,某些领域的法律编纂甚至在形式上使用了“法典”的名称,如美国《国内收入法典》等。因此,有必要对成文法、法典和法典化加以区分。其中,基于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需要,各国在经济法领域制定了大量法律,如作为经济法立法先驱的美国《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都是相关国家的国会、议会通过的成文法;法典则是成文法的高级形式,有大量成文法并不代表就可以制定或编纂法典;法典化既然是一种“化”,它体现的只是制定或编纂法典的一种动态趋势,并不等于即刻就要制定或编纂法典。因此,立法路径的选择应实事求是,力求与时俱进地有效解决现实问题,切实发挥法律的重要作用,而不能单纯考虑立法工程是否浩大或法律形式是否完美
有学者认为,法典化涉及大规模的起草,“即使是交错式法典化进路也存在许多方法上、实质上和实践上的障碍”。参见[英]赞塔基:《立法起草:规制规则的艺术与技术》,姜孝贤译,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第310-311页。,相应地,也不应将法典化路径绝对地理解为立法路径的必然选择。
从法治实践看,各国都重视在经济法领域制定成文法律,但又普遍没有采取单一的法典形式。当然,这并不排除随着各国法治发展到一定阶段,可能出现法典化的趋势。即使如此,各国也不会都走法典化的道路,因为在历史更悠久、国际共通性较高、相对更成熟的民商法领域,各国也并未都制定或编纂民法典或商法典。事实上,法典形式具有规范明确、稳定性高的优点,但其立法成本高,修法程序复杂,开放性、灵活性不足,往往难以及时回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经济法恰恰需要在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方面及时作出回应,其对政策性、开放性、灵活性有更高的要求。法典形式的上述局限会影响经济法的法典化路径选择。
第四,对法典形式的理解具有多样性。如何理解法典形式,会影响人们
对法典化路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判断。例如,在刑法领域,对于是否要仿照民法典编纂刑法典,就存在不同看法。有些学者认为,我国的《刑法》实质上就是刑法典
有学者认为,根据法典的基本特征,1979年通过、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均为刑法典,我国刑法已经法典化。参见张明楷:《刑法修正案与刑法法典化》,载《政法论坛》2021年第4期,第3-17页。,它不仅具有法典的基本结构和功能,还保持了开放性,这种开放的法典形式有助于及时解决现实问题。特别是近年来,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的发展导致新型犯罪形式不断增加,相关经济领域的犯罪更为突出,而通过刑法修正案的形式不断扩充刑法规范,有助于及时回应现实问题。同样,经济法作为回应型法,更要及时回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尤其是数字经济发展,带来了平台垄断、信息安全、数據治理等方面的大量问题,需要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诸多方面的立法回应。鉴于保持开放性、回应性对于经济法立法更为重要,不宜采取封闭式的经济法典形式。
第五,经济法典的制定或编纂存在诸多困难。由于经济法调整的领域差异较大,在主体角色、行为类型、权义分配、责任归结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经济法典的制定或编纂难度更大。仅以责任制度为例,在《民法典》中可以统一规定民事责任的十一种类型,并普遍适用于各类民事主体,但经济法的各类主体在地位、能力、行为类型、权义结构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不可能适用统一的无差别的责任形式。
参见张守文:《经济法新型责任形态的理论拓掘》,载《法商研究》2022年第3期,第3-15页。因此,经济法的具体立法大都规定了多种责任形式,如将其分门别类统一规定于法典中会非常困难,即使大量列举也难以穷尽。
“明智的起草者应该缩小法案的调整范围,而不是将很多主题硬塞进一个法案。”参见[美]安·赛德曼、罗伯特·鲍勃·赛德曼、那林·阿比斯卡:《立法学理论与实践》,刘国福、曹培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第124页。可见,与传统法领域的法典编纂相比,经济法典的编纂难度要大得多,对于法学理论和立法技术都是极大的考验。
总之,法典是法制建设和法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高级立法形式,不同立法领域的法典化程度会有所不同,因此,对其是否采行法典化路径不能一概而论,应综合考虑各部门法的特点,结合需要与可能,决定是否可以或应当走法典化道路,而不应强调“诸法一律”。对于经济法的法典化问题,许多学者曾进行过不懈探索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不同时期都有学者探讨过《经济法纲要》《经济法通则》《经济法典》《经济基本法》等形式。参见杨紫烜:《关于制定〈经济法纲要〉的若干问题》,载《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4期,第15-18页;李昌麒:《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经济法〉的几个问题》,载《当代法学》1991年第4期,第28-32页。,并提出了许多具体设想
参见程信和、曾晓昀:《经济法典:经济法集成化之历史大势》,载《政法学刊》2021年第1期,第92-101页;李建华:《略论经济法立法的模式和体例结构》,载《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第57-61页。,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但受上述诸多因素影响,采行法典化路径还确实存在较大困难。只有在未来经济法的法学理论研究和相关制度建设达到相当高度,以及其他各类立法条件都具备时,制定或编纂经济法典才更具有可行性。
(二)统合立法的路径
针对法典化路径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需要考虑采行统合立法路径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参见张守文:《经济法的立法统合:前提与准备》,载《学术界》2020年第6期,第46-53页。作为分阶段、分目标的“相对集中立法”路径,统合立法路径有助于弥补法典化路径的一些不足,并能够较为及时地回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经济法的统合立法,是在大量经济立法的基础上,对相关经济法规范的统一和整合。它不以一步到位地制定或编纂法典为目标,而是强调通过法律“立改废”的持续螺旋式升级,辅之以必要的法律解释和法律编纂,不断优化相关立法的结构与功能,提升立法的层级,从而实现更高层次的统合目标。因此,“立改废释纂”都会影响统合立法,有必要从这五个方面审视其中的相关问题,并揭示统合立法的重点。
从“立”的角度看,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针对经济法立法的严重不足,为了确保有法可依,体现立法“有胜于无”的精神,推进“立新法”便成为经济法立法的重要选择。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经济法领域的许多基本法律均已出炉,使“立新法”的压力大大减轻。当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一些新兴领域仍需制定新法律。例如,近年来针对信息化、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立法机关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领域,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并将其归入经济法部门。从总体上说,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要,不断制定新法律仍是经济法立法的长期任务。
从“改”与“废”的角度看,在“立新法”压力大幅减轻后,需要將立法的重点转向修改既有法律,并及时废止不合时宜的法律。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的背景下,随着财税、金融、市场监管等诸多领域改革的推进,特别是“放管服”改革以及其他配套改革的不断深化,近些年经济法领域的大量法律已被修改;同时,平台经济或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大量新问题,也需要通过对《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相关法律的修改来回应和解决。此外,一些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被废止,并且,越是低层次的立法,因不合时宜、阻碍发展而被废止的可能性越大。例如,随着“营改增”试点改革的完成,我国于2016年废止了实施多年的《营业税暂行条例》
参见2017年10月30日通过的《国务院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和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的决定》。,这与2006年《农业税条例》因农业税制度改革而被废止是一样的,只不过《农业税条例》的制定主体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其立法层级更高。
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农业税条例》于2006年6月1日被废止。在取消营业税后,增值税的转型需要在形式上提升立法层级,同时,还应按照增值税原理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相关具体制度,特别是纳税人的抵扣权制度。
参见张守文:《增值税的“转型”与立法改进》,载《税务研究》2009年第8期,第59-64页。
从“释”的角度看,法律的修改和废止侧重于对既有立法的局部或全部予以否定,而法律解释则侧重于从肯定的角度对既有立法予以具体化、明晰化,以保障法律的有效实施。事实上,在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立法中,许多制度规定都较为原则,加强其法律解释工作更有助于解决具体问题。基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改革开放之初作出的决议
参见1981年6月10日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我国的法律解释主要分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等,但对立法解释的认识存在一定争议
有研究者认为,法律解释权天然属于执法机关(包括司法机关)。参见陈斯喜:《论立法解释制度的是与非及其他》,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3期,第63-70页。,其应用极少,远不如法律的“立改废”那么常态化。
例如,税收立法方面的许多规定都较为原则。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等多部税收法律都仅有20余条,《烟叶税法》甚至仅有10条,目前主要是通过国务院制定实施条例的形式加以具体化。此外,国务院过去主导制定的多个税收暂行条例,大都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作细化解释。随着税收法定原则的落实,对税收法律的立法解释更为重要,只是目前还较为滞后。又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具体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的规定仍难以回应实践发展的需要,其中的“互联网专条”无法全面涵盖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为此,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作出了相应的司法解释。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2〕9号)。对于此类情况,究竟应推进立法修改还是立法解释,也是经济法立法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如果在广义上理解立法解释,则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等作为立法主体,都可以享有解释权
参见蔡定剑、刘星红:《论立法解释》,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6期,第36-43页。,其及时作出的立法解释事关经济社会发展,会影响经济法的执法和司法效果,对于确保立法的开放性、及时性,以及促进法律的全面实施尤为重要。因此,应在立法解释方面形成基本共识,并不断提升立法主体的解释能力,从而有效解决立法解释与行政解释、司法解释的不协调问题。
关于司法解释“泛立法化”趋势的讨论,参见袁明圣:《司法解释“立法化”现象探微》,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2期,第3-12页。
从“纂”的角度看,经济法的法律编纂,应建立在上述“立改废释”等立法活动基础之上。通过相关法律的制定,以及法律的持续修改和废止,并辅之以适当的法律解释,才能为相关法律编纂提供前提和基础。如果缺少统合立法,或者立法积累不足,就难以编纂经济法典。只有通过统合立法进行必要的法律编纂,才可能进一步推动经济法的法典化。这也表明推进法典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在短时期内,制定经济法典存在诸多困难,更为现实的立法选择,是结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以既有立法为基础进行统合立法,分门别类地不断提升立法层级和立法质量,使整体经济法作为一个系统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为此,在经济法的各个具体部门法领域,可以先分别进行不同层次的统合立法,并根据需要与可能,进行更高层次的立法。从规模与效益的角度看,制定超大规模的法典未必有效,而通过有效的立法统合,逐步形成各成体系的“法律规范群”,既有助于各类规范之间相互衔接,又能实现制度的开放发展,既能及时回应现实的发展要求,又有助于法律适用和遵从,因而相对于法典编纂,统合立法是更为适当、可行的立法路径。
参见张守文:《经济法的立法统合:需要与可能》,载《现代法学》2016年第3期,第62-70页。
通过上述“立改废释纂”持续推动统合立法,有助于避免重复立法,防止相关立法存在交叉、重叠或冲突等问题,增强立法的协调性、同一性和系统性。作为集中立法的一种路径,统合立法的目标是解决现实立法中存在的不协调等问题,使相关主体形成更为清晰明确的预期,从而提升其法律遵从度,降低其合规风险或法律风险,实现相关领域的良法善治。
通过提升立法质量构建良法,进而实现善治,是法治建设的重要方向。在促进社会发展和善治方面,法律制度特别是立法质量尤其重要。参见[美]安·赛德曼、罗伯特·鲍勃·赛德曼、那林·阿比斯卡:《立法学理论与实践》,刘国福、曹培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第5-10頁。
统合立法的重点是“三分”,即分阶段、分层级、分领域。在分阶段方面,各类法律制度的发展阶段或成熟度不同,对其进行统合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也不同,因而应明确相关立法的发展阶段。在分层级方面,统合立法是相关法律规范自下而上的统一和整合,因而应结合立法层级较低导致的相关问题,提升立法层级和法律效力。在分领域方面,统合立法并非在经济法所有领域一并推进,而是要基于每个领域的具体情况,决定其统合立法的具体路径和进度安排,因此,不宜在经济法的各个子部门法领域搞“一刀切”式的统合。
上述的“三分”表明,统合立法具有渐进性,是不断回应实践发展需要的立法完善过程。例如,随着各类税收暂行条例陆续上升为法律,在税法领域会形成近20部法律,但分税种立法可能导致
某些制度(如征收程序制度)存在重复立法现象,或者对相关基本制度(如有关税收征管体制的制度)的规定不足,因而需要通过推进统合立法加以解决。此外,在各类税种法律全部出台后,还可考虑制定能够整合各类税法共性制度的《税法总则》,这是税法领域推进统合立法的重要目标。
参见施正文:《税法总则立法的基本问题探讨——兼论〈税法典〉编纂》,载《税务研究》2021年第2期,第94-103页。
又如,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迅速,大量经济活动都涉及市场交易和价格问题,为规范市场交易和市场竞争行为,我国有40多部法律专门规定了价格条款或价格制度,需要结合这些价格制度的共性问题进行统合立法,因而应及时修订《价格法》,并确立其价格“基本法”地位。
参见张守文:《〈价格法〉修订:发展需要与改进方向》,载《法学杂志》2022年第4期,第1-15页。此外,在金融风险防控、金融监管等领域,也存在诸多共性问题,可在既有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以及其他金融立法的基础上,整合制定《金融稳定法》《金融监管法》等。
可见,上述分阶段、分层级、分领域的统合立法,比直接制定或编纂经济法典更为灵活,也更能体现每个领域的特殊性,从而有助于及时回应相关经济、社会和法律发展的具体需要。随着整体经济法的统合立法不断推进,还可考虑制定《经济法总则》。《经济法总则》作为更高层级的立法形式,能够对经济法领域各类分散立法中的共性问题统一加以规定,这在立法技术上也具有可行性。由此会形成有分有合、统分结合的立法架构,即“基本法+单行法”的立法体系。在《经济法总则》的统领下,既能保持各类经济法制度的独立性,又能增进其协调性,从而有助于发挥经济法体系的整体功用。
制定一部沟通宪法与单行法的经济法总则或者总则性的经济基本法,是回应目前法典化之不能与立法统合现实需要之间矛盾的实用主义路径。参见刘凯:《论制定经济基本法的路径选择》,载《法学杂志》2021年第8期,第82-94页。
总之,在推进统合立法的过程中,需要不断立、改、释、废、纂,通过分阶段、分层级、分领域的立法,不断提升立法的协调性和系统性。当然,在统合立法实践中,对于立法的具体领域、层次,需要具体分析,尤其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回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和法治建设的迫切需要,从而不断提升立法质量和效益,并通过推动经济法立法的高质量发展,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三、分散立法的路径
在梳理辨析上述备受关注的集中立法路径的同时,还要关注分散立法的路径。经济法的分散立法,主要体现为分领域、分行业的单行立法或个别立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为履行经济职能,需要建立统一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制度,在多个领域、行业进行分散立法非常重要。因此,这里的分散立法不是指立法主体的立法权分配意义上的分散立法(如地方分散立法)
在立法主体或立法权方面,涉及统一立法与分散立法的问题,需要完善相关立法体制。参见谢怀栻:《是统一立法还是地方分散立法》,载《中国法学》1993年第5期,第26-27页。,而是指立法方式、范围、对象方面的分散立法。
上述的分领域,涉及国家有关职能部门主管的一些重要领域,主要指宏观调控领域和市场规制领域,具体包括财政领域、金融领域、市场监管领域等。上述的分行业,主要是事关国计民生,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行业,正是基于这些行业的特殊性、重要性,需要经济法的特别规制,才需要专门的经济法立法。与前述法典化路径与统合立法路径不同,两类分散立法的路径更关注具体领域、具体行业分散展开的单独立法。
(一)分领域的分散立法路径
分领域的分散立法,具体涉及国家履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职能的各类领域,如财政领域、税收领域、金融领域、计划(发展规划)领域、市场监管领域等,这些领域既涉及国家立法关注的“重点领域”,又涉及“新兴领域”和“涉外领域”。上述各领域的立法会分别形成财税法、金融法、计划法、竞争法、消费者保护法等经济法的子部门法,每个子部门法都包含多种具体法律。从既往立法实践看,国家立法机关主要按照分领域立法的思路来推进经济法立法。
分领域的分散立法,与理论上的经济法体系最为契合,它能够及时回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因而历来是经济法立法关注的重点。同时,这些立法与各领域的经济政策相对应,体现了经济政策与经济法之间的紧密关联。因此,在具体立法过程中,需要分别关注财政政策与财政法、税收政策与税法、金融政策与金融法、产业政策与产业法、竞争政策与竞争法、消费者政策与消费者保护法之间的对应性和协调性。
例如,竞争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性及其相关法治保障已引起广泛关注。参见黄勇:《论我国竞争政策法治保障的体系及其实现机制》,载《清华法学》2022年第4期,第28-42页。另外,上述分领域的立法都有专门的执法机构,主要是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或规制机构,从而使立法更有依托,执法更有保障。上述方面都是经济法立法与民事立法、刑事立法重要的不同之处,体现了经济法作为现代法与传统法的重要区别。
参见张守文:《论经济法的现代性》,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第56-64页。
经济法立法的专业性强,依托相关政府部门或规制机构推进立法往往更有保障,但也存在着部门利益可能影响立法的问题,需要在全国人大、国务院层面进行立法协调,以保障相关部门之间的权力配置、利益分配等服从国家法治建设的总体目标,服务于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现实需要,从而不断提升立法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使相关立法更为稳妥可行并充分发挥其作用。
目前,上述领域的分散立法发展并不平衡。自1993年《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在1993年至1995年,分别进行市场规制、财税、金融三大领域的立法,逐渐形成了经济法立法体系“三足鼎立”的格局,而其他领域的立法则相对不足,如在计划或发展规划领域尚未制定基本法律,亟待在未来弥补立法空白,以解决分散立法的发展不平衡问题。
在上述鼎立的“三足”中,金融法领域的主要法律都已出台(目前正在制定金融稳定法),且大都被多次修改,相对最为完备。虽然市场规制领域在1993年就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重要法律,但《反垄断法》迟至2008年才正式实施。通过近年来“两反一保”等多部重要法律的修改,市场规制法的完备程度已大幅提高。与上述“两足”相比,财税立法虽起步最早,甚至在改革开放之初,诸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等涉外税收立法可谓开经济立法之先河,但国内税收立法进展缓慢,经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两次授权立法,形成了主要以国务院制定税收行政法规为基本立法形式的格局。直至国家1994年制定《预算法》并实施一系列税收法律法规,我国的财税立法才开启了与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匹配的发展阶段。随着近年来对税收法定原则的落实,我国的多数税种已制定相应的税收法律,但仍有几部重要税收法律尚未出台
这些税收立法的征税理据、税种定性、改制幅度和逻辑结构尤为重要,它们不仅影响立法的必要性、合理性,而且影响立法思路、制度协调、立法的类型化以及制度的内在一致性。参见张守文:《税收立法要素探析——以印花税立法为例》,载《政治与法律》2022年第5期,第2-13页。;同时,国债法、转移支付法的立法仍未受到足够重视。
由于各个领域的立法发展阶段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各异,因此,在较为成熟的立法领域,应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着重修改法律,推进法律的完善;在某些立法相对滞后的领域,仍应将制定新的法律作为重点,以解决有法可依的问题。例如,在财政立法方面,仅在《预算法》中对国债制度、转移支付制度作出原则性规定是不够的,还应加快制定国债法、转移支付法;在税收立法方面,应尽快完成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等重要税种领域的立法。鉴于是否开征房地产税争议较大,且立法时机尚未成熟,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立法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已作出授权国务院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的决定,因而其立法肯定会延后更长时间。
依据2021年10月23日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该决定授权的试点期限为五年,自国务院试点办法印发之日起算。这意味着将全部税收暂行条例上升为法律的目标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
与前述的集中立法路径相比,分散立法路径的局限性是相关立法的协调性不足,这在分领域立法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为此,应基于上述各领域立法的相对独立性和紧密关联,加强其相互协调。例如,在财税法体系、金融法体系、竞争法体系内部的各类制度之间,都应加强立法协调
参见王先林:《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与竞争法体系的协调与衔接》,载《中国市场监管研究》2017年第12期,第28-31页。
;同时,还要关注财税法与金融法、产业法与竞争法等各大领域之间的立法协调,以全面提升整体经济法体系的调整合力。
此外,经济法各领域的立法都要考虑价格、信息、风险等共通问题,由此也有助于增强各类立法的协调性。例如,财税法、金融法、竞争法、消费者保护法等重要领域的立法,都涉及价格因素或价格条款,通过加强价格调控和价格监管制度的协调,有助于提升上述各领域立法的协调性。又如,信息制度、风险制度與经济法的调整目标、调整手段直接相关,普遍确立信息公开与信息安全、风险防控等方面的制度,同样有助于增强相关立法的协调性。
总之,分领域的分散立法路径,一直深受国家立法机关重视,学界亦有较高认同度,其在经济法的各类立法路径中将长期占据基础地位。只有优化上述各个重要领域的立法,才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统合立法,进而推进法典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既需要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及时回应,又需要相关领域的立法及时调整。分领域的分散立法作为推进集中立法的前提和基础,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是经济法立法理论或法治理论研究的重点,对于深化经济法运行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二)分行业的分散立法
分行业的分散立法,主要是针对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进行单独立法。基于相关行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国家需要对其进行特别规制和相应调控,由此需要分别进行重点立法。由于这些行业的立法分别涉及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因而会成为经济法体系中产业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例如,国家针对交通运输业,已制定《铁路法》《公路法》《民用航空法》等重要法律;针对信息产业,已制定《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重要法律
从信息、数据要素以及相关市场监管的角度,特别是基于经济规制的逻辑,这些信息立法被归入经济法;基于信息权保护和信息规制的角度,也可将其归入信息法。参见张守文:《信息权保护的信息法路径》,载《东方法学》2022年第4期,第50-62页。,并积极推进电信法的立法;针对能源行业,已制定《电力法》《煤炭法》等重要法律,但还需加快开展石油、天然气方面的系统立法,目前正在制定更上位的能源法;针对房地产业,已制定《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建筑法》等重要法律。上述各行业的立法都与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紧密关联。又如,农业是我国的基础产业,涉及粮食安全和“三农问题”的解决,对国计民生影响巨大,国家着力推动的农业现代化、城镇化、乡村振兴战略,尤其需要经济法的促进和保障,相应的立法包括《农业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业机械化促进法》《乡村振兴促进法》等,其中涉及的“促进型”规范等,都具有突出的经济法特色。针对上述行业展开的分散立法,主要采取单行法的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涉及国计民生的多个行业中,有些还涉及自然垄断、国有企业、反垄断等方面的特殊问题
参见盛杰民:《中国反垄断的立法重点》,载《中国发展观察》2006年第6期,第7-9页;鲁篱:《公用企业垄断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第65-73页。,需要从相关行业和企业的公共性、公益性等视角考虑对其实施市场规制,并完善相应的经濟法立法。
例如,铁路、邮政、电信、电力等涉及自然垄断的相关行业,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公益性,需要对其管理体制、市场准入、从业资格等方面实施特别规制,以加强对消费者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特别保护,对此需要在专门立法中作出规定,并由专门机构实施监管。
对自然垄断行业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双重规制模式的探讨,参见张占江、徐士英:《自然垄断行业反垄断规制模式构建》,载《比较法研究》2010年第3期,第38-53页。其中,涉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平竞争等突出问题,对上述重要关系的调整或相关问题的解决,显然超出了民商法的调整目标和功能。同时,由于政府部门或相关机构的特别规制属于经济规制,而不是行政管理,体现经济法的法治逻辑,因而这些行业立法被归入了经济法而不是行政法。
各个重要行业的大量单行法及其分别调整,与民法领域主要通过一部《民法典》来进行基础调整不同。经济法领域对多个行业的分别立法,在整体上会体现出更大的复杂性、差异性,由此可能影响相关行业发展的公平性和行业立法的协调性,这是此类立法的局限。与此相关,即使是“相对集中”的统合立法,也难以实现对各个行业的全面集中统一,因为每个具体行业的法律定位、所要解决的问题、所要体现的具体法治逻辑等都各不相同。
尽管上述行业的立法存在差异性,也不能由此片面地否定其相互之间的关联性,而恰恰应基于其诸多方面的共性来理解和推进相关立法,否则,就无法将其统一归类于经济法。事实上,前面对各类立法差异性的讨论,已涉及相关共性问题,由此有助于理解和揭示各类行业立法的内在规律。
总之,分行业的分散立法与相关行业的重要性、特殊性相关,这些立法构成了经济法体系中产业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相关产业连接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因而在某个行业立法以及包含多个行业的产业立法中,会涉及宏观调控法规范和市场规制法规范,同时,也会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共性问题,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保障相关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推动相关行业或产业健康发展。由于行业、行业立法都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差异性,此类立法不会因统合立法而消失,反而会长期发挥重要作用。
四、相互协调的多元立法路径
前面着重探讨了经济法各类立法路径的选择问题,通过对集中立法路径和分散立法路径的分别解析,可以发现,选择不同路径皆有一定的必要性、合理性,应基于其相互之间的紧密关联,确立相互协调的多元立法路径。其中,分散立法的路径具有更为基础的地位,国家立法机关正是通过大量推进分领域、分行业的分散立法,体现对相关经济政策的法律化,以及对相关重要行业的特别规制,这些立法更能及时回应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但因其相对分散,在各类制度之间的协调性、统一性方面存在不足。集中立法的路径,则有助于克服上述不足,通过持续的分阶段、分层级、分领域统合立法,能够提升相关法律制度的协调性和立法层级,从而有助于为更高层次上的法典编纂奠定基础。
经济法尚不具备法典化的条件,但应当积极促进自身体系的优化升级,以子部门法典化为路径推进法典化进程。参见薛克鹏:《法典化背景下的经济法体系构造——兼论经济法的法典化》,载《北方法学》2016年第5期,第107-116页。但从统合立法到制定或编纂法典,立法难度不断加大,同时,其回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及时性也会相应下降,这是集中立法路径的不足。据此,可对上述几类可选择的立法路径概括如下:
上表中的集中立法与分散立法两大路径,侧重于解决不同的立法问题,对其认识和选择不能仅执一端,而应兼顾两类立法路径的共性与个性,实现两者的有机协调。
有学者认为,应做好对既有经济单行法的评估,推进《经济法通则》的制定与各经济法板块基本法创制之间的“双重并进”。参见商红明:《我国〈经济法通则〉 研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载《财经法学》2020年第1期,第35-52页。尤其应当对各类路径扬长避短,将适度集中的立法与分领域、分行业的单行立法结合起来,从而形成相互协调的多元立法路径,这是当前更切合实际的选择。基于经济法调整对象复杂、立法类型多样的特点,选择相互协调的多元立法路径,而不是某种单一的路径,更能有效回应经济社会发展对法治发展的现实需要。
据此,基于相关领域、行业的经济法立法的共性,以及提升立法层级、增强立法协调性的需要,应持续推进统合立法,从而为更长远的法典编纂奠定基础。同时,基于各行业、领域立法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应继续在具体领域、行业加强立法,从而形成更有针对性地解决各类具体问题的单行法体系,为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提供更有效的法律保障。
上述两类立法路径,不是相互割裂、非此即彼的,而是紧密关联的,在纵向和横向上应加强其相互协调。其中,集中立法路径要以分散立法路径为基础,分散立法中涉及的共性问题,需要统一协调的,则应通过集中立法路径制定更高层次的共通性立法。此外,在推进分领域、分行业立法的过程中,更需要加强各领域、各行业之间的立法协调,提升相关立法的协调性、综合性、系统性,保障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依法实施。
通过上述相互协调的多元立法路径,优化经济法制度的有效供给,有助于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促进经济和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有助于在法治框架下,充分运用规制性手段,实现经济性目标,从而实现目标与手段的有机统一,全面保障和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五、结论
对于经济法的立法路径,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存在诸多不同认识,而其具体路径如何选择,事关经济法治的未来发展,因而应基于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审慎研判,这对于巩固经济法大厦的根基,优化整体法律系统的运行效果,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实现多领域的高质量发展,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基于对经济法集中立法路径和分散立法路径各自利弊得失的分析,可以认为,仅采用任何一种具体路径都是不够的。为了有效回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加强经济法的制度建设,提升经济法治水平,应选择相互协调的多元立法路径,将适度集中的统合立法与分领域、分行业的单行立法结合起来,做到各取所长、
激励相容,这是更为可行的现实选择。
经济法的立法路径选择,是经济法的立法理论、法治理论乃至整体运行理论的重要问题,与经济法的本体论、价值论、规范论、范畴论等亦存在紧密关联,因而学界还可以从多种不同理论维度,进一步对其展开深入研究,这更有助于为经济法的各类立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并为其他相关部门法的立法提供借鉴,进一步推进经济法学乃至整体法学研究的深化。
Legislative Path Selection of the Economic Law
ZHANG Shouwen
(Law School,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of construction of rule by law, how to choose the legislative path of economic law is related to the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overall process of rule by law. The legislative path of economic law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The one is centralized legislative path (including codification path and unified legislative path), and the other one is decentralized legislative path (including separate legislative path by field and industry), both of which have their necessity, rationality, and limitations. Based on the needs and possibilities of Chinas economic law legislation, at present, we should consider the advantages of various paths, organically combine unified legislation with separate legislation, and form a coordinated pluralistic legislative path.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special legislation or separate legislation based on the particu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each specific field and industry. Also,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integrated legislation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level of legislation and enhance the coordination and systematization of legislation, so as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overall economic law legislation and achieve its diversified adjustment goals. The legislative path selection of economic law not only involves the legislative theory, rule of law theory or operation theory of economic law, but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ntology, value theory, normative theory and category theory of the economic law, and its indepth study is conducive to providing important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economic law legislation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law research.
Key words: economic law; legislative path; codification; unified legislation; decentralized legislation
本文責任编辑:邵海
文章编号:1001-2397(2023)01-0118-14
收稿日期:2022-10-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税收立法的核心价值及其体系化研究”(19VHJ008)
作者简介:
张守文(1966),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①相关领域法典化的较早讨论,参见吴汉东:《国际化、现代化与法典化: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道路》,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3期,第73-79页;江必新:《迈向统一的行政基本法》,载《清华法学》2012年第5期,第101-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