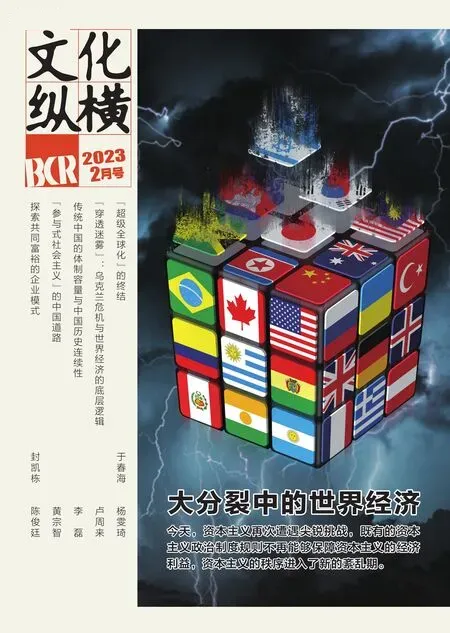“参与式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
黄宗智
一、问题与定义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民主主义”的理解多局限于西方式,尤其是英美式的“选举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这种民主基于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1]特别突出私人自由,并强烈倾向于将其他可能的民主形式排除在“民主”范畴之外。本文论证,我们需要澄清另一种形式的民主,这种民主可称作中国革命的“民众参与式民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有一定程度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但绝对没有达到西方那样高度独立化的分权程度,也没有同等的民众选举制度。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说是凌驾于那些三分机构之上的一个总揽大权的实体,它是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中“集中”的一面,是凌驾于西方式分立的三权之上的最高集中机构。正是这集中的一面,在西方许多观察者看来,乃是一个纯粹“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全能主义”(totalism)甚至“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体系,完全不可与西式民主相提并论。
最近十多年,这种将中国妖魔化为“极权主义”模式的意识形态在美国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原因在于,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呈现出社会分配越来越不公平的趋势。根据皮凯蒂的研究,如今占美国人口50%的下层群体只占有全国财富的3%,而最富裕的1%的群体却占有全国财富的40%。[2]正如皮凯蒂所述,广泛认同新兴极右民粹主义的主要是那些失去了中产阶级生活水平的中下层人员,他们认为自身的贫穷是由于大量有色人种渗透美国社会而攫取了自己的工作所致,也是因为美国企业将许多原来属于自己的工作大规模“外包”给了非西方的第三世界劳工。[3]这是美国日益强烈的反有色人种和反华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兴起的根本原因。[4]
要真正认识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我们不能仅凭借“威权主义”“全能主义”或 “极权主义”等单一化的范畴,而必须看到它的另一现代历史传统——“参与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正是中国的民众参与传统,才能协助我们真正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统治实质性的另一面,并由此看到另一种 “民主”的可能。
一如官方的词语“民主集中制”所表明,“参与式民主”的传统[5]和共产党领导的集中的政治传统,应该被视作一个二元并存互动(dyadic)的传统,区别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either/or dualism)。有的人会将“民主集中”认识为一个先民主(如民主讨论)、后集中(决策后无条件地服从)的(对立)二元,我则将这两者视为一个“中国思维”型的并存互动合一体,讲究的是两者之间的平衡,而不是一先二后。[6]我们可以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和改革时期的历史中,看到“民主”与“集中”双维的并存、互动、张力与合一,也可以看到两者失衡的现象。若不顾这种双维互动的传统,便不可能理解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实质和真髓,更不可能看到其具有前瞻性的未来可能。
二、中国革命史中的参与式民主传统
有的人会将“民主集中”认识为一个先民主、后集中的(对立)二元,我则将这两者视为一个“中国思维”型的并存互动合一体,讲究的是两者之间的平衡。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参与式民主最突出的实例之一,就是抗战时期民众参与革命的实际。在被国民党军队围剿而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入“长征”的转移和革命的低谷之后,中国共产党面对敌我双方火力相去较远的国民党和日本军队,竟还能在边远地区建立起19个成规模的解放区。到抗战结束时,这些解放区已经涵盖了约1.2亿的人口,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以上。显然,这不可能是仅凭自上而下的“控制”就能得到的成绩。抗战后的中国共产党,其实已经确立了足可与拥有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抗衡,并在其后获得最终胜利的基础。其中的关键因素正在于,它在最困难的时期成功地动员了大规模民众的积极参与,获得了他们的支持。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至为重要的获胜因素之一就是民众积极参与的“人民战争”:能够高效动员民众参军,激发高昂的士气,在敌后用游击战打击对方,从民众获得精准情报,有效动员敌人所做不到的后勤,等等。
解放战争之后,共产党再次凭借解放军独特的士气和组织能力,以及国内大后方民众的积极支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与当时全球最先进、最强大的美国军队打成平手。在双方技术、火力、装备等方面存在强弱悬殊的情况下,在对方占有机动、制空、制海等压倒性优势之下,解放军竟从鸭绿江反攻到“三七线”,并在“三八线”形成与美方“拉锯”的局面,由此获得板门店谈判的结果,即以“三八线”为界来划分朝鲜与韩国。如果没有解放军从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就已建立的士气,以及民众参与和特殊组织的韧性,这样的结局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它是不可能仅凭由上而下的极权控制就能做到的。[7]
美国流行的右派论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简单划归为“极权主义”的范畴,将其视作几乎是基督教中与上帝对立的魔鬼似的建构,显然是经不起认真考验的误识。我们必须要直面历史事实,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的 “集中”一面之外,还有“人民战争”中的民众积极参与的另一面。只有同时结合这两者,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和理解中国革命在抗战、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中所遗留下来的传统。
三、当代历史中的偏误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和社会过分地简单化和浪漫化。在计划经济时期,共产党民主集中的特殊性质曾经出现过倾向于过分管控的严重偏颇,也出现过失控的动乱偏颇。前者可以在“大跃进”时期的天灾人祸中清楚看到,后者则体现在陷入动乱与暴动的“文化大革命”中。
回顾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三十年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各个不同的阶段。
首先,在初级合作社时期,党建与民众参与这两者实现了成功结合。一方面,“党建”固然是一个建立渗透全社会、号令一致的党组织的过程;另一方面,民众也积极参与了这一过程,尤其是在土地改革和初级合作社中。因此,它不仅是一个号令一致的组织,也是一个民主集中制下民众积极参与的组织,更是一个借助民众参与的党建过程。[8]
如果没有解放军从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就已建立的士气,以及民众参与和特殊组织的韧性,这样的结局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它是不可能仅凭由上而下的极权控制就能做到的。
但我们也要直面以下事实:后来过度威权化和极端化的“大跃进”,是由于中央采用了不切实际的“越大越好”的基本战略,包括计划经济的确立与贯彻在内,都陷入了以管控为主导的治理和思维陷阱,将不符合实际的虚构目标强加于人民,犯了试图凭借组织意志来推动“大跃进”超前发展这一属于臆想的错误,其结果是使中国的经济和治理都陷入了灾难性的危机之中。
再后来,农村组织又基本返回到初级合作社的民众参与式民主,将最基本的组织和所有单位再次设定为基于自然村(区别于行政村)的“小组”,终结了超大的人民公社及其排除分户生产和建立大食堂等极端组织化、命令化的偏颇。然而,中央仍然保留了统一领导和“全国一盘棋”的计划经济组织,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壮大了严密管控人民(社会)与经济的体系。这一政治体系偏重由上而下的计划远超过由下而上的积极参与,官僚主义管控因此成为整个体系中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正如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最近明确指出的,官僚主义带有严重的脱离实际的倾向,重形式而不重实质,带有强烈的“推卸责任”“层层加码”“彰显权威”“化简为繁”“设置不必要的关卡”“媚上欺下”等诸多恶劣的倾向。[9]“大跃进”乃是当代历史中一个鲜明的实例。这种官僚主义问题特别需要民众积极参与的“民主”来加以遏制、纠正与平衡。
正是由于官僚主义化的过分管控,才促使毛泽东做出了过度激烈的反应,即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决策。他试图通过动员民众的积极性来克服官僚脱离实际和过分管控的弊端,但结果是,“文革”很快导致了无政府主义的偏颇和混乱,造成众多严重的失误,包括一段时期中较为普遍的暴力化行为。对被认作“阶级敌人”者进行过激打击,使许多无辜人士遭受粗暴行为甚至残酷虐待。从本文的角度来观察,“文化大革命”犯的乃是与“大跃进”相似却又相反的错误,它从过分由上而下的官僚主义指令和管控的极端,走到了过分无政府型动乱的另一极端。
这一政治体系偏重由上而下的计划远超过由下而上的积极参与,官僚主义管控因此成为整个体系中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至为重要的获胜因素之一就是民众积极参与的“人民战争”
这里,我们需要将前文所述的“积极参与”区别于另一种不同的民众参与,即共产党及其政府体系历来不少使用的、动员民众来协助“整党”“清党”的方法和传统。后者的目的主要是借助群众参与来揪出党和官僚体系内部的腐败分子,或借之来对党和机关进行整风。本文强调的不是那样由上而下的“群众路线”,而是民众自愿和积极的参与,并提倡将这种参与设定为关乎全民的战略性决策所不可或缺的条件。也就是说,通过民主与集中的结合与平衡互动,来防御高度集中的共产党及其政府体系中可能出现的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偏颇和失误。
对于今天的中国农村来说,仍然需要警惕一个问题。国家从2006年开始不再从农村提取税费,转向通过国家财政拨款来协助乡村的现代化,这虽然是一个良好的转变,但伴随国家拨款而来的,却是过度集权下乡村治理官僚主义化、形式主义化的严重弊端。[10]这一问题不是通过科层制化就能解决的。取鉴于历史,最好的办法不是进一步的形式化、程序化或数据化,而是名副其实的民众自愿的积极参与和支持。集中与民主参与的互动、结合与平衡,才是防御集权可能导致的失误的最佳方案。
四、改革中的民众参与
在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吸取了“文革”的教训,重新建立了新型的、由上而下与由下而上相结合的、一定程度上是去官僚主义化统治的民众参与。
(一)民众的新型“权利”
首先是“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民的参与式自主。承包制的广泛推行,意味着许多农民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计划经济统治之后,首次获得了各种各样的自主权利,尤其是生产和销售抉择方面的自主权。之后,他们又逐步获得了自由进入城市打工的流动自主权。这产生的结果是农业经济的大规模市场化和农民就业的大规模自由化。
最好的办法不是进一步的形式化、程序化或数据化,而是名副其实的民众自愿的积极参与和支持。集中与民主参与的互动、结合与平衡,才是防御集权可能导致的失误的最佳方案。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农民获得了生产和销售抉择方面的自主权
固然,承包制也有诸多限制,譬如粮农仍然受到诸多命令型的约束,必须要在国家保护“粮食安全”的大战略下进行生产,其自由抉择有一定限制。即便如此,仍然有众多的农民首次获得了可以自主种植、自主生产和自由销售的权利。其中一个特别突出的结果是推动了高附加值的“新农业革命”,如1、3、5亩地的拱棚蔬菜和数亩地的种养相结合的新型小农农场等形式。如今,这类新农业从业者已经达到大约1亿人的总数,相当于务农人员总数中的三分之一,而他们所生产的产量则达到了农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二。[11]
此外,是巨大的农民工浪潮,这一群体的规模如今已经达到将近3亿人。其中有“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他们选择在居住地从事非农就业,共约1.2亿人;[12]再则是“离土亦离乡”的外出打工农民工,共约1.7亿人。[13]固然,后者目前仍然仅有一种“二等身份”,没有正规工人的医疗和社会保障权利,其子女也没有在父母工作所在地上学的权利,属于一种“非正规”的就业。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自从1958年确立城乡户籍身份壁垒以来,农民首次获得可以自由进城打工的“权利”。[14]总体来说,农村的改革乃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真正赋权赋能性的民众积极参与式的改革,虽然距离真正消除“三大差别”还有一定的差距。
同时,还有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新型“中产阶级”的兴起。这一群体伴随城市企业的兴起和教育体系的大规模扩张而来,其数量如今已经达到3亿人。[15]这是一个与全球现代化大城市的中产阶级具有一定相似性的人群。在生活方式上,他们有房有车,收入和消费也已达到欧盟的中产阶级水平,可以与全球的中产阶级相提并论。尽管在人际关系、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上,中国的中产阶级仍然保留着许多深层次的独特特征,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在生活习惯还是人生观、价值观上,他们都与全球的中产阶级有一定的共同点,这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似的一个极其重大的变化。
(二)官僚上下层以及官僚与人民间的关系
与上述演变一起而来的,是将根据地时期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发挥为普遍实施一种上下级“发包与承包”机制的做法。
首先是中央和地方的“内包”关系:允许地方在中央设定的发展指标下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并凭借“官场”的竞争来激发地方官员们的积极性,促使他们为了自己的仕途而向属地企业伸出“帮助之手”,来获得有助于自身晋升的政绩。
同时,又凭借市场的运作规律来限制和淘汰没有竞争力的工程,包括地方政府策划的“形象工程”。[16]其中,一个关键的措施在于,中央将巨大规模的土地及其所附带的巨大资本,逐步发包给地方政府,给予其财源并激发其对属地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从而成功地推动了划时代的地方经济发展。[17]
在依赖行政“外包”的制度下,由官方提供“项目”资源来唤起各种人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就激发了大量由下而上的能动性、竞争性甚至创新性。
此外,在依赖行政“外包”的制度下,由官方提供“项目”资源来唤起各种人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就激发了大量由下而上的、为争得“国家”提供的财政资助而产生的能动性、竞争性甚至创新性。
以上几项主要的新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动力,成功推进了中国划时代的经济发展,促使中国行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的经济体。[19]虽然在人均收入的层面,中国仍然处于全球的中等水平,尚未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五、中国式的未来愿景:“参与式社会主义”
在上述当代中国的演变过程中,我们看不到西方式的选举型民主,也看不到完全的三权分立型民主,以及西方那样高度的私人自由权利;但能够极其清晰地看到一种新型的民众参与,它虽然没有西方式民主的特征,但也绝对不可因此被简单地划归为、被西方反共及右派民粹意见丑恶化为单一的“极权”压迫性制度。
相比计划经济时期,改革首先赋予了广大农村人民前所未有的能动性和自主性,使得许多小农户能获得生产的自主性,以及在市场上自主销售和营利的权利。伴之而来的是高附加值“新农业革命”的兴起,这是伴随中国人民食物转型——粮食∶蔬菜∶肉食结构从旧式的8∶1∶1转化为4∶3∶3的比例——而来的变化。从事“劳动与资本双密集”新农业的小农户,在市场参与度和农业收入层面要显著地高于过去的旧式粮农或一般旧式农民。[20]
其次则是3亿“农民工”阶层的兴起。虽然在户籍身份、福利和收入层面他们仍然是一种次等的“非正规”人员,但毫无疑问,相比计划经济时期,他们享有了前所未见的自主能动性,参与了改革后的市场经济和城市化大演变。未来的方向,应该是逐步迈向消除城乡之间、农民和市民之间的差别。
在最近二十年中,改革还导致了规模巨大的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包括中小型私营企业主及其白领职员,也包括众多新型专业人士。这一阶级在行为方式和追求上,乃至于在价值观层面都与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较为相似,虽然也有诸多源自中国文化和政治的不同。
最后,中国于2015年启动的“脱贫攻坚”工程,大规模动员基层干部和党员深入农村,协助底层贫民脱贫,到2021年宣布成功结束,总共协助将近一亿(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这无疑是获得相关民众支持的一项工程。
往前展望,由于最近二十年来的变化,也由于中国共产党一再申明的“社会主义”理念,以及党章和宪法一再重复申明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主导性目标,更由于近几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张,中国颇有可能达到比西方还要高的分配与社会公平程度。
它与西方的选举型民主、三权分立型民主以及高度个人自由化型民主不同,将更多呈现为一种中国式的、可以称作“参与式社会主义”的民主。
这一切不是要无视目前仍然存在的巨大的阶层差别和庞大的管控型官僚体系,而是要根据最近几十年的改革动向,设想一种中国式的前瞻愿景。它与西方的选举型民主、三权分立型民主以及高度个人自由化型民主不同,将更多呈现为一种中国式的、可以称作“参与式社会主义”的民主。它将较少采用选举制度,带有较低度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以及相对较低度的私人自由,但它也很可能将会具有比如今更高程度的民众参与和社会公平。
倘若如此,中国共产党将是一个越来越与民众参与式民主相结合、相平衡的治理与领导组织。在共产党的民主集中二元性实质之中,其命令型统治的一面将有可能会越来越倾向于转变为更符合民望的民众参与式统治,真正起到更高度的“领导”而非依靠指令的模式。在私人的自由权利方面,中国也许将会长期相对低于西方,尤其是英美式自由主义国家;但是在社会公平方面,中国应该能做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公允、更平衡的分配,也能更高程度地平衡好国家的集中统治与社会积极参与的民主。也就是说,创建一个真正值得被称作“参与式社会主义”的中国式民主模式。
六、中西“参与式社会主义”之异同
最近十年来,皮凯蒂关于西方国家不平等的研究以及据之号召的“参与式社会主义”(participatory socialism)改革方案,在全球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反响。他的重量级学术著作《21世纪资本论》,足有700多页厚,却已经卖到了200万册,还启发了全球100多个小组的后续研究。将上述中国实际和改革愿想与皮凯蒂提出的西方改革方案进行简单比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分别澄清两者的意涵,它们之间既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也存在着深层次的不同。
在共产党的民主集中二元性实质之中,其命令型统治的一面将有可能会越来越倾向于转变为更符合民望的民众参与式统治,真正起到更高度的“领导”而非依靠指令的模式。

中国为促进社会公平,已经在做的方案是进行较大规模的“扶贫”
一个重要的相通点是,皮凯蒂提出的“参与式社会主义”,是从德国和瑞典的企业主(资本家)与企业职工共同决策制度(co-determination)出发的提议。[21]它目前在中国尚未被实施,却是一个适用于中国的愿想,其关键在于建立一个具有实质性权力、能代表企业职工的工会,真正做到由职工与资本家分享企业决策的实际权力。而在2018年,中国已经提出要让现有社会 “群团”——不仅包括工会,还包括妇联、共青团等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群团组织——在未来能起到更实际和更强大的作用,通过他们的参与来推动向“社会主义”理想愿景的发展。[22]若能迈出这一步,中国将会更加名副其实地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能更加稳定地平衡集中与民主之间的关系。
正如皮凯蒂所指出的,在西方的企业中,长期为一个企业投入劳动的职工们对企业的认识和企业命运的认同,并不一定会逊于企业的资本掌控者,相比那些仅仅为了谋求某企业的股票增值而购买公司股份的投资者来说尤其如此。德国和瑞典成功的经济实例已经说明,参与式(部分)社会主义企业的绩效和生命力并不逊于完全资本主义型的企业。这种模式的经验无疑能对中国企业有所启示,值得中国认真考虑。[23]
皮凯蒂所提出的西方改革方案的核心设想是,围绕累进税收,特别是针对最富裕的那1%的人士的“财富”遗产税进行改革。他指出,一位突出的企业家在三四十岁创业之后,一般能够掌控该企业长达四五十年。但实际上,时间长了,他不一定还会做出最好的决策,而且他也已经获得足够的回报。皮凯蒂指出,在“二战”后和20世纪80年代之前,美国对巨富人士征收的财富税率曾经高达70%。他倡议,社会应该将这类财富税的一定比例,用于为每个25岁的公民提供一笔20万美元的资金,供他们进行专业技能进修、选择工作(使其不必像目前这样为了紧迫的生存压力而接纳最低等的工作),乃至购买住房。[24]但中国是一个才刚刚开始建立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国家,尚未建立起遗产继承税的体系,短期内不可能实现皮凯蒂那样的设想。中国目前已经在做的方案是进行较大规模的“扶贫”,以及由政府提供的逐步扩大的正规社会保障和福利。通过对最富裕的1%人士征收(针对收入的)累进税及(针对财富的)遗产税来为与社会公平相关的措施融资,无疑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进路。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就用来估算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而言,德国(31.9)和瑞典(30.0)目前相对比较均衡,美国(41.4)和中国(38.5,2018年)[25]则相对较高。显然,在这方面中美都还有较长的路要走。若以“财富”而不是年收入为标准来估算,那么最高的1%的群体和其余的群体之间的差值无疑还要更高,虽然这方面的数据目前仍然较为模糊、不够精准。
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明文将建立社会主义和追求“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设定为最高目标。与西方相比,未来中国对社会公平的追求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具体方案也会与皮凯蒂从西方历史现实出发的改革倡议有一定的不同。
与西方相比,未来中国对社会公平的追求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具体方案也会与皮凯蒂从西方历史现实出发的改革倡议有一定的不同。
自改革以来,中国已经制定了结合“社会主义”和 “市场经济”,以及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两者并存的大框架。这一大框架指向的是,让企业建立资本家和工会共同决策的体系,继续平衡不同阶层在收入和财富上的不均,以及稳步迈向动员“最大多数人民”为了自身“根本利益”而建设中国式的“参与式社会主义”,以此来平衡集中与民主这两个维度。这应该是再合理不过的发展道路和方向。
注释:
[1] 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与西方的三权分立的不同,参见曹正汉:《中央、地方与社会:中国治理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载《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
[2] Thomas Piketty,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3] [23] Thomas Piketty,“Thomas Piketty Explains Why the World is Ripe for‘Participatory Socialism’,”Fast Company, March 14, 2020.
[4] 我们需要将此股新潮流区别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之后兴起的右派极端反共意识形态浪潮。
[5] “参与式民主”当然与“人民”理念紧密相关。徐俊忠对后者的含义与演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参见徐俊忠:《何谓“人民”——历史的角色》,载《经济导刊》2022年第7期。
[6] 黄宗智:《从二元对立到二元合一:建立新型的实践政治经济学》,载《开放时代》2022年第4期。
[7] Philip C. C. Huang,“From the Third Sphere of Minimalist Governance to the Third Sphere of Party-People Co-Participation,”Rural China, Vol. 19, No. 1, 2022, pp. 1~30.
[8] 高原:《现代中国的乡村发展:微观案例和宏观变迁》,中国农业出版社2018年版。
[9] 《警惕公权力运行中的“内卷”现象,不能被裹挟 》,澎湃新闻,2020年12月18日。
[10] 桂华:《乡村治理中的体制性空转——基层形式主义的成因与破解》,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11] 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1980—2010)——一个历史和比较的视野》,载《开放时代》2016年第2期;黄宗智:《中国的新型小农经济:实践与理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12] [13] 智研咨询:《2021年中国农民工总量、外出农民工规模及农民工平均年龄分析[图]》,网易,2022年6月21日。
[14] 当然,其确立经过了一定的过程,从遭遇各种各样的阻碍,乃至于初期仅得到半正式的认可,而后逐步达到如今自由选择的阶段。
[15] 在众多不同的相关研究中,一项比较严谨的研究是使用欧盟的中产阶级测量标准:2013年每日人均收入达到36美元以上,120美元以下,将户主以此数的100%估算,户主之外的成年人以其50%估算,14岁以下儿童以其40%估算。据此,该研究得出2013年中国中产阶级的总数为2.54亿人,占中国总人口的19%(2002年只有0.125亿人,仅占总人口的2.4%),参见Bjorn Gustafsson, Xiuna Yang, and Terry Sicular,“Catching Up with the West: Chinese Pathways to the Global Middle Class,”The China Journal, Vol. 84, 2020, pp. 102~127。其后,同一组研究者又根据相似的方法,将估算延伸到2018年,划分下线为37.5美元,上线为125美元,得出当年中国中产阶级的总人数为3.44亿人,占中国总人口的25%,参见Terry Sicular, Xiuna Yang, and Bjorn Gustaffson,“The Rise of China’s Global Middle Class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IZA Discussion Paper, No. 14531, 2022, pp. 5~27。
[16] 周黎安:《如何认识中国?——对话黄宗智先生》,载《开放时代》2019年第3期。
[17] [18] 黄宗智:《从土地的资本化到资本的社会化:中国发展经验的新政治经济学》,载《东南学术》2021年第3期。
[19] 若以“购买力平价”(PPP)来估算,中国则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20] 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21] 德国的共同决策制度限于千人以上的企业。参见Thomas Piketty,Time for Socialism:Dispatches from a World on Fire, 2016-2021,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1;Thomas Piketty,“Transcript: Ezra Klein Interviews Thomas Piketty,”The New York Times, June 7, 2022;Philip C. C. Huang,“From the Third Sphere of Minimalist Governance to the Third Sphere of Party-People Co-Participation,”Rural China, Vol. 19, No. 1, 2022, pp. 1~30。
[22] 在中共中央2018年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第七部分对其有所论述。参见《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新华社,2018年3月21日。
[24] Thomas Piketty,“Transcript: Ezra Klein Interviews Thomas Piketty,”The New York Times,June 7, 2022.
[25]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33.2低点,攀升到2010年的43.7最高点,而后下降到2019年38.2。参见“Gini Index-China,”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I.POV.GINI?location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