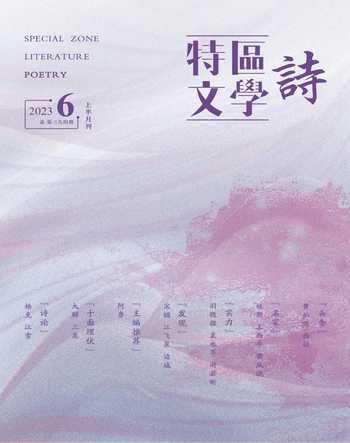“见微”的诗学
黄灿然的《洞背八年》这组诗,从写作时间看,是2014年至2022年。所谓“洞背八年”,指诗人在此期间,居住于深圳洞背村的八年生活。由此也不难揣测,这组诗中强烈的“潜自传”色彩。
《洞背八年》这个题目,会令人想到《黄灿然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中的“洞背集”,只不过在后者中,所收诗作仅包括“2014—2016”、也即在洞背村生活的最初两年的部分作品。而从《洞背八年》中,我们更可一窥“洞背八年”当中,黄灿然诗歌创作的实绩与概貌,甚至一些新的变化与倾向。
读这组诗,笔者最强烈的感受,是诗人从小处(小事物或小节)出发,既具体而微,又使诗意(意思、意味、意蕴)悠长深远的高超技艺,以及超越于技艺之上的诗人丰沛而神思凝聚一处的创造力和良好的身心状态。
笔者曾在别处论及《洞背集》的写作,“也许与诗人生活的变化以及所能触及的素材有关,更多关注微小的事物:蝴蝶、蟑螂、蚂蚁、苍蝇、蛾子、小狗、母鸡、壁虎、小树林、红薯藤……甚至绿道和水龙头,都成为诗人书写的题材。而从这些微小的事物中,也愈发可以看到,他的有着充分自觉的矜持、谦卑、温良与善意”(《综合的诗人及其所创造的——黄灿然诗歌创作论》,未刊稿)。这个判断,对于《洞背八年》中的多数诗作依然有效。在这组作品中,我们同样看到“鸡声、鸭声、狗声、/鸟声、虫声、蛙声”(《喧闹》),看到“嫩叶”“狗尾草”“小飞蛾”“白蝴蝶”(以上均为诗题)等“微”而不卑,反而相当“可观”(无论数量还是意蕴),甚至读来会令人一阵心动(甚或心惊)的小事物。
不过,本文以下想讨论的,不只是黄灿然“写了什么”的“什么”之“微”,更是“怎么写”的“怎么”之“微”(细微、精微、微妙)。其中,在黄灿然此前的诗中几乎未出现过的、因而也可认定为新的表征与倾向,尤其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以《给村口的银合欢》为例,在这首共有十行的自由体短诗中,埋伏着诸多押韵的“关节”,比如第二行开头的“便”与“遍”,第二行中间的“(路)旁”与第三行中间的“放(射)”,以及第二行结尾的“白花”与“白花花”。语音上的一致或相似,与语义上的关联而又差异(尤其作为名词的“白花”与作为形容词的“白花花”,以及第七行的问句“什么花?”与第八两行的感叹句“什么花!”),构成了饶有趣味,也别有意味的诗意空间。
继续看下去:在满树“白花花”的“白花”面前,“绿叶都隐退了,或被强烈对照得变浅黄了”。“白花”“绿叶”“浅黄”,堪称缤纷的色彩世界。而银合欢的白花,“满满地白,几乎是赤裸裸地白”,以至于“如果你们搬到某个山头,/ 那山头就会变成白头”。末行的“那山头”与倒数第二行最后的“山头”几乎不经意地构成顶针的修辞,同时,又与句末的“白头”构成三个同“尾”词的押韵。
这是诗人可望而不可期的幸运,抑或偶然为之的结果吗?还真不是。不信请看《瞬间》,“枣红色运动衣突然飘上来 / 晃了一下”固然有着不可言说的诗之神秘,但“绿色的农田”“远方的海天一片蓝”“枣红色的运动衣”的色彩对照,不也是鲜明的诗意之所在?《彩虹——给孙泽》中的诗句:“你拍了拍手臂,蚂蟥应声飞脱,/ 拖着一条弧形的美丽血线……”前一行最后的“脱”与后一行行首的“拖”的谐音,显然不是无意为之。
再看仅有七行的短诗《车过葵潭》:
一个、两个和更多
更像是山中湖的池塘,池塘邊
几十、几百、几千只白鸭子
弯着脖子在休息。一个
戴斗笠的农妇,用扁担挑着粪土
走在田埂上。一座、两座
和更多坟墓……
诗中第一行最后的“更多”与第二行起句的“更像”的“更”字之重复,以及第二行的“池塘”与一个逗号之隔的“池塘边”之间的顶针修辞,同样很难看作是诗人的随意为之。实际上,黄灿然对此有清醒的意识与认知。他说,“我认为自由诗是可以带格律的,或反过来说,格律诗是可以自由的”,并解释说:
“新诗之所以是新诗,是因为新语言有新语法。新语法有新节奏。如果要押韵,也不一定押在行尾,而是可以,甚至应该押在句尾。因为新诗是可以跨行的,一行诗可以有中间停顿,一行诗可以有几句(例如三五个词一个句号)或几个停顿(例如三五个词一个逗号);一句诗也可以有几行,甚至一首诗一句到底;一句一行以上的诗可以有一个或多个中间停顿、一个行尾停顿、一个句尾停顿;我们可以在所有这些停顿处押韵。”(李春俊:《新阶段:看山又不是山—诗人黄灿然访谈录》)
由于在现代诗中,句尾可能在行尾,也可能在行首,抑或行中,所以,押韵可能是在行尾实现,也可能在行首或行中实现。 “我们可以在所有这些停顿处押韵”,黄灿然不只这么说,实际上在写诗时也是这么做的。甚至,他的诗歌创作实践,比他所说的要走得更远——因为如前所述,他在诗中的押韵有时押的不是一个词语的末字之韵,而是首字的韵(如:更多、更像是),有点像排偶,却又并非排偶(因为排偶——按照王力先生的解释即“排列成偶”,需要两个并列的词语或短语的性质、形式相同,“更多”与“更像”两个词语虽然首字相同,也押韵,短语的性质与形式却不同)。同时,他还调动了顶针的修辞,以及语音与语义的相近与差异所带来的万花筒般散射的诗意网络节点与想象空间。此外,还调动了词语、诗句与诗形的相近与差异。比如上面所引的《车过葵潭》中,核心意象是池塘、白鸭子、农妇、田埂、坟墓,而构成这首诗之诗意空间的,除了这些意象,还有数量词(以至于这些数量词可以独立成行)。
第一行的“一个、两个和更多”与最后两行的“一座、两座 / 和更多”,形成鲜明的复沓效果和对照,两者的句式完全一样,所不同者只有量词单位(“个”与“座”),以及诗人有意为之的断行变化,以使诗的句式不至单调,外形也更好看(如果第六、七两行合并,末行就会显得过于长,过于臃肿,与这首诗内在的写意般的简洁相扞格)。而在第一行和最后两行的中间偏上位置,也即第三行,与“一”“两”“更多”又构成对照的,则是“几十、几百、几千”。于是,这三组数量词构成了巧妙的支撑与对照——中间这第三行量词的出现,将首尾两组本来显得平面化的量词呼应与对照起来,实现了极大的立体化。
如果说这是侧重于诗行的语音和诗形的视觉效果,那么,“池塘”(很可能是深碧色)与“白鸭子”、“白鸭子”与“戴斗笠的农妇”和“田埂”之间所产生的,则是语义层面的诗意之视觉差异。此外,首句的“池塘”(凹状)与末句的“坟墓”(凸状)也形成互补性的对照。更令人心惊的,是走在田埂上的“农妇”与不远处“一座、两座 / 和更多坟墓……”之间的对照,特别是“走”字,仿佛在暗示,她终会走向“一座、两座 / 和更多坟墓”中的某一座,更不用说她的斗笠与坟墓的形状正好一致,而“坟墓”后面的省略号,也更引人遐想。
于是我们看到,在“一个、两个和更多”与“一座、两座 / 和更多坟墓”这两组既有着相似数量,又有着形态差异的静物之间,安放着“几十、几百、几千只白鸭子”与“一个戴斗笠的农妇”两组同样既对照(一与多、人与禽)又有着某些相似性(都是可“动”的生物)的可“动”之物(人),因而在短短的七行诗里,貌似有着线条简约的水墨写意风格,实则关系复杂,相关的词语、词组与意象,在这些关系中达成微妙的平衡。
类似写法,在《洞背八年》中,还可举出很多。这些诗,从所写的事物来看极为常见,甚至算得上微末的物事(有时也包括人),从写法上看从小处入手,甚至从一些虚词切入,触点细微而敏锐,诗的写作和内在发展准确而微妙,最后呈现出的总体的技艺精微而令人感叹。《心想事成》中反复出现的“有”“当然”“刚好”;《复杂的天空》中云的复杂变化与云下之人的内心的复杂变化,最后却由于“更深刻的复杂变化”而变得“简单”的过程,都是如此,读来会令人回味再三。
在另一些诗中,黄灿然甚至不惜牺牲诗的一部分可读性(至少是好读性),来实现自己对语言的新挑战。比如《与书》:
早起的农妇与细藤蔓上沉重的瓜。
下午两点与昨天的云。还有雨点。
一只蜗牛,要多久才能爬过路面
与今天会不会有车经过把它压碎。
邻居的狗,凶叫但不凶而且很憨
与很多人很憨但很凶叫起来更凶。
大而傻的头和诡诈的嘴与少而稀
还有可能白吗的灰发和刻薄的唇。
八行形式感非常讲究的、齐整的诗,两行一节共分为四节。第一节读来没有任何障碍,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行的“与”前后各一个事物(农妇与瓜),第二行的“与”和第一行并不完全一致,而是在“云”之后,多了“雨点”,这样就打破了由于两行诗句式雷同而带来的单调之感。与第一节的通顺不同,第二节“与”字的前后两部分,很难连接起来读,甚至读的时候要有意省掉“与”字,才读得通。第三节中的“与”,也像扁担一样,挑着“邻居的狗……”和“很多人……”这前后两个句式相似而又对比鲜明的部分,不仅意味深长,而且堪称深刻。第四节再次变化,“与”字前后不再是各自一个部分,而是各自由“……和……”组成的两个部分(头和嘴,发和唇),其中,“大而傻的头”遥相对应着“少而稀……的灰发”,“诡诈的嘴”遥相对应着“刻薄的唇”,将两组词组的最后一个字连接,就成了“头—发”“嘴—唇”。此外,“少而稀 / 还有可能白吗的灰发”,其表达实在是有些“出格”,同时显得晦涩(多读几遍才会明晰)而令人感到新奇的。实际上,如果改成“少而稀 / (还有可能白吗)的灰发”,这句诗就好读得多,但因此而损失的,则是表达上的新奇感,以及诗行的齐整规则。回头去看这首诗的题目,同样显得晦涩的《与书》,其实际的意思则更像是“书写‘与”“论‘与”。将叙述的重心落在“与”这样一个显得抽象和无从把握的关系词上。诗中所写,至少部分重点,是在由“与”这个字所连接的关系上。
黄灿然曾说,他在《洞背集》之后所写的一些诗(主要指归入《苟活集》中的诗作),有意“反抗语言、叛逆语言”,“在与语言的关系上,不是维持微妙的平衡,而是带着某种火爆、摩擦、冲突”。通过《与书》等诗,我们也可得以窥见一斑。说这样的诗具有一定的“实验性”并不过分。对于诗人来说,“它也是一种需要,需要开拓自己的技术,磨炼自己的技艺”。(李春俊:《新阶段:看山又不是山 ——詩人黄灿然访谈录》)
《洞背八年》这组诗的最后一首,与总题同名。诗中有这样的诗句,“来时孤身,离开时各自带走 / 两本诗集和一个女人”(《洞背八年——别孙文波》)。带走的“一个女人”是谁?我们搁置不论。带走的“两本诗集”,据黄灿然在接受访谈时所说,是《洞背集》和《苟活集》。其中,“《洞背集》……是从《奇迹集》迁移过来的。《奇迹集》聚焦于一个恢复健康的中年诗人对他置身的香港这座现代城市的奇迹般的全新体验,而《洞背集》则是一个年过五十的诗人解除了工作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解除了现代城市的压力之后,对童年山村生活的重新体验……我基本上是沿用《奇迹集》的视角来写洞背村,只是题材完全不一样了……在《奇迹集》中,诗人以内心的纯真来发现城市的奇迹,而在《洞背集》中,洞背村以其自然环境唤起诗人内心的纯真”。这与我们阅读《洞背八年》这组诗作的感受也高度相合。《苟活集》则不同,“我感到自己对语言的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变。不想过于节制,不想特别注意分寸,不想操心是否语出自然,而是随机、即兴、放肆,甚至狂妄”。(李春俊:《新阶段:看山又不是山 ——诗人黄灿然访谈录》)对于黄灿然的这些自陈,回想一下《与书》《魔术》《狗尾草》等诗,即可理解。如果还读过黄灿然此种类型的其它一些诗作,体会当会更深。也由此,我们不难辨识出,《洞背八年》这组诗作,一多半可归入《洞背集》,一少半可归入《苟活集》。
其中,从诗歌形式来看,采用自由体诗的那些诗,大概率属于《洞背集》,而采用两行或三行一节,以非常整齐规则的行制展开的“格律诗”形式的诗,大概率属于《苟活集》。这两种体式并进的创作实践,在黄灿然三十多年的诗歌写作生涯中,也一直在或同时或先后交错地进行着。
由以上讨论,我们不难看出,《洞背八年》这组诗中明显透露出的“见微”或曰“触微”的新倾向,也即,从所写的题材来看,多是微小的物事(包括人);从诗艺的展开方式来看,黄灿然是从字、词、句的选择和安排,乃至从字里行间的诸多细微处着手,写出新花样、新面目的。前文曾提到,黄灿然这组诗作无论所写的对象,还是具体的写法,都是“微”而不卑的;相反,无论从其范围与数量,还是从其质量与深度来看,黄灿然都从微小的物事中开掘出了相当可观的诗歌意涵。
我们常说,“一叶知秋”“见微知著”。在黄灿然这里,“知著”是通过表面的“隐著”来实现的,具体说就是,并非通过隐去、抹除或取消那明显的、深刻的命题或话题,而是于“微”(细微、微小、幽微、微妙之处)中隐含(隐喻、蕴含)“著”(显著、宏大、深刻)的命意,以此方式,使读者有所感、有所“知”、有所触(动)。如果想到狗尾草所生活的“小世界”和“大自然”(《狗尾草》),想到小飞蛾所遭遇的或许是连它自己都不知道的死亡(《小飞蛾》),想到《车过葵潭》中“更多的坟墓”,想到《迷迭香》中“密集而带攻击性,/ 有着陶醉所包含的全部上升和沉沦”,想到《喧闹》中,“鸡声、鸭声、狗声、/ 鸟声、虫声、蛙声”之外,“还有窗外月光/ 巨大的无声”……自会明白,以上所论并非虚言。就此而言,可以说黄灿然通过“洞背八年”的生活与写作,愈发清晰了一种“见微”的诗学,至少是明晰了这样一种诗歌创作的倾向与方式。
宋宁刚,诗人、诗评者,哲学博士,西安财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